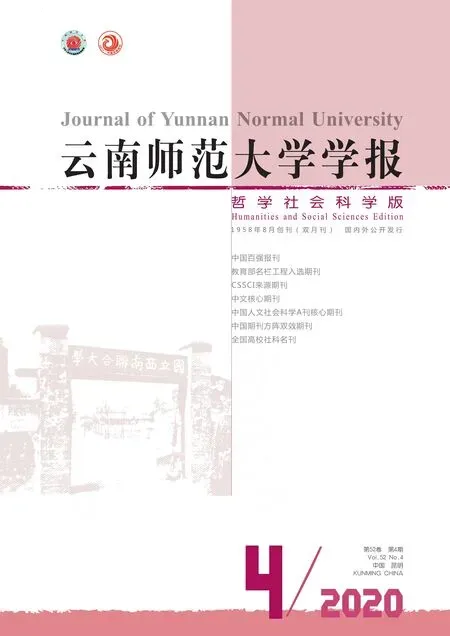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焦点与困境
——以对中国民族学会的考察为中心*
孙 喆, 许会娟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一、研究背景与学术史回顾
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华南、东南沿海等大片国土又相继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中国民族危机达到顶峰。开发西北和西南边疆、增强各族团结、强化民族国家建构、激发国人抗战斗志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和严峻使命。如时人所言:“夫边疆诸省,开发虽远,而蕴藏甚富。方或殊而同隶版图,俗或异而同为华胄。今日为长期抗战,固当益固各族之团结,而为建国大计,尤须策万世之远谋……所望有志之士,或潜心究边省之文物,或投笔奋四方之壮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凝各族为一家,纳边疆于同轨,进而收复已失之河山,完成抗建之大业。异日万里户庭,同跻郅治,不复有边疆内地之别。”(1)高长柱.边疆问题论文集·张群序[M].重庆:正中书局,1941:1.这一时期,学术界对边疆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并未因国民政府西迁而削弱,不但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势头,并且再次掀起了一个高潮。具体而言,这种时代特征体现在民族研究上,就是两大问题受到格外关注:
第一,国族整合和对“中华民族”观念的阐释。在团结抗战、救亡图存的话语体系下,国族整合和淡化民族观念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民族治理政策的出发点。同时,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也刺激和推动学术界对如何加强国家建构和民族凝聚力问题再做思考。在此背景下,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和阐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各领域学者对“中华民族”概念都作了新的表述,“中华民族”一词成为舆论宣传团结抗日的代表性词汇。1939年初,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先后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两篇文章,提出要慎用“中国本部”和“民族”这两个概念,认为前者是日本人缔造出来分化中国的,后者则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中华民族既不组织在血统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汉族文化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逐渐取长舍短融合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因此,在中华民族之内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也绝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信念,也是事实。(2)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N].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01-01;中华民族是一个[N].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2-13.“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出,对全面抗战时期的边疆和民族问题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对西南边疆民族的调查和研究。国民政府西迁后,西南地区因其政治地位的跃升而受到格外关注。西南各省民族众多,文化各异,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多样;由于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等原因,许多民族地区与内地隔膜很深。为了发挥西南地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作用,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力图从各个方面促进其开发和建设。各种资源空前集中的情形也给西南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在20世纪30年代较受冷遇的西南边疆和民族问题开始得到重视,“自国民政府有边疆政策以来,勿庸讳言的,其注视的重心,是在西北而不在西南,换言之,即只认蒙藏新疆为边疆而视西南各苗夷区域为内域”;然“自抗战以后政府西迁,西南边疆及西南边民的实况,始渐为执政诸公所明瞭,才深觉得这广大区域与复杂的宗族,实在不能不有特殊的治理方策和开发方案,实在应当和蒙古新疆作等量齐观,于是政府治边的范围乃始扩大,把西南的苗夷区域算作了边疆,把西南的苗夷人民认作了边民”(3)江应樑.请确定西南边疆政策[J].边政公论,1948,(1).。“西南成为今后抗战建国的重心,‘开发西南’‘发展西南’,不期然就成为全国人士一致的呼声了!”(4)王兴瑞.西康文物展览会[J].西南边疆,1939,(5).有人甚至直接提出“建国必自建设西南始”“抗战建国,固人人能言之,然言之非艰,行之维艰,国都移渝后,西南数省,遂为民族复兴地,是则建国必先建设西南明矣;”(5)邓汉祥.建国必自建设西南始[J].西南实业通讯,1940,(6).并认为“此民族觉悟之一大转机”(6)高长柱.边疆问题论文集·张群序[M].重庆:正中书局,1941:1.。而深入了解和把握当地的民族状况、树立和加强各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就成为建设和开发西南的重要前提。同时,辗转云集于西南地区的学者中包括相当数量的从事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人,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素材。这些不仅使西南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得到大力推动,也从客观上为民族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舞台,使其有了发展的机遇。由此,掀起西南边疆民族调查和研究的一个小高潮。
从当前学术界对全面抗战时期民族问题的研究来看,有学者从宏观上对民国时期民族研究的焦点问题作了梳理和总结,大体包括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和认同、中华民族复兴、民族国家和国族建构、民族地区的国家意识、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国界勘定等。这些问题可以说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但在全面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受现实状况、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等因素的影响,则突出表现为上文所提的两大问题。就这两个问题的学术史研究而言,怎样看待和评价“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是中国民族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和路径出发,对此问题进行阐述和解读,研究不断细化、深化、出新,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关于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建设、经济开发、文化教育、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观念认同等问题也已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概括而言,这些研究成果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和演变、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辩论、“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内涵及社会反响等均各有侧重地作了探讨。研究者基本承认,中华民族观念在全面抗战时期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中国最大的收获,也许不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是战争使得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不分地域、不分种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个利害与共、休戚相关的‘中华民族’”(7)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是一个[J].抗日战争研究,1992,(1).。而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开发与中华民族一体化理论的推行,客观上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及西南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从学理上而言,这两大焦点问题是互为表里、互为论证的关系,即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加强和完善中华民族一体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时,以这一理论的传播来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然而,如一些研究成果所表明的,这两个问题在当时还达不成上述的理想关系,中华民族观念在增强凝聚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内部之分歧、权力的斗争”(8)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J].中国近代史研究,2016,(4).。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主要体现在对“中华民族”和“民族”概念的理解上尚不一致,如较早时期顾颉刚和费孝通之间的辩论,费孝通从自己所掌握的理论及其在广西地区的民族调查实践出发,并不认同顾颉刚提出的“民族”和“种族”定义,提出:“若是我们的目的在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文化、语言、体质上没有混一的必要。若是我们的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标语式的新名词于时势并无裨益,“惟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9)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N].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5-01.虽然顾、费之争很快就结束了(10)费孝通后来提到没有继续辩论的原因时说:“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急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费孝通文集·第13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26~27.),但这一学术上的分歧是否就此消弭了?在西南地区从事调查和研究的民族学学者是如何围绕着这两个焦点问题开展工作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往的研究中,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考察并不够充分,而它们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为此,本文特意选择了一个以往受关注较少的专业从事民族研究的学术团体——中国民族学会作为考察对象,希望通过对其研究内容、发展轨迹的考察,对全面抗战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的状况和特点做进一步探寻、梳理和总结。(11)目前学术界涉及中国民族学会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李列.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1928~1949年)[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聂蒲生.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孟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1900~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朱映占.民国时期的西南边疆[D].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李会敏.中国民族学会研究(1934~1949)[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这些论著多以叙述其机构的发展或民族调查活动为主。本文则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加强对其学术史脉络的考察。
二、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民族学会及其学术活动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民族研究中,涌现出众多的学者、刊物和研究机构,正像有学者所形容的,“当时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学人、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受人注意的刊物,犹如群星灿烂。”(12)边众.论当前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中国民族学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团体。它成立于1934年12月,起因是蔡元培、凌纯声、徐益堂、刘咸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有感于“我国民族文化之复杂,殊有分工合作积极研究之必要”(13)徐益棠.七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J].西南边疆,1942,(15).,而国内大学设民族学课程者仅寥寥数校,且授课者大多为外国学者,于是发起成立此会。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徐益棠为理事会主席,孙本文等7人为理事,蔡元培等3人为监事,决议章程共计15条,会务4项:一是研究;二是调查及搜集;三是讲演及讨论;四是编行刊物。(14)徐益棠.七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J].西南边疆,1942,(15).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学会工作被迫停顿,一些会员撤至西南大后方。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时代要求相呼应,他们很快就以重庆、昆明、成都为基地,分头深入民族地区展开调查和研究工作,将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紧密结合起来。除自行前往民族地区考察外,他们还参加了自1938年以来,国民政府组织的各种民族调查活动,如1940年3月开始的对西南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的调查;同年5月针对傣族人口数量、分布区域等展开的调查等。1941年秋,各种条件成熟后,学会的复会工作开始提上日程。1942年10月,徐益棠代表民族学会向国民政府社会部呈递了《中国民族学会章程》《会务活动报告书》及团体概况等各项材料,正式恢复活动。
中国民族学会在成立之始,就明确提出以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这一宗旨与全面抗战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谋而合,加之西南特殊的多民族分布格局,使学会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学会成员对当时的民族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和研究。本文以其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西南边疆》为考察分析对象,将其关注的内容总结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
第一,少数民族族源问题。在当时学者看来,中国因历史悠久和土地广阔,以及地形和种族的复杂,自然形成了许多文化区域,有着许多不同的文化单位。“只是后来因为汉族文化的占了绝对优势,这些小民族,小区域的文化,都渐渐地被同化,被征服,或者也是被湮灭,或被忘却了”(15)楚图南.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的研究[J].西南边疆,1938,(1).,而这些“小民族”,“即少数的民族,但在国家民族和文化的构成上,却是一样的重要”(16)楚图南.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的研究·注二[J].西南边疆,1938,(1).。研究其族源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对于他们的极客观的研究和极正确的理解,不单是可以纠正了过去载籍上的许多错误,扫清种族间的许多的成见和误解,同时也当可以追溯出一部分中国文化的渊源和血缘”(17)楚图南.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的研究[J].西南边疆,1938,(1).。
第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历史渊源、社会制度、经济组织和形态等问题。其目的,一方面,“就学术研究上言,我们希望文化界人士,能多从这富有历史意味的社会制度及经济机构中,夺取到更广大的研究资料;就民族的大统一言,我们却又希望政府能早日对此种不适存在于现时代的社会经济组织,加以改进。”(18)江应樑.云南西部僰夷民族之经济社会[J].西南边疆,1938,(1).另一方面,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尝试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特殊性中找寻中国文化的共性。如江应梁通过对僰夷的家族组织与婚姻制度的研究发现,僰夷的宗法承嗣异于西南地区的很多其他民族,如嫡长子继承制度等全部仿之于汉人甚至更为严格,不论土司或民间,均可看出这种情形。土司及贵族的两性结合仪节,也与汉人社会无大的差别,但在下层中,则保留着一些较为原始的婚俗习惯,说明中原文化与西南边疆文化并非完全阻隔不通,而是存在着某些共通的地方,尤其是其社会上层,在很多方面与汉文化有所交融。岑家梧则在对花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颇为乐观地指出:“花苗历来处于恶劣环境之下,几经锻炼,使花苗有强健之体质,刻苦耐劳之习惯,既无特殊嗜好,又具精诚团结之精神,凡此种种,实为中华民族最健全,最优良之国民。际此抗战建国期间,吾人苟深切了解花苗之生活情况,进而改造花苗之经济生活,提高花苗教育水平,然后从而组织之,训练之,必能增加千万抗战到底之力量。”(19)岑家梧.云南嵩明县之花苗[J].西南边疆,1940,(8).试图从花苗质朴的遗俗中寻求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激励和鼓舞抗战斗志。
第三,少数民族教育和语言沟通问题。当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边疆为我版图之边疆,边民亦即我国民之一部。开化边民使与近代中原文化融为一体,以应付现局,实为刻不容缓之事”“开化边民,提高边民文化,其最重要的途径,无疑的是教育”;(20)陶云达.开化边民问题[J].西南边疆,1940,(10).而传达意志、推行政教的最有效工具,就是语言,因此,“非先实施语文教育不为功”(21)芮逸夫.西南民族语文教育刍议[J].西南边疆,1938,(2).。对于在数年努力之后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仍存在很深的文化隔阂这种状况,一些学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上。吴宗济提出:“这些民族的语言生活都各不相同,要使他们削足适履的都读商务的复兴教科书,或中华的新课程标准适用教科书(云南省立小学所用),究竟还有很多的隔阂。”(22)芮逸夫.西南民族语文教育刍议[J].西南边疆,1938,(2).陶云达亦认为,“我们只把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搬到边地,而未能因地制宜,致遭边民漠视。我们需要一种实验的边疆教育,就地取材,在当地社会日常生活中随时教授,参以新见解,新的生活方式,于不知觉中,逐渐推进,将原来的淘汰,用现代的代替。”(23)陶云达.开化边民问题[J].西南边疆,1940,(10).主张采取循序渐进、自然同化的教育方式,而不是削足适履式的快速同化。
总之,以上关于民族起源、民族社会形态、民族发展等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面抗战时期民族学领域学者们的关注重点,即如何以西南边疆民族为样本,对民族概念、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民族发展趋势等理论进行探讨和实践。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学会的研究大体上还是从学术立场出发,在认同和大力传播“中华民族”观念的同时,对“中华民族”框架内汉族与少数民族(或称边疆民族、边民)的关系问题持审慎、多元的态度。
三、学会发展遭遇的困境及原因
如上文所述,在全面抗战这一特殊时局下,以民族研究为宗旨的中国民族学会本应恰逢其时,蓬勃发展,但从实际情形来看,处境却颇多尴尬,从以下两个方面可略见一斑:
第一,学会会员数量不多,经费窘迫。学会于1934年创立时有会员33人,次年增至51人。1942年重建时会员降为33人,直至1946年战后才增至91人,如徐益堂在1942年总结学会成立七周年工作时所言:“中国民族学会成立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十二月,屈指计算,仅有九个年头,实足年龄,且只及七年零四个月。以言学术史上之地位,瞠乎后矣。此七龄之幼童,诞生于国难严重之际。自哺乳以至提携抱负,却已煞费苦心,而社会迄未加注意。”“同人呼号奔走,惨淡经营。至今日始稍获精神上之慰藉”。(24)徐益棠.七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J].西南边疆,1942,(15).学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的捐款,始终处于拮据状态。因此,学会能够在艰难的时局下坚持到战后并有所发展,固然得益于特殊时期社会对边疆和民族问题的强烈关注,与组织者的坚持精神和苦心经营也是分不开的。
第二,创刊工作推进不顺。中国民族学会成立伊始就致力于出版民族学研究成果,将编行刊物定为4项会务之一。初期由于经费困难,无力发行自己的刊物,只能藉中山文化教育馆民族组创办的《民族学研究集刊》发表会员的成果。1935年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时,确定将筹办《民族学报》作为年度重要任务;次年,在第二届年会上,拟定1937年6月为学报第1号出版日期,预计每季刊行一册;内容分论著、学术消息、调查报告、书报介绍等;每期字数10万,论著6万,其他各项4万,甚至连文章字号、页码数量及印刷费用等都做了设计和预算,但由于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出刊一事终不了了之。1942年,民族学会恢复活动后,继续提出:“《民族学报》始终为本会主要工作之唯一目标,当力求实现之,以期奠定学术界之基础焉。”(25)徐益棠.七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J].西南边疆,1942,(15).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目标仍难以实现。1943年,徐益棠在上报社会部的团体概况表中,被迫将学报发行一事定为战后研究计划,学会刊行工作只能借助凌纯声、方国瑜、徐益棠等以私人名义创办的《西南边疆》。
与同一时期备受政府重视、各界瞩目的以边疆问题为研究宗旨的中国边政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发展相比,中国民族学会仅能以勉力维持、困难重重来形容。以1941年由黄奋生主持成立的重庆边疆学会为例,在36名发起人中,少数民族精英占了一半以上;从其公布的会长和理监事名单来看,如果加上名誉会长、名誉理事及候补理事和监事的话,多达60余人。其中,名誉会长戴季陶、于右任、孔祥熙、冯玉祥、吴忠信、许崇灏、贺耀祖、陈立夫和朱绍良等,皆为当时党政军上层人物。名誉理事则多为驻边疆地区军政长官或少数民族精英,包括傅作义、邓宝珊、谷正伦、马步芳、马鸿逵、刘文辉、沙克都尔扎布、喜饶嘉措、章嘉策觉林、森吉堪布、龙云、吴鼎昌和黄旭初等。赵守钰、顾颉刚、刘家驹、黄奋生、黄次书、石明珠、闵贤邨、马鹤天、王则鼎、吴云鹏等10位知名人士担任常务理事,会长为赵守钰。(26)中国边疆学会缘起[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433~435.吸纳了当时党政军界、学术界及边疆地区各方面人士,颇具规模和影响力。重庆、成都、榆林3个边疆学会合并后,声势更为浩大,至1942年,总会会员发展到200余人,成都分会亦有200余人,榆林分会百余人,共计600余人,“汉回蒙藏,集于一堂,分工合作,幸有小成”(27)顾颉刚致谷正纲函[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438.。又如,同样成立于全面抗战前、经历过解散的新亚细亚学会于1942年6月恢复活动后,截至1943年9月,发展新会员172人,连同旧会员已不下六七百人。(28)新亚细亚学会会务概况[J].新亚细亚,1944,(1).其机关刊物——《新亚细亚》月刊也得以复刊。
作为抗战时期研究民族问题的代表性学术团体,中国民族学会在发展中所遭遇的困境基本折射了这一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的整体状况,至于为什么没有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若想比较清楚地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要回到当时社会各界对民族焦点问题的讨论及中国民族学会的学术立场来进行分析。
顾颉刚所提出的“中国之内绝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成若干种族的必要”(29)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N].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2-13(2).,在当时尽管不乏质疑之声;从现在来看,于理论上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牵强性,但它至少表明在全民抗战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开始对西方民族理论及其影响下的中国民族划分持慎重警惕态度,转而尝试以地域之别、文化之别取代民族之别,强调同源同流及民族融合,来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防止分裂,一致对外。而诸如顾、费的公开争论在之后学术界并未再有发生,从一个方面也说明出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已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舆论导向。
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和“民族同源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中华民族形成之“宗族论”(30)蒋介石提出:“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记录。此共同之记录,构成了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更由中华民族,为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国国家悠久的历史。”(中国之命运[A].蒋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2,6.),冀图通过以“宗族”替代“民族”概念的方式,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及学界关于民族概念的争论,强化国族构建。尽管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对“宗族论”褒贬不一,但这一思想很快便具化为4条指示,由行政院秘书处传电各省,下令遵照办理。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人民只有宗族之分支而无种族之区别;中国有史以来各宗族间时或发生战争,而此各宗族皆为同一种族,其疆域亦都在帕米尔高原以东中华民族版图之内,今人述史固不能将以往史事摒弃不提,但应阐明彼一时此一时之义;禁止滥用苗、夷、蛮、猺、胡虏、满奴、满洲、华北、华南等名称或名词,防止落入敌寇藉此离间我民族、分化我疆域之圈套;研究古史要对民族融和与国家统一等问题多加论述和阐扬,对足以动摇国人对民族同源祖先信仰之说如黄帝升仙、尧舜乌有等,皆应矫正。(31)此电文在多省档案中皆有保存,本文取自“奉发 委员长蒋关于民族及边疆问题指示”[Z].广东省政府公告,1943,(987).
在此背景下,中国民族学会内部在有关“民族”是否应该存在这一问题上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学者赞同以“国族”取代“民族”,如杨成志提出,以整个国家政治与国民义务而言,“同生长于本国领土内之人民,均是中华民国国民,在理论上,实不必有民族之区分”(32)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J].青年中国季刊,1939,(1).。但多数学者是在承认“中华民族”具有“民族”“国家”和“国族”三重含义的前提下,即“这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民族”,同时也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是经过几千年,融和古往今来各种不同的族类及其思想、感情和意志,混凝同化而归于一的”(33)芮逸夫.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订正在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发表之交[J].民族学研究集刊,1946,(5).。黄文山还借助“我群”和“他群”概念来阐发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的关系,指出:“中华民族之‘我群’,即为汉族……此为最初组织中国国家之民族,其文化、地理,自成一个单位,一脉相承,已经历数万年,屹然立于天地之间,久而不替了。在历史上,‘我群’与‘他群’之交涉,几占民族史最大的部分,然而所谓‘他群’者,终之莫不为‘我群’所同化,所变易,合一隙而冶”(34)黄文山.“我群”与“他群”——两个基本概念[J].政问周刊,1936,(1).;“他群”,则为“边疆及内地之浅化民族,其语言、习尚,乃至一切文化,尚需经若干年之涵化作用,始能与‘我群’成为一体者,然而从历史观之,‘我群’与‘他群’之融合,几成为近五千年来文化演进之主流”(35)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J].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1).。因此,在这些学者看来,“在整个中华民族内,由政治的观点来说,是不可分的整体,但由学术的观点来说,是可以析出不少个体的。”(36)芮逸夫.中华国族解[J].人文科学学报,1942,(2).他们对西南少数民族族源、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初衷除了学术上的动力外,当然还有现实的关怀,希望以此推动当局及社会各界对边疆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关怀和重视,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增进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但是,他们在提倡民族一家的同时,主张首先应该在调查的基础上对西南各少数民族进行细分,关注他们在生活习性、社会风俗、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制定各种针对性政策,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他们的精神文化水平。在承认不同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寻找路径,将其纳入中华民族体系框架之内,从而实现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学术和政治目标,“从政治上、主权上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凡属中华版图之人民,均是中华国民。这是毫无疑义。正因为这个原故,才有所谓开化边民问题,以及筹划开化方策。盖政府对于边民,因为他们是我国版图内的人民,有统治权,有教育责任,有保护义务”(37)陶云达.开化边民问题[J].西南边疆,1941,(10).。
总体而言,他们的工作是“试图建立一个知识体系,来说明中华民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又如何构成一整体的中华民族”(38)王明珂.简介芮逸夫先生[A].芮逸夫.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1943[M].王明珂,编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0.,进而探讨如何将它们从传统王朝时代的“边民”转化为“国族”一分子;对于这些“他者”如何同化于汉族,或能否同化于汉族,观点亦有所保留。这一研究理路在学术讨论上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在“民族同源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宗族论”等广为传布的战时情势下,未免多少有点显得敏感和不合时宜,其渐进式地实现民族融合的观点也引发了一些反对之声。如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中针对这些学者在云南开展的民族调查和研究工作说:“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夫学问不应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39)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7卷[M].长沙: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出版社,2000:206.
2008年,民族学家李绍明在接受访谈时提到,民族问题在抗战时期是很敏感的,但凡涉及民族问题的都得想点办法用边疆问题来替代,如中国民族学会因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后来发行的刊物只能定名为“西南边疆”,加上“边疆”字样。(40)王利平,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2).这段回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民族学会在当时的尴尬处境及其研究遭遇的瓶颈和背后原故。因此,在全面抗战时期,民族学会及民族问题研究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固然与时局艰窘有关,但与当时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和舆论导向应该说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尽管各种观点的出发点都是旨在维护国内民族团结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四、从中国民族学会看这一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的特点
中国民族学会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研究特点的专业学术团体。首先,从研究领域上看,中国民族学会是一个成员研究方向和兴趣比较一致的学术组织,会员基本为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领域研究的学者,且大多具有西方留学经历或培训背景,在学术渊源上与西方知识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在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当选为监、理事和出版委员会委员的学者中,除蔡元培外,黄文山、徐益棠、商承祖、胡鉴民、吴定良、孙本文、何联奎、杨堃、刘国钧、吴文藻、杨成志、刘咸、凌纯声等均是从海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而蔡元培早年也曾数度游学海外。其次,其成立的目的具有很强的“致用性”,它成立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与构建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紧密相连;在全面抗战特殊时局下,他们不仅力图将自己所学运用到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上,而且自觉将研究工作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在对西南各民族的考察和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寻找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历史渊源、提高各民族教育文化水平以增进民族团结、激励抗战斗志的主旨。至于学会在“民族”是否存在问题上与主流声音存在差异,只能说明在特殊局势下,“致知”与“致用”如何并行不悖、学术研究如何与国家政治目标相协调是当时学者们不能回避且需要不断求索和调试的一个大问题,并不妨碍其成为民族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术团体。因此,从中国民族学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境遇,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学会及民族研究在这一时期发展的几个特点:
第一,以中国民族学会为代表的民族研究团体虽然没有获得如其所期望的发展空间,但民族研究在总体上还是获得了很大进展。中国历史形成的疆域和民族格局特点,是中原地区聚居的主要是汉族,其他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受这一分布格局的影响,中国的边疆研究和民族研究始终互为表里,紧密相关。学者们“所遭遇到的不仅是地理考察的问题,尚有民族文化的探源寻根问题,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常将历史地理、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的问题混为一谈。这类研究在当时可能是不自觉的,因为在传统的学术分类中,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并未有明确的学门定义,而以笼统的史学加以涵盖,因此在进行史地考察时,这些问题是同时受到照应的”(41)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240.。随着国民政府西迁,西南地区不仅在文化、经济等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本身即为多民族聚居区的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也带动了边疆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尽管当时对民族概念、民族问题研究的方向等还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但研究受到关注并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亦是不争之事实。
第二,现实危机促使学者们开始结合中国历史传统和发展道路思考民族概念和民族问题的解决。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民族概念、民族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如顾颉刚认为当时各族之间隔膜情形的造成,“民族”二字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没有这个名词时,每次内乱只是局部的事情,很快便能解决。但现在用惯了这个名词,每有争执,大家首先想到的不是辨别是非曲直,而是民族之间的争斗,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私人之争极易演变为团体事件,乃至不可收拾。(42)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N].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5-10(2).而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这个名词是中国向来所没有的。满清政府统治二百余年,在他们的隔离政策之下,使得国内很清楚的分出‘满、汉、蒙、回、藏’五个部分来,恰好清末传进了‘民族’的名词,于是辛亥革命之后就有‘五族共和’的口号,好像中华民国之内真有这五个民族似的。全国人受了这个口号的暗示,每以一人一事的不满而赅括全体,渐渐分出彼此的疆界”(43)顾颉刚.西北回民应有的觉悟[A].宝树园文存·卷4[M].北京:中华书局,2011:66.。因此,“若不急急创立一种理论把这谬论挡住,竟让他渐渐深入民间,那么我们的国土和人民便会随处携贰了,数千年来受了多少痛苦而抟合成功的民族便会随时毁灭了”(44)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N].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2-13.!他所创造的理论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其核心是强调共同心理因素即“民族精神”在民族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虽然这一理论给当时的民族研究带来了一些困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真实反映出西方“民族”概念在中国的运用尚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它的提出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极大影响。费孝通后来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显然是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及“宗族论”的提出,其实都是西方民族理论中国本土化进程的阶段性体现。
第三,无论是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抑或认为其内部还可以析出若干民族,“国族即中华民族”的观念基本得到认可。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一词不仅“成为各种媒体中出现最为频繁,最能激发国人抗战斗志,最易为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所接受和乐道的时代词汇”(45)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86.,并且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不可替代的共同身份符号和情感纽带。
此外,全面抗战时期包括中国民族学会成员在内的学者们对西南边疆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思考对我们今天的民族工作仍不乏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