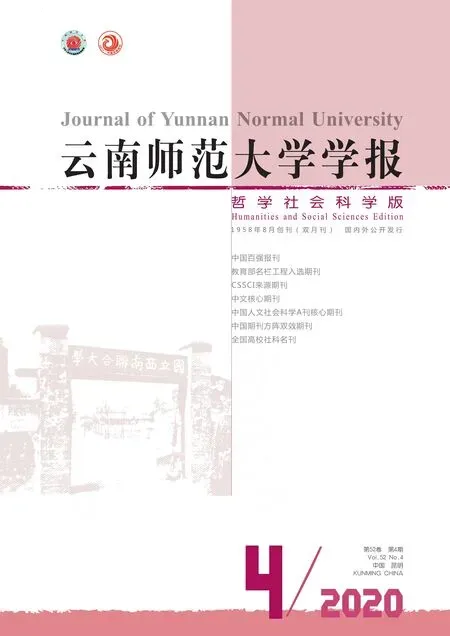坏消息告知与优死观表达(代主持人语)*
高一虹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本期主题为“坏消息告知与优死观表达研究”。
生老病死是人们生活的重要构成,其话语表述也是“语言生活”(1)李宇明.构建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序[A].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上编)[R].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的一部分。“死亡话语”即人们对死亡问题的言说、表达。这不仅仅是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的“文本”形式,而且也是包括文本生产、消费、分布在内的“话语实践”,以及更广意义上的“社会实践”。(2)Norman Fairclough.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Polity.1992;高一虹.死亡话语类型与社会变迁探索[J].外语研究,2019,(2).死亡话语反映并建构着社会观念的变迁,是语言国情的重要部分。
死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语言禁忌,长期以来学者对于死亡在实际生活中的话语表述研究很少。目前我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民政部统计,2010~2017年8年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13.3%上升到17.3%。(3)民政部官网.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老龄服务)[R/OL].http://xxzx.mca.gov.cn/article/sj/tjgb/.另据智研咨询发布的报告,2019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11%,世界排名第十,而人口老龄化增速世界第一。预计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4)智研咨询.2020~2026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研究及发展趋势报告[R/OL].http://www.chyxx.com/research/201702/493919.html.习总书记号召“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5)习近平强调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16-05-29(1).生命和死亡的质量是老龄事业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医学模式也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型。旧的模式认为疾病是单纯的躯体发生病理转变的表现,新的模式认为人是生物、心理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导致人类疾病的不仅是生物因素,还有心理和社会因素,要从生物、心理和社会统一的整体视角来理解疾病。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医学模式的转型,传统文化中只谈生不谈死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死亡”正在向话语化、公开化的方向转变;但新旧观念在社会实践中的张力相当大。
在西方学术界,“死亡学”(thanatology)是一门研究与死亡相关的行为、思想、情感及现象的综合学科,已有百余年历史。死亡相关话语的研究也较丰富。语言学研究视角包括语用学、叙事分析、语类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等;主题既包括死亡的文本呈现,也包括现实情境中的话语阐释。有学者指出死亡并不仅仅是客观物质事件,其话语构建具有条件性和政治性,随历史发展而变化。(6)Lynn Ann DeSpelder & Albert Lee Strickland.The Last Dance:Encountering Death and Dying (10th edition)[M].NY:McGraw-Hill Education.2015;Nico Carpentier & Leen van Brussel.On the contingency of death:A discourse-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ath[J].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2012,(2).在我国,“生死学”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台湾兴起,不久后传入大陆。华人学者在西方死亡学的基础上加入了儒家心性学理论,并进行了文化改造,用“生死”代替死亡。在台湾这一学科已有其系统,包括对殡葬等行业服务人员的培养。(7)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慧开法师.现代生死学开展的回顾与前瞻[C].第二届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2017.在大陆,生死学更侧重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解读死亡,(8)胡宜安.现代生死学导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不过近年来引起了医学、教育等领域的跨学科关注。2016~2019年间已召开了4届“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议题涉及死亡的哲学、宗教和文化观念、死亡教育、疼痛管理、安宁疗护等。相似活动还包括“北京大学清明论坛”“北大医学人文国际会议”等。对死亡的研究和成果的应用已成为新热点。
在上述社会和学术背景下,作为语言生活、语言国情的一部分以及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研究死亡相关话语的必要性已凸显出来。
医生对患者本人或家属就其生命的“坏消息告知”,是死亡话语的重要研究议题。目前医学界正在经历从生物模式向人文模式的转变,更关注生命的尊严。当病人被诊断出绝症,或病情恶化、面临死亡时,与谁谈,如何谈?我国时下的“坏消息告知”一般都是向家属进行的,但有越来越多的病人希望了解自己的病情,以便对有限的生命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安排。根据北京协和老年医学团队在2014年8~9月对北京市朝阳区900位平均年龄74.99岁的老人(男47%,女53%)所做的调查:80.9%的老人希望得病后知道实情,52.4%的老人希望对自己的治疗方案做决定;只有8.9%的老人愿意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接受创伤性的治疗。(9)Zhang Ning,Ning Xiao-hong,Zhu Ming-lei,Liu Xiaohong,Li Jing-bing,& Liu Qian.Attitudes towards advance care planning and healthcare autonomy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in Beijing,China [J].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15,Article ID 453932.http://dx.doi.org/10.1155/2015/453932.从尊重病人知情权的角度而言,向病人本人告知病情应是一种发展方向。如何向病人及家属告知“坏消息”,涉及语言沟通的方式方法,在国外已是一个兴盛的研究领域,也有相关的医患沟通培训,在我国还很少见。
老年人如何用言语表述自己对死亡的态度,乃至用文字形式规划自己的死亡,是死亡话语考察的另一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养老的责任正在向社会化发展,养老机构服务项目也正在向全面化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善终议题。作为善终愿望的表达,“生前预嘱”(living will)在我国是一个新语类或一种新的话语和社会实践,它是指人们事先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接受何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这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中国尚属新的语类、新的话语和社会实践,不具法律效力。2011年6月,中国首个民间生前预嘱文本“我的五个愿望”出现,推广尊严死亡。2013年7月30日,媒体对北京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并向公众普及和推广使用生前预嘱及“尊严死”的概念做了报道,在社会上引发了关注。根据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提供的数字,截至2019年底,已有约4万人在网上注册填写了“我的五个愿望”。尽管对于生前预嘱已有初步考察,(10)卜晓晖.中英文生前预嘱语类分析——中文版“我的五个愿望”与英文版“五个愿望”比较[J].中国社会语言学,2018,(28).但我国老年人对死亡、临终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们对生前预嘱有多少了解,是否接受其理念,未来的推广潜力如何,还有待实地调查。
本期语言国情研究栏目向读者呈现3篇社会语言学视角的研究论文,涉及上述坏消息告知和死亡态度两大议题。其中李芳的文章是有关医患“坏消息告知”的文献综述,向读者呈现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前沿。孟玲的文章则是“坏消息告知”的我国本土民族志,细致地报告了南方某医院某濒死病人从进入急诊直至死亡过程中的医生向家属告知坏消息的过程,具有实践启示意义。徐继菊、高一虹的研究考察了西南某养老院部分老人对“生命质量”的评价,呈现了他们的“优死”观及其蕴含的掌控自己生命的强烈愿望,以及对“生前预嘱”的了解状况。
坏消息告知和“优死”观研究从医疗和养老角度,呈现了死亡从不可言说到可言说的变化,呈现了从重生命长度到重生命质量的价值转变。这组文章从较微观的层面揭示了告知与规划的死亡话语对于民生的宏观重要性和发展前景,也再次凸显了社会语言学者考察该领域语言国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