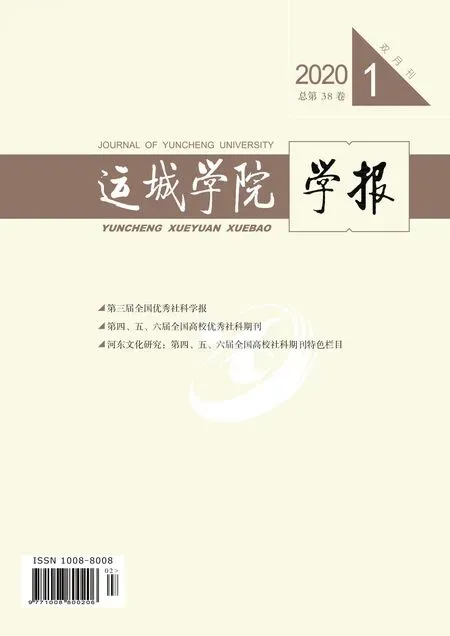我国对瑞德西韦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困境的应对
袁 姣 姣
(甘肃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兰州 730000)
2020年初冠状病毒疫情危机发生之际,美国吉利德公司在研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无疑是上万患者与国家的福音,但是一旦能通过实验,疫情下的我国药品需求市场将成为美国吉利德公司新的营利契机,受供求关系影响的药品价格将会高幅上涨。鉴于前述现状,为有效应对“COVID-19”引发的突发性公共健康危机需要充分利用《总理事会决议》构建的国际药品可及框架,有效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但自非典、甲型H1N1流感、H7N9流感病毒发生以来,我国至今从未实施过一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为有效应对“COVID-19”疫情,亟需就在研药品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鉴于前述现状,本文将对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必要性和困境展开研究,旨在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推进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
关于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研究成果较多,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研究滥觞于21世纪初期,且研究成果随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周期性爆发而不断更新。相关专著有4部,以“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搜索到期刊论文464篇。但研究成果集中于千篇一律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立法完善建议,且颇多完善建议因机械借鉴域外立法而缺乏可行性。关于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主要困境,学界的主流观点集中于相关立法缺陷因素。鲜有学者持片面观点,李明德认为我国当下的经济水平表明公共健康危机的解决不再需要完全依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政府在该买单的时候应该买单;关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立法缺陷,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申请主体范围过窄、申请事由抽象等立法缺陷是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零实施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一主流观点渊源于林秀芹学者2006年出版的专著《TRIPS体制下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至今尚无对这一观点的突破性研究。为应对这一困境,学界的主流观点强调取消实施条件限制,将申请主体扩大到任一利害关系人,这一主流观点根源于对《印度专利法》的片面借鉴,《印度专利法》虽然将申请主体规定为任一利害关系人,却通过实施条件严格限制了申请主体范围。就公共健康许可事由的细化,学界主流观点为将非传染性疾病纳入公共健康的范畴,结合药品价格、数量细化公共健康事由。综观前述现状可知,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困境仍未解决,而本文在前述基础上,将研究重点置于当下对瑞德西韦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立法及法外困境的应对上,以期突破现有研究成果,就立法及外外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完善建议。
一、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必要性
(一)“COVID-19”公共健康疫情优先于药品专利保护
1.“COVID-19”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刻不容缓
截至2020年2月17日,全国累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高达70548例,密切接触者高达546016人,累计治愈出院10844例。随着国际人口流动,病毒正在国际社会蔓延,一时内,意大利在两名武汉肺炎患者旅客在罗马接受治疗后,宣布全国将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世界卫生组织1月30日将我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为紧急状态。截至2020年1月29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国已处于《专利法》第49条所指之“紧急状态”。距离冠状病毒疫苗的临床应用还需3个月,难以满足当下的疫情需求。2月4日李兰娟院士带领的团队公布了其研究成果,证明阿比多尔、达芦那韦药物可抑制冠状病毒。美国吉利德公司研发的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和Merse病毒的药物瑞德西韦被国际社会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最有潜力的药物。截至目前,瑞德西韦在法国和美国分别治愈了两名患者,药用效果良好。鉴于我国当下的前述公共健康危机,瑞德西韦等药品可及性系关我国公共健康,而影响药品可及性的因素除“有药可医”外,还有患者能“买得起药”。具有公权力介入优势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因短期内有效降低药品价格的制度优势而广为国际社会实施,为应对未来药品通过临床试验后,美国药企“坐地起价”加重患者的药价负担,我国需充分利用国际药品可及制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保证公民近药权。
2. 公共健康危机优先于专利权的保护
新型冠状病毒等传染性疾病引发公共健康危机的情况下,公共健康保护的优先性决定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必要性。
一方面,专利制度本身的人文关怀决定了疫情下公共健康危机先于药品专利权保护。《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人类享有的分享科技进步福利的权利优先于对其发明所享有的知识产权。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的药品专利价值的实现与公共健康的保护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不合理的药品高价同时以公共健康和专利权人利益的损害为代价,导致药品专利资源配置的低效化,不合理的药品资源配置方式制约了最佳社会效用目标的实现。药品专利保护制度本身的垄断性是药品专利资源配置静态非效率性的根源。[1]272-274药品专利保护制度旨在激励药品专利权人的药品研发创新,因药品研发成本高、失败率高、风险大,有限的专利垄断期限是药品专利权人收回研发成本、持续研发,促进药品产业持续运作的制度保证。药品专利权人私人利益的保护是公共健康实现的基础,否则药品专利保护制度的缺失将导致无药可医的根源性公共健康危机。药品专利制度本身的事实性垄断是药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当专利保护所致高价药品的不可及性危及公共健康时,需实施强制许可将专利权人的私益合法让渡于公共健康。为应对当下爆发的“COVID-19”公共健康危机,避免高价瑞德西韦不可及性对患者生命健康的威胁,需通过实施强制许可降低药品价格。
专利强制许可完善药品专利传播激励机制,实现药品专利的社会效益。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看,患者对药品专利享有的合法利益源于药品专利本身的社会性。药品作为一种系关公民生命健康的特殊的商品,诸多国家最后将其纳入专利保护客体。随国际经济的发展,后虽纳入专利保护体系却仍保留了强制许可、Bolar例外等制度以保障公民的药品可及性。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来看,专利制度本身是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建立的一种契约,发明者享有的有限垄断权以其对核心技术的公开为对价,当下“COVID-19”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亟需瑞德西韦等药品专利信息的公开,仿药企业对药品专利的可及性系关无数患者的生命健康,因此当下公共健康保护的有限性决定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客观必要性。
(二)国际立法司法实践是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有力支撑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相关国际、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是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有力支撑。
一方面,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完善立法是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有力制度支撑。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渊源于《Trips协议》建立国际统一专利保护制度进程中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冲突问题的应对,为协调发达国家药品专利研发激励与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问题引发的利益冲突,《巴黎公约》为解决专利权人权利滥用引发的垄断问题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但未明确药品专利强制许可,《Trips协议》明确将公共健康的保护纳入强制许可、政府使用等未经授权的其他使用情形中。但因专利保护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仍饱受国际社会的争议。为此,2001年《多哈宣言》针对性地就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公共健康的解决,明确将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等传染性疾病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并赋予成员国在《Trips协议》弹性条款范围内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自由决定、实施权,但强制许可对药品生产商生产能力的限制仍然前述国家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主要制约因素,为此,后2005年出台的《总理事会决议》规定了强制许可药品专利的对象性进出口制度,该制度最终在《修改Trips协议议定书》正式生效。作为《Trips协议》的成员国,我国充分应用前述国际协议中的弹性条款,在《专利法》《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中确立了包括药品专利在内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将紧急状态、非常情况、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健康规定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事由,并依不同许可事由规定了不同申请主体、区别化强制许可启动程序。为类似于非典、新型冠状病毒所致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提供了制度基础,但随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提升,《Trips—Plus框架》下更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为此需重构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另一方面,域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为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提供了借鉴依据。印度、巴西、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均曾通过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来应对其国内公共健康危机。为应对“911事件”后国内的炭疽热病毒公共健康危机,对德国拜耳公司生产的高价药物cipro,美国不是直接通过其国内的医疗保险制度来解决其国内药品需求,而是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作为降价谈判筹码,促进药品降价,后加拿大也采取了这一药品降价措施。2016年,德国对日本生产治疗艾滋病药物的盐野义公司颁发了强制许可。印度为应对高昂抗癌药品索拉菲尼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实施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巴西为应对其国内的艾滋病公共健康危机曾对瑞士罗氏制药生产的奈非那韦和默克公司生产的依法韦伦实施了强制许可。综上,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许多国家药品降价的有效措施。
(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高幅度降价优势
相较于普通许可,降价的高幅度、高效性决定了强制许可是瑞德西韦药品专利的有效获权路径。一方面,相较于普通许可,许可的高效性决定了强制许可是瑞德西韦药品专利的有效获权路径。普通许可路径下,瑞德西韦药品专利权的获取以我国和吉利德公司的谈判为主,享有瑞德西韦药品专利所有权的吉利德公司享有完全的自主定价权,卖方主导的药品专利市场决定了我国处于许可使用费弱势谈判地位,高昂的药品专利价格将成为患者药品可及性的另一障碍。相较之下,倾向于保护公共利益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依据国家公权力,避免了长周期谈判对强制许可效率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相较于普通许可,降价的高效性决定了强制许可是瑞德西韦药品专利的有效获权路径。以域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为例,2012年印度对德国拜耳公司治疗肝癌与肾癌的药品索拉菲尼实施了强制许可,强制许可后的药品降价幅度高达97%。2001年,巴西对默克公司生产的依法韦伦实施强制许可后,降价幅度达40%。[2]2932001年,美国为应对其国内的炭疽热病毒危机,将强制许可作为谈判筹码,迫使德国拜耳公司降价50%。[3]163-165相较于普通许可获得瑞德西韦药品专利而通过国内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方式,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在高幅降低药品价格的同时也避免国内药品财政负担。
二、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困境
(一)强制许可将破坏药品专利创新激励机制
损害药品专利权人利益,破坏药品专利创新激励机制是我国当下对瑞德西韦等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较低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使用费和不受限的强制许可实施主体及范围将损害药品专利权人的垄断利益,破坏药品专利创新激励机制。
一方面,较低的许可使用费将破坏药品专利创新激励机制。我国现行《专利法》尚未明确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从域外相关司法实践来看,多为仿药企业净销售利润的6%左右,这一较低的许可使用费是发达国家反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主要原由。药品专利保护制度的本质在于通过赋予药品专利权人有限的垄断期限,激励药品研发创新,专利垄断期是专利权人收回药品研发成本、开展新药研发的主要方式。药品研发成本高、周期长、失败率高,数种研发失败药品的成本均需由一种研发成功的药品负担。有关研究表明,药品平均研究周期约为10年左右,研发成本高达数十亿至百亿美元,研发失败率高达90%左右。[4]10强制许可则借诸公权利,中止专利保护垄断期,授予仿药企业仿制权。远低于普通许可使用费的强制许可使用费将损害专利权人的私人利益,破坏药品创新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不受限的强制许可实施主体和范围将破坏药品专利创新激励机制。我国现行《专利法》尚未明确多个主体同时提出强制许可的情况下,实施主体的确定程序,不受限的实施主体范围将损害药品专利权人的垄断利益。再者,强制许可的实施范围、时间的不明确亦是药品专利权人利益损害的主要原因。因市场销售是瑞德西韦药品专利研发成本收回的主要路径。以“成本—收益”规则为基础的创新激励理论只有当收益远高于成本时,对专利权人的创新激励才能奏效,从药品的商品化过程来看,药品专利不仅激励药品的研发还激励药品的生产投资。区别新药研发的交叉许可使用,专利垄断期的长短系关专利权人的利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则因专利的提前公开而错失了最佳专利垄断期限,损害了专利权人的垄断利益。[5]225-286公共利益的过度维护将损害专利权人的利益。特别是对于“COVID-19”这种非常态化、周期性传染性疾病用药,专利研发成本的收回时间也极其有限,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使仿药成本低于药品研发成本,挫伤专利权人的创新积极性。无论是从“垄断激励”还是“竞争激励”理论的视觉,强制许可均会损害药品专利权人的利益。播种的动力源于预期的收获。
(二)可能加剧中美国际贸易摩擦
当下以知识产权为主要争议焦点的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是对瑞德西韦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又一困境。全球南北药品专利资源配置的差别性决定了除药品专利权人和实施主体之间的矛盾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更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从域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案例来看,广泛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制裁等其他贸易壁垒。泰国2007年因对美国雅培公司生产的抗艾滋病药物实施强制许可而遭受了美国的贸易摩擦,上世纪曾广泛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巴西、泰国、南非等国家也均屡次被美国列入“301”重点观察名单,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贸易制裁。[6]既上世纪美国屡次将我国列入“301重点观察名单”后,2017年为提高其专利产品的全球保护水平,曾就我国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提出指责,后国际贸易摩擦随华为5G标准必要专利纠纷而加剧。[7]知识产权商品化、资本化时代,包括药品专利在内的专利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此,关于吉利德公司专利豁免的宣扬可能只是美国提前通过药品专利临床试验的缓兵之策。既《Trips协议》后一直企图在全球确立更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美国积极放弃其专利利益岂不天方夜谭?瑞德西韦的药品专利由美国吉利德公司享有,瑞德西韦药品专利无疑是美国在当下中美贸易摩擦战中新的筹码。
(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立法缺陷制约了实施效率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是当下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的另一困境。我国现行《专利法》中,复杂的强制许可申请程序、公共健康许可事由的缺乏以及强制许可与同情用药制度的分离制约了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效率。
首先,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生命健康,遏制“COVID-19”病毒的蔓延。但《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规定的复杂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程序难以适应当下公共健康危机的紧迫性。《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第6条规定,紧急状态、非常情况下,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建议实施强制许可。建议主体和建议责任的不明确极易引发有关部门渎职行为的泛滥。其次,国内公共健康危机这一专门性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事由的缺乏,影响了强制许可的实施效率。《专利法》第50条的公共健康许可事由仅限于药品专利的出口,即类似于当下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需准用紧急状态许可事由,而这一事由的适用以国家紧急状态的宣布为前提,国家紧急状态的宣布显然迟于卫生部门对公共卫生部门对公共健康危机的确定。最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因缺乏与同情用药制度的链接而制约了强制许可的实效。对“COVID-19”重症患者而言,临床阶段药物的适用是其重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由于强制许可仅限于上市药品,尚处临床试验阶段的药品被排除在强制许可客体范围外。我国《药品管理办法》在最近一次修订中虽然也规定了同情用药制度,但瑞德西韦目前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三期随机、双盲临床试验4月底方可结束,试验完成后,即使通过快速上市审批通道也仍需花费一定时间方可正式上市,彼时疫情可能已经结束了。综上,前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程序的复杂性是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主要困境之一。
三、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困境的应对
(一)完善相关制度设计衡平药品专利创新激励机制
为避免药品专利权人的利益损害和药品创新激励机制的破坏,需构建合理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限制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范围。
1. 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
现行《专利法》仅规定许可使用费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则由专利行政部门裁决,具体的许可使用费计算标准尚不明确,这在扩大我国专利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权的同时也限制了药品专利权人的许可使用费预估值,药品专利权人的利益损害并非源于强制许可本身而是强制许可使用费和药品研发成本之间的悬殊。域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判例多将实施主体净销售额的4%—6%作为许可使用费计算方式。[8]瑞德西韦新型冠状病毒用途专利只是瑞德西韦药品专利的一种方式,据有关数据显示,除这一用途专利外瑞德西韦已经就治疗副黏病毒感染疾病、丝状病毒科病毒、SARS、MERS等冠状病毒等用途专利申请了多种专利,瑞德西韦既有的多元化药品专利布局分散了其药品研发成本及风险,易言之,瑞德西韦新型冠状病毒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使用费并非其研发成本的唯一收回路径。为平衡疫情公共健康危机与吉利德公司药品专利权人的利益,可以借鉴域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使用费计算方式,采用仿药企业净销售额5%计算强制许可使用费。
2. 限制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主体及范围
限制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主体及范围以平衡专利权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药品专利创新激励机制。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特殊之处在于瑞德西韦药品新型冠状病毒用途专利尚处于临床试验中,疫情经过后,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尚在专利保护期内。为避免强制许可提前公开药品专利而损害专利权人的利益,需对实施主体及范围及时间作出以下限制:一方面,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在审查批准相关药企的强制许可申请时需分析申请主体的实施条件、生产能力,授予具备实施条件的主体强制许可,多个申请主体均具备实施条件的情况下需依据其生产水平和“COVID-19”患者的药品实际需求分别授予一个或多个企业。另一方面,需同时限制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范围及时间。就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范围而言,因瑞德西韦药品功能的多元性,强制许可范围因仅限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再者,考虑到强制许可的实施效率,需依据瑞德西韦药品的市场实际需求,同时授权不同的仿药企业定时高效生产。就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时间而言,应仅限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疫情结束则需要即时中止瑞德西韦强制许可,将专利权人的垄断利益损失降到最低。
(二)弱化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
1. 优先采用“谈判方式”弱化国际贸易摩擦
为应对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可能加剧国际贸易摩擦的困境,需优先采用谈判方式弱化国际贸易摩擦。一方面,从域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例来看,许多国家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多采取将强制许可作为谈判筹码的方式,迫使专利权人降低药品价格。美国为应对2001年爆发的炭疽热病毒危机,将强制许可作为谈判筹码,迫使德国拜耳公司将其生产的药品西普洛单价从1.75美元将至0.99美元。[9]受同时期加拿大的强制许可威胁,拜耳公司亦降低了西普洛在加拿大的售价。巴西在应对其国内的艾滋病危机时同样采取谈判的方式,迫使罗氏制药降低了那非那韦在其国内的售价。另一方面,优先采用将强制许可作为谈判筹码的方式亦符合我国当下谨慎的药品专利政策,我国至今从未实施过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即使在2005年禽流感危机发生时,我国并未批准广州白云山对“达菲”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而是优先采用与罗氏制药谈判的方式,由瑞士罗氏制药授权我国国内药企仿制。[10]
2. 充分运用药品政策积极应对可能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
为应对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可能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需充分应用强制许可这一药品可及政策,优先应对当下“COVID-19”引发的疫情危机。虽然我国当下的药品可及政策逐渐倚重于药品可及政策,但从疫情对国家经济政策的损害来看,无论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作为降价谈判筹码还是直接实施,均是降低疫情应对成本的主要措施。医疗保险完善的许多域外发达国家也未曾放弃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加拿大和美国在应对炭疽热病毒危机时便充分应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以降低药品价格,而不是优先启动其国内医疗保险制度,不乏降低国内疫情应对成本的考量。“COVID-19”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不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医疗战役,更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等医疗硬件设备的建设成本、全国数万患者的用药成本、全国企业因疫情迟延返工造成的损失等都对我国年初的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据有关研究表明,按照我国经济去年的增速,截止目前一个月的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已超过17.5万亿。因此疫情应对成本同堂需考量。为此需积极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降低药品专利实施成本,进而降低瑞德西韦药品的市场价格,提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对危机应对效率,降低疫情应对经济成本。
(三)完善有关制度缺陷提高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效率
为提高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效率,需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申请程序,明确规定国内公共健康强制许可事由,有效链接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与同情用药制度。
1. 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申请程序
为提高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效率,需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申请程序。一方面,为避免强制许可申请主体滥用权力,提高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效率,需明确紧急状态、非常情况下享有建议权的有关部门,同时规定未履行建议权的责任后果。因类似于“COVID-19”病毒所致公共健康危机最先由医疗卫生部门发现,可以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提出部门明确规定为卫生部门。同时规定有关部门未及时提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渎职责任。以武汉最近爆发的肺炎疫情为例,有关部门对首次疫情上报信息审批程序的失职审批,延缓了疫情的最佳控制、救济时间。同理,为保障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效率和患者的近药权,需明确前述卫生部门失职的责任后果。另一方面,需简化紧急情况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程序。我国《药品管理法》虽然规定了紧急情况下的简易审批程序,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程序仍过于繁琐,[11]为此,需简化紧急情况下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申请程序,缩短专利权人和强制许可请求人陈述意见的时间。另外还需明确分离强制许可的生效程序与救济程序,避免强制许可的救济程序影响强制许可的实施效率。
2. 明确规定国内公共健康强制许可事由
为提高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效率,需将类似“COVID-19”病毒引发的紧急状态明确规定为国内公共健康危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事由。现行《专利法》第50条规定的公共健康许可事由仅限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出口,国内因公共健康危机引发的非常情况,需准用紧急状态许可事由,为避免国家紧急状态宣布程序对强制许可效率的影响,可以将同样适用于国内公共健康危机与国外公共健康危机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事由统一规定于《专利法》第50条。[12]在类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类疫情发生时,由卫生部门明确界定公共健康危机即可进入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程序,有利于保证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效率。
3. 有效链接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与同情用药制度
为提高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效率,需有效链接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与同情用药制度。当下瑞德西韦等专利药品是“COVID-19”疫情的有效应对路径,但出于临床用药风险的考量,同情用药制度下尚处试验阶段药品的适用范围仍然有限,仍然不能对尚处临床试验的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用于重症患者。本文认为,以当下的“COVID-19”疫情为例,考虑到临床试验阶段药品的用药风险与重症患者死亡风险的等同性,可以扩大同情用药制度的适用范围。[13]有效链接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与同情用药制度,扩大临床试验阶段药品的生产,提高重症患者的药品可及率。再者,为促进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需充分利用Bolar例外制度,充分利用既有的药品实验数据,提高瑞德西韦药品仿制能力,做好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准备。
四、结语
经前述分析论证可知,“COVID-19”疫情公共健康危机肆虐的当下,公共健康优先于专利权的保护,为保证患者对瑞德西韦专利药品的可及性,需借鉴域外立法,充分利用《Trips协议》构建的药品可及制度,有效降低药品价格,积极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但我国当下对瑞德西韦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主要面临以下困境:首先,较低的许可使用费和不确定实施主体、范围将损害专利权人私益,破坏药品专利创新激励机制;其次,因瑞德西韦药品专利权归美国享有,强制许可对美国吉利德公司经济利益的损害将加剧当下以知识产权为主要争议焦点的中美贸易摩擦;最后,现行相关立法中紧急情况下繁琐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申请程序、国内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事由的不统一以及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和同情用药制度的分离亦增加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困难。
为应对前述困境,需采取以下应对措施。首先,需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使用费计算方式、限制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主体和范围以避免专利权人利益损害对新药研发创新激励机制的破坏;其次,为有效降低疫情经济损失,优先采用谈判方式的同时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实施强制许可;最后,还需完善紧急情况下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程序、统一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进出口事由、有效链接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与同情用药制度,提高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效率,以期高效、经济应对当下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