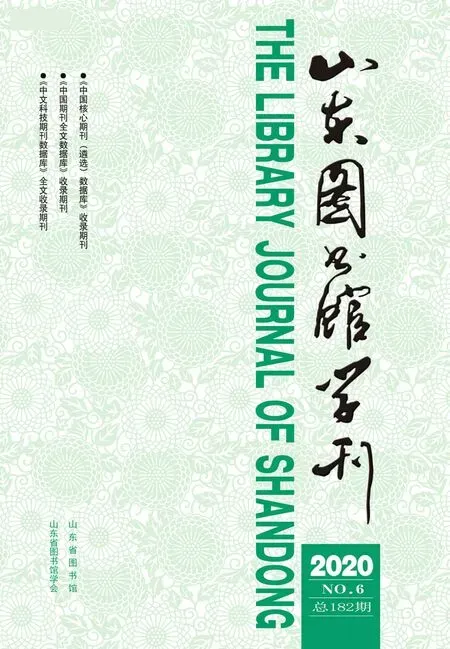论采访者与受访人平等关系的建立*
——关于提高口述历史访谈质量的思考
邓利萍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 200062)
1 引言
非洲有一句谚语:一个老人死了,就相当于一座图书馆坍塌了[1]133。这说明在大数据时代,挖掘、抢救和建设口述历史资源刻不容缓。口述历史工作的先行者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对口述文献进行了开发、收藏、整理与传播[2]。近年来,基于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的口述历史采集活动给我国图书馆人以乐观的期待。王子舟等认为开展口述史采集工作,有助于修复与增强图书馆的记忆功能,以消除图书馆被网络替代走向消亡的风险[3]。许多图书馆主持或参与了一些大型的口述史料工程,如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口述项目、湖南图书馆的“湖南红色记忆”和“湖南抗战老兵”口述项目、汕头大学图书馆的“汕头埠老街”口述项目和中国女性图书馆妇女口述项目[4]。
在口述访谈蔚然成风的形势下,口述史料数量暴增,于是口述历史的访谈质量也开始被关注[5]。对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者来说,口述历史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为挖掘历史事件的真相。越接近真相,口述史料质量就越高。衡量口述史料的质量有许多维度,但人们比较一致地聚焦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6]。很多人简单地以为,只要采访者亲临现场,对受访人进行面对面采访所获得的口述信息就很宝贵,以为这就很接近真实的历史。然而历史学者陈春声在《走向历史的现场》一文中指出,“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不会比官修的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7]。既然获得真实历史是如此艰难,那么如何进行口述历史采访才能获取真实的口述史料呢?根据笔者的口述历史采访实践经验,访谈所获史料的真实性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合理定位采访者与受访人之间的关系。
2 两个维度的定位偏差
在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中,采访者与受访人之间呈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1]4。如何让采访者与受访人建立起融洽的谈话氛围,是确保口述访谈质量的先决条件。我国口述历史访谈工作起步较晚,图书馆人虽已普遍意识到非物质口头文化遗产正面临迅速消失的严峻局面,也陆陆续续开展了对口述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抢救性挖掘[8],但是在口述文献采集的具体实践层面还不是很成熟,有时倾向于简单化处理。观察同道者的访谈,以及对自身访谈经历的省思,笔者认为,访谈者面对受访人的时候经常出现两个维度的定位偏差,这严重地影响到了口述访谈的质量。
2.1 信息互动关系的不平等
有的采访者局囿于本专业的知识结构,缺乏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于是采访的现实场景往往是采访者拿着访谈提纲或访谈清单,生硬地让受访人回答,自己则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地记录受访人的叙述。此时,受访人居于高位,采访者处于下位。采访者与受访人之间处于一种“尬聊”的交流状态。这样简单的一问一答显得十分生硬,不可能取得良好的访谈效果[5]。殊不知,口述访谈既非法庭审讯,也不是什么专案调查,而是两相情愿地合作探讨并记录当事人的历史记忆[1]59,因而建立平等的信息互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2.2 人格的不平等
很多采访者都存在把受访人加以工具化的倾向,即受访人被视为配合采访者完成采访任务的工具。此时,采访者居于高位,受访人处于下位。在口述史采访过程中,采访者是主动的,是采访的发起者,有明确的采访意图。受访者是被动的,是采访的对象,其谈话内容受采访目标的制约[5]。许多口述历史采访实践收效甚微的绊脚石并不是采访者前期工作准备得不够充分,也不是采访硬件设备提供得不够齐全,而是常常忽视了受访人的人格尊严。
3 建立平等关系的策略
3.1 “知道得比受访人更多”:平等信息互动的前提
口述史家唐纳德·里奇先生呼吁:做口述历史,须问得更多,问得更广,并尽可能问得更深,以丰富我们的个体记忆档案[1]3。人们通常认为,采访者对受访人进行访谈,就是要获取原先我们所不知道的信息,或挖掘、补充馆藏文献中所缺失的历史细节。那么其情状当然是采访者提问,受访人回答,采访者记录,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以往也有许多采访者在谈论访谈的准备工作时,强调了解受访人或与受访人相关事物的背景信息。但是如果真的要使口述史料成为文献信息中的精品,采访人必须完成浩繁的案头工作,其资料准备应当充足到足以与受访人平等对话的程度。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口述访谈团队关于案头准备工作的口号是“知道得比受访人更多”,有的采访者不免感到疑惑: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比受访人知道得更多呢?如果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比受访人还要多,那又有什么必要去采访这个人呢?答案是肯定的。
3.1.1 “知道得比受访人更多”的可能性
从事口述历史采访工作需要采访者具备一定的专业背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皆有口述历史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即使办公室助理K.L.Follette也是一位口述历史学家[9]。采访者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把时空跨度很大的大量事物结合起来思考。这需要做好“笨功夫”,即要全面查阅相关史料,熟悉受访人所经历的时代、社会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历史背景与相关细节[1]57。在这方面,历史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项目的执行者唐德刚先生做了率先垂范。在受命给张学良将军做口述传记时,唐先生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以及单篇文章,编成一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10]。通过浩繁的案头工作,唐先生实现了“知道得比受访人多”的前期准备。如在对历史亲历者抗战老兵采访时,采访者既要了解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也要了解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在正面战场中,采访者还要了解各个战区的情况。有关老兵参加的某个特定的战斗,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很方便且不受限制地查阅中国的档案和日军的档案,知道双方决策的过程,以及战事展开后的应变过程。另外,也可以通过档案再现与那场战斗相关的人事关系。以上这些方面的情况,受访老兵自己可能都是不知道的。而如果采访者采访前掌握了上述信息资料,就能够“知道得比受访人更多”,从而获得与受访人进行“平等对话”的实力。历史亲历者往往受一人一地的时空局限,而采访人可以突破这一时空局限俯瞰整个历史事件,这个道理美国学者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表述得极为透彻[11]。
3.1.2 “知道得比受访人更多”的必要性
出于对口述史料的深切关注,有学者认为应该多方挖掘口述史料,交叉比对、相互印证各种资料,笔者深以为然。但是访谈后的交叉比对的效果也有赖于访谈环节的质量,否则一大推不可靠的口述史料加以互相印证,获得的资料依然不可靠。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口述史料的可靠性呢?这就要求采访者在口述史采访的过程中,对受访人所叙述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拷问。只有知道得比受访人更多,才有实力去拷问、甄别受访人提供的口述内容的真实性程度。这里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如访谈清单的设计、提问的技巧和功力,以及访谈场所的选择等等环节,只有“知道得比受访人更多”,才能更加缜密、合理地处理这些环节。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采访者有必要尽可能查全资料信息,有备而来,当受访人遗忘、错记或一时想不起某些人或事的信息及相关细节时,能够及时做出准确的提示[1]58,以便采访工作能够顺利地进行,同时能够增强口述史采访的可靠性,从而提高口述历史访谈的质量。
3.2 “生命史”访谈:人格平等的情感纽带
口述历史采访不等于机械地向受访人汲取口述史料,它首先是采访者与受访人之间一种情感、信息的交流和分享。有些采访者不管对受访人表现出如何的礼貌和谦逊,但在骨子里还是把受访人视为实现访谈目标的工具,这是采访者与受访人之间人格上的不平等。这会影响采访者获得深层次的历史真相。
3.2.1 以“生命史”访谈为切入口
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将要开展的访谈属于“专题访谈”,访谈团队也不能直扑目标,而是应通过保持持续而密切的联系,与受访人事先建立起同情共感的和谐关系。相反,如果采访者未能与受访人建立起同情共感的良好关系,那么受访人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回避某些问题,使得访谈进行不顺利,获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也就不完整,掩盖了部分历史真实[12]。采访者与受访人是两个或多个生命的相遇,人们都有各自的期盼、兴奋点和痛点。因此,用“生命史”访谈为切入口,是一个明智之举。
比如在采访国民党军队老兵的抗战经历时,受访人不但不认为自己的抗战经历是一个光荣的记忆,反而觉得是一种耻辱的根源。在岁月的长河中受访人已经饱受压抑和煎熬,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会下意识地作“选择性的遗忘”[1]195。因此,在做“专题访谈”之前,采访者应首先抱着深切理解的态度站在受访人的角度,与之同情共感,以人格平等为情感纽带,消解受访人的心理障碍,让受访人产生今是而昨非的愉悦心情,将“生命史”访谈纳入到“专题访谈”之中,作为挖掘深层次历史真相、获得高质量口述史料的必经通道。因此,预访谈期间对受访人进行“生命史”访谈并不是在做无用功,而是情感铺垫,是为进入“专题访谈”前实现采访者与受访人在人格层面的平等关系。
3.2.2 用“生命史”定位“专题访谈”
在做口述访谈时,采访者用“生命史”去定位“专题访谈”,可以尽量避免信息失真。采访者应尽量做到换位思考,站在不同受访人所处的生命状态理解事物。比如对彩带工艺传承人的口述采访,如果能从生命史的角度予以观照,那么同一个工艺对不同传承人来说具有不同的意涵。对于有些传承人来说,彩带编织工艺就是一个饭碗,一个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但对于有的传承人来说,这个工艺就是他的人生意义所在,是一种感情的寄托,是快乐的源泉。在把彩带工艺视为人生寄托的传承人中,有的是因家底丰厚,不需要为生计而劳碌,或许只是带着兴趣来学艺的,父母也不指望他以此来贡献家庭的经济;也有些人是受高人指点,或参加培训时,其艺术感觉被激活。因此彩带编织在不同的传承人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阅读对抗战老兵的访谈记录时会发现:有些老兵更侧重于表达卫国的光荣,有些更多地慨叹战争的残酷,而有些则偏向抒发对牺牲战友的怀念。这些既与他们的战场经历有关,也与老兵具体的生命历程有关。论者多强调访谈前对相关历史背景、时代背景的了解,殊不知更重要的是对个体的生命背景或生命底色的了解。因为特定的个体与时代背景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比如一提起战争年代,令人马上想起浩劫、灾难,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在实际的访谈中,也有不少受访者说,他们安闲地避过枪林弹雨时期,回忆起来依然心有余悸却也深感侥幸。可见,光注重时代背景,却虚化、抽空受访人具体的生命底色,这样的口述史料难免成为“碎片”之嫌。
英国社会历史学者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指出,历史应该是为那些并没有发出声音的人而写的[13]。口述历史就是记录那些没有被记录的历史,记录那些没有被记入史册的人。每个生命都是“大历史”熔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职业或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需要从生命史的角度予以定位。口述历史工作首先应着眼于受访人的生命史,只有在方法上切实尊重历史和人生的整体性,将之视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体”,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口述史[14]。
4 基于平等关系的访谈实践
为迎接华东师范大学七十周年(2021)校庆,笔者的访谈团队对中文系九十多岁高龄的老翻译家王智量老先生进行了口述历史采访。在正式采访前,笔者根据受访人的生平划分了生命史的6个阶段。其中,受访人的人生第二个阶段(1948-1958)是在北京时期。在预访谈中得知受访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先后修读过法律和俄语两个专业,担任过俄语组(当时还没有俄语系)的团支部书记。又了解到受访人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奉命调到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但是我们为了对受访人做北京阶段的采访,搜集、梳理了一份十几万字的资料长编,包括以下内容:
(1)受访人在北京大学修读法律和俄语期间所有相关教师的名字、籍贯、求学经历、职务和重要作品。
(2)当时北京大学团总支的书记、副书记、各系团支部书记的籍贯,后来的去向。
(3)1958年前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名单、籍贯、学术经历、职务和主要作品,特别注意他们来自国统区还是解放区。
(4)受访人任职期间北京大学和文学研究所的大事记。
(5)因为受访人的专业是俄语,又做了1949年至1958年苏联科学家、艺术家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编年。
(6)深度挖掘与受访人相关的每个人物的社会关系网络,如同乡、同学、朋友、家庭和姻亲等。
事实证明,我们的资料长编在后来的实际访谈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现在印象比较深的主要有这样几条:
第一,打捞受访人意识深处的历史记忆。当我们想重建北平解放后的共青团生活时,先让受访人自己去回忆,当受访人叙述完以后,我们就开始抛出已经做足了功课的校团总支(后来成立团委)、各系团支部书记的名字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他屡屡惊叹,“这个人你怎么知道!你不说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个人,你一说我又想起……”。受访人常常处于兴奋活跃的状态。
第二,由于资料扎实,当场就纠正了一些受访人的记忆误差。
第三,在辩论中呈现历史事实。随着采访次数增多,相互了解和信任程度的加深,就可以从容地对受访人的一些回忆提出质疑。受访人也会重新思索一些重要的“生命坐标”来校正自己的记忆。在辩论中,排除了一些程式化的概念对记忆的干扰,以及前后记忆的叠加导致的错讹。
在这样的访谈中,议题、深度、广度和细节都在平等信息互动中得以大幅度的拓展,这是我问你答式的采访所无法比拟的。我们的访谈团队与翻译家王智量先生之间的采访关系,事实上已经不是谁配合谁的问题,而是互相合作探究历史真实的队友关系。在采访过程中,团队成员也处于兴奋状态,人们用武侠小说的描写来总结我们的访谈,说“只有自己武功好,才能逼出高手的武功”。可以想象,如果采访者对受访人及其相关情况知之甚少,受访人觉得访谈的索然无味也是可以预料的。
可见,建立在信息互动关系上的平等和以“生命史”为情感纽带所连结的专题性访谈,在具体采访实践中体现的是“平等对话”,是在探究历史真实的活动中地位的平等,而不是受访人对采访者单方面的的信息“授予”,更不是采访者直奔主题的口述史料攫取。
5 结语
综上所述,采访者与受访人存在着两个维度的不平等。一个是受访人向采访者单方面信息授受的不平等;一个是采访者将受访人视为实现访谈任务的工具的人格上的不平等。改变知识授受不平等的策略是,通过访谈前全方位的案头工作掌握比受访人更多的资料,从而具备跟受访人平等对话的实力,在访谈过程中对受访人进行信息的强刺激,使受访人打捞出意识深处的历史记忆,并与受访人的辩驳中使深层的历史事实得以呈现,最终实现访谈的议题、深度、广度和细节的大幅度拓展。消除视受访人为实现口述目标工具化的人格上的不平等,其表现方式是进行“生命史”访谈,在交流情感和信息的过程中完成口述史专题资料的采集,从生命史的视阈中理解受访者的口述资料,从而避免了口述史资料的碎片化。
可见,建立采访者与受访人的平等关系,对提高口述史质量具有战略层级的重要意义。
——基于武汉市部分对象的调查
——以湖南图书馆抗战老兵口述历史工作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