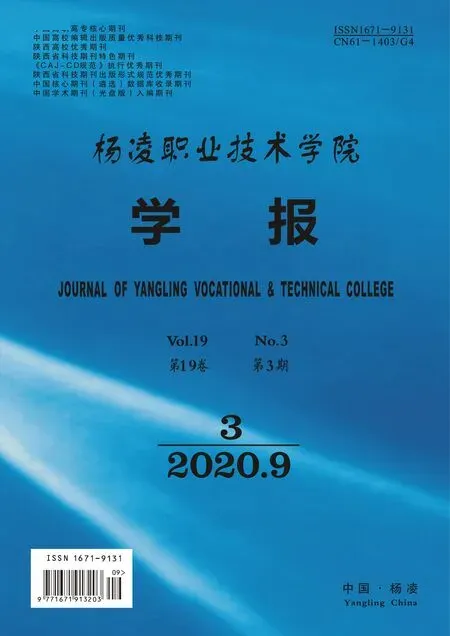《第三地晚餐》中男性形象的叙事策略
李淑君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对男性形象的叙写,诉诸于不同作家笔下便会有不同的显现。一般而言,在当代社会,女性作家笔下男性形象的塑造或多或少会有点“消解男性崇拜”的意味,尤其在“新女性”小说那里,这种解构更是达到了一定高度。而素有“北国精灵”之称的迟子建则不然,她在当代文坛始终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存在着,即便在女性主义写作如潮蔓延的80、90年代,她也未曾将自己归于其间,迟子建甚至坦言自己至今仍未明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定义及界限。尽管如此,女性的感性以及童年经历所酿就的悲悯与包容情怀总是显现于她的创作中。《第三地晚餐》是迟子建创作的一部以男女两性婚姻和爱情为主的中篇小说,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历经情感波折后最终回归家庭。与此同时,迟子建穿插讲述了诸多男性人物的情感故事,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人性的弱点,迟子建对此并非一味地包容,而是诉诸其理性的思考,显现出情感的节制。正是在这种“温情而不滥觞,忧伤而不绝望”[1]的写作中,读者得以领悟迟子建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思考。
1 《第三地晚餐》中的男性形象序列
迟子建曾说:“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优秀的作家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发现人类的个性事物,而是体现那些共性甚至是循规蹈矩的生活,因为这里才包含了人类生活中永恒的魅力和不可避免的局限”[2]。《第三地晚餐》以女主人公陈青为叙事主线,使得与之发生各种联系的男性依次登场。其中有她的情感对象、血缘至亲、事业伙伴等,这些身份地位迥异者,共同构筑起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序列。
1.1 情感对象
马每文,陈青的丈夫,市人大代表、受寒市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因《海苔窗》与陈青结缘,婚后利用其社会关系和金钱为陈青的兄妹调动了工作岗位,改善了陈家的生活,是众人眼中的模范丈夫,却因一次求欢的失败与妻子展开了冷战。最终在目睹了妻子的一系列反常举止后,领悟到了妻子无处寄托的爱,回到了她的身边。
徐一加,寒市有名的建筑师。紫云剧场将他与陈青联系到了一起,这段婚外恋情始于双方对彼此的欣赏,终止于徐一加的厌倦。但徐一加爱好猎艳,年近半百的他又与陈青的继女蒋宜云发生了关系,并谎称会为她而离婚。他的欺骗最终换来的是名誉的坍塌以及婚姻的破裂。
1.2 血缘至亲
陈大柱,陈青的父亲。年轻时为轧钢厂的工人,面貌丑陋且嗜酒,娶了貌美如花却失去一只胳膊的陈师母。陈大柱在偶然间为邻居王卷毛疏通了一次下水道后,两人开始私通,陈师母在隐忍数次后,最终将两人一同杀死。
陈墨,陈青的哥哥。轻微智障,经人介绍娶了走路一歪一斜的张红为妻。陈青与马每文结婚后,马每文将陈墨从废品收购站调到了邮政局,使其成为一名正式工人。
1.3 业内同行
老于,从事于《寒市早报》副刊部,陈青的同事。年过半百的他要接济一双儿女,还要照顾体弱多病的老婆。尽管他时常向陈青推荐一些“关系稿”请求刊发,陈青念在他的艰难境况,大多数情况下会答应他的请求。
1.4 同情对象
王斜肩,原名王林,一名送水员。不仅要照顾因意外事故瘫痪在床的妻子,还要抚育年轻的儿子。陈青怀着深切的同情,为其做了一顿免费的晚餐。
宰羊人,含冤入狱者。因他有杀害妻子的重大嫌疑而被判处刑罚,真凶落网后他才被释放。出狱后的他只能在血腥的宰羊中寻求内心的安宁。
《第三地晚餐》中涌现的诸多男性形象,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人性的弱点,为满足自己的性欲而出轨的陈大柱、不断寻求刺激的徐一加、为赚取中介费而罔顾稿件质量的老于以及不能直面情感冲突的马每文等,他们诚然有着“利己”的一面,用情不专的陈大柱及徐一加更是令人对当下婚姻的忠贞产生怀疑。但“迟子建式的写作”总在悲凉处存有一丝温情的曙光,与陈大柱、徐一加类令人唾弃者相对的则是王斜肩、宰羊人等用情专一者,小说中王斜肩为妻子擦拭屎尿的细节描写更是将患难夫妻的相濡以沫展现地淋漓尽致。除却性格鲜明者外,马每文与老于的形象则更具立体感,爱护妻女、善待陈青娘家人的马每文几近“完美男性”的标准,尽管如此,夫妻间发生矛盾时男性的自尊还是占了上风,以至他无视妻子的感受,导致夫妻二人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勤恳努力、忠于家庭的老于本性善良,却为小恩小惠而屡次向陈青推荐“关系稿”。迟子建在《第三地晚餐》中构建出的形形色色的男性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当下社会男性的真实写照。
2 《第三地晚餐》中男性形象的叙事手法
2.1 女性视角下的男性群像
人类学家曾说过,男女两性间的唯一相似之处,就是二者同属人类。这种说法在诸多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验证,男女两性作家性别的差异使其审美视角有所不同。尽管迟子建一再声称自己的写作并无女权主义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作家的身份使其在创作中总是不自觉地选取女性视角来展开叙述,除《第三地晚餐》外,《鬼魅丹青》以及《额尔古纳河右岸》《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作品均选取了女性视角的叙事策略。
《第三地晚餐》中男性的出场是由女性引领的。小说主要通过女主人公陈青的视角来构筑通篇叙事。以陈青为始,首先出场的是其婚姻生活的伴侣马每文,“睡衣风波”导致的求爱失败拉开了两人间冷战的帷幕,心情阴郁的陈青决意回趟老家;由此将镜头转而聚焦至陈青的娘家,嗜酒且脾气暴躁的陈大柱得以亮相,患有轻微智障的陈墨也被引出;借张红之口陈青得知了父亲的出轨以及母亲迷上了宰羊的场景,由陈青所见将宰羊人引出;在陈青的回忆中初恋男友与徐一加被接连引出;老于、王斜肩也依次由陈青这根叙事主线牵出。也就是说,以陈青为中心向外辐射,这些男性与其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的形象正是通过陈青的所观、所闻及所思呈示出来的。迟子建在此运用了有限叙事,而陈青作为报刊记者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女性独有的感性使得其成为叙事主体的不二人选,这种叙述视角的选取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作者的匠心独具,也令小说的叙事更加细腻。
2.2 女性衬托下的男性生活
首先,以女性之“细”反衬男性之“粗”。文本中一以贯之的是女性的感觉,诸多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描写正蕴含着女性对男性的同情与怜悯。譬如马每文与陈青的初次邂逅,“陈青注意到,马每文的灰色棉绒衫的胸口处溅着几点油污,她暗想这个需要下厨的男人也许已没有老婆了”[3],尽管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但传统社会缔造的“男主外、女主内”意识已经根深蒂固,衣食起居仍然依靠女性操持,马每文棉衫上的油污正说明了他此时的婚姻状况。而陈青在一个午后碰见了退休后的老于,从他的言谈中可见他对退休后的生活十分满意,但陈青关注的却是老于手中提的塑料袋,“一股浊黄的浆汁正从里面像鼻涕一样流泻出来,溅到老于穿着的已被磨秃了皮的黑皮鞋的鞋面上”[3],这里一方面通过陈青的细致观察道出老于生活之不易,另一方面更令人心疼老于的隐忍。
其次,以女性之“长”反衬男性之“短”。小说中的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对婚姻及家庭的忠贞较强。陈师母的隐忍与最终的“杀夫”、陈青多次伪造的“第三地之行”、徐一加妻子得知丈夫出轨后的果断驱逐甚至蒋宜云对徐一加婚外情的披露,无一不是由于她们内心深处对这些男性的失望,而这正是源自她们对爱情的忠诚。陈青更是如此,先后经历了与徐一加有始无终的婚外情以及和马每文的冷战后,她仿佛置身于漫长的寒夜中。陈青从马每文放置在卧室里的机票中揣测到了丈夫对婚姻的背叛,在历经了痛苦的内心挣扎后,陈青开始奔赴自己虚拟的“第三地之行”,尽管她将其命名为“第三地”,实际上却并非寻常意义上的男欢女爱之地,而是为陌生男性免费做一顿饭的场所。无处寄托的爱凝聚在了饭菜中,即便用劣质的调味料烹饪,陈青相信自己用心做出的饭依旧美味。正如马每文对妻子的爱缺乏感受,陈大柱、徐一加等男性更是一边享受着妻子的爱,一边厚颜无耻地寻求刺激,夫妻双方间爱与被爱的严重失衡使得陈大柱最终死在了妻子刀下,而徐一加也落了个被逐出家门的下场。
2.3 女性坚守下的男性出走
陈青的初恋男友、情人与丈夫带给她的分别是性的刺激、爱的觉醒以及爱与性相交融的复杂感受;陈师母的丈夫带给她的则是性的背叛;蒋宜云的情人带给她的是有性无爱的虚妄;徐一加妻子收获的则是丈夫的性背叛。在此需提及,上述女性身上并非没有不足之处,但她们有着共通点,“婚姻——爱”正是她们一致渴求的。陈大柱尽管给了陈师母婚姻,但他的“爱”始终是缺席的,这透过陈师母奴隶般的生活便可看出;徐一加将年轻的蒋宜云视作玩物,与其结婚的说法更是空中楼阁,但他对陈青的确有过爱意,不过其已有的婚姻却是横亘于其间的鸿沟;徐一加带给妻子的正是未婚时的陈青与年轻的蒋宜云所渴求的婚姻,但他的“爱”却在一次次的婚外情中出走了。
《第三地晚餐》中符合女性理想的主要有两类男性,一类以马每文为代表,有着优渥富足的生活;另一类则以王斜肩为典型,尽管物质匮乏但对妻子始终体贴有加。前者能够使女性享受美好的生活,后者可以带给爱人精神上的慰藉,这两类男性较好地将爱倾注进了婚姻生活中,做到了爱与性的统一。其间马每文与陈青虽因性产生了隔阂,但始终存有的爱最终将他召回到了妻子身边。换句话说,男女两性间的和谐与其说依赖于性或者爱,毋宁说取决于两者的兼存。无论是性或者爱的“出走”,都会造成男女两性间关系的失衡。当女性的坚守换来的是男性一次次的“出走”,她们原有的感性便受到了理性的钳制,取而代之的是或激进或平和的抗争,陈青的“第三地之行”、陈师母的杀夫、蒋宜云对徐一加的爆料等正是形式各异的反抗。
3 《第三地晚餐》中男性形象的建构基点
《第三地晚餐》中的男性有着各自的命运轨迹,而他们在迟子建笔下的形象建构,正是源于作者的写作立场与个人气质,总的来说,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建构主要基于三点,分别为苍凉背后的温情写作、理性与节制的情感态度及信任与忠诚,而信任与忠诚则是最不可或缺的。
3.1 苍凉背后的温情写作
苍凉背后的温情写作,是《第三地晚餐》中男性形象建构的第一个出发点。“温情写作”常见于迟子建的创作评论中,它似乎已经是迟子建身上的一个标签,殊不知这温情的底色却是苍凉,正因如此,对这温情的发掘也就愈加珍贵,“也许是生长在极寒之地的缘故,我特别喜欢炉火,喜欢它面对寒冬燃烧时的灿烂和不屈,虽然这样的火也会寂灭。作品苍凉背后的一缕温暖,在我眼里就是这样的炉火”[4]。《第三地晚餐》中男女两性情感悲剧下正埋藏着这样的一缕温暖,使人不至绝望。王斜肩对妻子的不离不弃以及马每文的回归家庭正是迟子建寓于作品中的温情,使得作品的整体基调不至过于感伤。除此之外,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迟子建在其中多次写到陈青为不同男性做饭的细节,“将芦笋切成条,里脊切成丁,豆腐切成块,葱切成段,姜切成丝,蒜切成片”[3],透过如此细致的描写可见作者厨艺之不凡,迟子建的日记《我伴我走》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陈青是迟子建的影子。通过陈青给马每文做饭的前后态度对比可见,男女双方间爱意的表达其实很简单,有时只是一顿用心烹饪的饭菜便足矣。
3.2 理性与节制的情感态度
理性与节制的情感态度则是迟子建笔下男性形象建构的第二个出发点。“我在当代女作家中,写作上是属于那种有理性和节制的,我想我对情感的态度也是可以用上面的两个词来套用。”[5]如迟子建所言,她在《第三地晚餐》中刻画出的是一个个具有立体感的男性形象,他们身上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有着令人批判的地方,而与之相对的女性形象也是如此。迟子建并不是女性主义者,她没有因自己的女性作家身份而有意对笔下的女性进行美化,而是尽量客观地再现当下男女两性在情感上的矛盾与纠葛,女性在诸多方面虽较男性而言更为包容,但同样有其冲动、缺乏理智的一面,迟子建对此也给予了一定的显现。
3.3 信任与忠诚
信任与忠诚可以说是《第三地晚餐》中男性形象建构的总体出发点。小说中的男女两性经过情感的考验,有的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有的则不然,作家对此并没有给出“大团圆”式的结局,但小说最终以马每文与陈青的重归于好作结,并提到了陈青将撕裂的睡衣重新缝补起来这一细节,令人为之动容。这正暗示着相互尊重、彼此坚守才是男女两性达到和谐状态的唯一途径,这也是迟子建所意图表达的。
4 结 语
《第三地晚餐》中涌现出诸多形象各异的男性,迟子建通过叙写他们与不同女性间的交往,将他们的爱情与婚姻观呈示出来。无论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情、名存实亡的婚姻还是历经情感波澜的最终复合,作家始终以冷静客观的笔触书写着他们的人生悲喜。面对纷繁的世相,迟子建在小说中延续了她的“温情写作”传统,小说最终以男女主人公的回归家庭作结,这正是作家心中葆有的一份爱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