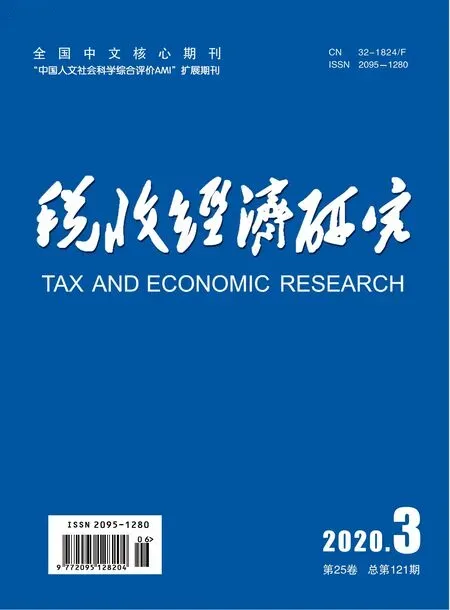论人工智能替代就业的税法因应
◆翟 帅
内容提要:向人工智能征税成为对自动化替代就业的时代回应。税收本质是对财产权人经济利用行为产生之收益的再分配,人工智能税并非一个独立的税种,而是针对人工智能取得、使用以及持有等经济行为进行调整的税法规范集合。我国应根据人工智能发展的水平,充分考虑税收中性原则,妥适调整税制体系。短期内,政府应关注如何以有效的税收政策回应因人工智能普及所引发的失业劳动者的保障与转型。长期看,妥适将人工智能销售、使用、持有等环节普遍纳入税收体系中,最大限度在科技创新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一、“人工智能税”的由来
工业4.0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认知技术的叠加与融合,人工智能(AI)水平显著提升,在枯燥(Dull)、肮脏(Dirty)和危险(Dangerous)的“3D”领域,功能各异的机器人已规模使用,大有“取代”既有雇佣格局的势头。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有分析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将冲击劳动力市场,将会减少至少510万个工作岗位。2018年斯坦福大学卡普兰教授也曾预测,美国注册在案的720个职业,将有47%被人工智能取代。2020年伊始,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宣布未来将借助AI技术降低员工数量,全面实现公司无人化。
严格地讲,技术作为一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本身没有价值负载,但“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客观上减少了企业对人力的需求,促使资本成为分配的主导因素,侵蚀着建立在劳动者之上的所得税税基,威胁到政府税收收入。为保障劳动者生产发展,政府必然需要增加支出为人工智能替代就业的结果“买单”,财政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掣肘财政稳健运行,极易引发“租税国危机”。有观点指出,既然对人类雇员在工厂创造的价值征税,那么对于接替人类工作的机器人也理应课以税收。于是,向机器人征税,向人工智能征税,一时成为化解人工智能冲击就业的时髦方案。
2016年卢森堡议员Mady Delvaux在欧盟议会提出向机器人所有者征税的议案,他认为如果机器人大规模替代就业,政府应向机器人所有者征税,将税款用于资助因机器人应用而失业的人群的培训上,促进再就业,并建议首先向工业、医疗等机器人应用较为广泛的行业开征机器人税。嗣后,欧盟议会以396票反对、123票赞成及85票弃权,否决了该议案。韩国政府认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工业制造、医疗手术、农业开发等领域的广泛使用,降低了企业雇工的意愿,扩大了社会失业率。基于此,韩国开始推动被外界称之为“机器人税”的税改,从2017年起逐步降低对自动化企业的税收优惠,将对投资工业自动化设备企业的税收减免优惠从7%降至2%,引导企业雇佣更多劳动者,并将所得税款用于失业补偿。同年,英国工党领袖Jeremy Corbyn向国会提议开征机器人税,税款用于工人的再培训,但议案最终未被通过。整体看,为抢占技术高地,发达国家对于开征“人工智能税”普遍秉持谨慎态度,抑制人工智能应用的税收政策仍“雷声大、雨点小”。
二、开征“人工智能税”的理论分歧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要求重塑税收制度,不论是称之为“机器人税”,还是“人工智能税”,抑或是“自动化税”,均表征着对自动化设备替代就业的税法调整策略。对于是否调整税制结构,开征“人工智能税”,形成抑制人工智能替代就业速度与广度的税收规范,学界存在泾渭鲜明的两个阵营,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税收立法实践。
支持开征“人工智能税”主要基于以下论据:第一,人工智能替代劳动者,既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也无需缴纳社会保险与所得税,税基减少导致税收收入降低,财政承压增加。对于创造财富的自然人与人工智能,未尝不可一视同仁地征税。第二,人工智能的普及势必减少、替代就业岗位,而资本拥有者将资金投入到机器与设备,不仅可以降低经营成本,还可获得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的减免,加剧了基于资本利得产生的贫富差距。向获利方征收人工智能税补偿失业群体,有助于弥补财政支出。第三,现有财税政策违反税收中性原则,加深了人工智能替代就业的程度。税收中性意味着税法要避免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但各国出于经济发展考量,纷纷制定支持人工智能开发应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开征人工智能税可以中和部分不利影响,回归税收中性原则。第四,征收人工智能税并非反对创新,而是以税收方式缓解人工智能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此外,向机器人征税还可以促进机器人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客观上提升机器人产业水平。
反对开征“人工智能税”存在以下论据:第一,人工智能对于就业的替代,不能仅看短期的阶段性效应,技术进步与失业之间长期来看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人工智能并非淘汰人类劳动,而是将人从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工智能的普及会在研发、维护、管理等岗位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总体来看并不一定减少就业岗位。因此,税收政策应符合社会长期发展脉络,不能阶段性的因噎废食。第二,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税收体制,势必扭曲市场功能,至少理论上会降低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水平(皮得斯,2008)。由于国家之间存在税收竞争,若对人工智能课以高额税收,或迫使拥有者转移至低税收国家,从而对本国的科技竞争力与工业实力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对人工智能征税还与国家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取向相矛盾。第三,不对作为生产要素的工具征税,是税收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诺贝尔奖得主Peter Diamond和James Mirrlees(1971)曾提出应避免向制造其他产品的中间产品征税,否则会降低经济效率,抵消税收的净收益。因此,向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工智能征税,很可能会抑制投资,伤及税源。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诸如掌上银行、登机牌自助领取机、加快文件制作的处理程序等技术均存在替代人工的实效,倘若对机器人征税,亦应向这些技术征税,否则就违反了公平原则。第四,人工智能本身是劳动工具,并非享有权利、负有义务和承担责任的法律主体,没有成为纳税主体的正当性。即使人工智能作用凸显,生产体系中“人”的角色也不可能被边缘化,人工智能的发展仍基于人类的创造。
三、“人工智能税”的可税性反思
可税性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秉承法律上的合法性,经济上的可及性以及税收政策的公平性。因此,探讨对人工智能征税,应充分辨析论证立法技术可否赋予人工智能税收主体的正当性,考察人工智能与就业之既存替代性程度可测量性,以及平衡开征人工智能税与产业发展效率的冲突性,避免对技术应用反应的过犹不及。
(一)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分析
2019年10月美国汉森公司(Hanson Robotics)研制的智能机器人苏菲亚(Sophia)被沙特阿拉伯授予公民身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国籍的机器人。但是,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法律上的主体,一直是法学界备受争议的问题。当前,即使已经非常灵敏的机器人在法律定性上依然属于物,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我国税法明确规定纳税人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因此,就目前而言,机器人欠缺法律主体的资格,不能成为税法上的纳税人。当然,“人工智能税”并非意味着机器人获得了纳税主体资格,成为税法上的劳动者,而是对机器人的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进行的税收调整,本质是资本利得税。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逐渐拥有“思考、学习、决策”能力的机器人亦若隐若现,那么,机器人可否拟制为与劳动者一样的独立纳税主体?在人工智能可否成为法律主体的论证过程中,人工智能被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不具有“自我”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仅能在编制程序范围内实现预设目的,强烈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其不能成为法律主体。强人工智能在编制程序外“自我”决策并实施相应行为,具有辨认能力和独立意志。有学者提出智能机器人系为实现人类特定目的而被设计和生产,并没有自己的独立目的,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中(吴汉东,2017)。持有相反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智能机器人具备主动性与自主性,并不是单纯受人类支配的客体,满足现有法律下主体所必备的本体、能力与道德要素,应当赋予其法律人格(郭少飞,2018)。笔者认为,要不要把智能机器人视为法律上拟制的“人”,归根结底是法律观念的变革,法律上的人仅是立法根据现实需要的确认或者虚拟。奴隶在某一历史阶段也并非法律上的人,即“人可非人”;因经济活动的频繁,赋予企业法人民事主体资格,将其确认为法律上的人,即“非人可人”。
虽然人工智能远不及人类意识活动的水平,但通过对人类逻辑思考模式的抽象与模拟,并将其翻译成数学的语言和算法,人工智能逐渐取得“类人”之具象,可替代人类从事简单、低级的劳动。因此,机器人可否成为法律上的人,不取决于自然伦理,而在于局部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对比,在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取舍。因此,具有工作能力与经济能力的机器人具有“类人化”趋势,既然能够替代人类工作,那么替代人类成为纳税主体亦符合逻辑推演。当然,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也许能够深刻改变某一行业的用工格局,但其全面“接管”用工市场仍有漫长的过程。因此,现阶段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人以法律人格,使机器人成为纳税主体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人工智能与就业替代的关联性分析
从历史发展维度看,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技术进步在替代一部分劳动的同时亦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技术进步与替代就业、创造就业总是此消彼长,对技术进步的最终评价则基于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的相对大小。一方面,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替代作用体现在减少了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在产出给定下,就业需求必定减少。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对就业亦有补偿作用。技术进步替代了哪些工作直观明了,相较之下创造了哪些工作显得较为隐晦。首先,诸如咨询师、设计师等依赖人类独特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应变能力的非程式化岗位难以被技术替代。其次,技术的研发需要大量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技术的扩散也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再次,技术进步还能创造新的消费需要,催生新的业态,这就增加了劳动岗位的供给。此外,技术进步导致产品价格降低,客观上提升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消费的活跃带动投资增加,继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因此,技术进步是一个逐渐发散的过程,技术进步初期所影响的产业规模有限,对就业的替代作用较为明显,在短期内可能降低就业。随着技术的广泛应用,基于新技术的产业链不断完善,长期内可能增加就业。当然,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恐非工业化时代所能比拟。
(三)开征人工智能税的利益平衡
法治建设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内生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中,法治灵活性的本质是与原则性在同一维度下的利益衡量。从目的看,法治的灵活性是以制度规范的特殊例外换取法律原则的实效,与法治原则性所追求的目的相一致;从形式看,法治的灵活性与原则性存在某种程度的相悖,表现为与某些原则精神相违背。细言之,当灵活性对原则性目的实现大于对原则普遍精神的损害时,这种灵活性就是恰当的和可以接受的。当灵活性对原则性目的实现小于对原则普遍精神的损害时,这种灵活性的追求就失去意义。我国早期税收立法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普遍存在内外有别的复合化立法格局,即使有违平等性,却是依据特定情况“不得不”采取的柔性手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保障公平竞争环境,内资外资税法逐步统一化。赋税可以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利杠杆(王成柏和孙文学,1995)。社会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劳动力短缺,促使人们研发使用替代人力的人工智能,因此大多数国家均制定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人工智能税”开征与否,在哪个环节开征,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否积极,需要基于既定的数据对未来发展形势做出准确预测,避免盲目实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四、税法应对人工智能替代就业的调整建议
虽然人工智能替代人力是大势所趋,但是现阶段开征中国版“人工智能税”的现实意义并不大,正如无法通过逻辑推理去证明任何一个宗教命题的真伪一样(周铭川,2019)。但基于新事物发展对未来性命题的讨论,并非毫无意义。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引领社会进步,但技术进步在一定时期并非合乎比例地让所有人受益,人工智能创造的价值属于资本所有者,但衍生的失业、贫富差距等问题却由社会、政府承担,因而税收体制亦应适时调整,避免脱逸现实。
(一)短期建议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指出经济发展源于科技进步与创新驱动,为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短期内发挥税收激励引导机器人产业的风向不会改变。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人工智能精度准、效率高将会成为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不二之选。据统计,到2020年中国企业每万名职工中机器人数量将达到150个。人工智能使用的普及不断淘汰人力,将失业者抛向社会,在一定程度增加政府支出,冲击财政稳定。当下,政府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以有效的税收政策回应因人工智能普及所引发的“技术性失业”劳动者的保障与转型,基于公平正义矫正市场优胜劣分配法则的不足,维护社会平稳发展。以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看,人工智能不宜成为独立的纳税主体,人工智能税仍是向其制造商者、销售者与使用者征税。人工智能涉及的税种集中于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与生产企业的所得税,不论是降低增值税税收优惠,还是提高企业所得税税率,增加企业用于“资本投资”部分的成本,将会削减其投资意愿,最终伤及税源。因此,基于我国税收传统,立法可以适时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妥帖的规范体系:一是反向激励机制,即鼓励企业雇佣劳动者,增加对雇佣劳动者的税费优惠,如同行业中雇佣劳动者较多的企业,可以享受减免“五险一金”配套缴纳义务,减轻企业雇工成本;抑或企业所得税中提高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与工会经费支出的扣除比例,助力劳动者转型升级。二是要求企业缴纳因人工智能应用而免于缴纳的社会保险支出,并专款用于失业工人的教育培训和失业补贴。三是针对使用人工智能创造的价值或增加值征税,将机器人视为劳动者,国家介入机器人使用阶段创造的经济效益。当然,从调节收入分配视角来看,“人工智能税”要避免僵化,应结合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在行业发展中的趋势确定合理的税基与税率。
(二)长期建议
制度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无人驾驶到机器人保姆,人工智能系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人类的认知水平,人工智能辅助甚至替代人类进行决策,不再是空中楼阁,借助人工智能从事单调、繁重、危险的工作,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表示出于降低税负的考量,资本所有者会将资金转向购置机器,造成政府税收不足的困境。从量能课税和税收公平的角度看,租税的人格化代表着现代税法的发展方向。税收的本质是国家治理体系,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税收主要源于间接税。随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不排除未来将机器人销售、创造价值、使用、持有等环节普遍纳入税收体系中,最大限度在科技创新与保障劳动者之间取得利益平衡,确定合理的税率。在未来的强人工智能时代,摆脱了只属于企业资本的附庸,人工智能机器人作为独立的纳税主体也未尝不能实现。当然,从方法论意义上,为减少社会转型的负担与成本,开征“人工智能税”在具体策略上应选择“试点试错”模式,避免改革风险在更大领域内蔓延,增加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