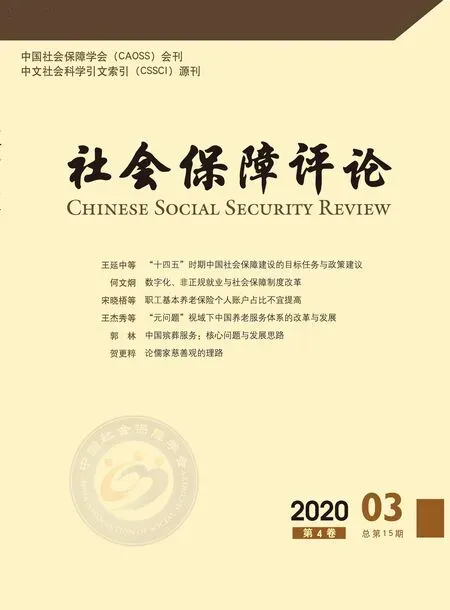慈善市场化的意涵、局限及行为选择
朱光明
汶川大地震以后,中国慈善事业及其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逐渐觉醒,开始寻找自身发展的出路和方向。作为慈善事业发展方向主张之一的“慈善市场化”,是当前中国慈善领域非常热门的话题。人们在探讨“慈善市场化”时,一般采用“公益市场化”的表述。这涉及对“慈善”概念的理解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慈善是指民间自发形成的、针对弱势群体实施的社会救济活动①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6 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慈善已经超出了救济的范围。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把“慈善”界定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提供服务的方式,依法自愿开展的面向弱势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的非营利性活动;从外延上看,慈善不仅指向扶贫济困、扶老救孤、助残恤病、救灾救难等各种救济活动,也包含促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事业发展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3 页。。这一立法表述就把慈善与公益视为内涵与外延一致的语词。易言之,慈善事业是指第三部门中排除了成员间互益性活动的非营利性事业即公益事业,有时也合称为公益慈善事业。因此,“公益市场化”与“慈善市场化”也是内涵与外延均相同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还常会把“公益”理解为公共利益、社会福祉、人类价值等更宽泛的意涵。比如“商业是最大的公益”的说法,所要表达的不是“商业是最大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慈善事业”,而是主张商业是实现公共利益、社会福祉等的最主要方式。市场或商业能够实现公共利益或社会福祉等,是不存在争议的客观社会现实。因而,在公共利益或社会福祉意义上探讨公益的“市场化”或“商业化”,并无实际意义,也不是当前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有所争议的命题范畴。“慈善(公益)市场化”命题要探讨的是慈善(公益)与市场化的兼容性及其实践的合理性,旨在洞察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角色定位与发展方向,为当下的慈善(公益)实践做出理性的行为选择。为避免“公益”的认知差异和概念变换,保证阐述的严谨性和一致性,笔者在下文中主要采用“慈善”的表述方式。若无特别说明,文中出现的“公益”①在下文中,笔者直接援引他人观点原文时,仍保持其“公益”的语词表述;对他人观点进行归纳阐述时,则根据语义改为“慈善”或“公共利益”的语词表述。一词与“慈善”同义。
一、慈善市场化的概念厘清
“慈善市场化”曾引发了被称为“两光之争”的业内知名人士之间的论战。无论是“两光之争”本身,还是由此引发的评论、解读和新的争论,任何一方的观点诠释都有其合理性,最终结论却大相径庭,导致“慈善市场化”成了萦绕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当代谜题。明晰“慈善市场化”的概念,是定纷止争的前提和关键所在。
(一)慈善市场化的若干概念解析
在“两光之争”中,徐永光是慈善市场化的重要倡导者,主张将商业市场模型作为理解和把握慈善事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视角,从市场主体、要素市场、市场规则和市场影响等方面,对慈善事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②徐永光:《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27 页。,追求慈善项目、慈善组织和慈善生态的不断优化,却未曾对“慈善市场化”做出明确的概念界定;坚持慈善利他性的康晓光,认为慈善市场化包含去行政化③徐永光强调慈善市场化包括去行政化和去道德化。在现实中,行政化与道德化的阻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不局限于中国公益发展领域。因而,去行政化与去道德化,应属于“慈善市场化”主张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慈善市场化”主张的要素内容。更何况,如下文所示,当前中国慈善发展也不一定采取去行政化的单一态势。、引入竞争机制、慈善组织吸纳企业管理方法、慈善项目设计与运行吸纳商业方法等4层涵义④康晓光:《义利之辨:基于人性的关于公益与商业关系的理论思考》,《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8 年第3 期。,也没有给出“慈善市场化”的规范性定义。目前,关于“慈善市场化”的概念描述主要有两种:有人认为慈善市场化是“一种运用市场的理念、手段与方式对公益进行重构和塑造,以实现公益行业的现代化、专业化、高效化为目的,进而推动整个公益行业发展的思潮与实践,以去行政化、效能至上、消费话语、技术崇拜、数据霸权、服务理念为基本特点”⑤曲晨:《美丽的新世界:公益的黄昏——公益市场化现象与思潮批判》,中国发展简报: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8466.html,2019 年12 月20 日。;也有人认为慈善市场化是指在慈善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来改革和完善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运用市场运作的平等、契约、竞争择优、创新、资源运用的高效等理念与价值,达到更好地满足民众需求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⑥邵丹丹:《刍议公益市场化的困境与突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S1 期。。这两种定义强调了慈善事业发展要借鉴市场化的商业模式,但在慈善事业的“非营利性”问题上都语焉不详。
与慈善市场化相似的概念是慈善商业化。有的把慈善商业化指向慈善机构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10 条之规定,慈善组织在中国大陆地区是特定法律概念,特指经民政部门认定为“慈善组织”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不包括未经认证但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为了涵盖上述两类组织,并避免混淆概念,本文使用“慈善机构”的表述,而不使用“慈善组织”的措辞。自己开展的或辅助企业开展的营利性的商业性活动②周子凡:《慈善商业化的法律思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1 期。;有的把慈善商业化界定为慈善机构以商业机构运行理念和方法为参照,开展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经营管理活动③王继远、陈雪娇:《商业慈善化与慈善商业化的法律规制》,《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6 期。;还有的把慈善商业化理解为慈善机构为增加收入、提高运营效率和实现慈善目标的营利性与非营利经营活动之和④黄春蕾、郭晓会:《慈善商业化:国际经验的考察及中国发展路径的设计》,《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4 期。。上述概念界定的内涵和外延对非营利性原则似乎是有所舍弃。如果承认慈善市场化与慈善商业化是围绕同一主题展开的论述,那关于慈善的非营利属性问题,无疑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综上而论,慈善市场化的主体可能包括非营利的慈善机构和营利的商业机构两类。慈善机构可能会为提高自身专业化、规范化和效益化,进行战略规划、机构设置与治理、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考核等活动;可能为筹集资金举办各种活动,诸如义卖、义演、晚宴、公益广告、行为艺术等;也可能开展针对慈善对象的收费服务;还可能开展面向非慈善对象的销售商品(含委托他人特许经营)、收费服务(含政府采购服务)、创办企业、开展投融资等经济活动。商业机构可能为慈善机构提供设备、筹款、技术、人力、传播、法律、财务、评估、投资等产品或服务;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开展营销活动,诸如无偿服务行为(如免费试用或体验)或准慈善活动(如销售配捐);以经营利润为重要指标,采取社会企业、公益信托、影响力投资等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或提供民生服务。
假定上述活动形式都属于“慈善市场化”范畴,以慈善机构为主体的慈善市场化包含无收入的管理活动和有收入的经营活动,其中有收入的经营活动涵盖筹款活动、对受益人服务收费、不以受益人为对象的商业经营和投资活动等3 类;以商业机构为主体的慈善市场化包含服务慈善机构和服务社会大众的两类,其中服务社会大众的活动又分为以营利为目标的经营活动和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经营活动。作者认为,不论商业机构的客户性质及其人数多寡,只要行为主体以营利为目的开展活动,就应从慈善活动的范畴内剔除。在一般情况下,“慈善市场化”的主体仅限于慈善机构,商业机构不具有法律拟制的公益属性和捐助法人地位,除非其坚持以非营利方式运行,否则就不是慈善市场化的适格主体。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等商业模式,指向了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涵义,却无视“非营利”这一刚性的约束条件,应视为市场的“慈善化”选择,而不是慈善的“市场化”安排。慈善市场化若包含以否定慈善的本质属性为内容的种种阐述,则把慈善推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中,否定了“慈善市场化”的逻辑自洽性。
(二)慈善市场化的概念界定
1973 年,美国学者列维特提出“第三部门”的概念⑤秦晖:《从传统民间工艺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中外慈善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香港)1999 年冬季号。,建构了一个“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社会分类逻辑范式。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都是人们用于解决和处理某些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手段,3 个部门之间的边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情势变更,还会出现一定变动,但各自的基本属性和核心特征不会发生变化。就常态运行而论,政府是唯一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形态,而市场或企业部门是唯一以营利为目的的部门。因此,坚持慈善的非营利属性,是保证慈善机构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慈善市场化”阐述之逻辑严谨性和周延性的前提。凡是具有营利结构模式的经营活动都不属于慈善市场化的范畴,只有以非营利方式开展活动的慈善机构①实践中,这类机构包括3 类:一是登记为非营利性法人,如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二是进行工商注册登记,股东确定不分红,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企业;三是无法人资格,但开展慈善活动的各类机构,如志愿者组织。,才是“慈善市场化”命题所探讨的行为主体。由此,慈善市场化是指慈善机构借鉴商业经验,为保持自身健康稳定有序的成长,实现组织架构、财务收支、人事管理和服务能力等方面的专业化、精细化、规范化和高效化,更好地服务和实现机构的价值诉求和社会使命而开展的非营利性的运营管理活动及其态势。
在外延上,慈善市场化包括两方面的活动:一是机构业务范围内的各种非营利管理活动,包括慈善劝募、项目运营和机构治理等;二是与业务领域无关,但有利于增加机构收入和改善财务状况的商业性经营活动,除了获得的收益不分红外,运营方式与一般商业机构无异。在理论上,慈善机构从业者的职业发展需要、同类机构的竞争、捐赠人的要求、受益人的反馈、志愿者的成就感和社会舆论监督的压力等都可能会迫使慈善机构不断改善运营效率和提高服务质量。倡导慈善市场化,是主动向商业机构学习管理经验,致力于提高慈善事业良性运行的效率,改善慈善机构动员、整合和配置社会资源,达成机构使命的效能,即“动员私人资源,包括金钱、时间、社会资本和企业家才能,以改善我们生活的世界”②马修·比索普、迈克尔·格林著,丁开杰等译:《公益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50 页。,而非改变慈善事业的基本架构和生态原理。
总之,解决“慈善市场化”争议的核心点在于慈善是否是与商业有着本质区别的存在,非营利性是否作为慈善的本质属性和开展慈善活动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非营利性原则不禁止慈善机构向服务对象收取一定的费用,而要求任何人不得对慈善机构的收入以利润形式进行分配或变相分配,慈善机构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只能依法继续用于公益目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剩余财产索取权。慈善市场化若意味着对非营利的慈善活动进行营利化改造,即指向营利性诉求的商业本质,会导致商业牟利行为披上慈善的“外衣”,就背弃了慈善的本质规定性。
二、慈善市场化的社会洞察
从社会发展逻辑上看,慈善市场化是社会分工在慈善领域的达成,是工业革命以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的一种反映。“社会中的组织趋向理性,目的在于生产效率提高,管理效能增加”③彭怀真:《社会学(第2 版)》,中国台北洪叶出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2 年,第290 页。。其背后有着深刻的资本逻辑:当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一切事物都需要依靠市场来获取,就形成了市场对整个社会的强迫力,产生“竞争、积累与收益最大化的迫切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持续的发展生产力的系统性要求”①埃伦·伍德著,夏璐译:《资本主义的起源:学术史视阈下的长篇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72 页。。慈善机构应“借鉴商业模式,形成完善捐助体系,科学、高效地管理和分配善款以有效解决社会问题”②Lawrence J. Friedman, Mark D. McGarvie, Charity, Philanthropy and Civility in Americ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2.之类的市场化主张,在本质上是资本话语在慈善领域的呈现和延伸。当前社会热议的“社会企业”“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投资”“慈善资本主义”等都属于这一资本逻辑的题中之意和表现形式。
(一)慈善市场化的滥觞及发展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是现代慈善事业的重要实践者和奠基人。在他看来,慈善是一个财富管理范畴的命题,旨在“使富人与穷人之间依然可以保持兄弟情谊、和睦相处”③安德鲁·卡内基著,杨会军译:《财富的福音》,京华出版社,2006 年,第1 页。。但是,现代慈善事业不再局限于贫困人口的具体救济,也关注贫困背后的动因。现代的“科学慈善”理念认为,贫穷是可以被识别、锁定和处理的问题,甚至是可以被人类最终消灭的社会现象,人们认知和把握社会问题存在的根源,就可以对症下药,最终实现药到病除④Richard Lee Klopp, The Rhetoric of Philanthropy: Scientific Charity as Moral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2015, p. 4.。为了达到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的效果,卡内基等美国慈善家创办了第一批以现代基金会为代表的组织健全的慈善机构,“最现成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就是借鉴他们所熟悉的大企业:设立董事会,任命负责人,视需要设立办事部门”⑤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第28 页。。这也成为了现代慈善事业对市场化探索的最早尝试。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概念开始兴起,“一些从事发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改变了它们对管理的想法,并急于从商业界引进最新的管理技巧以得到快速的解决办法,来了解它们在管理上的弱点”⑥David Lewis 著,冯瑞麟译:《非政府组织管理初探》,中国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第16 页。。此后,慈善市场化的发展轨迹不单体现了具有商业背景的慈善机构创办者的职业路径依赖,也开始表现为职业化的慈善机构管理者和从业者的主动行为选择。有学者发现,慈善机构实施的很多扶贫项目最终导致了受助人对慈善捐赠或服务的严重依赖,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和活力,不仅没有达到帮助效果,反倒造成了受助人及其所在社区社会生态状况的恶化,出现了“毒性慈善”(Toxic Charity)的现象⑦Robert Lupton, Toxic Charity: How Churches and Charities Hurt Those They Help,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1, pp. 3-6.。为克服这一问题,一些慈善机构开始引入“小额信贷”这一商业模式,作为实施社区项目的重要方式⑧Robert Lupton, Toxic Charity: How Churches and Charities Hurt Those They Help,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1, p. 113.,以实现社区发展和受助人能力的成长。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就是以对孟加拉国农村妇女开展小额贷款项目而著称。在实践上,慈善市场化已不局限于小额信贷领域,也包括疫苗等药品研发和农业生产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践①Olivier Zunz, Philanthropy in America: A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85-287.。为了摆脱传统慈善模式的桎梏,更多的人开始致力于探索新的慈善模式,慈善事业“不再限定为非营利,也可以通过营利的事业去做”②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第402 页。。
进入21 世纪后,慈善市场化在操作方式上开始嵌入了各种金融手段,比格莱珉银行的模式更复杂。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个国际公益项目为例③Andy Kessler, "Give Philanthropy the Market Te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 2020, A15.,2015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印度塔塔集团合作设立了一个慈善特许基金,这一基金的本金来源为30%的股权融资和70%的债权融资,股权部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塔塔集团按2:8 的比例分配,塔塔集团保持约14%投资回报,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只要求略有盈余或平衡即可。该基金主要是以优惠价格对印度贫穷地区提供太阳能电力支持。当地居民有了电力支持,就可以开展各种生产经营活动,比如开办商店和创办木材、小麦、蜂蜜加工、芥末油生产和水净化等企业,以此获取收入来支付电费。这样既实现了当地居民的脱贫,又实现了公益项目的规模扩张和可持续发展。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电力供应属于公共基础设施范畴。在这一案例中,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缺失,由大基金会和大企业联合投资补位,体现了慈善机构的商业运作能力,也体现了资本的逐利性无处不在。通过慈善的媒介作用,非民主的资本力量(如在美国)实现了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外交、宗教和公共教育等领域广泛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④Philip D. Byers,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That Our Resources Will Allow: The Black Church and Foundation Philanthropy, 1959-1979," Religions, 2018, 9(8).。对慈善从业者而言,“慈善市场化”的主张及其实践,除了可能满足慈善项目实施有效性这一目标,还通过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促进自身财务运作的稳健性和安全性,克服对大企业或大基金会捐赠的过度依赖。慈善机构急于摆脱资本对慈善活动的控制,却选择了自己变成商业资本的方式,表现出慈善立场的不坚定和对慈善模式的不自信,也印证了资本逻辑在现代慈善领域中日益强势的话语地位。
(二)慈善市场化的中国语境渊源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慈善事业在中国大陆地区曾沉寂了近30 年的时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慈善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同步启动,却有着迥异的逻辑进路。市场经济领域的经营主体是以去行政化为基本线索,无论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改革,逐步脱离计划经济模式,减少行政体制对日常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慈善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脉络,却是一种行政化建构的“逆操作”。1981 年,第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慈善机构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创办、具有编制的事业单位。这些官办机构曾一度垄断着中国慈善资金的捐赠通道和支配调度,其慈善活动成为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职能的一种延伸,是政府动员、整合和分配资源的一种方式,即政府部门通过向社会各界筹款的方式,来缓解因财政资金紧张造成的社会福利投入不足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慈善事业是官方先期孵化的产物,而不是源自民间自发探索的结果。中国慈善事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具有独立地位,即使慈善的民间性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并不会随之自然解构,人们对慈善事业的认知与分析仍然会按照“政府-市场”的二元结构进行阐述。因此,中国慈善市场化是以政企分殊为逻辑起点,而不是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三分法为范式。慈善机构需要从编制上脱离官方序列,实现行政脱钩,摆脱政府不合理干预,进而提出“慈善市场化”的发展主张,仿效了经济领域“弃政从商”的进路模式。慈善市场化与去行政化如影随形,根源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脉络的特殊性。但是,将去行政化视为慈善市场化的内涵要素,既不具有语义上的自洽性,也不具有实证层面的正当性,甚至行政化色彩重的慈善机构可能具有优异的业绩表现①褚蓥:《反思慈善改革:慈善的政治属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81-88 页。。去行政化主张的现实基础已经有所动摇,但去行政化仍是慈善领域中具有主导性的舆论倾向,成为具有鲜明伦理色彩的公益主张。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任何能够对人的态度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主观或客观属性的事物,抑或人对其表现为绝对服从的现象,都可以被界定为具有宗教性②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储昭华等译:《心理类型——个体心理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年,第241 页。。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呈现了巨大的爆发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慈善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威力和效能近似宗教的高度信赖。当下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存在种种不成熟的表现,如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法律法规不健全,专业人才匮乏,慈善捐赠量小,运行效率不高,缺乏竞争力,管理不规范,社会贡献度低等。这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基础差,起步晚,缺少时间积淀和经验积累有关。慈善事业的从业者和参与者在当下这一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又急于摆脱现实的困顿,就有了向外部寻求解决之道的冲动。因此,有人提出慈善市场化主张,倡导对市场经济主体成功经验的学习和借鉴,以突破行业发展瓶颈,有其客观的现实性,也产生了较大的行业影响力和感召力。与此同时,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缺乏本土化的经验积累和参考范式,借鉴国外经验成为必然的选择。美国的慈善事业成熟发达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引起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注意,且向世界头号强国学习,也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隐喻和情感诉求。人们表现出对美国慈善发展经验和模式异乎寻常的关注甚至是信赖,中国慈善发展也呈现出相当明显的美国色彩。一方面,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等积极参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主动为中国慈善发展提供资助、培训和交流机会;另一方面,中国慈善机构非常踊跃地前往美国考察、取经,对美国的相关范式和理念,如“慈善资本主义”“影响力投资”等进行探讨、借鉴和推崇,中国慈善领域也就出现了模仿美国范式,引入市场理念与工具,以提升慈善事业的市场化、效率化、专业化的创新思潮③褚蓥:《市场自由还是政府主导?——论中国公益创新的出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 期。。
三、慈善市场化的局限性
市场是实现公共利益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方式,但这不意味着市场化的手段必然能解决慈善事业所面对的问题,蕴含商业开发价值的慈善项目案例在实践上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慈善市场化作为慈善发展的一种探索,其增长空间有待进一步实证,不能武断地将其界定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和方向,应对其局限性进行深刻反思。
(一)“市场失灵”的存在不容忽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法则,实现效率最优化的资源配置。企业之所以能在效率方面相对优于慈善机构与政府,就在于企业受制于市场竞争的压迫性。这种压迫具有两面性:一是高效率的实现;二是“市场失灵”的出现,即市场对资源配置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会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行业垄断、贫富分化等问题,而且市场主体基于利润和风险的考虑,一般不会涉足没有经济效益、投入过大或周期太长的领域。慈善机构效率相对较低的观点,有其客观性,不排除行业内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却也不能忽略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慈善机构需要考虑效率,但效率最大化并非其本质属性。作为以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为使命的组织类型,过分强调效率性,不只是对人类理性改良社会的自信,还是对人为加快改良进程的迷思。慈善事业过分强调竞争性、规模性和扩张性等,未必是最优的理性选择。二是市场经济中具有高效率的商业机构是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的胜出者,不等于现存的所有或大部分商业机构在运行上具有高效率。
(二)市场化逻辑仅为分析慈善事业的认知工具
以市场运行结构为参考系的范式模型,不仅可以分析慈善领域,也可以分析政府部门。人们可以把捐赠人、慈善机构、管理者、从业者、受益人分别视为慈善事业的投资者、企业、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①徐永光:《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27-28 页。,也可以把政府的纳税人、政府机关、官员、普通公务员和民众如此类比,甚至宗教社会学对宗教也进行了这样的分析②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28-29 页。。慈善机构和政府同商业机构一样需要金融、人才和技术支持服务、开展宣传营销③徐永光:《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32-33、35 页。,但慈善机构与政府区别于商业机构的共同属性是非营利性。著名经济史学家波兰尼指出,19 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嵌入市场经济而变成市场社会④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的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156-157 页。,才形成了对市场的完全“依赖性”⑤埃伦·伍德著,夏璐译:《资本主义的起源:学术史视阈下的长篇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72 页。。人类对管理实践的探索早于商业经济的出现,市场经济逻辑并非人类社会的原发逻辑。商业管理的优秀经验成果,不能全部视为商业领域的独创;卓越管理模式的引入,并非只有商业领域对其他领域的输出,而商业领域独创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其他领域。主张和强调对商业机构模式的借鉴,佐证了市场经济模式的主导效应,体现了“市场社会”中资本话语的优势地位。但是,慈善市场化不能违背慈善本质及其发展的固有规律,只能把市场化认知范式视为一种方法论,而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更非慈善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和规律的归纳和提炼,不能将慈善市场化看作是分析、检验和评判慈善事业发展的唯一尺度。
(三)市场化模型适用的尺度问题
慈善领域不排斥行业内的竞争,不否认慈善与商业之间存在模糊的灰色地带。这一地带的存在以慈善与商业的本质差异为前提,从实证角度也无法推定慈善机构与商业机构必然选择趋同性的发展走向。“公益市场化所遵循的规则和商业市场规则如出一辙”①徐永光:《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34 页。的论断所指涉的,应是慈善(公益)机构进入商业竞争领域,或者购买并接受商业服务时,必须接受相应的市场规范,遵守市场契约精神,但不能无视商业领域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导向的客观属性,把慈善市场化理解为慈善机构的企业化转型。“公益市场也要遵循等价有偿原则”②徐永光:《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36 页。,意味着慈善(公益)行为会有相应的对价,但慈善(公益)服务的提供者和受益者所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无法进行数据量化,更难以效仿商业活动进行成本收益的货币化测算。慈善项目可以选择适度收费,收费并不是对慈善非营利属性的必然改变或否定。由于并非所有人都有付费能力,是否收费应是一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选项而不是必然的运行原则③彭海惠:《也论公益市场化》,中国发展简报: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8604.html,2019年12 月30 日。。项目收费的功能和效果也不宜被夸大。以价格机制为媒介,刻意追求慈善市场化,可能导致服务供给偏袒具有支付能力的群体,维护或加剧原有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关系。慈善项目也可以探索自身的标准化、示范性和可复制性,实现规模化的项目拓展,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服务有效供给,但规模化并不是商业领域的独有特征,甚至不是商业经营的必然选择(如高端奢侈品消费)。何况在“公益规模化在美国也是个难题”④徐永光:《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45 页。的情况下,把慈善(公益)规模化视为一种必然规律和未来趋势,缺乏实证基础和逻辑说服力。
总之,“慈善市场化”主张的适用有其局限性。以营利为目的、追求利润的市场逻辑无法在以非营利性为基本特征与原则的慈善领域贯彻。有学者指出了慈善资本主义实践案例的局限性:从业务领域上看,主要集中于疫苗研发等医疗服务、农业技术开发和小额信贷,这些实践及其研究往往忽视了所在国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及其作用,且慈善资本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手法,对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障碍几乎无所作为⑤Michael Edwards, Just Another Emperor?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Philanthrocapitalism, New York,Demos & The Young Foundation,2008, pp. 33-38.。另有学者指出,成功的小额信贷项目要求借款人具备工作勤勉的职业伦理、创业的精神素养、稳定的家庭和社区网络的支持,而美国的贫穷社区不具备这样的要素条件,导致小额信贷模式在美国无法落实⑥Robert Lupton, Toxic Charity: How Churches and Charities Hurt Those They Help,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1, pp. 120-122.。
四、慈善市场化的行为选择
慈善被称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平衡器,其自洽性在于慈善是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矫正。慈善对公民道德建设具有正面导向功能,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①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252 页。。在慈善议题上,人们不能把客观存在的实然状态,界定为道德上可欲的应然诉求。人有趋利避害的利己性,却不能时刻扮演精于算计的“商人”角色,也会有对道德崇高性的追求和服务社会的利他行为,中华文明在这方面更是有着不可动摇的深厚文化根基②康晓光:《古典儒家慈善文化体系概说》,《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4 期。。总之,慈善不回避也不反对动机利己性的存在,利己与利他具有一定的相容性③杨方方:《慈善力量传递中的义和利:相融与相生》,《社会保障评论》2019 年第4 期。,但必须坚持和贯彻对人性积极正面的道德引导。
(一)树立务实稳健的慈善发展观念
中国慈善事业整体表现不成熟、不规范、不专业,是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和问题。全民的慈善关注度和参与意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加强慈善文化传播和教育,但不能操之过急。中国慈善发展的制度创新、法律法规的健全和政策措施的激励,需要社会整体的成熟度提升作为基石,慈善事业生态的良性化更需要一个较长时间周期来孕育。提高受众的满意度,更有效、更精准地满足服务对象,是慈善机构应坚持的立场,但慈善机构不能一味地取悦捐赠人、受益人或其他利益相关方,应该坚持自己对社会价值的正向引导作用。慈善机构不能过于功利地计算短期的成效,需要有发展事业的忍耐力,长期投入以夯实基础,勇于为社会发展探索试错。
(二)设计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
慈善机构和慈善项目的成功主要表现为其使命所指向的社会价值的创造、促进与发展。慈善市场化必须坚持慈善的价值导向功能,不能屈从商业思维模式及其形式规则。慈善效果的呈现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审视慈善机构创造或促进了何种社会价值及其程度,在短时间内,面临着缺乏实证基础和量化指标的现实挑战。慈善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慈善机构效能评判的困境,却容易导致慈善机构把重点落实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上,如规范的组织结构、良好的财务状况、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与号召力、机构运行的可持续等。这些只是慈善机构使命达成的有利条件,却不足以验证慈善目标的实现。慈善机构价值使命的实现应保持“日拱一卒”的耐心,不忽视机构运行效能等客观需要,只是应把关注点从慈善机构自身转移到受益群体及其社区的状况改善上,不局限于供给者和受益者的主观感受,更重要的是形成客观准确又不失灵活的科学评估标准。
(三)建立理性规范的行业问责机制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慈善机构及管理者可能只顾眼前利益,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自我美化,来掩盖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以获取财务上的最优结果,或以欺骗的方式获取公众信任,来追求慈善机构管理者的狭隘私利。首先,要不断健全慈善机构和慈善活动的透明机制,拓展和加深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信息公开的灵活性、多元性、高效性和便捷性,优化税务征信、财务审计、登记管理、项目监控和机构评估等信息,使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有的放矢;其次,加强慈善文化的传播、慈善意识的培育、慈善知识的教育和慈善技能的培训,让社会各界真正了解慈善运行的客观情况,知晓并洞察慈善发展的基本逻辑和规则,掌握科学理性的慈善常识,尽可能对慈善事业做出客观严谨的判断,并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优化慈善事业的良性竞争;再次,建立科学有效的奖惩机制,对优秀的慈善机构进行表彰,对创新性的项目予以宣传推广、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建立一整套规范有效的保护合法、制止非法和打击犯罪的问责机制。
(四)设置过度市场化的制度“防火墙”
过度的慈善市场化,塑造市场逻辑的“商业道德神话”,必然会导致慈善异化,走向慈善的对立面。关于资本与利润,人们都非常熟悉马克思援引托·约·邓宁的一段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871 页。如果过度地推进慈善市场化,否认慈善的非营利属性,鼓吹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创新模式,甚至倡导“公益铺路-商业跟进-产业化扩张-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问题”的社会创新五部曲②徐永光:《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54-58 页。,本质上是把非营利的慈善项目转变为营利的商业项目。这一转变是否具有可行性和普遍性有待论证,但问题在于这一“创新路线图”会导致巨大的伦理危机:慈善机构承担了本应由商业资本承担的早期投资风险,并为商业项目提供了道德背书,进而沦为商业机构的附庸,其自洽性和正当性会受到质疑。慈善机构在制度设计上的非营利要求,否定了追求利润的可能性,是对人的自私性的深邃洞察和刚性约束,也是对资本在慈善服务领域寻求增值空间和市场扩张的有效遏制。
五、结语
近代以来,现代慈善发展的每个黄金时代都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在时间上高度吻合③马修·比索普、迈克尔·格林著,丁开杰等译:《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26-29 页。。现代慈善事业既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对其进行改良和矫正的重要机制。慈善市场化不应该也不能否定慈善机构的存在价值,更不能成为对慈善事业非营利性发展模式的批判武器。影响力投资是原有的市场、政府和慈善机构都无法完全满足人类需求,不能提供完美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提出的突破传统方式来组织企业、投资和慈善的系统创新之主张,并未否定慈善机构当前和今后的存在价值④安东尼·巴格-莱文、杰德·艾默生著,罗熙昶译:《影响力投资:创造不同,转变我们的赚钱思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2 页。。“社会企业不是慈善。要点在于,社会企业获取的价值,包括财务上的和社会性的,都是通过企业的运营来获得的,而不是通过慈善。”⑤德纳·布雷克曼·雷塞、史蒂文·A·迪恩著,方懿、李攀译:《社会企业法:信任、公益与资本市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188 页。即使把上述的“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均视为“慈善市场化”的探索,就慈善事业而言,这些探索也是慈善领域的一种增量改革,即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新一代企业家投身慈善领域后,开展的慈善范式创新,而不是原有慈善机构的集体“倒戈”。面对激烈的市场自由竞争,社会企业与一般商业企业相比,并不具有明显优势,只能看作是特殊的商业投资领域,并不能认定为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因此,坚持慈善事业的基本逻辑和发展路径,适度借鉴市场范式,才是把握慈善市场化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