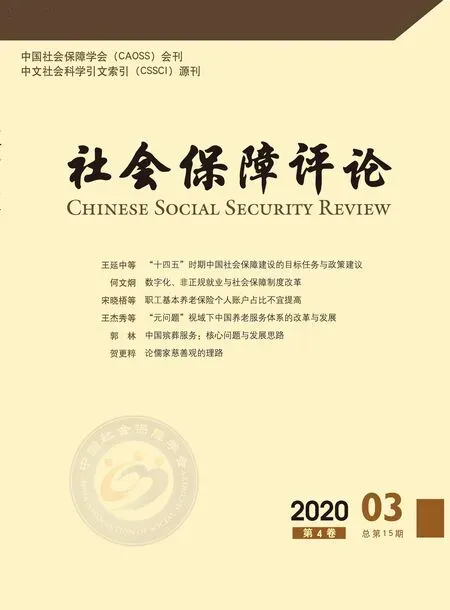论儒家慈善观的理路
贺更粹
慈善作为利他公益行为,离不开“价值观念与慈善文化的支撑。”①康晓光:《古典儒家慈善文化体系概说》,《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4 期。作为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慈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倡导“仁爱”的慈善观。“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论语·颜渊》篇载孔子曰:“仁者,爱人。”《说文解字》释:“仁,亲也,从人从二。”这说明,“仁”针对的是二人以上的人际关系,它要求人要对他人关爱。简言之,儒家的仁爱有三层蕴含:其一,“亲亲”;其二,“仁民”(仁爱他人);其三,“博施济众”(博爱)。仁爱构成了中国传统慈善思想资源的核心价值理念。
本文首先从儒家慈善观的理论基础——民本思想切入,对儒家以民为本的仁爱慈善观在国家政治实践中的体现,即儒家规定给人君的政治实践——仁爱人民之问题予以阐释,在此基础上论述儒家仁爱慈善观的具体落实——古代官方赈贫恤患的慈善实践与乡绅为善乡里的民间慈善实践。
一、以民为本:儒家慈善观的根基
“民”作为单音词,《说文》解为“众萌”。“萌”即“氓”,故又训“氓”为“民”②[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订:《说文解字》(附检字),中华书局,1963 年,第265 页。段玉裁注曰:“萌古本皆不誤。毛本作氓。”参见[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 年,第633 页。。其与后来作为复音词的庶民、黎民、丘民等大致相当,而更为通俗的称呼,则是使用至今的民众、人民等称谓。“本”即树木之根。根本稳固,树木才能枝繁叶茂。国家如同一棵大树,人民则是这棵大树的根本。人民安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即所谓“本固邦宁”③[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77 页。。传统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慈善公益行为,可以说都是围绕“民”这一根本而展开,强调以民为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总体上是由《尚书》的“民惟邦本”①[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77 页。“敬德保民”②“敬德保民”思想贯穿于整部《尚书》。如《蔡仲之命》篇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泰誓》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召诰》篇载:“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康诰》篇载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矜寡……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等等。参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453、274、277、402、350-360 页。和孟子所称的“民贵君轻”③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第328 页。构筑起来的,后来被概括为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④民本或重民的思想,并不为儒家所独有,先秦诸子大都有类似的观念。譬如墨家讲“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以民为本也”(《墨子·内篇·问下》);老子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吕氏春秋》言“宗庙之本在于民”(《吕氏春秋·务本》);等等。
在君民关系上,君要养民保民,为民做主。这点殷人早有表述:“施实德于民”,“古我前后(先王也),罔不惟民之承”。⑤[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29-230、235 页。其意为过去的先王皆以拯救和保护民众为目的。君民关系的这种界定,在于肯定“君”以服务“民”为本,国家政治要以民为本。因此,尽管君是民之主,民却是君之本,所谓“民者,君之本也”⑥[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春秋榖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55 页。。“天生民而树之君”,目的是“以利之(民)也”。故而,君主的使命在于养护人民,即“命在养民”。并且,君主的利益是从属于广大人民利益的,人民获利,君主必然也在其中,这就是“苟利于民,孤(君主)之利也。”⑦[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546 页。
不过,“君”不仅有对下之“民”的关系,也有对上之“天”的关系。《尚书·洪范》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这是说,上天关爱人民,所以选立天之子,使其身兼君师之职,协助上天安定民生,治理天下。天子犹如百姓的父母一般,教养百姓。但在同时,也意味着人间的权力渊源于上天,是天之所命,所谓“天之历数在尔躬”⑧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第207 页。也。战国时期的孟子引《书》论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⑨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第31 页。其意为,上帝(上天)设立君、师,其职责是协助上帝宠爱人民。荀子亦有如是表述:“天之立君,以为民也”。⑩[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第504 页。这是以天命的形式肯定上天立君旨在人民,“民本”意蕴昭然。
其实,夏商周三代的“天命-王权”论,是为了说明王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其认为,天命是人世间政权更迭、政治运作的主宰,尧舜禹禅让、商替夏、周代商,皆是天命所然。但天或天命毕竟又是抽象的存在,按《诗经·文王》所说,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那么,天命如何体现?儒家认为天命或天意是通过民意得以体现的,即“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⑪[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09 页。也就是说,上天与人民的视听是一致的,天命通过人民的耳聪目明考察人君的德行。民心向背是天命赋予或转移的根据,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①[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74 页。,人民的愿望、要求,上天必会满足。可见,根据儒家观点,天恩天威是依据民意来实施的。帝舜的天子之位,就是“天与之,人与之”②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第219 页。,来自天,同时也是民众的授予。人君顺应民意,即是顺应天意;反之,违背民意,即是违背天意。
所以说,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本于民心民意。清华简《厚父》③学界普遍认为其为周武王访于夏人后裔厚父的记载。载:“民心惟本”。这说明,早在夏人就已肯定民心是根本。敬德保民,方可得天命,为天子(或曰“作民之主”)。这是以天命的形式肯定民心民意,反映的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因此在儒家看来,“天子不过是受‘天’与‘民’委托的管理者,只具有管理、行政权,而不具有对天下的所有权”。④梁涛:《清华简〈厚父〉与中国古代“民主”说》,《哲学研究》2018 年第11 期。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阐述的。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人民的问题最重要——民为贵,强调了政治的合法性在于以民为本,人民的生命财产贵重于君主与社稷,那么,结果自然就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⑤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第328 页。。事实上,历史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⑥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第171 页。。
质言之,夏商周三代民本信仰关注的是政权的得失,是一种政治哲学。政治的合法性来自天命,而天命就是民意。以民为本,是为了配享天命、获得政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民为本是手段,为民之主、作君作王才是目的。民为君本,民与天齐,得民意民心者得天下,敬天保民的民本观念由是而生。支撑起国家的,说到底是人民的意志,民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着人君和国家的兴废。人君一旦丧德失仁,即违背天意,肆虐人民,那么天就会本着“惟德是辅”的原则“改厥元子”⑦[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453、394 页。,令新王取而代之。汤武革命,即是如此。因此,按儒家观点,人君的德行,才是获得上天青睐的关键。“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⑧[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400 页。王惟有敬德,才能获得长久的天命。人君要用德行来协调君民之间的关系,以增加民众的归附和向心力。
总之,“以民为本”作为先秦的主流意识形态,贯穿于三代的宗教、政治实践,并为执政者普遍接受。它是价值原则,也是政治原则。人民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意味着君主对民众的地位和作用要有正确的认知,要关爱和体恤民众,并以实际的惠民政策去履行治民爱民的职责。以民为本,当落实于切实的慈善关怀时,其价值意义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
二、养民教民:儒家规定给人君的政治实践
儒家以民为本的慈善观体现在国家的政治实践中,首要的考量是要爱民,因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⑨[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第234 页。爱民是现实政权能够长治久安的前提保证。而爱民主要包括两个向度:养民与教民。
养民,即解决人民的生存、温饱问题,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核心是发展经济、解决民生,自古以来就是为政者面临的严峻问题。诚如有学者指出:“民生好坏决定民心向背,民心向背决定国运昌衰,这是古今中外的一条公理。”①郑功成:《习近平民生思想:时代背景与理论特质》,《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3 期。人民是最高价值性的存在,君王应当成为收敛一己私欲,思百姓之所思,急百姓之所急,体认百姓所需所求的理想执政者,“则保障人民之生存,自为逻辑上必有之归结”②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10 页。。《尚书·大禹谟》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孔安国注:“为政以德,则民怀之。”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 年,第283 页。因为人民一旦沦入饥馑,生存无着,就会铤而走险,社会因此会陷入混乱,国家政权也将不稳。因此,为政之道,以爱民养民为大务。徐复观评论说:“天子或人君是应人民的需要而存在,人民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所以人君最大的任务便是保障人民的生存,于是爱民养民便是儒家规定给人君的最大任务。”④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291 页。所以,儒家始终强调人君要养民富民,这包括轻徭薄赋、使民以时、与民休养生息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以使经济问题能够得到初步解决。
接下来,按孔子“庶富教”的逻辑,是应当对民众实施教化。“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⑤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第136-137 页。孔子对冉有提问的回复,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解答:正向是富民之后需要教民,逆向则是要教民先须富民。只有先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使人民生活富足起来,教化才可能得以实施。先富后教实际成为社会的共识。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⑥[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中华书局,1982 年,第2132 页。。虽说这个“知”本身也是教化的结果,但它毕竟建立在养民富民的基础之上。二者的先后关系是不应当颠倒的。
孟子将孔子的仁爱落实于仁政,进一步具体化了孔子先富后教的原则,所谓“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⑦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第311 页。孟子非常重视养民,他再三劝诫统治者,施政勿夺农时、取民有制、轻薄税赋,使人民在经济上能够自足,这样人民才有实现道德提升的可能。仁德是依赖充足的物质条件提供前提和动力的。
孟子又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⑧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第5 页。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既富而教以孝悌,则人知爱亲敬长。如此,即便当时物质生产力水平低下,但老来终究可以衣帛、食肉;少壮之人,虽不得衣帛食肉,但亦饱暖有余。到了这一境地,道德生活高尚的王道社会也就不远了。所以,民众其实是好引导的。明君如果能够给民众以确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够抚养父母妻子,然后带领他们走向善的德行,他们就没有不愿跟随的。
因此,制定恰当合理的经济制度使民衣食富足,并在此基础上施行仁德教化,就是治国者所应当履行的基本国策。其中贯穿的是爱民的精神。《周易》节卦《彖辞》说,应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在物质产品一定的情况下,统治者“节以制度”,人民的负担就会减轻,爱民的愿望就可能得到落实。诚如《旧唐书·食货上》所云:“量入而为出,节用而爱人,度财省费,盖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富,而教化行焉。”那么,人民的“庶且富”是在统治者“节用而爱人”的经济制度下实现的,仁德教化本身已融入于其中,其能得以流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教化毕竟不等于庶富,它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和目的,它的重心在于通过对人民的引导与规范,使人民知礼向善、上下有序,这属于人文教化的方面。汉代学者总结了以严刑峻法著称的秦王朝迅速败亡的前车之鉴,感慨道:“刑罚不可以慈民”,“有教,然后政治”①[汉]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大政下》,中华书局,2000 年,第349 页。。良好政治应当从爱民出发,教化百姓。仁爱观念的播撒与执政者对民众的教化是相辅相成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儒家的教化涵盖“礼乐刑政”,不可简单化理解。《礼记·乐记》载:“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与德治相关,刑政与法治相关,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德治与法治并用而行,指归一致,都是为了合同民心,促进社会的和谐,从而使国家步入治平之道。
毋庸置疑,一个社会的良好秩序,需要道德和法律两种规范体系来维持,二者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儒家倡导仁爱,但并不因此而排斥法制,只是强调法律最终仍是为增进人的德行服务的。譬如西周法典《吕刑》所载:“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执政者的责任在于以礼法辅助德行教化,使人民明了孝悌、忠恕、慈爱、和睦、敬让等仁德,提高人民的精神素养。
故而,儒家肯定“德”“刑”在维系政治秩序中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谓“明德慎罚”②[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359 页。是也。显然,慎罚不是否定刑罚,而是以刑罚的长处来弥补德行的不足,以期德行达到一种完满状态。这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因此而形成德刑兼施并济的二元政治秩序。养民教民的爱民观念,重在落实于慈善的行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③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第65 页。。
三、赈贫恤患:执政者慈善责任的履行
随着三代以降王朝的兴替,人们逐渐认识到爱民的德政价值和施行慈善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周代统治者多强调继承文武的惠民保民传统,“子子孙孙永保民”④[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388 页。,“爰及矜人,哀此鳏寡”⑤[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661 页。。《周礼·地官司徒》要求各级官吏都应重视赈贫恤患、救助老幼孤寡。在执政者这里,慈善事业实际已成为了一种责任担当。
所以说,以民为本的慈善观并不意味一种空洞的理念,它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社会救助政策中有实际的体现。譬如齐桓公执政时的“振孤寡,收贫病”政策⑥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第1404 页。。而且,随着齐桓公称霸诸侯,齐国爱民、惠民的慈善政策也影响到其他诸侯国,所谓“再会诸侯,令曰:养孤老,食常疾,收鳏寡。”⑦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第158 页。后来吴越争霸,吴王阖闾“在国,天有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困乏”。⑧[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614 页。而越王勾践重视对贫困孤寡者的救助,提出要做到“越国之中,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①徐元誥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 年,第557 页。。诸如此类为了称雄争霸目的而实施的安定社会、收揽人心之举,客观上履行了为政者所应承担的慈善养民责任。
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为实行社会救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架构下,以民为本和施行仁政的理念得以系统贯彻。执政者应当担负的慈善救助责任,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领域,都产生了实际的效果。汉代流行“天人感应”论,董仲舒便是其典型的代表。他强调天人感应,借天权制约君权、关爱民众的价值取向明显。所谓“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②[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 年,第220 页。。在他这里,宇宙论和道德论是密切关联的,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皆源于天。因此,人的形体、德行、好恶、喜怒,皆化天而成。而“天,仁也”③[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 年,第329 页。,天的主要品格是仁,人君效法天,行仁、爱人则理所当然。而且,对于“王者以百姓为天”④[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 年,第148 页。的观念,统治者事实上已有一定程度的自觉,并在客观的层面,有助于督促各级官吏恪尽职守、落实国家制定的慈善救助政策。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诏告:“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咸加振恤。”⑤[清]朱铭盘:《南朝梁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474-475 页。开始于北齐的以备赈济的义仓,到隋唐时期,在官方的着力推广下兴盛起来。以民为本的慈善关怀,还体现在国家的恤老、慈幼、施药等多方面举措上。如《唐户令》载:“诸鳏寡孤独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⑥[日]仁井田:《唐令拾遗》,长春出版社,1989 年,第165 页。许多帝王还亲撰了蕴涵仁爱思想的官箴,如武则天的《臣轨》,五代后蜀主孟昶的《令箴》等。孟昶的《令箴》流传很广,其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宋太宗取此十六字箴言,颁行州县,敕令勘石立于衙署大堂前,故又称之为“戒石铭”或“戒石箴”,以警示各级官吏秉公办事,勤政为民,慈爱百姓。
概言之,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基于民本理念的古代慈善政策基本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唐宋时期,有了专门的慈善救助机构,对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实施救助。君主的治国理政,必须以仁爱人民为先,并成为慈善救济民众的最后责任承担者。爱民的理念通过制度化的措施而固定下来。
宋代赓续儒家的德治理念,加上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官方对慈善救助尤为重视,所谓“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八《振恤》,中华书局,1977 年,第4335 页。。宋代遍布全国各地的居养院,对鳏寡孤独者予以抚育赡养。同时,国家还建立了社会医疗救济机构安济坊,对鳏寡孤独贫病不能自存者予以收养并给以医疗救治。由于执政者的重视,宋代慈善事业制度严密、机构完备、设施齐全、救助范围空前广泛,其中的诸多慈善救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了元明清时期,官办的养济院、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慈善救助机构,对“老弱群体”的体恤关怀更为完备。元朝官方将恤孤养老当作为政的应有之责,《元史·百官志》云:“命经略使问民疾苦,常令有司恤鳏寡孤独。”《大明律》是明朝国家最重要的法律,《大明律·户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明亡清兴,清朝官方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慈善政策,重视对鳏寡孤独、残疾人、贫民的慈善救济。如顺治五年,即诏告各府州县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①《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一《顺治五年十一月》,《清实录》(三),中华书局,1985 年,第330 页。。其后,康熙、雍正、乾隆曾多次谕令重申,使养济院的诸项慈善措施更加具体严格,并使养济院扩展到了中国西部的边陲地区。
总之,古代执政者的慈善关怀,作为儒家规定给人君政治实践的落实,体现在从先秦至清朝历代官方的赡老恤孤、养民教民、扶危济困的不同慈行善举之中,其本身也构成为执政者重视民本、惠施仁政的重要表征。
四、为善乡里:乡绅慈善责任的落实
儒家肯定博施济众的“大同”理想社会。“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②[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658 页。,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③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第125 页。等,集中表达的正是博施济众的基本理念。历代的志士仁人,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在国家与社会的实际治理中,讲信修睦和扶养鳏寡孤独,以保持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绝非全然由官府负责,民间人士主要是乡绅们将慈善救助活动视为自身应尽的职责。
乡绅(或称士绅)是传统中国中深受儒家文化熏陶而活跃于乡村民间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不同于魏晋时期的门阀郡望,也区别于近世的土豪劣绅,是随着科举制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④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传统中国的乡绅阶层逐渐解体,但这是一个缓慢的变革。乡村社会的原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使得乡绅在地方社会事务管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延续着传统乡绅的社会职责。。乡绅是民,而非现任的官,主要是由退居的官员和拥有科举功名者所构成的,因此也不具备实质性的政治权力。换言之,乡绅的身份地位不直接关联土地财富,而是享有一定特权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精神价值代表。
在传统中国,“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⑤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3 页。。乡绅凭藉其功名、学识及财富,居于地方实际领袖的地位,身份地位自然与一般民众不同,是联系官与民的纽带。他们协助地方政府管理当地事务,对地方兴革事务均有把持,与代表官府的国家权威形成互有所长又协调合作的格局。尤其到明清时期,乡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成为乡绅之治,而基层社会则成为了所谓“乡绅社会”。在乡绅社会,乡绅在领导地方的治理中,除却政治上的庇护、经济上的周济,还有教化乡里的道德责任。乡土社会的安定与秩序,主要基于乡绅的作为。因此之故,“乡绅”不同于“地主”⑥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285-286 页。。作为地方精英,乡绅有素养、明礼法,是一邑之望。纵观历史,乡绅在每个时代都存在许多公益扶助、社会救济等慈善行为。这是乡绅能够胜任地方权威职责与教化民众重任,进而完成对地方社会实际领导的重要原因⑦衷海燕:《清代江西的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新城县的个案研究》,《清史研究》2003 年第2 期。,彰显了对人的生命关怀与为善乡里的情怀。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基层社会的慈善救济方面,王权、绅权与宗教诉求是一致的。①其实,儒释道“三教合一”理念,在传统中国的思想界早就产生,最迟在三国时就初露端倪,如时僧康僧会说:“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高僧传·康僧会传》)。唐代之后,“三教合一”日渐成为思想界一股不可小视的社会思潮,并成为历朝统治者着力推行的基本宗教政策。因此之故,在民间社会,“三教合一”更是大行其道。据清人柴萼《焚天庐丛录》载:“早在明英宗年间,民间就已‘绘老、孔、佛三像,名三圣祠……其义为三教殊途,皆以行善为本。’”参见任继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世界宗教研究》1984 年第1 期;刘晓东:《“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1 期。历史上主持赈灾事宜者,有官员、乡绅,也有佛教徒。慈善是佛教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佛教慈善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博爱观相融合,成为佛寺、僧侣与信徒广开救济贫困、施医恤病与赈济灾荒等慈善活动的动力机制,这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效益良多。同时,由于统治阶层的认同与提倡,与儒家博爱观相融通的佛教慈善思想得以流布社会各阶层,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以大发展并为统治阶层与世家大族所接纳。譬如,以家世学养鼎盛于北朝的赵郡世家李氏②鼎盛于北朝时期的赵郡李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世家大族,与当时的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南阳郑氏、太原王氏等高门著姓并称于世。其政治地位显赫,经济方面田连阡陌,文化方面以传统的儒家仁爱思想与佛教的悲悯情怀相融合而传家。因此之故,该世家望族的慈善活动尤为凸显。参见许秀文、王文涛:《北朝赵郡李氏的家学传统与慈善》,《石家庄学院学报》2014 年第5 期。,其儒佛兼修,将儒家的修齐治平、亲亲、仁民爱物与佛教的慈悲众生、业报轮回相结合,做出了许多慈行善举——慈善为怀,仁爱乡民,福泽子孙。李氏家族的慈心善举,是以彪炳青史。《北史》载:李士谦,终身从事慈善,“性宽厚”,“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凶年散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③[唐]李延寿撰:《北史》卷三十三《列传第二十一》,中华书局,1974 年,第1233-1234 页。如此作为与其儒佛道兼修大有关联。不过,世家大族的文化身份特征,毕竟是儒学。诚如钱穆所言:“门第与儒学传统有不解之缘。”④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 年,第169-170 页。儒家博爱的精神实质被世家大族化为家风,呈现在平素的待人处事之中。对此,有日本学者指出:六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在战乱动荡的社会里,在其聚居区中履行“孝义”的家庭伦理,同时也履行“友义”的公共道德,以此而为居住区的宗族、乡党提供教化、赈恤慈善活动。⑤参见[日]谷川道雄:《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续)》,《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6 辑。这一在民间推行孝义友爱的职责,日后主要由乡绅承担。
明清时期的乡绅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民间慈善活动⑥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每当发生灾难饥荒,乡绅们往往会率先捐资并组织募捐赈灾,主动施善为乡民排忧解难,承担赈济救助之责。如明代江南乡绅丁宾,每当家乡遇到灾荒,他都一如既往地积极赈济。据其同乡陈龙正所记,仅在万历十五年至十七年这三年灾荒期,丁宾捐出米、钱、布、絮等,共计白银三万余两。不仅如此,丁宾还细致周悉地亲临赈施。⑦[明]陈龙正:《几亭全书》卷五十八《题丁清惠公赈施条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十二册,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624 页。
前文已述,儒家“爱民”主要表现为养民与教民两个向度,所以,乡绅在施惠地方的过程中,也是围绕着生存与教化这两个方面。如明末民间兴起流行的“同善会”,是由当地乡绅组织的。其以扶危济困为目的,同时具有劝人为善的教化功能,这对稳定社会秩序具有良好的功效。又如作者在甘肃省的调研中了解到,民国十八年(1929 年),靖远遭逢大饥荒,乡绅乔永泰(1906—1994 年)与兄长乔永丰、乔永恒毅然倾资在当地设粥棚“放舍饭”,赈济乡民。四年后,乔永泰还出资在黄河上修建了一座大水车,以浇灌本村的两百亩旱田,该水车一直使用到解放以后。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他又组织乡民兴学建校,积极筹集建校款项,带头捐资三百块银元,无偿提供沃田五亩用于校址,创建了三合村第一所学校——“三合国民学校”,并担任校董,直至去世。如今的“三合荣侨小学”,就是在当年校址基础上扩建发展而成的。时至今日,当地村民对乔氏兄弟的慈心善行仍旧感怀。乡绅如此作为与其自幼习读儒家典籍,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颇深有关。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情怀,是乡绅力求在乡村社会贯彻执行的内容,并以此价值观念指导基层社会的运作管理。
身为地方领袖人物,乡绅在为自己的生存境遇努力的同时,尽己所能地帮助处于困苦境地中的他人。在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社会,遇到灾荒之年的贫苦农民,往往需要依靠赈济才能度过难关。乡绅慷慨无私的慈善赈济善举,是值得肯定与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