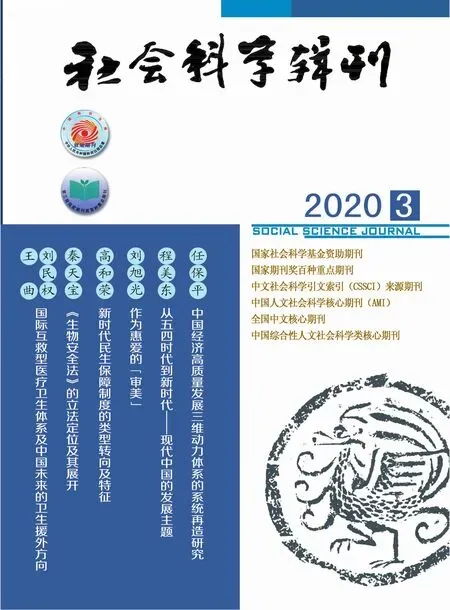国际互救型医疗卫生体系及中国未来的卫生援外方向
刘 民 权 王 曲
一、引言
关于灾难应对和灾害风险管理以及灾后重建的跨学科研究一直存在,在相关领域内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知识、经验和共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其他灾难(比如地震、洪灾)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与其他灾难一样,它同样在很短时间内对灾(疫)区的医疗力量(人员及设施)造成巨大压力,使之大范围瘫痪,导致大量本来可以被挽救的生命没有得到挽救、本来可以减少的伤亡没有得到减少。它与其他灾难的不同在于:一方面,地震等严重的自然灾害不但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且还会对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包括对医疗设施的破坏,为灾情期间和之后营救生命的工作增添许多困难,疫情则一般不会造成相同的损失并产生类似的影响。另一方面,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后,其影响区域基本上是固定的(除非有其他次生灾害发生),而传染性疫情则由于其传染性,如不及时控制或阻断传染,会导致疫区范围不断扩大。
我国在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援助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自1963 年新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起,已有50 多年的历史。最近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外医疗援助,是2014年西非发生大范围埃博拉疫情后,我国派出了许多医护工作者,包括公卫专家,开展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的医护支援主要为实物和人员,直接目的是充实受援国家的医护力量;也有小范围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建设,但重点是在直接帮助医治病人上。医护力量上的援助固然重要且需要继续,尤其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在相关发展中国家暴发时,然而,从长远来说,我们同样需要考虑怎样帮助受援国家和地区建立一个能长期抵御风险(包括重大疫情和自然灾害)的医疗体系。笔者认为,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也应该是我国向这些国家提供医疗援助的长期目标。
本文提出“能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这一概念,涵盖范围不仅仅包括医护能力,还包括流行病学和健康促进等防御疾病与疫情的公卫能力。考虑到现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这是非常必要的。在抵御重大自然灾害风险造成的人员伤亡方面,重要的是医护能力,当然也需包括少量的公卫能力。在抵御疫情方面,坚实的公卫能力建设,包括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公卫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及时的公卫措施能够大幅度缩减传播范围,减少医护需要。
目前全球在相关方面的倡议是以国家为单位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各自的体系,实际上,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小发展中国家,这是很难实现的,需要在地区间乃至全球层面展开合作,形成一种正式的互助互救型国际医疗卫生体系,包括建立一支强有力但非常设的国际医护公卫力量。而无论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还是通过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我国都能够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许将是我们能为全球提供的最大和最宝贵的公共品。
二、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
在对全球或地区供应链的讨论中,有对如何应对由自然以及人为灾难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在对“能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概念进行界定时,不妨将该系统看作是一个供应链,并以此为框架来思考。
首先需要说明,传统的供应链,特别是跨国乃至全球供应链,由一大组生产节点和相互间的链接环节组成。在针对灾害对传统的供应链造成的影响及其应对的研究中,关注点仅是构成这些供应链核心的产品,即相关产品的生产如何得以延续和上下游市场如何继续保持畅通。一个更具抵御风险能力的供应链即是一个各生产节点和联系环节都能更好地承受灾难及其影响并能从中快速恢复的系统,其目标是尽可能确保该系统不断裂、不崩溃,以更好地保护各利益攸关方的利益。
在健康领域,可采用同样视角来思考如何更好地确保某些医护和健康产品在灾情发生期间的持续供应,比如这次在应对疫情中显得弥足珍贵的口罩和呼吸机等。然而,仅在这一层面上思考能抵御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其意义大受局限。①目前文献中关于医疗部门供应链及其风险的讨论,主要从医院角度围绕药品和医护设备展开,参见Wang L.,Research on Risk Management for Healthcare Supply Chain in Hospital, Doctoral Thesis,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2018.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重点应该是考虑如何在确保日常的医疗保健服务得到有效满足的同时,还能在灾害导致对医护服务需求大幅度攀升时保证这些需求同样得到有效的满足。在灾情之中和之后的真正挑战是: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死亡人数、降低伤残和疾病规模,杜绝或控制可能出现的疾病新媒介;避免受灾害影响的人群出现长期健康问题(比如社会心理和精神性创伤等);维持灾难发生前的正常医疗服务。一个更具抵御重大灾害风险能力的医疗卫生体系,即是能有效迎接以上挑战的体系,一般需要某种组合的初级、二级和三级医护服务。除医护外,还需包括流行病学、传统公卫、健康促进和心理咨询及护理等各种专业力量。当然,还需确保以各类医护和公卫产品为核心的各产品供应链有效运作。
组成一个现代产品供应链的公司和节点可遍布某一地区、国家乃至全球。一些公司成为生产节点,另一些公司成为销售链接,其中一个或多个公司担当领头企业。根据领头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可出现多种不同的供应链模式。一种模式为领头企业自己拥有或控制大量的生产节点,并通过其自身实力对产品设计和规格进行全面控制。这被称为生产者驱动型供应链模式,是供应链模式的一个极端。与此相反,一个领头公司可能并不控制任何生产节点,但掌握巨大的市场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对产品的规格和分销渠道形成控制权,这通常被称为买方驱动型供应链模式。许多实际的产品供应链一般介于这两者之间。
上述分析为我们构思如何营造一个能抵御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提供了关键的两点:其一,可以甚至应该从地区乃至全球层面来考虑所需服务的提供者,而不必或者不应只从本国内部(或者只从某下辖行政区)来确定提供者;其二,存在一个谁为领头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其最终方案将取决于所预期遭遇的灾害情况,在哪些可能的条件下遭遇到,以及其他地区层面、国内层面乃至全球层面的因素。
三、国际能力的作用和地位
国际上已对建设具有抵御灾难能力的安全医院和设施给予了关注①2005 年1 月世界减灾大会(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eduction)在日本兵库县召开,共有168 国政府参加。大会通过了一个为期10 年的行动纲领,即《兵库行动框架》(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其中即呼吁各国建立安全医院。随后,世卫组织和其他机构牵头制定了一些相关举措以及技术指导。参见WHO and UK Health Protection Agency and Partner,Safe Hospitals:Prepared for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for Health Fact Sheets,Global Platform,May 2011,https://www.who.int/hac/events/drm_fact_sheet_safe_hospitals.pdf?ua=1,January 8th 2020.再之后,WHO 领头编制了一份安全医院指数(WHO and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Hospital Safety Index:Guide for Evaluators,2015,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8966/9789241548984-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January 8th 2020),并于 2015 年 3 月在日本仙台举行的世界减灾大会上得到认可。,但这与系统性思考相去甚远。仅有的一点系统性思考主要是关注以一国或一国内部各辖区现有医疗卫生机构和体制为基础,加强这些机构和部门的应急准备和反应。WHO 2011 年的一个文件最简明地表达了这一思路。在国际层面,该文件所规划的作用仅限于:“在WHO 范围内开展、促进、加强关于减少风险、应对灾难和灾后恢复的区域和次区域内合作,以及区域间合作,包括共享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呼吁WHO 成员国、捐助者和发展合作伙伴通过国际发展合作、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WHO在卫生应急和灾害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为卫生应急和灾害风险管理规划分配足够的资源。”〔2〕
虽然充足的资金和更密切的区域、次区域内部合作以及通过WHO 进行区域间协作的确很重要,但是国际层面的合作不能仅限于此。
对许多国家来说,以一国之力构建这样的能有效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很不现实的。首先,很多国家人口只有几百万,其中大部分居民集中居住在城市。一旦一场重大灾害(如大地震或超级台风)袭击了他们,完全有可能摧毁他们的整个医疗卫生系统或者严重地削弱它——即便在灾难之前他们遵循了国际组织关于建设安全医院的准则。其次,即使其医疗卫生系统经受住了冲击,但它难以独立应对灾情发生后大幅攀升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抑或更大可能被这些大幅攀升的需求所压。显然,在所设想的情况下,一国必须寻求国际援助,不仅仅是资金的援助,更是实实在在的医护能力和服务方面的援助。
在目前的国际构架下,也的确存在这样的援助,但仅以灾难发生后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方式出现。这种援助不但规模有限,而且远没有被纳入各国国家或地方医疗卫生体系的顶层设计之中。可以说,在现有的国际构架下,每个国家仅被提倡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能抵御重大灾害的医疗卫生系统;少量医疗卫生能力和服务的国际支援只在事后发生,并不进入人们的事前视野。
根据CRED〔3〕的一项研究,在最近的几个年代中,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在增加,而且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同一级别的重大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都比以往增加了。频率增加的原因目前还不完全明了,但可能与气候变化、近期重要区域内地球板块运动等有关。鉴于以上可能性,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各种重大灾难的准备,明确在规划各国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时,把来自外部的能力支援和对这一能力的依赖明确纳入各国的体系之中。
每个国家在规划其能抵御灾害风险的卫生医疗系统时,仅考虑本国卫生部门的能力,忽视了国际能力所能起的作用以及当重大灾难发生时受灾国家对这一能力的明显需要。原因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即每个国家的健康问题传统上只被视为该国的事情(或者仅被视为该国内部地方政府的事),每个国家的任务是依靠自己的资源设计自己的医疗卫生体系,建立自己的医护和公卫能力,以应付不断变化的挑战。如有需要的话,每个国家都可得到一些国际资金和技术指导来构建其系统,但在其体系的规划中不考虑当重大灾难来临时来自其他国家的医护和公卫能力的支援(尽管事后或许会有这样的支援)。虽然近年来这种模式已发生了一些变化①在供应侧,出现各种跨境招聘医疗卫生人力资源的做法;在需求侧,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跨境服务,包括旅游寻医。,但当前的主流思维仍然是停留在旧模式中。②WHO 也许是在倡导建立全球权利和义务框架方面走在最前面的。其2005 年版《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各国有及时监测和报告所有生化和放射性核素国际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义务,但责任仍落在各国政府肩上,WHO 仅提供技术性支持。然而,尽管每个国家通过自力更生或许能在日常满足其常规医疗卫生需求,但这种做法不足以满足当重大灾难发生时其大幅攀升的医护和公卫需要。③坚持旧模式的一个理由可能是,如放弃它,很有可能出现各国搭便车的问题。然而,本文仅倡导重大灾害后的医疗卫生服务相互支援,而非满足常规的医护和公卫服务需要。
事实上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重大灾害,因此当灾难在某国发生时,另一国给予该国的援助和支持(包括实际的医护和公卫能力的支持)不应被看作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的。一个明确包含跨国层面上的相互帮助和支持并以此为一个关键支柱的系统,是各国建立和维持其抵御重大灾难的医疗卫生体系的更经济更有效的方式。在这种安排下,任何国家都不需要单独发展其自身能力来应对重大灾难发生后(但在其他时间则大部分闲置着)大幅攀升的医护和公卫需要。只要一国有需要,就可在国际层面上快速组织和部署支援,包括弥足珍贵的实际医护和公卫能力的支援。事前安排当重大灾难在某国发生后国际层面所提供的支持,并不需要额外组建一支庞大的“共同力量”,也不需要将这支“共同力量”分散到各国成为各国一支单独的常备力量。它可以由各相关国家现有的常备医护和公卫能力组成,但需要每个国家事前指定其常备力量中的哪一部分为国际共同力量的组成部分。当重大灾难在某一国发生时,各国的队伍能够迅速调动起来并共同组成支援受灾国的共同力量,而在无灾难发生时,他们可留在本国机构内工作。当然,即使在平时,组成国际共同力量的各国医护和公卫人员,仍然需要接受定期的联合培训和模拟演习。④这与当相邻国家发生冲突时联合国派驻国际维和部队的情况既相异又相似。各国一般不会专门设立一支只用于国际维和的部队,而仅从现有军队编制中抽调,当然这些被抽调的官兵都必须经过相关培训。有需要时,他们被派往冲突地区执行维和任务,任务结束后则回国服务。人们可能会说,维和与发生灾害时的医疗卫生援助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派往冲突地区执行维和任务,顾名思义这是相关冲突国所不能自己胜任的事,而出现灾害情况时,受灾国可以进行自我营救。但问题是,如出现重大灾害情况,许多受灾国将无法自我开展有效的营救活动。
四、“领头羊”与冗余:当地执行者与国际支援力量
在一国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中,谁更适合扮演“领头羊”角色呢?本文所倡导的以满足受灾居民医疗公卫服务需要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体系中,“领头羊”的任务应包括规划、识别和组织该体系中的各服务节点,确定各节点的功能,并在需要时要求它们执行这些功能。“领头羊”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选择,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预期发生的具体紧急情况,可能发生的对医护和公卫服务需求的攀升幅度,需在什么情况下满足这些需求,以及可能形成的对医护和公卫力量的挤兑。这里,灾区当地的卫生当局和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所能发挥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显然,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它们都是前线机构,最有可能对需求做出快速评估,并且最有能力调动任何存活下来的当地资源和能力来启动第一轮搜援。它们身在灾区,对灾前情况和灾后情况的了解(包括任何幸存的医疗卫生能力)、对灾后地形和道路状况的了解,似乎都说明他们更适合担当“领头羊”角色。但另一方面,如果它们本身也已遭受灾害的重创,其设施和能力严重受损,抑或它们缺乏处理特定紧急情况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可能无法胜任担当组织和协调救援工作的关键角色,特别是在国际层面进行的合作。
对此可参照在克服产品供应链中断风险方面提出的应对措施。针对产品供应链中断风险的解决办法是让系统包含一定的关键“冗余准备”(redundancy)。例如,如果一个生产节点或分销链接在危机中中断,则可动员另一个储备节点或链接来完成任务。当然,这第二个储备节点或链接必须事前安排好。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即使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相关业务仍能照常延续。
为确保卫生部门不但能够继续保持而且能够大大增加其服务数量和扩大服务范围,以应对重大灾害发生后大幅攀升的需求,预先规划好关键的“冗余准备”是一项重要措施。由于系统中最有可能被灾难破坏的服务和链接节点恰恰是当地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和管理当局,因此如果指定当地卫生当局和服务提供者在灾后医疗卫生救援工作中起到关键的“领头羊”作用,那么迫切需要建立“第二道防线”。
需要说明,虽然强调第二道防线的必要性,但绝不应否定加强第一道防线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仅仅拥有第一道防线可能就足够了,特别是如果第一道防线通过一些合适的改造计划(比如安全医院计划)而得到加强的话。但真正的挑战是建设一个具有抵御所有可能灾害的医疗卫生体系①在相关文献中,全面风险防范方法(all-hazard approach)是指建立一种通用能力以应对各种不同的灾难。本文对此的解释稍有不同,主要指准备好应对不同级别和规模的灾害,不管它属于哪一种。,其中包括重大灾害甚至灾难性事件。拥有第二道防线就是为了应对那种可能性。如上所述,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一般意味着需要国际援助和国际层面上各援助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拥有一个强大的当地医疗卫生系统对各国更好地抵御各种灾难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建设一个具有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时,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建设一个强大的、具有抗灾能力的地方医疗体系上,显然是严重不足的。这里的目标不是用国际(地区甚至全球)行动来代替国内行动,而是做到两者兼备。在一个真正能有效抵御所有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系统中,我们需要两道防线,而且在必要的时候,需要第二道防线发挥关键的“领头羊”作用。
五、当前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虽然国际上关于建立能抵御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的主流思想仍停留在传统的各国自管的模式中,但近年来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也有一些进展,主要围绕自然灾害事件。②比如在东盟,参见 Liu,Minquan,Hazard-Resilient Health Services:A Supply Chain Approach,report submitted to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ERIA),2016.毋庸置疑,当一国发生自然灾害时,目前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通常包含医疗卫生援助部分,并且是通过动员国际医疗卫生能力来完成的。尽管如此,这一援助模式却远没有被国际主流思想接纳为各国构建抵御重大灾害风险医疗卫生体系的关键支柱,而仅被当作一种临时发起的“人道主义”援助。似乎各国在规划自己的能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时,抵御的对象不仅仅是灾害风险,还包括来自他国的医疗卫生能力援助。③拒绝接受援助的例子时有发生,其原因可能是多种的。
在一国面对重大灾害时,目前最有能力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网络还是联合国及其组织。具有人道主义援助使命的联合国主要机构包括粮农组织(FAO)、国际移民组织(IOM)、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开发计划署(UNDP)、人口基金(UNFPA)、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人居署(UN-HABITAT)、儿童基金会(UNICEF)、妇女署(UN Women)、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灾难发生时,这些组织共同行动为受灾国家提供广泛的援助,包括居所、粮食安全、营养、健康、教育、生计,以及物流和通信支援。存在一套机制来协调这些众多的机构和组织的行动,但这里忽略细节,仅说明关键的“集群(cluster)”法,即针对每一方面的援助分别指定一个“领头组织”来协调各援助机构的行动。①联合国系统在引领和主持世界上大部分国际行动和方案时(包括减少灾害风险的行动),一般都采用集群方式,即在其他相关机构的支持下,属于特定领域或主题的行动和方案由专业知识和功能最符合该领域和主题的机构领导。在与灾害有关的健康问题上,负责机构是WHO,得到包括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艾滋病规划署和联合国减灾战略办(现为减少灾害风险办事处)在内的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支持。参见 WHO,UNAIDS,UNFPA,UNICEF and UNISDR,Protecting People’s Health from the Risks of Disasters,2015,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documents/emergencies/protecting-peoples-health-from-risk-of-disasters.pdf?sfvrsn=f51de23c_2,February 8th 2020.比如,医疗卫生援助由世界卫生组织来引领和协调相关的援助。除此之外,联合国还会设一位人道援助协调员,全面协调对受灾国家的援助。在该协调员缺席的情况下,则由驻所在国的联合国机构协调员担当这一角色。
以亚太地区为例,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一般遵循的步骤和过程、各步骤采取的主要援助措施和可能提供的援助如下(我们的关注点是与救死扶伤直接有关的医疗卫生援助)。亚太地区的执行情况将援助过程分为几个阶段。②参见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亚太办事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灾害应急:国际工具和服务指南》,2013 年,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Disaster%20Response%20in%20Asia%20Pacific_A%20Guide%20to%20lntl%20Tools%20Services.pdf,2019 年 5 月 22 日。首先,在灾害发生后的 12—48 小时(第一阶段),在受灾国政府发表关于灾情的紧急声明并表明愿意或希望接受国际援助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会联合会首先派出紧急应对小组、区域救灾小组和实地评估协调小组;联合国系统则派出一个灾害评估和协调小组。根据需要,通过双边协调,周边或其他国家可向受灾国派出轻型、中型和重型城市搜救队。在一些地区,比如东盟地区,还会有区域组织派出的紧急快速评估小组,以及其他基于地区或区域层面的救援力量。如果提出要求,一些民间组织如国际人道主义伙伴协会也会组织提供某些援助。在这一阶段,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有可能为救灾提供一定的应急基金(紧急救援启动资金)。联合国则会在这一阶段结束时准备好一组情况报告。接下来的24 小时(灾难发生后第48—72 小时)为救灾第二阶段。在此期间联合国系统将任命一位人道援助协调员来协调所有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包括联合国和非联合国的行动;发起联合国系统的集群应对行动;建立人道主义援助信息中心;开展多集群前期快速评估第一阶段工作并完成灾情定义。如果联合国系统没有专门任命一名这样的协调员,则由常驻受灾国的联合国系统协调员担任该角色,负责以上工作。从第二阶段结束到灾难发生后整一周的时间为第三阶段。在该阶段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将派送各种救援物资、提供中央应急基金的初期拨款,并根据需要启动新的资金捐助呼吁。
第四阶段救援是在灾难发生后的第2 周和第3周。许多救援和搜索工作进入尾声。各城市搜救队在部署后7 至10 天内将撤离;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派出的实地评估协调小组在2 周至4 周后将撤离,联合国系统的灾害评估与协调小组则在派出3 周后撤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紧急现金补助在灾害发生10 天内全部拨出,多集群初期快速评估第二阶段评估也将完成。
接下来 3 周(灾难发生后第 4—6 周)为人道主义救援的第五阶段,也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最后阶段。在此期间,将进行第二次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的拨款,并根据需要进行新一轮资金捐助呼吁。
从以上介绍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典型过程来看,并不清楚灾后紧急医疗卫生救援起自哪里以及如何展开。当地医疗卫生系统的服务能力可能在灾害中遭受重创,但如果它们具有较高的韧性并迅速恢复能力,或许能开展部分救援并协助来自外部的人道主义救援队伍开展工作。这些外来救援队伍有处理特定伤亡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而当地的人员则拥有本地资讯和社会网络的优势,如果两方能够密切合作,更多的生命可以得到拯救,更多的伤残可以得到避免。但是,不能排除发生重大灾害后,当地医疗卫生系统的能力遭到倾覆性破坏的可能性,这样它们无法有效发挥以上作用,国际救援团队将成为唯一的防线。
目前由联合国系统主导的国际灾害援助构架实际是非常薄弱的,远远不能够满足刚刚经受重大灾难打击的国家的要求,尤其是在医疗卫生方面。首先,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也即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第一阶段——是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以及区域和双边安排,率先展开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紧急医疗卫生应对,而整个联合国系统,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在这一阶段几乎是不起作用的。直到灾害救援的第二阶段,即灾难爆发了整整2 天之后,联合国系统才真正开始引领国际紧急救援工作。如果所针对的是一些小规模灾难,这样的应急速度也许足够了,但如果发生的是重大灾难,这样的国际应急速度显然是不够的。在灾害发生的头两天,不少本可以得到挽救的生命已经逝去,不少本可以避免的伤残已经铸成。对于控制由灾难导致的可能的疾病传播来说,迟来两天的应对尚且受到质疑,更不用说做到最大程度地拯救生命和降低伤残。
其次,当灾难在一国发生后,目前由联合国及其组织直接开展的援助规模其实是很小的,时间是很短的。联合国系统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在呼吁和协调国际应急行动,而且主要是来自非政府部门及组织的行动。其协调能力也相当有限,远不能快速组织和引领大规模的救援工作,而这却是最大程度地拯救生命和减少伤残最需要的。①海地地震于2010 年1 月12 日发生,震级为7.0 级,对海地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包括对医疗卫生系统的破坏,导致该国大量人员伤亡。除了一些国家提供了政府援助外,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主要由许多国际民间组织提供,包括药品、设备、救援队等。然而,由于缺少有效和周密的协调,以及在处理救援和救济事务方面缺少足够的专业知识,不少援助单位并没有为救灾做出多少贡献,反而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de Goyet,Claude de Ville,Juan Pablo Sarmiento and Francois Grunewald,2011,Health Response to the Earthquake in Haiti,January 2010:lessons to be learned for the next massive sudden-onset disaster.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PAHO),January 2010,https://www.paho.org/disasters/dmdocuments/HealthResponseHaitiEarthq.pdf,January 8th 2019)。无论是在灾害援助方面还是其他方面,联合国系统本来就只是为国际行动提供一个框架,至于该行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成效,主要还需看各援助国的投入。
六、中国当前及今后的卫生援外方向
根据上文分析,笔者认为:首先,就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在医疗卫生方面所面对的任务,就是构筑一个能真正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体系;其次,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其在全球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倡导和推动全球卫生议程朝这一方向迈进;第三,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体量,结合以往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广泛提供卫生援助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的政治影响力,推动和帮助这些国家在国家层面建设这样的体系;第四,中国尤其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组建他们在灾情发生时所迫切需要的国际医护和公卫援助能力,并在有需要时扮演“领头羊”角色。
在国际层面,上文详细勾画的在各国国家层面打造的能抵御重大灾害的医疗卫生体系可被看作是一种“国际互救”型医疗卫生体系,它由各国参与又服务于所有参与国。在重大灾害频繁发生的当今,没有一国能完全幸免。正如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一份官宣中所说:“无论你的国家多么成功,多么富有,多么准备周全,你总会有需要国际社会来支持你的救灾和灾后恢复的时候。”②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主任Jagan Chapagain 在东盟地区论坛2015 年救灾演练上的讲话,2015 年6月 6 日,https://relief web.int/report/world/asia-pacific-countries-prepare-future-disasters,2020 年 4 月 1 日。的确,每个国家都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互救体系的受益者,包括中国。
中国在构建这一抵御重大灾害的医疗卫生体系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一,中国在卫生援外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中国在1963 年首次向非洲阿尔及利亚派驻第一支医疗队,帮助该国开展医疗服务活动。之后,中国一直积极从事多种形式的卫生援外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包括:对受援国派遣援外医疗队,帮助建设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捐赠医药和医疗器械,开展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培训,提供技术支持和紧急卫生人道援助,组织卫生志愿者项目,以及向国际组织提供多边卫生援助。〔4〕
以派遣医疗队为例,1963—2018 年中国先后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71 个国家派遣了援外医疗队,累计派出2.6 万人次。数据表明,派驻的医疗队截止到2018 年已经在当地诊治患者 28 万人次。〔5〕从可持续的角度出发,为了克服派驻医疗队不能解决当地自身能力持续发展的问题,援外医疗队除提供诊疗服务外,还通过临床带教、共同手术、举办专题讲座和培训班等形式,向当地医务人员传授医疗技术,为受援国培养了大批医疗卫生人才,为当地留下了“不走的医疗队”〔6〕。
在近期对地域性流行病暴发的应对中,我国发展了派遣短期工作组的模式。这是2014 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暴发时我国提供卫生援助的重要形式。这次援助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海外人道主义援助活动 〔7〕,也是一次贡献巨大的疫情灾害防治与修复的援助。帮助受援国家取得了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全面胜利,并实现了“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8〕
我国随后又陆续派出了短期专家组帮助安哥拉、圭亚那、马达加斯加等国防控黄热病、寨卡、鼠疫等疫情,同时还支持了非洲疾控中心的建设,并帮助非洲国家建立符合自己国情和发展水平的公共卫生体系。〔9〕
第二,中国实行的救灾模式的优势。在救灾方面,中国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快速反应能力和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视角和动员能力。例如,2010年1 月海地发生地震后,中国救援飞机是第一个到达海地进行营救的——到达时间甚至早于邻近的美国派出的救援飞机。①参见 UN News,“UN Rushing Aid to Haiti Following Deadly Tremors”,2010 年 1 月 13 日,https://news.un.org/en/story/2010/01/3264-72-un-rushing-aid-haiti-following-deadly-tremors,2020 年 3 月 22 日。这种快速反应能力得益于中国长期的抗灾救灾实践。中国是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大国,抗灾救灾实践相对较多,形成了一套相对有效的快速反应机制和能力。我们已开始把这一能力用于救援其他国家,但我们也可以与其他国家一起未雨绸缪,更长远地来规划其作用的发挥。
至于全国一盘棋,一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很少有灾难会同时袭击全国所有地区。二是因为通过我国中央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使得发生在我国任何地区的重大灾害,都不单由当地政府和人民去开展救灾,而是立刻成为全国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在我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中国的这一体制优势对照其他国家尤其明显,即使是美国这样存在一定中央政府协调和动员能力的国家也是如此。在日本,中央政府的这一能力则更小更弱。②在美国,自1979 年起(除小布什执政时的部分年份),联邦政府在紧急情况时的应急工作一直由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负责。在日本,由于其特定体制,即使发生了像2011 年的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和核泄露,中央政府的救灾动员能力还是广受限制。
如果要有效地帮助其他国家构建能做出快速反应的灾害应急机制,一国必须自己拥有这样的机制;如果要当任一国家遭遇重大灾害后为其快速动员和组织国际救援力量,一国必须自己具备这样的动员能力。中国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能力。
第三,中国的快速基建能力优势。除了以上两种能力外,这次疫情应对还清楚地表明,中国具有快速基建的能力。在这次武汉抗击疫情过程中,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在一周和10 天内完工,之后迅速将一些公共设施如体育场馆和会议中心改造成治疗中心与方舱医院,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快速基建的能力和经验,必将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行动中有效地帮助受灾严重且本地医疗设施不足或遭受重创的国家,开展救灾工作,最大可能地拯救生命和减少伤残。
中国的这一快速基建能力实际上早有显现。当2014 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爆发时,中国就是利用其快速基建的能力,帮助当地快速建造了一个有100 个床位的治疗中心和一个生物安全实验室,确保每天可以进行40 至60 人次测试。同时,中国还帮助建设了一批移动测试实验室,以此方法帮助治疗了 900 位病人。〔10〕
第四,中国日益壮大的社会力量。在援助体量和实力方面,中国还有一批正在崛起的力量,即日益壮大的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虽然一直以来中国政府是卫生援助的主体,但是,其他部门提供的卫生援助已初露头角。〔11〕目前全球卫生发展的角色日益多样化,如协调良好,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也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援助力量。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海外疫情中,许多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基金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阿里巴巴、京东集团、腾讯等私营企业,以及马云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老牛慈善基金会等慈善力量,都为受灾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这些崛起的社会力量可以成为中国政府开展海外援助的重要补充。
综上,除了继续通过各种援助方式支援其他国家更好抗击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外,我国须规划对外卫生援助的长期方向和目标。本文主张,从基本的公平原则出发,我国更需把援助的重心放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上,目标可以也应该是帮助他们构筑起本国能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医疗卫生体系。我国多年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卫生援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在重大灾害快速应对方面也有一套成功的做法和模式;我国更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能够快速调动的医护和公卫能力;我国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我国还能在联合国体制内来推动全球层面的议程和规划。总之,通过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依靠我国自身的力量,我们能够推动全球为广大的中小型发展中国家构筑好他们的能抵御重大灾害的医疗卫生体系,而这应该是我们能为全球提供的最大和最为宝贵的公共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