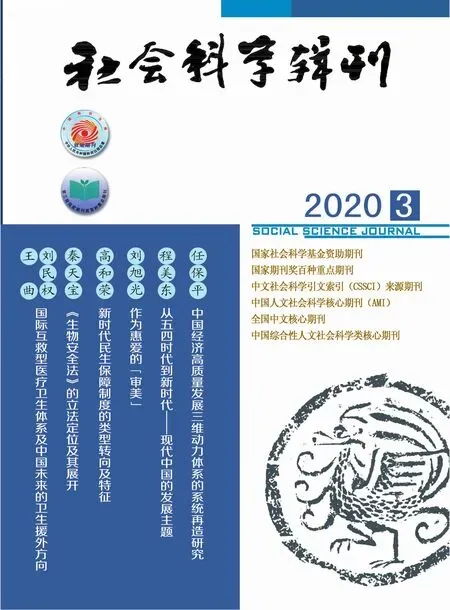新时代民生保障制度的类型转向及特征
高 和 荣
尽管“福利”这个概念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等概念则较早地被西方国家使用。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等概念及其所制定的制度与政策框架逐步传入中国,并在其影响下,形成了各类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根据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实际提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时代性命题,进而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服务、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治理纳入到民生范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当下和未来、国内与国际相比较的高度首次提出“民生保障”范畴,这是对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等相关概念的超越与深化,展示了我们在这一领域内的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由此更需要我们回顾我国自身民生保障制度的历史沿革,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明确究竟何为“民生保障”,民生保障的内容涉及哪些方面,可以将其划分为哪些类型,整个民生保障具有哪些显著特点,我们提出民生保障命题有何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我国民生保障制度内涵的历史沿革
“民生”这个概念古已有之,《尚书》 最早提出并强调“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告诫统治者要勤政为民,保障民众的生计。历代统治者均会采取一系列重视生产、减轻徭役与赋税的措施,以解民所困或施民以惠。然而,此时的“民生”还不能与“保障”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引进了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概念,认为社会保障应该注重多主体责任与多层次供给。真正把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到政府的职能层面则是本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事情。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政府对保障人民生计负有责任担当与道义承诺。要让发展的成果全民共享,全面建成覆盖全民、项目齐全、内容全面、保障适度、权责清晰、安全可持续的民生制度体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保证民生的举措主要由民生项目、民生制度、民生活动、民生水平及民生状态等几个部分组成,体现着政府对整个民众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状态的积极建构与主动作为。从历史沿革上看,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府提供的民生项目有所侧重、民生状态有所差异、民生水平不尽相同,但是整个民生保障内容都涉及到保民、安民、利民及富民等四个层次的政策安排与内容建构,它们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着民生项目当下性与长远性、整体性与层次性的有机统一。
具体而言,一是保民。“保民”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任务。它是构成统治合法性的社会维度。古人认为“保”的意思是“养”,“保民”就是“养民”,能够让民众活下来。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不仅是家庭及社会的任务,更主要的是统治的基本要求以及国家的社会职能,“保民”从来都不是针对普通百姓的,而是对统治者的基本要求,这其中的“保”不是“自保”而是“他保”,是国君对民众最基本生计的保障,内含“接济”和“托底”之意。《尚书》 讲“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说的就是君王要能够救济天下百姓,使之免于挨饿受冻,这是保民或养民最基本的内容,是德政或善政的前提。孟子说过,“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国语》 也言:“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国语·周语上》)《尚书》 《孟子》《国语》 等典籍虽然反映出一种治国理政理念及施政措施,构成了历代君王的国家治理要求,即君王要切实保障民生,灾荒时开仓放粮、赐谷济生。这些措施与积粟备荒、抚恤鳏寡等一起成为古代社会最常见的保民之策与养民之方,并以不同的形式传承下来,使之具有了时代性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期,还是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乃至进入新时代以后,党和政府始终把保民作为民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与优先目标,始终重视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持续开展与时俱进的社会救助政策供给及其活动。一方面,政府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群众基本的生活需要出发,任何时候均优先实施困难群体的生活救助,在此基础上逐步拓展救助项目,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标准,统筹救助层次。另一方面,政府及社会各界根据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民众生活需要的现实,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综合运用物质、生活、精神以及服务等救助类别,扎实开展长效救助与临时救助,乃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助,实行托底救助,努力探索项目、对象及任务的精准性,采取全程救助、全项目救助以及持续救助,坚持“低保托底扶贫”,做到“脱贫不脱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社会救助卓有成效。
二是安民。“安民”是指能够洞察民间疾苦、治理动荡不安的社会,切实安定人民生活。根据皋陶的看法,这是治国理政的核心要义,也是君王能否成就一番伟业的基本要素。《尚书》 中提到“在知人,在安民”,使民众免于恐惧。禹帝认为,能够安抚民众体现着君王的仁惠之心,从而得到民众的拥护,这就是禹帝所说的“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皋陶谟》)。初唐时期的孔颖达将这个“民”理解为“下民”“普通民众”,“安民”就变成了“安下民”。一方面,“安民”要能够洞察民间疾苦,“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察其疾苦而已”〔1〕,如果不能洞察民间疾苦,那天下不可能太平;另一方面,“安民”就要给予普通百姓基本的生活保障,足以“事父母”“畜妻子”,从而保证“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为此,君王当“修己”以“安百姓”,对民众须“齐之以礼”,让他们“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避免动辄“齐之以刑”,减少民众做出有违社会伦常、破坏社会规则之事。也就是说,通过“济世”“治国”“保国”等手段去“安民”,建立“太平盛世王朝”,凝练成安宁有序的社会秩序,安民成为重要的民生内容。
保障民众的日常工作、生活及整个社会秩序的安全虽然在传统社会里难以真正实现,但却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届政府十分关注的重要民生议题。历届政府把保障人民安全,特别是保障民众生产、生活、生命及财产安全当成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目的。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初就颁发了 《劳动保险条例》 及“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就职工因公负伤、伤残乃至死亡等方面予以规定。此后,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发展实际,发布了 《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颁布了 《工伤保险条例》,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各类困难群体的生活救助制度,构筑生产及生活安全保障体系。不仅如此,政府及社会各界致力于公共生活空间的安全建设,注重民众心理安全的建设,加强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安全处置,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治共享的社会安全综合治理体系。我国的安全指数全球领先,业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安定有序、安居乐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共识与最强声音,安民成为民生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三是利民。“利民”就是统治者要为民谋利,让民众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明君所应具备的德性,也是治理国家应有的规律。唯此,民众方可心悦诚服地顺从他。《文心雕龙》 中记载,舜帝曾经在祭祀中就表达了“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的理想与志向(《文心雕龙·祝盟》),这成为舜所以称帝并为后世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后世,墨子以“义”释“利”,把“义”当作“利民”之基,认为“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2〕。在墨子看来,治国理政当“利民谨厚”,须“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3〕,这样方能长治久安。后来,荀子提出“利民”就是“善生养人”,要采取“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等政策,以“善班治人”(《荀子·富国》)。在这里,这些利民之策的目的就是能够更好地“治人”,进而治理好国家。这表明,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下的“利民”就已经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要求与有效手段,难怪刘安把“利民”作为治国之本,告诫“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汜论训》)。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现实之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我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为民谋利的治国理念,在各个发展阶段实施了许多利民举措,让人民群众在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将改善民生之策作为国家治理的社会方略成为全党上下的普遍共识。一方面,为适应民众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中产阶层不断扩大、民生不断改善的客观需要,政府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20 世纪80 年代的800元逐步提高到2008 年的2000 元、2011 年的3500元直至 2018 年的 5000 元,并将子女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纳入到专项附加扣除中,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充分发挥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另一方面,政府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扩大义务教育年限,提升教育质量,普遍性地建立公共就业、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公共卫生以及公共环境等利民项目,增加公共服务的资金与服务投入,增强了公共服务供给的便民性与利民性,形成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有力践行了“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四是富民。中国语境下的“富民”虽然也可以用来描述民众的生活状态与生活水准,但更多地是指君王勤政与善治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是对君王特别是明君圣主的施政要求,因而体现着国家治理的逻辑链条,“富民”被当作国家“善治”与“易治”的条件与标志。管子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管子·治国》)孔子也认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4〕。孟子提出,富民就是要做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孟子·梁惠王上》)。所以,荀子说过:“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从政策措施上看,管子的“九惠之教”,孟子的“制民恒产”,荀子的“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及“节用裕民”等都是富民之策并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体现着治理的意图。后来北魏孝文帝推行了“均田改革”,通过“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以“兴富民之本”(《魏书·高祖纪上》)。善待人民、让人民富裕是历代君王强国梦的抓手,富民自然就成为民生的一部分,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真正实践。
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人民的富裕,富民成为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必然要求与重要表征。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依靠群众建立一个独立、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成为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与追求。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府便着手制定一五计划,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走“一化三改”道路,为实现人民富裕进行了开创性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20 世纪80 年代,政府相继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共同富裕等富民策略。21 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党和政府常谋富民之策,加大对民生事业投入力度,努力补齐民生短板,深化对社会保障认识,将社会保障上升到民生保障这个层面,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与幸福感,切实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富民与保民、安民、利民一起成为政府向社会的庄严承诺,政府把民生保障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强调国家在民生供给特别是民生保障中的责任担当,保民、安民、利民及富民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民生保障体系。
二、民生保障制度的诉求分类
民生保障是一个包含项目、制度及政策等在内的综合体系,涉及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及住房等多个方面,贯穿民众生产、生活的始终。从层次上看,每一项民生保障项目乃至整个民生保障体系都有待遇水平由低到高的问题。结合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总和这个指标,根据传统社会的保民、安民、利民及富民思想与实践探索,我们可以将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和富裕型等四种类型,体现了不同的民生诉求、责任担当与治理状态。
一是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托底,特别是给予特定项目和标准、特定对象及范围的托底是当今世界各国设立社会保障项目的通行做法,只不过发达国家不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把托底作为一种民生项目去理解与建设的,而是从公民权利角度去理解社会保障项目,强调社会保障是个人权利获得基本保证的标志,主张社会保障要能够解决个人的基本需要。就我国而言,新中国刚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聚焦于生存性救济,不仅标准很低、救济项目极少,而且以临时救济为主,常态性、制度化的救济并不普及。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从长治久安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把握好“治国”与“利民”、“强国”与“富民”的辩证关系,更加注重“兜底性民生建设”,注重托底型民生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切实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筑牢国家治理的基础。
从对象上看,托底型民生项目不仅满足当下应给予救助的群体,而且充分考虑到处于救助边缘的群体的基本需求,因此这个“底”所覆盖的人群理当做到“应托尽托”。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宁,执政之基才能巩固。从项目上看,托底型民生不仅包括灾害救济及各种临时救济,更包括日常生活、养老、照护、医疗、教育、住房以及突发性公共事件等涉及到人的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各个项目总和,避免某类事件的发生引发的社会动荡不安。所以,这个“底”应该是涵盖民众最基本生活的全部,是政府的“责任之底”。从方式上看,托底型民生项目着眼于治理的规范性与确定性,将过去的以临时救助以及零碎救助为主,改为现在的以常态化和规范化救助为主;变过去的一次性救助为主为现在的制度化救助为主,故而这个“底”成为政府的民生治理规范要求。从保障水平上看,托底型民生项目不能只满足于被救助对象当下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且要充分考虑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托”的这个“底”也要与时俱进地变化。就资金支出而言,托底型民生支出要达到城乡居民的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医疗保障、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等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之和的60%左右。①关于四种民生类型待遇标准的测算过程及结果,参见高和荣《论托底型民生》一文。从目标上看,通过托底型民生项目的建设,筑牢最基本的民生保障网络体系,不仅能够解民所困,让民众有尊严地活下来,而且要能够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动荡不安,促进安定有序,实现长治久安,这是托底型民生保障的治理意蕴、制度定位与价值目标。
二是基本型民生保障制度。托底型民生保障面向需要帮扶的生活困难群体,因而具有对象及项目的限定性,那种针对普通大众基本生活需要的项目则由基本型民生予以保障。基本型民生就是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设计、项目供给及政策实施,以便在最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实现有效治理。这不是从项目数量上探讨而是从保障水平、资金投入以及治理成效角度去探讨的。因此,基本型民生不是项目不全的民生,不是“绝大多数的民生事项”〔5〕,而是项目齐全的民生,包括衣食住行娱、生老病死葬等一系列民生事项,包括常态性以及非常态性的民生事项。这样的民生投入不能引发社会分化乃至社会不公,而是能升级社会的治理。从涉及对象来看,基本型民生应该面向除了需要托底保障的群体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解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就最大范围内夯实了治理之基。它是托底型民生的提升,也是改善型以及富裕型民生的基础。从保障项目上看,基本型民生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和心里层面;既包括个人层面,也涉及到社会层面,如民众基本的教育、基本就业、基本医疗、健康卫生、基本养老、长期照护、基本住房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政府及社会各界有义务予以保障;既包括日常性的,也包括应急性的。从资金投入和待遇水平上看,这些民生项目的投入要能够与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总和相当,这样的资金投入强度才能满足民众基本的生活需求,并为其进入到改善型乃至富裕型民生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三是改善型民生保障制度。人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样性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治理手段以及据此所供给的民生类型具有丰富性,以便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凝聚。所谓改善型民生是指民生项目进一步优化、民生待遇进一步提升、能够满足人的不同发展需求、有助于完善国家社会治理的民生保障体系,它着重解决民众如何通过适度缴费以提高自身生活水准的问题。因此,改善型民生可以从质和量两个维度加以规定。从量的方面看,改善型民生并非针对全体社会成员,而是以解决部分社会成员的较高生活需求为主要任务。改善型民生并没有涵盖全部民生项目,而是从部分民生项目需求入手逐步提高与完善,并努力扩大民生项目类型。不仅如此,它还兼顾民众个性化的需求进行差异化的供给,以增强某项民生项目供给的精准度与契合度。就民生保障资金投入来看,改善型民生保障的资金投入总量应该是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总和的1.5 倍左右,以便能够在保障基本的民生投入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运用到民生项目改善中。从质的方面看,改善型民生是人生存与发展的手段,着重解决部分民众生活水准及生活品质提升问题,解决民众在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之后还能够享有周到的生活服务以及良好的精神生活需求的问题,从而透过这类民生项目的供给增进民众的发展能力与发展平台、发展机会与发展前景,避免各类民生项目供给与获得过程中出现歧视,体现社会和谐与进步。
四是富裕型民生保障制度。富裕型民生是一种民生项目更加健全、民生待遇进一步提升、民生服务更加优质均衡、民生投入更具持续性的高质量保障体系。从价值基础看,富裕型民生扬弃发达国家的普遍主义原则,坚持共同富裕理念,把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与品质当作增强人民获得感的集中体现,把建设富裕型民生保障体系当作发展的成果与人民共享的必然要求,进而作为党和政府的初心与使命,这就使得民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目标的任务有机统一起来。从目标上看,在富裕型民生保障体系下,各类民生项目建设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目标,劳动与就业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的自由发展的中介;教育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播与灌输,而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激发与释放;基本物质供养已不再是养老保障的重心,周到而便捷的生活服务及长期照护成为养老保障的共识;医疗的目的不再仅是疾病的治愈以及生命的延续,而是健康生活的有力保障;住房不再是栖息之地,而是温馨的港湾及乐业的前提。从民生保障资金投入来看,富裕型民生保障的资金投入总量应该是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总和的两倍左右,以便能够全面优化各类民生项目的投入结构,提高民生供给水准及品质,让民众普遍地享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完善的生活服务、周到的精神生活以及充分的发展机会,使之成为整个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表征,通过民生投入让各种有利于国家及社会治理的元素充分发展,实现国家与社会治理任务及目标。
上述依据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总和划分的四种民生类型是一个有机整体,保障待遇及保障层次由低到高共同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全部社会发展阶段中,以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需要,不仅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更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体现了民生保障与国家治理的内在一致性与逻辑必然性的同一。
三、民生保障制度的中国本土化特征
透过整个民生事业的实践以及民生保障的内容及类型,从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等纳入到民生保障体系中,为中国的民生保障体系打上深深的国家治理印记,体现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目标,民生保障制度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民生保障制度成为构建公序良俗的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展示着中国特色民生保障体系的独特功能,彰显民生保障的文化特质以及由此所展示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使得中国民生保障制度具有迥异于欧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鲜明特点。
一是民生供求的义务性。众所周知,工业社会与个体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各类社会保险及社会福利制度的两个基础。它们强调工业社会的到来不仅使得个人面临着与前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风险因素,而且瓦解了前工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家庭保障体系,因而需要给予民众相应的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以应对社会的变革,这样的社会保障及其福利待遇是公民社会权利的一部分,构成个人立足于社会的基点,也是国家统治取得合法性的条件。由此鲜明地反映出,立足于个人主义及工业社会基础上的西方社会保障更多地强调个人的权利性和无条件性,而较少地突显获得社会福利的条件性与义务性;较多地考虑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结构性、制约性之后所形成的必要补偿,而忽视个人的福利获得对于国家及社会的引领性与建构性。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强调民生保障制度在国家治理框架下依靠政府及民众的共同推进,而不能脱离国家治理的框架,变成国家、政府或民众单方面的事情;民生保障制度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生活结构与自上而下的政策建构的统一,体现了民众获得相应保障的权利性以及国家或政府的责任性,蕴含着国家为实现治理目标所承担的义务性以及民众为获得此福利所需要的条件。在传统社会里,君主给予民众生活保障是取得统治合法性的前提,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否则必将遭到民众的反抗。正如 《尚书》 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山海经》 也说,大禹之所以获得禅让并称帝就在于“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6〕,进而安定了民生。反过来,如果民生凋敝乃至民不聊生,则天下民众揭竿而起推翻君主的统治。对君主来说,民生保障的条件就在于“勤”,对民众来说则在于“俭”,所谓“克俭于家”也包含这层意思,舍弃了这些必将出现“民人失据”最终导致“祸至无日”。到了今天,民生保障构成了国家现代治理的手段与抓手,民生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坚持个人的社会责任担当以及治理目标的客观要求,被赋予了国家及地方治理功能。因此,中国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现了国家及民众双方各自的义务性和条件性。
二是民生保障制度的整体性。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社会保障及相关福利必将落脚于自我幸福感与满足感的获得上,导致社会保障制度更多地考虑个人福利权益、福利项目及福利水平,自然就简单地以为个人福利的总和能够等同于社会的整体福利状态,进而较少地从长治久安高度去顶层设计国家与社会的整体福利体系,统筹推进整个福利项目、福利制度及福利政策的建设,各项社会保障或福利政策往往沦为即时性的选举工具,甚至成为政治交换的筹码。这使得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项目建设缺乏整体性、公正性与持续性,他们的社会保障建设呈现出单一性与趋同性,而无法体现各国民众生活乃至国家治理结构的独特性。这样的社会保障建设同国家治理使命没有任何关系,国家成为纯粹的福利提供者,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遭到民众的抗争,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与停摆。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民生保障制度建立在方法论整体主义基础上,在尊重个人独立性的基础上注重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群体性,强调人不能无群,坚持个人保障与全社会的保障存在着文化的相近性以及生活上的涵容性,个人保障受到整个民生保障战略及国家治理目标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民生保障以整体的形式、系统的方式、长远的目标呈现出来,展示了整个社会所要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我们把民生保障纳入到国家治理这个平台上,就是强调民生保障不仅要关注个体的保障项目和保障水平,注重民生保障项目设置的科学性建设,致力于把改善民生当作增强人民获得感的集中体现,当成发展的成果与人民共享的必然要求,而且要更加强调社会整体的目标与功能。民生保障承载着国家治理的任务与使命,透过民生保障以凝聚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团结,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三是民生保障制度的理想性。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较多地针对民众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以及教育、就业、住房等具有现实性、风险性问题,更多考虑政府当下的福利供给能力和民众福利需求的满足程度,因而他主要讨论个人或社会当下的福利项目及福利状态,讨论个人所面临的生活风险因素,但很少地考虑福利供求的历史与文化特性,较少地考虑福利供给的代际转移支付能力及可持续性,忽视了福利供求的未来走向特别是透过福利供求展示未来生活图景。在这种情形下,西方的社会保障更多地强调当下性与经验性,更多地考虑自身社会保障项目及待遇的可得性及可检验性,而较少地考虑社会保障对于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与此不同的是,我国的民生保障不只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行动,更多地蕴含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国家对社会成员生活状态的一种建构与担当。不仅着眼于解决民众当下的生活问题,特别是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且建立起体现不同发展水平与生活目标的多层次民生保障体系,满足各类群体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在物质生产力极不发达、治理水平极其低下的传统社会,民众描述了想象中最好的社会生活状态,成为“小康”“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提出了“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期盼。到了今天,民生保障作为社会建设的工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并与国家治理的任务及目标相偕而行,社会建设达到什么水平,国家治理达到什么状态,就需要并努力形成与之匹配的民生保障体系;民众的生活水平及生活需求达到什么状态,就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民生类型存在。最初我们致力于托底型民生及基本型民生的建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将要求我们践行基本型民生乃至改善型民生举措。当下,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富裕型民生保障制度的探索实践,显示出我们的民生保障具有面向未来的品格与特性,践行着民族复兴的功能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