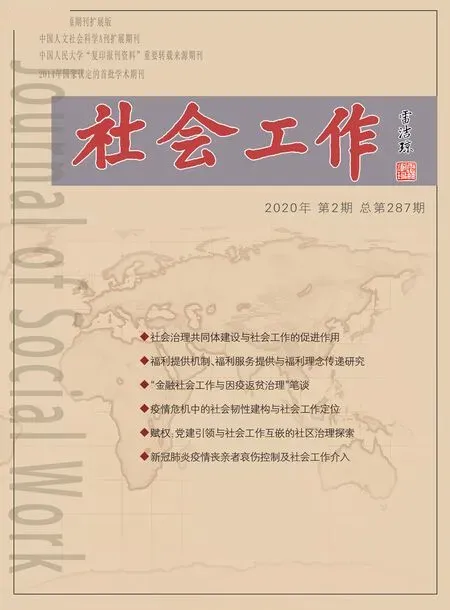从抗疫看公益基金会的专业能力建设①
蒋国河 任双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公益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是慈善等公益事业的重要载体,然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来看,其经历的是一场“大考”。所谓基金会,根据清华大学王名(2008)定义,可称之为“基于捐赠的公益基金”。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所有基金会都必须是公益性的,因此可将公益性视为基金会的本质属性之一。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种类型的基金会数量已经超过7500家。根据我国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各基金会根据资金来源不同可分为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前者主要靠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的公开募捐活动获得资金以从事公益事业。更具体的分类方面,根据徐永光(2015)研究,我国的公益基金会可分为8种类型,分别是政府支持的基金会、企业背景的基金会、社区基金会、宗教背景的基金会、家族基金会、独立基金会、专业运作基金会、大学基金会,整体来看,更加多元化、丰富化。不过,中国公益基金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成长的烦恼”,甚至暴露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的典型案例,如“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庆龄基金会雕像事件”,引发了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等中国公募基金会严重的公信力危机,其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修复。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部分互联网慈善基金募而不捐的问题也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公益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及能力也因此广受公众关注。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鲜见,以往关于基金会的研究,多集中于讨论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机制和绩效的评估。笔者结合金融社会工作的视角,就这一问题做一探索性研究。
一、公益基金会的抗疫表现与专业能力
应该说,面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重大疫情,各类公益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募集善款和物资运往湖北武汉和其他地区等重灾区,为全国尤其是武汉地区战胜疫情做出了贡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9日17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接受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98641.99万元。其中,接受资金77441.38万元,物资价值21200.61万元。截至2月3日12时,湖北省慈善总会共接收疫情防控捐赠资金合计341346.88万元,共接收疫情防控捐赠物资合计696.78万件,其中已转赠并实际到货捐赠物资合计402.76万件。除了这两家大型的官办慈善基金会,其他基金会也积极响应,如韩红基金会筹款2.78 亿元(截至2020 年2 月9 日);截至2 月10 日20 时30分,壹基金在水滴公益、支付宝公益、腾讯公益、轻松公益等平台的爱心筹款共计19450122.32元;截至2020年2月3日17时,爱德基金会募集善款、物资共计36769526.96元(含承诺捐赠),等等。同时,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新兴的一些社区基金会也积极参与到社区募捐、急需物质筹集和困难人群的救援当中来。公益基金会的这些行动对解决疫情防控燃眉之急功不可没,彰显着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价值与意义。
然而,公益基金会在这场世纪大考中仍然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从现有资料和新闻信息来看,疫情爆发后,各大公益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差强人意,或者说未达到社会对公益基金会的期许。先是有寿光捐赠蔬菜的处置风波,后又出现的武汉红十字会口罩分配不公事件,引发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又一次重大的公信力危机;韩红基金会停止接受捐赠事件也受到社会关注,该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一度得到社会较高肯定,但由于接收善款数目庞大,超出了基金会处理能力,不得不暂停接受各方捐款。此外,面对武汉封城和各地的隔离政策,各基金会在驰援灾区的行动中普遍遇到抗疫物质运输不畅,缺乏有效渠道和办法。上述问题反映了相关公益基金会在面对重大的救灾行动和巨量的救灾款物的统筹管理上暴露出的专业能力不足问题,并导致“工作方式失效①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语,引自其2020年2月1日接受网易科技《态度》栏目的专访。”。
公益基金会是慈善组织,从事的是公益金融服务,目标指向金融赋能,本质上可视为专业社会工作体系的一部分,更具体来说,属于金融社会工作的一部分。金融社会工作由谢若登的资产建设理论延伸而来(迈克尔·谢若登,2005),后由美国马里兰大学的Reeta Wolfsohn正式提出并发展,特点是鲜明地聚焦于金融能力建设(蒋国河,201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益基金会可视为金融社会工作的一部分。《社会工作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对金融社会工作概念的解释是:对21世纪的美国人而言追求金融福祉、积累金融资产是个人的责任,但研究者发现许多美国人难以达到此种程度,社会工作者因长期与低收入户和弱势族群的相处历史,因此社会工作者可以透过教育和训练去协助民众调整他们的行为,或是充权案主的能力,如此一来社会工作者能够有效帮助人们掌控他们的金钱和生活(Reeta Wolfsohn,2012)。金融社会工作的实务在美国开展较多。马里兰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于2003年设立“金融社会工作中心”,并开设相关课程。他们从跨学科的方式,分别从与金钱有关的认知、感情和态度探索金融行为改变的知识与技能。金融社会工作的发展,在美国引起重视。随着美国金融自由化、社会安全制度改革所得替代率下降、整体贫穷率及个人债务增加、个人金融知识欠缺的大背景下,金融能力(financial capability)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而社会工作者们一方面因为经常与经济弱势者打交道,原本就提供诸如现金救助、就业培训、实物给付(如住房、食物和其他援助)等服务,且在教育乃至训练养成中,具备行为变迁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成为适合协助经济弱势者建立金融能力的专业(Birkenmaier,J.,etc,2013)。
疫情之下,金融社会工作能够发挥独特的专业价值,能够帮助服务对象发展保障自己经济金融安全的能力,应对波动的不确定风险和脆弱性。即金融社会工作力图整合社会工作实践与服务、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的供给、以及市场经济私有部门对个体经济金融资源的提供,为所有人在生命全周期内的经济金融安全提供一种制度化的保障力量①黄进,《不确定的世界与脆弱性:金融社会工作的使命》https://mp.weixin.qq.com/s/Dot-AcanGQngObKm6ULqkg,2020。。而通过基金会链接金融资源或捐赠资金,实现急需资源的再分配(加拿大在新冠疫情中创设的紧急援助福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进而为疫情之下的社区居民提供物质援助和专业服务,保障服务对象的经济金融安全,提升他们应对不确定风险和脆弱性的能力,显然,可视为金融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当然,金融社会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工作,其不仅包括资源的链接角色,更重要的是通过金融来赋能弱势或困难群体,比我国台湾的辅仁大学成立了一个金融社会工作教育中心,其课程核心内容包括理财、信贷、个人发展账户等的尝试。具体实务活动包括:金融资产管理或理财方面的知识培训或咨询,协助家长建立家庭生活发展账户或制定家长生涯发展规划,提供短期免费创业课程或顾问咨询,创业小微贷款支持,协助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品质、包装和营销等。
从金融社会工作的专业角度来观察,我国的公益基金会在专业能力上存在明显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财务管理和物质调度的专业化能力不足。这是此次疫情中武汉红十字会等基金会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导致物流不畅,调拨不及时。管理者未更新知识和理念,仍贯守传统的统一管理、仓储和分配方式,未建立先进的应急调度系统,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形势,尝试去中心化、数字化的现代调度、物流模式。相比武汉红十字会,“外援”九州通医药集团协助管理后,凭借其专业的供应链、物流和分销能力,医疗物资到货至分配全过程仅耗费两个小时。同时,对慈善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来说,应坚持财物管理公开、透明的原则,在这方面,部分基金会也做得不够,账目不清,管理不善。
二是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专业伦理不到位。公益基金会的专业伦理可视为从事慈善组织工作应有的职业精神、价值观、使命感和道德感。公益基金会工作本质上是专业社会工作或金融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应该秉承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其核心是利他主义,关怀弱者,尊重、平等、接纳。此次疫情中,某些基金会出现在口罩等防护物质分配时,过多关怀民营医院和单位领导的现象,眼光“向上看、向钱看”,忘却了医护人员优先、弱者优先的基本伦理操守,是缺乏专业伦理操守和应有的道德感的鲜活表现。
三是面向民众的专业服务能力欠缺。公益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表现为承担运口罩、分口罩的角色印象,即仅承担收发职能的机构,甚至分配的功能都丧失,也没有救援。口罩之外,公益基金会还能做些什么?(金锦萍,2020)值得深入反思。根据《慈善法》,公益基金会等慈善组织设立的根本目的是开展慈善活动、提供慈善服务。民政部因此成立了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促进两者有效对接。在脱贫攻坚中,一些基金会已经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的做法,开始加强与基层对接,实现精准帮扶。但在此次抗疫行动中,大水漫灌的现象仍然存在。如针对红十字会的问题,王振耀尖锐地指出:“如果就是一个物资捐赠的接收站点,那还叫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应该恢复法律赋予它的主动援助和救助的职能和职责,而对于疫区人员的救援,尤其需要专业化的志愿服务能力。其他公益基金会也是如此,并且更是迫切需要拓宽专业服务能力。”为此,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文,强调对应急防控物资国务院实施统一管理、统一调拨,这就意味着应急防控物资将由政府来保障供应,因此慈善组织即便筹到资金,也难采购应急防控物资,无法按照募捐方案实施公益项目。疫情之下,公益基金会等慈善组织需要找到与自身宗旨和使命相关的方向,拓展公益服务项目,比如赋能医护人员或关怀医护人员家庭,让医护人员没有“后顾之忧”;关怀因疫情生活更加困难的群体,诸如贫困人群,有病患、孕妇的家庭,残疾人家庭,监护人被隔离的孩子、子女被隔离的老人及罕见病患者等,都会面临生活和医疗方面的困难,亟待关心和救助;或者关注那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这些都有助于向民众传递爱与温暖,凝聚人心,赋能民众,解决社会问题。
四是合作赋能的专业能力和体系建设不足。《慈善法》明确,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服务,可以自己提供或者招募志愿者提供,也可以委托有服务专长的其他组织提供。就公益基金会而言,可以协同其他社会组织力量,组建大的社会力量的联盟,建立直达社区的组织体系和联动机制,从而在疫情中,能够与扎根基层、社区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组织、志愿者队伍密切合作开展应急救援救助服务,实现合作赋能。但目前,多数公益基金会未发展起与基层社区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队伍等的紧密联系以及与社区基金会跨组织间的联动机制,形成对重大疫情的群防群治。应该说,公益基金会重视合作能力和共谋发展。2008年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公益元年”,在汶川地震灾后救援中,中国的公益组织开启了合作救灾模式,但这种合作更多的是基金会的行业内合作、基金会与政府的合作,基金会与商界的合作,而缺乏与扎根社区的专业力量和志愿者队伍的合作,导致在由于政府管控物质、社区普遍封闭等因素导致的传统纽带切断后,公益基金会只能游离在社区之外,未能发挥有效的救助作用。
诚如徐永光所指出:“中国的公益生态非常落后,不仅表现于有钱的机构和做事的机构没有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供应链生态圈。这为中国公益界打造公益供应链生态圈留下巨大的空间,需要公募基金会、慈善会与公益服务组织联合起来,让公益文化、文明深入到企业社区,与政府一起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途径”①徐永光,2019,《30年公益进退如之何?》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9-11-23/doc-iihnzhfz1230462.shtml。
二、公益基金会专业能力建设的路径
针对上述不足,后疫情时代,公益基金会应该励精图治,改善治理,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以善治助推“善业”。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加强专业建设:
一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伦理教育,巩固专业伦理和使命感、道德感。针对此次疫情期间,出现的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专业伦理不到位的情况,基金会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工作人员的专业社会工作伦理教育。一方面,对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基金会应通过继续教育或定期专题学习等形式,大力开展面向所有工作人员的专业伦理和价值观教育。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在继续教育的过程中,既应该注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政治教育、国家重大民生保障的政策理论学习,应注意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尤其是专业社会工作伦理、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等各类知识都需要深入地研究与理解。其次,各大基金会组织,要不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或经验交流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专业社会工作伦理知识进行讲解,或者邀请经验丰富的基金会工作人员分享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专业社会工作伦理难题以及应对方法,帮助基金会工作人员将学到的专业社会工作伦理知识应用于实践,进一步巩固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专业伦理和使命感、道德感。
二是加强具有复合型特点的金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既懂财务、管理又懂社会工作的新型基金会管理人才,提升专业管理与服务能力。首先,基金会在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加强专业伦理、专业背景与专业能力的考察,招聘的人员不仅要具备一定的乐于奉献、乐于公益事业的心理状态,同时还需要符合能力与岗位相适应的原则,优先选聘具备多种复合型能力的金融社会工作人才,或者具有在金融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双重经历的专业人才。当然,目前金融社会工作的发展在我国尚处于初始阶段,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有待加强。为此,基金会应该加强与相关社会工作院校的产学合作和协同育人,共建实习实训基地,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甚至实现订单式人才培养;其次,工作人员在入职基金会时,基金会需要加强对入职人员进行培训,一方面,使其了解本基金会的宗旨、理念、价值观和历史等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可引入相关线上线下课程,加强对员工管理知识、财务知识和金融社会工作等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有利于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多项专业技能提升,比如能够提供如前所述的金融资产管理或理财方面的知识咨询,或协助疫情家庭、社区建立个人发展账户或制定疫后发展规划,从而实现从一般的物质或款物管理、分配向既懂管理又懂社会工作服务的新型基金会管理人才转变。
三是加强应急志愿服务能力培训,提升面向基层民众的应急救援、危机干预和资源链接等专业服务能力。部分公益基金会由于长期处于舒适圈,很少应对大型的突发事件,导致在此次突发疫情期间暴露了自身应急志愿服务能力不足的缺点。此次疫情给了公益基金会一个警示:要“未雨绸缪”,而不能仅仅是“亡羊补牢”。公益基金会的应急志愿服务能力培训,应该涵盖面向基层民众的应急救援、危机干预和资源链接等专业服务。这里的应急救援能力的提升,并非一般的孤立的应急救援,而指的是,公益基金会必须学习如何把社区民众中的积极分子、志愿者、专业人士充分地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实是指的是突发和应急状态下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这方面的能力亟须提高。疫情之下,有可能爆发各种形式的危机,包括现场秩序混乱甚至失控、员工心理创伤以及组织应对不力造成的公信力危机等。基金会可以邀请经验丰富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和业界精英在基金会内部进行危机干预培训或者开展经验分享会,提升员工危机干预的能力。加强资源链接能力,实是要提升基金会的资助服务功能,提升资源链接的多元性和有效性。这在武汉封城的背景下,尤为重要。疫情期间,大多数基金会在物质资源的筹集和链接上优势。但武汉封城后,除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当地的慈善总会等慈善组织可以在城内开展业务外,其他基金会均难以直接开展活动。在此次疫情期间,一开始,基金会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募集和发放口罩等防护物质,但随着武汉封城和防护物质被政府管控,基金会的功能几乎停摆了下来,即使募集了众多资金也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因此被外界指责募而不捐。此时,亟须拓展资源链接的功能与形式。资源链接不仅仅是物质援助,还包括链接其他方面的资源。在此情况下,基金会应该转变思路,发挥服务资助或购买服务功能,针对疫区民众的多样化社区服务需求开展资源链接服务。比如,对于在疫情中出现心理问题的患者,基金会可资助相关心理服务机构或社会工作机构链接心理辅导服务;对于无人照顾的老人、孩子,基金会可链接人文关怀资源,为其链接福利机构,寻找适当的照顾人员;对于无法上学的学生,基金会可以链接网络教育资源,方便其进行网上学习;对于因隔离而影响复工复产的人员,可为其链接技能培训课程或电商资源,帮助其储备能力或拓展线上商机。这些资源链接对疫区民众同样重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人民群众生活生产上的困难和难题。
四是加强和发展社区基金会,密切与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队伍的合作。在此次疫情期间,国内基金会展示了自身的公益精神与责任,但同时也暴露了其社区根基的单薄和扎根社区的服务体系的薄弱,导致在武汉封城的背景下,基金会的活动异常艰难。为此,一方面,基金会须加强其公益生态建设,加强对中国的社区公益组织、草根NGO资助或购买服务,与社区服务机构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供应链生态圈。另一方面,各方协同,加快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社区基金会,扎根社区,能够兼顾到不同社区的具体需求,并且能方便、快捷地提供资源链接和服务。大型基金会可以作为母基金会,地方企业采取参与模式,动员社区群众,与地方政府进行融合,建立符合社区需要的基金会。对于已经成立的社区基金会,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和大型基金会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帮扶,比如,成立企业慈善基金,由社区基金会代为管理。发展社区基金会离不开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队伍的加入,在突发事件中,仅仅依靠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服务是远远不够的,社区基金会应与当地的社会工作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保证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有充足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队伍对社区进行服务。社区基金会能够延伸扎根社区的服务体系、发展合作赋能,从而既知道如何与政府、企业良性互动,也能真正扎根社会和基层社区,有效整合资源,参与到社区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当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