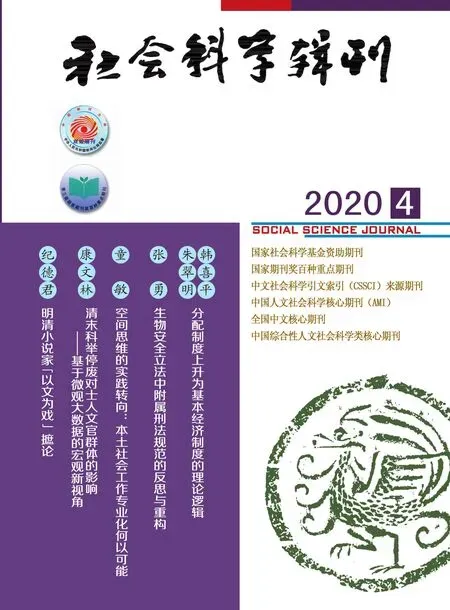晚清科举与学堂并立时期传统教育经费用途的转化
蒋宝麟
清代是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清廷及各省府厅州县支出各级科举考试及其他相关经费。除此之外,当时的教育经费还包括各种书院经费、民间津贴应考的宾兴、公车等“公款”、各级官学的学田收益以及其他各类民间办学经费等。这些经费名目均依托科举制而存续,可视为广义的科举经费。时人曾言: “若岁科考费、若宾兴费、若书院费,世所心营而目注之。所谓科举旧款也。” 〔1〕
甲午战败后,中国官绅开始广设新式学堂。戊戌变法期间,清廷曾令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为学校 (学堂),部分督抚遵旨在各省省城办理学堂,多有将书院既有经费拨入学堂的奏议。但因变法迅速失败,书院改设学堂之事因此中辍。庚子事变之后,清廷于1901年底至1902年,多次颁发兴学上谕,重令各省府厅州县新设学堂,改书院为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十年间,全国各地有近600所学堂系由书院改制而来。〔2〕书院改制为学堂,多数既有经费拨入学堂。与此同时,有小部分地区的若干官方科举经费与宾兴、公车、学田等款项开始充学堂经费之用。
中国书院史是历史、教育、文学和中国哲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领域。关于晚清时期的书院改设学堂亦有较多讨论,但书院改学堂中的经费问题鲜有论及。①王欣欣曾简略地从经费来源角度考察山西的书院改学堂问题。参见其《晚清书院改学堂中的经费问题》,朱汉民主编:《中国书院》第8辑,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4-84页。关于宾兴经费,毛晓阳对清代宾兴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废科举、兴学堂与宾兴存废的关系有专门论述。〔3〕杨品优对清代至民国的江西宾兴会组织有专门研究,其中包含科举废除后宾兴会组织的适应与转变问题。〔4〕张小坡对江南地区官学学田与宾兴的近代转变有过论述。〔5〕但科举制废除后宾兴等款在新式教育事业以及其他新政事业中的分配情况尚未厘清,仍有研究的空间。清代地方官学基本没有实际意义上的 “教育”职责,而直接服务于科举考试,与之相关的官学学田收入亦在传统教育经费之列。此外,商丽浩的专著对清代传统教育财政与近代各级教育财政有较为系统的论述。〔6〕大致而言,从甲午战后到科举制废除前,科举与学堂并立,这一时期的传统教育经费转化问题尚无专门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拟于制度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举制废除前各项传统教育经费用途转化问题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兼顾在处理学款问题上官绅、绅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各项经费的性质,以此呈现清末新式学堂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历史进程。
一、甲午后至戊戌变法前新式学堂经费中的 “外销”与 “正款”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推动,有洋务大员设立以教授科技与外语为主的各种新式教育机构,如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等。这些教育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各色洋务经费 (如海关税款)与督抚直接掌握的地方财政机构或洋务企业。②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各省督抚为筹款,绕开原本主理本省财政的布政使司(直接受户部节制),另设厘金、军需、善后和支应等各种带有财政职能的局所,故在本省的财政收支权上,督抚常越过户部而自行专擅,这是晚清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调整的重要表现之一。参见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1期,1947年6月。如1863年由苏松太道台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其经费由江海关船钞项下动支,1868年移入江南制造局后,再加之该局津贴银,其武学、铁船两馆的经费在二成洋税项下动支。〔7〕按船钞项即海关的办公费,二成洋税乃两江总督截留的关税。船钞与关税在当时虽属国家正款,但系咸同年间出现的新税种,经管权不属于户部,而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者使用时咨行户部,但是在户部仅是备案而已,例兼南洋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使用该款较为方便。③转引自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05页。而江南制造局是受江督节制、由江海关道任总办的官办企业。显见,上海广方言馆的办学经费并非专款,且在体制上并未纳入户部的经制财政系统之内。甲午战争结束后,各省官方开始创办与推广以教授西学 (实学)为主的普通新式教育机构,并冠以 “学堂”之名。1895年9月,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禀请创设天津中西学堂,10月奉旨准办,1903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盛宣怀向直隶总督王文韶禀称,天津该学堂的开办及常年经费来自于天津钞关所收的开平煤税 (系新征)、进口米麦税中抽取,加之由电报局与招商局 “捐缴”之款,开办经费动用米捐存银。〔8〕王文韶对此表示赞同,称赞盛氏:“就本任及经管招商电报各局设法筹款,不动丝毫公帑,洵属讲求时务,公而忘私。” 〔9〕
1896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江宁创设江南储备学堂,其筹备经费 “不动正款”,常年经费 “拟将仪征淮盐总栈每年节省商捐局用银三万两,皖岸督销局每年节省商捐局用银三万余两尽数拨给充用,如有盈余积存,作建堂经费。此两项均系臣新筹节省之款,应请归入外销”〔10〕。
以上王文韶所称 “不动公帑”与张之洞所言“不动正款”与 “归入外销”意义相同。不用 “公帑”表明天津中西学堂经费不动用 “正款”。即张之洞在上述奏议中断言同年北洋设天津中西学堂,“款由捐集,不动公项”,此次江南设立学堂与之相同,“系款由外集”。其中,“正款”等同于 “内销款”,“内销”与 “外销”是清代财政的两个专门概念。大致而言,内销指的是中央规定地方 (各省与府厅州县)的各项经费,有定额与专门用途,地方不能擅自变更用途与定额,收支须向户部报告 (即 “报部” 或 “奏销”)。而外销是没有定额的经费,有时用途不定,互为挪移,户部无法掌握这些经费的用途与数额 (“不报部”),地方上“自筹自用”的经费多归为外销款。晚清时期,由于地方应对各种战事、各项事业的扩展以及各项临时增加的支出,外销款数在财政经费中所占比例增加,从而中央对各省的财政掌控力度愈益减弱,制督抚也正是通过控制外销经费而扩张其财政权。①参见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1期,1947年6月;〔日〕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6-151页。
不过,并非所有督抚都有如此底气,能在创办省级学堂时应付裕如,均不赖 “正款”。1896年11月1日,新授安徽巡抚邓华熙在赴任前陛见,光绪帝对其言:“西学应办。”邓奏云:“学堂必须举办,才能造就人才。”光绪帝又云:“苦于无经费。”邓对云:“臣到任后察看情形,设法筹款奏明办理。”〔11〕同年12月6日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上谕,令 “各直省添设学堂,实力举办”,并称 “京师、上海两处既准设立大学堂,则是国家陶冶人材之重地,与各省集捐设立之书院不同,着由户部筹定的款,按年拨给,毋庸由盛宣怀所管招商、电报两局集款解济,以崇体制”,由军机大臣字寄户部与各直省将军、督抚。〔12〕按,该上谕称上海与京师的大学堂经费由户部拨给,却并未指明各省筹设学堂的经费所出之由。
1897年1月24日,邓华熙上奏,认为在京师与上海奏准设立的大学堂,按泰西二等学堂的制度,即属 “头等学堂”,其经费由户部拨款,则各省议设之学堂为 “二等学堂”,“所需经费亦拟请于各省正款内每年拨银一万两或八千两以作束修、膏火各项之需”。朱批由 “该衙门 (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引者注)议奏” 〔13〕。此前两个多月,邓华熙奏对时称能在赴任后 “设法筹款”办学堂,结果还是动用本省的正款。3月20日,总理衙门会同礼部、户部议复称,邓华熙请于各省省城另设二等学堂 “系遵照上年十一月初二日钦奉上谕,切实办理”,“自应准如所请。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咨行各省,一体照办”,关于请拨款事宜,“应由各该省妥定办法,即行奏明,请旨饬下户部酌量指拨” 〔14〕。在清代,从常规上讲,朝廷通过“解款协款制度”控制各省的财政收支,即各省奉朝廷之命征收各项赋税,同时奉朝廷之命开销各项经费,动支所剩余银两须运解邻省或朝廷。前引 “户部指拨”指的是户部批准各省可在本省正款中存留部分以拨付学堂。换言之,各省可多截留一部分本协解的经费。
同年7月17日,邓华熙上奏,请求获准在省城安庆创办二等学堂之建筑经费2万两,包括合肥县革员赵怀业、卫汝成的房产变价银1700两,“其余不敷,另筹足用” 〔15〕。8月28日,他再请准二等学堂常年经费每年约8640两,“拟于本省地丁、厘金项下,分别动支”〔16〕。地丁、厘金系税收之大宗,地丁大部分提解中央,亦有留支本省,厘金为本省留用。这就意味着邓华熙计划从本省地丁、厘金中拨付学堂经费,系报部正款。
当时浙江并未奉旨设 “学堂”,而是在杭州新设一所求是书院,兼授中学与西学,其常年经费与购置仪器、书籍等杂用费,除使用东城书院每年膏火银1000余两外,其余在杭州另五所书院的奖膏存典生息项下每年提利息洋3000余元,以及各局减并共洋4000余元,“均未动支正项”〔17〕。贵州则将贵阳的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将学古书院的基本金2000两全数拨用,另在善后局筹提2000两,作为该学堂经费。〔18〕与安徽新设学堂不同,浙江与贵州乃由书院改设学堂,书院的既有经费拨入学堂。
在20多年时间里,属于洋务的学堂与服务于科举的书院是两个平行的系统,但甲午之后书院改设学堂的思想与实践,使得两者间出现了部分由此入彼的转化。相较于规制、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等,经费的转置更直接易行。不久之后,戊戌变法开启了书院改设学堂的制度化进程。
二、戊戌、庚子后书院改学堂的经费问题
1898年7月3日,康有为上奏光绪帝:“各直省及府州县,咸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则一二所,其民间亦有公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有师生,皆有经费。惜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故经费虽少,虚糜则多。”建议在各省府州县乡设立各级学堂,使用书院、义学等之原有经费与各项陋规经费。〔19〕几天后,光绪帝接受康有为的建议①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92-495页。,于7月10日颁布上谕:“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各书院需用经费,如上海电报局、招商局及广东闱姓规,闻颇有溢款。此外陋规滥费,当亦不少,着该督抚尽数提作各学堂经费。”②《清德宗皇帝实录》卷420,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册,第504-505页。部分文字据茅海建所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洋务档”,原文有所修正,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94页。由此,各地书院改设学堂、书院经费用于学堂成为一项正式制度。
查明书院数量及束修、膏火等经费,是为了便于尽早改办学堂。清代书院经费来源较为多元,按来源的标准,大致分为官府赐拨、百官资助、民众捐输和书院经营等大类,所以是官款和私人(含官员)捐款兼而有之。清代书院经费的管理模式主要采取士绅联合经管的董事制。当下学界基本有共识,清代书院呈现明显的 “官学化”特征,特别是省城书院更受官府的控制。③例如,在山西,除省会太原与河东地区外,其余各府州县的书院经费“归绅士经理”。参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47页。因此,书院的经费管理亦受官府督导。
戊戌兴学上谕颁布后不久,部分督抚就积极响应落实。如山西准备将太原的令德书院改为省会学堂,常年经费4000余两改拨学堂,另每年在厘金项下拨银6000两。〔20〕同时,山西巡抚迅即查明所属各地的书院数目及大致的经费总额,并令各书院 “一律改为中西兼习之学堂”,但 “必须添筹经费” 〔21〕。据学者不完全统计,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时期,各省通令省城及各属书院改设学堂者数量甚多,惟山西一省就有109所书院改学堂,但因变法骤停,所以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改制的书院仅有20余所。〔22〕值得注意的是,书院改设学堂,书院既有经费多不敷用,而且一般仅占少部分。
从7月10日上谕颁布到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仅两月余,各省无论是新设学堂还是书院改设学堂,实际实施效果终归有限。戊戌变法终结后,书院改学堂以及新设学堂均告中辍。④据关晓红的研究,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下旨各级科举考试“悉照旧制”,书院制度保持不变,但并未明令停办学堂。学堂虽未被明令取缔,但事实上陷入停顿。参见关晓红:《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
庚子事变后直至辛亥,清廷推行新政改革,即“清末新政”。以兴办各级各类学堂为中心的新式教育制度改革,是清末各项新政中施行较早且范围较广的事业。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专门关于兴学的上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23〕
比较后不难发现,此上谕 (辛丑兴学上谕)与戊戌兴学上谕有诸多相似之处,其核心即改书院为学堂。这表明实际掌握朝廷大权的慈禧重拾三年前实际停顿的兴学改革举措。两个多月之后,11月14日,清廷再发上谕,催促各省督抚尽快兴办学堂。〔24〕
朝廷通饬各省 “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可见其对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兴学的急切之情。查相关资料可知,从9月14日兴学上谕颁布至11月14日,各省中仅有时任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报该省兴办学堂事宜。袁世凯称,在本年春间,他已应诏条陈,“以广建学堂为请,一面访订教习,筹商规制”,但因请假而使其筹办学堂的工作中辍。八月初二销假后,他通饬各属一律兴办学堂,“并筹赀择地先于省城改设大学堂”〔25〕。省城大学堂常年经费年需6万两,日后渐次推广,经费再随时增加。袁世凯计划将其整顿契税的收入拨充常年经费。在奏折附 《山东省城大学堂暂行章程》第四章 “经费”规定:“学堂常年需用经费,就现在办法估计,暂以六万两为限。候巡抚拨定的款,每年分四季赴藩库具领。嗣后如议扩充,原拨经费不敷开支,再行酌量添拨。” 〔26〕
朝廷将袁世凯筹办山东学堂的规章作为各省仿照办理的 “样板”。不过,细审袁奏及其附件,内中虽称省城大学堂系 “改设”而来,但未交代其究竟由哪一所书院改设;虽然袁世凯宣称其经费可从契税中拨充,但正式章程中并未确定。同样地,与戊戌兴学上谕不同,辛丑兴学上谕既未规定各省兴学的经费来源,也没有规定书院改学堂后旧有书院款项的去向。尽管如此,从之后各省督抚奏报的情形看,各地 (尤其是省城)兴学多以书院改设而成,书院经费多作为新学堂经费来源的一部分。
继袁世凯之后,从1902年初起,各省督抚、学政陆续奏报本省关于兴学的大致计划。清代江苏学政驻江阴县,江阴的南菁书院由时任江苏学政黄体芳于光绪初年创办,此后一直归学政直接管辖。戊戌年间,时任江苏学政瞿鸿禨奉旨改办高等学堂,除将原归书院的松江府川沙厅沙田继续招佃收租作为经费外 〔27〕,该书院还获上海县姚访梅的沙田万亩以增加收入。〔28〕辛丑年兴学上谕颁布后,江苏学政李殿林计划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正式改南菁书院为学堂,“办事支销系就书院原有经费酌为区画,未能添筹” 〔29〕。也就是说,改制之初,书院旧有经费 (沙田租息与存典生息)完全转为学堂经费,不多也不少。〔30〕除书院款之外,该学堂无其他款项挹注,导致办学经费紧张。直到1905年初,署理江苏巡抚端方将苏州鼓铸铜元余利项下每月拨银1000两作为南菁的常年经费。〔31〕福建兴办大学堂之法是先将福州的正谊书院地基的2/3划出,加之购置附近民房,供大学堂专用。其经费从福州各大书院的膏火中提出三成,“略资津贴,不敷之数,饬由司道力筹的款” 〔32〕。福建在省城兴学的方式是保留原有书院 (正谊属部分改制,仍继续办书院),将各书院的部分经费移至学堂。“的款”即基本金经费,而书院经费仅能 “津贴”而已,足见后者在大学堂经费中占比之轻。
还有将书院部分改制、部分保留的情形。江苏巡抚较早上报本省 (苏属)兴学诸事宜。当时,省城苏州的大学堂由戊戌年间奏请设立的中西学堂扩充后改名;省城的正谊书院改为苏州府的中学堂,仍名 “正谊”。大学堂年需经费数万两,中学堂年需经费万两,“均由藩库及善后局分筹济用”。此外,平江书院改为长洲、元和和吴三县小学堂 (三县同城),经费由三县 “就地设筹,如有不敷,由司局酌拨”。至于苏州原有的三所书院中,保留紫阳书院,“改课经算策论”,正谊、平江两书院作为附课。此三所书院原有支出的七八千两经费,“学堂添此一款,不敷尚多;寒士少此膏火,生计更窘,应请一律留作校士之用。庶贫老诸生及质地不能选入学堂肄业者仍得以养赡有赀,从容变化”〔33〕。这就意味着,一则苏州的三所书院并未全部改为学堂,而且三所书院的原有经费依旧保留原有用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举仍行,部分士子仍欲通过原制度进阶,未进入学堂肄业,书院膏火仍作为其生活来源之一。①此种因书院改学堂致士子失去膏火补助的担忧,在当时较为普遍。参见《论中国近日读书之不易》,《申报》1902年2月18日,第1版。二则书院旧款之于新设之学堂经费,仅占很少一部分。这种书院改制的模式可能较为普遍,曾遭舆论批评:“既诏改书院为学堂,则凡有书院经费自当悉充学堂之用。乃阅报章所纪一处有数书院者,改者虽改,留者仍留,不顾学堂经费之不足,又安能鼓舞人才耶?” 〔34〕
1902年起,各省陆续应诏兴办学堂。各省省城本为书院汇聚之地,加之督抚有权动用或筹措各种经费,无论是书院裁并改设学堂,抑或新设学堂,省城学堂的筹设较之府州县顺畅。况且,外属书院的经费可能更为短少。当时山西外府州县书院 “原有之经费,其每年实银六百两以上者不足二十处”,巡抚岑春煊先行将这些书院改设中、小、蒙养学堂;余下那些书院 “仅有钱文一二百千、三四百千不等,改设亦苦不敷”,所以暂时合并办学。〔35〕岑春煊仅指出动用书院旧款。无疑,在当时的书院改学堂的现实过程中,不可能不动用其他款项,包括宾兴、公车等公款,甚或外销性质的科举经费。
1902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令泰兴县将庚子年(1900)后的宾兴、公车息款,“每年提一半归学堂购置书籍,一半仍留为宾兴、公车之用” 〔36〕。1902年初,驻江苏扬州的两淮盐运使程雨亭在城内东关街创设中学堂,将安定、梅花两所书院的常款提出一半,作为中学堂经费;将两所书院改为校士馆,另一半书院经费作为月课、膏奖。两书院 “向章每月两试,一为馆课,一为小课,今校士馆仍循曩例。惟款既减少,则取额不克如前” 〔37〕。可见,在扬州,书院部分改设为学堂,书院的部分经费移入学堂,书院则以校士馆的形式存续。这是将旧式教育经费暂挪新学堂的做法。
尽管情形各异,但省城外的府州县兴学动用包括书院款在内的本地各项传统教育经费,是当时的惯例。大致而言,在清末兴学之初,将既有书院改建为学堂是创办新式教育最为便捷的方式。较之外属州县,省城 (及学政驻地)书院多由督抚、学政直接节制,且经费较为充裕 〔38〕,故省城书院改建学堂较为顺利,经费亦有保障。不过在科举制存续的情形下,书院并未完全失去凭藉,故主政者及经管者不会将书院经费全然用作新途。
三、官绅权力与地方各项传统教育经费的用途转化
清廷上谕所定兴学主体是由省至县的各级官员。从某种程度而言,地方官的态度与作为对本地兴学事业有重大影响。程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任直隶交河县知县,视事之初深感 “当以目前急务莫如学堂” 〔39〕,在年内即决定将废置已久的瀛南书院改建为学堂,通过各种清查手段,“合计共查出田一千二百七十八亩有奇” 〔40〕,将其租款拨入学堂。此外,他将庙产地十顷的租息与绅富的捐款拨入该学堂,最后建成交河小学堂。其实在一开始,县内士绅认为应办书院,是程坚持 “兴书院不如建学堂” 〔41〕。可见,在某些基层地方,创办学堂未必急迫,官员意志尤为重要。从交河县兴学之初的情形可以发现,当地官员与士绅就兴学及旧式教育经费的处置基本能达成共识,配合尚可。当时亦存在另一种情形,士绅兴学的态度较为积极,而官员并不急于行事。据黄炎培回忆,1902年他与张访梅、陆逸如商议在川沙厅办学堂一事,呈请同知将观澜书院改办川沙小学堂,但官员 “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许多人靠书院考月课,取得些膏火,补助他们生活,对改办学堂,成为正面的利害冲突,绝对不赞成”,所以他们在呈文中加了一句 “除同时呈请两江总督部堂批示外”,结果川沙厅不敢批驳。同一年冬天,黄炎培等人到江宁向时署理江督的张之洞投文,其措辞有根据 “上谕”的字眼,即获批准,川沙厅同知就不能反对。〔42〕
在一般情况下,各府州县及下级乡镇开办学堂,官府与经管书院、宾兴、学田及其他公共事业的士绅间需有一定协调。在清代,有许多书院设于乡镇。这些乡镇书院有许多也被改为学堂。1903年,四川巴县的廉九甲长生场里正李星门(李为廪生)等向知县具禀,称其经管本场三益书院的膏火田租,当年春天已将去年所收租谷设立蒙学28名,但非集中授课,只是由学生自行 “择师肄业”,现欲将秋收的租谷办理来年蒙学,并按朝廷颁行的 《蒙学章程》,设公立蒙学堂,获知县批准。〔43〕
在许多地方,书院、宾兴和学田等地方公款公产一般操之士绅之手,地方官有权督导,但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提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兴学之举往往受士绅权力的影响。1902年初,江苏松江府知府余石荪以在府城办学堂 “事不容缓,竭力图维”为由,饬令在育婴、全节、宾兴和浚河等公款内筹款,但相关绅董 “皆藉词推诿,未肯仔肩”。鉴于此,知府牌示:“查开办学堂为当务之急,本府前以经费支绌,松郡别无闲款可提,是以照会各经董酌量各该款项可提不可提,核复察办。……若如该堂历年既有盈余,规模又臻阔大,于此而不能酌拨经费,将群起效尤,学堂之设何日可成?”之后,知府又查明 “以上各款历年亦确有赢余”〔44〕。松江府一时兴学困难,症结在于经费,而知府欲将旧式教育经费在内的各项公款挹注学堂,遭经管各款士绅的推诿。知府牌示虽未明言,但既然各款本不紧张,那么科举制仍存与各款项用途变更带来经管权力的变化或为重要原因。最后,松江知府将云间、景贤两书院合并改设学堂,各绅董答应每年拨浚河、育婴善堂和书院等经费若干。〔45〕
在兴学之初,官府与士绅间的扞格常导致旧式教育经费无法顺利转入新教育体系之中。此外,具体操办新学堂的士绅与掌握旧款的士绅未必是同一群人,他们各自对学堂的态度甚或互相间的人际关系,对经费转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何况,这些款项有归一州县共有,亦有属一城、一镇或一乡独有。〔46〕如何在州县内的城镇乡之间分配,如何在一地中的不同区域内分配,如士绅间无共识,就易引发地域矛盾。
1902年初,浙江温州府瑞安县生员张棡等商议将莘塍的聚星书院改为河乡学堂,拟先用宾兴款购置书报,并联名呈请瑞安县衙。①张棡著,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87-88页。关于瑞安聚星书院改设学堂最初的情形,可参见徐佳贵:《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3-255页。按太平天国运动后,瑞安县逐渐建立全县于各乡 (含县城)两级宾兴体系,河乡的宾兴附设于聚星书院。几天后,县衙批准此案。〔47〕然而,河乡之北乡士绅对此颇不赞同,“有谓学堂未设,遽提款买书,多则无款,少不够用;有谓瑞城学计馆有书,尔南乡离城十余里,尚嫌远不去,北乡一二都离聚星三十里,焉能远来看书;有谓朋友借书尚有争执,今书归众用,焉能皆和;有谓宾兴有益寒儒,万不可提;有谓南北须分设学堂,公延教习为妥”。张棡认为其 “一派胡言,无非为阻挠提款之意” 〔48〕。不过,从张棡的日记来看,此后几年,南乡与北乡士绅为改设学堂及提拨宾兴款之事争议连绵。在科举制废除后,聚星书院仍未能即刻改为学堂,书院款产 “几为城绅觊觎”〔49〕。这一案例显见不同地域 (城乡)士绅间的矛盾。
在通常情况下,由于身在府州县城,亲近地方官,以及各类资源获取相对较易等原因,城绅比乡绅在支配公共经费与事业资源等方面更具话语权。1906年,江苏苏州府长洲、元和、吴三县(同城县)的书院、宾兴、公车等款由士绅潘祖谦将经管权移交长元吴学务总汇处,这批经费用来办理苏州府及三县学堂。1909年,吴县士绅柳宗棠等人禀请江苏提学使,对长元吴学务总汇处专办城中学堂而忽视各乡学务与该处设置的合理性等问题提出异议,长元吴学务总汇处则予以辩解。之后,两方激烈论争,各不相让,当时 《申报》连篇累牍进行实录报导。最后,提学使樊介轩以长元吴学务总汇处确于学部定章不符为由,将其撤销,改为长元吴教育会、劝学所经理学款处,仍由原总理蒋炳章任总理,但原绅董一律辞退,改为绅董一年一易,皆由公举;新处将腾出之款专门补助乡学堂。张小坡认为,在这一场论争中,“柳宗棠等人与长元吴学务总汇处都有一定立论根据,只是因看待问题的立场与角度不同而引发争论”②详见张小坡:《均或不均:清末江南新式教育经费的城乡配置及其论争》,《史林》2011年第3期。。此颇有见地。除此之外,因书院、宾兴等款分配引发的城乡矛盾亦为重要背景。从整体趋势看,从清末至民国时代,城乡之间的教育发展愈来愈不平衡,其中经费配置不均就是重要表现。〔50〕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地方为设立学堂而调动的旧式教育经费都较为充沛。四川保宁府接总督奎俊札饬,“催该府立即传集绅粮 (清代四川专指士绅与富户——引者注)妥筹办法,或就原有书院先行改并,或另筹款项创立规模,总须就地方情形设法办理 (学堂)” 〔51〕。接着,保宁府知府 “即传集阆中县令 (阆中为附郭县——引者注)、府县两学及院长 (即书院山长——引者注)、绅士迭次筹议”,商定将府城东的锦屏书院改设中学堂,添购书籍器具、建造斋舍书楼等需1万两,常年经费需3000两。书院的地租利息每年仅约1000两,其余经费 “体察各属出产丰绌,酌定数目多寡,分饬九州县,因地因时,察酌制宜,筹解备用,俟有成数,再行另议扩充章程”〔52〕。显然,书院旧款仅不足筹办经费之1/10,不足常年经费之1/3,巨大缺额由府属九个州县摊解弥补。而承担摊派责任的州县有可能在本地的旧式教育经费中挖掘经费以提解。
1903年9月,保宁府饬南部县摊解中学堂开办、常年两项经费,计每年银500两。为此,该县署理知县召集士绅筹议,“因县属三费、宾兴、学田各局支绌异常,无款可拨,禀请减练勇腾费申解”,但知府仍令 “在学田、宾兴或裁革户粮房参费等项内,议定指拨”。未及县内续议,新旧知县交接。新知县接事后再次与士绅商议,“调核簿帐,实无盈余,窒难提拨”,最后 “令宾兴、学田两局在外先行挪借,以济要需”。尽管有此方案,但此后南部县长期拖欠摊解府中学堂经费。①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编:《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第199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影印本,第238页。关于南部县拖欠及南部县催缴往返诸公文,亦详见该册。宾兴、学田两局即南部县设置专门管理全县宾兴、学田款项的机构,由绅粮主持。三费局则是道光年间在江北厅首设、咸同年间在四川各州县普遍设置的管理从民间抽收与命盗案相关的相验、招解和缉捕费用,亦由官衙派绅粮主持。〔53〕实际上,南部县的学田局除了常规支出外,“去岁又添支祭祀钱二百串,小学堂经费银二百两,今岁又添支出洋川资学费银一百两”;宾兴局 “于乡会试及留京帮费,应支之款,宾兴已属不敷”,加之 “去年又添支小学堂银二百两,钱一百串,省城学堂银二百两,解费十四两,张瑾雯安家银四十两,今岁又添支出洋川资学费银一百两”。此二局 “收款愈少,支项愈多,异常支绌”〔54〕。这就意味着此时南部县宾兴、学田经费除了应对既有支出外,又增加了新式教育支出。此案例或可窥见基层旧式教育经费同时应对新旧两种教育之窘迫。
可以肯定,保宁府知府办学甚力。但同时不能忽略的是,在经费未筹集充分之前,遽然办学未必于地方有利。差不多同一时期,陕西雒南县知县计划将县内书院改设学堂,拟从书院存款钱1800余串中提出1200串给学堂。署理布政使樊增祥批称:改建学堂,先须将各项经费开支 “通盘打算”,“再查书院本有之出息若干,现值扩充变置之时,尚须募捐若干,方能足用。经费筹定,再议兴工,此一定不易之办法也”。且书院本金已花去七成,“万一将来募捐不应,……不惟新学堂之斋舍空存,而且旧书院之根基亦坏”。故令该县“所有书院存款,勿许擅用一文。……如欲兴办,仰将经费筹足,章程拟定,另禀候批”②樊增祥:《批雒南县张令禀》,那思陆、孙家红点校:《樊山政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9页。按原文未标注时间,本文从樊增祥于1901年下半年至1902年以陕西按察使署理布政使判断时间。。樊增祥批驳出于学堂与书院均须维持而致二者经费均不足,此则 “两头不到岸”。
清代州县及更基层地域的书院、宾兴和公车等传统教育款产,官府虽有督导之权,但一般由本地士绅经管,后者所起的实际作用更大。在新旧教育并存且新式教育经费定制未成之际,官绅之间,新旧或不同地域、派系之间士绅关于公款经管、分配的矛盾时有多见。这既与晚清以来绅权扩张的基本趋向密切相关,又是基层教育经费须同时应对新旧两种教育形式的无奈写照。
结 语
1860年代后,中国大地上出现多冠以 “学堂”之名的新式教育机构,其与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体制并行40余年。甲午战败后,各省官方零星创办学堂,开始动支传统教育经费。庚子后,清廷全面兴学,传统教育经费的用途逐渐转向学堂并制度化。传统教育经费用途的转型是学堂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缩影。但这种转变并不全面彻底,且在转化过程中伴随着各种制度与现实的困境。但已是大势所趋,不可扭转。
如果将清末新政视作中国的整体性改革 (变革),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政治;第二是制度;第三是 “技术”,此非作 “科学技术”中的 “技术”解,而采宽泛意义,即与 “道”相对的 “术”,指方法、技巧等意义。清末新政中的“技术”特指制度中的非制度行事或无制度下的行事。本文显示,科举与学堂是两种不同的教育体制;在新式教育财政未确立之前,传统教育经费如何挹注新式教育则是技术问题。一方面,制度的存续仰赖各种技术维持,新旧两种教育体制并非全然对立,两者间的转换亦非全属 “变革”式,但在新政技术无法应对新制度时,旧制度只能加快彻底消亡的步伐。另一方面,局部的技术运作有时会弱化制度存在的意义并促其整体崩解,在科举制尚未废除前,学堂越过科举,从边缘走向中心,有多重复杂的原因,然其中之一即经费用途的转化致使后者逐渐虚化,走向“无用”,尽管这一原因并不是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