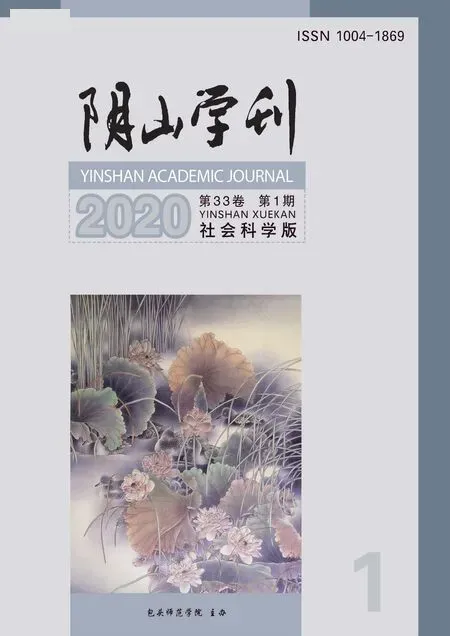论金宇澄的“在体化”写作
——以《碗》为例*
杜 宁 馨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2015年,《繁花》获茅盾文学奖之后,众多资深的编辑、评论家等都对其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在小历史中见大历史,在生机风物中见出世相大观。”文化评论者侯虹斌甚至认为:“茅奖需要《繁花》,更胜于《繁花》需要茅奖。”作为一名海派作家,金宇澄始终生活在上海市民中间,他善于从身边事物着眼,发掘在上海文化的浸润下普通市民百姓的人生百态。金宇澄的写作作为其个人生存实践的一部分,自传式色彩十分浓厚,更进一步来说这也是一种以更新个体生存视域,确认个体现时生存感为导向的“在体化”写作的突出体现。
什么是“在体化”,最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的是刘小枫,他对于“在体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审美现代性的问题上,他认为,在体论的问题既包含“观念之在”,也包含“身体之在”“观念之在”,与人现时的审美感受有关,而“身体之在”指的是人切实的生存感以及个体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1]。在刘小枫之后,杨俊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她认为,“在体化”用以表现“作为客体的知识传统如何真切而有效地与生命个体发生切实的关联,尤其是对个体的精神状态产生效力。”[2]在《诗学经典的在体化面向》一书中,杨俊蕾进一步论述了“在体化”的含义:“在体化”强调的是历史知识以时代特有的方式植入个体,尤其是个体精神世界的建构,在体化之“在(being)”含有存在主义哲学中“此在”意义,突出的是个体对于自我现时存在感的一种体认。[3]要言之,所谓“在体”就是人的“此岸感”——一种主体性的生存感。
因此,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体论”一方面包括对自我身体、真实感知的确认,另一方面也包括过往的历史经验以独特的方式渗透进个人生命体验的过程,即杨俊蕾教授所说的“在不同的时代发生切实的精神实现(resurrection in bodization)”。前一方面与人的直觉认知有关,而后一方面则与个人对历史经验和知识传统体认有关。具体到金宇澄的创作实践中,一方面自传式的写作意味着金宇澄在写作中对其差异性生存空间的直接认知,另一方面作者对历史的回溯性叙述和对上海文化的聚焦也代表着作者一种以历史经验和知识传统激活个体当下生存感的尝试。
作为继《回望》之后的另一部非虚构力作,《碗》中收录了两篇作品,一篇是标示为“非虚构”的《碗——北方笔记》,另一篇是《苍凉纪念日》,其中第一篇是主体部分,第二篇可以看作是对第一篇相关历史细节的再补充。这一文本主要讲述了因小英女儿北上吊唁母亲的契机引发的老知青们的回溯之旅。作者直面那段失序的历史,揭示了历史亲历者们以及之后的人们在当下时代的生存困境:他们缺乏对自我当下生存感的体认,缺乏历史认同感。因此,在这一文本中,金宇澄“在体化”写作的价值指向就在于:突破历史的桎梏,重新缝合起断裂的时代精神和民族认同,最终使过往的历史经验渗透进个人生命从而构成人真实的生命经验。概括起来,在《碗》这一文本中,金宇澄的“在体化”写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城市和乡村空间的交叉书写、国族历史的再阐述与转换生成的生命隐喻。
一、城市和乡村空间的交叉书写
不存在脱离空间而生存的人,也不存在全然相同的两种空间,不同的社会空间生产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模式,反之,一定的社会空间也促进了一定的社会生产模式的形成。正如福柯所言,“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以及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4],强调了个体与空间的关系,然而更进一步,福柯所说的空间不仅仅是人活动的场所,还意味着一种对个体的管制力量,空间内部微观的权力机制弥散于整个空间之中,并普遍的施压于人的身体和生存方式,成为影响人主体性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在体”就意味着在某一具体空间形成的个体。远赴东北的知青经历与年少时期的上海记忆,对不同时空的差异化体验成为作者以及这一类主体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成为导致主体“离心”化的两种差异性象征结构。
不同于《繁花》,金宇澄在《碗》中建立了一个流动的空间体系,在这一空间里,上海和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不再是毫不相关的两个地域空间,而是在永恒的时间之流中成为塑造个体的两种不同权力的表征。
首先来看文中的东北,这里埋葬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人的青春甚至生命:有意外坠井的小英,有被巨雷击毙的天津青年、有被冻死的叛逃者,还有被土锅炉炸死的上海青年胡某……东北成为一个颇为荒诞的时代坟墓。而作为小英这类知青的故乡,上海同样也是拒斥他们的存在。
“城市——乡村”,文本通过两个空间的交叉书写呈现出了这一代以及缺乏历史认同感的下一代对这两类的空间同时的疏离之感。离开家乡走向东北的老知青在返回故乡后成为故乡的“他者”,重返东北之旅反而具有了另一种“返乡”色彩。
“K,让所有的内容都融入记忆好吗,上海与东北融合在一处,上海闪亮的鼻尖,耳朵背后的污垢,广阔的北方原野,与沪西密集的棚户屋顶,都存放在你的记忆里。”[5]74两种极为对立的空间在历史亲历者的自我塑造中成为两种难以融合的对立性力量,此时的故乡不再是故乡,他者却也不再是纯然意义的他者。
年轻一代的知青离开了家乡扎根于遥远的东北的同时,也伴随着从原生的文化母体撕裂的过程,对不同空间社会生产模式和文化模式不完全的调节和适应,最终导致了群体内部认同的丧失和时代认同感的缺失,这一系列断裂的认同感成为老知青们和新一代虚无感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文本中有多处体现。“特殊环境,形成了特殊内涵,从当初特殊意味的大聚集,到七八年后特殊意味的大放归,这个人群始终富含特殊的浑浊度……与一般的校友同学会相比较,似更接近于狱友的聚首。”[5]31身处知青团体的一员,金宇澄看到的不是那个被无数人美化并且青春洋溢的知青团体,而是一个充满着分裂、斗争、死亡与迷茫的知青团体。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鼓励作家拥抱时代。萨特的文学介入论提倡的作家通过对世界的介入而达到对作家自由的确认,换言之,萨特的“世界”是“此岸”的权力空间,因而作家的介入性写作则正可被看作是作家在体性的表现,而金宇澄以自身经历为基础的,通过对几个不同政治权力空间的交叉叙事,达到了这一“介入”性写作的目的。
二、回溯性叙述与国族历史的再阐述
除此之外,金宇澄的“在体化”写作也通过回溯性叙述的方式重新阐释了国族历史。正如哈拉尔德·韦尔策所言,对个体过去以及所属大我群体(die Wir-Gruppe)的感知和诠释,既是个人和集体赖以涉及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因此,文本中的这一回溯性叙述使得过往的历史与当代人们的生存境遇联系起来,激活了历史经验与个体内在构成的有机联系,使之真正成为构成个体生命的重要因素。
在《碗》这一文本中,回溯的契机是由北上寻母的小英女儿引起的。小英女儿以及历史亲历者的老知青们对同一历史的追溯和各自的反映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历史的认知差异也成为他们当下生存差异的原因之一。
小英女儿在母亲的坟头,对素未谋面的母亲说:“姆妈,我一直不开心……我没开心过,我不开心”,这种历史的缺失感成为小英女儿不快乐的重要原因,父辈长久沉默使小英的女儿同上一代以及上一代的历史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断裂感,对她而言,所有的时空都是没有任何区别和差异存在的时空,而她个人的生命也无法在永恒的时间之轴中找到恰当的坐标,这种虚无感正是个人无法在现实处境中获得存在感的结果。
而对于老知青们而言,在这一集体性的文化创伤之下,他们即使离开东北返回家乡,但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掌控自己的人生。历史中的巨大冲击还远没有走完它的历程,直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此时此刻,关于小英的话题,已逐步沉寂,不再引动讨论的焦点……前来的人们,包括20年没见面的来宾,相逢之时,一脸的执着与兴奋,也满脸的麻木与迟疑,对于年龄不对,身份模糊的这个女青年,不再有任何的惊讶与感想,他们今夜今次一心一意要想见的,是周围这些还活着的老男老女——也只有加入这个群落,他们才可以映照,验证过去的自己。”[5]35此时的老知青们恢复了那个大我群体中的知青身份,也因此短暂的从此时的社会身份中抽离开来,在这一重聚起来的群体中塑造自传式记忆(das autobiographische Gedachtnis,即通过“回忆谈话”的社会实践,把过去经历的事情加以现实化的过程。)[6]。老知青们都知道那段知青岁月是痛苦的,但是离开对那段岁月的回溯,又无法对自我存在价值进行确认,过往的创伤性经验没有融入历史亲历者的个体生命中,也因而不会使他们在当下的生活语境中完成“甦生”。
因此,如何在这一巨大的历史创伤下,建立群体认同,唤起历史亲历者及其他相关者们当下的生存意识,作者认为,只有通过否定回溯,打破历史幻想的整体构架,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按照旧例穿插知青运动黑白资料带,定位‘青春豪情’比较脑残,根本不可能,片场也不允许,继续沿用旧口号……究竟取悦于谁,他们是最能读解历史的国民,老套路终归是一颗老树,累累蛀痕,应该劈了它……本片的立意,应该只为现在的青年。”[5]101“我”的这一回溯就隐含着否定,而作者这种自觉的历史批判意识,又构成了对当下自我存在意识的确认。
正如齐泽克指出:“真正的行动本身,不仅仅是遵循我们实际、现有的身份坐标,而应当是以回溯性的方式改变了行动者的先验坐标。”[7]对事件的回溯不仅仅是对其之后秩序的改变,更是对整体秩序的改变,因此,必然会涉及事件发生之先的秩序的变化,此时的过去已经不是纯然意义的过去,而是融入了整个全新整体的过去。作者这一批判性的回溯方式,使历史不再是纯然意义的历史,而是融入人们整体的历史体认中,成为“全新”的历史,这也就是金宇澄所说的,“书写是对个人历史的再翻动。”“板结”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只有经过这一整体批判性的回溯之后,才能成为人们“在体性”的生存经验。正如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立历史认同感的诸多尝试一样,一味地将纳粹大屠杀的事实看作是“另在(das Anderssein)”和“他物(das Fremde)”,并不能重新让德国人站稳历史脚跟,而只有以一种否定或者批判性的历史思维,将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纳入自我认同的历史特征当中,进而在一种道德距离上将其“历史化”,才能真正使处于失败意识中的德国人掌握这一历史经验,并最终弥合起个人对民族与国家的认同,使德国人的当下存在感得到切实的确认。
金宇澄曾这样评价过自己的这段知青经历:“(知青生活)让我有东西可以写,但对于整整这一代人来说,有这类回忆和经历,是不应该的,是一种灾难……在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因为我曾经那么熟悉的生活方式,被一点点地远离,暗淡和改变,应该是一种更深刻的痛苦。”[8]对于东北那段知青经历,金宇澄的态度是否定的,然而否定并不意味着抗拒,正如陈晓明所说:“一部作品以其自觉的艺术表现方法触及时代的症结性问题,但是又无法摆脱被时代决定的命运……这就是在审美层面体现出的历史意识,或者称之为审美的政治性。”[9]与金宇澄有意识的同我国传统叙事形态接续的语言意识相比,我以为,金宇澄的这种审美层面上的历史意识反倒是影响其写作的根本性原则,而这一意识的背后,则是个人如何在否定过往那个荒谬的时代的同时,促使个体当下自我存在意识的“甦生”,从而达到抵抗历史同质化、空洞化的目的。
三、井、碗与坟墓——转换生成的生命隐喻
如果说,金宇澄的在体化写作以对语言和空间的真实感知为基础,那么除了通过发掘过往历史知识,使历史经验切实有效的与生命个体发生关联之外,金宇澄在《碗》中,也试图将共同体的生活经验引入“在体”写作之维。
在张沛《隐喻的生命》一书中,隐喻不仅仅代表着语言的修辞性,更是一种“与生命同源同位的有机体。”[10]隐喻与个体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和价值。而文本中的关键性隐喻——井、碗与坟墓也是如此。这三个关键性隐喻贯穿文本始终,也成为沟通此一时代与彼一时代、生者和亡灵,当下与未来的生命隐喻。这些生命隐喻聚焦的不是生死轮回,而是人们当下的生存实际。在金宇澄那里,个体必然是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一小部分存在的,个体不可能脱离这一生命共同体,完成自我的“在体”生存。
首先来看“井”,在文本中,“井”是小英的死亡之地,也是通往“实在界”的一个创伤:“井台毕竟不是坟墓,只是通向坟墓的一个喉咙,一个进口。”[5]50小英的墓碑早已烂干净了,只剩下这方井口,时时刻刻提醒着前来凭吊的人们:二十年前那个曾经激烈、挣扎生活的生命,是如何在一片沉寂的夜晚中,在井里埋葬了她自己的生命。正如康德所说,时间与空间是一切“感性直观的纯粹方式”,而正是这些“先验感性”使得“先天的综合命题”成为可能。亦即是说,对时空的感知直接关系到认知活动的本身,而小英的生命因死亡这一事件同“井”建立起了联系,并进而由这一共时性的隐喻逐渐演变为不同经验域的“隐喻”,因此,在历史关联者的眼中,“井”就成为一个时间和空间结合的产物。
此时的“井”作为一个时空的统一体,为文本内部以及历史相关者建立了一个有关死亡的永恒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个人的生存经验与先前人们的生存经验就凝结在了一起。“小英消失了,她早已结束在地底深处那座潮湿的石头房子里,但她的力量,我感觉此刻已经延伸到了上海。她一直有话要说,有根须,有触角,曲曲折折,从东北嫩江一直通达于此。”[5]102小英没说出的话,通过这口“井”提醒着人们去试着聆听并且铭记。一个无声逝去的生命成为破除历史同质化可能性的创伤,成为一股将人们带出这死水微澜世界的潜在性力量。
而“碗”以及“坟墓”也成为文本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性隐喻。一个圆形凹陷的容器,向上是给予人生命的碗,向下则是埋葬青春与生命的坟墓。二者作为人之“生”“死”的隐喻,并不是处于截然对立的两段,而是处在一个转换生成的体系中。
“活的物质永远是活的吗?而死的物质永远是真死的吗?活的物质就根本不死吗?死的物质就从不开始活起来吗?”狄德罗的疑问触及生死转换生成的哲学问题。而在这一文本中,“碗”变成了祭奠死者亡灵,摆脱死者诅咒的器具。“小英……你还是回北方吧……如果它直立起来,我们也就可以冲出去,去把这只沉重的大碗彻底砸烂,也只有这样做,我们的苦恼才可以结束。”[5]104只有将这只囚禁着人的精神枷锁砸烂,老知青们这一代人以及之后的每一代人,才可以获得新生。“碗”成为共同体中人们认同危机的一个象征,这一认同危机不仅仅包含着对历史的认同、共同体本身的认同还包括自我认同危机。打碎的那只碗,并不代表着彻底遗忘共同体的创伤,而是对真正冲破那段荒诞历史桎梏的努力,只有建立一种新的共同体精神,才能使得如同小英女儿一样的青年人,在不断转换生成的生命之旅中真正获得“此岸”的生存之感。
北方荒冢所埋葬的那些年轻人成为永久的异乡人。农场墓地的入口处那块醒目的标语牌:“祖国万岁,青年万岁”映衬着荒凉的墓地,与那些被人逐步遗忘、长眠于此的青年们那日渐平缓的坟头形成了一处无比吊诡的景观,在这一文本中,作者将东北的青年墓地与法国拉雪兹公墓相对比,在他看来,不同于海蒂·霍因曼表现的拉雪兹公墓参拜者,前去东北青年墓地凭吊的人们并不是凭吊那些无辜丧失的生命,而只是对自己投掷进北国的那段青春岁月的缅怀,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葬在此地的异乡人的悲剧和自己的人生悲剧气脉相连。老知青们的悲剧伴随着过去时代的终结已经结束了么?在作者看来远远没有,只有记得住死亡,才能真正的活着。金宇澄《碗》中的坟墓隐喻,就成为隐喻着“实在”的永恒“客体之物”了。正如怀特海所说:“实际事态是一种体现过程,因而使一种形成态(等级展示),但他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个体‘达成态’,即通过某种方式骤然综合‘永恒客体’而将永恒领域中的分析性质包容在实际性中,这样永恒可能性及其分化为个体化的多种样态便是唯一实体的途径。”[11]要言之,实际事态以一种形成态的方式,通过永恒客体与“唯一实体”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如果将个人的生命形式看作是一种实际事态,那么,通过坟墓这一隐喻着死亡的永恒客体,便与整个的统一机体联系在了一起。坟墓成为联系生者与死者的重要中介,但除此之外,坟墓也表明,即便生命已经逝去,但是逝去的生命仍然处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并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人们的生活。
“每个东西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会过期……我开始怀疑什么东西不会过期。我想大概是,死亡不会过期,鬼不会过期。”[5]103金宇澄的这一系列隐喻,指向的恰恰不是未来,“未知生,焉知死?”人们只有在生之意识觉醒之后,才能真正明白死亡的价值。
结 语
金宇澄说:“我们没有宗教,常常意识不到感恩和知足……‘我’有衣穿,有饭吃,平安度过这一天,已经非常不易了,在这个世界里,人是无奈的,能够活着,领略美好事物就是一种享受。”[12]金宇澄无意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代言人,也无意成为人们精神的指引者,他只是潜伏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之下,努力开掘与自己有关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记录下自己曾经的过往以及身边的人和事。金宇澄作为时代转捩点的作家,自身就是一个历史创伤下的矛盾体,这一矛盾迫使他直面历史,并且探究过往历史以及文化传统在自我身上发生了哪些切实的精神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金宇澄的写作本身就是其生存实践的一部分,而所谓“在体化”的写作也即是对个体和写作实践之间关联关系的强调。
上海是一座文化森林,任何人都代表不了这座意蕴丰富,不断变化的城市,只能尽可能地描绘出与自身有关的某一截面,这是金宇澄身为一个当代海派作家的基本立场。以《碗》为例,金宇澄的“在体化”写作,一方面充实了对上海市民生活的实感描绘,破除了人们对海派文学创作的标签化印象,但更重要的却是,他从对上海方言的自觉运用以及自我真实的空间体验入手,以一种否定性的回溯方式,建立了个人同过往历史和整个共同体的关联,从而唤醒主体当下自我的生存体验,并使其获得了“此岸”的支撑。在这个意义上,金宇澄的海派写作使过往的历史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过往”,使海派文化也在个体认知结构的不断“甦生”中获得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