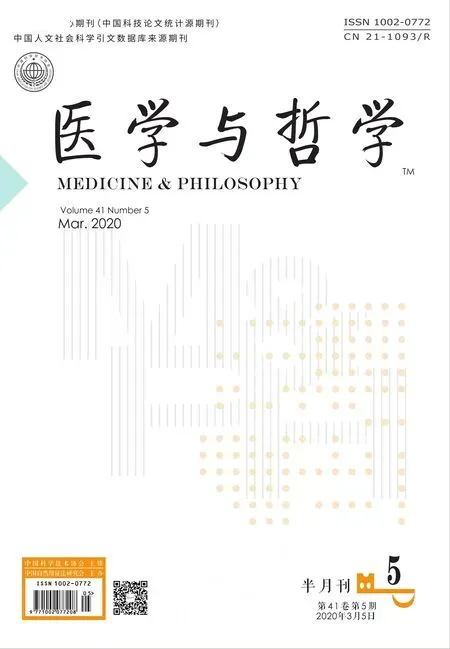论医学史的学科意义
翟海魂 吴海江 孙轶飞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时时回望,正是为了在对过往的记录、观察与思考中,沟通昨天、今天和明天,洞见历史、现实与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对于医学教育而言,回顾历史不仅是对其发展历程的梳理,更是需要在其中找到演进规律,因此医学史研究理应成为一门与医学教育既融合又独立的学科。而且最大的价值,即是为医学教育领域提供历史思维。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不断对话。无论我们从事什么专业,都离不开历史思维,这是极为重要的思维方式。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我们现在所做出的选择取决于过去的选择,并终将影响未来。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道格拉斯·诺斯应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从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教育学者瞿葆奎先生对这个问题也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但历史是“现在-的-过去”(the past-of-the present),它并没有完全过去,它以其独到的方式赓续于现在,流淌于未来。缺乏历史感的人,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肤浅的人;缺乏历史底蕴的学问,相对来说,恐怕也是比较肤浅的学问[1]。
意大利医学史专家卡斯蒂廖尼[2]也有类似表述:错误和胜利的交替演变,是历史的真正本质,在有时灿烂有时平淡的路途中,我们认识到有若干定律,今天视为坚定不移的原则,而在昨天则似含混不清;昨天的教义,今天已成疑问;今天的假设,明天可能成为真理。
笔者以为,历史思维主要包括三点:一是观察问题,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二是不能用局部的考察代替整体的把握。三是发展的眼光。善于从纷繁变幻的社会现象中探索变化原因、发现变化规律、把握变化本质。这对于任何一个学科都适用。
顾名思义,医学史是研究医学演进历史的学科,从研究方法来看属于历史学。路径依赖理论说明了人类思维的基本模式,不仅是在经济学中存在,而且是在所有的行为之中都有相同的逻辑,医学的进程自然也不例外。回顾医学发展的历程,从巫术医学到经验医学,再到医学的科学化,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由宏观至微观、由器官到组织到细胞到分子,所有的进步都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在,并走向未来。因此,医学和医学教育工作者都要学习医学史。下面就医学史的学科意义进行讨论。
1 认识过去,有助于理解当下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很多东西都源自于过去,都是历史演进的产物。只有回溯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存在意义和作用,并对我们的实践进行指导。
对于医学而言,其与人文关怀之间密切的关系即可从历史中找到依据。如英语中的“hospital”一词,原本不是指医疗治病的场所,而是为穷人提供护理和安慰性质的服务处所。它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医院骑士团,这个骑士团出现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他们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附近创办了圣约翰医院[3]。尽管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一机构更近似于赈济机构,与现代医院的功能大不相同。但是它对人的关爱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哪怕时隔千年依然有着高度的契合。医院这一名词的历史根源,为我们揭示了医学实践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意义。
对于医学教育而言,教学机构的历史提供了理解医学教育实践的视角。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学位制度源自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guild),其中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等级学位。当时的行会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种联盟,目的是同一个行业的人能够互相帮助扶持。而行会这个单词的拉丁文形式是universitas,大学university的由来正是源自于此[4]。
由此可见,大学的起源是由社会组织自发形成的教育机构,因此大学在其出现的初期具有高度的自治权,这也给大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是机构的发展总要依托于社会的发展,并且服务于社会,在18世纪末,法国对医学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将大学的管理权收归国家所有。在此之后,法国的医学教育出现了飞速发展,成为了欧洲医学教育最先进的地区[5]。
只有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才能发现,医学教育必须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才能良好发展,而不能简单地从中世纪的经验出发,得出教育机构应当自由化的结论。正是要纵观医学教育史的变迁,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我们目前要面对的问题,才能从现实出发对当下的医学教育问题产生正确的指导性理念。
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把本末由来梳理清楚不但有学术价值,更有实践价值。历史思维促使我们在面对每一个事物时都要思考如下几个问题:它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被创造出来?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在当下它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只有这样不断加深对过去的认识,才能有利于我们对于现在的理解,这也是医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价值之一。
2 反思医学实践,不断追求医学真谛
回顾过去几千年的医学,既有成就也有愚行和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并非没有价值。以科学哲学的观点看,每一个时代的医学都是由无数观点组成的相互关联并内在统一的观点体系。在这些体系之中,依据其权重不同而分为核心观点和外围观点。如果只着眼于体系之中的外围观点,则是忽略这个时代中真正主导医学思想的关键。我们对于外围观点的反思和审视,最终是为了认清医学领域中核心观点所存在的问题。而对于医学中实践部分的反思,即是通过外围观点直达核心观点的过程[6]。
海洛因的发明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1897年,拜耳公司的化学家费力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成功地合成出了二乙酰吗啡,随后拜耳公司将之命名为海洛因。海洛因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被用作止咳、新生儿哭闹、流感和关节疼痛等一系列常见疾病,甚至还打算把它作成提神饮料。1902年时,销售海洛因的利润占整个药品行业的5%,可见其销售量之大[7]。然而,医学界最终认识到了海洛因的危害并达成共识。1912年,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一致同意对海洛因严格管制[7],到了1931年的时候海洛因的合法贸易已经停止了。从此以后,海洛因再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成为了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这一药物造成使用者危害的典型案例之中,海洛因的危害即是外围观点,而其指向的是药物的成瘾性这一核心观点。当我们反思这一案例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海洛因一种药物的问题,而是一类药物的问题。这正是在科学哲学的指导下,不断反思医学实践的结果,而这种反思的对象更适合选取历史中已经发生的事例,正是因其发生、发展过程和结果更为清晰,更利于我们总结医学发展的规律,也正是医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价值。
3 汲取历史智慧,启迪现实问题的解决
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即是历史的流淌,我们在现实所遇到的问题,很多都在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情形。我们学习历史当然希望在其中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但是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现实问题当然不会在历史中全部都有具体的解决方法。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无法从医学史中获取灵感。
陈旧的知识固然不断在被淘汰,然而我们的关注点并不局限在旧知识本身,研究和反思旧知识如何被新知识替代,这才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例如,解剖学的创始人维萨里,如果以今天的解剖学水平来衡量,其著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错误,但通过研究维萨里开创现代解剖学的历史,可以了解到他不局限于古罗马盖伦医生的传统著作,而是坚持采用实践的方法来研究解剖学,从而得以完成划时代的进展。这种坚持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医学的精神,才是我们通过医学史的学习所想要得到的。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过程也同样对我们有所启发。最初,屠呦呦发现青蒿的水煎剂无效,而使用乙醇提取的成分效价很低。之后她看到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有“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领悟到之前的方法之所以无效,很可能是因为在提取时高温破坏了药物的有效成分。于是屠呦呦改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获得了有良好治疗效果的药用成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青蒿素[8]。回顾这一过程可以得知,尽管葛洪无从得知青蒿素的正确提取方法,但是他的著作却最终给人类带来消灭疟疾的希望。
历史经常以饶有意味的方式给我们启发,而是否能在未来继续从中获取智慧,则取决于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历史不能提供具体方案,但却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在历史的字里行间,写满了打破陈规才能有所创建的精神,以及多角度看问题的方法。关于历史给我们提供的灵感和启示,我们不应停留在某种具体的知识,而更应该探究前人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医学史作为学科的意义,也不是仅要求医学领域解决具体问题,而是要在思维模式的层次上给予指导。
4 学习先哲,为医学事业献身
现有的医学实践对技术过于相信和依赖,这在更好地治疗疾病的同时造成了医患关系的损害。如罗伊·波特[9]所说:“在西方,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健康、长寿,医学的成就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强烈地对医学产生疑惑和提出批评”。
而医学实践中的这些问题是需要通过医学教育来解决的。目前我们对于医学人文教育的加强,正是再次对于医学的本质进行认识。医生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病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医学人文教育的开展也是“复兴”,对于患者本身的关爱在生物医学模式下相对不够被重视,而现在我们就是要重新唤起医生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因其强烈的人文精神青史留名的医生不胜枚举,正是因为他们完全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将患者利益放在了至高的位置上,才能坚持对于真理不懈的追求,很多人甚至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解剖学家维萨里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当时的医学教育对于解剖学的研究严格遵守经典著作,而忽略了由实际进行解剖操作所得来的知识。而维萨里不被前人著作中的错误所影响,坚持进行了解剖学的研究,并和大画家提香的学生卡尔卡合作,将自己对于人体结构的观察写成了不朽的著作《人体的构造》。为整个现代医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维萨里本人最终因为保守势力的迫害,孤零零地死在一座小岛上,但是数百年后的我们依然被他缜密的思维、客观的研究方法、坚持求真的理念所指引。
维萨里所作的一切无疑为了真正认识人体并解除患者的痛苦,在他之后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从未曾断绝。200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巴里·马歇尔,为了证实幽门螺杆菌和上消化道溃疡之间的关系,不惜吞咽患者的呕吐物以进行自体试验。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外一科主任华益慰医生,因为身患重病而三次接受大手术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忍着病痛,把自己作为“活教材”向临床医生传授医术。
医生并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医生为了拯救生命而来,这就赋予了这个职业一种高尚的、超越于技术之上的属性。医生面对的不是机械也不是冰冷的石材,而是一个个热血沸腾的生命,要求医生不只是用脑子去思考该怎么治疗,还应该用心去感受、去帮助、去安慰。
如果细细数来,每一位合格的医生都会有类似感人的事迹,都会有在去伪求真道路上付出的艰辛,而这所有的付出,最终都是为了医学事业的进步,为了解除患者的痛苦。对于这种精神的学习,无疑增加了医务工作者的使命感,而这也是解决当下医患关系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5 把握规律,促进医学教育发展
什么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着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势发展。我们常说,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这重复出现的相似之处就是“规律”。通过回顾医学的发展,看到医学模式的转变体现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是呈螺旋式前进。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不断地继承历史,又不断地超越历史和创造历史。医学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在横向交叉或融合,出现了医理、医文、医工交叉的新学科群。学习医学史,有助于医学生了解医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指一定时期内人们对疾病和健康总体的认识,并成为当时医学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一种哲学观在医学上的反映。在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大体经历了四种医学模式。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的是神灵主义医学模式,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将疾病的病因理解为神灵的惩罚或恶魔作祟。而治疗疾病的方法当然是祈祷神灵的保佑或宽恕,或者采取驱鬼或避邪的方式免除疾病。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出现了,人们开始认识到人体的物质基础和疾病的客观属性。以中国古代中医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及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等人提出的“体液学说”等为代表。这一模式的哲学观以朴素的唯物论、整体观和心身一元论为基础。之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也大大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于是出现了生物医学模式。医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维萨里开创了现代解剖学,哈维创立了血液循环学说,莫尔加尼开创了器官病理学以及魏尔啸创立的细胞病理学等一系列成果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石,也标志着生物医学模式的建立。直到今天,医学的现状很大程度仍处在这一模式之下。
而当恩格尔医生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之后,新的医学模式又被建立起来。这一模式并不排斥生物医学的研究,而是要求生物医学以系统论为概念框架、以身心一元论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既要考虑到病人发病的生物学因素,还要充分考虑到有关的心理因素及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将所有这些因素看作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
回顾医学史中医学模式演进的内容,对医学教育改革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医学教育是一定要和同时代的医学模式相统一的。自从中世纪大学建立开始,便设置了神学、法律、医学三个传统专业,它们的职能分别是:协调人与神、人与人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身的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10]。可以看到,那时对于医学的定位,完全没有涉及社会、心理因素,也就是说从高等医学教育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是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完善,现在的医学教育,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体系,知识的正确性也和中世纪有了云泥之别。但是,从课程设置上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现有的高等医学教育绝大部分仍然是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在这种模式下,无论是基础课还是临床课,医学人文课程的内容都远远不足。
离开我们将近100年的威廉·奥斯勒,对医学和医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美国每个医师家里都挂着他的肖像。就是这位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名医大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医学实践的弊端在于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目前的医学过于依赖和相信技术,‘技术至上’导致医患距离的增大。其实,医学从来都没有与文化分开过。宗教、哲学、教育、社会、经济等任何能决定一个人生活态度的东西都会对其个人的疾病倾向发生巨大影响。”
现今困扰我们的许多医学问题,威廉·奥斯勒都早已给出了答案。行医究竟是科学、行业、专业还是某种综合体?威廉·奥斯勒在《行医的金科玉律》中是这样说的:“行医,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它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它是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行业;从本质来讲,医学是一种使命、一种社会使命、一种人性和情感的表达。这项使命要求于你们的,是用心要如同用脑。”[11]他讲这话的时候是1903年。威廉·奥斯勒对于医学教育改革有着超越时间的洞见,然而在他生活的年代未能完成这样的改革,这是囿于时代的局限性,同时也是他个人的遗憾。而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已经具备了医学教育改革的条件。如果不能顺应时代、因势利导,则不仅是我等医学教育工作者的遗憾,更是未能完成历史使命。
医学模式在前进,如果医学教育没有及时跟进,那么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如何能够和新的医学模式相互适应?当今,医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正是要使之与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相协调,认识到这一点是通过对医学史的研究而得来的规律。而要完成这一点,同样也需要在医学教育中增加医学人文课程的分量,这也是需要医学史教学来起带动作用的。
——基于期刊的计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