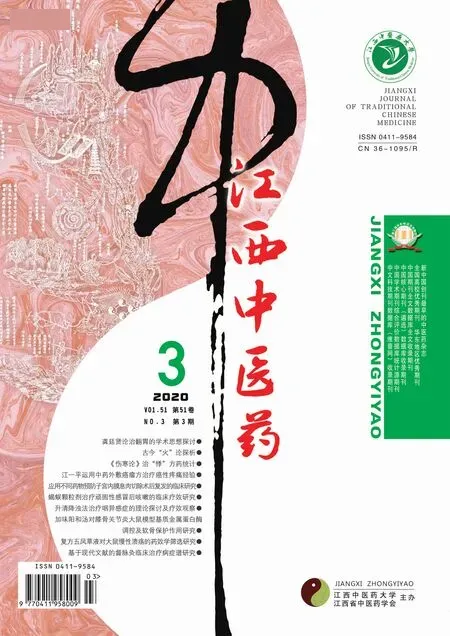脑-肠轴与抑郁症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 单柏溪 苏丹,艾志福* 喻松仁(江西中医药大学 南昌 330004)
抑郁症(Depressive disorder)是医学上第四大常见的疾病,给社会带来巨大负担,在普通人群中发病率很高,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因素[1]。它是一种临床常见的情感障碍性精神类疾病,核心症状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思维迟钝、缺乏活力、闷闷不乐、对生活丧失信心等症状[2]。抑郁症具有较高死亡率和高自杀率[3],增加了医疗支出[4]。据报道,抑郁症患者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5%,占全球疾病支出的12.3%[5]。近几十年来,许多理论试图解释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包括神经传递缺陷[6]、神经营养改变[7]、内分泌免疫系统功能障碍[8]和神经解剖异常。由于这些理论都没有被普遍接受,抑郁症的确切发病机制仍然很难确定,因此迫切需要找出导致抑郁的新的病理生理机制。广大学者对抑郁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揭示了肠道微生物群对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重要性[9-11]。据报道,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变化在肠易激综合征、糖尿病和肥胖症等多种肠道和代谢疾病的发病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的证据还表明,肠道微生物可以通过“微生物-肠-脑轴”来影响大脑功能和行为。本章主要对大脑和胃肠道之间的双向调节轴在探索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方法方面进行综述。
1 当前抑郁症的主要发病机制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临床研究表明,抑郁症与遗传、免疫、内分泌、心理等多种因素有关[12-16]。其中,单胺类神经递质假说是目前较为公认的抑郁症发病机制假说之一[17],据报道,中枢神经系统突触间隙内单胺类神经递质浓度水平下降可导致神经传递功能减弱,认知能力受损,从而导致抑郁[18]。5-羟色胺(5-HT)是一个重要的中枢神经递质,可参与人体的多种生理功能及病理状态的调节,如睡眠、饮食、体温调节和精神疾病等[19]。研究初期,研究人员发现缺乏5-HT 可能是引起抑郁症的重要原因。另外,研究发现缺乏5-HT 还会干扰其他神经递质的功能。因此,在临床上应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如氟西汀等)提高中枢5-羟色胺水平达到抗抑郁的目的。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属于儿茶酚胺类物质,研究表明,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浓度降低也与抑郁症发病密切相关[20]。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亢进导致神经内分泌改变参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是目前较为公认的另一种假说。研究表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中枢兴奋导致促肾上腺皮质素释放激素(CRH)分泌增加[21],大脑皮层感受应激性刺激后,抑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负反馈调节,增加了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活性, 导致海马区神经元受损,从而促发抑郁症[16-17,22-24]。所以,抑郁症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疾病,如果只针对单一因素进行研究,很难对抑郁症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2 微生物群-肠-脑轴及其与抑郁症的关系
2.1 肠道微生物概述 人体肠道中有将近100 万亿个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的细菌[25]。这些微生物对人体的新陈代谢做出重要贡献,如分解饮食中的复杂多糖[26]。同时,它们对免疫系统正常发育至关重要。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肠道和大脑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多种可能的机制。这些包括通过迷走神经、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以及微生物衍生的神经活性化学物质进行的交流。这些途径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还不清楚,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肠道微生物对大脑和行为的影响[9-11,27-28]。为了描述肠道微生物与大脑之间的关系,人们提出了“肠道-大脑轴”这个术语。例如,在老鼠身上进行的粪便微生物群移植可以使接受者的行为特征变得更像捐赠者。行为效应也可以追溯到微生物群的特定亚群。有证据表明,乳酸菌和双歧杆菌可以缓解焦虑和抑郁样症状[29-32]。特定的乳酸菌种类也可以改善应激小鼠[32]的社交活动,并恢复由高脂饮食[31]引起的社会缺陷。此外,拟杆菌类动物似乎通过改善特定的细菌代谢物来改善小鼠的焦虑和抑郁样行为和社交障碍。因此,肠道菌群可能是一个很好地反映自身内环境变化的代表[33],提示疾病风险的个体差异、疾病疗程和治疗反应。
2.2 微生物群-肠-脑轴的作用机制 微生物群的组成受到环境因素的干扰可能会对DNA 甲基化和其他表观遗传产生影响[34],这些影响对体内器官的发育至关重要。早期的动物模型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压力可以扰乱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肠道病原体可以影响宿主的行为。前期研究表明,无菌(GF)小鼠对约束引起的应激行为导致体内激素上调,这表明微生物群影响中枢应激反应系统——神经内分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然而,微生物群的影响或缺乏对行为的影响仍不清楚。通过对无菌动物模型的研究,发现肠道与大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表明,在正常肠道微生物缺失的情况下,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发育异常,导致应激反应的改变和海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减少[27]。当将使用常规饲料饲养小鼠的粪便转移至GF 小鼠的胃肠道时,观察到的异常情况可以得到改善。最近的研究[9,11]表明,经GF 和抗生素处理的小鼠比无特定致病菌(SPF)小鼠表现出更少的焦虑样行为[35],GF 小鼠表现出更多的探索性和冒险行为以及更多的运动,与SPF 小鼠相比,GF 小鼠在高架迷宫(EPM)的张开手臂上和亮暗箱的照明隔间中花费的时间更多。这些行为在细菌定植[11]的早期是正常的。GF 小鼠的脑化学与SPF 小鼠不同,研究表明海马区5-羟色胺受体1 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区域发生特异性变化。此外,在无菌小鼠中观察到与焦虑相关的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5-羟色胺的增加,以及调节神经突触发育和功能的蛋白质水平的变化,例如纹状体中的突触小泡糖蛋白突触素和突触后密度蛋白95(PSD95)。无菌小鼠纹状体中单胺能神经递质的转换也发生了变化,与恐惧和焦虑抑郁相关的几个大脑区域的神经生长因子也相对减少。幼龄无菌小鼠与正常肠道菌群共培养时,其异常行为可以恢复正常,而成年无菌小鼠与常规菌群共培养时,其异常行为则不能正常,为这种特殊的微生物-脑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发育窗口。因此,在发育过程中,大脑内的多条行为相关通路受到肠道菌群的影响,但其中一些影响可能仅限于儿童。无菌小鼠也表现出空间工作记忆和参照记忆的改变,这可能预示着海马发育受损[36]。综上所述,这些研究表明,小鼠肠道细菌的存在影响了与广泛的活动相关的神经元电路的发展,包括焦虑行为、运动控制、记忆和学习。
2.3 肠道菌群衍生物与抑郁症 事实上,后来的研究开始发现肠脑沟通的其他方式,特别是微生物衍生的产物,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向神经系统发出信号。例如,免疫缺陷小鼠的后代表现出肠道菌群失调、肠道完整性受损、行为异常(包括焦虑抑郁样行为),以及血清中检测到较高浓度的微生物代谢物,当把这些微生物代谢物注射野生型小鼠体内时,会诱发焦虑样行为。同样,在帕金森病模型中,肠道菌群或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会促进神经炎症,运动障碍和α-突触核蛋白病变。短链脂肪酸(SCFAs)是肠道膳食纤维细菌发酵产生的主要代谢物,据推测在肠道菌群与脑的相互作用中起关键作用。SCFAs 可能直接或间接参与沿脑肠轴的通信,因为它们的神经活性特性及其对包括免疫和内分泌系统在内的其他肠脑信号通路的影响[37-38]。此外,将抑郁症患者的粪便菌群移植到缺乏微生物菌群的大鼠体内,会传播类似焦虑的行为,但结果显示,接受焦虑患者微生物移植的大鼠粪便中SCFA 浓度比接受来自健康对照组的粪便的大鼠更高[39]。在躁狂动物模型中,丁酸钠逆转了行为亢奋,恢复了前额叶皮质、海马、纹状体和杏仁核的线粒体呼吸链丛的低活性[40],并逆转了大鼠的抑郁样和躁狂样行为[41]。这些研究揭示了情感行为与SCFA 之间的相关性,为抑郁症的治疗提出了新的思路
3 肠道菌群介导抑郁症治疗的研究现状
研究表明,喂养健康雄性BALB/c 小鼠鼠李糖乳杆菌可减少高家十字迷宫(EPM),强迫游泳试验(FST)和旷野试验(OFT)中的焦虑样和抑郁样行为。益生菌治疗组显示进入EPM 张开臂的次数增加,在FST 中静止的时间减少,在OFT 中心的次数和时间增加。据报道,益生菌治疗可以逆转炎症相关的抑郁样行为的增加[42-43]。在使用葡聚糖硫酸钠(DSS)喂养建立的小鼠结肠炎(胃肠道炎症)模型中,小鼠显示出胃肠道炎症和抑郁样行为的增加。然而,经益生菌双歧杆菌治疗后小鼠抑郁样症状减轻[43]。虽然益生菌在动物研究中的使用一直显示出对抑郁样行为的影响,但鲜有关于益生菌对人类抑郁症状的影响的报导。然而最近在一项研究中,每天接受干酪乳杆菌治疗2 个月的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出现的抑郁症状明显少于安慰剂组[44]。虽然在临床研究中益生菌治疗抑郁症还处于早期阶段,迄今为止,仅限于非抑郁患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临床前的实验结果提示我们肠道菌群可以作为治疗抑郁症中的一个潜在的方向。
4 展望
近十年来,人们在认识肠道微生物群对大脑功能的重要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肠道菌群作为人类的第二大脑,通过与中枢及周围神经系统之间的双向交流,影响神经内分泌、迷走神经、免疫系统以及细胞因子,从而影响了抑郁相关行为的发生。大量的动物实验表明,微生物群-肠-脑轴在抑郁症中起到重要作用。目前抑郁症患者肠道菌群变化的特点仍未完全了解清楚,了解肠道菌群之间、菌群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机制仍是研究的重点。在这一领域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在动物模型上进行的,而这些发现是否适用于人类还需进一步的研究。随着更高质量、多方面研究的开展,肠道菌群抑郁症的研究将给临床的有效治疗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