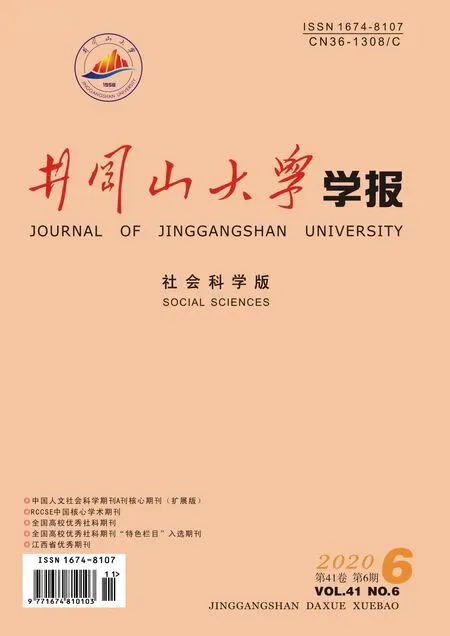列宁“非党组织”党性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时玉柱
(井冈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由于国内、国外两种矛盾长期积累叠加,1905年俄国爆发了一连串大范围的反对现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此次革命很快就因遭到了沙皇镇压而失败,但也使得不同行业、领域和阶层的广大居民阶层分化重组,许多由工人、农民、士兵等建立的非党的革命组织相继出现。列宁认为,这些“非党组织”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紧密团结和依靠的力量,而当时“非党组织”的革命行动大多是“非党性”的,并不具备真正的革命意义,应“在一切非党的组织内建立党支部;这些支部本着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的精神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领导”,使“非党组织”“从无党性到有党性”[1](P3)。列宁正是通过建立党支部这种依靠组织体系建设的方式塑造“非党组织”党性,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凝聚力量以开辟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模式。认真梳理列宁“非党组织”党性思想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运作方式等线索,对于实现新时代“党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阶级联盟”
哲学家看世界,习惯性地把目标聚焦在“哲学王”“精英”“君主”等天才圣贤身上,把他们奉为引领社会变革的“英雄”。马克思主义认为改变历史航向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行动主体往往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而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在领导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运动中,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策略上,都必须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等结成可靠的政治联盟。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联合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其他阶级用暴力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工具,才能消灭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并建立自己的统治。在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在对法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现状的分析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必须走向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获得农民支持才能“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2](P570)马克思恩格斯同时强调:“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以小工业者、商人、知识分子等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自然也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 “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3](P499)。
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联盟思想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他坚信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仅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而是要联合其他阶级和社会集团,争取一切进步的革命力量,使无产阶级摆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无权状态。1905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里批判孟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时指出: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最直接的同盟军,“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4](P566-567),将沙皇势力彻底摧毁。同年,列宁总结过去12年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经验时指出: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等联系在一起,“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得到锻炼,是十分必要的。 ”[5](P105)1905 年革命后, 列宁总结指出, 革命行动的失败正是由于缺乏集中统一指挥,工人和农民、城市与农村未能有效联合,对士兵的争取动员不足等原因导致的。他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应与 “今天由工人建立、明天由农民建立、后天由士兵等等建立的非党的革命组织”结成联盟。
二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联合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自由派利益集团坚持固有立场,认为农民虽有革命积极性,但还有平均使用土地、保留村社制等要求,因而不能建立工农联盟专政,应该用改良的办法完成俄国社会改造。依据当时国内外革命形势,列宁认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张其实质不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要彻底改变俄国民众的生存现状,必须联合农民等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政党和团体,建立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列宁在《四月提纲》里指出俄国第一阶段的革命由于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性不足,导致政权被资产阶级窃取,第二阶段应通过争取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无产者和农民,“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6](P14)。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列宁更加坚信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治联盟,革命行动是不可能达到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最终建成并具有组织生产、实现公正、发展文化、统一道德、提供保证等公共服务职能的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1919年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7](P362-363), 这种联盟可能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动摇的同盟者与“中立者”之间的联盟,也可能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精神各方面互不相同的阶级的联盟,不懂得这一点,就“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可以看到,列宁此时站在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本体的高度,其理论视野十分宽广且自成体系。列宁联合“非党组织”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与国家治理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都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二、使“非党组织”“从无党性到有党性”
列宁主义认为,在革命运动中具有主体意义的社会群体,一定是化多为一、化分散为联结、化差异为团结的过程,这一过程绝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无产阶级政党这一行动者积极构建的结果。无产阶级政党在与“非党组织”的联合中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这一核心问题,使“非党组织”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觉悟的工人主张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单一政权,主张用启发无产阶级意识、使它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办法而不是用冒险行动来取得单一政权。 ”[6](P21-22)。唯有如此,这种联盟才是有战斗力、生命力的,否则,“阶级斗争的能量永远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已。 ”[8](P198)换言之,革命运动必须在“阶级同一性”①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作为列宁主义而非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阶级同一性就是党依靠领导权通过思想整合、利益代表,把生产关系中的不同阶级团结起来,形成阶级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参见:[英]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中得到实现,而主导实现这一过程的就是党。也就是说,革命运动面对群众多样化、差异化、碎片化的民主要求、利益诉求和斗争领域的复杂性等问题必须靠党这一纽带进行调试与“耦合”,在一个阶级的领导下,建立集体认同感并形成凝聚力,可以更有效地在联盟中反对共同的敌人。
为什么党具有“阶级同一性”功能,或者说为什么要靠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才能团结不同革命主体呢?这是因为:第一,无产者不能“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要靠党进行“灌输”才能形成。列宁在《怎么办?》中驳斥了“经济派”让工人自发产生阶级意识的荒谬论断,认为这是唯心主义,工人阶级单靠自己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无法“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只有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才能使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秩序下物化的禁锢,实现内在超越;第二,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列宁对孟什维克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党虽然是阶级的党,但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它是大多数人利益的忠实代表,是阶级中最先进、最积极、最觉悟的那一部分,而不是群众的“尾巴”。因此,“几乎整个阶级都应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 ”[4](P473);第三,资产阶级政党带有软弱性,不能把反封建的任务进行到底。列宁与孟什维克主张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了激烈斗争,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政党先天狭隘、偏私、自利,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在行动路线上盲目短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者,不能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而应与“非党组织”进行联合为实现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
这里必须思考列宁反复强调的“非党组织”的党性问题。众所周知,列宁是把党的组织和非党的组织严格加以区分的,他认为不可“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4](P109),“非党组织” 是党的外围组织的组织阶梯。那么,“非党组织”要塑造什么样的党性才能和党保持阶级同一性呢?列宁认为,“非党组织”塑造党性就是要形成无产阶级意识,也就是要具有党的意识和党的观念,体现党对“非党组织”在思想、政治、组织、行动、情感等方面提出的行动要求。具体说:首先是阶级性。无产阶级政党是阶级对抗的产物,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列宁认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4](P672),党性首先就表现为阶级性。“非党组织”首先要塑造阶级性,具有阶级觉悟和阶级立场,进行阶级联合,塑造阶级意志和阶级情感、进行阶级斗争是具有党性的首要标志,如果没有阶级性,则阶级联盟中不同的个人、群体和阶层在意识上就会出现普遍的不统一,使党不可避免地同阶级组织相分离。其次是政治性。马克思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2](P40)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终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更加合理的政权,“非党组织”作为阶级联盟中的行动主体要坚定政治信念,站稳政治立场,维护党的权威,在意识形态上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构成,服从党的监督和政治领导,避免成为其他党派之傀儡,在组织上、行动上与党的要求协调一致。再次是思想性。列宁认为1905年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主因在于“非党组织”缺乏先进思想武装,只能提出诸如公民权利、改善生活等眼前的局部利益诉求。列宁称这种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被资本的思想家腐蚀了的思想为非党性,“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 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10](P128),要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增强“非党组织”的党性和行动上的能动性。至少具备以上三种意识,“非党组织”才能上升到党性的高度和境界。
三、“在一切非党的组织内建立党支部”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4](P526)1905 年革命的失败使列宁更加坚定延伸组织触角,在工会、合作社、士兵、青年、妇女等组织中建设党的组织体系的想法。因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激发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无产阶级通过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原则获得 “启蒙”,从思想一致变成组织一致;这种组织是道德与知识的有机体,实现了理性对感性的超越,具有“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4](P373)。 这个组织运用其完备的组织体系开展意识形态话语普及、宣传鼓动、利益输送、权威塑造等,能够形成组织化的力量,把广大劳动者凝聚成工人阶级的大军,把杂乱的社会群体构建成一支有机的、做好了行动准备的政治主体。所以,列宁对这种自上而下经过授权的组织深信不疑,“无产阶级联合成为阶级这一客观上极强的能力,是通过活生生的人来实现的,是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 ”[5](P105)强化“非党组织”的党组织建设已经成为革命运动的必然。
第一,以“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引领组织建设。在恩格斯去世后,面对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蔓延,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提出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在1903年同马尔托夫关于吸纳党员标准进行讨论时,列宁主张“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必须作为建设布尔什维党的基本标准。按照这一原则,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体系化建设提出严格要求:首先,“无限广阔地伸展自己的触角”[11](P4),从中央、地方和基层实现党的组织体系有效覆盖,构建秘密、统一、严密的组织体系。列宁主张要在农村、工会、军队、青年组织、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团体等群体中建立党支部,用“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6](P767),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阶级力量。其次,主张挑选那些对党忠诚、信仰坚定、思想觉悟高的“职业革命家”领导党组织。再次,用铁的纪律约束党组织,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使党组织服务于“千千万万劳动人民”[4](P666)并接受人民监督。 最后,吸纳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分子入党。列宁认为,党组织不是在数量上扩充党员,而是在质量上提高党员,要提高入党条件,把那些混进党内的冒险家、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不坚定的党员坚决清除出党。同时加强对党员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使党员在“学习再学习”中提高,保证党组织的革命性和战斗力。
第二,保持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工人、农民、士兵、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等组成的“非党组织”虽然成为革命力量,但这些阶层由于出身、文化水平、利益诉求等因素的差异,且他们是从封建的、资本的等旧的社会制度下扩充到革命队伍中来,难免带有旧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其无产阶级意识是脆弱且不成熟的。列宁认为,在“非党组织”中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一个必要性的前提条件就是保持独立性,“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4](P678),不履行这个义务实际上就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无产阶级政党成员参加非党的组织,在“非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应完全服从一个基本任务:“充分保证工人政党的独立性”以及“在被派到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当代表’的党员和党组接受全党的绝对监督和领导”[10](P129), 而不是像以普列汉诺夫、切列万宁等为代表的孟什维克鼓吹的那样——在革命中要安于充当从属和依附于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傀儡。
第三,同“非党性”思想作斗争。列宁认为,在“非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要同一切“非党性”思想作斗争,因为“非党性”、“超党性”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只会消磨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奋斗意志。当时,俄国党和“非党组织”内有三种“非党性”思想:一是孟什维克中的马尔托夫的“取消主义”和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把罢工、示威和街垒战吹捧成革命运动的最高形式,主张取消“非党组织”中党的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机会主义”分散的联盟。二是“经济派”的工联主义思想。他们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奉行资产阶级式运动,主张结成工会,通过合法斗争的形式同工厂主斗争以争取经济利益、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三是旧有的意识形态。“非党组织”中的大部分成员是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下被迫转到无产阶级队伍里,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往往带有村社制度、封建宗教(东正教)、专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痕迹。列宁认为,塑造“非党组织”党性必须同这些“非党性”思想作斗争。为此,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告全党书》《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等著作中专门揭批了“非党性”的“虚假性”和“虚幻性”。
第四,通过红色文化符号宣传“非党组织”党性思想。列宁认为,“非党组织”党性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并不是因为广大群众不接受、不认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久远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且它经过更全面的加工,它拥有更加体系化的传播工具,所以广大群众易 “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4](P328)。要跳出资产阶级“虚假意识”的控制,“非党组织”中党组织要通过各种红色文化符号开展宣传鼓动,造成舆论,把无产阶级意识、社会主义纲领“灌输”给无产阶级群众,增强他们的主体性。1905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各级组织通过加强“举行游行集会、创办报刊杂志、开展纪念活动、出版宣传册、进行文艺创作”[12]等方式有效引导公共话语,普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提高工农大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信仰,树立党和“职业革命家”在群众中的权威,把“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和“专横暴虐”所产生的“激愤之情”[13](P74)汇集成强大的组织力量。
四、列宁“非党组织”党性思想的时代启示
建立党组织以增强“非党组织”的党性,巩固与扩大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一大创造性贡献,列宁这一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也极具启发。习近平深刻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14]如何从列宁“非党组织”党性思想中汲取智慧,激发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伟力,无疑值得思考。
(一)强化“巩固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必须延伸党组织社会触角的意识
坚持党对“非党组织”的根本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5]。实现党领导一切,使党具有广泛代表性,必然要求把党的触角延伸到一切“非党组织”中,这也是社会主义国体的本质要求。因此,有必要通过党组织的体系化建设实现党对军队、国有企业、文化组织、群团组织、人民团体、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两新”组织等“非党组织”的有效整合,使组织设置趋向全域化、系统化和精优化。当前,西方政治价值观诱使“非党性”“超党性”沉渣泛起,有的主张“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一些私企和外企党组织遭到排斥甚至被“妖魔化”;有的社会组织党组织缺乏号召力和凝聚力,成了隐秘组织,等等。与这些不正常现象作斗争,需要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把握主动,从思想与行动两个层面深刻认识党对“非党组织”的组织覆盖和绝对领导的重大意义,把好党组织“入口关”,强化组织纪律建设,纯洁党员队伍,坚守“非党组织”姓党的政治属性。
(二)思想与政治上的独立性是“党组织”引领“非党组织”的前提性条件
列宁反复强调通过组织渗透方式增强 “非党组组”党性,特别要把握独立性原则。在思想上,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 “非党组组”,而不是放任“非党性”“超党性”这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肆意蔓延。这就要求党组织应保持绝对的政治权威,牢牢把握对“非党组织”的政治领导权,把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当前,随着科技革命与社会结构变化,工人阶级分化,“劳-资”关系调整,新社会组织涌现,社会阶层利益表达、话语趋向差异与多元,导致一些“非党组织”中的党组织式微并屈服于“资本”,逐渐沦为摆设、“面子工程”,甚至成为个别人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一些党组织在“非党组织”的运行中因“失语、失声”致使社会主义意识凝聚功能弱化而变成陪衬、点缀;部分党员认为自己受雇于人,不能把个人目标与党的整体目标有机耦合,等等,使党组织的组织力面临崩溃,这必然要求“非党组织”中的党组织在思想上与政治上坚挺起来,避免弱化、虚化、边缘化,以组织的独立性、权威性保证党的政治领导地位。
(三)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是党对“非党组组”党性原则提出的时代要求
在列宁的视野中,作为党的组织阶梯的“非党组织”的党性是党按照革命、建设与执政的需要对“非党组织”在思想觉悟、政治属性、阶级立场方面提出的要求。新时代应遵循一定的党性原则引导“非党组织”服务于党的事业与梦想。第一,政治性。政治性是“非党组织”党性的灵魂。服从党的领导,在思想、政治、行动上同党中央对标,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引导群众在思想与情感上认同党的政治任务,是“非党组织”在政治性方面的具体彰显;第二,先进性。具有先进性的“非党组织”应坚定党和人民的立场,以党的要求组织、宣传、教育群众,把党的意志、理论、目标化为群众的自觉追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道德和理想信念提高群众的思想、信仰和道德,把群众“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6](P318)。第三,群众性。 “非党组织”的群众性是党的群众性要求的延伸,也是“非党组织”党性的根本特点。发挥桥梁与纽带功能、强化对群众的情感粘合、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非党组织”群众性的必然表征。
(四)构建实效性活动载体是彰显“非党组织”中党组织功能的必然要求
从列宁“非党组织”党性思想看,“非党组织”党性塑造需要党组织的宣传鼓动与情感动员从而构建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行动意义,因而,构建实效性、常态化的活动载体中介是必然要求。活动载体搭建了相互交往的媒介,使人在共同的社会交往中凸显主体性并“发现他自己”①卡西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社会动物”不够全面,社会性不是人的唯一特性,也不是人的特权。在蚂蚁和蜜蜂的动物社会中也能看到明确的分工和极复杂的社会组织。但人的社会行动不同于动物,人有思想和情感。语言、宗教、艺术、神话等就是人的这种高级社会的有机组成。这些条件把有机自然界中的人的社会生活形式提进到新形态:社会意识形态。人的社会意识依赖于“同一化和区分化”的双重活动。人只有依托社会生活的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个体性。但这种中介不仅仅意味着是一种外部规定力量。人,服从各种社会法则,也能积极参与创造和改变社会生活形式的活动。党内各种教育实践活动,实际上为党员提供了一种交往媒介,能调动党员参与创造和改变的积极性(这种能动性的意识既体现在党组织内,也体现为马克思说的“改造世界”的自觉),也能在活动中使党员个体发现自身的不足,把党的意识和法则有效植入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行动选择中,以党性压制动物性,升华人性。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页。,从而形成组织化的力量。这就需要:首先,党组织活动应从嵌入走向开放,与“非党组织”的日常管理、文化建设等深度融合、互促共生;同时,立足群众的思想现状与利益需求,革新思想传导方式,在人文关怀、心理疏导与矛盾化解中凸显“非党组织”中党组织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其次,按治党从严目标,强化政治建设,以党内常态化、组织化、系统化的教育活动铲除损害党先进性与纯洁性因素,为党员补政治信仰之“钙”,校正党员思想意识方向,激发组织成员的示范引领效应。最后,提高党内政治生活格调。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革除党内的官僚主义、山头主义、分散主义、“两面人”现象、痕迹主义等“非党性”痼疾,避免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娱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