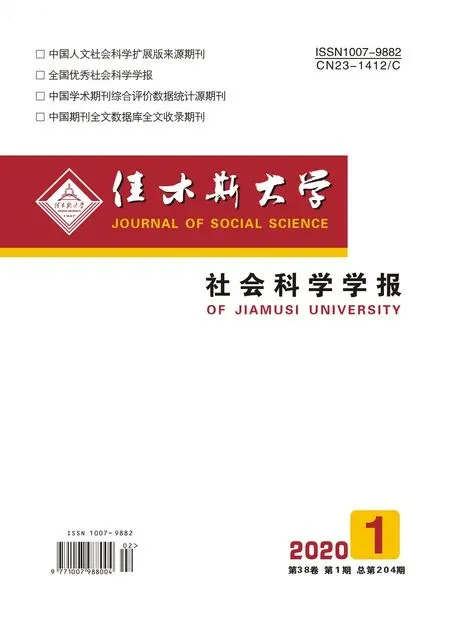张锡厚敦煌研究述评*
尹秋月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其中收藏的众多遗书经卷被劫藏到国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随即诞生了敦煌学。近一百二十年以来,敦煌学研究成绩斐然。1909年,罗振玉在《东方杂志》发表第一篇敦煌文学研究论文《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1],对敦煌遗书中所保留的经卷做了简要的整理编目,为敦煌文学研究拉开帷幕。作为敦煌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敦煌文学研究至今已走过一百一十个年头。在这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大批学者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对敦煌遗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可观的成果。敦煌学家张锡厚正是敦煌文学研究者中重要的一员。
在老师任半塘先生的带领下,张锡厚以敦煌文学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在敦煌文学领域做出巨大的成就。张先生的治学范围极为广泛,涉及敦煌文学的各个方面,对敦煌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俗文学研究
从敦煌文学研究历程来看,俗文学研究一直备受重视,敦煌变文、歌辞、曲子词等俗文学在敦煌遗书中占据极大的比重,反映唐代西北地区的社会现实和文学风貌,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得到较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张锡厚也不例外,在研究中极为关注敦煌俗文学的创作水平以及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敦煌文学》指出,敦煌文学中的多种文学样式“提供了唐代民间文学的丰富蕴藏,回答了我国文学史上长期难以解释清楚的某些文学现象”[2]120,如后人一直将词看作专咏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婉约文体,但是敦煌歌辞作为词的前身,却具备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特征,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题材,“可见词的前身——曲子一来是就不限于婉约,是以丰富的社会内容为前提的”[2]124。唐代歌辞在乐府和宋词之间作为过渡,补充了文学发展中的断裂。此外,作为一种白话韵文叙事说理的通俗赋体,敦煌俗赋是文人赋向通俗故事赋转变的重要节点,敦煌诗话是后世诗话小说之源头,敦煌词文对后世戏曲文学等民间文艺形式的繁荣具有重大影响[3]。敦煌变文继承诗词歌赋的文学传统,借鉴宗教文学的表现手法,吸取民间说唱和绘画音乐等艺术特点,在题材与结构上有所发展,以其韵散结合的表现形式,利用情节刻画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大胆的想象力,为后代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萌发后世话本、小说创作等某些艺术因素[4],通过对《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庐山远公话》三种话本的分析,张锡厚认为当时话本创作中已经出现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质朴炼达的文学语言,这说明唐代已经出现话本小说的雏形并流传到西北边陲,为宋代话本小说的发展做出贡献[5]。可以说,敦煌文学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补充了文学文献史上遗失的一环,展现了各种文体诞生之初的情况。在2000年出版的《敦煌文学源流》一书中,张锡厚从文学作品入手,更为细致地为不同文体分类,并进一步考证其源流演变,厘清文学的发展历程[6]。
除了对敦煌文学进行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外,张锡厚同样注意文学作品中体现时代风潮。在张先生看来,敦煌的通俗文学中流露出一种整体性的风格,在题材上包揽广阔的社会生活,在创作方法上受到民间艺人丰富想象力的影响,因此能够“在探索民间真实的同时,又能大胆运用具有浓厚浪漫色彩的艺术手法,使得某些超现实的想象、夸张呈现出晶光耀目的理想境界,却又比较接近世俗社会的生活真实和人物的性格逻辑”[7],加之俚语俗语进入文学作品,使文学语言通俗化,乃至出现以王梵志白话诗为代表的通俗诗风,形成独特的通俗风格。在《敦煌文学源流》一书中,张锡厚对这种风格加以补充,认为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丰富多样也是重要的特征之一,并将这些特点总结为“民间性”[6]13。
张锡厚对敦煌文学民间风格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对斯坦因、伯希和编号的遗书和俄藏敦煌手稿加以考察研究,可以发现敦煌遗书中残存一些时人辑录的赋集,据《略论敦煌赋集及其选录标准》一文考证,敦煌赋卷在选录作品时有较为鲜明的标准,其一便是要求赋作对社会现实和人情世态为题材,引人向善,催人奋进[8]。再看《敦煌诗歌考论》中对民间通俗诗歌的概括,其内容多为劝善修道以及对民间风习的反映[9],可见在唐代的边塞之地,重视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正是这样的喜好使通俗文学体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共同点。
二、王梵志及其白话诗研究
王梵志其人在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并不多,仅《太平广记》和《桂苑丛谈》中有一些关于其身世的零星记载,且具有鲜明的神异性质,难以看作信史,《全唐诗》中更是没有收录王梵志诗。但正是这样一位传世文献中忽略的诗人,在敦煌遗书中却留下了三百余首诗歌,不能不引起学界的注意,早在1925年,刘复《敦煌掇琐》中就已注意到王梵志及其诗歌。然而由于资料较少,王梵志诗的研究难以展开。
甫一进入敦煌文学领域,张锡厚就将目光停留在王梵志的诗歌上,这也是任半塘先生的建议。但是这样一位诗人,其生平难考,前人经验及成果亦有限,研究的难度不言而喻。张锡厚以敦煌遗书中的二十八种写本①作为材料,加以整理,从中梳理出王梵志的人生经历,并指出王梵志以口语俚语入诗而形成得“平易蕴藉,惊世骇俗”的诗歌风格。同时对其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和在通俗诗派的意义价值加以探析。
关于王梵志诗研究,张锡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敦煌残卷中辨其诗歌,考其生平,还原了初唐通俗体诗歌巨擘王梵志的形象与地位。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录诗作、考证诗人生平与考察诗歌内容形式这三个部分。
校录诗歌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正如前文所述,张锡厚以敦煌遗书中二十余种写本为参考资料,整理出王梵志诗集,1983年出版的《王梵志诗校辑》是张锡厚关于王梵志诗歌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辑录敦煌遗书中的王梵志诗歌,为后来人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此外,张锡厚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敦煌残卷中的王梵志诗歌加以考辨,如《苏藏敦煌写本王梵志诗补正》一文根据《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中公布的苏藏敦煌遗书残卷,对王梵志诗进行补正[10];又如《斯四二七七残诗卷考释》一文针对敦煌遗书内斯四二七七残诗卷中的诗作是否属于王梵志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此卷诗歌在内容上与王梵志诗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对佛教教义完全尊崇,对现实生活则从未提起,后者重视反映现实生活,在宣传教义的同时强调僧侣的腐败,对佛门戒信条多有调侃。从措辞中推论,此卷作者应是一位出家离俗、超然物外的虔诚佛教徒。虽然不能纳入王梵志的名下,其体式格调、语言运用、表现手法或多或少受到王梵志诗的影响,可以说是梵志体诗歌,不过在思想情趣上与之有巨大的差别[11];《整理王梵志诗集的新收获——敦煌写本L1456与S4277的重新缀合》一文考证S4277与苏藏L1456有着不容置疑的共同之处,原属同一写卷。L1456卷王梵志诗的发现,证明王梵志不仅是著名的通俗诗人,还长于依曲填辞,可以说是诗词兼善的名家里手。同时,可以证明词的发现可以上溯到唐代初年,为词学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12]。
考证诗人生平是解读王梵志诗歌的思想情趣及其形成原因的前期工作,然而传世文献中记载零星,张锡厚通过对王梵志诗歌的研读,进一步复原王梵志的生活经历,《唐初白话诗人王梵志考略》一文首先考察诸多诗人对王梵志诗歌的称引,判断王梵志的生活年代之下限,继而通过诗歌中记录的社会实景,提炼出具有时代烙印的府兵制这一政治制度,从而判断诗歌写作于初唐。此外,王梵志诗歌中有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措辞,也证明了王梵志式生活在初唐的诗人[13]。从诗歌的内容中来看,王梵志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读过儒家经典与诗书,半路出家信奉佛教在繁重的赋税徭役和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大约在五十岁以后渐趋贫困潦倒,深刻感受到世态炎凉,因此他的诗歌中表现出底层人民的生活境况、沧桑的人生感受以及对宿命的无奈叹息。
考察诗歌内容与风格是王梵志诗歌研究的核心工作,王梵志诗歌中描绘了唐代边陲社会生活实景,通过对其内容与风格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其创作风格,对唐代历史与社会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浅论》则以王梵志为切入点,探析王梵志诗歌中体现的、唐初社会繁荣掩盖下的种种矛盾[14];《论王梵志诗的口语化倾向》考辨王梵志诗一“隐”一“显”一“俗”三个特点,“隐”在通过异于传统的朴实口语传达生活哲理和愤懑情绪,体现一种素朴蕴藉的诗学理想;“实”在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写作,以内容的现实化与语言的口语化结合,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情状;“俗”在其内容与形式的通俗化,俗中有理、有情[15]。《虚幻的佛国与真实的人生——王梵志诗世间日月明浅析》一文集中探析王梵志诗歌中流露出的来世观,劝慰人们遵循佛戒,忍受今世痛苦,以赎前世罪孽,求得来世富贵。值得注意的是,王梵志的来世观冲破宗教思想,以死亡对抗黑暗社会,向社会现实发出抗议,在宣扬教义的同时,也积极反映社会现实,对灾难深重的人生深有感受,诗作具有人民的思想感情[16]。
王梵志白话诗在唐宋时代有着广泛的影响,以其为代表的通俗诗派在唐初广受欢迎,这既是王梵志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也是社会偏好的选择,更是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对唐代白话诗派的发展及唐诗的繁荣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其人其诗在传世文献中却难觅踪迹。敦煌遗书中为后世保留了重要的文献资料,经过张锡厚的辑校,王梵志诗歌重见天日,唐代西北边陲的社会现实生活也得以重现,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更为清晰。
三、唐代文人诗赋残卷校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敦煌遗书中保留的唐诗残卷也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韦庄、孟浩然、岑参、高适、刘希夷等诗人的佚诗被发现,《全唐诗》的缺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
张锡厚也不例外,借助敦煌遗书补充传世文献中的诗文记载。在唐人诗歌方面,韦庄的《秦妇吟》是一篇长篇叙事诗,真实记录了黄巢起义冲击下的社会现实,规模宏大,内容复杂,艺术成就卓越,但是失传已久。幸而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九种写本,使《秦妇吟》的重现于世成为可能。张锡厚将敦煌遗书中的九种写本参看,整理成文,并赞扬诗歌中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能够突破个人阶级局限和传统观念限制,如实描写历史真相,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6]120。《敦煌写本李白诗集残卷研究》一文指出,伯二五六七号记载李白诗凡三十七题四十二首,皆收录于宋以后的李白诗集中,诗题与传世文献有少许出入,考证为《李白诗集》的中唐写本。此外,斯二〇四九中模糊可见《将进酒》的诗句。张锡厚指出,目前能够看到的唐人抄写本就是敦煌遗书中的部分,借此可以探测宋元以来对李白作品的改动。敦煌本《李白诗集》残卷讹误甚少,是极为难得的珍本,也是考察唐宋以来李白诗歌异文的重要依据[17]。《敦煌本故陈子昂集补说》一文考证敦煌本《故陈子昂集》十卷为卢藏用原编的最珍贵的唐人抄本,也是后世流传的陈子昂集最古最早的本源,能够校正、补充传世的《陈子昂集》,可见敦煌本《故陈子昂集》的校勘价值[18]。《敦煌写本王绩集残卷校补》一文考证同治四年陈氏晚晴轩本《王无功文集》、东吴李氏研录山房校抄本《王无功文集》两种版本与敦煌遗书中的《王绩文集》属于同一源流[19]。此外,《敦煌本毛诗诂训传的著录与整理研究》一文中指出,敦煌遗书中还保存着六朝唐人传写本《毛诗诂训传》的原貌,从中可以考察六朝唐人诗学之风气,重现六朝唐人《毛诗诂训传》抄本之旧式,使湮没已久的《毛诗音》及其撰者又复显现于世,明辨六朝唐人传写字体之流变[20]。
在宫词方面,敦煌本《宫词》残卷书写皇家宫廷活动,展现出多姿多彩的皇家生活和嫔妃活动的真实场景,具有李唐王朝的色彩,根据措辞可以判断其作于中唐晚期。据张锡厚考证,敦煌本《宫词》内宫殿题名、称谓指代、博戏乐舞等专称,全都出现在《全唐诗》,但是通过检索发现,敦煌本《宫词》和《全唐诗》所载宫词全无雷同或互见之作,可见敦煌本《宫词》皆为《全唐诗》未载,敦煌本《宫词》能够弥补《全唐诗》的缺失遗漏,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21]。
在文人赋方面,敦煌遗书中伯希和编号残卷中保留了许多传世文献未曾收录的赋作,多为唐人写本,前人未曾做过集中的整理。在这种情况下,张锡厚抄录、校理出二十篇赋作,发表题为《敦煌赋集校理》《敦煌赋集校理(续)》的两篇文章。后增补《文选》收录的《西京赋》《登楼赋》《啸赋》以及高适《双六头赋送李参军》四篇,又加上新近发现敦煌写本和敦煌影印本中的《恨赋》《观音证验赋》《浑天赋》三篇,结集出版为《敦煌赋汇》[22]11。这些数量不多的赋作证明了敦煌地区存在集结成卷的赋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情态和审美情趣,是赋体文学流变研究的生动材料。
1995年出版的《敦煌本唐集研究》以敦煌遗书中多种文体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对敦煌遗书中的《王绩集》《王梵志诗集》《故陈子昂集》《高适诗集》《李白诗集》《白香山诗集》《甘棠集》《云谣集》和《宫词》残卷以及敦煌赋集进行研究,考证诗人的时代生平、文学作品的著录及源流,在文献学的角度剖析敦煌遗书的价值与意义[23]。2006年,由张锡厚主编的《全敦煌诗》二十一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面汇集并重新校勘敦煌遗书中出现的诗歌作品,同时公布新发现一千二百余首诗歌,补充前人研究之缺漏,在敦煌文学研究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24]。毋庸置疑,敦煌遗书保留了许多唐人写本,对后人考察文学作品的发展源流大有裨益,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四、对今人研究的述评
自敦煌遗书被发现以来,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任半塘在《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展开第三时期》一文中便呼吁学界研究者:“将经文遗书从古董桎梏中解放出来,面对大众,化零为整,焕发学术价值。”[25]在这样的号召下,许多学者投身于敦煌文学研究,力图还原残缺的文献,恢复其文献学与史料学的价值。敦煌文学研究成果虽颇为可观,但其中亦有许多错漏偏颇,需要在进一步研究中加以补充纠正。
张锡厚的敦煌学研究中,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与考订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探幽发微 佚篇荟萃——读敦煌赋校注》一文介绍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收录赋作25篇,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可以说是第一本介绍敦煌赋作的专著,其特点有三:在校注前勘校全文;在校注中征引繁富;标注叶韵并在叶韵角度考辨行文之是非,补充校注,集校集注[26]。
2003年至2005年,张锡厚陆陆续续撰写《是“根”还是“恨”——重读敦煌本十恨诗》[27]《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缺题二首补正》[28]《读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札记》[29]《敦煌诗集残卷辑考辑误》[30]《整理敦煌文集与文字录校——重读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及其相关评论》[31]《读诗随笔》[32]《敦煌本咏孝经十八章补校》[33]一系列论文,指出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出现的疏误,尤其文字校录上的错误,如“根”“恨”“粮”三字的辨析。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如所录诗作不全,直录而未校他本导致以讹传讹,未经考证导致录校带有随意性,对疑难字句辨认错误,对待模糊不清的文字不加探析而一概施以空围等等。同时,借助其他校本,与徐俊使用的底本参看,在《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的基础上进行深入考释,进一步辑考诗歌,还原诗歌的本来面目。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张锡厚对待学术严谨审慎的态度,对学术成果的高标准高要求,为敦煌诗歌研究做出贡献。
面对其他研究者的质疑,张锡厚亦直面不同的声音,在讨论中辨明真相。《关于“敦煌本唐集”“怪圈”及其他——兼答徐俊同志》便是反驳徐俊对自己的辩难,从“敦煌本唐集”的概念,到《敦煌赋集》的辑录拟名及选录问题,对徐俊提出的异议加以解释阐明[34],由此而使得学术研究更加明朗。正是严谨的治学精神,使得张锡厚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真实可信的成果,推动敦煌文学研究的长足发展。
张锡厚的研究并不仅限于以上几个部分,而是以全部的敦煌文学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对敦煌遗书进行广泛且深入的思考与探析。如将敦煌遗书看作史料,从对边地社会生活的记录中还原历史真相与文献真相,试看《新罗僧慈藏入唐礼五台考》中借助已经发现的敦煌五台山文献,考证《五台山赞》中的“新罗王子”或指慈藏[35];再看《关于敦煌赋集整理的几个问题》一文通过对敦煌赋卷的整理,指出敦煌遗书中既有残篇断简,也有连续抄写几篇赋作的长卷,进而明确敦煌写本中已有赋集存在[36]。此外,敦煌文学中流露出的民间性质也引起张锡厚的极大重视,这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直到逝世前,张锡厚一直投身于敦煌文学研究,由张先生主编、周绍良先生做顾问的《全敦煌诗》更是为敦煌文学研究领域留下珍贵的文献材料。张锡厚的研究工作正如任半塘先生所说,真正做到了将敦煌遗书作为文学材料与历史材料,从中拼凑出完整的文学作品与文学史脉络,并寻绎其文学文献及史料学价值。
[注 释]
①关于张锡厚在敦煌遗书中所整理出的王梵志诗歌写本数量,任半塘在《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开展第三时期》一文中提及一共二十二种不同的写本,张锡厚在《王梵志诗校辑》一书的前言中提到自己整理出二十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