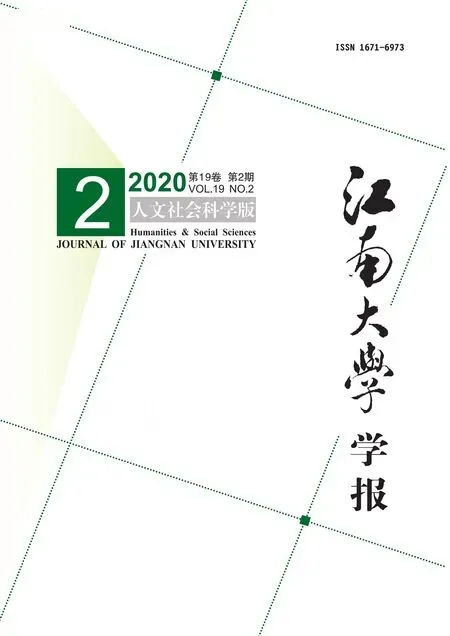诗酒精神:《将进酒》的哲学之维
朱承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200062)
李白的《将进酒》,千载流传,至今不衰,文人喜其文辞气象,歌者喜其五音繁会,酒徒喜其狂放恣肆,一篇诗作,各取所需,故而自来解者、注者众多,传唱不息。中国自古有“诗言志”的思想传统,以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意志和思想,“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正义·序》)正是如此,《将进酒》除了其艺术成就之外,也还蕴含有李白个人的意志气象及其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道:“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1]120元代萧士斌说:“此篇虽任达放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词耳。”[2]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认为:“从来豪杰精神,不能无所寓……李、杜之诗……皆其一生精神之所寓也。”[3]故而,透过其诗歌的文辞,还可以发掘李白的精神旨趣和思想格局。“歌诗合为事而做”(白居易:《与元九书》),就《将进酒》一诗而言,除了其在诗词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之外,还展现了诗人的平生意气与思想情怀,表现了李白之安身立命的精神所寓,以及他对于现世生命的深沉感受,此中有“玄理真义”。具体来说,这种“玄理真义”就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诗酒精神,即以“酒诗”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对于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看法,实现艺与道的结合、具体感受与抽象反思的结合、审美与求真求善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将进酒》除了文辞、音律上的杰出艺术造诣外,还蕴含着中国哲学意义上的深沉思想,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展现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精神气质,体现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本文将试图阐发之。
在整篇小说中,“我”不管同父亲还是母亲都自始至终进行着看起来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的无效对话,“我不能把我要讲的事讲清,哪怕一点点”[3],所有的对话和沟通似乎也被文中反复出现的大雾所遮蔽,变为一团“更浓的雾”。
抗癌药物主要影响人体的造血系统,使造血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人体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血小板、红细胞以及白细胞等含量也会大幅下降,给患者的肝功能带来严重的伤害。其他药物抗凝药物会加快释放组织脂蛋白酶,使血液中的三酰甘油含量迅速下降。
一、流动不居的世界观
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将决定其对于人生、社会的态度,如果《将进酒》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李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话,那么开头两句就展现了李白的世界观,表达了他对所处世界的一个总体性看法。李白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集中表现在其对时间的看法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这两句诗,构造了时空交错的画面,一方面是黄河奔腾的壮阔场景,一方面是青丝变白发的时间流转。严羽曾说:“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1]120在《将进酒》的开始,李白以黄河之水、青丝白发起兴,通过水流不息与韶华流逝两类司空见惯的自然和生活场景,来奠定了这首诗的基本精神基调:岁月不居、时光如流,人生易老、及时行乐,恃才顺性、随遇而安,宏图终空、狂歌纵酒。
在中国思想史上,以河流比喻时间,早期最为著名的是孔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将人的生命时光比作流水一样从不停息的逝去,一去不返。应该说,从流水的意象出发联想到时间的易逝,李白与孔子有相同之处。无独有偶,李白之后的宋代文学家苏轼也曾以流水比喻时间,不过苏轼从中看出了奋发的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意外的发现某处水流逆行,并以此为意象感受到人生不能过于消极,不要哀叹岁月匆匆,而是要从偶然性中看到奋发有为的契机。大致可见,“流水”是思想家、诗人思考时间问题的一个重要意象。孔子、李白、苏轼等人的“流水”之喻,通过日常生活的所见来表达对于人生的感叹,正如有论者在讨论孔子逝水之喻的时候所指出的,“这其中既有对时间流逝作对象化的认识之后所产生的一般的理性理念,但更多的还是对人生的感慨和叹吁。”[4]感叹之余,也包含至深的哲思。水流不息的具象场景,背后反映的是人“以类观之”的抽象移思,这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是常见的,其中著名的如柏格森将时间理解成一条“无边无底的长河”[5]并且绵延不尽。这也说明了,日常的生活场景往往是哲学抽象之思的源头活水,生活意象给人们理性反思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首先是顺应人生的情势。人的一生总是会因为世事人情而遭遇到各种情绪,李白更是一位情绪敏感的诗人,当他不得意时,他要举杯消愁、散发弄舟,“乱我心者,今日之日不可留……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作为一个重视生命感受的人,李白总是顺应情绪的变化,用自己的行动将情绪释放出来。所以在《将进酒》里,他自觉人生得意时,要及时将人生的欢愉表达和释放出来,展现生命的美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进酒》)李白认为,人不必以理性的计较、利益的考量来拘束生命的本质,不能将自己的奔放生命束缚在蝇营狗苟的生活算计中。自然的生命有追求欢悦的冲动,应该顺从这种本性实现自我的欢愉,要如王羲之所说“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王羲之:《兰亭集序》)古典诗歌里所表达个性解放的气质,顺应情绪的变化,尊重个体的生命感受,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庄子曾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在庄子那里,内心不系于外物,不刻意的纹饰和扭曲自己的心志来应对事务,才是自然正道。宋儒程颢也曾在答复张载的《定性书》中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8]程颢也主张将“顺应”作为处世的根本方式。所不同的是,李白的“顺应”更多的是“率性而为”,顺从自己的生活感受,而庄子的“顺应”是无为而顺,程颢的“顺应”则是“公其心顺天下之物”,各有侧重。李白对于生活感受的顺应,既有其怀才不遇而索性对自己的放纵,更多也有对于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通透体认后的自在之感,他认为,人生只有顺应内在的感性欲求并及时行乐,才是真正的体认了“天道”。无论是庄子、李白还是程颢,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顺应”都是中国思想对于“性与天道”体认后的不同反映,不过,李白的“顺应”观,往往是为期望人们积极参与康济群生、修己安人的社会和伦理活动之正统儒学所不能接受的。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对于普通人来说,富贵是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正常追求,虽然孔子接着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但这里强调的是人们应该以正义合理的方式取得富贵,而并非反对“富贵”本身。这句话的潜台词也还在于,如果“富贵”与“道”相洽,则是可以泰然处之的。对于个体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富贵关涉人们的实际生活感受,“富”能帮助人们满足物质欲望,不至于遭受冻馁之患;“贵”是高等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拥有权力并接受他人的尊崇。早年的李白也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够被帝王赏识,获得权贵的青睐,如他曾以“生不用封万户候,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与韩荆州书》)这样逢迎的话,去干谒荆州刺史韩朝宗,以期得到被重用的机会。不过,李白一生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为此他深感失望,甚至到了晚年最后的时刻,李白也还表达了宏图未展的失望情绪:“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李白:《临路(终)歌》)在多次不蒙重视的情况下,李白对于“富贵”失去了信心,仕途无望,于是常常在诗酒里寻找精神安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其一)李白也从不断写诗著文、干谒权贵的名利客,变成了“一醉累月轻王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的诗酒仙。
在《将进酒》里,世界变动不居、韶华一去不返。在李白看来,人既然认清了追求永恒、追求来世或者回到美好的过去是一场徒劳的苦役,不如放下担负,顺应世界之变,珍惜当下,及时追求现世的欢愉。正如李白在另外一段文字里所表述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认为,光阴不为任何人停留,浮生若梦,死生不定,不能辜负良辰美景、桃花烟柳,所以应该顺应天序,及时“为欢”,秉烛夜游、坐花咏诗、痛饮金谷、飞觞醉月,将欢娱进行到底。李白的这种“顺应”的达观人生态度,在《将进酒》里,更是有着充分的表现。具体来说,其物来顺应的人生态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此,李白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打开了对于世界的认知之门,申而言之,将人们从庸常的日常生活里提升到对于终极问题的思考上,即:人应该如何应对不可逆的时间和不停歇的世界?人既无法回到过去,也不能奢望来世,那么所能做的只能是珍惜现在,在现世和当下的生活中寻找愉悦。接下来,李白将告诉人们,面对变化不居的世界,应对一去不返的时光,只有“饮酒”才能使人得到慰藉,在饮酒放歌中及时行乐,从而以混沌之心志,应古今之时变。
第三是顺应眼前的处境。处境或者情境指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具体情况,比如孟子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就是指的人所在的具体情景对于人的行为的直接影响。在酒宴上,人们酒酣耳热,尽兴畅饮,在这种处境下,李白劝说他的朋友们要“乘情直往”,在酒局上汪洋恣肆的饮酒纵歌:“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李白:《将进酒》)这里的“烹羊宰牛”来自曹植的酒局,“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曹植:《箜篌引》)在这个酒局上,曹植也是呼朋唤友、大快朵颐、酣畅饮酒。“三百杯”则来自于另一场著名的酒局,《世说新语·文学》“郑玄在马融门下”刘孝标注引道:“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暮,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10]郑玄在自旦至暮的酒局上,在三百余人的“奉觞”下,顺应情境,痛饮三百杯而面不改色。李白化用这两场历史上著名的酒局,来说明在这种情境下,必须要顺应情势、乘兴而饮。个人生命精神的放纵,在宴饮的局面下,不再受到限制,而是得到彻底展现,这种“杯莫停”的亢奋以及“长醉不醒”的沉沦,是个体生命的真实展露。《将进酒》里的狂饮、放歌的行乐,给参加宴饮的人带来精神上的欢愉和肉身上的放松。这种狂放的生命精神,正是中国思想里自由不羁、热烈奔放之精神状态的写照,是中国传统文人传统中的非理性气象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另外一种向往[11],与儒家所倡导的礼仪、道德、伦理和秩序完全不同,与道家的清静、无为、寡欲也存在巨大差异,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特有的“诗酒精神”,以诗意的方式来渲染饮酒对于美好生活的意义,并通过饮酒来表达对于人生、社会和历史的感怀。
二、物来顺应的人生观
差不多在放学的时点,大雨终于倾盆而下。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我看到房檐下一朵一朵的颜色鲜艳的童伞如莲花次第开放。马老师提议要走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她老师生涯的最后一天也刚刚结束。于是我最后问了一下我小学一年级的同桌,小陈。他或许是我转学前唯一能称上朋友的人,也是我所见过普通话说得最标准的同学。
借助日常的意象是为了呈现内在的思想。《将进酒》从黄河之水的自然意象、个体不断老去的人世变化出发,推至“时间之理”与“世界之理”。在诗中,黄河水“从天而来”,奔流到海,一去不返,“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自然景象进入了人的致思之域,李白从流水意象中看到了时间的不可逆性;少年人从青丝变白发,青春不再,时光稍纵即逝,“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李白:《秋浦歌十七首之一》),岁月迁转也令人感慨系之,李白从人的韶华易逝中体悟到了光阴的宝贵性。在李白看来,时间永是流逝,光阴一去不返,少年转瞬即老朽,世界永在变动之中。“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齐物论》)时间从来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愿而有所停顿或者逆转。李白感叹时间的延展向前,正如黄河之水日夜奔腾不息,也绝无转头重来的可能性,水流的不可逆性让人们体会时间的不可逆性,“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因此,在时间之流里,世界变化不居,人生无法重来。除了流水之喻外,李白也还曾直接表达过对于天地不居、岁月易逝的感叹,他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万物迁转不息,天地只是万物的客舍;光阴转瞬即逝,历史只是光阴的过客。人只是天地之间的匆匆过客,人类历史也只是永恒中的瞬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6]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时间从不为任何人停留,历史奔流向前,世界总是在千变万化之中,这即是李白对于世界的总体看法。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世界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运行,正如黄河之水必然会奔流到海、人必然经历从出生到死亡的变化,李白对于变化的世界与人生的感慨,既是其生活感悟,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事物之所以存在于时间中,是因为他们是有限的;他们之所以流逝,并不是因为他们存在于时间中;反之,事物本身就是时间性的东西,这样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客观规定性。”[7]在黑格尔看来,事物因其具有时间性从而是有限的,生灭变化是其客观必然性,由此可见,由事物所构成的世界更是变动不居的。套用黑格尔的语言,李白所用的河水、头发之喻,用两种具有直观时间性的存在来抒发对于时间的感慨,也说明了事物所具有的时间性和世界的变化性。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期望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去改变某种形势、改善自己的才性、脱离某种非理性的情境,考虑自己在各种情形下的得失以及审慎合理的展现自己的才性,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将进酒》里,李白却以自由奔放的“诗酒精神”来对抗这种“实用理性”,不去计较得失进退,而只是“顺应”生活的情势。关于“顺应”,庄子曾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应,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一般人都是希望把握世界,而庄子只是想顺应世界,任由万物去留。李白此处,也颇有“因任无为”的庄子之风,不过庄子顺应的是自然,李白顺应的是情势、才性与处境,在这种顺应中,李白展现了自由、顺任、雅致、狂放的中国“诗酒精神”,而这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展现的别样途径。
日前,记者从福州省漳州市工商局获悉,今后,在漳州市社区开办自行车修理店、缝纫店、保洁站等,可不办理营业执照;如果服务社区的家庭服务业企业规模做大,还可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
第二是顺应才性的发展。才性是人的自然禀赋和后天文化养成并在使用过程中展现的能力之综合体,“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才”是在具体的生活场景运用中所体现的能力。自然给予人的禀赋有所不同,在生活中能否才尽其用也各随际遇。但不管人有什么样的才性,总归会发挥一些作用,关于才性之“用”的问题,前有庄子,“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庄子·人间世》),要么是《逍遥游》里大觚的“无用之大用”,要么是“不才之木”的保全生命,“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庄子·人间世》)后世有明代“异端”李贽所谓“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9],这些都与“天生我才必有用”遥相呼应。李白在诗中认为,如果不论一时一地的得失,人们的才性必然会得到其妥当的运用,不管有多少失去的东西,最终也可能会以各种形式予以回报,所以人应该乐天安命。于是,李白表达了这种怀才不遇式的典型“自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在自己的才华没有施展和用武之地,个人处在生活窘困之际,抱怨、哀叹对于生活于事无补,不如怀有一种乐观的心态,静待生活处境的转圜。这种顺应观,当然能够安抚人心,但是也会成为很多人逃避现实、自暴自弃的借口。庄子的顺任自然,在一定意义上放弃了人的社会责任和伦理义务,呈现出完全顺应自然乃至无为的精神状态。但李白这里的“顺应才性”,实际上还期待着回报,“必有用”与“还复来”,其实是希望放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能够得到回报,隐然有凌云之气。故而,在一定意义上,李白这里的表达,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不孜孜计较于一时一刻的得志与财富,并以此顺任自己的才性发展,不能因为某时某刻的需求而扭曲自己的人格与才情,从而获得短暂的利益;二是要坚信自己的才性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也会得到物质利益上的回报,因此也不能完全丧失生活的信心而变得一蹶不振并郁郁寡欢。这两重含义,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面几句诗所表达的“及时行乐”做铺垫的。换言之,劝慰他人和自己要顺应才性的发展、相信自己定会得到恰当的施展,实际还是为了“及时行乐”寻找恰当的借口。
三、绝圣弃利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李白生活的唐代是儒道佛思想纵横交错的时代,在对待时间或者历史问题上,从宏观的角度看,三教各有不同。儒家思想里有“往后看”的历史观,认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美好的时代,因此需要向历史学习,甚至回到历史上的尧舜时代;另外,儒家思想里还有诸如孟子的“循环史观”,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认为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循环发展,社会历史的盛况一定可以往复重现。不管是“往后看”还是“循环史观”,儒家都倾向于将“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当作值得回去的时刻,而批评当下,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并希望未来也是过去的再次重现,所谓“挽复三代之治”。道教认为通过丹道修炼人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突破个体肉身的限制、羽化登仙并获得不死的肉身,获得长生久视的无限生命。道教的这种追求,赋予了人们在大化流行中永生的希望,因而人们可以忽视当下的欢愉,而将幸福寄托在未来的登仙。因而,对于期望修仙的道教徒而言,真正的“时间”在于未来。佛教相信轮回的观念,人的生命循环不已,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呈现因果轮回循环之状。佛教认为如果人不获得超越性的智慧,不能通过解脱而证成佛道,就可能陷入永恒的轮回。因而,佛教倾向于否定现世生活的意义,认为如不通过涅槃证成佛道,现实的人生就是苦海而不值得重视。在一定意义上,儒佛道三教的时间观、历史观都超出了普通人的日常经验认知,容易将生活的价值寄托在过去或者未来,或者通过否定时间的流变来获得精神的安慰,而忽视了人们对于现实生活、当下人生的感受,特别是个体生命对于大千世界丰富而多维的直接感受。李白在《将进酒》的开始两句里,以肯定时间的流逝、世界的迁变,作为其全诗的基调,与当时盛行的儒家、道教、佛教都有所不同。他从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个体直接的肉身感受出发,立足于现世,既不追念过去,也不寄托来世,更不奢望永生,而是将世界当作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一维向前,既不会停驻,也不会重来。在世界诗歌史上,德国诗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曾经过一生的升沉不定以及艰苦卓绝的奋斗,营造出移山填海、沧海桑田的壮丽景象,也因此希望时间停止、留住美好瞬间。李白则不然,既没有对于时间流逝的哀叹,也没有对于现实美好的眷恋,只是在尊重常识的基础上,强调人要顺应时间的流变,顺应自然的规律,将自己投入到大化流行的过程中随之迁转。
卡尔曼滤波在线性高斯模型条件下对目标的状态可以进行最优估计,但是实际应用中,系统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非线性特征,为了精确估计系统的状态,必须建立适用于非线性系统的滤波算法[14]。所以,本文提出了将EKF与传统二阶软件锁相环相结合的方法,在EKF滤除噪声且捕获有用信号的基础上通过二阶锁相环获取理想的信号频率。
纵情诗酒的李白写道:“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李白:《将进酒》)在“钟鼓馔玉”的富贵生活与“长醉不醒”的混沌生活二者之间,李白宁愿“长醉不醒”。醒来要面对失意与落寞,只有在狂饮酣醉中才能忘却失望连连的名利之事,体会精神上的奔放自在。因此,对于此刻的李白来说,“饮酒放歌”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而世人所追求之钟鸣鼎食的富贵生活则未必如是。
不仅富贵不是最为美好的生活,就连一般士人所追求的功名、圣贤事业也不是。物质上的富贵、精神上的不朽,在“酒”面前,李白统统将其放下,“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行路难》)。人们来世界一遭,总希望在这世界上留下点“东西”,这种留下来的“东西”,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活在别人心中”,其极致者曰“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个体的肉体可朽,但个体又是社会意义上的存在者,必定要以一定的方式留存于社会历史上,在儒家看来,立德、立功、立言,就是使得个体精神生命在社会历史上留存的方式,而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往往非圣即贤。正是因为如此,在受儒家至大影响的传统社会里,士大夫才华的成就出路,要么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期望进入仕途为帝王重用,从而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如李贺诗所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十五首其五);要么是“慕圣希贤”,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修为、智慧,成为圣人,甚至将“成圣”作为“第一等事”(王阳明语)。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以及对于圣贤的向往与崇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古代士人生活的主流价值观。人的生命有限,人往往总是希望突破这种有限获得无限,对于没有彼岸信仰的人来说,自身的无限或者是普通人所希望的人丁兴旺、家族传承,通过子孙的铭记与祭祀来实现“无限”;或者是通过上述所言之立德、立言、立功的方式,活在他人心中、历史书上从而变得“不朽”。放达者如李白,在《将进酒》里则表达的是另外一种“不朽”的价值观。
李白从来就是“非主流”的天才,类似于庄子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对于流俗之人所珍视的功名、圣贤事业,表达了一种轻视的态度。故而,在《将进酒》里,李白依然是挑战人们的主流价值观,甚至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来强调“圣贤”的无意义。立德、立功、立言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董等一干圣贤,在李白的笔下,都是寂寞无闻之辈,只有“饮者”才具有历史意义。在李白看来,圣贤及其事迹,都毫无意义,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为此,李白引用三国时期曹植的故事来为其佐证,曹植在魏太和六年被封为陈王,“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李白:《将进酒》)此句化用“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曹植:《名都篇》),既是借用曹植的名句,某种意义上也是向没有历史功业只有诗酒名声的曹植致敬。在世人眼里,或许曹植的父兄曹操、曹丕更有历史价值,他们建功立业,被臣属们颂圣称贤。但李白认为,或许曹操曹丕的功业根本不入其眼,他所看重的是曹植的宴饮欢愉,认为这真正的人生价值之体现,具有可兹借鉴的意义。正是因为对于功名利禄的参透,才有了后来睥睨王侯、傲然于世的诗仙、酒仙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
世人都将进德修业、建功立言作为人生的追求,而此事极难,即使或有实现也须费尽心思,故而在此一途中少有欢愉之情。中国古典的诗酒精神,希望能够以饮酒之欢乐破解人生之忧思,曹操说:“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李白更是说:“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四)在李白的诗中,没有多少愁苦是美酒不能消解的,酣醉一场,自然能够解开愁肠千结。对于士人来说,功名以及圣贤事业,给人带来无尽的生忧思与烦恼。由此,李白认为完全不值得将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意义的圣贤事业中,不如树立一种超越名利、超越功业的价值观,这样的人生将更加有意义,也将能消解“终极”的“万古之愁”。人生在世,其终极关怀要么在于肉体生命的不死,要么在于精神生命的不朽,李白认为时间永远流逝,绝不会为个体所停留和回转,肉体生命终会黄河之水奔流不还,精神生命的不朽也只是镜花水月,所以人生不如通过非理性的“醉酒”,在麻木和混沌中实现“超越”。在此,肉体和精神的“万古之愁”与终极关怀,都被“长醉不醒”所消解了,也就是李白所希望的“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这样,跟消解人生惆怅相比,代表名利的“五花马、千金裘”除了具有能够换酒的价值之外,也就一文不值了。
《将进酒》中的长醉不醒和弃绝功名,是李白对于现实生活的失望以及对于理想生活的展望,将文人的生活理想与艺术理想结合起来,将襟怀抱负与狂放自任统摄起来,在功名利禄、圣贤事业之外,是传统士大夫实现人生价值的一条“诗酒”之路。包括李白在内的传统文人,他们超脱人生羁绊的诗酒精神以及蕴含在其中的超越名利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绝如缕,也是古典时代文化生活的一种写照。在诗酒精神的鼓动下,他们“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情焉动容,视通万里”[12],以文辞超越了其自身肉体生命的有限性。他们的精神与文采,在中国古典时代大放光彩,如冯契先生所言,“大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他们的诗都构成了时代画卷。”[13]中国传统的诗酒精神,更是为后世人们在劳作的困苦与无奈中,增添了一份诗意的慰藉。
四、小 结
《将进酒》一诗既反映了李白的安身立命精神,也代表了传统豪放文人的生命气象和中国文化中的诗酒精神。《将进酒》是诗坛绝唱,更是酒林大旗,是中国传统诗酒精神的典范式承载。从思想上来看,它一方面承续了先秦以来道家飘逸豁达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由于其文学造诣高、影响久远其人群广泛,也在一定程度上融摄到中国士人的精神生命里,又经由士人传递到普通民众那里,从而强化了中国文化的诗酒传统。正是由于《将进酒》的巨大影响,故而可以成为思想史的一个话题,我们才有必要对其所蕴含和展现的哲学精神予以分析。诗歌本身不长,但其精神底蕴深厚,展现了诗人延展向前的世界观、物来顺应的人生观和绝圣弃利的价值观,虽然这些观念有可能让人消极、懈怠,甚至有可能使人放纵于非理性的狂悖精神不能自拔,但同时,对于人们摆脱希高慕远、自卑悲观、沉溺名利的心理,也有着重要的纠偏意义。就此而言,《将进酒》里所体现的活在当下的现实感、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不慕名利的洒脱情怀,展现了中国思想文化中悠久的诗酒精神,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中重视个体生命感受之真精神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