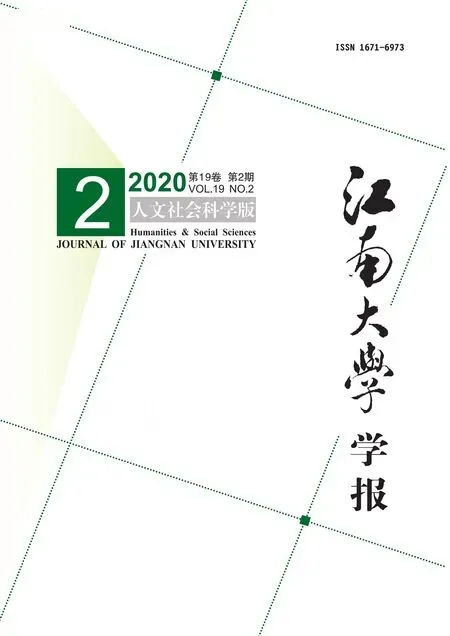中国电影片名的新修辞翻译策略探究
何爱香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国优秀电影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提升国家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之一。因此,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而电影片名的翻译又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电影片名作为语言使用的鲜活实例,体现了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深层次的价值理念与审美习惯,包含着大量的文化元素。由于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特征迥异,中英文电影片名在内容呈现和表现手法上产生了极大的差异。电影片名的翻译涉及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它还涉及到文化、理念、审美等问题。本文从当代修辞理论——“新修辞”理论出发,结合具体的电影译名实例,思考中国电影译名这一现实实践问题,提出译者要以受众为中心,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调试,使电影译名具有感染力,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二、“新修辞”理论与电影译名的修辞本质分析
在西方,最有影响力的修辞定义有三种:一是“说服艺术”(art of persuasion),二是“良言学”(science of speaking well),三是“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的一门实践”(the practice of influencing thought,feelings,attitude and behavior through symbolic means)。[1]第三种定义为当代普遍接受的修辞观,即“新修辞”(New Rhetoric)。“新修辞”理论是在古典修辞学基础上继承与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修辞理论,代表人物有帕尔曼(Chaim Perelman,1912—1984)、理查兹(I.A.Richards,1893—1979)和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1897—1993)。与传统修辞相比,“新修辞”更加关注修辞者、受众、社会因素、话语内容、话语形式以及效果,强调“根据具体情境因势而动”。换言之,修辞除了与辞格、演讲技巧密切相关,它还是一种认知活动和认知视角,关注语言的社会功用,成为有效运用语言、影响受众、消除分歧、取得认同的实践活动和话语艺术。[2]4如果说传统修辞把劝说当作是消极、被动地把自己的主观意志施加于人的单向过程,那么“新修辞”则认为说服是交际双方相互沟通、化解分歧的双向过程,是劝说对象认同的结果。这种积极运用语言资源拉近原先分离感强烈的双方距离,诱导语言交流并使受众予以合作的行为,就是一种修辞行为。[3]
“名”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或无关紧要的抽象概念。对某事某物如何称谓用辞可反映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使用者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以及政治立场和文化价值观等等。人们对事对物的称谓用辞,无不影响外部世界,影响受众。[3]由此可见,“名”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能够改变人的想法,影响人的行为。陈小慰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名称用辞从来不是信手拈来,而是体现了修辞者的良苦用心,是修辞运作的结果。从本质上看,它们是根据语言所处的社会及文化习惯,针对特定受众的修辞选择,迎合受众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及对丑陋现象的排斥,旨在博得受众的兴趣和好感,树立正面形象,进而实现修辞者让受众作出符合其意愿和修辞目的的态度转向,最终促成预期行为的发生。[3]
译名,顾名思义,指翻译过来的名称,是把一种语言的名称或概念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名称或概念。表面上来看,译名是一个语言层面的问题,是翻译技巧的问题,仅关系到名称的转换而已。其实不然。由于不同国家在民俗、宗教、文化、地理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同一事物或概念在不同受众心中可引发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的联想和感受。翻译的目的就是要让来自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们跨越交流障碍,从而使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在当代西方修辞语境中,修辞也无一不与“交流”“交际”有关。翻译与修辞关注的根本焦点都在“如何弥合与消除差异,通过有效交际促进人们相互理解”[2]1。因此,在翻译电影片名的过程中,译者运用语言手段,有效地影响处于另一语言文化中的受众,这也恰恰体现了电影译名的修辞本质,从而决定了电影片名的翻译活动归根结底是一种修辞行为。
三、中国电影译名修辞功能得失案例分析
中国不乏好电影,但真正能走进国际主流市场、赢得外国受众认可的电影却为数不多。电影译名就像浓缩的广告词,承载并传递着影片的精神与内容,对影片的对外推介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修辞得当的电影译名让佳片如虎添翼,能够激发受众的兴趣,使翻译的功用得到充分的体现;反之,修辞不当的译名会让受众觉得电影了无趣味,因而毫无走进影院观影的兴致,甚至有时还会对影片内容产生误解,影响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的传播。下面就中国电影译名修辞功能得失做一些案例分析。
1.修辞得当
案例一:《卧虎藏龙》(2000年),由李安执导,斩获金球、金像等诸多国际大奖,是美国电影史上首部票房超过1亿美元的外语片,甚至在世界影坛掀起了一阵中国古典武侠的飓风。可以说,这与影片地道的英语翻译及成功的译名密切相关。“卧虎藏龙”一词出自南北朝诗人庾信的《同会河阳公新造山地聊得寓目诗》:“暗石疑藏虎,盘根似卧龙”①出自南北朝诗人庾信的《同会河阳公新造山地聊得寓目诗》,见于https://www.slkj.org/gushi/194022.html。,指睡卧着的龙与虎,后引申意为“隐藏着未被发现的人才或隐藏不露的人才”。而龙在西方文化中常常是邪恶势力的象征,被描述为一种巨型怪兽,长有巨爪和翅膀,凶猛异常,破坏力极强。译者将影片片名译为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让西方受众从中看到了与他们所认知的完全不一样的龙虎形象,从而更好地激发西方受众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是修辞得当译名的经典之作。
案例二:《中国合伙人》(2013年),英译名为American Dreams in China,该影片由陈可辛执导,讲述了三个拥有同样梦想的年轻人共同创办英语培训学校的创业励志故事。这三个人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青年人一样,心中都怀揣着一个美国梦。该片若直译为Chinese Partner 或Partners,反而显得平淡无奇,无法激发受众的兴趣。相反,American Dreams in China(意为“在中国实现的美国梦”)这一译名,不仅符合电影主题,还反映出中国年轻人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奋斗的精神,蕴涵了“中国梦”;另外,以受众熟悉的话语方式更能拉近中国影片与外国受众之间的距离,从而更好地实现了对受众的预期影响。
案例三:《我不是药神》(2018年),由青年导演文牧野执导,英译名为Dying To Survive(意为“拼死活下去”)。这一译名可谓匠心独具,刚一问世,就受到影迷们热烈的追捧。它没有直译中文片名,而是立足于影片内容,展示了慢粒白血病人为了能够活下去而托人从印度买回仿制药,与死亡相抗争的过程。“be dying for sth or to do sth”这一短语,意为“渴望,急切去做某事”,表达出一种为了达成某个目标而不顾一切的态度。译名中出现两个语义完全相反的词:dying(垂死)和survive(幸存、活下来),通过这种表现矛盾的修辞,给人一种视觉上的震撼,极大地突出了生、死两个极端。因而,短短三个词的译名(Dying To Survive)体现出了生存和死亡之间的冲突,表现出一种向死而生的决然,让人更加深刻感受到整部电影的感情基调,也感受到语言的力量,令人叫绝。
2.修辞缺失
案例一:《孔雀》(2005年),顾长卫执导,影片英译名为Peacock,讲述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尽管影片以“孔雀”为名,但自始至终都是讲人的故事,全程并没有出现孔雀或如孔雀一般华丽的人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雀是吉祥、幸福的象征,被视为优美和才华的体现。而在西方,孔雀往往带有贬义,是骄傲和虚荣的代名词。因而,西方受众看到Peacock 这样的译名时,极易产生与电影实际所传递的意义和内涵不相符的理解。事实上,在这部电影里,孔雀有着美丽的羽毛,却不能飞,象征着那些虽有才华却被困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人。
案例二:《我不是潘金莲》(2016年),冯小刚执导,英译名为I Am Not Madame Bovary(意即“我不是包法利夫人”),讲述了一个农村妇女李雪莲被丈夫诬蔑为“潘金莲”,为了纠正这一句话,在长达十多年的岁月里,坚持不懈为自己洗刷“不白之冤”的故事。电影的明线是李雪莲的上访,但真正探讨的其实是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是一部严肃的现代中国“官场现形记”。众所周知,潘金莲是《水浒传》中的人物,几百年来在中国一直被视为妖艳、淫荡、狠毒的典型,而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塑造的经典悲剧人物。她充满欲望,对纸醉金迷的生活充满向往,背叛丈夫,最后走向毁灭。将片名译为I Am Not Madame Bovary,用包法利夫人这一外国受众熟知的形象来类比中文片名中的潘金莲,这看似运用西方受众熟悉的人物,拉近与西方受众的距离,实则不然,该译名极有可能让西方受众对电影内容产生不恰当的联想与判断,以为是一个有关“荡妇”的故事。因而,这样的译名不但不能彰显中国文化,反而会弄巧成拙,引发西方受众对影片的误会,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四、中国电影片名的新修辞翻译策略探究
著名修辞理论家伯克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语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4]因而,翻译的成功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译文中传递的信息能否为受众所认同,二是受众对说服者言谈方式是否认同。这里不仅涉及到“译什么”的问题,还涉及到“怎么译”的问题。电影片名中包含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审美习惯等诸多因素决定了译者需充分考虑不同语言文化受众的偏好,采用恰当的修辞翻译策略,在话语内容和话语构建方式上进行必要的调试,进而实现影响译语受众的预期目的。正如陈小慰所言:“译者对受众的影响不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结果,也不是一种无可作为的被动期待,而是需要译者跨越语言文化障碍,通过与受众的互动和有效运用语言象征资源诱导促成的积极修辞之为。”[3]哈里克曾提出,作为说服手段的四种象征资源是论辩内容、诉求策略、话语构建方式和美学手段。[2]201这些象征资源对中国电影片名的翻译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确保电影译名内容真实可信
在电影片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如果过分强调译名与原电影片名的忠实对等,而不考虑电影本身真正传递的意义和内涵,翻译的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冯小刚执导的《唐山大地震》(2010年)译为Aftershock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影片改编自华裔女作家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讲述一对龙凤胎姐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命运被完全改写的故事。唐山大地震让24万多的鲜活生命葬身瓦砾之中,它所带来的伤痛在人们记忆中是永远难以磨灭的。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回首往昔仍是唏嘘不已,心情无法平静。虽然不少观众认为《唐山大地震》这一片名似乎“名不副实”,因为它并没有还原1976年发生在唐山的那场历史灾难,而是将更多的镜头转向了地震过后人们心灵所受到的巨大创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片名似乎比《余震》更能触动心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票房。但其英译名若仅直译为Tangshan Great Earthquake 则很有可能无法受到外国受众的认可。对于西方受众来说,唐山大地震是陌生的,因而直译的片名无法让他们产生共鸣,甚至还有可能引起误解,以为这是一部有关地震的灾难片。相较之下,Aftershock无疑更加贴合电影的主题,确保了译名内容的可信度。
又比如,《建国大业》(2009年)译为Founding of A Republic,《甲午风云》(1962年)译为The Naval Battle of1894,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汉英两种文化不同的修辞特征和受众的不同喜好,即汉语受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业”“风云”这样的词,如果采用直译的方式,会让不喜言辞过分夸张的西方受众感到失真、空洞,从而不予认同;因而,经过适当调适、改写,译者用西方受众所能接受的较为平实的语言进行淡化处理,反而更能增加信息的可信度,为受众接受。
2.贴近受众的情感需求,实现认同
伯克认为,修辞成功的关键在于认同,说服是认同的结果。[2]105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在翻译时如果采用直译的方式会造成信息空白或信息缺失。[5]译者应从“自我受众”的角度,进行“自我思虑”,对译语受众可能面临的局限进行想象预设,包括语言本身的制约、译语习惯、意识形态和视域等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隐喻的制约、修辞传统差异的制约等。[6]因此,诉诸受众喜好、情感、需求、欲望和价值观,满足受众预期,有助于电影译名在受众心中产生预期效果,进而实现认同。
例如,由乌尔善执导的悬疑动作片《寻龙诀》(2015年),英译名为Mojin-The Lost Legend。该影片是根据盗墓小说《鬼吹灯》后四部改编而成,主要讲述摸金校尉为了彼岸花入墓倒斗的故事。根据导演乌尔善的解释,“摸金校尉”并非简单的盗墓者,而是中国古代的一大盗墓门派,不同于英文中的盗墓者“tomb raiders”或者“grave robbers”。若将这部电影片名直译为西方受众所熟悉的“盗墓者”,势必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差。因而,该影片的英译名使用了部分音译(摸金:Mojin)的方式,简单明了,不仅保留了原片名中的文化音韵,还能有效调动西方观众的好奇心和观影欲望。同时,通过增加“The Lost Legend”这一明示化的处理,有效地填补了译名的信息空白,明确了影片题材,贴近了受众对新信息的情感需求,进而实现受众认同。
再如,许可导演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黄飞鸿》系列影片,堪称中国功夫片中的经典之作。当时,中国功夫电影还未在国际上被认可。虽然黄飞鸿在华人文化圈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但对于欧美等国的受众来说,却很陌生。若将片名直译为Huang Feihong,恐怕没有什么吸引力,容易造成信息的缺失。因而将其改译为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如此译名让西方受众很容易联想到美国经典电影OnceUponaTime inAmerica(《美国往事》),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也弥补了原名的信息缺失。
3.构建得体的话语方式
由于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社会心理、风俗习惯、语言规范等,两者在话语构建方式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正如陈小慰所言:“一个民族普遍接受的话语表述传统在另一个民族中可能被视为偏离规范,唯有熟悉的行文组篇方式才能有效影响受众。”[2]211不仅在“说什么”方面要考虑译语受众预期,还要充分了解“怎么说”才能贴近受众的话语构建方式。电影译名亦是如此。唯有获得受众对表达方式的认可,电影译名才能对受众产生预期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因而,在进行电影片名翻译时,译者可尽量套用或借用译语受众熟悉的表达方式。
例如,王家卫导演的处女作《旺角卡门》(1988年),其片名被译为As Tears Go by,还有赵崇继导演的代表作《甜言蜜语》(1999年),同样借用了在欧美国家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名字,将其翻译成Sealed with a Kiss。其中,As Tears Go by 是滚石乐队的经典歌曲,而Sealed with a Kiss是著名歌手布莱恩·海兰的代表作。译者通过借助西方受众熟悉的话语表达方式来构建电影译名,大大地提升了电影译名的话语修辞效果。
又如,周星驰的喜剧影片《国产凌凌漆》,英译名为From Beijing with Love。有些人觉得这一片名翻译得“莫名其妙”,但事实截然相反,该影片译名恰恰是修辞得当的成功范例。《国产凌凌漆》的部分情节正是模仿了在西方国家有着极高知名度的007系列电影中的一部——《铁金刚勇破间谍网》,其英文名就是From Russia with Love。因而,译者套用西方受众所熟悉的这一表达方式,可以激发他们的观影兴趣,使其产生更为丰富的联想,从而获得对影片的认同。
还有,姜文执导的《一步之遥》(2014年),其英译名为Gone With The Bullets,同样是可圈可点。导演姜文就曾公开表明,该片译名是《让子弹飞》Let The Bullets Fly 和西方作品Gone With The Wind 的“合体”。中文片名《一步之遥》所要传递的是一种功败垂成、无可奈何的感觉,片中所有人物的命运都在‘一步之遥’的地方陡转,寓意晦涩。而英译名更显直白、朴实,通过套用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去”)这一西方受众熟悉的表达方式,喻意“一切随子弹而去”,大大提升了影片译名的修辞效果。
4.运用恰当的美学手段
美学修辞是修辞研究中的重要部分。翻译时,恰当地运用美学修辞手段,可使语言更加优美、得体、富有感染力。电影是一门艺术。好的电影译名除了吸引受众的眼球,还具有“导看”的功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美学修辞手段往往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语用色彩。因而,在翻译电影片名时,译者还需根据语境,得体、恰当地运用一些美学修辞手段,从而更好地实现电影译名的效果。
例如,路长学导演的处女作《长大成人》(1997年),英译名为The Making of Steel,主要讲述一个青年在成长过程中的痛苦蜕变。译者将片名译为The Making of Steel(意为“钢铁的炼成”),就是运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以此反映主人公在生活的磨难中浴火重生的过程,让观众对影片所呈现的内容有一个更加直观、生动的感受。
另外,台湾导演九把刀执导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2年),英译名为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此处的apple是指瞳孔、眼珠。瞳孔是眼睛最重要的部分,所以“the apple of one's eye”这个成语常用来比喻“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某个最心爱或珍贵的东西”。苹果apple也是始终贯穿该片的一个细节,从柯景腾参加婚礼前吃苹果时坏坏的样子,到回忆学生时代女主角送他的一件画有大大苹果的衬衫,喻意“你是我最喜欢、最关心的人”。因而,该译名通过暗喻这一修辞手段,极好地突出了该片的内容和情感基调,给受众一种非常“美好”的联想。
五、结 语
关于电影片名的翻译,学界已有诸多讨论。翻译技巧主要涉及音译、直译、意译、创译、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翻译理论主要涉及目的论、接受美学、语用顺应论、互文性、改写理论等。[7]旅美学者魏永康则认为,修辞翻译是一种比起直译或意译更为重要的翻译方法。[2]200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8]电影片名的翻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修辞行为。“新修辞”理论为中国电影片名的翻译提供了一些非常值得借鉴的翻译策略。因此,在电影片名外译过程中,译者应培养和加强修辞意识,以受众为中心,从“译什么”和“怎么译”两方面做出恰当的调适,精心构建电影译名,使电影译名真正发挥其电影“名片”的作用,助力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