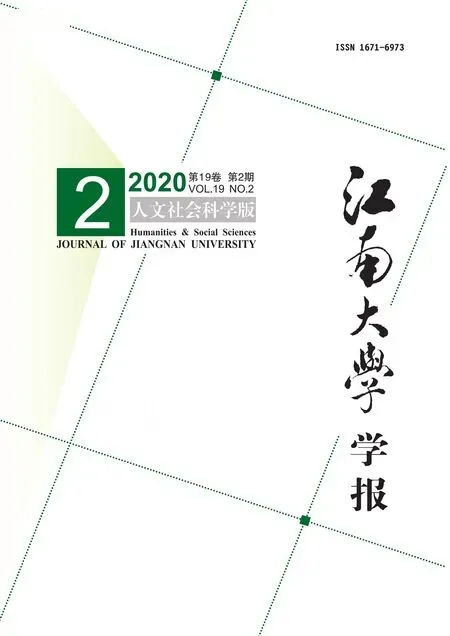列维纳斯的“他者”之思和佛学中的“无我”之见
张俊萍,刘增荣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
一
法籍犹太人E·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的伦理学思想贡献中,最为重要的是创立了一个新的、激进的“他者”理论,从而形成了对自古希腊以来以自我为主体的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传统的彻底反动。列维纳斯的他者不是另一个自我或者“他我”(基于自我的换位思考而产生的另一个存在主体),而是一个打破并逃离了整体性的束缚、拒绝被自我认识和同一化的他者,一个具有异质性和绝对外在性的他者,是不可被认识和理解的溢出和无限。[1]在他的理论框架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既不是认识关系,也不是存在关系,而是伦理关系:当“我”面对他者,“我”必须对他者作出回应,而回应(response)与责任(responsibility)意义上一致,对他者作出回应就是对他者负责。[2]这就是列维纳斯“他者”理论的哲学认识论核心。
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亦令人想到佛学中的“无我”观。“无我”观是佛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佛教的三法印之一,且最为重要,被称为“印中之印”。佛学理论认为,所有以“我”为名的执着和贪欲都是假借我之名。构成世间有情众生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就是造成“假我”之相的根源,它们使自我产生了欲望和“执念”,随着欲望和“执念”加深,自我所感之苦也会加深,并造成对他者的不利,产生世间众多矛盾。《心经》中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①出自《心经》,见于https://www.gming.org/fojing/xinjing/yuanwen.html。只有认识到构成“我”的“五蕴”皆空,才能了悟自我为无或空。佛学中的伦理观和道德实践观都是以否定“我”这样一个实体为前提的。
应该说,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是一种具有深远的犹太教智慧的哲学,而佛学中的“无我”学说是一种带有佛学思辨性的宗教伦理思想。两者均以深厚的理论渊源为基础,以深刻的人文关怀为依托,两者所注重的对他者的关注和“克己利他”的伦理观,对于我们的日常伦理生活有一定的启示和实践价值。作为东西方的智慧表达,两者均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学界对两者的比较和辨析尚有不足之处。本文从理论渊源、逻辑路径、“自我”观、自我与他者关系、道德实践诉求等方面比较并辨析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和佛学的“无我”学说,评估两者在自我与他者关系问题上的观念价值和意义。
二
应该说,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和佛学中的“无我”学说的共同立论基础都是首先破除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自我,但因为二者的思想渊源不同,在逻辑上各有其道。
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以反思和批判西方哲学本体论传统为起点。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列维纳斯,把欧洲遭遇种种危机的根源归结于本体论思想传统。西方哲学史上的本体论形形色色,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斯多德的实体论、黑格尔的逻辑学、谢林式的同一哲学、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雅斯贝尔斯的大全思想等。本体论的思维方式都以主体“我”为中心话语,无视主体之外的他者,“虽然柏拉图至高无上的善和笛卡尔无限的实体都为突破自我留下了缝隙……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马丁·布伯的‘我—你’理论、海德格尔的共在理论,开始把自我与他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然而,对于主体权利的过分强调,必然将他者消融在自我之中”[3];自我主体性的膨胀性还导致对异质性的排斥,从而导致民族的排外性、排异性暴政。列维纳斯认为,这就是西方文化出现危机并使得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种种恶果的根源。
列维纳斯巧妙借鉴并改进了其师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向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他者”学说。在胡塞尔那里,所谓意向性,是指意识的客体关联性,即意识活动总是指向某种外在事物,以其为对象和目的。胡塞尔认为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构成主客体之间的桥梁和媒介。在意向性中,意识离不开对象,对象也离不开意识,它们并不互为因果,而是相互包容的。[4]关注意识的意向性,实际上就是关注主体和客体、意识和意识对象相互依存、彼此同一的关系。[5]7胡塞尔的现象学虽然强调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但仍没有逃离唯我论的束缚。列维纳斯批判这种将他人置于“我”的经验之下的说法,但借鉴了其意向性,并将其理解成一种“开放”,即在伦理层面上自我的主体性对他者的开放,从而为自己的学说所用。
列维纳斯还深受晚期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影响。海德格尔在其学术生涯后期一反他前期对“此在”的分析和揭示,而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发现一条通达“本真存在”之路。这是由“在场的存在”即“此在”,向“不在场的”或“缺席”的存在即“本真存在”的转向。[5]25列维纳斯借鉴了这种“不在场的”和“缺席”的存在,将其发展成具有绝对“他性”、位于总体性之外的、不可理解和把握的“绝对他者”。列维纳斯提出,“他者的超越性就是他的卓越、他的崇高、他的权威,其具体含义包含他的赤贫、他的背井离乡以及他作为陌生者的权利。”[6]76也就是说,他者的超越性就在于他者是与“我”绝对不同的他者,他者以其特殊性超越于“我”的认识之外、存在之外,他者不可能被“我”认识,更不可能被“我”据有。
犹太文化也是列维纳斯“他者”哲学形成的重要推动力。身为犹太人,他从小就受到希伯来文化的熏陶,尤其是深受一位名叫寿沙尼的犹太修士的学说的影响。他把寿沙尼列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样的大师之林,还承认自己“发表的所有关于《塔木德》的研究成果,都得益于他”[7]。《塔木德四讲》正是列维纳斯对《塔木德》的哲学释读,是其“他者”哲学的集约性论证。由于他将犹太思想、宗教情结融入于“他者”哲学中,其“他者”具有强烈的希伯来上帝的意味,表现为一种神圣性和无限性。[8]
列维纳斯糅合了希伯来文化和欧洲哲学,创立了“他者”学说,走出了欧洲本体论哲学的阴影,颠覆了西方传统观念,提出了他者优先于自我的思想,彻底转换了自我与他者的位置。
虽然所有“言哲学、创宗教者,无不建立一物以为本体”[9],然而佛学从来就没有一个西方哲学所持的本体论,其在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自我有无实体”的认识等方面与世界其他宗教和哲学大相径庭。也就是说,佛学倡导的是非本体论,它破除了对人的存在本身的本体论思考和对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诉求,用对自我的探究及其推演而成的“无我”论消解了人的本质这个命题。
佛学中的“无我”之说,首先建立在对婆罗门教的自我观的破除和颠覆的基础上。“我”(atman)在梵语中的原意为呼吸、气息,引申为生命、自己、自体、自性、本质、自我等。[10]婆罗门教的实有思想认为,“我”是生命轮回的主体,人的身体因“我”而生,人的活动也由“我”而起,所以“我”是恒常存在的主体。[11]“我”就是生命、灵魂,是某种具有完全自由意志、不可毁灭的实体,“我”就是“自在”——自己为自己存在的原因,是不依赖任何条件、常恒不变的自作主宰者。而佛学坚决否认“我”,否认恒常不变的“我”。它认为,不管是永恒神性的“我”,还是感受主体的“我”都是虚幻的;既无独立、实在的自体,也无“我”主宰的存在;不存在一个支配世间的不生不灭的绝对的本体或灵魂。
佛学中“无我”学说还依托于其“缘起论”。释迦破梵天创世之说而立因缘生法,认为大千世界的生成没有本体,只以缘生,即自然界的一切皆无自性,都是由相互依存的关系和条件决定的;既否定有生成一切的本体,又特别强调一切皆因,一切皆果。根据缘起论,世间万事万物生住异灭,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住异灭不断,因而也就没有常住不变、恒常主宰之本体。而由五蕴和合而成的有情众生之“我”,也不是恒常不变之“我”。正如《五蕴譬喻经》中所说:“观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时焰,诸行如芭蕉,诸识法如幻。”①出自《五蕴譬喻经》,见于https://site.douban.com/233599/widget/notes/190241132/note/516347100/。因而,在佛学理论中,世俗经验上的“我”即日常生活意识中所体认到的“我”,是虚妄非真的,它不是恒体自性,是处于随世流转之中。那么,人类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我”的“本体”念头呢?佛学告诉我们:“平常任何一个人的身心结合,生命绵延,一概是业力使之……由于心理作用的发展,期间自有一种意识联系前后,构成浑如一体的感觉,而生发了‘自我’认识……”[12]佛学唯识论对此解释得十分具体:人有“八识”,第七识是“末那识”;末那识又称为我识,是意识的根本;它执取第八识(阿赖耶识)的见分或其种子为“我”,使意识生起自我意识,由此而形成烦恼的根本和一切众生自私自利的根源。所以,正是以五蕴和合而成的“自我”的意识使人产生了自身相续存在的真实有“我”的“错觉”,但究其根本,“诸法皆由因缘而有,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了无常住自性,故现象之有,实则非有。一切有情众生乃是五蕴集聚而有,十二缘起而生,同样无常住自性,故现象之我,实则非我”[13]。
三
虽然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与佛学中的“无我”学说都颠覆了自我的重要地位,但列维纳斯在伦理学的语境中又重构了自我,而佛学则创构出一个“大我”的境界。
列维纳斯的自我不以“我”为中心,也不是将其他东西纳入到“我”的范围之内,为“我”所用,成为“我”的一部分,并且借助这些被纳入其中的部分进一步佐证“我”的主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主体性的消解,相反,自我的主体性是通过他者建立起来的,他者相对于“我”来说是主动的,而“我”是被动的。这种主体性只有通过他者与“我”的关系才能生效。[14]在列维纳斯看来,自我身上存在着开放性的趋势,这是由他者的命令所导致的,“我”必须为他者负责,无条件地为他者负责,即人类在本质上不仅是利己者,更是利他者。可见,列维纳斯并不否认自我的主体性,只是否认其利己的主体性。他认为,自我仍然具有主体性,但自我的主体性是在对伦理意义的探求中构建起来的,正是他人的在场才构成了自我的主体性,“我”是为“他”的一种主体性,这个主体已经不再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认知主体,而是一个责任主体、伦理主体。所以说,列维纳斯在伦理学的语境下重构了自我。他主张,他人的地位高于自我,凌驾于“我”之上,当“我”面对他人时,当他人以其裸露的、无助的、毫无防护的双眼对“我”进行质疑、控诉时,当他人以其苍老的、垂死的、布满了皱纹的脸对“我”进行哀求、呼吁时,当那些无家可归者、流浪者、乞讨者、寡妇、孤儿命令“我”对其回应、负责时,“我”的主体性就被唤醒了。[15]
再来看看佛学中的“无我”。佛学“无我”之说,看上去是要否定自我的存在,实则不然,“无我”只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我”的存在和功用,它只是否定主客二体,而认为“我”是存在于万事万物的因缘和合之中。[16]其实,佛学体系从未否定行为主体、人格主体的自我的存在[17],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感受和思考的主体,生老病死、修行解脱都会丧失基础和意义。佛法所说的“无我”,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自我的实质,然后运用正确的方法寻找到背后的大我。[18]大我,就是三法印中所说的“涅槃寂静”,是佛法中的最高人格境界,就是消除自我的界限和束缚,运用缘起的观点来看待世间万物,获取一种智慧感,然后以平常宁静之心去对待所得所思。[19]大我的实质仍然是“无我”,只有通过“无我”才能到达大我的境界,即“有大我故,名大涅槃。涅槃无我,大自在故,名为大我”的涅槃之境,如《涅槃经》所说:“一切诸法悉无有我,此涅槃真实有我。”①出自《涅槃经》第二十八卷,见于http://text.xuefo.net/show1.asp?id=510247。就是说,人们平常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中的“我”并不是真实恒常的,只是因缘和成;唯有涅槃境界里体认到的大我,才是如如不动的,才不会因为外界的变化而生爱恶之心。
所以说,佛学在“无我”之说的背后,实质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是从“假我”到“无我”再到“大我”自我发展演绎而来的。我们心识在活动时会产生“我”的感受,并且由于心识不断如流,在“识”中产生的“我”的感觉也会形成一种连续感和同一感。这种“我”虽然是存在的,但只是在心识活动之时产生的一种幻影,是“假我”,并非“实我”。正如《成唯识论》所说:“内识所变似我似法,虽有,而非实我法性,然似彼现,故说为假。”②出自《成唯识论》卷一,见于http://www.quanxue.cn/CT_FoJia/ChengWeiShi/ChengWeiShi01.html。从根本上讲,这种“假我”处在不断因缘和合的变化之中,没有自性可言,所以也是一种“无我”。
四
在自我和他者关系问题上,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和佛学“无我”之说虽然立论的依据不同,但两者均主张自我对他者的友好、有利、崇奉、负责的立场,形成了根本上的利他主义的精神风貌。
在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中,他者被构建为一种绝对的无限他者,其地位被提升到极限。这种他者的存在完全不受制于自我也不依托于自我,它高高地凌驾于“我”之上,不仅超出了“我”的认知和理解,还对我施以命令。此处,他者对自我的支配、他者的贫穷、自我的顺从、自我的亏欠,都是第一位的,“他者必须是一个在我之外的绝对他者,也即一个不同于自我的异质性他者”[3]100。自我会不断地临近无限的他者,并在伦理层面与他者建立关系,但他者仍是外在于我的,保持着绝对的他性。他者在与自我的关系中从弱势或平等的一方提升到了伦理层面上的首要地位,成为绝对他者,具有绝对的他性,而自我要无条件地为他者负责。
列维纳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关系:他者超越于自我之外,我只能仰望他者,对他者充满敬畏之情,真心诚意地听从他者的召唤,愿意为他者献出我的一切。列维纳斯认为,这样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构成了所有人类关系的前提,所以,在他这里,伦理意义先于存在意义。列维纳斯用伦理、用他者取代了存在、自我在哲学中的中心位置。他也经常把自己所建构的这种自我与他者的新型地位关系称为伦理学:“伦理学是与他人、与下一来者的关系。”[20]“我们把这种他者的在场所引发的对‘我’的自发性的质疑,称为伦理学。他者的陌生性,他者被还原为‘我’、‘我’的思想和‘我’的占有物的不可能性,最终被实现为对‘我’的自发性的质疑,被称为伦理学。”[6]43他也由此提出:“第一哲学是伦理学。”[21]
在佛学无我论体系中,他者,并非是与“自我”有差异的个体,自然也不是自我的对立面。既然构成“我”的“色”“受”“想”“行”“识”都是空,既然由五蕴和合而成的自我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没有自性可言,那么他者,作为有情众生,也同样“五蕴皆空”。佛学体系否定了“我”这样一个实体,以此类推,与“我”类似的他者也是缘起性空。“诸法无我”,意味着所有个体都无恒常自性,如《金刚经》所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③出自《金刚经》第六品和第三十二品,见于https://www.jingangjing.net/。。所以,从本体论意义上讲,他者与自我都是“假我”,都是一种“无我”。
同时,在佛学体系中,他者,也如自我一样,可以进入“大我”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讲,他者和自我也是平等的。自我和所有的他者都是平等的,众生平等。佛陀临涅槃时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22]可见,众生不仅生而平等,不存等观问题;而且众生本性清净,能体悟宇宙人生的终极实在,均可被渡。同时,即心即佛,迷则为众生,悟则为佛。成佛靠的是自己心中的本来真性,这点真性是“‘在凡不减,在圣不增’的,没有有无之分,只有显隐之别……这种大平等精神,使人不仅可以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人,而且平等对待其他一切有情众生”[23]。可以看出,众生不仅在“本体”上是平等的,在成佛上也是平等的。
进一步说,由于以上两方面意义上的“众生平等”,当自我面对他者,面对的是与自我同样具有佛性、同样可以获得觉悟的他者,自然生起‘同体大悲’之心。“观一切众生与己身同体而生起悲心是谓‘同体大悲’……慈悲乃是无差别的平等之爱,讲求普爱众生。”[24]自我与他者本为一体。从同体大悲之心出发,自然可以用普遍、平等无差别的悲心怜悯一切众生,不舍一切众生。[25]105所以,佛学伦理主张的自我对他者的态度,也是一种平等、怜悯、敬仰、奉献的态度。大乘佛法,主张普渡众生,就是这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典型体现。尤须指出的是,大乘佛法强调的通过渡人来渡己的方法,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在这里,利他与利己是完全同体的,体现了佛学在此伦理关系上的彻底性。
五
在救赎(解脱)论上,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与佛学的“无我”学说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表达了类似的伦理诉求和道德实践要求。
身为犹太人的列维纳斯在对二战的思考中发现,西方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和西方传统本体论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是给个人、社会造成苦难的罪魁祸首,西方传统本体论不是对主体权利过分强调,就是将他者消融在自我之中,甚至提倡奴役并宰制他者。列维纳斯本人在二战期间除妻儿外的全部亲属均被纳粹杀害,自己也在纳粹集中营中备受折磨,这些苦难经历让列维纳斯重新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思考人类和社会的救赎途径,他将伦理学确立为第一哲学,将他者确立为伦理主体,提出以他者为核心的形而上的伦理学,反对本体论哲学中的自我观,提出了他者优先于自我的思想,强烈要求自我面向他者,牺牲自我利益去关注他者并为他者负责,从而实现自我与他者地位从前高后低到前低后高的转变,传达出深切的人文关怀。
列维纳斯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定义为一种面对面的伦理上的相遇,而相遇即面向他者之脸。这里的脸是一种隐喻。脸作为“他者呈现自身的方式”[6]50-51,一方面,是赤裸裸的,它暴露无遗,它受到威胁,似乎在诱惑“我”施之以暴力;但同时,他者的脸禁止“我”杀戮,脸就是“你不可杀人”这一条禁令。另一方面,脸也是最贫乏的,脸部显现出本质的贫乏,证据在于人们总想用脸部表情和姿态遮掩这种匮乏和贫穷,“它就是这样一个穷人,为了它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对于它我亏欠得太多太多。而我,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与他者面对面,我就是千方百计对这条禁令做出回应的那个人”[26]。
此外,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其目的不在于将任何特殊的存在同一化,而是允许特殊性的存在和多元化发展。[27]也唯有这样,自我才能得到救赎,社会才能得到救赎,人类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佛学的宗旨也是实现自我和众生的解脱或者说救赎。佛学中关于人的解脱理论的逻辑起点,就是通过认识“无我”来破除“我执”,最终进入涅槃世界。“我执”即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一个恒常不变自在的“我”,或过于执着在意自我,或执着于满足自我的欲望、本性,或太关注自己以至于忽略别人、外物,总而言之,是根据已有的经验或自己的感悟区别出“我的”和“非我的”。正是在这种分别的基础上,人会站在自我中心的立场看待世界,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向外索取,甚至不惜损害他人或大众的利益,将自己与众生和世界割裂,造成“我”与“非我”的二元对立,造成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更造成痛苦。“我”反复地权衡利弊得失,千方百计地去占有“我”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将外物和他人作为“我”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佛学伦理认为,如果把“我”当作宇宙的中心,就会造成不可救药的利己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而这正是人类社会产生冲突和不幸的根源。“佛教要的是治理人世的创伤,要治理人的病痛、人的烦恼。”[28]因此,佛学提出以“无我”来对治“我执”顽症,主张消灭分别心,培养慈悲(利他)心;主张克己利他,灭尽贪欲,自我解脱,并普渡众生,达到最高境界——涅槃状态。可见,“无我”实际上是要求以平等心去认识自我、认识众生、认识万法,破除执着心、分别心,克服自我与他我、个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融自我于他我、群体之中,获得终极解脱。“佛教以普渡众生为根本宗旨,以慈悲之心悦护万物”[29],其“慈悲观主张爱护众生……广施仁慈于一切有情,寻声救苦,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由大慈大悲所生的忘我利他精神是佛教道德实践活动中的主旋律。如‘五戒’中的第一戒就是‘汝不可杀生’……‘四摄’中第一即是要求布施”[30]。这些思想有助于缓解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有利于个人、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发展,能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共荣。
六
什么是他者?如何面对他者?是哲学、伦理学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列维纳斯“他者”理论和佛学中的“无我”学说虽然理论渊源、逻辑路径不同,但都是以破除本体论之意义上的实在“自我”为起点,它们在推导自我与他者关系方面,在道德实践要求和救赎论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两者均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审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视角、一个深刻看待世界的方法、一条完善自我人格的路径。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极端利他主义,因为在对他者负责的过程中,人实现了“我”与他人的外在的连接,将自我引向无限的维度,避免自我堕入本体论之更深的孤独和痛苦。而佛学中的“无我”思想也并非是单纯取消自我的消极学说,它以深刻的人文关怀为依托,告诉世人烦恼与不幸正是缘自我们自身的执着和妄念,并指引人们通过克己利他、灭尽贪欲、普渡众生,达到自我解脱,证得涅槃寂静。
总而言之,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是一种为他人的哲学,他者居于伦理学的首要地位,自我的主体性通过面对他者而构建,进而成为对他人无条件负责的伦理主体。佛学中的“无我”学说消除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差别,甚至否认了实体的“我”,主张众生平等,强调放下分别心、破除我执。两种学说都蕴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对多元存在的包容,两种学说在其伦理诉求上不谋而合,都是在自身体悟的基础上,从大众或以往最易被忽略的他者的利益出发而创立的,其现实意义和人性关切不仅在当时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