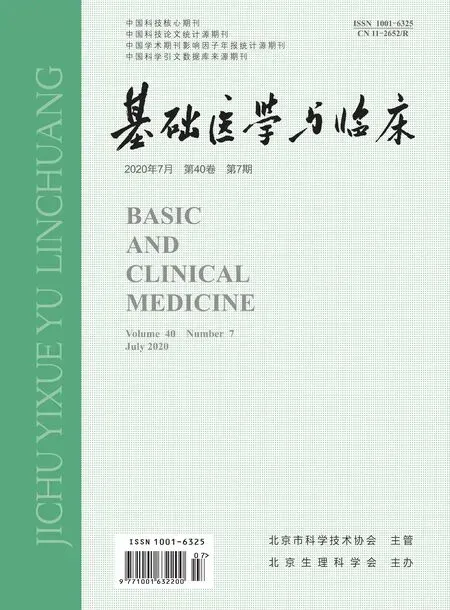COVID-19的消化道受累
宋 锴,吴 东,杨爱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消化科, 北京 100730)
2019年12月,由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 coronavirus 2,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在中国武汉首先被报道,之后病例逐渐增多。人冠状病毒(hCoVs)主要包括α和β冠状病毒,β冠状病毒包括SARS-CoV-2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等[1]。经二代测序证实, SARS-CoV和SARS-CoV-2的序列相似性约为79%[2]。
多数COVID-19病例以发热及呼吸系统症状(咳嗽、呼吸困难等)为主要及首发表现[3],但随着发病人数上升及研究深入,消化道在COVID-19中的重要性逐渐显现。美国报道的1例COVID-19患者在入院前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其粪便标本首次检测出SARS-CoV-2 RNA阳性[4]。后续研究发现有消化道症状的COVID-19患者并不少见,甚至有些以消化道症状为首发表现[5]。粪便核酸检测阳性,提示该病经消化道传播的可能性不能完全被排除。这促使本文作者思考消化道与COVID-19的联系,以及对诊断、治疗及防控产生的意义。本文复习了目前与COVID-19消化道受累相关的文献,并探讨其发病机制、临床表现(症状及实验室检查)、内镜发现及病理改变,以及消化道症状与预后的关系。
1 发病机制
通常认为COVID-19消化道受累的机制包括两方面:1)病毒直接攻击消化道上皮细胞;2)细胞因子介导的免疫损伤。
2003年SARS暴发时,SARS-CoV表达具有能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 ACE2)结合的受体结合结构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s, RBDs)的S糖蛋白,可利用ACE2为入侵细胞的主要受体[6]。SARS-CoV-2与SARS-CoV有较高的基因同源性,两者均表达相似的S蛋白,并具有相似功能的RBDs[2]。目前研究证实,SARS-CoV-2也能利用ACE2作为入侵细胞的受体[7],且亲和力更高[8]。
除了肺Ⅱ型肺泡上皮细胞(AT2细胞)外,ACE2在人体其他部位也有表达,甚至大量表达,包括心脏、肾脏和胃肠道等[9],这也提示SARS-CoV-2的感染靶点可能不仅仅是肺。胃肠道上皮细胞高度表达的ACE2使其可成为SARS-CoV-2的入侵靶点。Zhang等[10]通过分析单细胞转录组的数据,发现食管上段、回肠和结肠上皮细胞都能表达ACE2。Xiao等[11]对COVID-19患者的胃肠道组织活检显示,病毒的宿主受体ACE2在胃肠道腺上皮细胞的细胞质中染色阳性,在胃、十二指肠、回肠的腺上皮细胞的细胞质内可检测出病毒颗粒。另一方面,虽然食管鳞状上皮也有少量表达ACE2,但是在其细胞质中却几乎不能检测出SARS-CoV-2 RNA,这提示SARS-CoV-2主要侵袭消化道的腺上皮细胞。研究还发现,SARS-CoV-2在肠道上皮细胞内进行复制,待其RNA和蛋白质组装完成后可从上皮细胞排出,使得消化道成为可能的传播途径[12],这也是COVID-19患者粪便SARS-CoV-2核酸检测阳性的理论依据之一。
此外,细胞因子高度分泌引起的胃肠道组织内的炎性反应可能是产生消化系统症状的另一原因。在多数疾病中,炎性反应虽然具有清除病原体的保护作用,但过度的炎性反应也可能造成组织损伤和器官功能障碍。重症流感和SARS的研究也证实,过度的炎性反应是患者病情加重的主要机制[13-14]。在COVID-19中,炎性反应也发挥着双刃剑的作用。与健康人相比,COVID-19患者血浆中的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包括多种白介素、纤维细胞生长因子、集落刺激因子、IFN-γ、TNF-α等)浓度均更高。与非ICU的COVID-19患者相比,需要收入ICU的COVID-19患者IL-2、IL-7、IL-10、GCSF、IP10、MCP1、MIP1A和TNF-α的血浆浓度均高于非ICU患者[3]。Zhao等[15]指出,94.73%的COVID-19患者C反应蛋白(CRP)水平升高,7例患者中有6例IL-6浓度超出正常值。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的高表达将引起炎性细胞的趋化与聚集,导致胃肠道组织的炎性反应及损伤。病理检查结果也证实这一点。一项消化内镜活组织检查的报告显示:COVID-19患者的胃、十二指肠、直肠固有层可见大量浸润性浆细胞和淋巴细胞,以及间质水肿[11]。
2 COVID-19的消化道症状
越来越多研究报告了COVID-19患者入院时出现的消化道症状。本文复习并总结了12篇文献共计2 312例COVID-19确诊患者的研究结果[5,16-26]。
患者入院时的消化道症状中,最常见的为腹泻、厌食、恶心和呕吐,较少出现的还有腹痛、反酸等。综合这些文献,消化道症状发生率为11.6%~25.4%,腹泻为2.0%~23.7%,厌食为1%~39.9%。2003年的SARS疫情中,高达38.4%的患者出现腹泻症状[27],相比之下COVID-19的消化道症状发生率较低。国内外的多数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3,16-19,24-26]。在一项涉及中国30个省552家医院共1 099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一共有42例(3.8%)患者表现出腹泻,出现恶心或呕吐的患者有55例(5.0%)[19]。然而,也有研究显示消化道症状较常见。在一项纳入了140例患者的研究中,55例(39.6%)出现消化道症状,包括恶心(17.3%)、腹泻(12.9%)、厌食(12.2%)和腹痛(5.8%)[21]。上述不同结果可能与患者来源及纳入标准有关,但也不排除COVID-19的临床表现具有较高的变异性。总的来说,COVID-19的消化道症状并不少见,值得临床工作者注意。
此外,COVID-19患者的消化道受累可作为首发表现,甚至可能仅出现消化道症状而缺乏呼吸系统表现。在一项包括138例COVID-19患者的研究中,14例(10.1%)的首发症状为腹泻和恶心,比发热和呼吸困难提前1~2 d出现[5]。Xi等[28]发现,在74例有消化道症状的患者中,有21例(28.38%)始终未出现呼吸系统症状如咳嗽和咳痰,而仅表现出恶心、呕吐和腹泻。这些研究都表明,在COVID-19的防控工作中应重视消化系统症状,轻视或忽视可能会影响疫情防控,甚至加速疾病的传播。另一方面,若能够及早重视消化道症状,可能有利于早期发现和治疗。例如,有接触史但仅表现为消化道症状的患者也应该按照规定进行隔离观察,必要时接受SARS-CoV-2的检测。
除了起病阶段, COVID-19患者在疾病转归中也可能会出现消化道症状。Lin等[22]对95例COVID-19患者住院期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58例(61.1%)有消化道症状的患者中,仅11例是在入院时即出现,而大多数均为住院过程中出现。Fang等[20]指出,消化道症状多于起病后1~10 d出现,中位数时间3 d。腹泻症状于起病后1~8 d出现,中位时间3.3 d,腹泻可持续 1~14 d,平均为(4.1±2.5)d,有22.2%的患者出现非药物相关性腹泻。
值得一提的是,COVID-19患儿的病情比成年人轻微(症状更轻、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指标异常更少)[29-31],但消化道症状与成人类似,甚至也可作为主要症状。在一项包含171例COVID-19患儿(中位数年龄为6.7岁)的研究中,出现腹泻的患儿有15例(8.8%),呕吐有11例(6.4%)。另一组研究包括31例患儿,其中3例(10%)出现腹泻,且均以腹泻为首发症状,伴或不伴发热,无明显的感染中毒症状[31]。根据现有结果可以判断,消化道症状在COVID-19成年或儿童患者均可能出现,故值得重视。
3 粪便病毒检测
COVID-19患者的粪便可检测出SARS-CoV-2 RNA,这一发现备受关注。自从第1例粪便核酸阳性的患者[4]被报道后,越来越多的粪便核酸阳性病例被发现。尽管单凭粪便SARS-CoV-2 RNA阳性尚不足以证实传染性,但经消化道传播的潜在可能性不容忽视。综合目前的数据,确诊患者粪便中SARS-CoV-2 RNA阳性率为6.2%~47.4%[22-23,32-33]。其中,Wang等[32]检测了153例COVID-19确诊患者的粪便标本,发现44例(29%)阳性。在另一项研究中,62份粪便样本中有4份(6.2%)阳性,另有4例患者肛拭子检测为阳性,并伴有胃肠道中病毒的检出[33]。美国初发的10例COVID-19患者中,粪便核酸阳性率高达70%[25]。不同的阳性率可能与患者例数和检测试剂盒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不同有关。此外,具有传染性的SARS-CoV-2已经从粪便中被分离出来[11],但这一结果尚需要更多验证。
有研究显示腹泻患者粪便中SARS-CoV-2 RNA 检出率较无腹泻患者更高,同时粪便中病毒载量也更高[23,34]。但需要强调的是,没有消化道症状并不代表着粪便SARS-CoV-2 RNA为阴性。在44例无消化道症状的患者中,仍有4例(9.1%)患者检测出粪便阳性[23]。关于腹泻症状与粪便核酸阳性率之间的关系,不同研究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42例有消化道症状的患者中,有22例(52.4%)患者粪便检测阳性,而无消化道症状的23例患者中有9例(39.1%)为阳性,两组没有显著性差异[22],这可能与样本量和检测方法有关。
目前有研究显示了患者粪便SARS-CoV-2核酸阳性的出现与转阴都滞后于咽拭子的结果[35-37]。Ling等[35]对66例粪便核酸阳性的患者进行观察,直至其中55例患者转阴,得出粪便核酸阳性的中位持续时间是11 d。与咽拭子转阴相比,78.2%(43/55)的患者粪便标本转阴时间滞后于咽拭子,中位滞后时间为2 d。Zhang等[36]的研究也发现,口咽拭子SARS-CoV-2核酸阳性的出现至少比粪便核酸阳性提前1 d,且咽拭子的转阴时间至少比粪便样本提前2 d。这些结果提示,若患者就诊时检测粪便核酸阴性,也有可能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转为阳性,应该引起临床工作者的警惕。另外,鉴于粪便核酸检测阳性的滞后时间并不长,在疾病的早期是否可以考虑对咽拭子阴性而又高度怀疑COVID-19的患者加测粪便SARS-CoV-2核酸?同时,对于恢复期的患者,鉴于粪便中SARS-CoV-2 RNA转阴时间滞后于口咽拭子,是否应考虑将粪便核酸检查应用于患者的恢复期,以进一步降低病毒经粪便传播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粪便核酸阳性的发生率并不低,文献报道的最高发生率达70%,因此,在运送患者粪便标本时,医护人员应注意防护。若患者出现粪便核酸阳性,则应该加强对其粪便等排泄物的管理,以免造成感染播散。在检测准确率方面,粪便核酸检测的准确率和咽拭子核酸检测相近[36]。
4 消化道内镜发现及病理改变
COVID-19患者消化道内镜下的病变差异较大,从无异常到糜烂、溃疡,甚至出血。在病理切片中,可见消化道腺上皮组织中的炎性细胞浸润、水肿等炎性反应表现,还可在消化道腺上皮细胞的胞质内检测到SRAS-CoV-2核酸阳性。Xiao等[11]对1例COVID-19患者的消化道标本进行荧光染色处理,显示食管、胃、十二指肠、直肠黏膜上皮未见明显损伤;但在胃、十二指肠和直肠的固有层中,可见大量浆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伴间质性水肿,食管鳞状上皮仅偶见淋巴细胞浸润;病毒核衣壳蛋白的染色主要出现在胃、十二指肠及直肠腺上皮的细胞质中,而食管上皮细胞中未见染色。在另一项研究中,6例患者中有1例严重病例发生消化道出血,经内镜检查出血灶位于食管距前牙26 cm处,有多发圆形疱疹样糜烂及溃疡,直径4~6 mm。溃疡表面被覆一层白苔和血凝块,部分融合成块并有少量出血。在该病例中,食管糜烂出血部位及胃、十二指肠、直肠组织都可检测到SARS-CoV-2 RNA。而其他5例在内镜下无明显异常改变,其中1例重症患者的食管、胃、十二指肠和直肠也可检测到RNA,但另4例非重症患者中除了1例仅在十二指肠中检测出SARS-CoV-2 RNA外,其余3例均不能检测到核酸[22]。这些研究表明消化道的病理改变可能和COVID-19的严重性有关。此外,SARS-CoV-2在消化道腺上皮细胞中的大量存在说明了该病毒的嗜消化道腺上皮细胞性。
5 消化道症状与临床预后
有研究提示消化道症状与COVID-19不良预后相关。Jin等[28]对651例COVID-19患者(包含74例有消化道症状的患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有消化道症状的患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肝损伤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无消化道症状者。此外,伴有消化道症状的患者进展为严重/危重型COVID-19的风险也明显高于无消化道症状者(22.97%vs8.14%,P<0.001)。Wang等[5]和Pan等[38]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认为消化道症状与COVID-19的严重性有关。在COVID-19的治疗方面,Mo等[39]对难治性COVID-19进行了研究。非难治性被定义为:治疗后呼吸症状明显缓解、不使用激素和退烧药的情况下体温正常≥3 d、治疗后胸部影像表现改善、住院时间≤10 d。不符合该定义的患者即为难治性。而男性、入院时伴有厌食症状是难治性COVID-19的危险因素。以上研究都表明,消化道症状的出现可能与不良的预后相关,也提示临床医生应该关注并监测出现消化道症状的患者,防止疾病的恶化。
6 结论
本文讨论了COVID-19患者的消化道受累表现。消化道症状不仅可以出现于COVID-19疾病初期,甚至成为首发表现,还可贯穿临床转归全过程。粪便SARS-CoV-2核酸阳性及消化道病理显示腺上皮受侵,都提示COVID-19患者经消化道传播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因此,本文作者强烈建议临床工作者不能因重视呼吸系统而忽略消化道表现,及时关注消化道受累有助于COVID-19的诊治和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