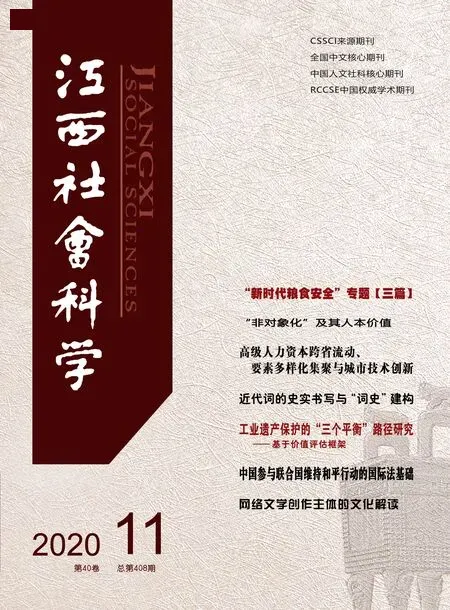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的声音叙事
卡森·麦卡勒斯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其作品对时代与社会的观察最为动人。她在作品中利用声音(包括对话、收音机声、钢琴声等)叙事,构建出多声部的作品,使其作品价值得以提升。声音叙事背后所涉及的美国南方伦理道德、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消费主义陷阱等论题发人深省,从而使其个别的角色描写升华为南方地域认同以及“二战”后美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反思,变成全面“向内审视”。麦卡勒斯试图在其作品中通过声音叙事来治疗“孤独症”这一“美国式疾病”。
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是美国南方文学作家中不可忽视的一员,22岁时就发表了第一部作品《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1940),被称为“年轻的天才”[1]。文学史对麦卡勒斯的评价呈现两极化。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在读了《婚礼的成员》后称赞麦卡勒斯“很可能是当代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2](P275),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只是一个“次要作家”,更有甚者认为其小说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所以作品未必优秀。但麦卡勒斯作为南方文艺复兴(The Southern Literary Renaissance,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①后期作家,在其小说中表现的历史观念与国家意识较前辈们“向后看的历史意识”更为直观,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使得其作品的视野更为宏观,也洗脱了所谓的“自传”的嫌疑,从其对时代的观察与社会的反思看,其绝对是一个“重要作家”。
麦卡勒斯在自己的小说中通过声音叙事多维度呈现对国家的反思与批判,直面历史,寻找家国出路。这些声音背后所蕴含的美国“二战”时期的南方历史认同、美国政治经济问题等内涵,将治疗个体的“孤独症”②变成了对美国国家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
一、种族对话与南方之殇的新探讨
《婚礼的成员》(下文简称《婚》)中,12岁的南方小镇女孩弗兰淇每天与黑人保姆贝丽尼斯(Berenice Sadie Brown)和表弟约翰(John Henry West)困在厨房里,她与贝丽尼斯之间的对话声音是《婚》中最常出现的声音,她们之间的对话只是“坐在厨房餐桌边,把同样的话说上一遍又一遍”[3](P4),“孤独、隔绝和恐惧填满了三个角色,就像他们蜷缩在厨房的桌子旁边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日常状态的相似物”[4](P14)。弗兰淇在这样的交流中逐渐失声,“孤独症”更为严重。弗兰淇的梦想是离开小镇,治愈自己的“孤独症”。为此,她一遍一遍与贝丽尼斯沟通,可是贝丽尼斯拒绝认同她的梦想,交流陷入僵局,“每到下午,世界就如同死去一半,一切停滞不动”[3](P4)。即便这样,当弗兰淇哥哥即将结婚的消息传来之际,弗兰淇还是主动提及婚礼,开启她们之间的对话:
“真古怪”,她说,“就这样发生了”。
“发生了?发生了?”贝丽尼斯说。
约翰·亨利在一旁听,安静地看着他们。
“我从来没有这么迷惑过。”
“可你迷惑什么?”
“整件事。”弗兰淇说。
贝丽尼斯回应道:“我想你脑子准是被太阳烤煳了。”[3](P4)
对贝丽尼斯来说,婚礼就是一个消息、一个喜讯,不存在任何其他意义,所以她不断发问。然而对于长期孤独与精神隔离的弗兰淇来说,婚礼带给弗兰淇的是实现梦想的可能性,因为她的哥哥与嫂子都生活在“冬山”,远离小镇。所以弗兰淇的语气“迷惑”而不确定。对话最终像往常一样被贝丽尼斯轻松地以“脑子准是被太阳烤煳了”为由粗暴地压制。贝丽尼斯“每句话都是否定的,想尽办法要把婚礼的意义打发掉”[3](P105)。
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关系密不可分,权力通过言语规训得以实现。《婚》中,为了打消弗兰淇离开小镇的想法,贝丽尼斯一再出言压制弗兰淇。但贝丽尼斯是黑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对话模式是不可能发生的。从《婚》的时代背景看,这样的对话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婚》以20世纪40年代为背景,此时的南方,3K党、种族隔离等问题先后出现,种族对抗不断加剧,这在南方甚至整个美国都是最主要的政治问题。小说对话声音中所显示的权力关系的错位可以理解为是对种族主义的反思。在错位中完成移情,当弱势与强势、主流与边缘完成错位,移情才会真正发生,种族问题也才有可能解决。而这种错位发生的根源却是因为贝丽尼斯的语言中蕴含的其他元素,比如接下来的对话中出现的宗教思想。
“看着我”,贝丽尼斯说,
“你嫉妒了?”
“嫉妒?”
“嫉妒你哥哥要结婚?”
“没有。”弗兰淇说:“我只是从没见过像他们俩那样的人。今天看着他们走进来,感觉很怪。”
“你就是嫉妒。”贝丽尼斯说:“去照照镜子,看你眼睛的颜色就知道了。”[3](P5)
这段对话接着讨论“婚礼”,贝丽尼斯用两个问句、一个肯定句给弗兰淇下了定义“嫉妒”。“嫉妒”与基督教之中的“妒忌(envy)”相对,是不可饶恕之罪。“任何流露出这些罪过的灵魂都将被打入万劫不复之地。”[5](P364)尽管弗兰淇极力否认:“告诉过你,我不是嫉妒。”贝丽尼斯却说:“灰眼睛的人好嫉妒,这事千真万确,谁都知道。”[3](P22)贝丽尼斯的定论源于自己曾因哥哥的婚礼而嫉妒。因为她自己信教,她的“嫉妒”可以通过告解缓解,得到救赎。贝丽尼斯常说弗兰淇吃得太多,认为弗兰淇的食量根本不是一个人的食量,“粗鲁自大”“贪嘴”“懒惰”与七宗罪中的“自负”“暴食”“懒惰”也相对应,这些都是“万劫不复”的罪过,弗兰淇完全无法得到救赎。为了打消弗兰淇离开南方的想法,贝丽尼斯对弗兰淇讲述诺亚方舟的故事,诺亚“每种动物收留一对儿”[3](P104)。她认为弗兰淇爱上一个婚礼是不可思议的。显然,这些话语都加剧了弗兰淇的孤独。弗兰淇整日困在厨房,不参加教会活动,表弟约翰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祈祷,弗兰淇却只会在黑暗中寻找“声音”排解害怕与静寂,显然就不能从宗教意义上得到缓解,这只能加剧她的“孤独症”。贝丽尼斯用宗教声音对弗兰淇实行了“精神隔离”,用所谓的“这事千真万确,谁都知道”[3](P104)增强了话语的分量。贝丽尼斯自己是浸礼教的信徒,清楚地知道“七罪宗”的后果,她用“罪”来规训弗兰淇。麦卡勒斯“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又都坚定不移地信奉着上帝,并用自己的‘信’与主人公的‘不信’进行着激烈的角力”[6]。而在《婚》中,这种“角力”就变成了贝丽尼斯对弗兰淇的“规训”。
贝丽尼斯的声音中还蕴含了父权和南方传统伦理内涵。贝丽尼斯时常用弗兰淇的父亲来压制她:“你清楚你爸爸对在这房间里玩球的态度。”[4](P49)弗兰淇外出不归家,贝丽尼斯会给她的父亲打电话,因为她知道弗兰淇最害怕的就是父亲。“你的父亲检查食品账单的时候,数目那么大,很自然地怀疑是我私吞了呢!”[3](P141)弗兰淇与父亲之间的对话经常是弗兰淇说而他爸爸不回答。比如她说:“爸爸,我得告诉你,婚礼之后我不回来了。”[3](P69)但是父亲没有回答,“他倒是有耳朵……他只是没有听”[3](P69)。《婚》中弗兰淇自幼丧母,沉默寡言的父亲很少跟她交流,为数不多的交流也是一再地对弗兰淇进行规训。例如当他发现弗兰淇偷用家里的工具时,他教训道:“如果你不明白事理,不知道有些东西不能碰……那就得好好教训你才行。从现在起给我规规矩矩,不然就得挨训。”[3](P70)为数不多的交流所起到的强大的压制效果显现出父权的强大存在,虽然父亲常常缺场。贝丽尼斯运用父权压制弗兰淇是很讽刺的。黑人女性在南方受到的压迫是最为严重的,贝丽尼斯却用父权一再压制弗兰淇,贝丽尼斯没有意识到自己声音中的父权声音,意味着在权力关系错位之后,黑人女性也很难获得自己的主体意识,难以觉醒。有学者认为:“贝丽尼斯的话语中包含了南方文化中的性别意识,抑制了弗兰淇的个体自由发展;弗兰淇的语言与其身份意识构建联系紧密,她为发出自己的声音所做的抗争折射出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话语表达所受到的压迫。”[7]《婚》中弗兰淇所受到的压迫是双重的,不仅抑制“个体自由发展”,而且存在种族压迫。更为重要的是麦卡勒斯通过错位的权力关系来反思种族关系。贝丽尼斯也未因权力关系改变而成为真正的主导者,她只不过是父权的传声筒、代理人,社会对她的压迫依旧存在。弗兰淇意识到自己的失声,通过“寻声”自救,贝丽尼斯却从未有此意识。
种族问题的解决绝不是简单的地位的对换,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对待留在黑人身上的伤痕,这些伤痕更多地表现在黑人精神上对白人社会的认同,她们沦为南方传统的卫道者。黑暗的蓄奴制不仅代表南方黑暗的历史,更是南方衰落的根源,不论对于白人还是黑人而言,其都是南方之殇。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即便扭转,白人对黑人的规训与影响也是无法消除的。麦卡勒斯正是通过错位的权力关系设置来正视历史。只有正视伤痕,彻底反省,才能真正解决种族问题,不顾历史与伤痕的对话达不到消除种族主义的效果。
二、收音机——帝国强权的反思
麦卡勒斯在数部小说中都提及收音机这个物品。这跟时代有关,20世纪40年代正是美国广播行业的“黄金时代”。但收音机显然是麦卡勒斯刻意设置的物品。《婚》的创作经历了从1941年到1946年五个春秋,不仅小说创作的时间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期间,小说的时间背景也是“二战”。“在这个夏天,巴顿追击德国人穿越了法国,俄国、塞班岛也同时在开战。”[3](P30)这与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吻合。这一时期,广播产业空前繁荣,战争宣传和商业广告都离不开广播。1938年,美国“联网广播”系统建立,从此收音机广告大为发展,到“二战”时期,“由于新闻纸张和其他资源的短缺,广播成为广告客户为数不多的促销宣传渠道之一”[8](P506)。广播进入其发展的“黄金时代”。麦卡勒斯在《婚》中第一次提到收音机时这样描述:
餐厅里的收音机几个台搅在一起:战争新闻夹杂着含混的广告,隐约传来一支轻音乐队有气无力的曲子。收音机开了整个夏天,最终他们已经充耳不闻。有时候声音太大,吵得他们快聋了,弗兰淇就会调小一点。其他时间,收音机里的音乐和人语彼此往来缠绕,到八月时节他们就不再理睬它了。[3](P13)
《婚》中弗兰淇最为常见的活动就是在晚饭后与贝丽尼斯、小约翰一起待在厨房里,大多数时候都是打牌度日,弗兰淇终日觉得自己特别孤独。空旷的厨房里除了三个人外,收音机的声音就一直存在,宛如一个背景音乐。这也是隔绝的小镇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唯一的外来的声音。整个夏天,厨房里的收音机都一直开着,传出各种信息,广告声的“含混”和“轻音乐队有气无力”的隐约存在,突出了“战争新闻”的主导地位。这不仅符合当时的战争形势,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美国的政治主张和战争时期的政治宣传。罗斯福上台之后采用的“炉边会话”(fireside chat)③的形式初步建立了广播的政治功能,“二战”的“广播宣传战”[9]也使得广播更多地背负起政治宣传的功能。美国政府在正式参战之前,就通过广播揭露法西斯的残忍暴行,刺激国内反法西斯情绪。在1941年美国加入“二战”后,为了破除美国“孤立主义”(isolationism)④的影响,罗斯福也不断地在“炉边会话”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美国参战后,收音机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为了维持国民信心和国内稳定,广播“必须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成为国家的工具”[9]。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开始对广播进行审查,广播公司“尽管声称保持政治中立,他们还是作为公共服务设施为政府广播‘施政新闻’”[8](P478)。
“战争新闻”作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信息”,受到美国政府的审查,所以《婚》中收音机里的“战争新闻”就呈现为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的“信息”。贝丽尼斯在闲暇时间爱开收音机打发时间,通过收音机知道“信息”。战争时期,民众对于“战争新闻”特别重视,在美国加入“二战”后更是如此。“无线电广播对战争的报道也作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听新闻广播已经成为一种全民的习惯,美国民众可以从5600万台收音机中收听到战争的消息。”[8](P487)小说里,收音机中源源不断的战争新闻,几乎响彻整个夏天,也与收音机的强大影响对应。民众在收音机的帮助下完成“政治观念”的认同,而政府却在收音机的帮助下对民众的思想得以控制。麦卡勒斯对于收音机在战争中的作用十分清楚,她曾说:“过去的这一年怪异的,摇摆不定的特征。闪电战——欧洲的溃败——收音机中的葬礼进行曲,预示着每一场新的陷落——残骸的前身,曾经是所谓的‘民主政治’。”[8](P132)小说中的收音机,体现了麦卡勒斯对“民主政治”的反思,以及对国家集权的反思。阅读麦卡勒斯相关的资料可知,她支持美国破除“孤立主义”的影响,希望美国尽快参与到“二战”之中去。而从小说中弗兰淇对收音机的拒绝看,麦卡勒斯对战争的态度十分矛盾,她既希望自己的国家参与到“二战”之中去,因为她认为反法西斯战争是正确的事情,但她对美国在战争期间通过收音机控制民众的方式却又十分反感。学者曾经这样评价道:“卡森对社会不公正以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强权的军事侵略所感到的愤怒大多明确地表现在她的小说中。”[2](P93)但矛盾的是:“她觉得即使盟军最终赢得了战争,到那时,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可以继承呢?”[2](P211)显然,麦卡勒斯批判的是大众传媒的政治属性使人们丧失自我辨别的能力。在当时来说,麦卡勒斯这种思想是十分先进的,法兰克福学派也有相关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传媒的批判十分彻底。马克思·霍克海默(M.Horkheimer)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指出:“广播公司虽说是私人企业,但他却代表着整个国家的主权。”“广播是国家的咽喉。”[10](P144)在收音机的控制下,弗兰淇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几乎“快聋了”。她调低音量,甚至在贝丽尼斯要求她打开收音机时拒绝。在小镇旅馆“蓝月亮”中听到收音机声时,想到的是“墙后的死老鼠”。在麦卡勒斯看来,收音机传来的消息,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控制着人们的听觉,国家权力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通过收音机这个载体遍布每个角落,“收音机(广播)增加了现代社会集权和单一倾向”[11](P18)。麦卡勒斯在小说中体现的观念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那个时代,“听新闻广播已经成为一种全民的习惯,美国民众可以从5600万台收音机中收听到战争的消息”[8](P487)。在无聊的时候,贝丽尼斯反复要求弗兰淇打开收音机,甚至会引用收音机中的新闻来打断与弗兰淇的交流。“对了,我今天早上听收音机说,法国人正把德国人赶出巴黎。”[3](P23)贝丽尼斯对待收音机的态度与弗兰淇截然相反,更符合大众的做法。广播“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了听众,使所有听众都被迫去收听几乎完全雷同的节目……在官方广播中,人们……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11](P109)。贝丽尼斯虽然被迫成为听众,但也变成了真正听话的受众。威尔森·凯撒(Wilson Kaiser)在评论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时也曾关注到其中的收音机设置,他认为:“收音机通过束缚于亲密的场景把这些‘大众’现象融入了日常。”[12](P295)而麦卡勒斯在小说中设置收音机,不仅想让“大众现象”融入生活,她更想强调广播作为政治工具的实质,而贝丽尼斯的态度是社会大众在小说中的剪影,她们被规训而不自知。大多数的人同贝丽尼斯一样,接受收音机中的任何消息,不批判,甚至将收音机中的信息当成谈资跟别人交流,融入社会。“收音机广播提供了通往更广阔的世界的通道,米琪(《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女主人公)继续觉得她被周围的环境所陷害。”[13](P22)
弗兰淇却不断说:“我说不清为什么,但就是不想再开收音机,让我想起太多这个夏天的事。”[3](P121)这表达了麦卡勒斯对国家政治的反思以及其对时代发展的精准把控。相比于“大众文化”,她更推崇“知识分子化”的建设,而知识分子的呐喊注定是孤独的。“民主政治——知识分子化与道德的自由,能随意去选取对于我们而言具有最大生产力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去建立我们自己独立精神价值的权利,那就是‘美国理想’的呼吸。”[14](P132)弗兰淇的“孤独症”显然就是麦卡勒斯所追求的“独立精神价值”的表征。麦卡勒斯通过收音机声音的描写反思大众传媒背后的帝国强权控制,也寄希望于知识分子应该在大众传媒面前保持理智,承担自己的责任。
三、钢琴——资本主义的剥削噩梦
麦卡勒斯几乎在每一部小说中都提及了钢琴,《心是孤独的猎手》主人公米琪的梦想是拥有一架钢琴;《金色眼睛的映像》中被丈夫背叛的兰顿夫人的日常喜好是听钢琴曲,她的丈夫曾揶揄过这个高雅的爱好;《没有指针的钟》中黑人舍曼弹得一手好钢琴,还有一副好嗓子;《婚礼的成员》中的犹太调琴师不断地在寂静的夜空下重复调琴,打破小镇的宁静,使得主人公弗兰淇烦躁不已,却又无法逃脱。可以看出,麦卡勒斯真的很喜欢在自己的小说中提到钢琴,一是因为她幼年时学习过钢琴,二是因为在美国南方社会的这个大背景之下,钢琴不再是简单的物品,而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到了20世纪40年代,钢琴又因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钢琴是传统南方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对于南方淑女来说,学习钢琴是必修课。南方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比较低,南方传统文化倡导的是绅士保护女性,女性则要做“淑女”。在南方,钢琴总是与上层社会的身份无法分开。2019年上映的电影《绿皮书》中,一个黑人爵士音乐家到南方表演,观众其实都是当地的上层社会人士。《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琪出生于一个普通白人家庭,家中唯一的房产因为弟弟惹的麻烦而失去,父亲受伤没有工作,靠着妈妈给租客提供住宿与餐食维持生活。她是家里最被忽视的一个孩子,要照顾年幼的弟弟,不能跟两个姐姐一样快乐地玩耍。她从小就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因为她一直都跟两个姐姐挤在一个房间里。她从小就想学习音乐,想要学习钢琴,可是她的家庭条件根本满足不了这个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时常去自己家房客的房间中听收音机,因为收音机中经常有钢琴曲传出来。后来辛格先生搬进她家之后,甚至允许她自己调换喜欢的音乐频道,她很是高兴。久而久之,她的钢琴梦想被收音机所代替。20世纪40年代正处于收音机的“黄金时期”,收音机的普及显然也促进了高雅音乐的传播,使得如米琪这样的贫困女孩有了梦想。收音机搭起了米琪与钢琴之间的桥梁,使得普通的小女孩也开始做梦。
《没有指针的钟》中的黑人角色舍曼的身世贯穿整本小说。他不同于传统的黑人,天生一副好嗓子,还会弹钢琴,有着一双蓝色的眼睛。他其实是黑人与白人的混血,但是一直想象自己的母亲是一个被白人强奸的黑人。他有着强烈的黑人的种族自尊心,但是一直以来也遵守着南方社会的规训,对白人虽然仇恨却处处忍让。这部小说中,黑人舍曼终于拥有钢琴,虽然还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但是拥有钢琴之后的故事充满紧张与危险。舍曼所购买的钢琴代表的是除了阶级之分以外的南方普遍存在的种族之分,种族之间的界限被舍曼以消费这种外在表现形式打破,他花钱租了白人社区的房子,买了新家具,这些消费与米琪的“梦想”显然不一样,是一个黑人通过拥有物品来挑战种族隔离。
舍曼最终因为搬进白人社区而被白人种族主义者萨克杀害。萨克没有因为这件事承担任何的后果,指使他的大法官更不可能受到任何的惩罚,因为在白人至上主义影响的南方司法界,白人拥有的权力大于黑人,黑人在现实中受到私刑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屡有发生。黑人完全无法得到任何公平的对待。舍曼的父亲与母亲相爱触犯了南方白人传统中的黑人与白人不通婚的伦理,触发了白人社会的禁忌,南方传统的绅士文化中的保护女性就是以预设白人女性被黑人侮辱为理论基础的。显然麦卡勒斯完全无视传统禁忌,挑战南方传统伦理。涉及种族歧视的各种相关法律早已成为事实,法庭一般都由白人掌控,舍曼父亲案子的法官和陪审员都是白人,黑人的权益很难保障。舍曼的身世就是麦卡勒斯对南方种族关系的艺术刻画,冲突与禁忌都得以体现,却又符合种族歧视的南方大环境。钢琴成为这场冲突的见证物,虽然最后也被炸得破损不堪,但是萨克的孩子们还在院子中弹奏玩耍,预示着这样的血腥冲突并不会使白人反省。法律不改变,种族歧视就会继续,老法官就如同南方种族歧视的法律体系一样,老旧但强大,黑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丝毫没有还手的能力。麦卡勒斯关于种族关系的观念的开放程度,很难让人想到她是一个南方白人作家,她的小说对黑人的同情与种族冲突的刻画都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显得更为人性化。
小说中,舍曼被萨克用炸弹袭击之后,放在园中的钢琴也被炸毁,在这样凄厉的场景中,萨克的孩子们却在弹着这架损毁的钢琴,场面莫名的诡异与讽刺。穷白人萨克被法官利用,去报复黑人,他的孩子们弹奏这架破损的钢琴,表明穷白人对于白皮肤的极度守护本身会让自己被上层白人剥削而不自知,为了守护自己仅有的白皮肤的尊严,他们痛恨黑人,誓死也要守住所谓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界限,仿佛只有守住这个界限自己就是一个“上层的”“有尊严的”白人。孩子们弹奏钢琴,说明未来这种冲突也不会结束。
不论是一条人命的消失还是新的仇恨的建立,钢琴就是钢琴,但它背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对比高收入阶层所谓的“炫耀式消费”,大众消费主要是指当时因为“福特主义”的兴起而形成的普通人或者可以说工人阶级的消费行为模式。麦卡勒斯却通过米琪与舍曼的遭遇挑破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而在南方黑人身上,不仅要遭受资本主义剥削,还要承受种族歧视的恶果。
麦卡勒斯显然对20世纪40年代被消费文化影响的南方现代社会有很深刻的理解。收音机与钢琴背后的消费文化使人们异化,收音机背后的大众传媒促进了拜金理念的进一步传播。底层的人们,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财产与地位的观念,或者有物品与阶级的相对关系的观念。大众媒体的存在促进了这种观念的传播,物品消费被美国梦笼罩。实际却是,一边因为种族隔离受到歧视,一边因为经济基础差而毫无地位,黑人与底层白人还是躲不过南方旧时上层白人精英的盘剥。传媒的兴起本身就促进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拜金美国梦的传播。美国梦从富兰克林时代的务实,到20世纪40年代,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变得拜金而虚无。美国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底层白人与黑人来说,已经变成了“美国噩梦”。米琪与舍曼却仍然愿意为了听到钢琴的声音而失去生活与生命,令人惋惜不止。
四、结语
麦卡勒斯作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第二代作家,其小说有着更多的家国情怀,她不仅通过贝丽尼斯与弗兰淇之间的对话表达自己对于种族主义的看法,也通过小说中收音机与钢琴的书写表达自己对于帝国主义强权和经济剥夺的深层理解与反感。由此麦卡勒斯通过声音叙事实现了全面“向内审视”。对于本土的关注使得麦卡勒斯成为一个美国作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南方作家。而其对于“美国式疾病”的探讨与反思,有着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引自肖明翰《美国南方文艺复兴与现代主义》(《当代外国文学》1996年第4期),主要指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普遍具有较为保守的历史观念。
②麦卡勒斯在《孤独——一种美国病》中说:“孤独是最大的美国式。这种孤独的属性是什么?看起来,似乎他本质上会是一种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吧。”本文中所指的“孤独症”不同于病理意义上的孤独症(自闭症的别称),特指麦卡勒斯所描写的“二战”时期美国人的精神状况,以“孤独”和“精神隔离”为表征。
③炉边会话是美国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1882—1945)的一档广播节目,罗斯福在其中宣传其政治主张,这个节目陪伴美国人渡过大萧条与“二战”的危机,也开启了收音机宣传政治思想的先河。
④孤立主义是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要地位的政治主张。这种主张与美国远离欧洲大陆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主要主张不干涉。“二战”初期受到孤立主义的影响,美国曾长期不参战,直到“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才参与“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