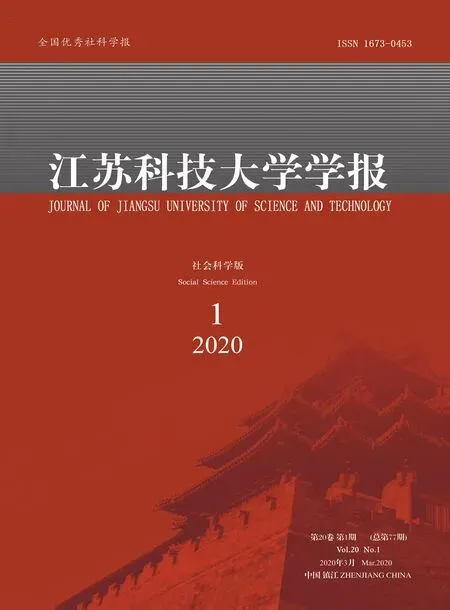新型消费模式的蔓延:个体化视角下“一人式”消费的产生与发展
徐 颖, 范和生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当前,伴随着我国社会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网络化浪潮,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产生的“虹吸效应”吸引了大量青年涌入,我国的单身群体规模日益扩大。根据2018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单身人口数量已达2.4亿,并还在持续上涨中。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单身等同于孤单,如今的单身青年更加注重表现和关注自我,越来越注重高品质的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生活质量,甚至从被动单身到主动选择单身。庞大的单身人群催生出新消费态势——“一人式”消费。“一人式”消费开启了单身群体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并日益成为消费社会中的新型消费业态。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三浦展将消费划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以大城市为导向的消费社会,城市中的精英群体是消费主体,具体以百货在城市的遍布为代表;第二,以家庭为导向的消费社会,主要追求“大而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家电的畅销;第三,以个人为导向的消费社会,追求个性化和品质化,因而以追求个性化服务和各种奢侈品牌为代表;第四,以利他为导向的消费社会,追求共享和质朴,以“无印良品”的盛行为主要表现,在此阶段,人们更加喜欢自然世界,更加注重分享与精神层面的满足[1]。不难看出,我国正处于以个人为导向的第三消费社会。根据2018年11月天猫统计的消费数据,网上购买迷你微波炉、迷你洗衣机以及一人份火锅的人数增长迅猛,与去年相比,分别增长了980%、630%、200%,“一人量”商品成为大趋势。各类电子商务平台和投资产业也抓住了单身热潮的商业契机,纷纷扩资投放“迷你”“KTV”“自助火锅”等“一人”经济体于各大商场、电影院和餐饮店,从而造就了一人食、一人住、一人旅游等产业链的延伸与拓展。“一人式”经济对发达国家而言已经不足为奇,但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环境而言是新鲜事物,其发展与蔓延的态势很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相关文献回顾
个体化是现代性研究中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含义的重要议题,其概念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在早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指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标志着传统型权威向合法性权威转型,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个体化的进程。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在其“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理论的论述中揭示了个人从传统家庭结构中剥离是现代社会的走向,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到社会团结中个人主义的问题[2]。由此,关于从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中脱离并强调个体独立价值的结论开始萌芽。随后,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其著作《新时代精神》中将个体化释义为:当个体真正意识到挣脱共同体的束缚而实现自身价值、目的、人格的重要性,个体化就会成为当代人社会生活的主要倾向[3]。杜博斯(Dubois)和比奥沃斯(Beauvais)通过分析个体目标的追求、自我需要的满足、契约性、个体定位、内在性五个方面被操作化的个体主义的概念来区分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4]。另外,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中引出了个体化进程中个体的精神表现与状态。他认为,一方面,在个人自由增长的同时,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随之相伴而生,个人自由的增长代表个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控制越来越得心应手以及个体力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日益加深的个体化进程又意味着个体孤独感与不安全感日益增加[5]。相较于早期西方社会学派对个体化的研究,鲍曼、贝克等人对个体化社会和个体化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更为系统的阐释。
首先,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第二现代性”,即“自反现代化”,他从国家集权、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分工和大众消费中概括出个体化的三重维度——解放的维度、重新整合的维度及去魅的维度,并认为个体化并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和人类的发明,而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自然生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境况[6]。
其次,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用“流动现代性”替换“后现代性”,认为个体化是个体身份从承受者(given)向责任者(task)转型以及使行动者承担完成任务的责任并对他们行为的后果负责。由此,他更加关注个体化进程中自由的非均衡性分配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消费私人化带来的道德冷漠与政治疏离[6]。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立足于结构主义立场认为,在传统性被现代性取代的时代,解放政治让位于生活政治,而个体化进程与生活政治紧密相连,选择自我是实现个体化的核心内容[7]。
国内学者对个体化理论的研究深受鲍曼、贝克等学者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农民工、高校大学生、女性群体并囿于中国个体化社会特征与影响的整体框架中。事实上,中国个体化浪潮的兴起与发展是“集体化人格”时代国家对本土道德世界予以社会主义改造和非集体化之后市场化与消费主义冲击所共同作用的结果。阎云翔通过分析黑龙江下岬村在集体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结构,并基于贝克的个体化理论提出了“个体化的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的个体化可以纳入“两次现代性”的解释框架[8]。焦玉良认为,一方面,个体化与组织化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面向;另一方面,二者又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他主张从组织化的现实出发来解释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现象[9]。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网络化进程的加快,个体被赋予极大的自由选择权和行动自主权,同时也面临城市空间被挤压、陌生人社会带来的不安全感、不稳定性的个体化风险,这一风险作用于个体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目前学界对“一人式”消费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是关于“一人式”消费的舆论报道,缺乏专业、深入的学术研究。因此,个体化理论能够为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与“一人式”消费现象提供一个可能的切入点与解释机理,从而凸显中国社会个体化及其消费的映像与进路,以推动新型消费结构的升级。
二、 心理动因:“一人式”消费的产生
任何消费行为总会受到一定心理动机的支配,这种来自个体内部的动力反映了消费者生理上、心理上、情感上的需要。众多单身青年“求新”体验的满足、碎片化的情感需求以及身份认同的渴望则不同程度地作用于“一人式”消费行为并促其产生与发展。
(一) “求新”的内在催酶:“功能性”消费向“体验式”消费范式的转换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个人价值的追求与探索日渐成为主导;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和移动在线支付的兴起极大推动了“功能性”消费向“体验式”消费的转变。在体验经济时代,商品对于消费者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功能属性和经济价值,而在于其所属的文化意义(cultural meaning)。伯恩德·施密特(Bernd Schmitt)认为,体验式营销(experiential marketing)是从消费者的感官(sense)、情感(feel)、思考(think)、行动(act)、关联(relate)五个方面设计营销的,有效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理性消费者”的假设[10],而“新”这一元素是体验式营销的着力点之一。青年消费者的“求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商品正式上市的“新”,即“新事物”,出现周期短;其二,商品样式、款式的“新”;其三,商品符号属性的“新”,即能够承载青年的新需求与新消费理念。众多单身青年思维活跃,富有反抗精神,其“求新”“求异”的消费心理驱使其欲通过各种消费活动实现自身的地位提升和价值追求。不同于传统经济模式,各类商业消费市场敏锐捕捉到正在快速崛起的单身群体这一新势力,从衣食住行到娱乐、休闲、社交一条完整的“单身产业链”由此呈现。以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各大商场、电影院的“迷你KTV”——“咪哒”为例,作为业界耗资投入的新商业模式,其电话亭式的外观构造充分迎合了单身青年的舒适度需求,社交与服务功能也尽可能被剔除,而更加专注于歌唱本身,有效避免了传统KTV中“麦霸”存在的尴尬。不可否认的是,消费者在实际购买、使用和消费商品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极大影响了个体自身的偏好、选择及行为方式的呈现,对商品的时间、质量、价格等基本因素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欲望。“咪哒”的人均消费仅为20~30元,系统录入的歌曲达20万首,因此无论现场亲身体验还是消费价格,这种“一人式”KTV都能够有效满足青年个体“求新”的日常生活体验与追求低价的消费心理,从而在传统消费市场脱颖而出。
(二) “碎片化”的情感需求:“碎片化”消费新场景的搭建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在改变传统一对一、固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带给个体更多话语权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类社会及个体本身。移动互联网及其技术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体时间、注意力以及情感的碎片化,碎片化又构成网络化社会信息传播的基本特征和青年个体日常生活的表征。同时,在个性化消费升级的时代里,环保、共享、智能、健康等理念推动消费朝重型方向发展,新消费模式的更迭引起需求端的变化,需求由此变得越来越颗粒化、碎片化、个性化。碎片化的需求最先被视频APP、简书、手机小游戏、喜马拉雅电台等线上平台精准识别,如前一段时间火爆朋友圈的《旅行青蛙》中的“割草”“备粮”“搭帐篷”等常规动作就充分利用了玩家的碎片化时间。这一消费新场景既折射出青年群体“空巢”又“空心”的孤独心理状态,又凸显出个体化社会中单身青年在线上或线下寻求圈群精神寄托以满足自身情感归属需要的积极尝试和努力。因此,碎片化的情感需求要求创建新场景(包括虚拟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而场景又激发新需求,伴随商业的自我进化与更新,从而形成一种自我满足式的消费闭环。逐渐地,线下的实体商业也从“瞬间式触发”“情感式交互”“便捷式愉悦”等消费者心理反应的角度开始进行个性化场景的搭建。“一人式经济”的背后正是一个人的消费体验和实际需求偏好,一些行业和品牌据此及时面向众多“单身一族”尤其是“空巢青年”推出了定制化服务与商业营销策略。例如,锐澳鸡尾酒在2018年推出RIO“微醺系列”,并以“一个人的小酒”概念成功契合了新生代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和偏好,轻松打入年轻人的市场;“海底捞”为单独吃饭的青年提供玩偶陪吃的个性化服务。总之,青年个体“一人食”“一人旅行”“一人住”等一系列消费实践在满足其碎片化情感需求的同时,推动了消费结构的升级,改变了一人即孤独的刻板印象。
(三) 符号消费中新身份认同的建构:“编码”与“内化”
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消费方式是个体身份认同的主要手段之一,通过消费获取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11]。消费者正是通过购买商品满足自身的真实需求并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对消费的选择行为是个体将无意识领域的主观形象投射到消费品上的反应。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到来,青年群体个体化特征日渐凸显,消费的符号性在青年的消费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符号消费的需求愈来愈强烈。同时,伴随着身份、地位衡量标准的变化,青年个体不再拘泥于传统门第、权力、财富、职业的身份建构方式,而是更多地从消费方式、消费理念及消费程度出发并在思想和行为上建构新的消费观,在解构自身身份认同的同时重新进行编码,从而构建新的身份认同系统,以期最终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确定自身所属的真正位置。王宁指出,“我”就是我所消费的东西和我所采取的消费的方式,此外,“我”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是由“我”对自己的看法所决定,个体消费实际上是在创造、维持或改变身份认同[12]。特定的阶层、阶级身份已经不能为人们提供认同感和归属感,人们只有通过消费并与世界、集体产生联系、建立关系,才能够获得一种新的、多元的身份认同。单身青年对于新身份认同的编码与内化无形中为“一人式”经济多元商业模式的开发与创新带来了基本需求与动力,规模化生产正朝向定制化和个性化生产转变,日益变化的非普通需求悄然改变着商业形态。一人撸猫、一人遛狗、一人旅行在当下显得丝毫不孤单,市面上更新的单人套餐、小型电饭煲、水壶、自动咖啡机、共享健身房、共享单车、无人货架等成功迎合了青年群体的新需求,也直接体现了其独特的品味、价值观、人生态度等。青年群体通过一人式消费行为的符号化呈现,并围绕身份认同的目的实现进一步延展,在广告、时尚、偶像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单身青年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价值观已然发生颠覆性改变。由此,“一人式”消费正在消费市场快速走红。
三、 技术之变:“一人式”消费的发展
“一人式”消费的产生和发展除了青年个体内在心理需求的推动,还有技术因素的推波助澜。显然,“一人经济体”的迅速扩大带给消费市场更多的营销商机,众多商家适时抓住了单身人群这一潜在的经济新风口,并基于UGC与PGC相结合的传播路径、社交圈群内日常化的广告植入以及“共享”理念模式中的社会化营销,以期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一) “个人门户”+“人际媒介”:基于UGC与PGC相结合的传播路径
个体化浪潮的兴起使得个体脱嵌于历史既定的身份、支持系统以及社会义务,个体自由选择通过其自身所处的特定场域和习惯进行自我身份建构。同时,总体性的社会范式逐步瓦解,个体很难在现实的集体社会与组织中获得安全性庇护,转而投入到网络化生存中,以寻求网络圈群的内在防御,抵御个体化社会带来的风险。在这种现实背景下,相关商家利用单身青年网络化生存常态,将UGC(用户生成模式)与PGC(专业生成模式)相结合,构建了“个人门户”+“人际媒介”及以社交和分享为其内容生产与传播动力的新传播模式。在“个人用户”(社交媒体账号)模式下,每个用户都可以在自己的账号中构建一个传播中心,它在整个传播网络中是一个传播节点,扮演着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多重角色,高度统一地推送内容,精准的用户定位和分众传播选择与多种传播渠道和媒体平台实现内在联动,最终形成新的运行机理,经由“个人用户”进行的信息传播能够更好地推动个性化内容的消费。各类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打造以“一人式”为主题的网红产品,以此吸引单身人群的关注与进一步消费。以近两年来火爆的“抖音APP”为例,集高流量于一身的大胃王“密子君”在线发布一人吃播的日常视频后,不仅获得网络用户的大量点击率与关注度,其推荐的“一人食”餐厅也激起众多青年个体的消费欲望。在当下新的传播逻辑里,短视频、自媒体和社交平台越来越成为爆款助推器。由此,在“互联网+”的消费环境下,普通视频用户、网红以及明星在平台PGC模式提供的技术环境(美颜滤镜、剪裁工具)中完成UGC模式里的多样化内容生产,最终形成诱发注意(attention)、引起兴趣(interesting)、进行搜索(searching)、促成购买(action)的消费实践生产循环和“滚雪球”的传播路径[13]。所有的平台用户在潜移默化中成为“行走的广告”,藉此为消费行业节约了大量的广告资本投入和时间精力的消耗。这种强大的、无边扩张的网络纽带及其技术效应不可避免地成为推动“一人式”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 社交圈群内日常化的广告植入: 个体注意力的吸纳与投放
目前,各类社交圈群内部日常化的广告投入与个体注意力的吸纳成为推动“一人式”消费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微信朋友圈为例,资本产业通常选择相关产品销售的代理人或微商进行模式化的广告宣传与日常曝光,通过微信朋友圈推送与“一人玩”“一人食”等单身经济内容有关的广告,采用微信建群的方式将拥有共同消费需求的人聚集在一个群中,并根据个体网络化“在线生存”的特征,定时或不定时推送商品广告信息和宣传卖点,最终达到唤起青年消费群体购买欲望的目的。电子媒介的不断更新与发展推动信息社会进入强势媒介时代,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原有界限日益模糊,注意力成为信息社会最有竞争力的资源,个性化的产品服务和营销手段成为吸引用户注意力的有效方式。因此,相关代理人(消费者)会以自己的社交圈为中心建立社会关系网,尽可能吸纳周边单身青年受众的注意力,促进成员的圈层化集合、交流及相互推荐,将现实社会中的“硬广告”与网络空间中的“软广告”投放同步进行[14]。互联网时代,注意力的流动性、稀缺性和广泛使用使其具有货币功能,俨然已成为当下最为紧缺的资源。从实际结果看,加深他人对广告的视觉印象即获取注意力,可以大大减少商品流通的时间和库存成本,潜在培养和促发青年尤其是单身青年的消费动机。在青年个体消费习惯不断得到充分迎合的情况下,个体会自觉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积极转发广告,转发即是一种劳动实践。一方面,青年个体在转发过程中完成自身欲望需求与广告商传达的消费意识形态的统一,即经济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有效的注意力可以引起人们无意识的模仿行为,正如泰拉诺瓦提出的“潜在的接纳”(latent adoption),这种注意力的吸纳交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肌理之中,并与其他日常行为联系在一起。当前,众多单身青年的朋友圈俨然已构成“价值网”和资本价值传输及价值生产的一部分。在此情况下,用户与社交平台的黏性和“一人式”经济效应得到极大增强。
(三) “共享”理念模式下的社会化营销:“好物分享”的行动逻辑
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技术加持,使得以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形态不断涌现并带动了“一人式”消费的拓展。不同于传统的占有式消费,共享经济穿越消费主义,在资源整合与综合利用基础上强调共享与体验式消费。当下的“分享”则是通过多元化互联网平台和共享理念形成以使用权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多的电商平台为了迎合“互联网+”的时代背景而植入“共享经济”理念和商业模式,创设了一种新的市场化的电商平台和公共产品服务系统,面向“单身一族”进行社会化营销。不可否认的是,个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分享范围和消费空间在移动线上支付的普及中得到了快速扩展。近年来大火的“小红书”购物App就是其中的典型。“小红书”作为共享经济时代中新的消费网络文化载体,其以青年群体为主要受众目标,主打生活服务,增设单身青年的宣传安排和业务增长点,一方面通过赞助爱奇艺《偶像练习生》和腾讯视频《创造101》等火爆综艺节目,以获取大量的曝光度和话题讨论度;另一方面吸引具备高流量的当红明星加入,众多明星或网红在其平台上分享各自的护肤、美妆、穿搭、拍照等私人经验,在满足网络围观者对明星日常生活的好奇感,呈现一人生活的精彩与乐趣的同时,扩大“一人经济体”消费理念与“好物分享”行为的传播。不同于淘宝、京东等电子商务购物平台,“小红书”除了借助网红或明星效应吸引用户,还以高质量的用户生产内容为主界面和营销着力点,不断促进平台用户基于美食、潮牌等内容的分享,当其分享的数据内容到达一定程度,平台内部的专业工作人员则会通过精细化的数据筛选和处理,形成供自身品牌使用的产品资料库,从而掌握用户的消费倾向和消费意愿,也即掌握消费市场。“好物分享”的个体行动者会出于社交、功利、互惠、利他、炫耀等目的而向他人推荐各类产品,在这种行为的逻辑生成中,个体的身份认同、组织承诺、社会资本构成其持续分享的重要心理机制[15],而这种心理机制促使了一人到共享这一理念和消费形态的自然生成。
四、 外部环境催生:“一人式”消费的蔓延
“一人式”消费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青年群体新的异质化消费心理、消费需求以及技术加持与“一人式”消费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当下的社会经济环境也息息相关。
(一) 城市社会发展与结构性变迁:“总体性社会”到“个体性社会”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总体性社会中(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的社会发展结构停滞僵化,各种社会资源由国家牢牢掌控,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被置于集体组织的机械团结之中。这种“集体化人格”的组织方式在发挥一定程度上的正效应后,其负效应逐步凸显。对个体而言,追求独立与自由的权利被囿于集体主义的框架中,无法得到真正释放。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促使我国城市迅速发展并发生结构性变迁,同时开启了我国从“总体性社会”到“个体性社会”的转变,为“一人式”经济的发展与蔓延提供了社会土壤。“一人式”经济依托于单身青年形成了新型资本产业链,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及都市的便利化设施为单身青年衣食住行等生活场景和日常消费提供了必需的公共设施和最基础的社会保障,因而也是单身青年尤其是“空巢青年”社会生活的基础条件。
特别是在聚集了全国大部分资金、技术、人才和生产要素的北上广等发达城市,其完备的公共服务设施能更好地满足青年群体的个性化消费体验,其产生的“虹吸效应”也吸引了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然而,都市的空间格局也被快速的城市化所挤压,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力量的推动及空间与时间的变化催生出大量“空巢青年”。“空巢青年”或“单身一族”的多样化需求使得“一人式”经济应运而生。因此,“一人式”经济可以说是城市社会发展与结构性变迁的产物。从“总体性社会”到“个体性社会”结构之变的背后折射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二元社会体制导致社会解构与重构交织进行的现实。信息技术的发展、时间的延展和空间的拓展虽然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但其差异的弥合还需要较长时间,众多“被动消极型”和“内在导向型”的单身青年在城市社会结构性变迁的现实背景下,不可避免地衍生出集体性焦虑、被剥夺感、群体心理失衡和孤独感等社会心理病症[16]。为摆脱现实的社会心理困境,青年群体往往会积极调整心态,关注自身终极价值的合理追求,并通过“一人式”消费实践彰显自由与个性。
(二) 家庭结构的嬗变:“自我文化”传统下“实践性亲属关系”的式微
时代的变迁不断冲击原有的传统家庭结构与伦理等级体系,传统的以家庭为目的的关系结构逐渐转化为以个体为目的的结构,个体化带来家庭规模核心化、夫妻关系平等化、家庭形成自主化及亲属关系疏远化的嬗变,并且在家庭结构流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内生的“自我主义”也不断重塑横向的性别权利结构和代际间的权利结构,实践性亲属逐渐式微。费孝通将中国人的“自我主义”与西方经典的“个人主义”区别开来,认为自我主义一切以“己”为中心,只看重自己的利益,它的形成与中国传统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差序格局密切相关。在个体化和自我主义的作用下,个体行走于“靠自己”与“靠家里”两间的弹性选择中,走出一条既反抗又依赖的弹性个体化之路,个体也需要根据实践不断重新界定亲属关系的距离,由此形成家庭个体化的弹性空间[2]。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个人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建构了个性化场域与社会机制,而家庭结构的变迁也对青年个体的消费心理产生深刻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个体深嵌并受缚于家庭和集体,以“集体利益为重”是传统家庭生活和集体生活所倡导的生活态度。在传统消费理念下,企业也主要关注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市场,其产品和服务主要倾向于消费能力较强的家庭消费单位。
但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个体不再紧紧依附于传统家庭组织。高度现代性的当下,个体的自主意识日渐觉醒,个体不断通过不同类型的消费文化实践来重新界定其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以往家庭群体奉行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准则演化为更加注重个体自由、能力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嬗变意味着实践性亲属关系式微,家庭所认可的“标准化人生”或“非选择性人生”逐渐瓦解。个体主动剥离于家庭等集体单位,通过个性化的消费探索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成长的生活空间,进而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艾里克·克里南伯格(Eric Weinberg)在其著作《单身社会》中指出,单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逐渐赶超核心家庭数量,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单身社会”。当下,单身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现象[17]。“一人式”消费实践可视为单身青年享受独立和自由的生存智慧和生存策略,“为自己而活”的个人价值理念在“一人式”消费中得到最大化的诠释与表达。
(三) 网络社会崛起与社交方式新变化:人际关系网络的互通互联
随着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个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个体已然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中抽离出来。传统“熟人社会”共同体结构的瓦解与隐退意味着个体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一个人的经济》中鲜明指出,高龄化、少子化、网络化三者相互联动,结合成一个巨大的“一个人的经济体”[18]。当下,Web2.0时代正向Web3.0时代快速转变,社交网络也由业余化、专业化走向一体化,社交网络的时空脱域性与制度抽离性使得线上缺场交往逐渐代替线下在场交往,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交往方式、交往选择、交往意识及交往功能的变化与发展速度加快。因此,互联网产业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网络社会的崛起和人际关系网络的互通互联。越来越多的青年个体依托网络化生存,由此带来虚拟社交方式的兴起和普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网络匿名性、缺场性的作用下不断重构与形塑,以“我”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由此形成。
在杨雄看来,“单”和“群”是单身经济需求的核心,个人消费能力的增强和高品质的商品需求构成“单”的表现形式,但他们又有情感陪伴的“群”的社交需求。正是这种既“单”又“群”的群体特征带动了“一人式”经济理念在消费、文化、投资等领域全面开花[19]。在新差序格局下,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连接和虚拟空间的建构吸引了大量青年尤其是单身青年涌入。部分主动选择“孤单式”生活方式的单身青年依托各类社交圈群进行衣食住行等消费内容的讨论与交流,参与创造“单身消费文化”,并积极调整心态,基于不同单身青年相互讨论与分享的结果,利用碎片化的社会时间进行网购、外卖等娱乐性和饮食性消费,充分享受“一人式”的新生活方式。抽离于现实空间的网络社交方式与匿名化的网络环境为网络消费提供了大量的消费人群和规模化的传播路径,最终也为“一人式”消费的发展和蔓延创造了大量的可能性[20]。因此,经济模式的变化既是社会多元发展的客观现象,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五、 结语
在个体化社会里,单身人口数量的逐渐增加及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衍生出“一人式”经济的新商业形态和模式。众多单身青年的“求新”体验、情感需求以及对获得身份认同的渴望直接构成“一人式”消费产生的内在动力,新媒体技术加速了“一人式”消费的传播与“重复式消费”,为商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消费价值。另外,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家庭结构的嬗变以及网络化社交的社会环境推动了“一人式”消费的蔓延。事实上,“一人式”经济虽已崛起,但仍处于初期阶段,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单身青年自身也面临超前消费、炫耀性消费等风险。因此,为了使单身青年获得更多的商业化服务,促进“一人式”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企业需要更加注重“单身经济”的开发,提升用户交易的规模和频率,并据此设计和推广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单身青年需自主规划、理性消费,警惕消费主义的滋生,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对于该问题,也有待后续的深入研究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