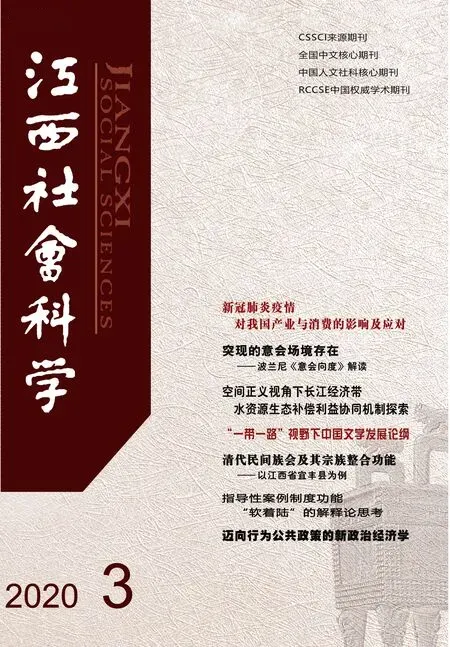“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
谢红星
在蒙古族法制传统的影响下,以及考虑到元代建立之初的特殊政治形势,元廷废弃了律令法典,同时编集条格和断例,将宋代以来各种法律形式按其内容整合为刑事和非刑事两大类,整体表现为“弃律用格例”的倾向。随着律令法典被废弃,判例在元代的地位和作用达到顶峰,元代法律出现了强烈的“例化”的特点,这既是蒙古民族法制传统的延续,也是唐代后期以来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整体发展趋势之结果。明清王朝恢复了法典传统,但其法律体系不再是“律令法律体系”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典为纲、例为目,成文法与判例相混合、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典例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的形成及特点,与元代“弃律用格例”之下法律体系的变迁及特点有着密切联系。由此,元代成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律史上据有承前启后的承接和中转地位,再次佐证了中华法律文化之整体性和连续性。
关于元代法律体系变迁与特点,一直以来,孟森、蒙思明等前辈学者将其概括为“惟以判例惯例为典制,无系统精密之律文”,进而得出“政治简陋,法令粗疏”,“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元无制度”的评价。[1](P14)[2](P36)然而,法史学界并不满足于这一概括与评价,而是深入探讨元代“弃律用格例”法律现象之内在机理,并得出“蒙古本位”说、“家产制国家”说、“草原法文化”说、“族群复杂”说、“儒吏矛盾”说、“判例法上升趋势”说等观点。①总体而言,大部分学者将元代“弃律用格例”现象归之于蒙汉二元划分、蒙古本位的政治观念及体制、蒙古习惯法的强大影响等外在因素,一部分学者则从中国传统法制自身的“内在理路”出发,认为元代法律体系“弃律用格例”更多是唐中后期以来律典地位相对下降,格、敕等单行法以及断例地位持续上升趋势之必然结果。
客观地说,元代“弃律用格例”现象之形成,外在因素的影响和传统法制的内在历史惯性二者皆有之,也很难确定哪一方面的因素占主导。但法史学界长期以来更为关注外在因素影响,对传统法制内在惯性于元代法律体系的影响着墨不多。然而,阐明元代法制与秦汉以降中国传统法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实为证成元代法制为五千年中国法制之有机且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华法系整体性、一贯性之关键,宫崎市定、胡兴东等学者对元代法律体系与唐宋法制变迁之间的联系有一定阐述,但对元代“弃律用格例”于明清法制之影响,则未做进一步探讨。近数年来,杨一凡、陈灵海相继提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一说,认为明清法律体系是以典为纲、以例为目的“典例法律体系”②,本文基本赞同杨、陈二先生观点,并进一步从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整体变迁之视角,探讨元代“弃律用格例”之由来、在中国法律史上之地位,以及对明清“典例法律体系”生成之影响。
一、废而后立:“弃律用格例”及元代法律体系之再造
自春秋战国以降,古代中国法律体系便表现为一种成文法的体系,律和令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要构成。秦汉时期,律令以单行法的形态存在,繁多而芜杂。魏晋之际,法典化运动兴起,结出以唐律、唐令为代表的律令法典,生成强大的律令法典传统,这一传统自唐中期后虽不断遭遇格后敕、编敕等单行法地位上升与断例作用扩大之挑战,但仍顽强维续并存在于宋代。
(一)“弃律用格例”的发生
到了元代,律和令为主要构成的“律令法律体系”基本解体。以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废止金《泰和律》为标志③,元廷中断了借用汉化的金代法律创制本朝法律体系及法典之进程,废弃了律令法典传统。之后,虽有朝臣试图在承认南北异制的基础上,寻求制定融合蒙俗汉制于一体的律令法典的折中方案,但“中朝大官恳恳开陈,而未足以回天听。圣意盖欲因时制宜,自我作古也”[3](P83)。被废弃的律令法典传统在元代始终没有恢复,元代法律体系及法律形式,整体表现出一种轻视法典、强化格例的倾向,即“弃律用格例”。
重视条格和断例,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废弃律令法典。元朝之前的宋朝,编敕和断例的作用大幅强化,却并未根本动摇律令法典的地位;元朝之后明清王朝虽然以例作为法律体系的主要构成,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例的作用,却重新制定了律典、令典乃至会典等法典。无论自逻辑还是历史事实而言,“用格例”并不以“弃律”为必要前提。因此,元代废弃律令法典传统,在中国法律史上就显得尤为特异,并不能仅从唐中期以来律令法典地位相对下降,格、敕、例日益受重视的趋势中寻求解释,而必然存在其他更为特殊的因素。
从表面看,废弃律令法典传统,与元代建立之初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有密切关系。蒙古政权入主中原之初,基于治理中原汉地之需要,曾有一段时期继续采用以《泰和律》为核心的金代法律体系,以其为创制新法的重要参照和中原汉地司法审判的法律依据。但是,忽必烈作为不懂汉语、不识汉字,虽对中原文化有一定了解掌握却并不服膺的征服型统治者,对被他和蒙古铁骑征服的金朝及其法制文化,内心深处很难说不存在强烈的轻蔑和警惕之意,此其一。其二,李璮叛元降宋严重影响忽必烈对汉族臣僚的信任。中统三年(1262)二月,驻扎山东的李璮叛元降宋,并牵连到他的岳父、忽必烈非常信任的平章政事王文统,由此严重影响了忽必烈对汉族臣僚的信任,自此,忽必烈大力削夺汉人世侯的权力,有意疏远汉族朝臣和地方官吏,汉臣的失势使元廷中推行汉法的力量大为减弱,反之维护《大札撒》等蒙古旧法的力量却在增强。其三,海都等叛乱诸王对忽必烈有限“遵用汉法”方略的责难,加大了行用汉法的阻力。面对公开的叛乱和潜在的抵制,忽必烈不能不认识到继续推行汉法的阻力和不利,认识到以《大札撒》为核心的蒙古旧制旧俗对于凝聚蒙古贵族人心、维护大汗权威和黄金家族内部统一的重要价值,他不可能全面行用律令法典传统的中原汉法来削弱蒙古旧制,只可能为了维护蒙古旧制而废弃中原王朝向来的律令法典传统。
从深层次讲,以《大札撒》为最高权威的蒙古族法制传统对元代废弃律令法典传统,起到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大札撒》是由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期间和大蒙古国建立初期颁布的一系列命令、向臣民发布的训示以及部分蒙古族习惯构成的纲领性法律文件。对黄金家族来说,《大札撒》是必须共同遵守的最高准则,是大蒙古国内普遍通行、具有最高权威的行为规范。元朝虽然是忽必烈仿效中原传统王朝结构建立起来的政权,但从根本上仍是蒙古帝国的延续,统治基础还是蒙古贵族。忽必烈绝不可能全盘否定和抛弃蒙古国的制度,相反,他保留了大量的蒙古旧制,尤其是,为了彰显自己取代阿里不哥的正当性,他必然也必须表现出对《大札撒》的遵循与认同。而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大札撒》都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其既不具备法典严谨之结构与精炼之语言,内容也多为成吉思汗针对具体事件、案件发布的命令、训示和蒙古族的习惯,是在生活习惯基础上形成的习惯法和从具体判决中总结、引申出来的司法成例的汇编,较为原始和粗疏,缺乏抽象性和概括性,并且表现出强调遵循先例以及从案例中总结规则的“例化”的特征,这一特征及传统深刻影响了元代建立后的立法。《泰和律》被禁用后,元廷并没有像历代王朝一样制定出一部自己的律典,仅仅是颁行了一些单行的条格和法令,至元二十八年的《至元新格》“宏纲大法,不数千言”[4](P85),表现出简短粗疏的风格。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朝廷委任何荣祖更定律令,辑成《大德律令》,但因为过多援引中原汉地的法律条文和内容,“与《泰和律》相差无几”[5](P244),违背了《大札撒》的风格与传统,《大德律令》没有通过,未能颁行。英宗朝的《大元通制》和顺帝朝的《至正条格》的内容都是对单个制诏、条格、断例的整理和汇编,其以条格和断例为主体,不具备以律令法典为范式的中原法典的特点。虽然,对条格和断例进行汇编可能也借鉴了宋代编敕和编集断例的做法,但更多是立足于蒙古族自身的法制传统,遵循了《大札撒》的立法方式和风格,即,针对特定场合、特定情况、特定罪行而个别立法,“给每一个场合制一条法令,给每个情况制定一条律文;而对每种罪行,他也制定一条刑罚”[6](P28)。由此反映出《大札撒》在蒙古族法制传统中一以贯之的至高权威,以及对元代废弃中原王朝律令法典传统的决定性影响。
(二)“弃律用格例”后元代法律体系的再造
废弃中原王朝的律令法典传统,拖延施行中原汉法的进程,使得元代立法整体上滞后于适用的需求。蒙古统治者以军事征服者之姿态,希望扩展以《大札撒》为核心的蒙古本族法制在中原地区的适用,但与其意愿相悖的是,中原汉地发生的各式复杂的司法案件很难适用简易宽疏的蒙古旧法。在前朝法典被明令禁止适用、蒙古旧法不可全用,又没有本朝其他成文立法可资引用的情况下,各级司法部门便陷入了无法可依的困境。为解决这一困境,中书省以皇帝的名义不断发布圣旨条画,为司法实践提供临时性法律依据,同时各级司法官吏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章程。
圣旨条画和判例的大量及无序涌现,必然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妨碍国家统一法律秩序之形成:“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并缘为欺。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条多至数十。间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比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7](P82)元廷虽然决定废弃中原王朝的律令法典传统,不想以制定律令法典的方式解决法律适用混乱不一的问题,但还是在实践中存在各种诏令、条画、判例的基础上,通过辑录、增删、修改、创制,将其汇编成综合性法律文件,努力形成较为统一的法律适用规则,《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即是这种努力的代表性成果。
《大元通制》颁布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共2539条,具体包括制诏94条、条格1151条、断例717条、令类577条,“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敕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8](卷二八《英宗纪二》,P629)。现存《通制条格》系其中条格部分的残本,仅653条。条格部分的篇目,据元人沈仲纬《刑统赋疏》,包括《祭祀》《户令》《学令》《选举》《宫卫》《军房(防)》《仪制》《衣服》《公式》《禄令》《仓库》《厩牧》《关市》《捕亡》《赏令》《医药》《田令》《赋役》《假宁》《狱官》《杂令》《僧道》《营缮》《河防》《服制》《站赤》《榷货》27篇,残本《通制条格》存《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杂令》《僧道》《营缮》19篇。[9]可见,条格部分的篇目采用的是唐宋时期令的篇目结构,且与金《泰和律》篇目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足以表明《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性质上属于非刑事方面的法规。关于断例部分的篇目,沈仲纬《刑统赋疏》的记载是:“名令提出狱官入条格,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足以表明《大元通制》断例部分属于刑事方面的法规。
《至正条格》颁行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四月,共2909条,其中制诏150条、条格1700条、断例1059条,“书成,为制诏百有五十,条格千有七百,断例千有五十有九。至正五年冬十一月有四日,右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里怯不花、平章政事铁穆尔达识、巩卜班、纳麟、伯颜、右丞相搠思监、参知政事朵儿职班等入奏,请赐其名曰《至正条格》”[3](P87)。在体例上,《至正条格》不再包含“令类”,仅有制诏、条格、断例三纲。其条格部分,据《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四《史部四十·政书类存目二·至正条格》,共有27篇,分别是《祭祀》《户令》《学令》《选举》《宫卫》《军防》《仪制》《衣服》《公式》《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狱官》《杂令》《僧道》《营缮》《河防》《服制》《站赤》《榷货》,韩国发现的《至正条格》残本条格部分见《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狱官》10篇,缺17篇,篇目名与《大元通制·条格》诸篇高度相似。从内容上看,《仓库》篇是仓库管理、运输、钞法方面的规定,《厩牧》篇是关于驼马草料供应的规定,《田令》篇是农村、农业生产和土地管理方面的规定,《赋役》篇是征收税粮、豁免、摊派杂役及免除方面的规定,《关市》篇是关于和雇和买、市舶的规定,《捕亡》篇是关于追捕盗贼和逃人方面的规定,《赏令》篇是赏赐方面的规定,《医药》篇是医药和医疗机构管理方面的规定,《假宁》篇是因事给假及期限方面的规定,《狱官》篇是审判制度和监狱管理方面的规定,都是非刑事方面的规定。断例部分,从韩国《至正条格》残本看,《至正条格·断例》有11篇,包括了《名例》之外的所有11个篇目,与《大元通制·断例》一样,均属于刑事方面的规定。
总之,虽然元代“选择了省事的办法,直至灭亡,既没有编纂律令格式,也没有编纂敕令格式”[10](P94),但元廷在尽可能保留法律文献原貌的前提下,力求删繁就简,将宋代以来各种法律形式按其内容整合为刑事和非刑事两大类:凡内容以刑事为主的规定,不管是律敕格式申明还是断例,都纳入“断例”之中;凡内容以非刑事为主的规定,不管是令格式还是敕例,都纳入“条格”之中。从而把唐后期至宋金分类越来越繁杂的法律形式,以及元初以来中央和地方产生的各种圣旨条画、判例简化为两大类,努力使国家立法更易于分类,适用起来更加方便。这种将国家法律重新体系化的尝试和努力,虽然在元代没能也不可能形成以严格的法典为核心,各种法律形式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严谨规范的法律体系,却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元代法律体系之“例化”
“例”在古代中国使用较广,含义不一。考之原义,例在古代中国原指判例或先例,此乃例本源之义,后来其含义逐渐拓展,被用来指法律原则或规定。本文主要从例本源之义即判例④、先例来使用例、“例化”等术语。
(一)元代之前的判例
春秋战国以降,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成文法的传统,但重视经验、援引先例的做法发自于先民敬天法祖的观念深处,并在成文法产生后继续深刻影响帝制中国的法律生活。敬天法祖的观念下,先民认为已经发生的事实具有可供借鉴的功能,祖辈的行事方式和成功做法不仅必须纪念,也值得模仿,由此,他们把以往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论的证明,重视寻求和援引历史上正面的事例,作为今后行事之指引,换言之,经验胜于逻辑,事实胜于雄辩。判例是西周礼、刑的主要存在形态,西周礼是源于习俗和惯例的习惯法,是习俗和成文法之间的一种法律形态,西周刑书很可能是以刑罚为目,将相应的判例附于其后,通过“以刑统例”,部分实现“以刑统罪”的不成文刑法。
战国以降,成文法上升为主要的法律形态,但判例并未消失,相反,由于早期成文法存在的过于具体、狭窄的缺点,判例在秦汉法律体系中继续滋生和成长。秦代有廷行事,是从具体案件中归纳和提炼出来的断案成例,汉代有决事比,同样是司法裁量权行使而产生的断案成例。魏晋之际,法典化运动兴起,律典、令典的产生使成文法体系的发展超越了秦汉以来因循的轨道,完成了成文法产生以来的关键转折,对法典的推崇必然趋向于限制判例的产生与作用,因而在魏晋隋唐,判例没有太多正常生长的土壤和存在空间。
唐中期之后,随着停止修纂律令法典,不但格后敕成为主要的法律形式,对判例的运用也开始增加,如《开成格》规定大理寺和刑部可以“比附”断案,而且“比附”断案“堪为典则”者,可以“编为常式”[11](P551),明确赋予了中央司法机关比附成例断案和编撰判例的权力。至宋代,一直以来的法典化运动发生重要转向,法律体系中的非法典化成分大为强化,其表现之一就是作为司法判例之断例被大量编纂,其法律效力得到了成文法的认可和司法实践的支持,朝廷明确指出:“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12](卷一九九《刑法一》,P4964)在法典化运动兴起后沦为成文法体系之边缘化异己物、不被正式认可长达上千年后,判例终于获得认可,通过编修断例集的方式,被接纳为正式的法律渊源。
(二)判例与元代法律体系
元代,随着律令法典被废弃,判例的地位和作用达到顶峰,出现了“审囚决狱官每临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7](P83)的现象,而这种援例断案的做法也得到了元廷的认可:“后至元元年,准江西省咨,但该有罪名,钦依施行。圣旨:依例,泊都省明文检拟,外有该载不尽罪名,不知凭何例定罪,都省议得:遇罪名,先送法司检拟,有无情法相应,更为酌古准今,量情为罪。”[13](P199)在朝廷的许可下,各种判例飞速生长,加之成文立法的滞后,出现了“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局面。判例成为元代法律的重要存在形态,元代的许多法律是通过判例构建起来的,判例起着补充和证成成文法的作用,甚至很多时候就是在创制规则。在元廷编修的法规《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中,各种法律形式被归纳为非刑事类的条格和刑事类的断例两大类,而无论条格还是断例之中,判例都是重要存在形态。
第一,条格中的判例。条格虽是非刑事方面的立法,但很多条格中的规定乃是从判例中总结和引申出来的,此外,判例本身又对条格中的一般性规定进行修改和补充。以《通制条格·户令》为例,其下首先列《户例》一目,是为户籍、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制度方面的一般性规定,之后“投下收户”等49目中,罗列了大量的圣旨条画和判例,如“嫁娶”目之下,就列举了马元亨告刘友直案、大德七年十一月吉文烈告孙邦练案、至元十六年五月樊裕告刘驴儿案、至元十一年六月樊德告王招抚案、庚子年十二月十八日王荣案、至元二十一年七月李秀告令狐坤案、至元八年三月张德用一案、大德七年正月陈天佑案、大德七年四月王钦案等案例,对《户例》中一般性规定进行补充和修改。“亲属分财”目下至元三十一年阿张案和至元十八年王兴祖案,则是以判例直接确立了不同子女继承权以及可以继承财产范围的规则。[9](P48-56)此外,据胡兴东考证,《通制条格》现存653条中,以案例(判例)形式表达的有114条,占总数的17.45%。[14](P85)从现存残本来看,《至正条格》同样如此,其条格部分包含了大量的判例,补充、修改乃至直接创制一般性规定,如:大德六年,陕西省安西路惠从案通过否定前朝地产所有权,确立了解决“异代地土”纠纷的法律规则。元贞元年(1295),安西路普净寺僧人侁吉祥告西邻王文用将门面并后院地基卖给宫伯威不问该寺院一案,礼部通过“僧道寺观田地,既僧俗不相干,百姓虽与寺观相邻住坐,凡遇典卖,难议为邻。合准王文用已经卖西邻宫伯威为主”的判决,否定了寺院与相邻百姓法律上相邻关系的存在及两者相互间的优先购买邻人资格,构成对不动产买卖邻人优先购买权的一般规定的补充。至元十年二月,御史台在魏阿张一案中,以“魏阿张孝奉老姑,守节不嫁”为由,奏请对魏阿张不仅“官为养济”,而且“免除差役,更加旌表”,获得都省的批准,从而拓展了“孤老幼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仰本路官司验实,官为养济”的圣旨规定。至治二年,刑部在象州知州周德贤一案中,以周德贤“持权弄法,挟私任情,民有小过,辄生罗织,锻炼成狱,擅立红壁,以仇其民”为由,确立规则,对立红泥粉壁惩戒犯人的职权行为进行规范,“今后果有例应红泥粉壁之人,开具本犯罪名,在外路分申禀行省,腹里去处申达省部,可否须侯许准明文,然后置立,仍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纠察”。[15](P63、P67、P86)
第二,断例中的判例。在元代,断例本身并非指判例,而是指刑事方面的立法规定,正如殷啸虎所言,元代断例是“将那些‘断一事而为一例’的典型判例及中央官署对此发布的有关命令分类汇编以后,上升为对同类案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通则性的规定”,但也正因为如此,元代断例立法中包含了大量的判例,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一种有机的结合”。[16](P63-69)更准确地说,判例是元代断例的基础,断例中的一般性规则、通则性规定是从判例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大元通制》断例部分已经佚失,但根据它与《至正条格》的关系,可以推定其中包含许多判例。《至正条格》残本和《元典章·刑部》中保留了许多断例,据胡兴东考证,《至正条格》残本断例部分以案例形式表达的法律共有232条,占所存423条的54.85%;《元典章·前集·刑部》共752条,其中,以案例为载体的有516条,占总数的68.62%;《元典章·新集·刑部》共95条,其中,以案例为载体的有59条,占总数的62.10%。[14](P87)判例构成元代断例的主体部分。或创制规则,作为之后同类案件判决的直接依据,如大德三年三月,保定水军万户审理其下属百户刘顺奸占民户何大妻子案时,在是否除去刘顺为官资格上,直接适用了至元二十三年四月神州路叙浦县丞赵璋与苌用妻子陈迎霜通奸案,进而判决“百户刘顺所犯,若依赵璋例除名不叙相应”[17](P1540)。又如延祐五年(1318)十月初六,宁国路宣城县捉获武多儿偷盗陈荣祖桎木板舡案,在处罚上直接适用了先例钱庆三偷铁猫案,判决“比依钱庆三偷铁猫例,将本贼刺字拘役相应”[17](P2170)。或作为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说理依据,强化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遵循先例的典型特征是既有案件的判决会成为后来案件的判决依据”[18](P29),如延祐七年六月,地方司法机关在审判信州路余云六与徐仁三、陈嫩用武力抢夺客人王寿甫财物案时,适用了窃盗罪条款,判令刺配,“比依窃盗一体刺配”,但呈报刑部时,刑部援引先例“杨贵七”案,认为余云六等人的行为属于“同谋白昼持仗截路,虚指巡问私盐为由,将事主王寿甫用棒打伤,推入水坑,夺讫钱物”,应以强盗而非窃盗定罪,最后决定对已经判决的刺断不再改判,但加重发配到奴儿干地区充军。[17](P2183)
总之,元代通过立法将法律形式归纳为条格和断例两大类,严格来说,条格和断例中既有判例,也有成文法,但判例是基础,是主要的存在形态,是各种法律形式的主要载体。换言之,在废弃律令法典传统的同时,元代法律出现了强烈的“例化”的特点,元廷虽努力将各种法律形式重新体系化,却未改变其法律“例化”的特点。
(三)元代法律体系“例化”的法律史观照
一方面,元代法律“例化”是蒙古民族法制传统的延续。以《大札撒》为核心的蒙古法制,具有强烈的非成文化的特点。《大札撒》的内容多为蒙古旧俗和成吉思汗对一些案件的判决和训示,是在生活习惯中形成的习惯法和从具体判决中总结、引申出来的判例的汇编,较为原始和粗疏,表现出强调遵循先例以及从判例中总结规则的特征。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在思维习惯和法律适用方面,仍遵循蒙古法制传统,以《大札撒》为最权威的法律,以遵循先例为适用法律规则、修正法律规则甚至创制法律规则之基础。
另一方面,元代法律“例化”也是唐代后期以来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整体发展趋势之结果。自唐后期始,成文法典的地位和实际作用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格后敕、编敕等单行法和判例的地位上升,尤其到了宋代,作为判例的断例大量编纂,南宋和金代大量吏员出身的官员更为重视司法实务中形成的先例,客观上又增加了对成文法典的轻视,并在元代时到达巅峰。元廷不再像以往中原王朝一样费时费力制定律令法典,而是编集条格断例结合的汇编式法规,同时,条格、断例中又包含了大量的判例,并以判例为适用、修正、创制法律规则的基础。日本学者认为:“元代未曾颁布律令,这绝非因为元是异族统治的王朝,相反,它正是中国自身在经历了唐至宋的社会大变迁后,已无暇顾及像中世一样立法的后果。对此表现得最充分的,就是宋以后所见的法律权威的动摇。”[10](P94)这种动摇,反映的是唐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相对稳定的成文法典暴露出不适应社会快速变迁之需要,成文法典的实用性下降,国家对法典的需求和热情大为减弱,“试阅二十年间之例,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较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7](P82)。蒙古民族的固有法制传统和唐后期以来古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趋势结合在一起,导致元代呈现出强烈的“例化”特点及倾向。
元代法律的“例化”特点及倾向,对明清法律体系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两代恢复了被元代中断的法典传统,重新制定了律典甚至令典,同时又继承了宋元立法重视判例的做法,形成以条例、则例、事例为主的例的体系,构成对成文法典的重要补充和修正。“例”正式成为明清法律体系的主要构成,与元代法律的“例化”特点不无关系。
三、“弃律用格例”对明清法律体系的影响
明清两代恢复了被元代中断的成文法典传统,但是,明清的法律体系与唐宋时期相比,已大为不同。唐宋法律体系中的法典,是律典和令典,明清法律体系中的成文法典,包括会典、律典和令典,会典乃“大经大法”,载“经久常行之制”,律典与条例合编,名为“律例”,实际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令典则有名无实,逐渐消失。唐宋法律体系中判例的适用一开始受到严格限制,在宋代虽获朝廷正式认可,被接纳为正式法源,但宋廷尚未摸索出行之有效地处理例与其他法律形式相互关系的办法,未能建立起系统的例的体系,以例为构造元素的法律术语多而复杂,有条例、则例、断例、旧例、近例、定例、常例、优例、乡原体例等,明清法律体系则不仅以例为法律体系之主要构成,而且努力将元代各种例整合,最终形成了条例、则例、事例三者有机配合、互为补充的体系。换言之,明清法律体系已不再是律令法典传统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典为纲、例为目,成文法与判例相混合、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典例法律体系”,这一“典例法律体系”的形成及特点,与元代“弃律用格例”之下法律体系的变迁及特点有着密切联系。
(一)律典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
元代废弃律令法典传统,“正刑定罪”的刑事法律规范主要规定在“断例”之中,较多体现为判例的形态。明王朝建立后,在光复汉唐法律正统的思想指导下,恢复了被元朝中断的法典传统,制定了《大明律》。但《大明律》在明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已不能与唐宋鼎盛时期的律典相比,这是因为:第一,在明代大量的“常经之法”中,《大明律》仅仅是其中一种。明代初期的“常经之法”包括《大明律》《大明令》《诸司职掌》《大明集礼》《宪纲》《皇明祖训》《御制大诰》《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军法定律》《教民榜文》等,其中《诸司职掌》规定各衙门职掌,《军法定律》是军事方面的法律,《宪纲》规定监察制度,《皇明祖训》更是皇室家法,《大明律》对它们不可能居于统率地位,而至多是同等位阶的法律。第二,朱元璋基于“明刑弼教”的立法观念,重视律典的传播和遵守,将《大明律》从12篇体例改为6部体例,语言风格一变为文字浅显,通俗易懂,力图打破“法在有司,民不周知”的局面。因此,与唐律相比,《大明律》更易于传播、更便于遵守、更加实用,但从法理的角度看,《大明律》体系结构的逻辑性稍逊,文字凝练典雅稍逊,立法技术也逊色于唐律,“明律虽因于唐,而删改过多,意欲求胜于唐律而不知其相去远甚也”[19]。例言对“实用”的过分强调使《大明律》“泯然众人”,不再像唐律一般具备统率其他法律的风范、气质和水准,而是下降为与《大明令》《诸司职掌》《宪纲》《皇明祖训》《御制大诰》《军法定律》一般无二的法律。
《大明律》在明代法律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不能不说与元代对律典的废弃有密切联系。在律典被弃用近百年之久后,成长及生活在元代条格、断例约束之下的明初君臣,其法律记忆与习惯,更多是对“弃律用格例”的因循,即使在恢复汉唐正统之政治意识的主导下重新制定律典,其律典体例、内容,也较多受到了《至正条格》等元代法律的影响。《大明律》第一次制定即吴元年律令,“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20](卷九三《刑法一》,P2280),令在前而律在后,这与《至正条格》“令”性质的条格在前、“律”性质的断例在后体例相同。此外,“吴元年律”仅“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6篇而无“名例”,“洪武七年律”虽恢复唐律12篇体例却置“名例”于末尾,直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才改“名例”为篇首,显然与《至正条格·断例》“名令(例)提出”有相当关联。另外,有学者以有关婚姻的条文为例,指出《大明律》各篇条目与《至正条格》篇目更为接近。[21](P38)
《大清律》沿用《大明律》的6部体例,语言风格一如《大明律》,决定了它仍不能承担起统领整个法律体系的重任。与此同时,条例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虽说律还起着提纲挈领的功能,但具体案件审理中征引得越来越多的是例。此外,就位阶关系而论,《大清律》和各部院则例处在同等的位阶上,两者是平等位阶下相互分工和配合的关系,《大清律》不存在凌驾于各部院则例之上的法律效力和位阶。尤其是,在《大清律》之外,清代通过《吏部处分则例》已经形成一套独立于律例所规定刑罚的行政处分体系,《大清律》已不再是规定法律制裁的唯一法典,如果违反则例但后果尚不严重,则适用《吏部处分则例》进行行政处分,无须一断于《大清律》。可见各部院则例内部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从行为模式到行政处分的闭环体系,其实施和运转不一定非得要借助《大清律》,自然,《大清律》也不具备凌驾于各部院则例之上的位阶,不存在统领各部院则例的可能,只是作为一部“正刑定罪”的普通刑事法典而存在,它仍然是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法典,在“明刑弼教”的理念下,仍然因为其“正刑定罪”内容的重要性而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但并不是清代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基本法”或“基础规范”。这既是唐后期以来律典地位持续下降趋势之延续,更可以说是元代“弃律用格例”之余波所致。
(二)令典逐渐消失
令作为法典而编纂始于晋代,至唐代,令典几经修订,蔚为大观,与律典共同构成法律体系的支撑。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后,随着敕、令、格、式被重新定义⑤,令的数量急剧扩张,令典篇幅增加,盛极一时。随着宋王朝的覆亡,盛极一时的令典迎来命运的转折。元代废弃了律令法典传统,不制定律典,也未制定令典,自晋代以来一直作为国家基本法典的令典戛然而止。当然,元代法律体系中条格部分的内容和功能大致与传统令典相当,“名废而实不废”,但以条格为载体的元令与唐宋令实际上存在较大差别,其既不以法典形式出现,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例化”特点。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出于光复汉唐法律正统的想法,重新制定了《大明令》,但篇数、条数远远少于唐宋令典。虽然,朱元璋在颁布《大明令》的圣旨中声称令文减省的原因是“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22](P231),但是,一部删减到不足原来1/10、只有区区100多条的法典,如何还能像原来那样“设范立制”?何况《大明令》中纳入了刑法通则性内容,虽然这主要是因为制定令典时律典尚不完备之故,但不可避免淆乱了令典的体例和内容。《大明令》虽具备令典之外表,其体例、内容及在国家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却不能与唐宋令典相比。当然,《大明令》之外,《诸司职掌》等典章实际上也起到了令的作用,发挥了令“设范立制”的功能,在《大明令》《诸司职掌》之外,明王朝仍保留了以诏令形式发布国家重大事项的传统,历朝君主发布的诏令如诏、制、诰、敕、册、手诏、榜文、令中,许多可视为单行令,但大量单行令的存在,反而凸显出《大明令》作为令典的名不符实。退一步说,明代即使有令,亦非以严格意义的法典形态存在,《大明令》作为令典名不符实。明初君臣虽制定所谓令典,其真正所习惯及因循的,仍是元代随事而立、随时编集的条格而已。到了清代,令之名从法律体系中消失,则例和行政类事例承担起令“设范立制”的实质功能,如果说实质意义的令仍然存在,作为法典的令典则于名于实俱不复存在。清代之令不仅不以法典形式出现,而且如同元令一般,再度表现出强烈的“例化”特点。总之,在元代“弃律用格例”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令再也没有恢复为严格的法典形态。
(三)例被整合与规范
元代法律体系呈现出“例化”的特征,各种例野蛮生长,漫无限制,不可避免对法律秩序的稳定性造成严重破坏。明代建立后,一方面继承元代的做法,承认例为法律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重视例的制定,将例广泛应用于刑事、国家行政、民事、经济、军政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开始,明廷开始制定《问刑条例》,将经久可行的刑事例进行辑录整理,整合为具有长久效力的“常法”,改变了刑事例只以权宜之法存在的状态,实现了对例的初步整理与规范。
清代建立后,把明代各种纷繁复杂的例进一步简化为条例、事例、则例三种主要类型,并明确其性质、用途和生成程序。清代条例主要指《大清律》所附刑事例,乾隆十一年(1746)定为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实现了修例的经常化、定期化和规范化。清代则例调整范围进一步扩张,已不限于经济立法,而成为非刑事例的主体,清王朝充分运用则例这一法律形式,建立起空前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清代事例内容基本是非刑事方面,很少涉及定罪量刑的刑事内容,与同属非刑事方面的则例相比,事例更为具体,而抽象性和概括性不如则例。例的制定也实现了规范化。清代条例除了一部分是承袭明代条例而来,其生成途径包括:根据皇帝的谕旨或大臣的建言直接创制;从典型案件的判决中归纳出一般规则定为例,具体又包括皇帝在审批案件时直接以上谕创制条例、督抚题奏案件时附请定例、九卿议准定例、群臣遵旨会议定例、理藩院议复定例、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定例等。则例的生成途径也是两种:一是以上谕创制;二是臣工条奏,经皇帝批准后产生。事例在清代有经过由下而上方式形成的,如“奏准”“议准”“覆准”“题准”等,有自上而下产生者,如诏、敕,谕、旨、令等,但无论以何种方式,事例的产生都有明显的“因事立法”、一事一例的特点,都是在出现问题之后,针对具体情况提出解决对策,经有关部门讨论,最后仍须皇帝批准,形成事例。
从条例、则例、事例的生成途径来看,明清例的形成与判例、先例关系极为密切。事例本身就是因事立法,一事一议。则例的规定较为简约和抽象,但许多则例的规定本身就是从事例发展而来,是对多个事例规定的概括和抽象。条例的生成包括“因案生例”和“因言生例”。“因案生例”之“案”指成案,是典型案例,虽然,成案作为典型案例,在乾隆三年之后不再具有必然的法律效力,但毫无疑问,成案是条例的重要来源。“因言生例”表面上似乎是皇帝的谕旨或大臣的建言成了条例的来源,实际上不排除皇帝的谕旨或大臣的建言也是基于处理具体案例的需要而发,实质上仍是“因案生例”。要言之,明清条例、则例、事例广义上讲都是因判例而生成,与判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显然是对“弃律用格例”的元代法律体系“例化”特点的继承。但是,与元代直接以典型案件作为判决依据从而形成断例不同,清代更多是对典型案件进行一定的概括和抽象,将其升华为具有某种一般性的条例和则例,因此其法律体系更为稳定、一致和简约,更多具备成文法体系的特点。
总之,明清王朝重新制定了律典,但律典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已不能和唐宋鼎盛时期律典相比,而是较多受到了元代法律体系中“断例”的影响;表面上重新制定了令典,却令典外有令,名不符实,终于在清代令典则于名于实俱不复存在,各式各样的则例作为实质意义上单行令的汇编,与元代条格名异实同;以例作为法律体系之主要构成,某种意义是元代法律体系“例化”特点之延续,同时,又吸取了元代法律体系中例野蛮成长漫无限制进而破坏法律秩序稳定性的教训,对各式各样的例进行整合与规范,逐渐形成以条例、则例、事例为主的例的体系,延续并升华了元代法律体系“例化”的特点。由此而论,元代确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
四、结语
传统中国的法律体系,向来被日本学者认为是一种“律令法体系”,但是,正如将“律令法体系”概念引入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张建国自己所指出,虽然“唐以后的各代法,也可以视为律令法体系嬗变之一阶段”,但“此后律令法系嬗变的结果,与早期中华帝国律的地位已有所不同,而令更是逐渐消失了,但这种变化正是新的研究起点”。[23](P99)唐宋之后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整体上已与此前颇为不同,刘笃才将其称为“律例法律体系”[24](P178-187),杨一凡、陈灵海进一步称其为“典例法律体系”。从“律令法体系”到“典例法律体系”,元朝正是一个关键的转变期。元统治者凭借塞外游牧民族之强大武力,摆脱中原王朝“律—令”法律构成之千年定式,果断废弃了在宋代就已经摇摇欲坠、难以为继的“律令法体系”,初步发展起以条格和断例为主体、带有强烈“例化”特点的法律体系,为明清成文法典传统与成文法体系的再造提供了丰富多样和更加直观的参考素材。
虽然,正如忽必烈建立元朝时从未想过自己的王朝不足百年即被汉族王朝所取代,元代统治者废弃法典传统和“律令法体系”的目的更不是为了将来的恢复和再造,但是,历史的发展难免偶然性与戏剧性。宋代朝廷通过对令、格、式关系的重新调整,竭力维持“律令法体系”的基本格局,却无法解决编敕、断例、申明、看详、指挥等单行法和判例大量增加及冲击律令法典实施的问题,整个法律体系变得极为庞杂,检索困难,适用不一,“律令法体系”名实不符、难以为继。元代朝廷放弃“律令法体系”,自己虽尚未能成功另起炉灶,却为明清法典传统和成文法体系的再造另辟蹊径:其条格、断例之编纂风格,多为明清重新制定律令法典所继承;其“例化”之特点,亦在明清条例、则例、事例的生成过程中得以延续。基于此,元代可谓明清“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律史上据有承前启后的承接和中转地位。
本文之目的,不仅在于阐述元代和元代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及特殊地位,也在于借此佐证中华法律文化之整体性和不间断连续性,进而启发学界重新审视和珍惜华夏先贤寻求“良法善治”的过程、努力与经验。虽然,儒家坚称“有治人,无治法”,但事实上,关于法律体系如何才能变得更加严谨、科学、实用,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华夏先贤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思考、探索与努力尝试。从“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到“条章备举,何为更须作例”,再到“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华夏先贤在经验理性与逻辑理性、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法条繁多与简要、法律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不断做出选择和进行调适,其探索大国“良法善治”的历史轨迹,给今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源和想象空间。
注释:
①仁井田陞、岩村忍认为元代未能颁布律典的原因在于族群之间差别过大,矛盾重重,故在统治上实行分治主义(《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59年版,第525-537页);姚大力认为元代拒绝颁行律典的原因是蒙古本位下对汉民族和中原法律文化的防范(《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129页);宫崎市定认为元代放弃律典一方面是宋金以来律典地位持续下降趋势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专制君主不断强化对法律创制干预的必然结局,此外,元代官僚体系中胥吏势力的抬头也是修律长期未果的重要原因(《宋元时期的法制与审判机构——〈元典章〉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背景》,载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胡兴东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中国古代判例法运作机制研究:以元朝和清朝为比较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
②参见杨一凡:《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修正》(《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5-19页),《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8页);陈灵海:《〈大清会典〉与清代“典例”法律体系》(《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第402-428页)。
③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宣布:“禁行金《泰和律》。”见《元史》卷七《世祖纪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8页)。
④法史学界很少有学者直接做出中国古代不存在判例的结论,但也大都认为古代中国的“判例”“判例法”绝不同于普通法意义上的“判例”“判例法”,古代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本文遵从法史学界的习惯用法,同时认为古代中国判例不同于普通法上判例,也不是判例法国家。
⑤《宋史·刑法一》载神宗改制:“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