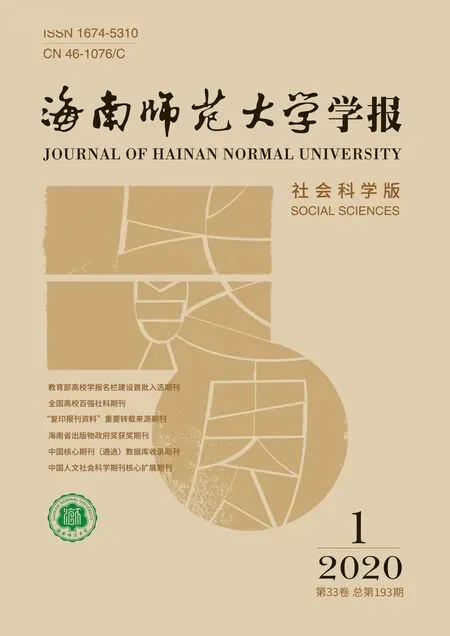外在于世界的“文学”与“主体”:兼论小说《斯通纳》中的空间隐喻
杨 光
(深圳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的小说《斯通纳》(Stoner)出版于1965年,在近年又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小说主角斯通纳是一个出身农场的少年,在大学修习农学专业的过程中,因为被一堂文学课所吸引而“弃农从文”,最终成为一名文学教师。小说通过讲述斯通纳从少年直至死亡的一生经历,描绘了个体在面对世界时的种种抉择、抗争与困境,从而展开了对个体存在意义的叩问。此书作者也是一位作家、学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通纳“弃农转文”的安排不会是偶然的,它必然包含着作者本人对文学的思考。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了,在书中文学对于斯通纳、对于这本小说本身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我们就首先以文学作为切入点,逐渐深入到对小说中诸种问题的讨论。
一、文学作为新视角
在小说开头,作者描述了斯通纳“转文”的经历。这一转折引出了全书的情节,同时也定下了基调:暗示了文学对于斯通纳的意义,故而有必要首先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
文学教师阿切尔·斯隆开的公共课《文学概论》让农学生斯通纳十分苦恼。不过随着课程的进行,他似乎有所领悟。在某一堂课上,在老师的提问过程中,他忽然对周遭世界产生了新的感受:
威廉·斯通纳几乎感觉不到身边有同学存在,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咕咕哝哝地抱怨着,然后慢慢腾腾地走出教室。大家离去后,斯通纳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钟,眼睛盯着前面那道窄窄的地板木条,这块地板早已被他从未见过或者认识的学生们不安分的双脚磨掉了漆,蹭得光光的了。他在地板上滑着自己的脚,听着自己的脚底从木头上蹭过时粗糙的刮擦声,感觉透过皮革的粗硬质地。接着,他也站起来,慢慢走出教室。(1)[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此时的斯通纳处于一种出神的状态,仿佛感知不到其他人的动向。取而代之的是他对于周围细微事物的极端敏锐。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脚、鞋子,还有鞋子的质地,仿佛第一次感觉到他们。而当他走进校园之后:
斯通纳听着他们的咕哝声和鞋跟踩在石头路上发出的磕碰声,看着他们的脸蛋,都被冷气冻得红扑扑的,弯着身子抵御着一股微风。他好奇地看着他们,好像以前没见过这些同学,好像自己离他们很远又很近。(2)[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15页。
这种感受有些像什克洛夫斯基所讲的“陌生化”,艺术作品刷新了人们的认知,使得人们对于熟悉之物有了更深刻、更新鲜的认知:
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间长度,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作的方式,而被创作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3)[俄]什克洛夫斯基 :《作为手法的艺术》,[爱沙尼亚]扎娜·明茨,[爱沙尼亚]切尔诺夫编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但事实上,斯通纳的感受又不完全是对熟悉之物的新经验——自然也包含这一点,而是更进一层地,从对于外物的新认知向内发展为对自我的认知:“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他还从未以这种方式感知过自己。”而回顾过去时,“斯通纳仿佛感觉那段时光虚幻不实,压根就属于别人,那段已经逝去的时光,好像不是他习惯的那样正常流逝,而是断断续续地流逝着。”(4)[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16页。
过去成为了异于自己的存在,当前的自己面对过去似乎成了一个“旁观者”:“他还感觉自己从时间中被移了出来,旁观着时间在自己面前流逝,像个宏大、并不均匀地翻转着的立体景观。”(5)[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16页。一方面,斯通纳似乎借着文学的启灵,获得了一种自反性的视角,可用以反省自身;在另一种意义上,他获得了新生,仿佛从过去的浑浑噩噩之中猛然觉醒,拥有了感知世界的能力。所以,在此文学不是让斯通纳对于外物有了新感觉,而几乎是唤醒了他,赋予了他感觉。概而言之,文学给斯通纳提供的是一种新的视角和感知方式,让他从此以后可以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这种新视角异于甚至可以说对立于他之前作为“农学生”与农场主之子的视角,后者立足于现实世界,紧密关联着人们的衣食,前者则完全是超脱于这一视角之上的世界,或者直接称之为精神世界,从而使他可以用一种审视、反思乃至略带批判性的目光看待现实世界与过去的自己。这也正是斯通纳会忽然觉得过去自己的经历“压根就属于别人”的原因。
斯通纳这种“弃农从文”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弃医从文”的自述。“幻灯片”事件也像这次读诗经历一样,让当事人获得了一种类似的“惊颤”之感,从而彻底更改了人生道路。不同之处在于,鲁迅一以贯之地在找寻医治中国的良方,这次事件于鲁迅而言是豁然地发现“此路不通”的警醒。但在这一从学医到学文的追寻过程中,他一直对自己的目标与选择有清醒的认识。反观斯通纳,他去读农学时,并没有清晰的目标,他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故而连清晰地“抗拒”也没有:“‘你们真的想让我去吗?’他问道,似乎半是希望得到否定的答复。‘你们真的想让我去吗?’”(6)[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4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不但让斯通纳获得了一种新视角,还让他获得了主体性。不过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只有一种新视角的获得,才使斯通纳有能力充分地反观自身;只有通过这种反观,一种对自身的认识、一种主体性才可以获得。在此,文学对斯通纳的意义才完全显现:只有意识到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的存在,才有可能以此“位置”(postion)为支撑点获取这一视角。同时,一种对自身的认知能进一步促使反观行为的深入推进,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文学带来了新的眼光,更重要的是,文学提供了用以观看的新的落脚点。由此,文学于斯通纳而言是发现“新世界”的惊喜,也是用以发现的方式。这也暗示了全文的基调:斯通纳一生都恋栈这一世界,维护这一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也终于困顿于这一世界。
概而言之,我们已然知晓《斯通纳》的结尾以斯通纳之死告终,而在本书开头的这段经历事实上描述了斯通纳的“生”。从这一刻起,斯通纳被唤醒,正式开始了他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与交互,妥协与对抗。而这本书所记载的,也便是一场斯通纳与世界的遭逢。
二、作为“飞地”的大学
本书的第一节描述了斯通纳的“生”,第二节便谈到了“死”。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了。每个人都面临一个抉择:是否响应号召,踏上战场?斯通纳的两位好友接连参战,其中一位最终在战争中死去。而当斯通纳向他的老师斯隆咨询是否应该上战场时,他的老师大发脾气:
战争屠杀掉的不仅仅是几千或者几万的年轻人。还屠戮掉一个民族心灵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失而复得。如果一个民族战争频仍,很快,剩下的就全都是残暴者以及动物,那些我们——你我以及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污秽里培养出的动物。(7)[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43页。
最终斯通纳没有应征入伍,并因此似乎经受了人们的指指点点。也许此时的他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老师。直到暮年之时,历史再次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又一批年轻人踏上疆场,他才终于感同身受。在此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踏上战场的场景又意味着什么,值得作者再次书写?当然,战争是残暴的,是在大地之上的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激烈对抗。它留下“残暴者”以及“动物”,摧毁学者们“拿出生命去建构的东西”。(8)[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43页。
不过如果从与世界的关系上来看,战争是世界内部的对抗,它似乎与大学,与文学无关。大学就像是一座“飞地”(enclave)。按照英文的解释,enclave(飞地)是“a place or a group of people that is surrounded by people or areas that are different”(9)参见《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615页。,即,“被不同的地区或族群所围绕的另一空间或族群”。换言之,“飞地”构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另一空间,这一空间具有与外在“空间”不同的运行秩序和生活方式。当外在世界秩序崩毁时,“飞地”可为其中的居民提供一种屏障;同时在平日,它又负责对抗外在世界本身:surround一词不仅意味着“围绕”,还意味着军事意义上的“包围”,这其中也隐含着紧张的对立关系。正如斯通纳的好友戴夫·马斯特斯所言,大学是“庇护所”,在浊世横流中小心翼翼地持存一点清净。而反过来,大学里的人又需竭尽心力维持大学自身的纯洁。这不仅仅是出于自身的原因对自身栖身之所的维护,还因为出于空间的自身逻辑,必须有人这么做;否则“大学”这一空间的“逻辑”将会失去,大学也便不成其为大学。正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论述空间逻辑时所说:
空间在建立某种总体性、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准确地说,人们不能将它从这个系统、这种逻辑、这种总体性中排除出去。相反,它应该在这一目的(实践的与战略的)中表现出它的作用。(10)[法]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可是战争摧毁了这种脆弱的平衡,从学校征兵的行为强制性地将二者进行了关联。这也正是之前的斯隆、后来的斯通纳面对战争时焦虑的因由。大批教职人员卷入战争,学校被迫卷入了世界的纷争。战争对大学、文学以及依托它们而存在的学者的世界产生了威胁,同时也对他们费心建构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威胁。这大概可以解释斯隆在斯通纳前来与自己商讨是否应征时的激动情绪:眼见自己的世界可能要分崩离析了。从此角度而言,两次大战不单单是物理世界进行的大战,也是“庇护所”与外部世界进行的战争,是他们努力维护自己世界纯洁性的战争。“有很多人类的对抗、失败和胜利,很多并非军事之争,史书中也没有记载。”(11)[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44页。而这也正是斯通纳的战争。如此,在后文中发生斯通纳与准系主任劳曼克斯的对抗也便容易理解了。
劳曼克思的学生沃尔克报名参加了斯通纳的研讨班,然而未能达到斯通纳的要求。斯通纳评分时给他打了F。在后来的考核中,斯通纳作为评审成员之一惊讶地发现作为沃尔克导师的劳曼克斯一直有意引导正常的考核流程,替学生解围,意图使其通过考核。
当斯通纳发现这一点时:
他几乎感到有种生理上的不舒服。他向下望着桌子,看到两臂间自己的脸影反射在锃亮的栗色桌面上。影子黑乎乎的,几乎认不出五官,好像看到一个鬼魂隐隐约约从硬木中出来,过来迎接他。(12)[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189页。
而当他看穿劳曼克思维护学生的伎俩后,“他等着自己知道必须得做的事,他怀着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强烈的厌恶、愤怒和悲哀心情等待着。”(13)[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190页。这种情绪乍看或许会显得过于激烈,但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学生的问题,还在于这个学生的导师妄图不择手段使自己的学生取得学位混入高校。这是斯通纳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这种行为毫无疑问会玷污学校的纯洁性。维护自己的世界,自己最后的底线的意图使得他必须毫不退让:
我这是阻拦他拿这个学位,我这是阻拦他在某个学院或者大学教书。说穿了我就是想这样做。对他来说,要是当上教师,那将是一场——灾难。(14)[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198页。
而后面一段话说的更明白:
他(指戴夫—引者)说——对那些贫困者、瘸子们而言,大学就像一座避难所,一个远离世界的庇护所,但他不是指沃尔克。戴夫会认为沃尔克就是——就是外面那个世界。我们不能让他进来。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变得像这个世界了,就像不真实的,就像……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他阻止在外。(15)[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204页。
然而斯通纳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劳曼克思不久后担任了系主任一职,他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学生沃尔克避免了被驱赶的命运。而之后的许多年时间里,劳曼克思都不曾真正忘记过这“一箭之仇”,他多年来通过排课等问题来给斯通纳穿“小鞋”。斯通纳也从未屈服过,直到临终前因为退休问题,自己生了病才算间接达成了一次劳曼克思的心愿——按期退休了。
作为外部世界的象征,沃尔克、劳曼克思最终还是侵入了大学。斯通纳苦心维护的自己的世界正在逐渐被侵蚀。正如他在家里苦心为自己搭建的书房被夫人轻而易举的摧毁、霸占。作为象征性的文学世界的大学、书房终于还是坍塌了。作为文学空间物质载体的大学、书房有可能被侵占,但文学本身仍在。那么,至此,我们可以追问,首先,斯通纳维护的这些处所:大学、书房,这些被认为是外在于世界的空间到底意味着什么?文学又意味着什么呢?
三、大学作为秩序的象征与意义的持存地
戴夫·马斯特斯曾道:“斯通纳把大学当作一幢巨大的仓库,类似座图书馆或者货栈,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挑选能够成全自己的东西,大家在里面共同工作,犹如一间公共蜂巢里的小蜜蜂。代表着真、善、美。”(16)[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34页。
斯通纳、斯隆是典型的工蜂,他们辛勤工作、酿蜜,在蜂巢里寻找能成全、丰满自己的知识养料,同时也为蜂巢贡献自己的蜜糖。与此同时也训练新的蜜蜂,培养下一代,保障蜂巢的延续。整个蜂巢有自己的规则和秩序。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学就如蜂巢一般,它是有序的象征。在里面生活或许有些辛苦:它要求人们努力工作,不停地学习、阅读、写作、教书。但是它又简单明了,只要付出努力便会获得收获。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获得收获。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共同工作”,是“真善美”。
然而,沃尔克却是一匹害群之马,一只坏蜂。他投机取巧,不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去学习,在研讨课上夸夸其谈;为了应付考核答辩,他为自己的课题做了精心的准备,对其他却一无所知。然而,我们很难说沃尔克真的是一个平庸之辈,事实上他在自己课题上展露的才华表明他是有能力做好相应的工作或完成课程的。然而他不够努力,他采用的规则或许是“世界”,抑或说是“社会”上的规则:用最小的努力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而如果不是斯通纳的坚持,他应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便在导师的配合下取得好成绩。在此意义上,斯通纳们扮演了蜂巢的“卫道士”的角色。而劳曼克思、沃尔克更像是入侵蜂巢的马蜂们。
马蜂们本身也没有错,只是他们完全不依照蜂巢的规则来行事。他们有自己的规则。劳曼克思并不真的以为自己是错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心保护自己的学生。“斯通纳几乎恐怖地意识到,劳曼克思的忠心耿耿不仅可怕,而且绝不会改变。”(17)[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314页。斯通纳本质上却并非针对他的学生,只是针对这一事件本身。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劳曼克思倾向于“投资”“报偿”的行为方式。正如后来在他要求斯通纳退休时,承诺在其退休前将他晋升为正教授。在斯通纳因患癌症退休之后——这并非响应他的要求,而劳曼克思虽不明白为何斯通纳会忽然同意自己的要求,但仍然遵守承诺,开始操办为斯通纳晋升职称。从这个意义上,劳曼克思是一个爱护弟子,且对对手信守承诺之人。在世俗的意义上,劳曼克思甚至会被看作是一个可信赖之人,而斯通纳大概会被认为不近人情。然而这是一种商业社会的行事规则——习惯于将各种事情等同于利益交换,用交易的眼光看待事物,同时忠于达成的交易,正如遵守合约。本质上,这是对于利益的遵守,然而,却不遵守真理。这正是斯通纳与他的不同之处。正如斯通纳最后对他的评价:“你是个好人,我想。你肯定也是个好教师。但在某些方面,你却是个无知的杂种。”(18)[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310页。劳曼克思确实很无知,所以他总是以为或威逼或利诱,总是可以逼迫斯通纳改变主意。然而,劳曼克思不明白的是,斯通纳要求某件事的时候,其要求的便是这件事本身,而不是将之作为讨价还价的条件。
回过头来再看书中的两场世界大战。战争本身便是现实世界极端无序的状态,这时一切秩序、规则都崩溃了。这不再是学者们生活的大学:一切都是可见的,通过努力便可以获得应有的结果;也不是学者们研究的书本,能够通过多年修习逐渐变得清晰。这都是他们可以把握的领域,但现实世界却不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现实世界的排斥何尝不是对不能把握的未知世界的恐惧?更何况是本来便无法把握的现实世界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战争状态呢?
再看斯通纳的两段感情,他的婚姻十分不幸。她的妻子是银行家的女儿,从小受到严格的规训,难以与人顺畅地交流。而斯通纳只好将自己亲手打造的书房作为栖息的港湾。书房与大学对于斯通纳发挥着相同的避风港的作用,而后他与自己的学生凯瑟琳陷入一段疯狂的婚外恋情中。相较于自己在家里被妻子摧毁的书房,凯瑟琳的居室是斯通纳可以舒心安然的环境,他甚至将自己的部分书籍放在凯瑟琳那里。在此,这种对比就很明显了,妻子所在的家庭是不可控的、不可预料的,秩序是崩毁的。而凯瑟琳的居室则成为了庇护所与港湾。或可说,凯瑟琳为他的感情生活重新建立了秩序。
而当初,他与沃尔克的争端的部分原因之一,是沃尔克在发言中攻击了凯瑟琳的发言。凯瑟琳是一个富有灵性的真正的研究者,这种对于凯瑟琳的保护事实上与他对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对于大学的保护是相一致的。这一对师徒正好与沃尔克和他“忠心耿耿”的老师劳曼克思形成对应的关系。当然书里的两段婚姻、两次战争等也形成了对应。事实上,这是本书结构上的一个特色,充满了严谨对称的建筑风格。这大概可以视为对秩序的追求在艺术形式上的体现。
本书以“生”开头,以“死”结尾,中间写了两次战争、两段感情。它们交替出现,相互照应。在空间上则是大学/世界相互对应。人物关系上也存在延续/对应的模式,比如斯通纳和他的老师斯隆。当斯通纳年轻时,经历了第一次战争,去向老师询问如何抉择;当他老了,经历了第二次大战,开始明了老师的内心。与这对师徒形成对立的劳曼克思师徒,则作为外部世界的入侵者象征,提供了另一种价值观的参照。斯通纳的妻子伊迪丝与他后来的情人凯瑟琳也形成对比。前者与斯通纳难以正常交流,斯通纳靠躲在书房里为自己寻觅安静;而凯瑟琳更接近于斯通纳的灵魂伴侣,他们在情爱之外,还是志同道合的学术伙伴。而伊迪丝的出身——银行家的女儿本身便提供了强烈的象征。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伊迪丝也是无辜的,她从小被父母所规训,所以才成为后来的样子。而她最终又将这一点投射在女儿格蕾斯身上,在她的规训下,女儿终于也变成了她希望的样子。女儿被伊迪丝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学校、邻里之间“受欢迎”,慢慢活成了她期待的样子。这其实也是大众心中所认为的好孩子的角色。“应该”有的样子,依据的是“世界”的规则。有意思的是,格蕾斯极小的时候是在父亲的书房学习长大的,直到母亲的干预,那时候她甚至不敢与父亲相互打招呼。可以说格蕾斯的命运同样体现了本书的主题:书房/大学与外部世界的抗争。而格蕾斯的遭遇也体现了一种命运的延续或者轮回:伊迪丝被自己的父母规训,她终于回过头来摧毁了自己的女儿。在此外部世界扮演了一种对于个体的异化力量,而作为庇护所的大学、书房、文学则提供了对抗“异化”的城堡。不过格蕾斯的命运没有完全重复她的母亲,她最终离开家庭,远走他乡。这一点又隐隐呼应了她父亲的命运:终于离开了生养自己的土地、父母,只在父亲死去时回来看了一眼。至此,本书形成了一种对于“自然秩序”的完整隐喻。从生到死,季节轮转,而人们的命运也在此中轮回不休。
这种秩序井然的空间或可说是大学及其依存于大学的学术生活所具有的形式上的特征。那么这种形式给人提供的是什么呢?“你总觉得这儿有某种东西,有某种东西值得去探寻。”(19)[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36页。斯通纳究竟探寻的又是什么呢?在将死之际,斯通纳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想当一名教师,他成了教师。但他知道,他永远知道,人生的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冷漠的人。他曾梦想过某种政治,某种绝对的纯洁。他寻求过妥协和突击性消遣某些无聊琐事。他曾想象过智慧,在漫长的岁月的尽头,他却找到了无知。还有什么呢?他想,还有什么呢?”(20)[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336页。
在弥留之际,斯通纳在旁侧的书籍中拿到了自己曾经出版的专著,他抚摸并打开了它:“以为会从中找到自我,在那已然褪色的印刷文字中。而且,他知道,自己的一小部分,他无法否认,已经在其中,而且将永远在其中。”(21)[美]约翰·威廉斯 :《斯通纳》,杨向荣译,第340页。在本书的开头,斯通纳通过文学获得了新生,找到了自我;最终他死去了,然而在死去的关头,他再次找到了自我。他死了,他的书却留了下来。包含着斯通纳思想的书籍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于死亡的抗拒。“在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了一把尘土之后,它们常常还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22)[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而“作者之死”意味着文本形态的最终成型,意味着“文”的诞生。同时,“文”也作为作者的精神形态继续存在。作者死的这一刻,既是死亡,同时也是他的新生。这有些类似于巴赫金常说的生死二重性的味道:“哪里有死亡,哪里就有降生,就有交替,就有革新。”(23)[俄]巴赫金 :《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6页。而本书的结构也暗示了这一解释:“在所有这些复现的中心是睡和醒的生活的循环圈。是白天的自我的挫伤,夜晚的自我巨人的复苏的循环图。”(24)[加]诺斯罗普·弗莱 :《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在此种意义上,大学、文学提供了一种获得人生意义的空间,一种超越有限的生命最终达到无限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文学所具有的秩序正象征着永恒。这种模仿自然秩序的文本结构、对于人命运的探讨也使本书获得了一种古希腊史诗般的素朴美感。
四、结语
文学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问题,从古希腊的“模仿说”开始,便已经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这也是该本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不过更切近相关主题的论争应该是20世纪西方学界有关“文学是否是自为的”这一争论。而在中国也有过一个相似的讨论,那便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界发生的,究竟是“为人生的文学”还是“为文学的文学”的论争。这两场讨论当然具有不同的理论背景与社会现实,但大致而言都是文学界与学术界面对失序社会时的一种反应。鲁迅弃医从文的经历是一种典型的实践型思维,希望能够通过文学救治人们的精神,从而产生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这是一种希望通过文学实践干预现实并影响世界的方式。包括其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在西方则有以雷蒙·威廉斯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强调文学的“实践性”。
而相反的,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部分学者,以及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都倾向于将文学视为一种自为的系统,淡化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过,这种理论立场也是相对而言且并非绝对的。事实上,如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后的许多学者往往十分强调文学的批判性,这同样是一种与世界的关系,而这种与世界的对抗性关系正契合《斯通纳》中体现的立场。
通过之前的分析,应该不难看出,在《斯通纳》中展现出的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文学意味着永恒的真、善、美,而世界则是无序的、丑恶的。事实上,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究其原因,大概与他们都受到理论家弗洛伊德的影响有关。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或文化与个体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文明或文化的规则在于防范个人,维持群体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个性难免受到压抑:
尽管文明被认为是一个有利于人类普遍利益的目标,但每个个体实质上都是文明的敌人。显然,既然人不可以单独存在,人们就应当感到,那些为了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而由文明期望于人们的牺牲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此,必须保卫文明,防范个人,文明的规章、风俗和命令都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产生的。它们的目的不仅在于影响财富的一定的分配,而且在于维持这一分配;确实,它们不得不保护一切有助于征服自然和生产财富的事物,防范人们的敌意冲动。(25)[奥]弗洛伊德 :《论文明》,徐洋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6页。
在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中,对于这种思维的接受最为明显:“发达工业社会的成就能使人扭转进步的方向,打破生产与破坏、自由与压抑之间命运攸关的联合,换言之,它是能使人懂得作乐的科学,以使人在反抗死亡威胁的一贯斗争中,学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本能,用社会财富来塑造自己的环境。”(26)[美]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966年政治导言》第1页。又如马尔库塞在《导言》中说,“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27)[美]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1966年政治导言》第1页。
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弗洛伊德思想以及其后思想家的影响,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了一场反文化运动,这也正与《斯通纳》成书的年份(1965年)重合。不同的是,反文化运动倾向于以破坏世界规则作为反抗的象征,而斯通纳型的学者则选择栖息在自己的永恒城堡里,只有自己的世界被侵犯时才奋起反抗。虽然道路不同,但其实殊途同归。不过,至此,这一话题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而延伸到主体面对世界的遭遇了。
我们很难说种种人生抉择以及对于文学的认知是对是错,但如果学者们仅仅只在意文学世界本身的清净,一旦世界崩毁,覆巢之下又焉有完卵呢?艺术家或许不喜欢污秽,但最美丽的花朵却又往往盛开于污秽之上。“诗句,按照阿赫马托娃的说法,的确是从垃圾中生长出来的;散文之根也并不高明些。”(28)[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47页。不过面对沧海横流,有人自成一统,有人立于中流,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一种选择。通过之前的分析,不难发现,本书乃至其背后潜隐的思想资源都带有一种二元对立的意味,即存在着理想世界/现实世界、内/外等的截然划分。这当然可追溯至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传统,以及其成书时代不久以前的结构主义思潮。《斯通纳》没有正视世界的复杂性、所秉承思想框架的僵硬自然是其缺点。不过,不敢面对世界仅仅维护自己蜂巢的工蜂虽然看起来懦弱,但也有出奇勇敢的时候。而有时候,仅仅是蜂巢的存在本身,其秩序性、永恒性已经构成了对世界的批判与反抗。回过头来,单就个体而言,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被大世界所吞没,已经是生活中的勇士了。按照戴夫的说法,斯通纳是现时代的堂吉诃德,却没有自己的桑丘。这一说法是准确的。斯通纳便如堂吉诃德一般,为了自己的原则或者说浪漫的理想与世界抗争,无论荒诞也好,悲哀也好,他都是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