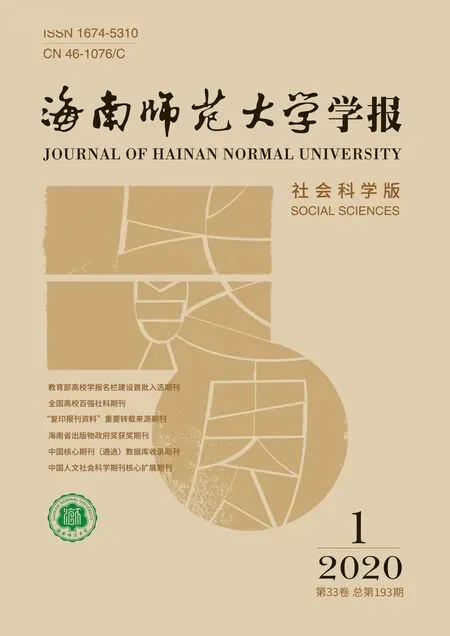《摩罗诗力说》中的“鲁迅拜伦”形象
——以《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补校为基础
刘 锐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论:“鲁迅拜伦”概念的产生、阐释及释疑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的接受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变异”。在特定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催生出的这种“变异”和与之相应的历史需求,会直接而明确地反映在对外来文化的择取和改造上,在此之中,我们或许可以窥到一种通过直接表达难以显现的隐秘的文化内涵与民族心理,而其中这个有意或无意为之的“变异”过程,更是如二度创作,值得推敲和琢磨的地方很多。
就如本文所要探讨的“鲁迅拜伦”,正是在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变异”机制下产生的。但需要说明的是,“鲁迅拜伦”的说法属于本人生造,这源自于“竹内鲁迅”这一说法的启发。正如竹内好对鲁迅的研究一样,那个“鲁迅”并不完全是鲁迅本身,或者说相对于所谓“回到鲁迅那里”的研究,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偏转,所以,这个“鲁迅”是被竹内好构建起来的。竹内好“充满了主观意向的读解鲁迅人格精神与研究鲁迅动机”,及“判断鲁迅的价值取向及其构筑的鲁迅形象一起被看做是‘竹内鲁迅’的内涵”。(1)靳丛林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页。在对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以下简称《材源考》)所提供的《摩罗诗力说》材源与原文的对勘阅读中,我发现其中的拜伦也是鲁迅在接受外国文化的过程中改造的“变异”产物,在鲁迅对材源的增删、改译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个富有鲁迅内涵的拜伦形象,所以把其冠名为“鲁迅拜伦”。显然,这个拜伦是鲁迅在日语材料中二度改编而来的,北冈正子的书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她未做进一步阐释,而利用好《材源考》并对其中提供的这部分珍贵的原始材料进行更加精细的对勘阅读,无疑才是对北冈正子这份学术成果和探索精神的最好回应。相对于北冈正子较为宏观的比较,笔者所进行的是一种精确到字词的微观比较,近似于传统的校雠之学,是对北冈正子比较的一种补充,故而谓之“补校”。
此外,有人会问,《摩罗诗力说》涉及到著名非著名、大大小小八位诗人,为什么单就拜伦说之?为什么不论述“鲁迅普希金”“鲁迅裴多菲”“鲁迅克拉辛斯基”呢?对此,笔者认为要在《摩罗诗力说》中体现这种文化接受中的“变异”过程及其结果,“鲁迅拜伦”当是最有代表性、最应该也最有可能被单独选出来加以讨论的。理由是:第一,《摩罗诗力说》中述及八位诗人的内容共五章半(第四、五、六、七、八章及第九章前半部分),其中述及拜伦的内容就占了两章(第四、五章),接近总和的三分之一,所以拜伦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篇幅的占有量上;第二,在章节之间的内容勾连以及在此基础上鲁迅对整个“摩罗诗派”的描述,(2)如果仅看原文,似乎是鲁迅自己凭空建构出了“摩罗诗派”,将拜伦突出并以其为主线,但逐句对比材源后就会发现,这个建构的流派是在鲁迅对材源的译述中不自觉形成的,在其他诗人的论述中提到拜伦并与之联系的是各类材源的作者,鲁迅只是加以整合罢了。拜伦都处于中心地位,并以拜伦作为摩罗诗人之间相关联的纽带;(3)如《摩罗诗力说》第六章雪莱部分,说雪莱“识裴伦于瑞士;裴伦深称其人,谓奋迅如狮子,又善其诗,而世犹无顾之者”;第七章普希金、莱蒙托夫部分,说普希金“其时始读裴伦诗,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小诗亦尝摹裴伦”,说到莱蒙托夫则言“裴伦之摩罗思想,则又经普式庚而传来尔孟多夫”;第八章波兰三诗人部分,说密茨凯维支“后渐读裴伦诗”,说斯沃瓦茨基“性情思想如裴伦”;第九章的裴多菲部分说“裴彖飞幼时,尝治裴伦暨修黎之诗,所作率队纵言自由,诞放激烈,性情亦仿佛如二人”。而且,以上原文在《材源考》中都提供了相对应的材源。第三,在原文与材源的对勘中不难发现,鲁迅在最先确立了拜伦的中心地位以后,凡述及到的诗人,如果有条件的,都依照拜伦对此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一种刻意的同构性改造。(4)如提到过莱蒙托夫在读拜伦传记时,发现自己的某一经历和拜伦相同,于是再将自己的同一经历加以述说,这是在生平上的同构。还有一种属于在作品内容上的同构,通过改译某一诗人的作品,使其与拜伦的某一作品之间建立一种同构性,如鲁迅在述及普希金《高加索累囚行》(今通译为《高加索的俘虏》)时,对一段四百多字的材源进行了简写,参照拜伦《海盗》便可以发现,其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设置。
二、材源:拜伦形象东渐的“日本中介”和鲁迅的接受可能
要提及“鲁迅拜伦”的前提,我认为是要先理清拜伦从西方向东方的传播途径以及鲁迅的接受条件,进一步说就是当时鲁迅所能看到的所有关于拜伦的材料和鲁迅可能接受的程度以及历史环境。在后来对“鲁迅与拜伦”的研究中,多是在一种鲁迅接受的拜伦和原拜伦之间的比较研究,即便有研究者注意到日本这个中介,也是顺带而过,真正的落脚点还是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之下。(5)相关研究成果如高旭东《鲁迅与英国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宋庆宝《拜伦在中国:从晚清民初到五四》(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张娟平《拜伦的形象:从欧洲到中国——以1900—1917年间拜伦在中国的译介为重点来考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等。当然,并不是说这种研究跳过了“日本中介”就没有意义,但是纳入到鲁迅研究的范畴下来说,依据中介实事求是进行探源式的研究似乎更有意义,而非将鲁迅当作是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二手材料。
要弄清拜伦形象如何从西方传入到中国,可以说,考察鲁迅在日本译介环境下对“日本拜伦”的接受是其中的关键,从头至尾的传播线路简明表示,即“西方—日本—鲁迅—中国”。(6)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近百年来中国对拜伦的接受,是沿着鲁迅的思路往下进行的。详见黄静,王本朝 :《鲁迅的“拜伦”言说与被言说——〈摩罗诗力说〉“拜伦观”的接受史研究》,《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所以,如果不要将眼光放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上,只是较为客观地考察鲁迅的接受及拜伦形象的变化,这里所谓的“日本中介”才是真正的源头,这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证的直接的文字材源;二是间接的可能的影响;三是当时的历史环境。
直接的文字材源,即北冈正子考证出的木村鹰太郎(以下简称“木村”)所著《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以下简称《拜伦》)和木村所译拜伦《海盗》这两本书,(7)此外,木村鹰太郎于1904至1907年间还翻译过拜伦的《巴里西耶》《该隐》《马塞帕》三部作品,鲁迅没有直接作为材源进行译述,但不能排除鲁迅看过的可能,属于可能的间接影响途径。在《摩罗诗力说》第四、五章中,除了个别找不到材源和鲁迅自己根据理解添加的句子外,(8)如“人则曰,爰灭罪恶,神可颂哉!”一句,北冈正子表示找不到相应的出处,但校读上下文,可知这当是鲁迅添加的一句话,带有批评语气,也是为了连接上下文。凡经确证的材源,都出自上述两本书。北冈正子通过比较,认为木村寄托在拜伦身上的思想,有三点:“期待天才的出现”“在拜伦的‘摩罗主义’中寻求和现在的强者斗争并取代其地位的力量”,以及“把世界看作优胜劣败之战场”。(9)[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在可能的间接影响途径中,还有在当时日本汉语译介环境中的“拜伦形象”的影响。清末流亡日本的革命者是当时汉语译介群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去国飘零,在日本接受到西方文化,开始了一种带有寄托性质的译介。差不多在鲁迅来到日本的同时,由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上便刊登了被称之为“英国大文豪摆伦”(10)东京《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一年第二号(1902年第2期)。的照片,与此同时在《新小说》上连载的梁启超的对话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有对拜伦《哀希腊》的节译,并通过小说人物的对话,将中国的现状与之联系了起来,(11)小说人物李君对几句歌词评点道:“句句都想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东京《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一年第三号(1902年第3期)。同时《新中国未来记》中还有梁启超对拜伦《异教徒》一诗的节译,这些节译是第一次以汉语为载体对拜伦的译介。作为已经受到过梁启超影响并且初到日本且语言不通的鲁迅,很有可能会被梁氏译介的拜伦及其作品所影响。1903年,马君武根据自己对拜伦的阅读所得,撰有《欧学之片影》一文发表在同为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其中《十九世纪二大文豪》一节中有对拜伦的介绍及评价,相比于梁启超的介绍,马君武的材料则更详实,风格也更个人化,(12)《癸卯新民丛报汇编》,1903年,第1080-1081页。此外马氏于1905年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全诗,但鲁迅几乎不可能看到。(13)马君武译《哀希腊》一诗,最初发表在《正谊杂志》1941年第1卷第6号上,其译序说乃乙巳(1905)年回家省亲时所译。继马氏之后,苏曼殊第一个较为全面地翻译拜伦诗歌,诗集出版于1908年秋,这已在《摩罗诗力说》发表半年多后,但是之前与鲁迅有过交往的苏曼殊很有可能把自己理解的“拜伦”传达给鲁迅,并与之交流。(14)鲁迅晚年对《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者增田涉讲过,当年苏曼殊也是《新生》杂志的创办同人(详见增田涉 :《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页)。这就可以确定二人在当时有过接触。而且1908年二人发表在《河南》上的文章,原先都打算发表在后来没有办成的《新生》杂志上,那么作为《新生》同人的苏曼殊对于鲁迅《摩罗诗力说》中涉及的拜伦,与鲁迅有过交流并对其产生影响是极有可能的。这对一个同样将要开始传播拜伦的人,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接受途径。
此外,仅从木村《拜伦》的创作初衷及精神寄托上,即可判断,当时的日本社会和中国晚清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有契合之处,“社会万般事物停滞,人类腐败”,而文坛充斥着“软弱无力之文学家”,“自称天才,冒牌文人众多”,“阿谀、谄佞、伪善、嫉妒、中伤盛行”,(15)[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1页。正如龚自珍所呼唤的“风雷”(16)[清]龚自珍 :《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样,在同时代的社会里,拜伦式的反叛无疑是具有普世性的。这为鲁迅接受拜伦,提供了极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
上述的“日本中介”作为客观因素,决定了鲁迅的接受可能。另一方面,从主观条件上讲,也就是鲁迅的接受程度,同样不能忽略。实际上,纵观鲁迅对外国文化的接受,或者将范围缩小至《摩罗诗力说》中对外国诗人的接受,都呈现出偏向于被压迫和富于反抗的弱小民族的文学,而拜伦恰恰是一个出自大英帝国的诗人,这一点看似让人费解。实则,理解了鲁迅对尼采的接受,再理解鲁迅对拜伦的接受就顺理成章了。有论者认为鲁迅对尼采的选择,不只是因为在日本所学外语是德语,其中也多少含有对尼采“叛逆性的反霸权心态和立场”的选择。(17)[澳]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如果以此推想,鲁迅选择英国诗人的深意就很容易理解了,即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强国,从其内部找出具有代表性的反抗者,其影响力将是被压迫小国和其他大国的反抗者所不能比拟的。(18)比如对勘《摩罗诗力说》的这一句材源与原文:“由是言之恶魔亦神之所创也”(木村材源)与“由是言之,则魔亦神所手创者矣”(鲁迅原文),鲁迅对这句是直译,是讲魔的由来,源自神的压迫,在这个结论上鲁迅完全承袭了木村。也就是说反抗者的催生来源于统治者的压迫,是从统治者内部自身开始瓦解的。这一点,应是鲁迅对拜伦之于英国的一个比较深切的领会,所以会有这种选择。此外,鲁迅接受的程度还要取决于所掌握的外语,就以在南京矿物学堂所储备的一点英语能力,决定了鲁迅不能从英语直接接受以其为载体的外国文化,(19)至少能确定,面对《摩罗诗力说》中涉及到的英文材源,即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波兰》二书,当时是由周作人口译转述给鲁迅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从口语翻译向书面翻译转化,发生“变异”也是不可避免的。(详见周作人 :《知堂回忆录·七八·翻译小说 下》,止庵校订 :《周作人自编集·知堂回忆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此外,鲁迅晚年也说过“我是不会看英文的”一类的话。参见鲁迅 :《331116 致吴渤》,《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8页。只能是通过磨砺已久的日语来接受。
三、塑造:“鲁迅拜伦”诞生记
鲁迅对木村的材源进行译述并杂入创作的过程,不能不说是塑造另一个带有强烈鲁迅色彩的文学性拜伦形象的过程。北冈正子将鲁迅《摩罗诗力说》中拜伦形象与上述木村材源中的拜伦形象(以下为叙述方便,简称“木村拜伦”)做对比后,一方面认为鲁迅在取材上着眼于“反抗压迫之原动力”,选取“表现强大意志力量、复仇精神和对神进行反抗”的内容,而舍弃拜伦“快乐主义和女性观”的材料。另一方面,认为鲁迅和木村同样“高度评价拜伦的反抗精神”的同时,鲁迅以人道主义为基石,并“没有从肯定优胜劣败必然性的强者理论出发蔑视弱者”。(20)[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3-5页。这基本上说清了鲁迅在对拜伦材料的择取上所寄托的个人思想,但是拜伦在《摩罗诗力说》中作为一个形象来展示,并没有体现在北冈正子的研究中,或者说这种宏观上的对比,也很难对作为文学形象的“鲁迅拜伦”做出勾画。而且,以往国内在鲁迅对拜伦接受并改造方面所做的研究,也就是有研究者所谓“拜伦”的言说与被言说史,(21)黄静,王本朝 :《鲁迅的“拜伦”言说与被言说——〈摩罗诗力说〉“拜伦观”的接受史研究》,《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也都一贯是从思想上讲的,没有涉及到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的拜伦,也没有以此来对早期鲁迅进行阐发。所以,这里想通过对原文和材源的精细比勘,在译与作的缝隙间来描摹并解读一番。
(一)“固孕于野蛮”:对拜伦身份气质的改造——草莽绿林气的英雄形象
对于作为曾是晚清臣民的周树人来说,不论西方的实情如何,他所能理解的拜伦是有限的。所以,一个真实客观的拜伦并不符合鲁迅要塑造的“摩罗诗人”的形象,鲁迅需要的是撒旦式的人物,目的在于反抗统治者。以当时的日本来讲,不论是木村还是鲁迅,所描绘出的拜伦,首先是一个英雄形象。但是,与木村直接承袭西方拜伦不同,《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拜伦”具有不同于以往的蛮性,不再是具有贵族气质的英雄,而是尽可能地展现出一种草莽的绿林气。
作传先讲出身。鲁迅在文中交代了拜伦家族的斯堪的纳维亚“海贼”出身和迁居英国的家史后,对木村“材源”中所带有贵族字眼或含有贵族信息的内容,在简写的同时尽量做了删除。如对勘这句:
一千七百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拜伦夫人在伦敦霍尔列斯大街宅邸生下一子。即乔治·诺爱尔·戈登·拜伦,第六代贵族也。(木村材源)
裴伦以千七百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于伦敦……(鲁迅原文)(22)[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7页。
改变很明显:一是,删去了“第六代贵族也”,意在开始就不再强调其贵族身份,与前文突出的“海贼”呼应,以增强其反抗的凶悍性;二是,删去了如“拜伦夫人”“伦敦霍尔列斯大街宅邸”等带有贵族气和过于带有城市化气息的词语。
后来,拜伦反抗社会而责骂声四起,他不能再居于英国,去意已决后,有过一句自述,对勘如下:
“社会因何理由对余持有偏见,余更不解也。吾祖先系诺曼第贵族,协助威廉侵入英国,征伐英国,吾家有勋且高贵也。然今吾家名遭亵渎。设若世界批评正当,吾对英国无价值,设若其批评谬误,则英国对吾无价值矣。”(木村材源)
使世之评骘诚,吾在英为无值,若评骘谬,则英于我为无值矣。(鲁迅原文)(23)[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16-17页。
鲁迅删去了“社会因何理由……吾家名遭亵渎”两句。显然,拜伦不满于如今“吾家名遭亵渎”的现状,所以这里是述说“吾家名”不能遭如此亵渎的理由:一是入侵英国的功臣,二是“有勋且高贵”。鲁迅这里的改动,与上文对贵族身份的避讳是保持一致的。而且,笔者认为鲁迅删去这样的自述,对这种带有蛮气的英雄形象的塑造,更深化了其意义。因为拜伦的这种自述中含有一种不彻底的反抗心理,以为祖上有功,至少要被庇护,甚至存在《水浒传》中“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态,意在说明其对社会的不满,目的是为了让它变好,展现出的是一个忠君的谏臣形象。鲁迅这种做法受章太炎主办的《民报》中的排满思想的影响很大,排满在于推翻统治,目的是革命的,而非改良或保皇的,如果是木村拜伦的自述,则有了后者的倾向。删掉这两句以后,直面国家(或民族)这个抽象概念,且不再提及贵族身份,拜伦的革命形象便明朗多了。
可见,在对拜伦基本生平史实的译述中,鲁迅是要祛除拜伦的贵族身份并突出其海贼的家族背景,带来一股平民化的草莽气,以此来应和“摩罗诗人”的呼声。这一方面是源于鲁迅对主流一贯的挑战姿态,只有用这样一个带有强有力的蛮性的绿林英雄形象,才可以达到对正统的颠覆,具有反抗的彻底性。另一方面,这不能不说是鲁迅对一种原始的民间力量的汲取,正如他面对萎靡不振、老气横秋,且自以为是天朝上国的晚清政府及社会所开的“药方”一样:
尼佉(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獉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惟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发展既央,隳败随起,况久席古宗祖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其煌煌居历史之首,而终匿形于卷末者,殆以此欤?(24)鲁迅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我们如何看待鲁迅的这种删改?它的来源在哪里?很明显,如果鲁迅只以日语材料为媒介,在对拜伦的接受上是不可能有如此蛮性的形象被塑造出来的。难道是如一些日本学者所说那样,鲁迅在以日本为中介接受拜伦(以及尼采、克尔凯郭尔)的同时,直接“把握到了欧洲的近代,并将其作为与四千年的传统文明彻底异质的东西”,(25)[日]伊藤虎丸 :《鲁迅与终末论》,北京: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2008年,第26页。超越了在“日本中介”中的拜伦形象,而形成了一个较之他所接受的日本材源中的拜伦更接近欧洲原拜伦的拜伦形象。这种说法虽然极具启发性,可是终究属于想象层面上的“把握”,鲁迅作为一个青年和晚清的臣民,在他循序渐进的认知过程中,思想的跳跃程度是有限的,即便在其改译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异质”,在无法确证其接受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寻找的焦点转移到可能促使这种“异质”出现的来源上,而不是替鲁迅做凭空猜想。
我认为,对鲁迅译述中出现的“异质”,还应当从鲁迅所接受的日本材源之外的本土经验中寻找。在这一方面,中国固有的“侠”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很大,更大层面上可能是民间文化所带来的。“侠”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国儒、墨等不同文化形态中的精华,与西方的“骑士”或日本的“武士”等概念不同。首先,其中所蕴含的反抗性(“侠以武犯禁”)、正义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其韧性(“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些都是在少年鲁迅身上就已经有所体现的。(26)如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期间,对于邻近私塾先生对学生的过分体罚不满,就与自己的伙伴策划了对那位私塾先生进行惩罚的义举。参见周作人 :《知堂回忆录·四〇·贺家武秀才》,《周作人自选集·知堂回忆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其次,鲁迅对拜伦进行中国式侠士的塑造,本身就带有一种同构性投射,因为“侠”代表一种来自民间的、非正统的、底层的力量,而对于家道中落、从小康堕入困顿的鲁迅来讲,这种对拜伦身份平民化的改造,似乎是一种自我期许与内心隐幽的显现,也是处于鲁迅那个社会地位且有相似经历的人应有的精神气质。所以,在“鲁迅拜伦”那种原始生命力的构筑上,还有“侠”这样一种传统色调。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侠”,似乎更多的是在鲁迅之后才不断被学界描述和阐释出来的概念,也可以说和鲁迅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并不能说在被描述及阐述之前就没有存在,或者说在鲁迅身上不存在。这也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述的“存在主义”及“终末论”之于鲁迅的关系一样。
(二)以尼采塑拜伦:对拜伦精神的重塑———决绝而彻底的反抗者形象
历来研究者对鲁迅所认识到的尼采与拜伦之区别,都以《摩罗诗力说》总论(前三章)中所言为准则,即前者是“欲自强,而并颂强者”,后者是此“欲自强,而力抗强者”。(27)鲁迅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0页。这固然是二者的不同,但这是重塑之后的不同,后者身上的那种“力抗”的深邃与彻底,恰恰是从前者那里投射过来的,或者说是鲁迅在尼采身上找到了契合点,并以此代为塑造自己心中的摩罗诗人形象。
以当时中日两国的具体情况而论,在日本,木村译介拜伦所寄托的是一扫社会之糜烂、腐败、虚伪的颓气,意在改造;在中国,包括鲁迅在内的一部分人则意在革命,与清廷处于一个对立的层面。所以,木村拜伦与鲁迅拜伦在最终旨归上不同。这样一来,两个拜伦形象就具有不同的精神,在反抗社会带来冲击力的前提下,木村拜伦就成为一个不彻底的反抗者形象,而鲁迅拜伦则是一个决绝而彻底的反抗者形象。
或许可以这样说,鲁迅拜伦的身上带着深深的尼采烙印。其实就在鲁迅接受到拜伦的同时,在日本社会对尼采的接受更为深刻而普遍。(28)参见[澳]张钊贻 :《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7-182页。尼采 “超人”精神之果决,似乎是鲁迅注入到木村拜伦身上的一针强心剂,甚至可以说在有接受限度的条件下,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战士”,就是尼采所讲的“超人”。尼采是游离于拜伦之外的主角,乃至在《摩罗诗力说》全文中,如一个跳跃的精灵贯穿其中。所以,在有接受可能并转化的条件下,以尼采的精神来重塑木村拜伦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下面比勘文本。
拜伦帮助希腊独立之事历来被传为佳话,但是木村与鲁迅关于此事的叙述口吻,则有不同:
伦敦希腊协会委托拜伦协助希腊独立。拜伦虽素爱希腊,然见当时之堕落情状,略感失望。如恰尔德·哈洛尔德旅行时,叱希腊人为“世袭之怒”,为“自由苗裔之奴”,希腊之行亦略有踌躇,然希腊不可不救也。……拜伦接受希腊独立协会之委托,决往希腊。(木村材源)
比千八百二十三年,伦敦之希腊协会驰书托裴伦,请援希腊之独立。裴伦平日,至不满于希腊今人,尝称之曰世袭之奴,曰自由苗裔之奴,因不即应;顾以义愤故,则终诺之,遂行。(鲁迅原文)(29)[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30页。
细勘后发现有三处改动:一是,把“虽素爱希腊,然见当时之堕落情状,略感失望”改为“裴伦平日,至不满于希腊今人”;二是,把“略有踌躇”改为“不即应”;三是,把“不可不救”改为“顾以义愤故”。从“略感失望”到“不满”是一种态度的变化及情感的深化,因“失望”而有犹犹豫豫的所谓“踌躇”,相对应的被改为了因“不满”而态度坚决的“不即应”,这样的改动,使得从木村到鲁迅的拜伦形象明显在性格及精神气质上发生了变化。更巧妙的是第三处改动,二者的结果当然不违史实,可拜伦答应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木村是因为“踌躇”而说法暧昧,即“不可不救”,而鲁迅投入了决绝的态度,明确说“义愤故”。
需要另行说明的是,鲁迅对摩罗诗人的塑造,也是通过借用诗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完成的,将作品在译述过程中进行裁剪、加工,选择相应的内容,扩充到诗人的塑造框架中去。所以,就拜伦而论,对其作品进行译述的同时,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传内之传”,即讲拜伦生平及思想的同时,也穿插进拜伦作品中的人物,其实是另一个拜伦,是对“传主”的补充。(30)如上文所比勘的两段,其中木村原文中“世袭之怒”及“自由苗裔之奴”是拜伦笔下的人物恰尔德·哈洛尔德所言,在鲁迅原文中却直接被改为拜伦所言,这样一来,效果就更加不同了。正如拜伦戏剧《曼弗雷德》中曼弗雷德与精灵(神)的对话,木村和鲁迅的译述是不同的:
(曼弗雷德因为失爱而绝望厌世,辗转反侧无法排遣痛苦而想忘怀却不能忘时———笔者按)精灵出现问曼弗雷德曰:“忘掉何物,忘掉谁,又为何故?”曼弗雷德心乱如麻,思绪混杂,不知何故作答,谓精灵曰:“汝等鬼神,吾不坐祈祷,不作回答:欲知端详,请看吾之内心,吾不能将他说出。”“忘怀,忘怀自己———此即吾之所求。”……只要忘却心中苦痛,如何方能如愿?精灵曰:“惟有死亡方能忘却。”然曼弗雷德之苦恼竟至怀疑“死果能令吾忘怀乎?”(木村材源)
鬼神见形问所欲,曼云欲忘,鬼神告以忘在死,则对曰,死果能令人忘耶?复衷疑而:弗信也。(鲁迅原文)(31)[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17-18页。
鲁迅将一问一答处理得很简单,删去了曼弗雷德面对神的那种欲说还休、犹豫不决、吞吞吐吐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对于所要表达的反抗性的个人主义的主题有喧宾夺主之嫌,而且鲁迅删除后,又加了一句“复衷疑而弗信也”。从一再怀疑到绝不相信,态度是明确的,直指对神的反抗。
推敲这些细节(32)此类的例子在补校过程中还发现了不少,篇幅缘故,不再赘述。,可见鲁迅前后的处理是统一的,并不矛盾,其夹杂在“译”当中的“作”也绝非偶然,而是以自己的生命色彩对所译述人物的投射,如果关照鲁迅留日时的举动,就会发现,从断发到“弘文”纷争,(33)在东京弘文学院期间,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十二名官费留学生对学校的“十二条规定”中相关经费的部分提出质疑,并进行抗议,最终以胜利告终。几年后(1910年)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对于此次反抗显得颇为得意,他说“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鲁迅 :《101221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7页)。按,“加纳”指弘文学院的校长加纳治五郎,“三矢”即学校的教育干事三矢重松,“牛入”即弘文学院所在地名。再从“剪辫风波”再到弃医从文,彻底而决绝是他贯彻在行动中的精神底色。
(三)拜伦的温情影子:却步于极端的人性流露——兼说《摩罗诗力说》中的易卜生
正如北冈正子所阐明的那样,鲁迅与木村所共同推崇的反抗精神,最大的区别在于鲁迅的反抗是人道主义的。(34)[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4页。具体体现在《摩罗诗力说》中那个带有温情的拜伦形象,这似乎是在反抗之外,一种具有鲁迅内涵的灌注,以此才可以说是从“木村拜伦”到“鲁迅拜伦”的真正蜕变,而只是如北冈正子以“人道主义”来涵盖都显得有些笼统而简单了,似乎鲁迅不断在拜伦身上所刻画的细节,才是描述鲁迅拜伦之温情一面的关键,也是鲁迅生命个体投射的聚焦点。
如果细致对勘《摩罗诗力说》中关于拜伦部分的原文和材源,就会发现鲁迅在对拜伦的材源译述中突然插入一段关于易卜生的文字,它既非鲁迅自己所作,亦非木村《拜伦》《海盗》两本材源所载,北冈正子认为它“可能另有材料来源,但不知在什么地方”。(35)[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26页。这固然是鲁迅从别处抄译来的,但是就其安插在文章中的位置来看,笔者认为,这段文字如此突兀地出现在这里,必有蹊跷。所以,在鲁迅译述编排的层面上,笔者更愿意把它看做是鲁迅之“作”,先抄录如下:
此其所言,与近世诺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见合,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曰,吾又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36)[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26页。
这段文字所处的位置,正是《摩罗诗力说》中关于拜伦部分两段内容的中间(第五章开头)。联系上下文,会发现鲁迅将易卜生的材料看似很突兀地插入,实则是在对拜伦重塑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分水岭”的作用。前一部分明显还是一种尼采式的拜伦重塑,比勘如下:
拜伦詈社会曰:“由如此硗确不毛之地,吾人果能收获何物?吾人之感觉狭隘。吾人之道理微弱,生命短促,真理乃如深藏之宝石。一切事物据习惯至谬之权衡定之,所谓舆论实有全能之力。而舆论则以黑暗蔽地球,令善恶判断决于偶然。(木村材源)
其言曰,硗确之区,吾侪奚获耶?(中略)凡有事物,无不定以习俗至谬之衡,所谓舆论,实具大力,而舆论则以昏黑蔽全球也。(鲁迅原文)(37)[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26页。
有三处改动:一是,删去“吾人之感觉狭隘。吾人之道理微弱,生命短促,真理乃好深藏之宝石。”;二是,把“全能之力”改为“大力”;三是,删去“令善恶断决于偶然”。这里就显示出区别来了,鲁迅的改动在于所谓“上征”(38)“上征”一词,出自《楚辞·离骚》:“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一句,训为“上升”,这里引申为“向前、前进”之义。,是为希望考虑,且纵观文本中出现的五个“上征”,更传达着“一个民族在衰颓中所真正需要的那股涤荡的清气和上征时的凭借”。(39)刘锐 :《复古的心情:〈摩罗诗力说〉词汇在笺注学及符号学意义上的考释——以“庄骚”为例(上)》,《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翻译》(总第82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而木村引用拜伦的话,显然有一层悲观情绪在里面,认为面对“硗确不毛之地”,觉得自己感觉狭隘,道理微弱,生命短促,似乎面对这个难以改变的社会,一切都那么渺小。而且,对于舆论的描述,木村用了“全能”这个词,鲁迅改为“大力”。可见两人对舆论的认识及应对的信心也是有差别的:木村是显得悲观绝望,“全能”之外再没有个人反抗的余地;鲁迅改为“大力”,里面隐含了与舆论相对势力的描述,显然是对舆论之外的个人抗争注入了一股“上征”的力量。如“令善恶断决于偶然”,这样对木村拜伦的悲观有补充作用的话,也被删去了。这也是上文所说的鲁迅以尼采“超人”精神重塑拜伦的实例。
接着便是那段关于易卜生的材料。引述的是易卜生戏剧《社会公敌》中的医生斯托科曼的事,讲他如何面对整个社会向自己投来的强大舆论,即舆论再强大也并不可怕,关键是在与之对抗并不动摇的同时,不是以暴力抗争,不以此仇恨社会,反而坚持对社会投有一种温情。这似乎是鲁迅在拜伦之外真正认同的东西,而相反的一面确实存在于木村拜伦身上,是鲁迅极力想从木村拜伦身上割去的部分。但是,在译述过程中,面对木村留下来的关于拜伦的客观史料和作品,并不能做较大的改编,同时又要有所寄托,我想这是鲁迅插入这段“春秋笔法”的用意。
再往下看,鲁迅之后的改译,发生了一种策略性的转变,即此前面对木村的材源,鲁迅的改动和添加,都是向着有利于自己论述的方向进行,如身份、精神气质等都是按自己的标准处理的,但在插入易卜生的材料后,改译走向了与此前论述较为对立的一面,摆脱了之前自己塑造的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转而将拜伦及其作品中暴力、仇恨的一面展现了出来。鲁迅的用意很明显,他在易卜生的材料之后插了这样一句话:
顾裴伦不尽然,凡所描绘,皆禀种种思,具种种行。(鲁迅原文)(40)鲁迅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 卷,第81页。
面对无法做较大改动的材源,又要保证译述的相对客观性,鲁迅只能做出这种策略性转变,将关于拜伦的后一部分译述,作为一种自己排斥的反面教材,而用易卜生作为自己所要表达之内容的补充,易卜生的材料是正例,后一部分的拜伦材料是反例。这里所谓“禀种种思,具种种行”,除了把此前介绍的拜伦笔下人物的另一面译述了出来,如曼弗列特、康拉德、卢希勒飞为反抗而采取暴力并走向灭亡的部分,并且加入了此前因快乐主义和女性主义而被排斥的《唐璜》的内容。但是,所有这些几乎均指向一个方面,就是木村拜伦的不平哲学的最终结局——以暴力为反抗献身到最终死亡,即“为不平而死”,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破坏复仇,无所顾忌”,只为了一死,不考虑自身之外的其它。当鲁迅面对这种不可做较大改动的材源时,插入易卜生的材料,再采取反向的对拜伦的译述策略。笔者认为是在以这样一种转变来暗示自己心中的想法。因为作为一个反抗者,拜伦的结局并不是鲁迅心中期望的结局,但是拜伦作为鲁迅树立的摩罗诗人的代表,又不宜对其直接做出某方面的否定,所以在与易卜生的对比中,隐晦地给出自己的答案,即易卜生式的做法中体现出的韧性而持有温情、止步极端而远离暴力复仇这两方面,才是鲁迅的选择。
鲁迅到日本的第二年(1903年),便加入了在日本的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41)关于鲁迅是否加入光复会,林辰做过精当绵密的考证,结论是加入过。笔者完全赞成林氏的考证结果,并在此处引用以立论。参见林辰《鲁迅事迹考》,《林辰文集·壹》,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17页。当时的留日学生针对盘踞中国东北拒不撤兵的沙俄军队,组成了“抗俄义勇队”,同时也反清,后来日本警察接受清政府之请,将此组织强行解散,改名“国民教育会”,通称“义勇队”。1903年7月以后,这一组织“转变为以宣传、起义和暗杀为手段的革命组织”,就在该组织中诞生了后来的光复会。(42)[日]山田敬三 :《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秦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从光复会的前身可见其从发展伊始,就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反清团体,而身在其中且被认为是“坚决走革命道路的人士”的鲁迅,所做出的行动选择,可以与鲁迅对木村拜伦的重塑互证,在暴力所表现的走向极端之外,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鲁迅都有不同于时人的另一番考虑。据后来在上海对鲁迅执弟子礼的日本学者增田涉回忆,鲁迅在光复会中接受过暗杀任务,但是被他拒绝了,理由是大概会被捕杀,“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43)[日]增田涉 :《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页。这是即将要充当刺客的青年面对所预想的后果时心中的极大不安,也许他是在想,革命是不是就等同于死,死了以后与自己相关的人又该怎么办?从这些不安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作为一名革命者内心最深处的温情,这并不是革命不彻底,而是如何革命的问题。
所以,鲁迅在几年之后面对木村拜伦的形象时,将自身的选择与温情带诸笔端,与拜伦及其笔下的人物产生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删又不可,褒也不是,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改变自己的译述策略,在客观地呈现出拜伦及其作品中人物的暴力以及为革命赴死的选择时,插入了易卜生作品中医生斯托科曼面对社会压迫时那种“韧”的坚持,以此否定如拜伦般的“刚”的断裂。几十年后,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起自己所吃的鱼肝油和对敌的壕堑战法时,显得那么从容,自己活得更好更久是为了更好的论战,让论敌不舒服,而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如许褚一样的赤膊上阵很愚蠢,只能躲起来打,做“韧”的战斗。(44)鲁迅 :《两地书·四四》,《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5页。
这是作为晚清留学生的鲁迅所选择的革命方式,我们从留日时鲁迅对革命方式的选择和对拜伦形象的重塑上,可以看到一个止步于极端暴力革命行为的青年鲁迅,和他身上所带有的温情,正如新文学开端时他喊出的“救救孩子”一样,“救”才是鲁迅一生贯彻的主旨。如果说鲁迅摒弃了拜伦暴力的一面,而为他塑造的拜伦形象注入一股温情的话,关键就在于“救”。鲁迅拜伦与木村拜伦在反抗性上是一致的,都是“毁”,而他们的本质区别在另一个层面,即鲁迅拜伦是为“救”而“毁”,而木村拜伦就是为“毁”而“毁”,这正是因为鲁迅所裹挟的底色是温情。如对勘下面两句:
拜伦既爱为自由而战斗之华盛顿,亦爱蹂躏世界之拿破仑之大意志。(木村材源)
裴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鲁迅材源)(45)[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24页。
这里有一处词语的改动,即把“蹂躏”变为“毁”。我们只从词意的角度分析,就可知这个改后的词在句中的意义更丰富。“毁”相比于“蹂躏”,多了一层意思,即有“毁”就有“建”,“毁”在这里首先是变革(这在上文也论述过),这是鲁迅及当时的革命派最彻底的要求,在革命之后会有秩序的重建。而“蹂躏”的意义在这里明显很单一,固然也是一种毁坏,但并没有到变革的地步。所以,木村所谓“将无数苍生作自己欲望之垫脚石”,(46)[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4页。正是对这里“蹂躏”一词作的最好注脚。此外,木村所谓的“蹂躏”一词,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界对它存有一种普遍的接受,(47)当时日本的留学生报纸中,论及欧洲列强对弱国的侵略或其它侵略事件时,多会用到这一词语。如《印度灭亡论》:“凡一旧国而被数种族之蹂躏,其国民之元气已非百年不复”(《浙江潮》第一期);余一《民族主义论》:“及拿破仑起,张民权之帜,而蹂躏全欧。”(《浙江潮》第二期);《南阿独立英雄古鲁》:“汉忧匈奴,晋代则胡人入居中国,唐以后则契丹女真相继蹂躏。而求如岳武穆、仲山甫、文信国者,已如麟角凤毛。”(《游学译编》第七册)。引文标点为笔者所加。而之所以说鲁迅在晚清时对世界的认识水平高于当时知识界,从这些细微之处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通过以上分析,就会发现鲁迅对拜伦的塑造,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将人道主义温情注入到拜伦身上,另一方面又对拜伦生平及其作品中暴力的一面予以保留,使整个拜伦形象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张力正是鲁迅自身抉择的一种体现,是后来他关于革命策略的论述在其文本中最为原始的投射。所以,《摩罗诗力说》中拜伦身上那层若即若离的温情,是鲁迅附于拜伦身上的影子,只是长期被研究者们过于频繁的“摩罗”呼声所掩盖,而易卜生的作用也就连同在其间自动消融了。
可见,“鲁迅拜伦”在被塑造的过程中,种种细节所呈现出的正是当时鲁迅内心的隐幽与选择。在研究早期鲁迅文献匮乏的情况下,“鲁迅拜伦”这一形象所投射出来的,或许更接近鲁迅自身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