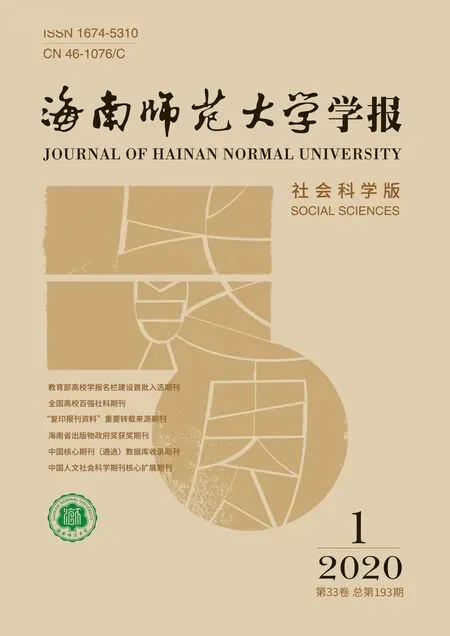黄宗羲人性论新探
刘聚晗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自古以来,吾华学人莫不以其人性论为基础而论学论治。孔子“性相近”肇端。其后,人性问题概有六说:性善说;性恶说;人性中既有善也有恶说;性无善无恶说;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不善说。在这诸多人性学说中,黄宗羲的人性论不容忽视。梳理其研究成果发现,学界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继承孟子以来的性善论,孙叔平、李明友、施扣柱、张师伟、朱光磊和贾庆军等学者持此观点(1)详见孙叔平 :《中国哲学史稿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6-307页;李明友 :《一本万殊——黄宗羲的哲学与哲学史观》,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5-54页;于述胜,张良才,施扣柱著,张瑞璠主编 :《中国教育哲学史》 第3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7-240页; 张师伟 :《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116页; 贾庆军 :《黄宗羲的“人”之辨》,《船山学刊》2011年第2期; 朱光磊 :《由“自私自利”通达“天下本体”——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人性论新解》,《福建论坛》2013年第5期。其中,施扣柱除看到黄宗羲继承孟子的性善论以外,还提及其将自私自利视为普遍人性的观点,但她并未看到“私”具有自然至善的本质内涵;朱光磊试图调和“私”的善恶兼备矛盾,将“自私自利”视为性善论背景下的自然起始状态。;二、属于自然人性论,侯外庐、任继愈、许哲民、冯天瑜、谢贵安、肖永明等先生秉该主张(2)详见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1页;任继愈 :《中国哲学史》 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页;萧萐父,许苏民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2页;冯天瑜,谢贵安 :《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0页;肖永明 :《明清之际人性自私说的启蒙意义》,《湖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这些学者看到了黄宗羲人性论的独特价值,惜未对其进行全面分析。笔者通过全面审视、深入探索,将黄宗羲的人性论归为自然至善说,并尝试对其作出合理地评价和定位。
一、宇宙本于至善:黄宗羲人性论的逻辑起点
黄宗羲关注人性,始于对宇宙本体的重视与强调。他从“一本万殊”的世界观出发,分析理、气、心、性之间的关系,总结宇宙本体的特性。
黄宗羲用“一本万殊”来阐释人与万物、人与世界的关系。他在《孟子师说·人之所以异章》中说:“天以气化流行而生人物,纯是一团和气。人物禀之即为知觉,知觉之精者灵明而为人,知觉之尘者昏浊而为物。”(3)[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人之所以异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在黄宗羲看来,人与物都是气之流行的产物,“一团虚灵之气,流行于人物”(4)[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尧以天下与舜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社,2012年,第123页。而成知觉。知觉为人、物共有之特质,然而二者仍有本质区别。由于气之清浊昏明不同,人既有知觉又有灵明,物只有知觉而无灵明。在此基础之上,黄宗羲得出结论:“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草木有草木之性,金石有金石之性,一本而万殊,如野葛鸠鸟之毒恶,亦不可不谓之性。”(5)[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道性善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7页。申言之,黄宗羲认为天地万物本于“气之流行”则同,呈现出的本性则万殊。
黄宗羲在其“一本万殊”世界观的前提下,以人为认识主体,讨论理、气、心、性之间的关系。对此,他说:
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夏,温衰而凉则为秋,凉盛而寒则为冬,寒衰则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6)[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浩然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依黄宗羲之见,人与物同体,都是“气”所生。以人为认识主体分析,“气”生“心”,“心”是“气”的灵处。该灵处之“心”不是岿然不动的寂体,而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在这一特定内涵的范围内,性即理。在理气关系上,就虚实角度而言,黄宗羲主张有气无理,气为实,理为虚,气流行不息,理即气之流行的客观规律。理气不是并存的两个物体,而是一物之两名。对此,他在《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二》的案语中进一步解释:“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7)[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二》,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8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5-356页。在心性关系上,黄宗羲继承自古以来儒学“天人合一”的逻辑,将宇宙之理气合一观延伸到人之心性合一观。他认为性即心之条理,见于心之运动中,不存在超然的、独立的性。在这里,黄宗羲借用主宰与流行这对范畴,将性与心对举,指出其是主宰与流行的关系,性是主宰,心是流行。主宰与流行、本体与发用不即不离。论证如下:
人身虽一气之流行,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即流行之有条理者。自其变者而观之谓之流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谓之主宰。(8)[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浩然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1册,第61页。
黄宗羲将本体理解为流行的存在,阐明了理气心性一元论。刘宗周虽提及该观点,但并无理论说明。黄宗羲则对此加以论证,不仅超越了乃师的理气心性一元主张,还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说。二程认为:“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9)[宋]程颢,程颐 :《河南程氏·粹言卷》,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第1227页。朱熹亦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10)[宋]朱熹撰 :《答张道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 第23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2755页。也就是说,程朱学派主张理先于气而存在,理是本,气是末;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在此基础上,程朱提出其人性二元论,这正是黄宗羲所批判的理一分殊说。
“一本万殊”,一方面是黄宗羲理气心性一元论的前提,另一方面是其判断宇宙善恶性质的理论基础。
关于宇宙,黄宗羲将它归为本于至善。他说:“浑然至善之中,万物一太极也,盖无处非大德敦化矣。”(11)[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君子深造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0页。亦云:“盖一阴一阳之流行往来,必有过有不及,宁有可齐之理?然全是一团生气,其生气所聚,自然福善祸淫,一息如是,终古如是,不然,则生灭息矣。此万有不齐中,一点真主宰,谓之‘至善’,故曰‘继之者善也’。”(12)[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道性善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1册,第77页。天地万物同本于太极之气,在未有天地万物之时,太极就具备浑然至善的性质。既生天地万物之后,万物成为至善的分有者。由于太极之气的阴阳流行变化,天地万物之性有过、有不及,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没有完全一样之理。但是,此“万有不齐”之中,一气相通,拥有共同之理则,即所谓的真主宰——至善。换言之,宇宙或曰太极本于至善这一真主宰。这就是黄宗羲宇宙本于至善的观点。
综上可见,黄宗羲从“一本万殊”世界观出发,提出宇宙本于至善这一基本思想。基于理气心性一元论,他把宇宙本于至善观作为论证人性自然至善的逻辑起点,一方面主张万物一太极,均属于大德自然流行之气;另一方面强调人得气之精者而成为自然至善之性体,表现出对生命本质的高度关注。那么,人性的自然至善具体是指什么呢?需对其内涵进一步探究。
二、人性自然至善:黄宗羲人性论的内涵解读
黄宗羲从宇宙本体论出发,在宇宙本于至善的理论支撑下,提出人性自然至善说。所谓的人性自然至善,其含义如何呢?他说:
凡人之心,当恻隐自能恻隐,当羞恶自能羞恶,不待勉强,自然流行,所谓“故”也。(13)[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天下之言性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7页。
虚灵不昧之性体也。为善去恶,只是率性而行,自然无善恶之夹杂。(14)[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7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其言性也,以为阴阳五行一也,赋于人物,则有万殊,有情无情,各一其性……人则惟有不忍人之心,纯粹至善(15)[清]黄宗羲 :《万公择墓志铭》,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17页。
黄宗羲认为人性自然纯粹至善。阴阳之气变化莫测,气之精者予于人。该至善之精气于人心自然流行,它会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而萌发恻隐之心或羞恶之心,不待勉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需率性而行,自然无善恶之夹杂。可见,黄宗羲的人性论与传统儒家学者相比别有新意。那么,什么是“自然”?什么是“善”?“恶”又从何而来呢?为了使自己的人性学说更具说服力,黄宗羲分别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内涵界说。
(一)“自然”的内涵界定
“自然”首发于老子,系其无为思想的体现,指宇宙万物自己的、最原初的状态。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6)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9页。河上公注解道:“‘道’性自然,无所法也。”(17)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第163页。吴澄说:“‘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别有自然也。”(18)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第163页。陈鼓应亦云:“道,纯任自然,自己如此。”(19)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第163页。“道”是老子哲学的专有名词,是万物根源。它化生万物而不遵循一定法则,故曰“法自然”。这成为后来道家学者的共同认知。可见,在道家眼里,“自然”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万物自立性的存在方式;其二,意为万物的自我生成、自我运动性的成长过程。
“自然”在老子发端之后,不断被后世儒者吸收、扩展并异化运用。它在历史流变过程中,“自然界”这一概念始终蕴含其中。当然,它与现代汉语中所说的自然界不同,是指排除了人间纷纭世故的某个清净雅致的地方。除此内涵之外,后世儒者将道家无为的“天地自然”变为社会秩序中“人的自然”。董仲舒首开其端。他说:“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莫之丧而自亡,是谓自然之罚。”(20)[西汉]董仲舒 :《春秋繁露》中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第209页。在这里,董仲舒将道家之“自然”世俗化,运用到人的意志与行动整个领域。此时的“自然”,已拥有了与主宰天相通的拟人化概念。于是,“自然”宿命性、非人力可为的意蕴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自然”与“天理”的融合。晋朝郭象注解《庄子·齐物论》时说:“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为人之所为。”(21)[战国]庄周著,[晋]郭象注 :《庄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页。其意盖谓,上下、尊卑的世俗等级秩序是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更改。郭象的这一“天理自然”观被宋代理学家广泛运用。程颐说:“人事胜,则天不为灾;人事不胜,则天为灾。人事常随天理,天变非应人事。”(22)[宋]程颢,程颐 :《河南程氏外书》卷第五,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4页。朱熹谓:“盖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23)朱熹 :《尽心说》,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第23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3273页。在这里,程朱只不过是想表达人的道德性是先天的、超验的意思而已。社会世俗中的道德伦理这一应然法则从而被当成自然之理。在此前提下,程朱将“自然天理”与人性结合,提出了其“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思想。所谓“天命之性”,是从天理中来的纯善人性。正如程颐所说的“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24)[宋]程颢,程颐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3页。,“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25)[宋]程颢,程颐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2页。。所谓“气质之性”,是秉气而成,随气之清浊、昏明的不同而有善恶之分的人性。即二程认为的“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26)[宋]程颢,程颐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页。朱熹继承二程的这一主张,并进一步加深二元人性之间的对立。他指出“天命之性”是出乎天理的道心,“原于性命之正”,是善的;“气质之性”是出乎人欲的人心,“生于形气之私”,是恶的。(27)[宋]朱熹 :《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在此基础之上,朱熹进一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教化主张。总之,“自然”一词被后世儒者异化运用后,已不再是道家的天地万物本然自然之意,而是具有封建道德伦理的宿命化、天理化之意。
程朱学派的自然天理观受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家的反对。元代以降,统治阶级利用程朱理学打造非人性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于明代达到高潮,从非人性特质逐渐走向反人性方向,弊端显现,问题重重。在此背景下,王阳明从批判程朱人性观着手,希望打破其自然天理观。他将天理移到人心,强调人心的主宰作用,提出“良知即性”观,“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28)[明]王阳明 :《传习录》,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年,第6页。“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29)[明]王阳明 :《传习录》,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49页。。虽然王阳明仍和程朱学派一样强调维护“天理”,即封建伦理纲常,但他从人类的人性自觉角度出发,仍不失为一种进步。
黄宗羲继承王阳明开辟的人性自觉思维路径,沿循程朱学派“自然天理”与人性论相结合的逻辑思路,重新界定“自然”内涵。他在《孟子师说·性犹杞柳章》中说:
第先儒言性即理也,既不欲以性归之知觉,又不可以性归之天地万物,于是谓性受于生之初,知觉发于既生之后。性,体也,知觉,用也,引《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以证之。静是天性之真,动是知觉之自然,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在人心,推原其上一层以为之性,性反觉于渺茫矣。告子不识天性之真,明觉自然,随感而通,自有条理,即谓之天理也,先儒之不以理归于知觉者,其实与告子之说一也。(30)[宋]黄宗羲 :《孟子师说·性犹杞柳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2页。
概括言之,黄宗羲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性存在人心之内,随感性认识自然融通为知觉。只有明了知觉自然而然、自有条理,才能真正认识“天理”。程朱学派将“理”与“知觉”分离,“推原其上一层以为之性”,犯了和告子一样的错误。
不仅如此,黄宗羲进一步解释道:
仁、义、礼、智、乐,俱是虚名。人生堕地,只有父母兄弟,此一段不可解之情,与生俱来,此之谓实,于是而始有仁义之名……当其事亲从兄之际,自有条理……不待于勉强作为……先儒多以性中曷尝有孝弟来,于是先有仁义而后有孝弟,故孝弟为为仁之本,无乃先名而后实欤?即如阳明言“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亦与孟子之言不相似,盖赤子之心,见父自然知爱,见兄自然知敬,此是天理源头,何消去存天理而后发之为事父乎!(31)[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仁之实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
一言以蔽之,黄宗羲从名实角度论仁、义、礼、智、乐(虚名)与孝悌(实有)之间的关系。他从分析此二者前名后实的关系出发,否定以程朱、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本末倒置的天理人欲观,确立自己的天理人欲一体说。黄宗羲认为天理与人欲由“自然”贯通而融为一体,自然而然又复归自然。为说明这一观点,他从修养论角度亦云:“盖此心当恻隐时自能恻隐,当羞恶时自能羞恶,浑然不著,于人为惺惺独知,旋乾转坤,俱不出此自然之流动,才是心存而不放,稍有起炉作灶,便是放心。”(32)[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仁人心也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41页。
总之,黄宗羲提醒人们不要人为干预,不要将天理、人欲二分,应顺从人性而自由发展。可见,黄宗羲所认为的“自然”,超越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超验之划分,乃是指万物的本然(静)与自然(动)状态,即它自古自始即如此的存在方式与运动形式。他的深层意蕴为尊重人的意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性“自然”的核心。
综上所述,“自然”在我国古代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它由道家天地万物之自己而然的原始义逐渐演变为儒家社会→道德→自然天理的延伸义。程朱学派秉持万物一体仁的思想,沿循儒学社会化的路径,将自然天理运用到人性论中。黄宗羲打破程朱理学的自然观,重新界定“自然”概念。黄宗羲所谓的“自然”,既是对其原始义的复归,又是对其原始义的超越,是明末清初特殊时代的产物。
(二)“善”的内涵界定
性善论由孟子发端之后逐渐成为儒学思想家的主流观点。很多学者不断阐释性善之内涵。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已。”(33)[宋]朱熹 :《孟子集注·告子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8页。在孟子看来,人性天生包含“仁义礼智”四大善端,非外部灌输,亦非后天学成。它内化于人,不会消失,是道德规范先验的存在,为人的行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是人异于禽兽之所在,即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34)[宋]朱熹 :《孟子集注·离篓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3页。。在孟子人性善端说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性分三品,以中名之”的人性观。他将人性分为斗宵之性、中民之性与圣人之性(35)[西汉]董仲舒 :《实性》,《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4页。,认为人性之“善”是指名教伦理。正如他所说的“性有善端,心有善质”(36)[西汉]董仲舒 :《深察名号》,《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9页。,“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37)[西汉]董仲舒 :《深察名号》,《春秋繁露》,第370页。。韩愈继承董仲舒的人性主张,倡导“性三品”说,认为人性之“善”包括“仁义礼智信”五方面内容。他说道:“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其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38)[唐]韩愈 :《原性》,《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李翱主张“灭情复性”的人性论,不再把人性之“善”当作仁义礼智四大善端,而是把它看作仁义礼智的完成。对此,李翱曰:“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39)[唐]李翱 :《复性书》,《李文公集》,《四库唐人文集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页。宋明学者依理气、心性而论人性之说愈繁,但无论是程朱理学派还是陆王心学派,亦或功利学派,他们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人性之“善”是指“仁义礼智信”五方面内容。可见,传统儒学思想家将性善的内涵归结为维护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
黄宗羲的人性论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学思想家的观点,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儒学千百年来的思维惯性,为人性之“善”注入了新内涵因子。
首先,在继承方面,黄宗羲沿循乃师刘宗周的思维理路批判程朱理学,打破了程朱理学的人性二元论。
刘宗周提出“性只是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对此,他说:
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所以为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当然,乃所以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识得心一性一,则工夫亦一。静存之外,更无动察;主敬之外,更无穷理。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慎独之说,而后之解者往往失之。(40)[明]刘宗周 :《语类》,吴光主编 :《刘宗周全集》第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1页。
这里,刘宗周认为“气”与“理”是统一体,“理”是“气”之理,存在于“气”之中。“气质之性”之外并无另一“义理之性”,“义理者”也就是气之所以然的理,即“气质之本然”。换言之,“义理之性”即气质中之性。此外,刘宗周又主张心即性,气质、义理是心性合一,从而提出理气心性一元论。这种观点不但否定了程朱的性二元论,而且也突破了王阳明心性体用的观点。
黄宗羲创造性地继承了乃师刘宗周义理之性在气质之性之中的说法,对程朱学派人性学说进行批评。他说:
程子“性即理也”之言,截得清楚,然极须理会,单为人性言之则可,欲以该万物之性则不可。即孟子之言性善,亦是据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之于物也,若谓人物皆秉天地之理以为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是。夫所谓理者,仁义礼智是也。禽兽何尝有是?如虎狼之残忍,牛犬之顽钝,皆不可不谓之性,具此知觉,即具此性。晦翁言“人物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不知物之知觉,绝非人之知觉,其不同先生乎气也。理者,纯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全!人虽桀纣之穷凶极恶,未尝不知此事是恶,是陷溺之中,其理亦全,物之此心已绝,岂可谓偏者犹在乎?若论其统体,天以其气之精者生人,尘者生物,虽一气而有精尘之判。故气质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在人虽有昏明厚薄之异,总之是有理之气,禽兽之所禀者,是无理之气,非无理也,其不得与人同者,正是天之理也。(41)[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人之所以异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35页。
黄宗羲直言程子“性即理也”之说有其局限性。它只可以言人性,不可以言物性。对主体的浑说是导致二程对孟子性善说形成错误认识的关键原因。“性即理”之所以不能针对物性,是因为假如按照程氏所说,人与物“皆秉天地之理以为性”,那么人与物理应同得其全或同得其偏。可见,程氏“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之说法颇具有逻辑错误。在黄宗羲看来,朱熹“人物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的说法亦有其不足之处,人与物都有“知觉”,只不过不同而已。“气之精者生人,尘者生物”,人禀受“有理之气”,物禀受“无理之气”,故人之性善,物之性有善有恶,“气质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
整体言之,黄宗羲通过批评程朱理学人性论,修正并超越其业师刘宗周的人性观,从而打破了宋明理学在人性论方面的论证体系。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其人性自然至善说,并明确人性“善”之一方面的内涵。
黄宗羲继承孟子人性善端说,重新界定人性之“善”。他说:“盖人之为人,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外,更无别心,其憧憧往来,起灭万变者,皆因外物而有,于心无与也。”(42)[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仁人心也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41页。换言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乃人性“善”之内涵。不仅如此,黄宗羲还从已发未发、继善成性的角度阐释其内在意蕴,主张性善是从未发之不变本体已发为完满之性善的过程。对此,他说:“在人亦然,其变者,喜怒哀乐、已发未发、一动一静、循环无端者,心也;其不变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梏之反覆,萌蘖发见者,性也。”(43)[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二》,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7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页。亦云:“如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虽然,未可以为善也,从而继之,有恻隐,随有羞恶,有辞让,有是非之心焉,且无念非恻隐,无念非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而时出靡穷焉,斯善矣。”(44)[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五穀者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3页。黄宗羲继承并发展孟子人性善端说,将恻隐之心作为性之根,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随其变化而变化的。由此可见,黄宗羲所谓的人性“善”,一方面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其中,恻隐之心是其根,未发之善端到已发之完满善的过程是其实质。
其次,创新方面,黄宗羲将自私自利之心作为人性“善”之内涵。对此,他说: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人之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己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45)[清]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原君》,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黄宗羲从政治角度论人性。他从以下两个维度来肯定人的自私自利之心:其一,人类从原始状态开始就是自私自利的,不谋求人类的公共利益,同样也不排除人类的公共危害。据此来讲,自私自利是人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是人之常性亦是人之常情。此时的“自私自利”,我们尚不能看出其是善还是恶,暂且将其归为非善非恶;其二,黄宗羲将古之“天下为主,君为客”与今之“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实况相较,得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己矣”的结论,并发出感慨与愿望:如果没有君主,人人可以实现自身个人利益,以君主的大公满足大众的大私才是立君之道与为君之道。此时的“自私自利”已显然属于善了。可见,自私自利之心是黄宗羲人性自然至善说中“善”之另一方面的内涵。需说明的是,这一内涵实质上是在肯定公平公正的公众之大私,而非个人之小私,尤其是非君主之私。
黄宗羲将自私自利之心作为人性善之内涵,并以此为基础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其首创。这种观点的深刻性、创新性超越了以往思想家的人性论。
中国传统人性论普遍对人性之私进行价值否定。先秦时期,孟子提出人性善端论,坚决否认人具有自私自利之心。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说,主张性恶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46)梁启雄 :《荀子简释》,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7页。可见,荀子虽然承认自私自利之心属于人性,但将其归为恶的范畴,予以价值否定。韩非子继承前法家人物管仲、商鞅、慎到的人性论主张,指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47)[战国]韩非 :《饰邪》,《韩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6页。。易言之,法家较荀子更为激进,明确主张人性自私,自私自利之恶性是应该被根除的。此外,主张兼爱的墨家与主张无为的道家同样主张贵公去私。墨子认为:“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子认为天下为父母、学者、君王者众,而仁者寡,皆不可以为法,故圣王法之。”(48)[战国]墨翟 :《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页。在墨子看来,只有无私的天才是可效法的对象。老子亦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49)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1页。由此可见,先秦诸子在“公”与“私”的实然义与抽象义方面也许有分歧,但是在其价值义方面却出奇一致,都主张贵公去私。《吕氏春秋》中用《贵公》《去私》两文来融会贯通先秦诸家观点。秦汉时期,诸思想家对人性之私的否定之势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其中,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0)[东汉]班固 :《董仲舒传》,《汉书》卷五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2页。之说成为后世思想家的共识。至宋代,随着理学的兴起,对人性之私的价值否定发展为一种较为成熟严密的理论体系。二程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51)[宋]程颢,程颐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第312页。朱熹云:“人心、道心之异者,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52)[宋]朱熹 :《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陆九渊曰:“私意与公理,利欲与道义,其势不两立。从其大体与从其小体,亦在人耳。”(53)[宋]陆九渊 :《与包敏道》,钟哲点校 :《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页。可见,程朱理学主张要以天理之公克服来自气质之性的人心私欲,即使主张“心即理”的陆九渊仍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无疑是对先秦以来“贵公去私”的进一步强化。与此相较,以李觏、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功利学派学者持有迥异观点。李觏为利欲正名道:“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54)[宋]李觏 :《原文》,王国轩点校 :《李觏文集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6页。陈亮提出公私合一论,云:“天运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55)[宋]陈亮 :《祭土道甫母太宜人文》,邓广铭点校 :《陈亮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1页。叶适对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持坚决反对态度,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56)[宋]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4页。在李觏、陈亮、叶适等人眼中,人性之私显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仍是需要克服的。正如陈亮所说的“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於法而不可御也”(57)[宋]陈亮 :《人法》,邓广铭点校 :《陈亮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4页。。总之,宋代功利学派曾为人性之私正名,但他们的观点并不彻底且被排除在主流意识之外。因此,总体而言,传统思想家对人性之私进行了价值否定。
此外,明中期以降,出现了一批具有进步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公开宣称“私”乃人之天性,应予以肯定。李贽从“人必有私”出发,肯定了人们追求私有财产、满足欲望的合理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58)[明]李贽 :《藏书·德业儒臣后论》,《李贽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26页。顾炎武从肯定人性之私出发,提出利用人的私心实现社会改革愿望的主张。即他所谓的“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59)[清]顾炎武 :《郡县论五》,华忱之点校 :《亭林文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60)[清]顾炎武 :《日知录》卷三,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1页。。可见,自明中期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对人性之私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看到了人们追求物质、生理等需求的正当性。但与黄宗羲相较而言,这些思想家没有对“私”这一概念作出界定,并将其归为人性善之内涵;更没有看到封建君主自私自利的本性是天下大害,把人性论作为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依据。因此,相比之下,黄宗羲的人性自私说更加全面而深刻。
总括而论,黄宗羲人性自然至善说中“善”之内涵既包括仁义礼智之传统意蕴,又包括自私自利之心的新因子。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黄宗羲创新思想的智慧结晶。既然黄宗羲将人的自私自利之心归为性善范畴,那什么是恶呢?
(三)恶从何来
黄宗羲认为人性虽自然至善,但由于气之过与不及、习之不同造成社会生活中人性善恶的表现形式各异。首先,他在《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三》案语中道:“窃以为气即性也,偏于刚,偏于柔,则是气之过不及也。其无过不及之处方是性,所谓中也……人性虽偏于刚柔,其偏刚之处未尝忘柔,其偏柔之处未尝忘刚,即是中体。”(61)[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三》,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7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20页。人性的外在表现有偏刚之时,有偏柔之时,形式各异,善恶掺杂,但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人性的本质“中体”。也就是说,人性本善,不包含恶。恶是气之过与不及之时于生活实际中的表现形式。对此,黄宗羲亦云:“通书云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刚柔皆善,有过不及,则流而为恶,是则人心无所为恶,止有过不及而已。”(62)[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7页。不仅如此,黄宗羲还借用乃师刘宗周的话说明其恶是习之罪的观点。他说:“先师蕺山曰:‘古人言性,皆主后天,毕竟离气质无所谓性者。生而浊则浊,生而清则清。非水本清,而受制于质,故浊也。水与受水者,终属两事,性与心可分两事乎?子谓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时而浊,未离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终锢于浊,则习之罪也。’”(63)[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道性善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77-78页。最后,黄宗羲总结道:“常人有常人之起作,学人有学人之起作。一动于纳交要誉,便是常人之起作,舍却当下;浅者求之事功,深者求之玄虚,便是学人之起作,所谓凿也。只为此小智作祟,凿以求通,天下所以啧啧多事,皆因性之不明也。”(64)[清]黄宗羲 :《孟子师说·天下之言性章》,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17页。“常人”与“学人”的生活方式不同,各有起作。他们若能各安其性、各尽其职,就会助社会秩序良性发展。天下之所以“啧啧多事”,是因为人们不能透过各异的人性表现形式明晰人性的本质。总之,黄宗羲主张恶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是气之过与不及;二是习之不同。人们不能明了这一问题,故将人性的善恶多样表现形式误当成了人性之善的本质。
扬善去恶是思想家的共同追求。然而,区分人性表现形式善恶的根本尺度是什么?评判主体又是谁?广大学者对此莫不绞尽脑汁,却又莫衷一是。
在第一个问题上,黄宗羲的答案具有历史的发展眼光。他曾言:“盖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气无穷尽,理无穷尽,不特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气为方来之气,亦不以已往之理为方来之理,不特气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65)[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河东学案上》,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7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黄宗羲将人之理与天之气纳入空间的平行互动以及时间的一维性之中,二者在时空中的变化是永恒的。申言之,黄宗羲认为,大德敦化,在空间上呈现出万物并育,理气均无穷尽的状态;小德川流,道并行而不相悖,在时间上表现为日新不已、无时而息的过程。因此,黄宗羲得出结论:“不以已往之气为方来之气,亦不以已往之理为方来之理。”从理气心性一元论的视角看,该结论运用到人性学说上可知,人性表现形式的善恶评判标准同样是日新不已的,应随时代而变迁,因地域、文化而有差异。即,人性表现形式善恶的根本尺度是能否符合社会时代变化发展的需要。
在第二个问题上,黄宗羲继承“心即理”观点,认为人心是判断人性表现形式是否为善的唯一主体。他说:“穷天地万物之理,以合于我心之知觉,而后谓之道。皆为人心道心之说所误也。夫人只有人心,当恻隐自能恻隐,当羞恶自能羞恶,辞让、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无有移换,便是允执厥中。”(66)[清]黄宗羲 :《尚书古文疏证序》,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5页。他反对道学家将人心、道心一分为二的观点。在黄宗羲看来,人只有人心,不存在道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人心本来应有的状态,不失此本心就会符合人性的本质状态“中体”。可见,黄宗羲把人心作为判断人性表现形式善恶的唯一主体,并尤为重视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反对人心之外的绝对、永恒之道德规范支配人心、戕害人性。
综上所述,人性自然至善说这一新释较全面地反映了黄宗羲人性论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性善论、自然人性论的内在局限。它以宇宙本于至善观为理论支撑,其思想内涵包括以下三层意蕴:其一,人性的本然与自然状态是至善的,它自古自始即如此;其二,它既包含仁义礼智的伦理之善又包括自私自利的人欲之善;其三,由于气之过与不及、习之不同,人性善的表现形式各异,善恶混杂。判断某种表现形式是否为善应以是否符合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尺度,以人心为唯一判断主体。总之,黄宗羲的人性自然至善说的本质是“自然”,核心是尊重人的意识,目标是教人向善。
三、贯通古今中外:黄宗羲人性论的历史意义
黄宗羲继承宋明理学家的思辨方式,从理气一元论的角度重新诠释人性。这不仅是古代人性论的一个高峰,还是对明末清初特殊时代的超前反映,更以其启蒙性特质成为近代观念之先声。
首先,与传统思想家相比,黄宗羲的人性自然至善说打破了其论证体系,更加尊重人的世俗本性,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哲学话语中,“性”属于“自然”范畴,是指天地万物自己的原始状态;“善”则属于“当然”范畴,是指天地万物应有之理,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故庄子说“性者,生之质也”(67)[战国]庄周 :《庚桑楚》,[清]王先谦 :《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53页。,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68)[战国]荀况 :《正名》,梁启雄 :《荀子简释》,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9页。,“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69)[战国]荀况 :《性恶》,梁启雄 :《荀子简释》,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7页。,孟子云“可欲之谓善”(70)[宋]朱熹 :《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0页。,董仲舒亦云“善者,王之教化也”(71)[西汉]董仲舒 :《实性》,《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6页。。黄宗羲一改前人固见,他的人性自然至善说将“性”与“善”看作“自、当一体”“自、当本合末离”。申言之,在黄宗羲看来,人性善既是自然的又是当然的,不仅是人应有之理,还是人本身自己的状态,是人之所以为人有别于他物的本质规定,故“自、当一体”。人性善是本,人性善的表现形式是末,其表现形式各异,故“自、当本合末离”。这打破了传统思想家的人性论证体系。此外,黄宗羲论人性的本质与外在表现,很明显看到了人的多元心理结构、个体生命生存状况与人性的关系。他所表现出来的以人为本取向,是对传统既定价值的重思和怀疑。自孔子将人性分为上智、中人与下愚三类以来,历代思想家都将人性局限在此道德规约上。这样的人性主张所包含的伦理关怀,缺少一种主体意向性指征,在价值上是不均等的,是对普遍人性关怀的伦理缺失。特别是程朱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来,存理灭欲的价值霸权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事实选择并不断流变。这种价值强加或价值依附是黄宗羲所深恶痛绝的。他公开宣称人性自然至善,无需他人着力,提倡意志自由,并主张用公众普遍之私心对抗君主一己之私欲。这种新颖的论证体系与公平、公正的人性观是传统思想家所不能比拟的。
其次,与同时期的思想家相较,黄宗羲与其他进步学者一样,对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做了超前反映,只是认知更加深刻。经济方面,随着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市民阶层突起,要求经济自由和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政治方面,封建专制政体日益加强、完善但积弊已深。由于统治者不知改造时弊,于是士人阶层开启了政治自觉。一些有识之士自由结社,与市民联合呼吁社会改革。思想文化方面,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达到顶峰,但因其对人性的制约而受到进步思想家的攻击。随着西学东渐思潮,耶稣传教士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传至中国。以利玛窦为主的传教士推行“学术传教”政策,进行“以儒释耶”活动。在此社会背景下,一些进步学者利用西学“以耶释儒”,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前提下借助天主教思想重构儒学。他们明确提出人性自私说,强调个体的价值与地位。黄宗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肯定个人私欲、利益的合理性,而且以肯定人性之私为出发点,对封建君主家国同构专制统治模式进行了批判,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理想;对培养人才的学校教育展开讨论,主张贯彻“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教育方针。这种提倡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改革思想是对明末清初社会现实的超前、深刻的反映,其启蒙性特质成为近代观念之先声。
依上所论,黄宗羲从理气心性一元论出发,以宇宙本于至善为逻辑起点,对人性自然至善说作出内涵界定。他一方面主张维系儒家传统道德伦理,以防人们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中迷失自我;另一方面高扬自我主体意识,解构专制皇权以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黄宗羲的人性论不仅为其政治学说、伦理思想及教育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还凭其超越传统思想家的近代性特质而成为近代观念之先声。其精神内核是以人为本、多元开放。这种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我国国民性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黄宗羲的人性论不仅对明末清初的人们具有重要引领和指导作用,还对近代甚至当代的我们提供重要借鉴价值。虽然如此,黄宗羲的人性论仍有其历史局限性。他的宇宙本体论与人性论仍是经验性质的推演,因此,有些论说难免存在逻辑错误,更无法用现代方法进行验证。黄宗羲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人性善,物性有善有恶,不接受万物平等的释道观点。这和其他儒士一样,有其狭隘之处。总之,黄宗羲的人性论有其历史进步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应辩证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