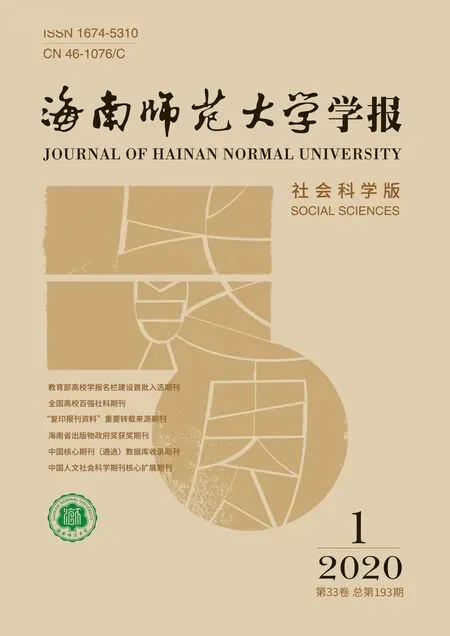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敞开性与混杂性
范云晶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20世纪90年代之于翟永明而言,既是一个变化显豁的创作阶段,(1)翟永明这样说:“80年代与90年代所写的作品,的确是我创作过程中一个明显的划分。”翟永明 :《完成之后又怎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又是一个承接80年代和新世纪创作的关键环节,具有“常”与“变”双重特征。就其作为节点的连接作用、所呈现出的写作实绩以及所蕴含的变化这三方面来说,这一阶段对于翟永明而言,尤为重要。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翟永明90年代诗歌写作的变化是多向度和多层面的,既包括写作技艺、语言特质、题材范围,也涉及观照视角、写作意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面向事物开口度的加大与意义表达的混杂。前者指诗歌表现领域的扩大,后者则涉及诗歌技艺与涵容的双重变化。这两大特质的获得,主要通过“转喻”语型的运用,“公共场域”勾连生出的多声部发音以及“我与非我”的人称混合等方式实现。这些表意方法的运用,实现了言说之物的扩展,完成了思想的传递和意义的表达,也使得翟永明的诗歌由内敛走向了外放,更具包孕万物的综合性诗意和更加开阔的表现空间。
一、以“转喻”语型为主导的意义扩展
20世纪90年代,翟永明的诗歌由80年代的“以隐喻和暗示为主导语型,深入而自觉地女性主义‘自白’倾诉期”转向了“采用转喻和口语的融合性语型,给激烈的情绪降温,将更广泛的日常经验、历史、文化,做‘寓言化’处理的深度命名‘克制陈述’期”(2)陈超 :《女性意识及个人的心灵词源——翟永明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隐喻”曾是翟永明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重要修辞手段,最具隐喻色彩的典型意象是“黑夜”,以及由此引出的“黑夜意识”。“黑夜意识”甚至成为女诗人的标签,基本可以涵盖包括翟永明在内的女性诗歌的整体样貌。“隐喻”之于表达效果的最大作用是“暗示”特征。“隐喻”与“暗示”为主的语型,恰好深度迎合了诗人当时的表达意愿,符合不吐不快,情感喷薄的需要。到了20世纪90年代,诗人的写作观念发生了变化,她渴望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向外部空间,试图触及和言说更多事物。诗人需要寻找相应的语型,采用更合适的语言方式,以实现言说愿望。转喻和口语为主的融合性语型,恰好满足诗人的这种言说要求。如果说隐喻指向纵深,转喻指向的则是所牵延事物的多与杂,最终实现了诗意的扩展与丰富。
台湾学者郑慧如对转喻的理解有助于对翟永明诗歌“转喻”语型的认知。“隐喻是代替,转喻是A和B并置后撞击出语词外的意涵;隐喻诉求意义的精确,转喻诉诸意义的流动;假如有不易判断的语义,隐喻造成模糊,而转喻所造成的则是歧义……”(3)郑慧如 :《语意的蔓延与逸轨——论诗的转喻》,《诗探索》2011年第2辑。相对于隐喻而言,转喻给诗歌带来的表达效果主要是勾连出更多意义的流动性以及歧义的生成这三个方面。这些在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中都有着鲜明地体现,主要表现为语义的并置与扩展,流动与变化,歧义与杂糅。
首先是语义的并置与扩展。隐喻更像是纵轴线,指向深度,而转喻则位于横轴线,指向多与杂。多与杂特征的生成主要借助词语对事物的转喻,从而与其他人物、事件以及场景发生勾连,然后借助联想能力,将这些不同层面、不同时空的事物并置和连接。在并置和连接的过程中,言说重点自然转向另一事件。所谓的另一事件,或者具有现场感,或者具有历史深度和文化寓意。在一个凸显事物代替另一事物之后,诗人往往还会通过能够与之形成毗连的事物,建立新的逻辑关系,将突显事物的意义转移到产生逻辑关系的事物上,从而牵出诗人真正想言说的多个事物和主题。简言之,就是用“间接表达法”来替代“直接表达法”。(4)[法]热拉尔·热奈特 :《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吴康茹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4页。
在《编织和行为之歌》中,诗人借助编织行为和编织声音的同一性,将两个人、两个时代、两个故事和场景并置。“我(翟永明——引者注)在这里将她的作品与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件‘行为艺术’并置在一起,因为她们都是女艺术家,也因为她们的作品都与编织有关。”(5)翟永明 :《九十年代诗一首〈编织和行为之歌〉》(2012年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8b17d40100pef2.html.而后又由两个牵延出第三个,甚至是与这两个相关的其余所有——由古代花木兰到现代编织者再到与爱情、艺术和战争有关的一切。最后,诗人又借助这些女性牵出了三个重要主题,即爱情、艺术和战争。通过毗连性特征,诗歌以由远到近的转喻方式,完成了与另一人物同样行为的转换、对接与并置。
《编织和行为之歌》先写了古代织布机的声音(唧唧复唧唧),然后写“两根编针切磋的声音”,这一声音的发出其实与手的忙碌行为有关,最后又由手的忙碌,引出了编织者。在一层又一层的意义衔接链上,诗人逐渐接近了诗歌的言说主体——具有编织行为的女性,然后再由此引起诗人想真正论及的话题。更具意味的是,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为主旋律的声音四次出现,每次出现的因由以及所引出之物既相似又不同:相似是诗歌所述场景都与这一行为有关,不同之处是引出的具体人和事。第一次是现代编织者。此时诗歌已经出现了转喻,诗人将古代声音转喻给现代人。第二次是花木兰。从表面看,这一次好像是在本义基础上的运用,诗歌内部却暗藏玄机。诗人通过相似性与对比性(相反性)两种并置方式,用想象的场景转喻了现实的场景,完成了虚实转换:真实的木兰必然会老去,但是想象中的木兰则会永远年轻。第三次是广义的妻子。诗人把吟诗和织布并置,两者即关乎日常生存,又关乎爱情;第四次是广义的女人。“那个女人”——“木兰”——“妻子”——“三个女人”,这四者之间暗含着意义的转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由此形成一种既“是”又“非”的确定中的模糊感,从而将这一问题的思考引向所有女性的命运。“唧唧复唧唧/两手不停∥她们控制自己/把灵魂引向美和诗意/时而机器,时而编针运动的声音/谈论永无休止的女人话题/还有因她们而存在的/艺术、战争、爱情——”。(6)翟永明 :《翟永明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28页。
当然,诗歌复杂意义转换链的形成还要借助多种表意策略来完成,比如用委曲迂回的方式逐渐接近言说中心。在将声音作为最初的转喻链开端的时候,诗人没有将其直接抛出,而是采用了先疑问后反衬的方式,最后才抛出了问题。这就使得诗歌在转喻链条的起始阶段,或者说转喻行为尚未发生之时,就已经暗藏了向其他意义向度延展的可能。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疑问具有持续性和递进性,诗歌整个言说向度的铺展和走向都是由此来主导。
其次是语义的变化与流动。因转喻而生成多种事物的并置,必然带来诗歌意义和言说向度的延展和扩充。这种延展和扩充使翟永明的诗歌富于变化性,从而打破呆板单一诉说的限定,具有流动性特征。以《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7)翟永明 :《翟永明的诗》,第163-169页。为例加以阐说。从题目上看,这首诗本身就蕴含多变可能,只不过是同一事物内部的变化,因为不管是多少种方式,都还是按摩方式。但是深入诗歌文本就会发现,这些方式不单单是针对按摩而言,诗歌是由按摩的几种方式开始,最后牵出的事物比按摩行为本身多得多。
这首诗至少存在三个主题或者更多主题的交叉。最直接的主题是按摩师的工作。诗人重点提到的“按摩”“针灸”“拔罐”等行为都是按摩师的基本工作环节;稍微递进一层的主题是需要按摩的病人身体的不适。诗人将按摩与人的身体联系在一起,通过容易出问题或容易损伤的身体重要部位,将主题从“按摩”转移到了对“身体”的关注上。比如,“腰”“骨椎”“头部”“神经”“肌肉”等词语的出现。第三层主题是经由按摩师的技艺和“我”思维的带动,诗人将按摩身体的行为(对于身体疼痛的缓解和疗治),转喻为其对存在之痛的洞察,而这已然超越了身体之痛。“疼痛”将上述三个主题串联到一起:盲人按摩师因为疼痛而实施按摩行为;人们需要按摩是因为身体“疼痛”;盲人按摩师所解决的问题是身体的“疼痛”。在对“疼痛”的体验与认识这个问题上,盲人与我们相同又相异,“他的两手推拿世间的问题/盲人有盲人的方式∥他思索下手的轻重缓急/与我们的方向一致”。诗歌中的“他”具有两副面孔:他们与我们一样也要承受各种“疼痛”;他们又与我们不同,仿佛是洞穿一切的“世外高人”,能够直接参透生命的秘密,指出事物的实质问题,“他的手掌熟知全世界的穴位/他的手掌兼修中西两种功力……一男一女,两个盲人/看不见变易中的生死/看得见生死中的各种变易”,起到了扩展和加深言说意义的作用。
借助“疼痛”,诗人将肉体之痛转化为内心之痛与生命之痛,并一再深入推广,最后变成一种更具形而上意义的存在之痛。“我知道疼痛的原因/是生命的本质,与推拿无关/但推拿已进入和谐的境界/盲人一天又一天敲打/分享我骨头里的节奏。”这一将主题和言说中心引向更深层面的诗句,其实生出了诗歌的反题——诗歌题目原本是推拿,但是此处却说“与推拿无关”——这种是与非、肯定与否定的转换,正是转喻语式的独特功用之一——“转喻因边界而来的组合因而可能漫无止境,或和谐,或反逻辑”。(8)郑慧如 :《语意的蔓延与逸轨——论诗的转喻》,《诗探索》2011年第2辑。在言说中心不变的情况下,意义向四周延伸,变得漫无止境、丰富多样,增加了诗歌的张力与包容力。
最后是语义的歧义与多解。由并置所引出的意义变化与不确定,最终带来了翟永明诗歌在意义理解上的扩展、歧义和多解。《潜水艇的悲伤》可称为歧义与多解的典型范例。从题目上看,“潜水艇”本身就是一个寄托深层寓意的核心词。同时,其所承载的多重转喻功能同样不可忽视。在大方向上,“潜水艇”一词与写作有关。“笔墨”以及“写作的潜望镜”透露出这一深意。“开头我想这样写”“于是我这样写道”“从前我写过 现在还这样写”,这几个具有“提示”作用的句子,表明了翟永明对于“写作”本身的综合性和本体性思考:写什么、怎样写、写的意图以及通过写来表现什么等。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写作理路的调整以及对于写作认识的矛盾心态。诗人想要寻得的是穿透事物表面,触及生存真相,探及事物内核的有效写作方式。上述三个具有提示功能的句子标明诗人是在思考写作问题的同时,引出了更多的现实。“国有企业的烂帐 以及/邻国经济的萧瑟 还有/小姐们趋时的妆容/这些不稳定的收据 包围了/我的浅水塘”,甚至是“追星族”“迪厅的重金属”等等,(9)翟永明 :《翟永明的诗》,第242页。都指向了当下消费社会的欲望。
由于所指内容的多样,“潜水艇”以及“水”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之前的“潜水艇”,来自于诗人的想象。诗人所能看穿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主观臆想中的现实,因此这样的写作注定无效、甚至越来越远离现实。诗人想改变和制造的“潜水艇”是具有穿透力和摩擦感的有效写作,是在现实基础上的一种提升,是“穿透现实”的“超现实”。由于“潜水艇”意义的变化,与之相配套的关键词“水”的意义也具有两种。诗人由之前对“水”的深信不疑,变为了对“水”的怀疑,进而要自己“造水”。无论是“潜水艇”功能的变化,还是对“水”的态度的变化,都表明了诗人试图调整写作路向,实现有效写作理想的决心。
诗人找到了写作的路向,但对“现实”的认知还存在疑问。因为这关系到诗歌写作的真正功效。诗歌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纯粹的再现和摹写,更多是极具个人特征的“自我创造”:在直面现实、不回避现实的基础上,一种尊重现实,并超越现实的具有穿透力的写作方式。“现在 我已造好潜水艇/可是 水在哪儿/水在世界上拍打/现在 我必须造水/为每一件事物的悲伤/制造它不可多得的完美”。(10)翟永明 :《翟永明的诗》,第243页。这首诗歌融现实批判与写作反思于一体,是彰显翟永明个体生存困境、精神困境与写作困境的综合性文本。诗人触及到了对于写作和现实之真假的深层问题,颇具形而上哲学意味和辩证思考意味。
并置与扩展,流动与多变,歧义与多解,凸显了翟永明诗歌转喻语式的多种表意功能。三者互为因果、互相激发与拉动:意义并置与语义扩展带来了诗意的变化与流动;语义的流动与多变又使诗意变得歧义与多解。“转喻的叙述性流畅的语言,使诗人做到了视角与心灵,语态与心态的合一。”(11)陈超 :《女性意识及个人的心灵词源》,《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第184页。被言说的不同事物,在并置关系中纵横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这种平行中的交错,纠缠中的平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诗歌言说的广度和深度,诗意的密度也得以增加。
二、“公共场域”作为“媒介”的时空拓展
进入20世纪90 年代,翟永明实现了对以自塑自怜为特征的私人空间的突围,开始向公共空间位移,并形成了新的“空间意识”。翟永明坦言这种改变的缘由,是女性诗人向酒吧老板兼诗人身份的转变(12)具体论述可参见翟永明等:《黑夜诗人的变化与坚持——翟永明访谈录》,《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0期。。无论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选择,与封闭和相对恒定的私人空间相比,公共空间的主要特点是敞开性、临时性以及多变性。这三种特性的具有,主要与公共空间所涵纳的人事的不定和多变有关。三种特性使公共空间在作为诗意生发初始和结束的终极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媒介”作用的“中介”特质。它更像是一种装置,或者说临时场所,容纳不同的人、事、物轮番进入。“中介空间”特征不但打破了翟永明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二维特征,而且改变了其言说向度,成为破解这一时期诗歌意义谜团的关键。
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中的公共空间大致包含两大类:一是具有“被看”特质,长于虚拟、想象与虚实转换的舞台空间;二是适合交流和交往的现实公共空间。“舞台空间”与“现实公共空间”具有诸多共性:首先,两种空间都是半独立、半敞开,兼具公共性和独立性。“舞台空间”就舞台自身而言是敞开与虚构的,供人观赏;后台则是封闭和现实的;“现实公共空间”对于某个人而言,在个别时段(这个人在此空间时)具有独立性和封闭性,同时它又可以任人自由出入。这就为在这些空间上演虚构与现实、个人与他人的故事提供了方便。其次,这两类“空间”不受现实时空限定,具有时空延展性。前者不受现实时空限定的原因在于舞台的虚拟性以及表演性,虚实结合特征使其能够做到时空交错;后者不受时空限定的原因则在于容纳人物之多。一方面在现实存在的人物身上可以上演不同的现实故事;另一方面通过联想和想象,将此时此地之外的人与事纳入其中。最后,这两个空间都可以借助诗人的局外人视角,以自我回忆或展望,以及对他人的经历想象的方式完成超现实时空的延展。
首先是舞台空间。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中,出现了很多直接或间接与戏剧和舞台有关的优秀诗作。《脸谱生涯》《祖母的时光》《孩子的时光》《道具和场景的述说》都是如此。诗人通常借助舞台及舞台上的道具,以及戏剧特有的客观性与间接性等突出特点,来实现这一表意诉求。正如袁可嘉所说:“戏剧效果的第一个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出好戏是依赖某些主要角色的冗长而带暴露性的独白而获得成功的。”(13)袁可嘉 :《论新诗现代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5页。戏剧性及其自带特质的引入,使得诗歌中的舞台空间兼具直接呈现与间接表达双重特性,有利于完成想象与真实、时间与空间的转换。
《道具和场景的述说》关键词在于“述说”二字,不只是道具本身的述说,还包括观众与舞台上演员的间接述说。这一诉求的实现不是依靠人的直接表达,而是通过物将情感与思想传达出来。舞台上的“道具”,即,鼓、琴、幕、台、扇的直接表现与间接述说作用,皆因其作为舞台之物的属性而存在。道具的作用从大方面来说有两个:一是舞台上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道具对演员情绪的渲染、故事情节的推进以及舞台效果的增强;二是舞台下的作用。道具连接的是台下的观众,其所传达的和观众所理解的涵义或达成完美契合,或发生裂痕。如果理解的涵义契合,那么台上台下两个表面看来分裂的世界,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如果理解的涵义存在偏差(意图谬误),那么台上和台下恰好构成既同一又分裂的世界。在或同一或分裂的两种可能性中,诗人想表达和试图传达的,得到了充分的呈示和展现。概言之,这些道具有一种将台下观众深藏于心的故事引出的神奇作用,它串联了过去与未来、现代与古代、虚构与真实。台上虚拟世界和台下现实世界被勾连在一起,彼此引燃,彼此牵延。比如诗人笔下的“鼓”:
鼓声滚过 如白色的急雨/如私密的耳语/它首先进入高烧和发痛的耳膜∥能疾能徐的诉说/能轻能重的爱抚/仿佛这声音已不再是/聆听者周遭的击节∥(现在,谈谈鼓/谈谈鼓中的阴阳/连环的击放/鼓师的腕力几乎举不起/一缕清嗓的高亢/两根手指的豪情涤荡)/这声音在聆听/急风中的所有节拍/并伺机加入孤独而冒险的/清澈的冰雹(14)翟永明 :《翟永明的诗》,第144-145页。
在描述鼓声特点的同时,诗人又以现代小说中常用的“元小说”的方式,现身于诗行,将这些道具自身可能具有的延展意义直接说出来。这就形成了两种表达效果,诗人既是沉浸其中的抒情和叙说者,又是客观冷静的旁观者。这一表意方式是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最鲜明的变化,也是最显豁的特点。诗人的这种看似理性的分析和补充,并没有跳脱之感,反而增强了这些道具意义的延展性、勾连性以及情感烘托作用。“现在,谈谈……”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增加了诗歌真实性的同时,又加强了道具的言说与联想功能。诗歌中仿佛有两个“翟永明”在打架,更准确地说是博弈:一个是诗人的、感性的、听从内心的翟永明,她在此处扮演诗歌叙说者的角色;另一个是作为局外人、理性睿智的翟永明,作为诗人的纠正和补充,将其拉回现实。诗人进出诗歌的两种状态,不妨看作是为了匡正20世纪80年代自说自话表达方式的一种有效策略与尝试。
其次是以交流与消费为特征的公共空间。这类空间主要包括咖啡馆、酒馆、茶馆、舞厅、电影院、公园等等。《咖啡馆之歌》《乡村茶馆》《去过博物馆》《小酒馆的现场主题》《莉莉和琼》《游泳池边》都是典型诗作。身处这样的空间,人们会因对自我社会角色和身份的短暂抽离而卸下伪装,展现出与原来的不同。这种不同因同一个人的不同侧面,和不同人的多个侧面的融合,而具有多面性和多变性。同时,诗人也由单纯的自述者变为亲历者和旁观者,或以看客身份客观评价他人的故事和事故,或以主角身份被他人言行勾起自我思想的神游,或以配角姿态进入与他人交往的空间,构成了极为复杂的意义场域。“有人在看/有人在被看/没有人错过/灵魂的一幕幕上演”。(15)翟永明 :《翟永明的诗》,第153页。
在《咖啡馆之歌》中,诗人将故事发生地点设在了异乡(曼哈顿) 的咖啡馆,时间是下午、晚上和凌晨三个不同时间段。不同性别、不同国别之人,因为“咖啡馆”这一作为媒介的临时空间而被捏合在一起:讨论着“乏味的爱情”的“我们”;来自外州,过着“萎靡不振的田园生活”的夫妇;操着“纯正的当地口音”的“你”;“谈着伟大的冒险和奥秘的事物”的“他”和“她”轮番登场,在交谈论辩中,或悲伤、或回忆、或慨叹,用不同声部合唱了一曲“咖啡馆之歌”:
邻座的美女摄人心魄/如雨秋波/洒向他情爱交织的注视∥没人注意到一张临时餐桌/三男两女/幽灵般镇定/讨论着自己的区域性问题∥我在追忆/北极圈里的中国餐馆/有人插话:“我的妻子在念/国际金融……带着所有虚无的思考/他严峻的脸落在黑暗的深处/我在细数/满手老茧的掌中纹路带来/预先的幸福(16)翟永明 :《翟永明的诗》,第115-116页。
“在一个封闭空间和一个特殊时刻,人是最松弛的。也是最真实的。这是对人性洞察和描摹的最佳角度。”(17)翟永明 :《在克制中得寸进尺——与木朵的对谈》,《完成之后又怎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4页。每个人的不同思想和不同行为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早已涨破“此时此刻”咖啡馆这一固定时空限定,具有容纳更多事物和扩展更多诗意的可能:不同的人和事以及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突然出现在同一时间和空间,诗人以拼贴的方式,将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并置,无形中扩展了诗歌的意涵;对于每个人而言,他们戴着面具伪饰的疲惫现代人的多面性被激发出来,得以在咖啡厅这特殊空间展现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同样是一种扩展。诗中的“我”作为旁观者,可以自由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既在这一时空,又不在这一时空。“我”人在咖啡馆,却可以通过思绪的飘忽不定,以想象的方式回到过去;“我”的思绪还可以“飘”到咖啡馆以外的地方,最后还可以回到咖啡馆。需要重点强调的是,这种拼接与捏合,并不是事物之间毫无关系的生拉硬扯,而是具有一种勾连关系的交织与融合。“我”的双重身份以及“这是我们共同的症候”,“我已经习惯/与某些人一同步入地狱”(18)翟永明 :《翟永明的诗》,第116—117页。的具体表达,已经鲜明显现出不同人、事、物的综合性言说与融合特征。
通过舞台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媒介”作用,诗歌实现了三重扩展:一是真假与虚实的黏合与转换。虚实与真假既同一又不同,人性的复杂得以彰显;二是跨时空的错位与对接,不同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与融合,诗意的复杂性得以彰显;三是诗歌与现实关系远近的缩放。通过诗人与现实关系远近的变化,“在日常经验与回忆中建立了奇异的互补关联”(19)周瓒 :《论翟永明诗歌的声音与述说方式》,荒林,王红旗主编 :《中国女性文化》第一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258-259页。,现实的复杂性得以彰显。
三、“多角色”混合与“多声部”发声
20世纪90年代,翟永明把眼光从自我封闭世界投向了外部世界,诗歌中出现了更多“我”之外的“他者”。与20世纪80年代诗歌不同:“他者”不再只是诗人主观臆想和借助想象自我构建出来的“虚构物”,而是具有独立性且有生命的个体;“他者”也不再处于与“我”相对甚至“对立”的立场,而是与“我”相异或相似的“实存体”。诗人以“对话”和“潜对话”的方式,客观冷静地观察并试图与“他者”进行交流和沟通。“他者”虽然以群体的方式进入翟永明的诗歌书写领域,但是作为言说主体的诗人并没有缺席,而是以隐在的方式,将自己的声音混合在他者的声部之中,构成了这一时期翟永明诗歌的“多角色”混合与“多声部”发声特征。
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翟永明采用了类似于小说全知全能视角的远距离观察方式,适合近距离审视的第二人称视角,以及擅长内心剖白的“第一人称”内视角,这三种视角融合的综合性观照方式。在综合性观照世界时,不同观照视角和人称之间随着叙述的推进而自由转换与异变。“我”通常扮演双重角色:或者作为事件的参与者,“我”在其中;或者化身为躲在诗行背后的清醒的“旁观者”,将他者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我”在其外。诗人一方面不放弃自我思考和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又需做到客观,冷静与克制。在表意效果上,“我”既是隐在的,又是现身的,形成了“我”是“我”,又不(只)是“我”;“你”是“我”,又是“你”等诸如此类的“我与非我”的混合。这可看作是翟永明为了避免20世纪80年代以“我”为绝对言说中心强行发声的全新策略。
借助“我”与“他者”的混合发声,翟永明完成了由“我”到“非我”的转变,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他者”身上所显现的生存现实,也完成对自我更加本质化的揭示与再认识。“我”与“他者”互为启发,互相审视,隐藏于人性和生存底部的真相得以呈现和揭示。正如欧阳江河所判断的那样:“属于叙述声音中的他者声音,其现身使作者的自我描述声音一下子变得无名无姓、面目全非,难以被单独辨认和倾听。这也许正是作者(即诗中的主要叙述者)想要面对的一种局面:主要叙述者可以用‘他者语言’来叙述,也可以将自我中隐而不显的部分交给这个‘他者’代现,从而完成自我形塑。”(20)欧阳江河 :《词的现身:翟永明的〈土拨鼠〉》,《站在虚构这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55页。
1992年,翟永明创作了诗歌《壁虎与我》,至少昭示出三个“新质”:一是诗人与“他者”走向了沟通、交流与对话;二是我与“他者”的关系既是观察与被观察,同时也是彼此激发;三是通过对“他者”的观照,“我”完成了自我审视。此后,这三种新质愈加鲜明。此处采用整体观照的方式,进一步对翟永明诗歌这三个新质进行剖析与阐说。
首先是“我”与“非我”的交织与转换。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中的“我”,一方面是叙述者,另一方面可能是诗歌中的角色“我”,还可能包含着“你”“她”或者“他”,“依然是‘我’的人称,但此时我已成为一个客观的陈述者”(21)翟永明 :《完成之后又怎样》,第29页。。所以,翟永明诗歌中的“我”既是我的单纯指称,又是全部人称的组合,具有既单一又混杂的双重特性。
诗歌《脸谱生涯》由“舞台”勾连起了两个世界,也完成了“我”与“你”的角色互换。“舞台”所具有的表演功能,使得“我”是“我”,又不是原来的“我”。由于“脸谱”的作用,“我”具有一定的伪装性,真实的“我”隐藏在脸谱之后。随着“脸谱”被摘下和戴上,“我”的形象也在变化。在脸谱的作用下,我与你完成了角色互换,“我”甚至变成了“你”,即戏中之人。真与假在这一过程中变得虚虚实实,暧昧不明。戴脸谱的“我”和摘脸谱的“我”,演绎不同人物的人生。“偌大的夜晚是我的背景/我是我,不是脸谱中的你”;“你,几乎就是一缕精神/与你的角色汇合/脸谱下的你?已不再是你”。(22)翟永明 :《翟永明的诗》,第159-161页。在这种转换中,“我”已经因分不清虚实而无法确认“你”的存在,也无法认清你,更无法认清自己。“我”与“你”的真假同时被揭示出来,通过“我”确认“你”,通过“你”来映照“我”。这种映照所带来的结果有两个:一方面是“我”与“你”的多面性格揭示;另一方面也使双方变得不是更加清晰,而是更加复杂,并由此揭示出人性以及生存的复杂。
其次,是“我”与“她”的映照与交织。20世纪90年代,女性仍然是翟永明关注和执意书写的对象,但是这里的女性已经不再是以“我”为绝对言说中心的个体,而是更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的“她”或者“她们”。“她(们)”在翟永明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比如《塔》《迷途的女人》《三美人之歌》《时间美人之歌》《祖母的时光》《十四首素歌》《她也叫丽达》《剪刀手的对话》等等。在这类诗歌中,翟永明一方面意在言说“我”是“她”,通过“她”来透视“我”;另一方面又表示“我”不是“她”,“她”在“我”之外,“我”对“她”在进行近距离沟通或远距离观察的同时,“我”和“她”又都是“她们”的一员,属于同一阵营与群体。
在颇具寓言性的诗歌《塔》中,翟永明说出了“我”与“她”的复杂关系。具有封闭和囚禁特征的“塔”,将女性分成了两部分,“塔里的妇女”和“塔外的女人”,两者在互相审视的同时,也存在身份互换的可能。而同时,两者又作为一个整体,在“你”的观照中现身。《塔》颇具寓意地展示了“我”与“她”之间的关系:“我”与“她”互相审视,也可能互相转换;“我”与“她”又是同一类人,看“她”又何尝不是在“看我”。
书写女性命运时,诗歌中“始终有一个‘我’存在,我(翟永明——引者注)实际上把个人的命运与其他的历史或现实的女人的命运放在一起加以考虑”。(23)张晓红: 《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叙事组诗《莉莉和琼》,看似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在讲述莉莉和琼的故事,“我”仿佛是缺席的。但是到了诗歌的第九节,也就是最后一节,“我”却以高调姿态现身,讲述“我”与莉莉的关系,同时也就揭开了“我”隐藏在莉莉和琼身后,偷偷打量以她们为代表的女性命运以及芸芸众生的事实。“我独自站在直街横街的交点上……我身旁匆匆走过的美貌男女/他们褴褛的衣衫或华贵的服饰/是每天的风险/与我毫无干系/但我站在这个横竖的点上/多少足迹已与我纠缠不清”。(24)翟永明 :《翟永明的诗》,第141-142页。《时间美人之歌》中,诗人借助时间因素,把“我自己的时间段和‘美人’的时间段通过写作,融合到了一起”。(25)翟永明 :《完成之后又怎样》,第46页。《十四首素歌》是作为女性的“我”与同为女性的“她”(母亲)之间的潜对话。20世纪90年代以后,诗人又将这一视阈扩展至古代,创作了《鱼玄机赋》,显示出对女性命运的深度思考和对自我的深入审视。
最后是“我”与“他(你、他们)”的交织与转换。这里的“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确作为“她”之对应面的男性“他”;另一种是超性别的“他”。所谓超性别,是指诗人并没有明确指明“他”是谁,或者说到底是“他”还是“她”并不重要,而只是作为与“我”有关或无关的他者存在。诗人在处理这对关系时,与处理“我/她”关系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从性别上说我可能是“她们”中的一员,“我”与“她”可以互相转换,我与她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可能,虽然两者是不同的个体。但是“他”对于“我”而言,永远只是“他”。此时“我”对于他者的描述,不再具有对抗性和带有明显性别对立特征的主观色彩,而是心平气和地、客观冷静地陈述我眼中的他(们)。在叙述语式上诗人由独白变成了对话,不再是自怜或者自傲,而是以平和心态与他者进行对话或者潜对话;单一的抒情也变成了克制内敛的叙述。在情感上,诗人有客观的评价和观感,也有作为朋友的主观欣赏;有警醒、有反思也有批判。无论哪一种态度,都是出于理性的审视与客观判断。
诗歌《友人素描》对“他”和“她”都有所书写。诗歌中提到了包括“他”和“她”在内的四个友人,建筑师友人、动力学友人、图书馆友人以及艺术家友人。从表达意图上来说,我与“他”与“她”的关系在诗人看来并不相同。“他”只是作为“我”之外的他者存在,而“她”则存在与“我”同属一个群体的可能。写到建筑师友人“他”时,诗人这样说:“他们与我同住这一空间/他们 以及那些建筑体的神情/都在表明/他们仅仅是 阴霾天空下的/性爱之身”(26)翟永明 :《终于使我周转不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页。;谈及图书馆友人“她”时,诗人则这样表述:“我们该怎样 应付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吸进去就像吸牛奶/吸进去就像吸进/大量的化妆品 并确保/我们的皮肤/泛出青白的颜色”。(27)翟永明 :《终于使我周转不灵》,第21页。这恰好昭示出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我”与“他”和“她”之间交织或转换方式的不同。
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中,人称大量混用的因由与对于意义表达的优势,学者们总结得非常精到。敬文东这样说:“人称不是随便使用的,在某些时候——尤其是在人们的说和写之中——它有着相当的致命性。一个人使用什么样的人称来说话,同时也就表明了他的立场和态度,也表明了他观察世界、进入世界的角度与方式。”(28)敬文东 :《从“静安庄”到“落水山庄”——诗人翟永明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所谓的“致命性”是指对于写作成败与意义传达好坏的决定性作用来说。就翟永明这一时期的整体诗歌创作来说,人称大量混用以及彼此之间的转换应该是成功的,它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诗人向外敞开与向现实开放的诗学诉求,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揭橥了诗人面对现实与生存时,所产生的内心的纠缠与矛盾。“诗人隐身而让几个不同的声音‘说话’,这些不同的声音在争辩也在复调式平行共响,它们都是诗人灵魂中几个不同的‘我’的体现。它们的不同话语和意识,是诗人共时承受的内心矛盾的展示。”(29)陈超 :《女性意识及个人的心灵词源》,《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第185页。
以“转喻”语型为主导的意义扩展,“公共场域”作为“媒介”的时空拓展,以及“多角色”混合与“多声部”发声这三种表意方式融合在一起,构成了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敞开性与混杂性特征,彰显出翟永明不断求新求变与突破自我的诗学追求。敞开性与混杂性虽然作为翟永明一个阶段的诗歌文本特质存在,但是其意义又不止于此。当代著名诗评家唐晓渡在谈到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戏剧化”方法运用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她(翟永明——引者注)总是着眼于由写作行为所牵动的经验主体和语言现实之间既相互敞开又彼此隐匿、既相互澄清又彼此遮蔽、既相互诱导又彼此遏制、既相互同化又彼此异化的复杂关联展开其探索意向,以始终保持住问题及其难度。”(30)唐晓渡 :《谁是翟永明》,《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此处,唐晓渡论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经验主体与语言现实间的复杂关系,而敞开与混杂恰好是这种复杂关系的准确命名。从这个角度讲,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表意方式不仅是单纯的词语以及由此形成的表意效果,也不单单关乎诗歌创作,而更多与创作主体本身的精神向度密切相关。诗人既敢于呈示真实内心与精神本真,又勇于自我修正,并不断实践。正是这种源自个人内心真实的写作态度与写作诉求,才使得她找到了现实与诗歌写作的最佳契合点,并创作出既具有鲜明个人诗学特质,又具有时代症候的优秀文本。如此,她才会坦诚地说:“我想我不会有意识地去营造诗歌中的时代感和现实的使命感。因为个人的人生经验总是包含在时代和历史中,而时代与历史又是人类个人经验的总和。只要我在写,我的写作就与时代和历史有关。”(31)翟永明 :《完成之后又怎样》,第165页。这也是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敞开与混杂特质的更大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