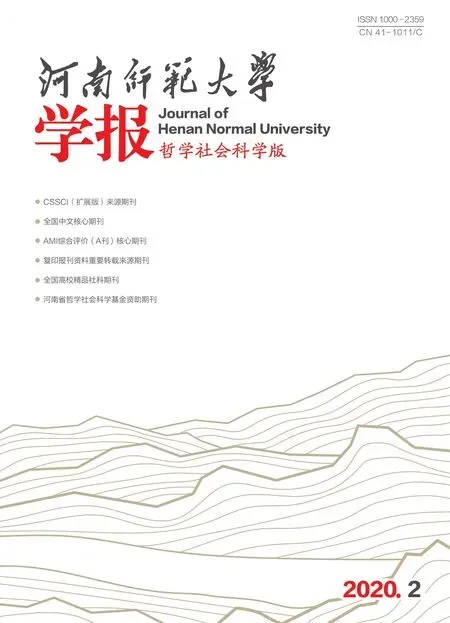妇女无名:明清山西碑刻题记女性研究
姚春敏,丁雅琳
(山西师范大学 华北区域文化研究中心/戏曲文物研究所,山西 临汾 041004)
碑刻作为第一手资料,包含着许多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信息,往往能补正文献记载之不足,是研究民间社会史的宝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碑刻题记是碑刻须臾不可分割的部分,位置多处于碑文后部、碑阴与碑侧部位,内容主要有创修人员题名、工程及刻碑开支以及补记等,意在永为记耳。现存山西碑刻题记中有大量关于女性的记录。据不完全统计,在笔者收集的近万通明清时期三晋碑刻中,有五分之一是与女性相关的碑刻。这部分内容很少有人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前人在传拓、整理碑刻时,只注重碑阳正文内容,而对那些主要记录捐施名单等内容的碑阴和碑侧的题记则不大重视,题记中的女性更容易成为被忽视的对象,从而湮没不彰。
本文以笔者数年田野调查收集到的山西女性碑刻题名为中心,尝试研究明清山西民间社会中女性署名的基本状况。首先,对女性碑刻进行整理归类,将碑刻中的女性题名加以梳理,借以探明清时期山西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建设的状况。其次,以统计学的方法,对女性碑刻做数字化整理和深层次剖析,结合社会史学、民俗学、经济学以及宗教学,对碑刻题记中的女性做进一步探究(1)因为是题记中的女性研究,所以本文并没有把墓志铭和贞节牌坊的碑铭纳入其中。。然后结合同一时期的小说以及诗文集中的女性进行分析,客观评述“妇女无名”的现象。由于三晋地域辽阔,各地差异较大,借以研究问题的资料又主要来源于笔者十年来田野调查中发现和整理的碑刻及近年来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恐有片面性,因此一些分析难免有偏颇、疏漏之处,还望同仁批评指正。
一、女性独立资助庙宇、道路等公共建筑的修建
明清时期,在三晋民间地方事务的建设上面,女性帮助男性(包括丈夫和儿子)修建庙宇、道路、水井及桥梁等公共设施的情况,屡屡见于碑刻记载。如明景泰年间《重修观音阁碑记》:“有李翁文旺者,系本村人也,平日存心长厚,好为舍施,目击心伤,不能自安。兼之善妻氏。”(2)《重修观音阁碑记》,明景泰七年(1456),现存山西省离石区交口镇石盘村圣母庙。明万历年间《玄天祖师庙募缘碣》:“洪洞县娄村里韩家庄村北,今新建立玄天祖师上帝老爷楼台神庙一座。主修竖造香老李尚虎、室人郭氏。”(3)《玄天祖师庙募缘碣》,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现存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韩家庄。再如清雍正年间《重修观音阁碑记》:“自起工以来十年有余,李翁之失妇不知几废其心思,几竭其财力,朝夕不安寝。兴不宁,然后倾者竖之,圮者补之,颓者坚之,坏者修之,庙貌正侧依然如故。”(4)《重修观音阁碑记》,清雍正十年(1732),现存山西省汾西县加楼乡李庵庄观音阁。此类碑刻均记载了妻子或者母亲协助男性修建公共设施的情况,数量众多,不赘列。
明清碑刻文献中反映女性不借助男性,而是靠自己的力量修筑庙宇的亦有30余通。如明万历年间的《修建玄帝庙记》:
万历丙申岁三月有三日,会玄帝圣诞之辰,本山善氏杨、赵二姓素耽善事,襄然欲修葺焉。遂语人曰:“善在人为,奚论男女?”乃普化四方善信家,得其所资,于正殿妆塑玄帝神,东殿妆塑药王孙真等神,西殿妆装塑子孙百子等神。兹迩工完,请余为记。余惟洪濛判而万物各有所统,庙貌建而神灵各有所司。矧玄帝敕镇人间善恶风化,所系药王活济生民命脉攸关,子孙锡胤,广嗣宗祀,所赖二氏拳拳注意于斯,盖知重哉!(5)《修建玄帝庙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现存山西省泽州县大阳镇西山村玄武庙。
由上文可见,此玄帝庙为杨、赵两位妇女提议修造,碑文中甚至直接发问:“善在人为,奚论男女?”两位女性不惜四处化缘才得以修葺如此宏大的工程。虽然碑文的书写者为男性,但也折服于两位女性的勇气,特意在碑中感谢“所赖二氏”。提议修建庙宇的女性,大部分是中老年女性,俱为人祖母、母亲与妻子者。如《重修河东庵记》载:“北祀三教,东祀关圣贤。稽其始,盖万历八年本镇乡绅张号鸿盤之祖母受封□人李氏创修焉。”(6)《重修河东庵记》,清顺治五年(1648),《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阳城县卷》,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再如《重修极乐庵经理碑记》:“有已故才宫王一室,妻李氏年几七旬,孀居好义。出资□□□□,为之□而乐施者继之。”(7)《重修极乐庵经理碑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89页。除了女性以独立身份推动庙宇的修建以外,明清时期的女性还组织各种“会”与“社”,她们自任会首与社首来承办宗教活动。如明代万历年间山西阳城白衣菩萨会和另外一个不知名的会,参与者全是女性。从碑刻看,白衣菩萨会女性成员均来自一个大家族,23位女性全是王门某氏,会首为“王门李氏”,显然是个世家大族(8)《白衣菩萨会碑记》,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现存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另外一个无名会参与了本村阎王殿的捐款,参与者姓氏比较庞杂,有王门某氏、茹门某氏、张门某氏、杨门某氏等,会首是李门郭氏、赵门郭氏、裴门张氏和张门王氏(9)《重修阎王殿碑记》,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现存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郭屿村白云观。。
另外,明成化年间《重建清泉寺碑记》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维那头女善人:李妙缘、□妙纪、 笛妙善 、弓妙览、孔妙顺、张妙全、樊妙通、郭妙善、常妙德、李妙通、张妙慧、燕妙云、姚妙得、段妙庆、索妙云、鲁妙善。”(10)《重建清泉寺碑记》,明成化七年(1471),现存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存和川镇安上村。“维那”是佛教用语,此处的“维那头”相当于会首。清代乾隆十一年《海潮庵重修碑序》载“遂推孟门焦氏、刘门张氏、刘门王氏等作社首”(11)《海潮庵重修碑记序》,清乾隆十一年(1746),《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城区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乾隆十四年《建立香亭碑序》载“□□村念佛会领众女善人等贾门李氏、贾门张氏”(12)《建立香亭碑序》,清乾隆十四年(1749),《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黎城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77页。。这种女性成立组织完成宗教任务,不独碑刻中多有记载,明清小说中也曾经多次出现。比如《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八和六十九回,专门描写张、侯两个道婆自己当会首,组织了80名妇女进香团,骑驴坐轿,行程200余里,到泰山顶上娘娘庙烧香(13)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中华书局,2005年。。碑刻与小说记载的相似性恰恰说明清代女性独立结社的普遍性。
二、女性姓名的书写方式与排序
在近千通女性题名碑刻中,女性姓名较为普遍的书写方式为某门某氏,数量占到了一半以上。目前发现单个碑刻中以某门某氏方式书写女性数量最大的是山西省晋城市的《海潮庵重修碑记序》(14)《海潮庵重修碑记序》,清乾隆十一年(1746),统计来源于现场,碑现存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临泽村,海潮庵已不存。,共有462位某门某氏的捐款名录。另外一通碑刻《濩泽南关明道厢崔家巷创修观音堂碑记》共计有248位某门某氏捐款名单,其中出现了7位某宅某氏:“赵宅□氏、□宅李氏、□宅刘氏 、吕宅司氏、黄宅薛氏、□宅□氏、□宅李氏。”(15)《濩泽南关明道厢崔家巷创修观音堂碑记》,清乾隆五年(1740),《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城区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某宅某氏的书写方式应该是某门某氏的一种变体。此外,先写男子之名,然后在其后加“室”,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作法。如“功德人吴进原,室张氏、李氏,男吴纪,室张氏;功德人李进广,室冯氏、杨氏,男李文,李进孝,室任氏,男李淳,室郭氏,孙男李□”(16)《重修圣母庙功德碑》,明景泰七年(1456),现存山西省离石区交口镇石盘村圣母庙。。再如,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玄天祖师庙募缘碣》:“张天相、室人韩氏;李应芳、室人韩氏;韩守暹、室人王氏;韩希周、室人师氏;韩廷益、室人张妙善;张邺臣、室人韩氏;韩廷臣、室人乔氏;李时定、室人王氏;张大岗、室人梁妙善;张大林、室人段氏;李仲收、室人乔氏;张大松、室人乔氏;张秉科、室人樊氏。”(17)《玄天祖师庙募缘碣》,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现存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韩家庄。都属此类情况。
另一种较为普遍的书写方式是某某氏,如张李氏、王杨氏等。此类书写方式数目颇多,约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重金装南殿三大士诸佛神像碑记》:“王燕氏银二钱、姬郭氏银二钱、姬柳氏银二钱、姬李氏银二钱、姬杨氏银二钱、杨姬氏银二钱、姬王氏银二钱……姬吉氏银一钱、姬程氏银一钱、姬吉氏银一钱、韩杨氏银一钱、马姬氏银一钱、李成氏银一钱、赵段氏银一钱。”(18)《重金装南殿三大士诸佛神像碑记》,雍正十三年(1735),现存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凤城镇汉上村佛堂。此类碑刻存量较多,恕不赘列。不过,以上某门某氏以及室人某氏的称呼明代均大量存在,而普遍意义上的“某某氏”的称呼却要晚很多。从目前所见山西碑刻来看,最早出现在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广泛流行开来,比学界普遍认为的这种称谓只是在清朝中期以后才成为文书中已婚女性的最主要称谓方法要早数十年(19)阿风:《徽州文书所见明清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博士论文附录。。
除了以上这些数量较多的书写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数量不多,但是极具代表意义的书写方式,如:
女善人 靳妙善粮二石 薛妙真、张妙善银五分 秦妙惠银五分
女善人 侯妙会丝三两 景妙清银五分
苏妙惠 董妙会 苏妙贞 曹妙真 郝妙善银五分
王妙贤米一斗 王妙善帽一顶 张妙绿 李妙善 任妙会米一斗(20)《重修三教庙碑记》,明嘉靖五年(1526),现存山西省隰县黄土乡谙正村老君庙。
这通碑刻题名中出现的女性姓名皆冠以妙善、妙清等宗教字眼,这样的碑刻目前发现了近30通。明成化年间甚至在碑刻题名中出现了整个家族女性全有妙字的现象。“功德施主在城太坊善士李友谅同室人孙氏妙清、长男李厚、男妇梁氏妙喜、长女李妙然”(21)《琵琶院创造释迦佛三大士共成缘记》,明成化十四年(1478),《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城区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33页。这些女子应该都是在家的居士,有专门法号。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到清代数百年间,山西从南到北,碑刻中几乎所有有名有姓的女性全出现了“妙”字,这一点在河南、河北和陕西的同期碑刻中并不多见。
除了以上几种女性书写方法以外,还有些较为小众的书写方法。如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增建三官庙碑记》“姬崇盛妻张氏银一钱”(22)《增建三官庙碑记》,清同治十一年(1872),现存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凤城镇汉上村三官庙。。从碑刻题名来看,姬氏家族捐款人数众多,唯有姬崇盛一人以妻子的身份捐资,可以推测张氏的丈夫姬崇盛可能遭遇不幸,才由妻子来替自己捐资。另外还有一种夫妻同时出现在碑阴中的表述,道光七年(1827年)《重修东岳庙记》有:“徐明文钱五百文,妻宋氏钱二百文。”(23)《重修东岳庙记》,清道光七年(1827),现存山西省黎城县东阳关乡辛村东岳庙。另有:“张世岗银四钱,妻银二钱四。张禄银三钱,妻银三钱。王仕鹏银三钱,妻银二钱五。张世兰银三钱,母银二钱五。岳玉□银三钱,妻银二钱。张□银二钱,妻银二钱。张许银二钱,妻银二钱五。”(24)《创建真武庙并花果圣母庙碑记》,清雍正十一年(1733),《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平顺县卷》,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133—134页。以上这种书写方式看不到妻子的姓氏,但是明显可以看到妻子与丈夫所捐银两截然不同,甚至有些妻子捐款数目超过了丈夫,这意味着丈夫与妻子均以独立状态向庙宇捐资,从而说明在清代一些女性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而且可以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庙宇和公共事务的捐资。
在现有碑刻资料中,还出现了一通多种女性姓名书写方式并存的碑文,如乾隆二十一年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府城《重修关帝庙碑记》,碑文有某门某氏、女善、某氏多种书写方式:
刘门冯氏捐银十两 南社门氏谷三石 西郜村杨捐银二两
贾四女善银二两 东尧庆捐谷□斗 山头银一两五钱
磨山库银一两五钱 东□众善钱一千 海潮庵捐谷一石
鲁村邢捐银一两 河西众善谷八斗 七岭店捐米五斗
刘门李氏银一两 南大社钱八百□ 王台铺麪店钱七百五十文
万家庄谷七斗五升 十字阪捐钱七百 王门张氏捐银一两
常门李氏一钱 水北捐小麦五斗 保福谷六斗五升
北寨捐谷五斗五升 南渠女善谷五斗
……
林炳文施看墙石□□□ 黄头女善捐谷四斗五升
焦新芳施钱一千二百 张天兴施谷一石 司宗施钱八百
赵子濯施银一两 张世强施钱七百 续金扬施谷五斗
张天明施谷五斗 水北女善捐谷五斗 赵应才施银五钱
赵府成施银五钱 秦大悦施银五钱 林谦吉施谷四斗
丰安女善捐谷四斗 王在兴施谷四斗 续长寿施银五钱
……
宋氏 宁氏 秦氏 张氏 张氏 张氏 张氏 裴子旺 祁氏 母氏 原氏 段氏 李氏 宋氏 李氏 贺治巳 潘孝 焦全江 高氏 张氏 李氏 牛正高 杨浩 郎氏 张氏(25)《重修关帝庙碑记》,乾隆二十一年(1756),现存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府城关帝庙。。
林林总总的碑刻题记中,对老年妇女的记载最为认真和翔实,一般会直接点出她的母亲身份,且是独立身份。如《重修菩萨庙碑记》“女善人:时秋母、邦孝母、□□母、勤书母、邦洗母、宗国母”(26)《重修菩萨庙碑记》,明万历三十年(1602),《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襄汾县卷》,三晋出版社,2016年,第113页。。又如《封赠王同春母孺人御制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疏恩将母,弘推锡类之仁,移孝作忠……江南提调学政按察司佥事王同春母,赠孺人”(27)《封赠王同春母孺人御制碑》,顺治十八年(1661),《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沁水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除此以外,更为常见的书写方法就是加“太氏”或者“娘娘”,如“张大宅太氏陈银一两,王二宅太氏张银一两”(28)《泽城西南隅五里许□南社重修庙宇楠塑金粧碑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现存山西省晋城市城区西上庄社区庞圪塔村玉皇庙。,“怀仁王四娘娘马氏,老四府娘娘孙妙庆”(29)碑额为“从善如登”,乾隆三十四年(1769),现存山西省寿阳县清平村九江大王庙。,等等。
另有数通比丘尼捐款的碑文,表述方式如同比丘。如《重修龙岩寺记》载:比丘尼真性施金六箱(30)《重修龙岩寺记》,明正德十年(1515),现存山西省霍州市李曹镇秦家岭村龙岩寺。,又如《濩泽南关明道厢崔家巷创修观音堂碑记》,主持比丘尼真性,同徒如祥,徒孙性芳、性容、性禄、性成(31)《濩泽南关明道厢崔家巷创修观音堂碑记》,清乾隆五年(1740),《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城区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但也有碑刻题名中的女性书写仅为笼统表述,如“众女善人化谷五担”(32)《泽城西南隅五里许□南社重修庙宇楠塑金粧碑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现存山西省晋城市城区西上庄社区庞圪塔村玉皇庙。,并无具体女性姓名。另外,康熙四十二年重修圣公圣母祠的活动中,妓女崔凤捐献了五百钱(33)《重修圣公圣母祠碑记》,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现存于山西省临汾市蒲县东岳庙。,也被记载于碑刻中,且排序依照所捐数目而列,并未刻在最后。
三晋碑刻题名中的排序一般是按照捐资数量多少排列。当碑阴中有男性捐款、女性捐款、男性外化银两、女性所化银两时,碑刻在排列顺序上并没有严格排出男女的不同位置。如:
常盛号 杨登福 武张氏各施银一两 杨汉祯 武士阳各化施银一两
王斌 武宁邦 武昌盛 霍天福 武深 贾玉贵 武成望 武恭蘸杰 武在德各化银一两
杨学稳化施银九钱六分
王贵 武来 王代位 武王氏 魏登禹各化银九钱六分
杨汉智 武斗全 武斗银 籁天有 王俊各化施银七钱四分
武凯 武世安 魏登顺各化银七钱二分
武秉公 贾万智各化施银二钱二分
马旺财 苏焕 马李氏 武可清 梁庆元 苏起福 武稳 杨盛各化银六钱
魏全富化施银五钱 魏登智施银五钱 马付氏 武世里 武成功 贾玉美各化银五钱(34)《真武庙重修碑记》,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现存山西省皮影木偶博物馆。
同时,碑刻中也并没有先男后女的排列,而是依照捐资顺序严格排列:
张荣喜室人闫氏男虎小子、淲子、四小子、黑小子、虎小子妻李氏施银五两
张明祉室人张氏男添职、添德施银二两
许养氲室人闫氏男正宜妻张氏施杨树一朱(株)施银一两
刘门冯氏捐银十两 南社门氏谷三石 西郜村杨捐银二两
贾四女善银二两 东尧庆捐谷□斗 山头银一两五钱
磨山库银一两五钱 东□众善钱一千 海潮庵捐谷一石
鲁村邢捐银一两 河西众善谷八斗 七岭店捐米五斗
刘门李氏银一两 南大社钱八百□ 王台铺麪店钱七百五十文
万家庄谷七斗五升 十字阪捐钱七百 王门张氏捐银一两
常门李氏一钱 水北捐小麦五斗 保福谷六斗五升
北寨捐谷五斗五升 南渠女善谷五斗 赵庄小麦四斗五升
彰冻小麦三斗五升 崔庄捐小麦三斗 水北村捐谷五斗
柳树库银六钱四分 魏家河库张银六钱 刘门刘氏捐银五钱(35)《重修关帝庙碑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现存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府城关帝庙。
大量碑刻记载让我们断定,明清时期的山西民间,当女性与男性的捐款同时出现时,极少有碑刻因为性别因素而把女性全部放在最后,大多是以捐款的数量为排名顺序。清代嘉庆年之后,甚至在男性捐款杂沓的名录里出现了“妓”和“乐户”(36)《重修后土圣母祠记》,明景泰七年(1456),碑阴有乐人刘四同、室韩氏的记载,现存于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后瓦村后土庙。的捐款,并且也不是按照身份排列,而是按照捐款数量间杂在一堆男性之中。
三、妇女无名考
姓名是人在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符号与标识,亦是人成为独立个体的一种象征。它与家族结构、价值观念、风俗好尚息息相关,也常因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名字可以曲折地反映世变,其所透露的历史文化信息十分丰富(37)刘增贵:《汉代妇女的名字》,《新史学》,第7卷第4期,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4页。。在上千通三晋明清女性题名碑刻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女性仅仅有姓无名,甚至个别连姓也看不到,仅以“某妻”来替代。此一发现似乎也证明了长期以来的论断:明清时期女性被父权与夫权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从而沦为家庭的奴仆。所录上千通女性碑刻中,更有甚者,一些单身老妇人不仅无名,而且死后不许入葬祖茔。“今在祠堂同主家甲头合户公议,即有老妇非随夫合葬之时,亦不得葬于祖茔之内,如有违,义葬老妇与祖茔内者,罚银五十两,合户公用”(38)《静升王姓合户公议不许寄葬老幼妇碑记》,乾隆二十九年(1764),现存于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红庙。。她们不但被剥夺了名字的使用权,还被剥夺了无夫之妇的埋葬权,传统社会一贯尊老的传统也不能阻止其族人对单身老妇人的蔑视。
根据周朝礼制,新生儿出生一个月后,由父亲为他或她取名。此后,男性在举行冠礼时取字,女性则在笄礼时取字。由此,妇女在未嫁之前应该有名,甚至也应该有字。但是,“妇人无名、以姓为名”似乎也是古已有之,如汉代《白虎通·嫁娶》云:“妇人无名,系男子之为姓;妇人无谥,用夫之爵以为谥。”(39)班固:《白虎通义》,中国书店,2018年,第42页。宋人叶梦得云:“古者妇人无名,以姓为名,或系之字,则如仲子、季姜之类;或系之谥,则如戴妫、成风之类,各不同。周人称王姬、伯姬,盖周姬姓,故云。而后世相承,遂以姬为妇人通称,以戚夫人为戚姬,虞美人为虞姬。”(40)叶梦得:《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页。清代阮葵生曰:“古士大夫妇人皆名,近代皆氏而不名,与市井闾阎无异,好礼者耻之。五雅及《本草》所载草木鸟兽,多有数名,未有无名者,妇人亦人也,而草木鸟兽之不若耶!妻之称谓。”(41)阮葵生:《历代笔记小说大观·茶余客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0页。甚至近人陈东原也认为:“妇人无名,系男子之姓以为名。”(42)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页。从汉唐到民国对于中国古代妇人是否无名的讨论一直是热门话题。
诚然,传统社会的人们已认定妇人无名是确凿的事实。但是,当代学者在分辨了大量文书、档案以及契约等文献后,对此提出异议。如陈宝良利用墓志铭研究明代妇女无名的问题,认为按照惯例,妇女虽不可说无名,但其所谓的“闺名”对外往往是保密的,除了娘家的人知晓,或者丈夫在婚前通过“问名”仪式方可获知以外,即使其子也对其母出嫁之前的闺名茫然无知(43)陈宝良:《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第421页。。阿风利用徽州契约文书发现:明代的土地买卖文书中除了一部分有“谢申娘”、“李氏夏娘”、“汪氏”、“吴希庆妻黄氏”、“汪爱民妻李氏亥娘”等称谓外,仍然以“某阿某”的表达方式居多,如“王阿何”之类(44)阿风:《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田土交易中的权利与地位》,《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邓小南则利用契约文书研究了隋唐时期妇女的称谓与名字,认为在唐代的户籍登记制度中,家中有男性户主时,作为妻子或母亲被载入的女性,一概只录姓氏而不见其名,但我们绝对不能由此而推论当时社会习俗中女性即不称名甚或没有名字,因为户籍中所登载的女儿都是有自己的名字的(45)邓小南:《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笔者十余年田野调查发现的上千通女性碑刻中,绝大部分女性似乎也只是有姓无名。但是综合各种文献以及学界前辈的研究,笔者认为明清时期妇女并非无名,实为有名不彰,且主要为妻子无名,女儿有名。明弘治元年(1488年)《本宗折枝记》是一通对女性姓名记载非常翔实的碑刻:
母生二子四女:长曰勖,字时勉,娶郭氏,生二子二女。长曰继武,次曰继科。长女讳荷钱、次女安钱、次女金钱。
次曰昂,字时口,娶宋氏,生二子二女。长曰继祖,次曰绍祖。长女小蒲、次女小崇。 姊妹四人:长姊适南厢东郜弼,次姊适本厢姬英,次姊适龙曲北陈有名,次妹适赵庄东李尹。
大明弘治元年二月吉日祀子崔勖立(46)《本宗折枝记》,明弘治元年(1488),《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高平卷(上)》,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94页。
这通碑中的所有妻子均有姓无名,但是家族中的女儿全有名字,族中女儿出嫁之后在本宗内依然明确称呼其名。由此,我们翻检了李雷主编《清代闺阁诗集萃编》中八十位著名女诗人的情况,有闺阁中人、孝女、节妇、烈妇、革命者、知识分子、早期办教育者、最早的女留学生等,几乎包括了当时女子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她们无论出嫁还是待字闺中,均有姓名。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出现明代女性作家245位,清代女性作家3676位,大部分都有姓名。除此以外,在大量的明清小说中,女性无论出嫁与否,其姓名记载也是清清楚楚的。但是,这种情况在笔者所研究的碑刻题名中却极为鲜见。这大抵是因为,碑刻格式与竖立方式是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逐渐形成和确立的,宗法意识更强,且要公之于世,所以更加严苛和正式。结合多种史料推论可知:明清时期的妇女有名,但是并不会书写在碑刻、家谱以及档案等一些正式的文书中。此类文书一般要公开镌刻与出版,具有严格的格式与书写规则,而传统社会的女性囿于所谓的“贱者避焉”(47)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9页。,故而在贵其名的公开场合找不到其名字的踪迹。所谓“古时妇女无外事,故名不闻于人”(48)袁庭栋:《古人称谓漫谈》,中华书局,1994年,第187页。。
目前所见碑刻题名的例外有三种:其一,偶有记载的女性姓名大部分出自世家大族,如上文所举碑文。其二,女性嫁到夫家后成为居士,给自己一个独立的法号。其三,妓女的艺名姓名书写非常完整。
四、余论
从碑刻中我们发现,明清时期有些女性所捐或所化银两数量异常惊人,如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重修关帝庙碑记》:女善人刘门冯氏、续门陈氏所化布施银一百余两(49)《重修关帝庙碑记》,清乾隆二十年(1755),现存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府城关帝庙。。其余化银五十两以上者也有数位女性,该碑中并未标明其夫君姓名。另外,有些碑刻中女性虽和丈夫并列书写,但却以独立身份捐款且捐资多于其夫,如前文中道光七年(1827年)《重修东岳庙记》碑阴有张许捐银二钱,其妻捐银二钱五的记载。由此可以推论,明清时期,妇女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支配金钱的权利,这些钱财可能源自于娘家带来的嫁妆,也可能源自于妇女的经营抑或其他。这部分“私财”大大拓展了女性在婚姻前后的经济权利,也使得她们在很多情形下有经济能力干预家庭、家族内外事务,家庭和社会地位得以提升(50)毛立平:《妇女史还是性别史?——清代性别研究的源流与演进》,《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
传统社会中,尊重母亲是贯彻始终的一种社会准则,这是因为在古代家庭伦理秩序中,长幼人伦之序要高于男女两性之别,故而女性长辈的地位尊于男性子孙,母亲无疑是传统女性扮演的最光彩的角色。在男权社会中,它赋予了母亲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所以有人说,中国无女权,却有母权,不无道理。我们在碑刻题名中发现,如果母亲的地位非常尊崇,一些庙宇与村落基础建设甚至直接是由母亲提名而搞起来的,如《河山楼记》“至工匠饮馔之需,老母亲勤于内……凡此皆出高堂老母亲亲为料理”(51)《山河楼记》,明崇祯七年(1934),《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阳城县卷》,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95页。。即使是继母,也在家庭中享有至高的尊敬,为继母立碑也是此时民间的风气。如康熙十三年(1674年)《贾罕张家崖窑里院》中有:“世上继母有万千,惟我母亲里中先;三从四德人难比,主家有道左堂前。儿子感恩无答报,孝当竭力把名传;今日刊碑留铭后,阖家安乐万万年。父张足屏,母赵氏。”(52)《贾罕张家崖窑里院》,康熙十三年(1674),《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襄汾县卷》,三晋出版社,2016年,第185页。为继母刻碑显然是一种道德表彰,碑刻中的母亲即使是继母也在家庭中处于至尊地位。对于明清妇女地位的探讨,仅从碑刻单方面来看,比较复杂,因为女性在一生中经历了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等不同的家庭角色,在不同的角色中,女性的经济地位与财产权利有着不同的变化。
在明清碑刻题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该妇女是否具有财产支配的权利,无论女性独立出资抑或女性出资多于男性,碑刻里的妇女无名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她们没有完整姓名被刻录的权利,妇女无名背后确实体现了当时女性地位低下,依附于男性的社会现实。但是,碑刻文字显示,母亲身份被无限强调,折射出作为母亲的女性身份的被需求和被放大。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依附于男性,她们的姓名被烙上夫家的烙印,以某门某氏、某某氏而存在,一个姓名可以指代无数的妇女。她们存在于父亲、丈夫、儿子姓名的背后,她们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生育。在碑刻中,母亲身份的被强调和被放大,源自于一种男性视角的需求。男性希望和期待女性成为什么样的身份,女性就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文人笔记、历史传记及碑刻题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