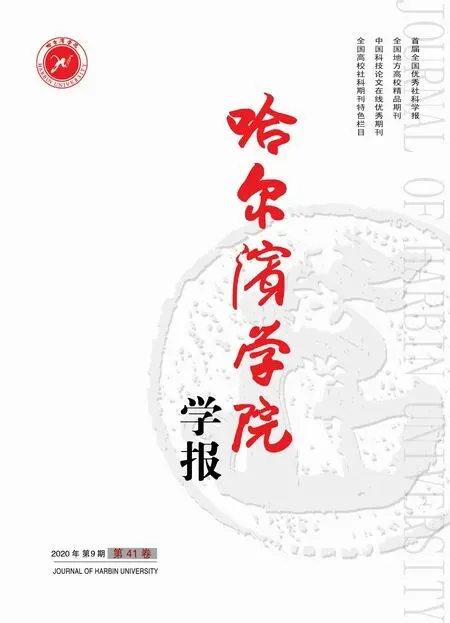闺阁精灵的赤子之心
——谈凌叔华小说中儿童视角下的女性主体意识
罗 茜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和启蒙运动的日深,女性个体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女性作家通过手中的笔发出女性独有的声音。女性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使中国女性第一次走上了话语主体的历史舞台,构成了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作家群体诞生,她们从题材的选择到作家主体情感的抒发,都浸透着女性特征,以女性的敏感和直觉不断探索着女性文学的世界”,[1](P1)凌叔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鲁迅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评价凌叔华为“高门巨族的精灵”。[2](P11)与同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庐隐、冯沅君、丁玲、石评梅等“新派女性作家”不同,“闺秀派”作家凌叔华在作品中聚焦于豪门贵族的新旧女性,反映她们闭锁在深闺高宅里细腻的情感世界和面对无声悲剧的顺从麻木,揭示小说中女性主体意识的陈旧落后,因此评论者对凌叔华小说的研究更多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展开。本文从叙事理论中的叙述视角入手,结合凌叔华最擅长的女性话语书写,选取她作品中较为独特的儿童视角,探讨凌叔华选择儿童视角对其小说中女性主体意识叙述的作用及成因。
一、赤子之心:儿童视角的运用
依据叙事学原理,叙述视角是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关系,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作为视角的一种类型,儿童视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全新的叙述模式,指“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3]申丹在其《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指出四类视角的划分标准:“一、零视角(即传统的全知叙述);二、内视角(人物视角);三、第一人称外视角(包括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四、第三人称外视角(即等同于热奈特提出的外聚焦)。”[4](P228)凌叔华小说中运用的儿童视角,大多数为第二类内视角,即固定式的人物视角。这种固定式的人物视角,可将读者的眼光聚焦到承载叙述视角的人物身上,在他(她)的带领下进入情节,将人物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感知的喜怒哀乐、前后的心理变化等都直观地传递给读者,拉近彼此距离,产生情感的共鸣。
作家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她对儿童有着深厚的感情,将其比作“心窝上的安琪儿”。[5](P785)作为以女性文学赢得社会关注的作家,她的一些小说用全知视角展开故事,借助固定的儿童视角作为补充来塑造小说中女性的形象。读者跟随儿童观察高门贵族女性卑微的家庭地位,以儿童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来感受封建大家庭女性的悲欢离合。由此可体会到,作者用孩子的天真无邪衬托旧社会女性的思想麻木,讽刺意味更浓,更能深刻地揭示男权社会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
《小英》中的主人公小英得知三姑姑要嫁人,要“装文明样的新娘子”,特别兴奋,一直幻想着看到三姑姑“头上蒙着好看的粉红长纱,穿着好看的花衣服,手上抱着一大堆鲜花”的模样,并一直询问姑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新娘子。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在见到三姑姑婆婆之后逐渐破灭了,“那个吓人的老太婆,脸生得直像一个南窝瓜,那两只眼,看人的时候,比大街口那个宰猪的还凶。”小英看到这样一个老太婆的形象,不免心生害怕,难以入睡。到三姑姑婆家,小英观察到屋里“没有大地毡和舒服的坐垫子,有笨大的盖碗”,说明其家境并没有自家殷实,但姑姑“却要站在一旁,替那老太婆装烟袋”。与祖母的谈话中,小英听到三姑要伺候婆家人到深夜,腰酸背痛,还要在吃饭时站着服侍他们,不禁为她感到委屈和心疼。作者以小英的儿童视角来记录她所看到的三姑姑在婆家奴仆般的生活。作为孩童的小英,虽不能明确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但已直观地感受到姑姑今后生活的不幸,以至于在最后说出“三姑姑不做新娘行吗?”的人物话语,与故事开始时对三姑姑做新娘的热切期盼形成对比。凌叔华通过小英的视角,来揭示封建社会三纲五常对女性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三姑和祖母面对不公平的待遇却只能掩面哭泣,一味顺从,这也体现出男权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男尊女卑观念的根深蒂固,女性主体意识的淡薄甚至缺失。
《一件喜事》中,父亲纳妾,小主人公凤儿随着亲人和家里的孩子一同向父亲道喜,感受到的是过年般的喜庆,但却看到五娘对父亲娶新姨太太之事一直郁郁寡欢。她不明白五娘为何今日“像一支红芍药花,可是闪着银白色的光,脸相没有平日可爱,狠狠的闭着嘴”;也搞不懂为何父亲大喜之日五娘却要哭了整整一天,更不理解她说“喜欢死的人死了,就快活了”的含义,只是天真地搂着五娘的脖子道:“你别死”。凌叔华以凤儿的视角来观察她所看到的五娘今日种种怪异的行为,通过她的不理解,反衬出一夫多妻制度给女性带来的精神痛苦。在男权社会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在婚姻中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五娘面对父亲纳妾一事的不满,显示出她存有潜在的女性主体意识,也向往一夫一妻制的男女平等。但在现实面前,她没有释放女性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或是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改变令她伤痛的现状,比如勇敢逃离这种制度的压迫。五娘的软弱使她毫无反抗之力,一味地默默承受。小说的题目为《一件喜事》,但在五娘这里却是一件悲伤却又无可奈何之事,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八月节》中,凤儿跟随妈妈和姐姐前往京城与父亲同住,本心疼爸爸孤独的生活,到住处才得知父亲已有三妻四妾和哥哥姐姐。在她看来,“珍儿说话时,漆黑的大眼睛像八哥眼那样一溜一溜的转得很可爱”,二者并无差别。但听到生了四个女儿的妈妈同五娘讲心事时已经大致晓得什么是“命”的意思了,也隐约懂得三娘趾高气扬是因为有了儿子,“五哥是家里大家捧的孩子,谁也不敢惹他”,但爸爸却分不清女儿的名字。以凤儿的视角,她不太明白母亲为何会半夜应邀前去打牌及三姨太换饼所为何意,但读者却可以从以上种种事件中感悟到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对女性的压迫。母凭子贵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的体现,在这样的体制下,没有儿子的女性只能忍受家族的百般践踏。
与其他的视角相比,儿童视角表现出直观性和单一性的特点。所谓直观性,指儿童处于“人之初”阶段,本身就生活在自己纯真无瑕的世界里,只能凭借最基本的直觉判断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物。但成人文学中儿童视角的运用,恰恰是为了表达超出儿童感知的那部分内容,儿童只是担任了外部社会的观察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儿童视角实际展现的是成人的世界。凌叔华正是以儿童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和感受高门贵族的女性世界。《小英》中,主人公小英前期得知姑姑要当新娘子异常欢喜,后期通过自己的观察已隐约感受到三姑姑今后生活将会不幸福。但作为儿童的小英只能直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三姑姑不做新娘行吗?”小说戛然而止。读者已通过作者的叙述给出了答案:不能。深受封建礼法迫害的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一味地顺从,没有反叛精神,女性主体意识近乎丧失。儿童视角的运用让我们能从更直观的角度去体会当时社会中女性隐忍悲哀的生活方式。
上文提到,凌叔华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大多数为固定式人物视角。这种视角将儿童主人公限制在自己的所见所闻之内,展示自己所观察到的世界,因此呈现单一性的特点,读者跟随人物视角走进了他们的视野。《八月节》中通过凤儿的视角,我们只看到母凭子贵的三姨太目中无人、张扬跋扈的一面,却无法从文本中进一步了解她另外的性格特征。但这正是凌叔华所要达到的效果,值此一个突出的特点就能体现出一夫多妻制的男权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盛行,已造成女性心灵的扭曲变形,仿佛生儿子就是她们的毕生所求,也是她们改变命运最重要的途径,以此揭示出旧社会传统女性的卑微与无奈。
“五四”女性文学大多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凌叔华以上几篇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并没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有的只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凌叔华是想以反面叙述来描写女子悲哀的命运,以孩子的天真无邪衬托女性面对不公压迫时的麻木、无动于衷,给读者带来更强烈的心灵冲击,不禁为可怜可悲的女性感到痛惜。
凌叔华以儿童视角观察世界,窥探男性主导的社会下女性的生活状态。她希望通过儿童的眼光揭示当时半新半旧社会中闺秀们迷茫无助、女性主体意识普遍衰弱的社会现状,唤回男权社会中女性对自身主体意识的重视。如《小英》里的三姑姑,作者渴望她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拥有平等的女性价值;《一件喜事》里的五娘,作者期望她自主选择婚姻,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八月节》里的母亲,作者盼望她重视女性自身价值,不要沦落为生儿子的工具,不要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
二、知人论世:闺阁精灵的喜悲哀愁
“知人论世说”最早由孟子提出,指理解一部作品,要研究作家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及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社会土壤。凌叔华运用独特的儿童视角来体现女性主体意识,与她自身高门巨族的成长环境、所处的时代背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其时代背景而言,新文化运动使得女性作家迅速崛起,在文学创作中为女性话语权赢得一席之地,女性主义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她们的创作不约而同地选择女性反对封建礼教、争取独立人格、倡导自由解放等来体现新时期女性的主体意识。凌叔华前期作品也大都是以女性视角来体现封建社会女性的生活,唤起各界对处于生存困境之下女性的同情。五四后期,对儿童世界的关怀成为女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凌叔华也逐渐转移到以儿童为主要观察视角的文学创作。不同的是,同时代女作家在作品中大多书写孩童纯净善良的心灵,凌叔华则将儿童与多愁善感的女性相结合,通过儿童视角揭示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尴尬,生活处境的艰难,内心世界的寂寞空虚。
新旧交替的五四时期,落后的封建思想刚刚被冲破,女性意识伴随着社会改革、妇女解放运动而产生。现代中国知识女性在上世纪初第一次灵魂苏醒,主动向外探索“自我—女性”与时代的联系。但由于五四之初,妇女解放运动毕竟刚刚开始,女作家们还不能完全挣脱传统因袭的重负,因此深居豪门贵族的“闺秀派”的闺阁化创作相对隐晦。凌叔华借用儿童视角叙述女性主义,实际上也给自己的作品穿上了一层保护的外衣,呈现出一种温和的批判,这是凌叔华在特定情境中创作女性文学比较舒适的一个突破口。
就其个人成长环境而言,凌叔华自幼就生活在高门巨族的大家庭环境当中,自小思想就更直观更深化地受到封建化礼教的制约。其身为妻妾的母亲在家族中并无话语权,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只能忍气吞声。从母亲的生活中凌叔华体会到了女性的艰辛以及在男性当家作主制度下女性的可悲可怜之处。又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无法为自己的生活做主。作为高门巨族的精灵,凌叔华并没有像普通的大家闺秀那般安于享受表面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而是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使女性群体在社会中获得不只是身体上,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真正意义的自由解放。因此凌叔华在小说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主动以一个儿童的视角记录她们身边发生的一切,将封建大家庭的故事,一一生动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种“自我表现”的创作,是在凌叔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发生的,也正是在作者自我情感的抒发中,鲜明地表露了女性的人格和价值,而且包含了她对妇女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思考。
此外,叙述视角的选择不仅是一种叙述方式的选择,也是作者创作方向、价值观念的体现。凌叔华女性文学中除运用全知视角,更是选择儿童视角与之相辅相成。儿童是凭着感觉来把握世界的,女性是通过感性来体察世界的。因此,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旧社会中,儿童在对事物的认知判断上更接近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比男性更能体察女性。采用儿童视角,通过儿童澄净的眼睛观察女性,往往能不露痕迹的探索与其相关联女性的主体意识,深入其空虚寂寥的内心世界。“凌叔华也因此成为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由对外索取和认同,转向对自身意识本体进行注目和审视的最早的女作家之一。”[6]
三、结语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更深一步来说需要女性“人”的觉醒,即意识到女性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意义的存在,而不是一味地依附男性。凌叔华笔下的这些女性,她们压制了个人欲望,压制了“人性”,不具有完整独立的人格,也就造就了她们主体意识的淡薄甚至缺失,这与孩童的“解放天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真正的女性解放不是女性主义压倒男权主义,女权话语占领男权话语,而是要实现女性身体、心灵、精神、人格等方面与男性真正的自由平等,和谐共存。
凌叔华运用儿童视角审视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活,批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戕害,同时又对旧社会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个性的泯灭、人性的枯竭感到可悲与惋惜。儿童叙述视角本质上是对成人经验的疏离,儿童的直观感性与成人客观理性形成一种对立。凌叔华在小说中借助儿童视角观察异于成人眼光中的女性世界,从而也就建构起了作者以澄净的儿童世界来反衬成人世界的麻木与冷酷,完成对旧时封建社会的批判的创作理想。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