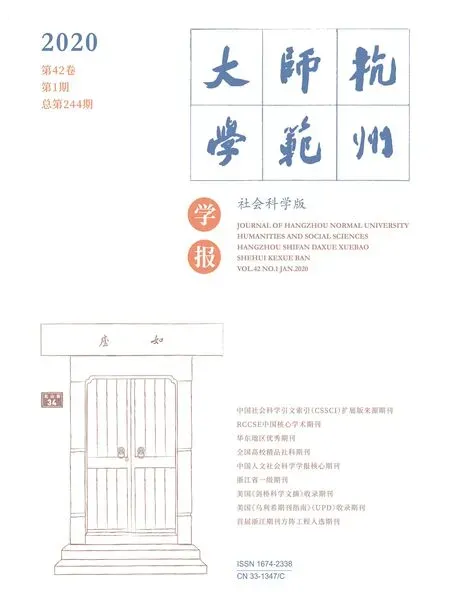《孟子》新解三则
蒋国保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301 )
一、“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尽心下》第16章云:“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对此章的“合而言之”,朱熹这样解:“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1](P.376)正是根据朱熹这一解释,后来的大多数学者都将“仁”与“人”合起来解说,例如杨伯峻将此章译为:“孟子说:‘仁的意思就是人,仁和人合并起来说,便是道。” [2](下,P.329)但清华大学教授廖明春先生却认为这样解释不妥。在廖先生看来,只有具备两个东西、两个对象才谈得上所谓“合”,然而这章中合起来说的两个对象,不应该是指“仁”与“人”,因为“人”在此章里,是用以定义“仁”的,而不是用以表示与“仁”对等的并列关系。那么,如何理解才合理呢?廖先生凭借其深厚的文字考据功夫,从考据角度,推断此章当脱落“义也者,路也”五字,原本应该是:“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义也者,路也。合而言之,道也。’”(1)以上对廖先生观点的转述,是根据本人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所闻,也许有不尽准确之处,但大义不误。廖先生的见解独到,如据之以把握此章,则此章就变得很容易理解,让人一眼看上去就明白。所谓“道”,就是指合“仁”与“义”而言之,或者说,道乃统摄(合)“仁”与“义”之谓。
当年朱熹那样注解的同时,还特意添补了这么几句:“或曰:外国本‘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则理极分明,然未详其是否也。”[1](P.367)。朱熹添上这几句,言下之意是想说,如果此章真如“外国本”(2)廖明春先生以为即“高丽本”。所载有那二十字,那么此章所要表达的道理,就极其分明,不像无那二十字似的不好理解,但因为对所谓“外国本”是否真有那二十字他未能详细了解,难以断定,所以他不敢径直依据“外国本”解释此章。廖先生显然是受了朱熹“外国本”说的启示,才敢于推断此章当脱落“义也者,路也”五字。但他自己并未这样交代,却说此系出自考据。既以考据示人,廖先生自然很明白,乾嘉考据重要的一个方法论原则,就是孤证不足据,更不用说以推理代替证据。可与以往的考据不同,廖先生对这一考据并没有提供充足的文献证据(3)如果廖先生后来就这一推断给出了充足的文献证据,笔者在此预先向他道歉。。
我认为廖先生的推断,在两点上缺乏认真的推敲。其一,在孟子那里,“道”就是“路”的意思,现在再以“义也者,路也”定义“道”,岂不等于以“路”定义“路”;其二,根据杨伯峻先生的统计,《孟子》中“之”字出现1902次,除了“夷之”(人名)外,统共有6种用法,其中5种用法,都不是以“之”字为代词作宾语用的,剩下的一种用法,像“合而言之”“何以言之”[2](下,P.278),其中的“之”字都是以代词作宾语用。杨伯峻先生的统计以为“之”字的这种用法,在《孟子》中共出现844次。廖先生所解,显然也是将此句中的“之”字视为代词作宾语用,但他认为“之”字在句中既代指“仁”又代指“义”。问题是,以“之”为代词而兼代两种对象的用法,好像不见于先秦文献。如果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文献里的确未出现“之”为代词而兼代两种对象的用法,那么要使廖先生所解得以成立,就只有将“之”看作语气词,但在动词“言”字下紧接语气词“之”字的用法,在先秦文献里,好像也找不到明确的例子。如果就《孟子》而言,无论是“合而言之”还是“何以言之”(一再出现),其“之”都有明确的代指对象,并非作语气词用。
对廖先生的见解提出以上不同意见,目的不是为了推翻他的考证,而是想借机提出一个问题以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不添“义也者,路也”五字,《孟子·尽心下》第16章是否也解得通?作为抛砖引玉,我先谈谈我的看法,衷心希望得到大家的回应与批评。
我认为该章不添那5个字,也能解得通。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将该章作这样的理解:该章所谓“道”,具体就是指“仁”,只不过它是就“合而言之”的意义来说的。照这样理解,“合而言之”句中的“之”字,就不是代指句首的“仁”,也不是如杨伯峻先生所解那样系代指“仁”与“人”,更不是如廖明春先生所解那样系代指“仁”与“义”,而是代指“人也”。那么,将人“合而言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仁”字所显示的,是将两个“人”合在一起,用今日的说法,就是人与人之际,即人与人形成了伦理关系。“仁”原本是指每个人(个体)都具备的“恻隐之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它一旦就人际关系上来把握(爱人),就成为人伦的基本原则(道)。根据这一理解,不妨将《孟子·尽心下》第16章作这样的还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人),(仁也者)道也’。”
我一时无法为自己的这一理解找到古典文法上的例证,但我自信这一理解符合孟子“仁义”说的本义。孟子“仁义”说对孔子的“仁义”说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既将“仁义”并提,又明确地以“道”统称“仁”与“义”。 以“道”统称“仁”与“义”,在孟子看来,并不是简单地将“道”视为“仁”与“义”的统一体,而是在以“仁义”定义“道”的同时,又将“仁”与“义”区分为用处不同的“道”。“仁”“义”同为“道”,只是从它们都具有规范人之行为正当性的作用这一共性上来强调的,但由于人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则用来规范人之行为的原则(道),也就有必要区别言之。区别言之的话,虽同为“道”,但“仁”与“义”各有各的适用范围,各有各的特殊规范作用。就个体自身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2](下,P.267),“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2](上,P.172),“仁”是规范人之内在精神意识活动的“道”,而“义”则是规范人之外在行为的“道”,所以“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2](上,P.172)。人一旦不遵循“仁”而思想、不遵循“义”而行动,就意味着自己抛弃自己;就家庭言,“亲亲,仁也;敬长,义也”[2](下,P.307),“仁”是指对父母的亲爱,“义”是指对兄长的敬重;但用“仁”与“义”分别规范亲父母、敬兄长的情感,在孟子那里,并不是说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情感,也不是强调亲爱父母与敬重兄长在情感上有根本性的不同,而是说将爱父母的情感用于敬重兄长,原来的血亲情感“仁”就成为“义”。就群体言,“仁”是规范人伦之“道”,而“义”则是规范人之具体行为之“道”,所以孟子强调说“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2](上,P.191)。
以上所谈,限于“道”与“仁”“义”的关系。如就“仁”“义”本身关系言的话,孟子既以“人心”与“人路”区别“仁”与“义”,则显然意在强调“居仁由义”[2](下,P.316)是统一的道德过程,以为一旦“仁”立就必定“义”行。既然认为“仁”立必“义”行,则孟子势必与孔子一样认为“仁”与“义”的关系乃“体用”关系。有其“体”必有其“用”,“体”决定“用”。孟子一旦将“仁”“义”关系确定为“体”“用”关系,他就一定会将人之最根本的人伦之“道”确定为“仁”。孟子之所以一再说“当道,志于仁而已” [2](下,P.291),“君不乡道,不志于仁” [2](下,P.293),将“道”之担当、“道”之向往,与“志于仁”并提,就因为他坚信人“道”之根本为“仁”,而“义”则是依据“仁”才可能合适于人的人之具体行为原则。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孟子“合而言之,道也”,正是从“仁”为人伦之“道”的意义上讲的,因为只有从人伦(人与人的关系)上讲,将人(个体)“合而言之”才能讲得通。
二、“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
《孟子·离娄下》第26章云:“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无所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对这一章,历来的解释,异见纷呈,尽管各能自圆其说,但在我看来,亦都有费解之处,凭之都难以透彻地理解孟子真实的意思。这里不妨举3例,以窥一般。
(一)朱熹在《孟子集注》中解云: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故者也。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然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若人之为恶、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1](P.297)
朱熹这是按照人们总是就可经验的事物以求不可经验的事物之理的逻辑来解释孟子所谓普通人都是从“故”的角度谈论“性”。由于他将“故”视为“已然之迹”,且比方为“若所谓天下故者”,那么他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意思:天下普通人都是就“天下故者”言谈“性”。问题是,“天下故者”何意?他没说,我们只能据“已然之迹”的说法将之理解为“天下之迹”,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世界万物,因为万物都是“理”(“性”)的体现,万物可以说是理发用而留下的痕迹(故),所以通过“故”可以认识“理”,认识“理”,也就把握了“性”。依照朱熹的《格物补传》的说法:“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之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 [1](P.7)他那样解,只能说合乎他自己的哲学立场与论证逻辑,但未必合乎《孟子》的本义。其解释所以不合《孟子》本义,是因为他忽视了《孟子》的那一章不是在谈物与人共有的“性”,而只是在谈“人性”。正因为这个忽视,他置“故者以利为本”一句于不顾,殊不知《孟子》正是以此句点明普通人之所以以“故”言“性”的原因。
(二)杨伯峻在《孟子译注》中,未作过多的语词诠解(4)只作两注,一是从朱熹注“利”为“犹顺也”;另是注“日至”为“冬至”。,而是直接这样翻译:
孟子说:“天下的讨论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之理。我们厌恶使用聪明,就是因为聪明容易陷于穿凿附会。假若聪明人像禹的使水运行一样,就不必对聪明有所厌恶了。禹的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假设聪明人也能行其所无事,(不违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实行,)那聪明也就不小了。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以后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 [2](上,P.196)
杨氏将“性”翻成“人性”,突破了朱熹的解释,但由于其又从朱熹解“利”为“顺”,所以他仍然像朱熹一样,也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此章,只是他认为此章非一般的谈认识论问题,而是具体的谈认识“人性”问题,与朱熹稍有差别。
(三)唐满先在《十三经直解·孟子直解》中这么解:
“天下之言性也”的“之”,作用同“所”字。故:指事物的本来情状和道理。利:顺。行水:使水运行。行其所无事:指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日至:这里指冬至。孟子说:“天下人所谈论的事物的本性,就是事物本来所具有的情理罢了。事物本来的情理以顺其自然为根本。所以讨厌某些人的聪明,是因为他们喜欢穿凿附会。如果聪明人像禹疏导洪水一样,那就不会讨厌他们的聪明了。禹疏导洪水,是因势利导顺其自然的。如果聪明人也因势利导顺其自然,那聪明也就大了。天是很高的,星辰是遥远的,如果寻找它们本来的运行规则,一千年的冬至节候,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 [3]( P.552)。
很容易看出,唐氏此解,在思想上受朱熹那个解释的影响十分明显,只是为了比朱熹更明确地突出该章所谓认识论主旨,他修改了朱熹的一些说法,将“性”诠为“事物的本性”,将“故”诠为“事物的本来情状和道理”,将“利”诠为“顺”,并特意交代系指“顺其自然”。由于比朱熹更彻底地认为该章谈的是认识论问题(5)作者特意强调:“本章谈能够认识和顺应事物运行规律的人才是聪明人。”见唐满先等《十三经直解》第4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2页。,否定该章是从实践理性谈人性问题,所以唐氏对于该章所谓“性”“故”“利”这三个关键词的诠释,多是增字为解,难免有臆测之嫌。
上面三解,在解“利”为“顺”上是一致的;而在解“故”解“性”上都有分歧(6)对于“故”或解为“已然之迹”,或解为事物本来的道理“所以然”;对于“性”或解为“理”、或解为“事物本性”、或解为“人性”。。既然有分歧,就说明它们都不是的解,都有质疑的可能。何以疑?疑在此章究竟是一般地谈认识事物之理还是特殊地谈人性?在我看来,要破解此疑,关键要正确理解“故者以利为本”;而要正确理解此句,又当正确理解“故”与“利”这两个关键词。
先看“故”字。根据杨伯峻《孟子词典》中的统计,《孟子》共出现“故”字100次,分为4种情况——作名词“是故”“故旧”用2次,作名词“道理”“原因”“所以然”用9次,作形容词“老”“旧”用2次,作连词“所以”用87次。从“故者以利为本”句在原文中的语境来看,将此句首字“故”作形容词与连词解都显然解不通,只能作名词解。这就是朱熹、杨伯峻、唐满先三先生都将此句中的“故”字作名词解的原因。虽然都作名词解,但朱熹选取了共用了2次的那层意思,而杨伯峻、唐满先都是选取了共用了9次的那层意思。既然他们那样解“故”字就原文语境论都不能令人信服,那么《孟子》中“故”字还会不会有另一种用法,被他们所忽视了呢?于是我特意查《说文解字》,看许慎怎样解“故”字。《说文解字》涉及“故”字的解释有二:一是“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4](P.50);另是“故,使为之也” [4](P.67)。前一种作名词解释,是将“故”“古”互训,以“故”为故旧,特指“识前言者”;后一种作动词解,是将“故”解为“使对象作为”。我认为,在“故”字这两义中,取后一义解该章中的“故”是贴合《孟子》本义的。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故者以利为本”句中的“利”字不当解作“顺”,而应视同“何必曰利” [2](上,P.1)句中的“利”,解作相对于“义”的私“利”。
那么,将“利”径直解作“私利”(利益),纵观《孟子》中“利”字的用法,是否说得通?回答是肯定的。按照杨伯峻《孟子词典》的统计,《孟子》使用“利”字凡39次,用作“利益”义的26次,用作“使有利”义的6次,用作“以为利”义的2次,用作“锐利”义的4次,用作“顺”义的1次(7)他所举的例句就是“故者以利为本”。。由此可见,除了用作“锐利”义的不计,余下的35处“利”字,按照杨伯峻自己的理解,也只有一处作“顺”义解,而其余34处“利”字都可直接(26次)或间接(8次)作利益解。就此而论,不能不令人费解,他们(8)指朱熹、杨伯峻、唐满先三先生。有什么理由不依据那34处的用法,将该句的“利”字作“利益”义解,而偏要作“顺”义解?仔细地分析之,我觉得这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孟子》所谓“利”绝大多数作“利益”义用,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若不将“故者以利为本”句中的“利”作“顺”解,那么他们对“故”的解释就说不通。而他们之所以对“故”作那样的解释,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故”字尚有“使为之”义。
问题是,若将该句中“故”字按“使为之”义来解,就一定合乎《孟子》本义吗?这个问题,从《孟子》本身,似乎难以找到直接的论证解答之,但可以从思孟学派的另一经典《性自命出》中找到解答的直接论证。《性自命出》这样论述“性”与“故”的关联:“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历性者,义也;绌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5](P.106)由此可见,在思孟学派那里是从“交性”的意义上将“性”与“故”并提。“性”“故”并提之“性”,具体指“人性”,无可置疑,那么与“人性”密切相关的“故”具体指什么?它只能特指人的作为。“故”之此义,《性自命出》在定义“故”时说得十分明白:“物之设者之谓势,有为也者之谓故。”[5](P.106)
基于上面的论证,我大致这样理解《孟子·离娄上》第26章:全天下的人们谈论人性,都是根据人自身的作为(则故)来谈。以人自身作为为准则来谈人性,也就是以利(于人有益)为根本原则来谈。以“利”为根本原则来谈人性(9)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他必定从“仁义”谈人性,反对从“利”谈人性。是不明智的(所恶于智),因为那样谈人性是穿凿附会的谈法。明智的谈法,就像大禹治水使水顺着水性向下流那样,不是从人为作用于人性的意义上来谈,而是从人无所事事的意义上来谈。天空无论多么高,星辰无论多么远,如果求得那个使天那么高、星辰那么远的原因,一千年中的冬至日,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言下之意是说,如果真能从人无所事事的意义上了解人性之所以为人性的原因,那么人之本性是善还是恶,就很容易弄明白。
三、“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
《孟子·公孙丑上》第2章有云: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此为《公孙丑上》第2章中的一段。此段论述要数“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两句最费解,所以大多学者对它的解释,常常受大家有关解释的影响,在南宋之后,这具体就是指受朱熹解释的影响。朱熹这样解释:“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袭,掩取也,如齐侯袭莒之袭。言气虽可以配乎道义,而其养之之始,乃由事皆合义,自反常直,是以无所愧怍,而此气自然发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于义,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也。”[1](P.232)
朱熹此解重在强调,孟子于这段论述中指出,他所善于养护的“浩然之气”,是通过不断积累善行而培养起来的,而不是偶然地做了合乎道义的事(善行)就能萌生的。尽管这一解释未必十分准确,但它的影响却甚大,以至于现当代大多学者都依据朱熹的解释来理解之。比方说:
(一)在20世纪60年代,杨伯峻依据朱熹的解释,将这一段翻译为:“公孙丑又问道:‘请问什么叫做浩然之气呢?’孟子说:‘这就难以说得明白了。那一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一点不加伤害,就会充满上下四方,无所不在。那种气,必须与义和道配合;缺乏它,就没有力量了。那一种气,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所产生的,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取得的。只要做一件于心有愧的事,那种气就会疲软了。’” [2](上,P.66)
(二)20世纪90年代,唐满先仍根据朱熹的解释将此段这么解:“袭,突然袭击。‘义袭’是指突然行义或偶然行义。慊:满足,快意。孟子说:‘这种气是不断把义聚集起来(即平日行事都合乎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行义而取得的。如果做了亏心的事情,这种气就空虚无力了。我所以说,告子不曾懂得义,他把义当作心外之物了,这种气必须日积月累不断行义才能培养起来,一旦做了不合于义的亏心事就没有力量了。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对不合于义的言论不在心里想它,采取回避态度,所以孟子说他把义当作心外之物。” [3]( P.451)
在时间上先后相隔八百多年的一脉相承的这三种解释,似乎向世人表明,古今注家在理解“浩然之气”乃“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义上已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后世的学者很难、也没有必要再突破该解。可是,我仍然想表达自己对该段论述之有别于上述理解的看法。尽管我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解就一定贴合《孟子》的本义,但我想我公开说出自己的不同理解,定有益于促进对《孟子》该段论述的更深入的理解。
朱熹等人的解释,实际上并没有给此段中的“气”以定义,未说明孟子所谓“气”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东西。“气”这个范畴,是中国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之一,但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常常用以称谓不同的东西,或指物质性的东西,或指精神性的东西。就《孟子》而论,孟子关于“气”的论述,集中在《公孙丑上》(凡16次)。归纳分析那16处“气”,会发现孟子主要是从与“心”“志”“体”(人体)对称的意义上使用“气”,如“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2](上,P.62),这足以说明“气”充沛于人之身体,但它并非如中医所谓贯通人体的气脉,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与人之思想与意志互为因果的精神性的东西。所以我将《公孙丑上》中的“气”解为人之“生命精神”,而将“浩然之气”解为人所固有的“正大刚直的生命精神”。
“浩然之气”既指人所固有的“正大刚直的生命精神”,那么为什么说它“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集义”未必如朱熹所说,是指不断地积累善行,因为假使不断地做好事却不能从中体悟做好事所体现的生命真谛,或者不断地做善事只是为了博得名誉与利益,那么它非但不能产生出“正大刚直的生命精神”,反倒会严重地阻碍这种生命精神的培养。“集义”应该是指归集各种合乎义的行为以体悟其所以然。
至于“义袭”,我认为也不能依据朱熹的解释,将之解释为“突然行义或偶然行义”。因为即便是偶然的行义,如果能从中真正体悟出行义所体现的人之生命意义之所在(生命真谛),人也有可能将“正大刚直的生命精神”树立起来,未必非得不断地行义才能树立起这一生命精神。那么,当如何理解?我认为,要正确理解“义袭”义,关键是要把握“袭”字义。“袭”字在《孟子》仅于“义袭”句中出现1次,而朱熹将它解为“掩袭”(突袭、偷袭)。可照此解,“义袭”就成了偷袭或突袭而获得的义行(行善),就更令人费解。明明是行善(义行)为例却偏偏要以偷袭或突袭的方式去做呢?或许连朱熹自己也觉得这么解有不近情理之处,所以他特意补充说“非义袭而取之”乃指“非由只行一事偶合于义,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也”[1](P.232)。问题是,这一补充解释,既然将“袭”理解为“掩袭于外”,那么“袭”的对象是“外”,就与“义”无挂搭;况且,“义”也不能臆断的解释为“行一事偶合于义”。
《说文解字》释“袭”为“左衽袍” [4](P.170),系向左边开前襟的袍子。《康熙字典》引春秋汉唐典籍文以解“袭”云:“重衣也……注:上下皆具曰袭。……又服也,又合也,又因也,又入也,又受也,又掩其不备也。”[6](P.12)。在这些含义中,我觉得取“服”(服从义)、“合”(符合义)、“因”(因袭义,模仿义)、“受”(接受义)、“入”(合乎义)这五义以解“义袭”之“袭”,都能解得通。但我更倾向于选取“合”“因”来解“义袭”之“袭”,“非义袭而取之”或可理解为,不是只要行事合乎义就能萌发正大刚直的生命精神(浩然之气);或可理解为,不是简单地模仿义行就能产生正大刚直的生命精神。我认为这两种解释,无论选哪一种都比朱熹的解释更贴近孟子“仁义”并提思想的本义。
根据上面的辨析与论证,我将本节开头所引的孟子那段论述作如下翻译:“请问老师擅长什么?孟子回答说:‘我能辨析出非通常话语的真实含义,我善于养护我自己的浩然之气。’请问什么叫做浩然之气?孟子回答说:‘这难以说得明白。它作为一种生命精神,极其博大,极其刚健,以正直养护它而不伤害它,它就能充沛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它作为一种生命精神,与义和道相配合;没有了义与道,它就失掉了力量。它是归集各种合乎义的行为以体悟其所以然而产生出来的,不是简单地模仿义行就能产生的。行动起来一旦心中感到不快乐,就会失掉继续干下去的勇气。我所以说告子不曾懂得义,就是因为他不从人之内心世界谈义,而是从人之外在的行为谈义。人的内心,一定会想很多事情,你不要制止之;不要忘却内心所欲,也不要助长内心所欲。不要像宋人那样做:宋国有个人担心地里的禾苗不长就把它拔高些,(拔完苗)疲倦地回来,对家人说:我累坏了!我助禾苗生长了!他儿子跑到地里来回一看,禾苗都枯了。全天下不干拔苗助长傻事的人很少。以为无益处而放弃不做(指不去培养浩然之气),就如种庄稼不除草的人,是懒惰;去做助(浩然之气)生长的事,就如拔苗助长,是糊涂——不但没有益处,反倒会伤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