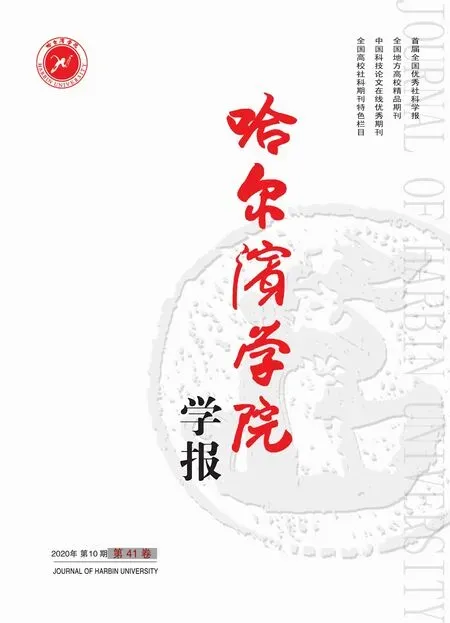荣庆与晚清“新学”
张 帆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荣庆,字华卿,鄂卓尔氏,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1840),死于民国六年(1917),晚清重臣之一。荣庆幼年时期家境日趋困难,景况萧条,但其天资聪颖,成绩名列前茅,于光绪九年(1883)会试中式。光绪十二年(1886),荣庆进入翰林院,后累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他的仕途逐渐通达,并且在这一时期与山东巡抚袁世凯交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打响后迫使两宫西逃,于次年签订《辛丑条约》,奕劻负责北京善后相关事宜,荣庆成为奕劻的得力助手。两宫回京后荣庆提调政务处,为其后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光绪二十八年(1902),荣庆授为刑部尚书,因清末新政而创立京师大学堂后管理学部事宜。后又调为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参与预备立宪事宜。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慈禧相继逝世,荣庆充随入地宫大臣。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荣庆远离混乱的北京政局以遗老的身份居于天津。
一、荣庆与清末“新学”
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加之西方列强加快侵略步伐,清廷顽固派一改之前对变法的态度,认识到变法的重要性。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发布上谕,统治阶层希望通过变法改变局面,同时成立以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新政的办事机构。而新政极为重视教育问题,“废科举,重新学”成为此次教育改革的重点,学务成为新政首要任务。
(一)推行《奏定学堂章程》
推动教育变革、发展势必制定学制来对教育事业进行规范。早在1902年,张百熙向朝廷呈上《钦定学堂章程》,又称之为“壬寅学制”。它主要包含纲领、功课、学生入学等方面。此为晚清在新思潮冲击下的较之完善的学制,是近代中国首个学制,但仍存在某些局限。例如,在学制中并没有提及到女子教育相关内容,说明“壬寅学制”还存在封建残余观念,顽固派对“壬寅学制”也是有些不满的。《钦定学堂章程》中高等学堂课程中规定“无论其政科、艺科均为伦理第一,而伦理课程包括外国名人言行”。而《奏定学堂章程》在其高等学堂课程中规定记载是“人伦道德是指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择其心日用而明显简要者”。[1](P330)将其对比可以从后者中看出明确删除外国名人言行的学习内容,同时通过以上改变能够看出顽固派虽说言语上变革教育,但是思想仍是保守居上,这就给新的学制颁行提供一定的机会。
荣庆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到:“本日奉谕,会同张尚书管理大学堂事宜,拟谢恩折。”[2](P60)荣庆任为管学大臣,推动新的学制颁行。于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三(1903年6月2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着即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悉具奏,务期推行无弊,造就通才,俾朝廷收得人之效,是为至要。”[3](P5036-5037)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将其上奏建立《奏定学堂章程》上奏,得到皇上谕旨批准,“著其次第推行”。[4](P352)《钦定学堂章程》最终以“颁布未及二年,施又废止”退出历史舞台。
《奏定学堂章程》成为其晚清教育正式实施的学制,仍然沿袭《钦定学堂章程》中的不同学堂体制下的教育方式,对所有学堂教育体制进行再次完善,最为主要的还是将大学堂办学推向正规化,为后期实现现代的新式学制奠定重要基础。
(二)推动废除科举制度
变革中国教育体制,最为重要的当属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当时中国教育过于死板化,不利于培养全面人才。当然,身为学务大臣的张百熙和荣庆也是深知科举制度的负面影响。
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袁世凯就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弊端,他联合张之洞、端方上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袁世凯在奏折写到:“为时艰急需人才,科举阻碍学校,谨详陈得失利弊,酬筹变通方法,拟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一途。”[5](P735)不过袁的语气还是比较委婉的,仅仅是递减科举中额,多注重学校而已。并没有针对性提出废除科举制度。毕竟朝中顽固派势力比较强大,不敢贸然提出。袁仅是谨慎提出建议,不敢大刀阔斧地提及到废除科举。光绪帝仅仅朱批写到:“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5](P739)
光绪三十年(1904)荣庆不久便与张百熙、张之洞联名奏陈《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奏议中明确提出:“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明矣。……凡科举抡才之法,皆已括诸学堂奖励之中。然则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6](P107)荣庆、张百熙上疏到学堂教育的优势。不难发现两位学务大臣与袁相通的是两者所上奏的奏折语气也是较委婉的,“并非废罢科举”侧面反映出不敢贸然提及废除科举。
由于之前的两次上奏,清廷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来加强学堂教育,袁世凯联合张之洞、赵尔巽等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上奏写到:“拟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办办法以期有利无弊。”[5](P1186)语气较之前几次更为强硬。最终清廷可能从朝中臣子不断上奏中逐渐认识到科举制度弊端,于1905年9月2日,清廷发布其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4](P115)最终科举制度被废除,广设学堂,开启新式教育。
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荣庆在日记写到:“日本新闻报馆主理德当猪一郎偕译员高尾到,言中国学生只见明治初年之书,不免意见激烈,宜加以监督,并图录用,宜看等差。当答以朝廷急求才,故奖励颇为优厚,现在停罢科举,专重学堂,望之甚殷,责之不得不严。本大臣毫无学识,承乏教育,惟视学生如弟子之心,始终不易。”[2](P100)通过这则小记,可以看出荣庆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将教育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学堂上。再有,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教育受到日本影响,中国学生多读明治初年的书籍,不仅如此,在学堂管理方面也是“蒙询日本留学生及学堂章程”。[2](P109)
(三)关注留学事业
清朝末年,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思想等,荣庆也是在时代发展中逐渐摒弃传统观念,与时代共同进步。通过荣庆所撰日记,发觉到荣庆虽然为士大夫,但是他的某些思想是比较“新潮”的。他不同于维新派人士“激进”学习西方,同时也不与朝中顽固派为伍,这也是最可贵的地方。荣庆读《国闻报》,阅读严复的《原富》译本,认为其“语多可采”,[2](P60)认可西方的观点。荣庆同留洋之士尚其亨进行交流,认为“其言论固仍可采”。[2](P101)
荣庆与张百熙两位学务大臣逐渐认识到留学的重要性,于光绪三十年(1904),与张百熙、张之洞共奏《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主张道:“于时局实在情形,办事艰难之故,毫无阅历。……如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其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使之出洋游历,分门考察,遇事咨询,师人之长,补己之短,用以开广见闻,增长学识,则实属有益无弊。”[7](P21)荣庆希望能够让朝中大臣有其留学的机会,他也在日记中谈及到选派朝中大臣留学之标准:“请嗣后派学生必以中学优者为第一,如学生尚未卒业,可多派通籍之士。”[2](P91)通过筛选派遣留学的臣子,不辜负难得的学习机会。
(四)发展师范教育
随着新学的逐步发展,荣庆同众多学务大臣有意发展师范教育以教育国民、普及教育。荣庆联合张之洞、张百熙上奏道建立师范学堂的必要性,“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学堂必须有师,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省城之普通学堂,犹可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同时针对于发展师范教育,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主张:“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其已设有师范学堂者,教科务改合程度。”[8](P119-120)
二、清朝学部首位尚书——荣庆
学部是清末新政中设立的教育行政机构,于1905年设立,总管清末新政中的教育事业。荣庆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为学部尚书,成为清朝历史上首位学部尚书。其实,对于荣庆出任首位学部尚书一事可以说较之震惊。
早在清末新政之前大刀阔斧进行教育改革之前,张百熙就上疏进行教育改革,“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与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各抒所见,条议以闻。”[9](P15)由于张对待教育的思维较之新颖,1902年清廷发布上谕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3](P4789)由张负责新学事宜。而荣庆由于在庚子事变后,协助奕劻负责北京善后相关事宜,成为奕劻的得力助手。“两宫”回京后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荣庆“以政务提调相属”。[2](P51)随后,荣庆于1903年“会同张尚书管理大学堂事宜”,[2](P60)与张百熙共同管理学部事宜。张百熙早在戊戌变法之时就主张针对性提出教育改革,加之朝廷任命张为学务大臣,让世人深信由张出任学部尚书一职。但光绪三十一年(1905)荣庆升为学部尚书,其日记自述:“蒙恩调学部尚书,菊朋座侍,范孙右侍,任大责重,报称实难,殊为悚惕。”[2](P92)或许“悚惕”一词也是表达出荣庆个人对出任尚书一职的不可思议。
不仅荣庆觉得此事不可思议,更多朝中人士对此事倍感疑惑。《五云日升楼》记载到:“乃乙巳冬设立学部,海内喁喁,以为尚书一确,非张莫属。及发表荣庆为尚书。”[10](P10)而当时有人更直接质疑“然则荣氏之来,其为鱼朝恩之观军容以监制一切耶抑将驰入赵壁而夺此军符耶”。[11](P75)将荣庆就任学部尚书比喻唐朝鱼朝恩以观军容之名实则握其实权,反映出对荣庆出任此职的不信任。至此不禁疑惑到为何不是众望所归的张百熙出任此职?
首先,张百熙作为学务大臣主管教育事业,他的教育思想与措施触碰到封建顽固派的利益。《清史稿》评价“百熙一意更新”,[12](P9507)可见张百熙还是存在大刀阔斧进行教育改革的勇气与魄力。由于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看到张的教育思想,深恐无人与之抗衡,所以于1903年任命荣庆为学务大臣。同时清朝朝廷中重要官职由满汉官吏共同担任,这也是固化的传统。荣庆于1905年任用为学部尚书之后,张百熙“乃销学务差”,[13](P626)辞去学部职务。
其次,荣庆被任用为学务大臣之时,做事谨慎,慈禧多次向他询问“并学堂事宜”,[2](P61)荣办事皆以慈禧的旨意为准绳,可见荣庆在学部事宜多听于顽固派,是顽固派掌权所需要的臣子。加之荣庆作为主管教育之臣,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华教育界》对于荣庆的教育思想记载到:“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剂之,故中体西用之说,重读经以存圣教,不得废旧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戒用外国名词。”[14](P1)可见荣庆并没有完全做到学习西方思想,发展近代西方教育也仅仅是原地踏步,很难跨出封建思想束缚的门槛,这也与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思想不谋而合。从荣庆的日记中也可以察觉到他对传统经学重视。《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删除外国名人言行,并且要求“重经史学及学生行检,谨遵办以挽颓风”。[2](P110)光绪三十三年(1907),荣庆对教育内容进行调整,“前三人为一班讲经,张、朱为一班讲史,唐、宝为一班讲掌故及外事。”[2](P122)其频繁在日记中记录经学教授内容,彰显他对经学的重视:
“十一月初五日,陆师进讲克明俊德七局。”[2](P110)
“十一月初八日,陆进讲致知在格物句。”[2](P110)
“十一月十四日,陆师进讲君子贤其贤四句于勤政殿。”[2](P110)
“十一月十八日,陆师恭讲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二句于乾清宫。”[2](P110)
同时,张百熙与荣庆作为学务大臣,共同管理清末新政教育事业,但是二人的关系没有想象的融洽。二人的学术思想既各不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歧异。其主要的原因是对待教育的不同态度:张百熙敢于改革,大刀阔斧学习西方;而荣庆谨慎为上,治学思想没有那么前卫,于此,二人存在分歧亦是正常。通过张百熙与荣庆在官场上的矛盾,也能够反映出满汉官吏在朝堂的权利倾轧。
三、结语
荣庆作为晚清的重臣,虽然进入仕途之初并没有得到重用,从其日记中可体会其失意之感。但在庚子事变后,荣庆迎来仕途的“春天”,朝廷逐渐委以重任,其个人也发觉自己身上所背负的重任,办事格外谨慎。荣庆作为清朝首位学部尚书,不能否认他为推动教育现代化所做的努力。他以自力推动新的学制实行,助力废除科举制度并希望朝中大臣有留学机会,努力为清朝的繁荣昌盛贡献已力。辛亥革命后,荣庆目睹了清朝灭亡,留下无限伤感,自此久居天津远离北京混乱政局。无论从其日记中,还是相关史料里,都能体会到他作为臣子的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