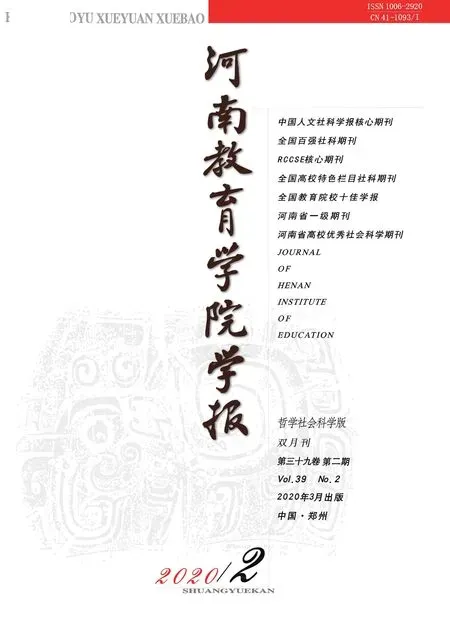通神、祈福与逸乐:历史学视野中贵州石阡木偶戏的文化内涵
李 渌
木偶,古称傀儡。以演员操纵木偶以表演故事的戏剧叫木偶戏或傀儡戏,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位于贵州东北腹地之石阡,保留着中原汉族的原始木偶戏艺术。石阡木偶戏是杖头木偶戏在贵州的遗存,这与其存在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悠久历史密不可分。在西南地域,石阡建制悠久。据史料记载,早在秦嬴政二十八年(前219年)就已置夜郎县,隋开皇元年(581)置寿州于石阡,唐武德四年(621)置夷州。民国《石阡县志》载:“石阡得名始自元,置石阡等处军民长官司隶恩州宣抚司,明初改石阡长官司,至永乐十一年置石阡府。”[1]408明设府至今已六百余年。石阡木偶戏正是在这厚重的历史文明环境中得以根植和发展起来的。石阡自明初设府以来,历代来石阡“守土”的流官积极传播中原汉文化,再加之历史上石阡境内的龙川河入乌江水路通达,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地的商人来石阡经商者甚多,中原汉族的地方戏和木偶戏随之传入。
虽然官方史志缺乏记载,但我们可以从一些诗词中看到明清时期木偶戏在贵州境内流传的情况。如王阳明的七律诗《龙场傀儡戏》中载:“处处相逢是戏场,何须傀儡夜登堂。繁华过眼三更促,名利牵人一线长。稚子自应争诧说,矮人亦复浪怨伤。本来面目还谁识,且向樽前学楚狂。”[2]146《石阡县文化志》中选录有明崇祯辛未科进士费道用的《淡言步蔡远卿韵》诗:“高台百戏看伶优,才说收场转眼留。随俗悲歌皆木偶,凭人轩轾总虚舟。聪明自古多招射,贫贱原来不用愁。豁鼻巨肩闲谷相,赠君重咏四宜休。”[3]7中原传入的木偶戏,与石阡风俗相结合,接收当地的语言声腔,形成了具有地域风格的石阡木偶戏。黔东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也使得这一独特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保留下来,如今成为贵州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其他地方的木偶戏艺术相比较,石阡木偶戏原始古朴,内容丰富,有自己的独特的表演风格。至今,石阡木偶戏依旧活跃于黔东北乡村地区,保留了古代木偶艺术的原生形态及文化内涵。2005年8月石阡木偶戏申请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书中就载有179出剧目,所有剧本内容均由历代不同戏班的木偶艺人口传保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从艺术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入手,研究其内在的戏剧特质、文化价值及保护措施,对石阡木偶戏的本体却少有研究。在时空变迁之中,这一遗产的物质留存不断在变化和调整,其诸多文化元素渐趋形成象征符号。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在人类学、历史学的观照下,探讨石阡木偶戏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以期为这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文化遗产在未来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更丰富的资料。
一、石阡木偶戏文化内涵之观察载体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通过对传承人的深度访谈、现场观演、剧目研读等方式研究石阡木偶戏的文化内涵。石阡县坪山乡的木偶戏班饶家班的传统剧目中流传的唱词,为石阡木偶戏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也是研究过程中极佳的观察载体。以下罗列三份剧目中的不同演唱内容来归纳石阡木偶戏的文化符号。
其一,在口传剧目《请神科》中有以下唱词:
弟子烧起一柱(炷)真香,二柱(炷)明香,三柱(炷)宝香,香不乱烧,神不乱请,烧起五色祥云绕绕,盖吾弟子身前,盖吾弟子身后;……奉请梨园会上千千师祖、万万师爷。唐朝敕封风火院内,金花小姐,梅花娘娘,宫堂里内、老龙太子、神神请在香炉头上受领真香。来,是立香奉请,去,是倒香奉送。(1)本文所引石阡木偶戏唱词均出自饶世光的《石阡木偶戏国家传承人口述整理本》,下不一一标注。
其二,在口传剧目《赐福天官》中有以下唱词:
诗书千卷、黄金万两,献上主东君,后来他子子孙孙来个福以长、寿以长,福禄福寿久久长。
其三,在剧目《姑娘出台》中有以下唱词:
和尚、和尚,你是天上掉下来的天和尚,将你天上星斗盘一盘,哪样星君独一个,哪样星君姊妹多。过天星君独一个,七仙女来姊妹多。紫薇星君当头坐,二十八宿排两旁。叫声和尚你听着,且听奴家盘天河:天上黄河哪个开,月里桫椤哪个栽。天上黄河老龙开,月里桫椤古老栽。
《请神科》道出了石阡木偶戏通神的历史功能,《赐福天官》道出了石阡木偶戏祈福的文化意蕴,《姑娘出台》蕴含了石阡木偶戏与民娱乐的生活精神。
本文以贵州省石阡县木偶戏班饶家班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通神的历史功能、祈福的文化意蕴、逸乐的生活价值三个方面分析石阡木偶戏的文化内涵。
二、石阡木偶戏之通神功能
民间信仰中的“神”是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人们所崇拜的人死后化作的精灵、神仙等。木偶戏之通神功能表现为木偶戏艺人把人们的愿望通过一定的仪式转达给神灵,又把神灵的“庇护”转达给人们。通神包括祭祀性的请神、酬神、送神三个环节。从事木偶戏表演的艺人充当了人与神的桥梁,满足了人们求助神灵的愿望,这也是石阡木偶戏能够在民间存在的基础。历史上,石阡是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本土夜郎文化的交会地区,木偶戏这种通神的历史内涵和存在价值,使其在具有“信巫”特征的西南少数民族中具有了坚强的生命力。
石阡木偶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通神艺术。木偶戏班的艺人们自称能与鬼神通话,并能在祈者与神灵之间起到报告愿望、传达旨意的作用,或是借助正神的法力驱赶作恶的鬼魔,或是以歌舞表现、贡品等取悦神灵,使其赐福于祈者,最终实现驱灾除病、保佑平安之目的。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石阡县坪山乡饶家戏班的班主饶世光说,只要他们默想木偶宗师陈平仙官,就会与这位保佑戏班的神灵接通联系,从而被赋予“法力”,再利用优美的木偶说唱表演“娱神”“抚神”,采用“以法斗法”的方式,便可达到“扫除瘟疫”“赐福人间”的目的。木偶戏艺人们总是通过这种“接触神灵”的方式来显示他们通神的本领。
从古至今,石阡木偶戏在演出时与神灵的沟通都是通过一套完整的仪式,包括立牌位、请神、演出、送神来实现其“祈福还愿”的目的。舞台搭建好后,戏班艺人就会立牌位请神。请神时,香案设在后堂或在主家堂屋,香案上摆放各种供品,香案正中放一升大米,中间插一牌位,上书“正乙冲天风火院内岳皇戏主金梅二宫”,右书“大汉楚国陈平傀儡仙师”,左书“中天星主北极紫薇元清大帝”;戏班班主亲自焚香、点烛,立于牌位前作揖鞠躬,念咒密语,恭请相关神灵。演出结束,再由班主举行送神仪式,请众神各安方位。在请神和送神中,班主还要颂唱词曲,饶家班的《开坛科》唱词是:
五楼世界我立起,洗手焚香请神灵,双膝跪在城云地,要请满堂奉神灵。请前坛祖师黄世明、养坛师公饶奉祥、祖师饶法兴、师太饶法开、师公饶法林、师伯饶法清、师叔饶法正、传渡师父饶法明,大庙之中,小庙之内,一切神祗(祇),请在化坛纸上,受领真香。
从木偶戏班班主的确立上也可以看到通神功能的存在。在石阡木偶戏艺人们的心中,木偶戏的宗师陈平仙官只接受那些具有诚实、讲信用、有爱心、尽职尽责的优秀品质的班主的祈愿。对于神灵没有肯定的班主,陈平宗师就不会保佑,他们就不能胜任替人还愿消灾的演出。所以,班主的确定不仅依赖上辈班主的考核,同时上辈班主还需借助“神的决定”来影响班主的推举,对其品质的评判最终是由神灵来决定的。这就使得选出来的班主因神的威慑力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进而做到热爱戏班、尽心尽力地帮助主家实现消灾祈福、保佑平安的愿望,使其真正成为戏班的灵魂人物,这也是木偶戏艺人们非常向往和羡慕的荣耀。
三、石阡木偶戏之祈福功能
祈福自古为中国较为传统的民俗,指人们向神灵许愿,特别是在遇到厄运或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时,希望得到神明庇佑,增加福运,化险为夷,平安度劫。民间祈福文化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祈求人寿年丰、多子多福是我国民间传统文艺活动都包含的意蕴。如《周礼·天官·膳夫》就记载有“凡祭祀之致福者”[4]1。与中国的其他传统戏曲相比,石阡木偶戏在这方面的功能更为突出,辟邪纳吉、恩泽万物的祈福色彩更为明显。相传汉高祖时期,蝗灾严重,汉高祖很是担忧,陈平仙官便以木偶演戏,所到之处,蝗灾皆平。从此,木偶戏就传于四方,流于后世。这个故事凸显了木偶戏“驱病驱鬼”、“扫除瘟疫”、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功能。
流传于云贵高原地区的石阡木偶戏,区别于官方文化、上层文化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并兼具当地仡佬族、土家族等民族民间特色。在民间发挥的强大祈福功能是它得以保存至今并深受人们喜爱的内在缘由。在田野调查中,石阡木偶戏的艺人们都会说,木偶是有灵性的,无论何家何人有难,只要向木偶宗师陈平仙官许愿,顶上木偶戏的牌位,演出一台木偶戏,就能事事顺利,平平安安。在当代,石阡民间邀请木偶戏班演出的目的,大多也是祈祷丰收、祈雨、祝福新生婴儿、庆祝新人成婚等。石阡木偶戏申请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书中推荐的剧目《财神图》《瘟蝗症》《大团圆》《五台山还愿》《双麒麟》《安安送米》等都具有祝寿、驱邪、祛病的内涵。比如石阡饶家班剧目《赐福天官》道:
诗书千卷、黄金万两,献上主东君,后来他子子孙孙来个福以长、寿以长,福禄福寿久久长。
《香山还愿》开篇就唱道:
小生,艾方卿,娶妻付氏赛金,自从夫妻匹配以来,恩同于水,义重于山,夫妻膝下无有子嗣接后,我们在花园许了愿,观音菩萨灵验,送来了一双娇儿,到如今要去还愿。[3]92
再比如剧目《神皇土地上台》:
一网去、二网来,双打梅花捧雪开。三网去、四网来,打出一个娃娃来。把这个娃娃交给主人家,交给他天地君亲师五大圣人,让娃娃百年长寿好运来。
可见,在祈福内涵中“祈生还愿”的文化符号尤其突出。石阡木偶戏在为家庭“生子还愿”时演出的《仙姬送子》《双麒麟》《香山还愿》等都是为主家祈生、佑子的传统剧目。祈福与祈生,让石阡木偶戏与世人的生殖愿望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四、石阡木偶戏之逸乐功能
逸适安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大众在其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逸乐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很早就衍生成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价值体系。很多历史学家正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的逸乐精神,李孝悌认为:“要提醒研究者自身正视‘逸乐’作为一种价值观、一种分析工具、一种视野以及一个研究课题的重要性。……研究者如果囿于传统学术的成见或自身的信念,不愿意在内圣外王、经世济民或感时忧国等大论述之外,正视‘逸乐’作为一种文化、社会现象及切入史料的分析概念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对整个明清历史或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解势必是残缺不全的。”[5]序9
时空变迁使得石阡木偶戏这一遗产的物质留存、历史记忆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逸乐精神作为其本质内涵及文化符号传承至今。在田野调查中,通过现场观演等方式,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了这一传统地方戏剧之逸乐生活价值。
从演出表现形式来看,石阡木偶戏显示了民间逸乐文化的元素。其主要表演形式唱、念、做、打,均表现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听起来悦耳。比如,石阡木偶戏表演时,有只说不唱的“念白”,所念词句精练、幽默,音乐表现抑扬顿挫、有松有紧,特别是它的表现形式之一“数板”,将节奏自由的语言纳入固定节奏的规范之中,将人们生活中的道理用诙谐、快乐的方式传达出去,极具娱乐功能。比如,剧本《薛仁贵战摩天岭》中有这样一段数板:
人老了,人老了,人从哪里老?人从我这头发老。少年时,青的多,白的少;到老来,白的多,青的少,看到看到就白完了。人老了,人老了,人从哪里老?人从我这眼睛老。少年时,远的看得多,近的看得少;到老来,近的看得多,远的看得少,看到看到就看不到了。[3]54
它以一种通俗、诙谐的娱乐方式将日常生活中的认知观、人生观传达给民众,让他们在逸乐中接受真善美的教化和熏陶,这也是石阡木偶戏深受民众喜爱的主要因素。
再如,石阡木偶戏里的武打场面精彩纷呈,是吸引民众争相观看的主要因素。它根据剧目、剧情的特定环境以及人物的特点设计不同的武打动作,一般武生、武旦动作飘逸,丑角的武打则滑稽且具有杂耍性,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这也是石阡木偶戏具有逸乐内涵的特色之一,精彩纷呈又诙谐滑稽的武打场面是使民众尽情欢笑的逸乐要素。
从演出选择的内容来看,贵州石阡木偶戏具有民间逸乐文化的根基。首先,表演的剧目内容大多来自《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故事。表演内容选择喜剧、闹剧,舍弃悲剧,擅长表演历史闹剧和武打剧。其次,它的表演语言选择与地方风貌、乡土人情、语言习惯等相同的戏曲语言风格,更多地展现石阡方言的特色,表演习俗与石阡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同时,艺人绝大多数生长于农村,有较深厚的生活基础,表演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娱乐气氛,因而深受大众喜爱。
在石阡,每当冬令农闲或春节期间,各村寨都要集资请最好的戏班唱“撰本戏”,少则数日,多则月余,连台演出,通宵达旦。很多乡村,普通人家在娶亲、祝寿、迁新居、生子等重要日子,也会邀请木偶戏班来祈福还愿。经历几百年的实践,石阡木偶戏已经成为黔东北地区乡村民间欢度节庆、集体逸乐、自娱自乐的重要方式,在调节单调的乡村生活、活跃生活气氛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五、结论
中华民族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保留了人类文化宝库中精湛的技艺和手艺,而且是对大众生活形式的一种创造。石阡木偶戏作为人类文化发展之轮上的一个链条,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梳理“石阡木偶戏”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与符号,离不开用历史的眼光对其进行历时性发展的观照。时空变迁之中,这一遗产的文化背景、物质留存及历史记忆随传承主体、地域受众而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痕迹,形成了多维度的想象空间。如今,石阡木偶戏诸多文化元素渐趋形成象征符号,其文化内涵则因重构而建构出丰富的意义,可以说,石阡木偶戏是微观呈现区域个性文化的极佳聚焦点。
从历史起源、演出内容、演出功能和形式等方面分析石阡木偶戏深刻的文化内涵,为我们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戏曲学等领域研究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多学科学术价值的珍贵资料,同时也可以向国内外充分展示石阡木偶戏作为“边缘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不仅可以唤醒当地人的文化自觉,也可以让更多有识之士参与到木偶戏的研究与传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