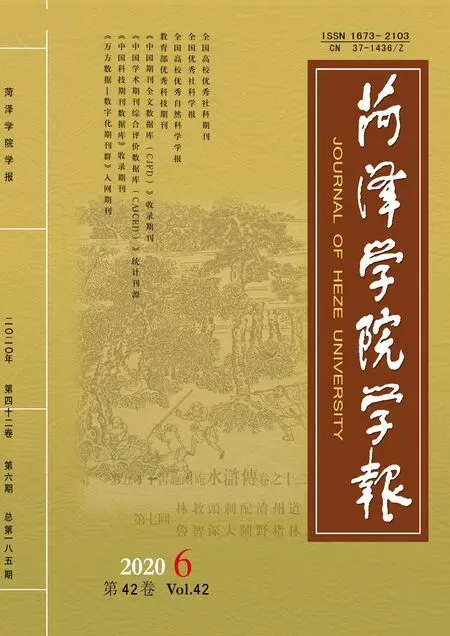毕飞宇小说的女性生存境遇
——以《玉米》《青衣》《平原》为例*
周 敏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毕飞宇是当代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在近乎20年的创作生涯中,尽管他的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发生过重大变化,但是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由此也被誉为当代最关注女性的作家和“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无论是都市题材的小说《哺乳期的女人》《林红的假日》《推拿》,还是乡村题材的《玉米》《平原》,都成功地刻画出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他用日常化的叙事执着于书写男权社会下平凡女性的弱势地位,以平静温和的方式进行现代性批判的启蒙。在《青衣》《玉米》《平原》中用轻缓流畅而又智慧的话语以及沉重的人性主题为读者构筑了一个复杂的女性世界,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女性在物质、权力、欲望和情感尊严下的苦苦挣扎,在命运的轮回里左冲右突。
一、“人在人上”的欲望蛊惑
中国社会发展史形成了中国社会独特的政治型范式和官本位的思想,这种思想最直白的民间表达就是“出人头地”“做人上人”,它是中国人潜意识里难以割舍的情节与执着的追求。它的正面价值是让人积极向上,服从权威。负面价值是窝里斗。毕飞宇曾在《沿途的秘密》里将之称之为鬼:“我们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身上。”[1]他的小说《青衣》《玉米》《平原》都写出了鬼文化场域下平凡人物追求“人在人上”的刻骨疼痛。在这些作品中,那个鬼在生活的日常里依附在每个人身上作祟,蛊惑人们钻进它的圈套,掉进痛苦的深渊。
在《青衣》中,19岁的筱燕秋痴迷艺术,在自己青春生命即将绽放华彩的档口,因为不想让出舞台给别人一次机会而采取激烈手段让他人毁了容。被迫退出舞台的她内心埋藏着巨大的痛,这个痛就是“不甘心”。她太渴望那个让她成为仙子的舞台,太渴望成为那个众人仰望的嫦娥,成为“人上人”。因此当二十年后机会又一次来临,为了登台,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为了登台,再一次背弃了对徒弟的承诺霸占住舞台。因为出人头地已成为筱燕秋一种执念,二十年的等待后,让她为抓住这一刻机会奉献出女人的肉体。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着人都渴望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的认同,但是为了做人上人而不择手段地将别人踩在脚下,出卖肉体,损害身体,这是社会规则所不允许的。毕飞宇借嫦娥之口说出了筱燕秋的感受:“人是自己的敌人,人一心不想做人,人一心就想成仙。”[2]因为仙高高在上,高高在众人上的优越感让筱燕秋心醉神迷。
极权时代,权力的威力可以被无限放大,以赤裸裸的形式显示着耀眼的光芒。在《玉米》中,在贫穷封闭的王家庄,村支部书记是最高权力,他横行霸道荒淫无耻,20年里他睡遍了村里他看得上的女人,横穿“老中青三代”,甚至是刚过门的新媳妇。作为在权力利益浸润下长大的王连方的长女玉米,享受着村里人的高看,早已领会权力的重要:“权力就是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里握出汗来,权力会长出五根手指头,一用劲就是一个拳头。”[3]母亲生了弟弟老八后,玉米逐渐成为这个家里的家长。为了让自己在妹妹们中拥有绝对的说一不二的权力,她用心谋划的第一件事就是设计一步一步训服最不听话的玉秀。提起婚事,她知道自己肯定比同村姑娘有“更好些的未来”。那个出身卑微长相难看的彭国梁因为解放军飞行员的身份让她产生了飞黄腾达的梦想,因此恨不得一口将亲事定下来。王连方倒台失去权力后,飞行员主动退了婚,玉秀玉叶的受辱被报复,墙倒众人推的巨变让玉米绝望,心高气傲的玉米知道,只有把自己嫁给权力,这个家才能一切重来,“给我说个男人”“手里要有权”,有权是玉米嫁人的唯一条件。玉米匆匆嫁给了手握重权的老男人郭家兴做填房,把自己卖给了权力。相比于玉米的强势和工于心计,玉秀的追求简单很多,她不管家事,只喜欢在外卖弄姿色,凭借父亲王连方对她的宠爱,她在家里啥活也不干,并不把玉米放在眼里。玉米结婚后,无处安身的玉秀只能投靠玉米。然而在姐夫家里,她发现了玉米地位的卑微,为了能够长久地留在郭家,她花费心思收买郭家兴的女儿郭巧巧,阳奉阴违不软不硬地与玉米对抗。这是那个追求“人在人上”的鬼在作祟。《玉米》中的玉秧是个在家里被严重忽视的孩子,凭着自己的苦读考上了师范终于在家人眼里大放光芒。但是在学校里,她平庸的一切引不起老师的注意,来自农村又遭受着城里孩子的排挤,她在别人的冷落与伤害中积聚着怨气,因此当魏向东以学校护卫队长领导的身份向她表达器重并“委以重任”时,她感觉到了“自己有用”,也终于有了“出头”的机会,监视同学的“特务工作”让玉秧上了瘾,她尝到了有权整治别人的甜头。
相比玉米三姐妹,《平原》里的吴蔓玲是被“人在人上”这个魔鬼蛊惑得更为惨痛的女性。吴蔓玲是个从大城市来到王家庄的知青。刚到王家庄的她就喊出了著名的要做乡下人不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做女人的口号。她颠覆了城里人和女性的形象,成了王家庄的“亲闺女”和“铁姑娘”,政治上的出色,劳动上的拼命使她很快成了王家庄年轻的支部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一句“前途无量”的肯定让她彻底屈从了魔鬼,上大学、招工回城的机会被她一次次放弃,为了在男权的社会赢得权力,她比男人更像男人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在王家庄,她热衷于“与人斗”并感觉到胜利者的“其乐无穷”,因为她总是胜利者。“人在人上”的鬼让吴蔓玲完全痴迷。
二、男权主体下的悲哀
男权社会下,权力的社会主体只能是男性。女性作为男性主体观照的客体,只是作为男人认识自我的的参照物而存在。林幸谦在《女性主体的祭奠》中说:“在中国的宗法父权社会里,女性在‘天’‘阳’‘乾’‘君’‘父’等宗法象征主体下,即被定义为附属于男性的他者概念之下。”[4]他者的身份规定了女性只能是男人们建构历史的“陪衬物,是胜利者的垫脚石和鲜花,是失败者的眼泪和殉葬品。”[5]
《青衣》中一向以孤傲的仙子嫦娥自居的筱燕秋,为了重上舞台圆梦“嫦娥”,最终还是选择向老板献上自己“冰清玉洁”的肉体,这个“女人最古老的法宝”产生的羞辱让她心魂不宁,灵魂被啃噬,她无法面对丈夫关爱的眼神,人变得神经质,那歇斯底里的尖叫喊出了蚀骨的疼痛。
“每个人的身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权力和等级的影子,多数人受惠或受害于此,但自己却不察觉。”[6]施桂芳是村支书王连方的老婆,作为村里的第一夫人,应该是夫贵妻荣,但是在这份荣光背后,她要忍受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对王连方在村里的荒唐行径,她不能过问;她肩负为王连方家传宗接代的任务,在王连方的吼叫下,她必须没完没了地怀孕生育,直到生出儿子。在儿子出生后,她成了家中可有可无的影子,王连方连和他说话的兴趣都没了。她就是作为一个生育工具而存在。
男权社会规定了女子的“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物,从不是独立的个体。在王家庄这个小社会,每个出了嫁的女人都不再被使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一个属于男人的标签来称呼:财广家的、有庆家的、大贵家的等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权力可以是杀人的大棒,对抗权力的后果人们心知肚明。王连方靠着手中的权力,肆意地侵犯女人的身体十几年,但是却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王家庄的女人怕他也巴结着他,王家庄的男人也被权力压得猥琐。在自己的女人被王连方侵犯享“呆福”时,他们不敢怒更不敢言只能把仇恨发泄到自己的女人身上。女人遭受着来自自己男人的另一种欺辱,只能承受着“不要脸”“骚货”“狐狸精”的骂名。
波伏娃说过,结婚是少女唯一的谋生手段和使她的生存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方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路。玉米对自己的婚姻有过考虑,父亲的荒淫和母亲的无奈已让她明白“官人家的男人是不能让人放心的”。于是那个箍桶匠的儿子、身为飞行员的彭国梁点燃了玉米对爱情的美好幻想,她坠入爱河。但随着王连方因为上错床被双开,两个妹妹遭轮奸,彭国梁听信谣言斩断关系,这一系列的突然变故让玉米彻底领悟权力才是过日子最重要的东西。她必须抓住嫁人这个女人唯一的机会才有可能让王家一切重新再来。在那个宾馆里,在她自己扒光了衣服爬上了老男人郭家兴的床的同时,心高气傲的她也扒光了自己的自尊。嫁到郭家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振兴计划,她在床上变换各种花样讨郭家兴欢心,为了套住他的心,她必须尽快怀孕。玉米不知不觉中重蹈了母亲的命运,成为男人的性奴和泄欲的工具。
男权社会下,男人总是在成功地引诱女人出轨后,再无情地用传统的观念把他们抛弃。有人说男性对女性的处女情结来源于女性是“皎洁的白纸”意识。男权文化建构的女性处女情结,实质是将女人看作是物化的属性。玉秀被王家庄的男人糟蹋后,心里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被人嚼过的甘蔗谁还愿意再嚼第二遍?”“一个破货”,在欲望与自轻自贱的挣扎中玉秀再一次被男人欺辱和遗弃,在欲死不能的痛苦中承受怀孕产子的苦果。
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只要男权存在,女人就摆脱不了被改造的命运。这种改造多数像施桂芳、像玉米,但是在《平原》里,毕飞宇还给我们赤裸裸地展示了男人对女人的改造给女人带来的人格悲剧。在王家庄吴蔓玲这个“铁姑娘”只能以“非我”的状态存在,“铁姑娘”是她不能蜕掉的壳,而“前途无量”则把她钉死在了王家庄。理智使她无法像他人那样恋爱,情欲却让她难以压制,人格分裂后她的结局是极其悲惨的。
三、同性的相争与伤害
男权社会下,女性作为被欺压者,没有条件与男人抗衡,为了获得“人在人上”的快乐,她们更倾向于将同是弱者的女性当成对手。西苏说过女性在父权的引导下变成自己的仇人,憎恨自己,与女性为敌。她们通过伤害同性的他者来获得自己的主体性权力。
为了男人丢下的一点好处,明争暗斗,相互打击伤害,相互嫉妒,导演出无休止的女人的战争。三个女人一台戏。这是女性的悲哀。
在《青衣》中,为了一个能够引人注目的嫦娥角色,三代女青衣忘掉了曾经的师徒情分名争暗斗:筱燕秋孤傲不把他人放在眼里,李雪芬忍无可忍针锋相对,最后以两败俱伤而告终;春来作为筱燕秋的爱徒,为了争夺台上的主角,利益面前师徒关系迅速瓦解。嫉妒让人性彻底扭曲。
男权话语下,女性不仅被侮辱被侵害,还被要求替施暴者承担责任,而真正的施暴者却堂而皇之逍遥法外。王家庄的女性是被王连方欺辱,面对强权,她们无法摆脱魔爪进行反抗。然而作为不幸者,她们在承受家里男人们冷暴力的同时,还得忍受玉米门前的羞辱。为了替母亲报复和震慑那些与父亲有染的女性,玉米抱着弟弟小八子去那些女人的家门口坐着,用锐利的眼光和只有她们之间能懂的特殊话语震慑对方,一个也不放过。她的揭发和挑衅给母亲争回了颜面。但是却不自觉地拿起了维护男权利益的贞操观羞辱了同性。
女性的权力之争多发生在家庭内部。传统家庭中,男性永远是主宰,一旦男权缺席,一些具有某些优势的女人就会迅速上位扮演起家长的角色。玉米是非常聪明的,她利用父亲去外面开会的空隙恩威并举拿下了玉秀独揽了家中大权。在郭家,这两个“前世冤家”继续斗法,郭巧巧成了玉秀抗衡玉米的有力武器。郭左与玉秀的隐秘恋情让玉米感受到的不只是伤及脸面的危机,还有她在郭家地位。她懂得男人最在意女人的东西,于是假意让郭左给玉秀介绍对象,一句“玉秀呢,被人欺负过的,七八个男将,就在今年的春上”让玉秀被郭左踩到脚下。同根相煎是最深的痛,玉秀在遭到轮奸羞辱后玉穗在王家庄伙伴面前给玉秀扣上“尿壶”“茅缸”,使她在王家庄再也没法呆下去。《平原》中的三丫是个热情率真的女子,她如飞蛾扑火般地爱上了端方并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端方。但是母亲孔素贞就因为端方母亲的态度,决意要断掉这门亲事。在她知道女儿三丫与端方发生了关系后,迅速安排了与鳏夫瘸子的婚礼,三丫的抗争最终丢了性命。
毕飞宇的小说以女性形象的丰满生动而为读者喜爱。他的小说写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榨和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他将作为女性的主宰者和改造者的男性描写得单薄苍白,由此呈现在这种隐性的权力压制下女性所遭受的悲惨境遇。他对特殊时代人性的追问和反思具有温和的启蒙主义思想,呼唤着女性主体性的回归。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