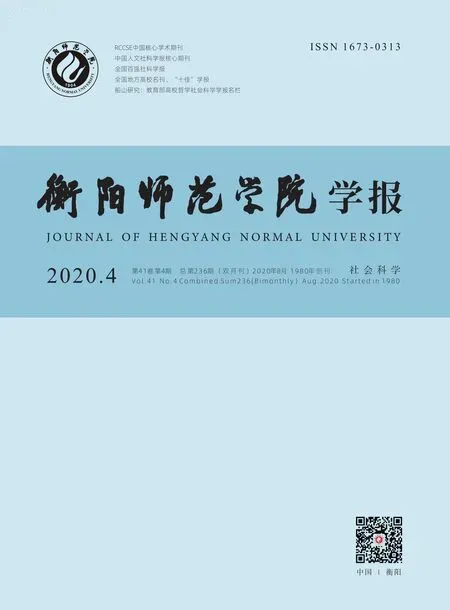山崎暗斋濂溪学文献与文献学思想
王晚霞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199)
山崎暗斋(1618-1682),名嘉,字敬义,号暗斋,又号垂加,通称长吉、清兵卫、嘉右卫门,是日本江户时代重要的朱子学者,门人众多,称为崎门学派,影响甚大。目前中国学界对山崎暗斋的研究不多,且集中在暗斋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它们以朱谦之的《日本哲学史》 和《日本的朱子学》、王守华和卞崇道的《日本哲学史教程》 为代表。近几年研究侧重点逐渐丰富,但整体而言,仍以暗斋与朱子学的关系为多,当然也有个别文章关注了暗斋的神道思想、政治思想等。相对于暗斋在传播和发展宋学中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对他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推进空间,尤其是山崎暗斋搜集整理了多部宋学文献,但目前学界对其文献思想鲜有论及。此外,对暗斋推动濂溪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亦鲜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而濂溪学作为宋学或说是朱子学的理论原点,不仅不可回避,且必须深入钻研。本文立足山崎暗斋的文献整理成果,以三种濂溪学文献为中心,探讨暗斋的文献学思想及其学术价值。
一、山崎暗斋文献整理实践
暗斋著述基本概貌,可由存世的《山崎暗斋文集》[1]得知。
(一) 著述概况
暗斋的著述主要体现在《山崎暗斋文集》,四卷四本。由该文集可知,暗斋的著述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暗斋自著,包括《垂加草》《垂加文集》《续垂加文集》《垂加文集拾遗》《辩本朝纲目》 等,这几部分加起来篇幅不长。第二类,也是占绝大部分篇幅的,是文献整理类,如《文会笔录》《周子书》《图书抄略》《蒙善启发集》《孝经外传》《朱易衍义》《中和集说》《武铭》《仁说》《朱子训蒙诗》等。这类著述无一例外都加上了日文训读,有助于宋学经典在日本的传播。这其中少量是宋学经典原文,大量的是由对宋学原文的摘录、汇集后进行重新整理、排列、考订、编辑而成。所以,研究暗斋在日本的影响力,必须研究其文献学思想及其价值。
鉴于暗斋编纂的文献众多,下面只以其中三种濂溪学文献为例详细考辨其文献学思想。
(二) 三种濂溪学文献
理学开山祖周敦颐,因其故居前之溪名濂溪,故世称濂溪先生。周敦颐在南宋时从祀孔庙,封汝南伯,在元朝又被封为 “道国公” ,明清两朝在继承前代各种肯定与褒扬的基础上,又有皇帝赐匾、题诗、注解濂溪著述、优恤后裔等尊崇。历代朝廷对周敦颐的尊敬重视,推动儒林对濂溪之学风靡景从,宋代胡宏、朱熹、张栻在序、跋、题、记中反复阐发周敦颐思想学说的学术史价值,认为它是上继孔孟、下启二程,延续断裂一千五百余年之道统。伴随朱熹精心注解的《太极图解》《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以及黄幹、陈淳、蔡元定、游九言等接继朱张二人之说,在新的维度上进一步拓展深化濂溪之学,濂-洛-关-闽的学术承传次序由之渐稳,成为儒者共识。由周敦颐开创的濂溪学,简称濂学,如此稳居朱熹等倡导的道统论之枢纽地位,便成为宋学、朱子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原点。作为当时国际先进思想,宋学很快就传播到东亚各国,由此推测,濂溪学传入日本大概在镰仓时代前期[2]。整体上看,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僧对濂溪学的崇敬与受容,是宋学在江户时代崛起为日本社会主流思潮的反映。江户初期,被弟子称为 “日本的周濂溪”①的大儒藤原惺窝(1561-1615) 及高足林罗山(1583-1657)力推宋学;其后,山崎暗斋将宋学在日本推向全盛。暗斋整理的文献中有三种濂溪学文献。
1.《周子书》日本正保丁亥(1647) 年刊本
此本是暗斋搜集整理濂溪学及相关史料的集合,不分卷次,内容有五部分:一是《太极图》和朱熹注《太极图说》;二是朱熹注《通书》和朱熹的《记通书后》《通书后录》《周子太极通书后》;三是周子的8 篇遗文;四是遗事,主要是一些儒者的评说,类似于其他濂溪学文献中的诸儒论断;五是事状,还有朱熹的三篇序。
卷尾有小跋云: “周子之书,朱子所集次,余未见之。度氏《濂溪集》附谢氏《濂溪志》,徐氏《周子全书》皆非其旧矣,爰不自量参考编次,以俟异日得原本云。正保丁亥五月四日。山崎嘉跋。” 牌记为 “天保十四卯正月,风月庄左卫门河内屋万助求板” 。天保十四年(1843) 暗斋已离世,可知此本只是重印。明万历21 年胥从化、谢贶编有《濂溪志》②。文中度氏指度正,谢氏应是指谢贶,徐氏指徐必达。由小跋可知,暗斋虽然知道但并未见到朱熹编辑的周敦颐集,而度正本、谢贶本、徐必达本都不是原本了,于是暗斋自己参考前述书稿,选定编辑了这本书。
2.《周书抄略》日本延宝七年(1679)年刊本
此本将周子著述中的部分内容按主题分条归类罗列,然后围绕该主题再选取相关的史料辅之,如周子遗事、诸儒评议等,又附加暗斋评议,组合在一起。《周书抄略》按主题分为上中下三部,内容依次为《周书抄略序》《天地凡四条》《人伦凡五条》《为学凡四条》。每条以周子著述中的内容为主体,下附二程、朱熹等人的相关问答、解释、评论,以示阐发。
此本的体例与任何一种中国濂溪学文献都不同。暗斋将周子著述中的具体思想内容分为三部,分别与天地有关,与人伦有关,与为学有关。读暗斋《周书抄略序》可知其关注点在周子的 “诚” 的思想。 “盖天地之心,诚而已矣” ,可以说这是暗斋编辑本书的初衷。序末署时为延宝七年(1679)。从体例上讲,暗斋以引用其他人的史料来注解周敦颐著述的这种做法,也就是以经典来解释经典,同时又严格核实史料、典故真实性与出处,既有文句训诂,也有对文献的批判,其附加的个人评点也没有完全忽略宋学看重的义理分析。
3.《濂洛关闽》
《文会笔录》是暗斋代表作之一,共20 卷。如上所述,这是暗斋在研读朱子学相关文献后,按20 个主题,将相关史料抄录、整理,并对这些史料附加简单评注而成的文献著作。《文会笔录》第十卷题作《濂洛关闽》,分为之一、之二两部分。此本史料分条罗列,无二级标题,围绕周敦颐进行选摘、抄录,共计108 条。史料来源用小字注于文中,来源文献主要有宋朱熹的《朱子语类》《朱子文集》、宋二程的《遗书》、宋张栻的《南轩集》、宋吕祖谦的《东莱集》、宋叶采的《近思录集解》、明蔡清的《蔡虚斋集》、明薛瑄的《读书录》《读书续录》、明周木的《延平答问补录》、明胡广的《性理大全》、朝鲜李滉的《退溪集》等。藤井伦明对《文会笔录》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作了非常全面的考证[3],从中可见江户朱子学者所阅读的儒学文献、兴趣点及对朱子学做进一步思考的情形,也可窥知宋学在日本传播的大致情况。
此本史料是山崎嘉独家抄录,体例略仿于中国古籍中的编纂类书。从文献来源看,《濂洛关闽》与中国已有的濂溪学文献类似,但从史料的排列看,却并非抄录于中国已有的濂溪学文献,而是在阅读文献之后自己分别抄录的。此本内容有与中国濂溪学文献相同者,如朱子问答、语类部分,也有诸多不同,如《退溪集》《读书录》等。暗斋生活的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末清初,但活跃于清初,这时的中国已有多本濂溪学文献问世。中国的濂溪学文献从宋刻十三卷本开始到明末的多种《濂溪志》,在整本体例上、内容上,均未见有如《濂洛关闽》那样安排的。但若分卷观之,则会发现此本的内容和体例,与中国濂溪学文献中的诸儒论断部分类似。由暗斋前面的序中可知,他看过胥从化、谢贶编辑的《濂溪志》,或许还借鉴了它对诸儒论断部分的编排方法。
概括地说,《周子书》主要内容是周子本人遗书,《周书抄略》是分题归类,《濂洛关闽》是分条罗列,后两者接近于中国濂溪学文献中的诸儒论断。如果把这三部书结合起来,就占据了中国各本《濂溪志》至少两卷的内容,同时也是其最为核心的部分。在宋代以后,中国学人对濂溪学文献的整理一般有三种做法:一种是专以周敦颐本人著述为主;一种是以周子后裔史料为主;第三种是以地方志的整理方法,杂汇多种周敦颐相关史料,或称作《周敦颐集》《濂溪志》。其实中国濂溪学文献也是这样从一个个类别慢慢发展为内容丰富的《濂溪志》。例如,宋朱熹编的《伊洛渊源录·濂溪先生》,实际上就类似于《濂溪志》的诸儒论断卷;元金履祥编的《濂洛风雅·周濂溪》,实际上开启了《濂溪志》的艺文志卷;宋无名氏编的《周元公年譜》三卷倪灼跋本,实际上开启了后来《濂溪志》的周子世家卷等。由暗斋《周子书》跋语可知,当时中国的濂溪学文献在日本流传不广,以至于他也只是有所听闻而未曾亲见,鉴于此,他才自为编订。由此可知,暗斋编的这三种文献对推动濂溪学在日本的传播,极有帮助。
二、山崎暗斋文献学思想的特点
根据以上对暗斋著述的分析,有人或许会认为暗斋所做的就是剪刀加浆糊的黏贴式编辑工作。实际上,文献工作和编辑工作的确有类似的地方,如它们的对象都是作品,其目的都是为了生产制作出更高质量的作品,但也有众多不同点。
文献的内涵,历史上一直在变动中,本文认同 “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字资料、图物资料、音像资料等,均为文献”[4]4这一观点,因此,对应的文献工作是指: “对文献进行整理结集、分类收藏、检索利用,这一整个过程就是文献整理,或称文献工作。”[4]8文献学,概略讲即是对文献进行研究的学问。古籍中常采用的版本、标点、辑佚、校勘、目录、辨伪、注释、考据、目录和索引编制、检索,以及审定、结集、讲习、翻译、编纂、刻印[5]等,都是文献研究的方法。
编辑的内涵,在广义上 “是指为了社会文化生产所进行的一系列整理、加工、积累、传播的文化创造活动” ,狭义上 “是指在出版过程中所从事的出版物整理、加工等系列化工作”[6]。
综上,文献工作与编辑工作差异如下:一是主体不同。在出版社,作品的编辑主体是出版部门的编辑人员,他们对更大范围的作品市场、文化趋势更有把握;文献整理作品的主体是编者,对区域内的市场并不关注,更侧重自己的整理思想。二是立足点不同。出版部门编辑的立足点既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也有传播知识的义务,目标是市场。文献编者的立足点往往与此不同,多数不会顾及到市场经济利益,更多是从文化传承角度上考虑。三是对象不同。编辑工作多数面对的是作者已经完成的作品,不需要自己动手整合出作品;文献工作面对的是杂乱浩瀚的原始资料,需要编者整理成作品。相对来讲,文献工作更具有 “创造性” 。四是作用不同。编辑工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策划、联结作者和读者的中介、提高质量的加工作用、美化书籍的增值作用等[7],可见其虽然也有前期策划,但更多地是在书稿完成之后起到一种优化美化作用。在具体工作内容上,编辑工作多数只是涉及非实质性的文字加工、技术上的加工处理[8],这部分工作文献整理也有,但其只是文献成品完成前的最后环节,在此前有大量的其他工作要做。四是依据不同。 “古籍校勘与刊印校对的主要区别是有没有明确正误是非的原稿依据。”[9]101古籍校勘之所以成为一种专门学术,就因为它 “没有或缺乏明确可信的原稿原版作为判断正误是非的依据”[9]101,而刊印校对有原稿作为判断是否正确的依据,这点是学界共识。对于有些著述将古代大量文献整理、编纂、注释、撰述、编修作品一律纳入编辑学范畴③,本文以为失之牵强,不大准确。
根据以上分析来看,山崎暗斋在文献学实践中会使用编辑方法,但更多的是使用文献学方法,其所做的在整体上可称之为文献整理工作,而非编辑工作,体现出来的是文献学思想,而非编辑学思想。暗斋的文献学工作重点是文献编纂,所整理的文献体现了他的文献学思想。
(一) 编纂意图:忧虑
暗斋的学术兴趣是宋学,其文献整理的重点也是宋学,其史料取材都来自儒学经典,从最早的《洪范》《周易》《尚书》《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到宋学道统传承中的几个人如周敦颐、二程、朱熹、张载的著作,其他人的著述较少关注,这也是暗斋的编纂旨趣所在。
暗斋为什么要编纂众多宋学经典?主要是因为忧虑。作为一代大贤,暗斋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儒学经典的价值,又目睹日本缺乏可靠经典文献的学术现状,于是编纂了众多文献。同时,他忧虑日本人难以理解儒家经典。在《白鹿洞学规集注序》中,暗斋说他 “集先儒之说,注逐条之下,与同志讲习之” ,是因为 “叹我国小大之书,家传人诵,而能明之者,盖未闻其人” ,故而他编是书,以便广为讲传。在《孝经外传序》中,他慨叹 “惜乎此书非曾氏门人之旧,是以晦翁仅为刊误而不及训解,恐未发挥微言也” 。这些书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于是暗斋谦逊地表示: “爰忘予固陋,表出小学所载而掇取他书之言为外传十章,以述晦翁之意云。”
他叹惜日本人视野狭窄。他在《感兴考注序》中说: “朱子没,后未有继作者,独明之《方逊志斋》④,其殆庶几乎,惜哉命之不幸,莫见其成也……数百年来,朱书斯渡人,人读《诗传》而不得其旨,此篇则不惟无读之,知其名者亦眇矣。” 也就是说,他因担忧日本人不知朱熹《感兴诗》而编此书。在《大家商量集序》中,他小结前人说: “然不顾己言,不察人言,而终于告子之见,可惜耳。” 故而自己集众说于此,以开阔本国人思想境界。
他忧恐日本人读到不好的刊本。在《近思录序》中,他论述诸相关续录之书 “嘉尝阅之,不满于心” ,末言 “其他可惜者犹多,今不尽论之也” ,因而自编一本,以彰显《近思录》的价值,让日本人读到值得读的经典。他在《朱易衍义序》中说: “但恐为大全所汩,而不能反其本,于是乎为《朱易衍义》云。” 又如《东鉴历算改补序》: “尝忧乎难定于一矣。”
(二) 指导思想:重回归文献,轻理论研究
纵览暗斋所有学术成果,他只有少量著作,多数是整理的文献,文献后都附有简短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也创作了多篇有关濂溪学、宋学的诗文,阐发对濂溪学、宋学的热爱与思考,只是这部分被其特点鲜明又耀眼夺目的文献整理工作覆盖了。相对于理论研究,暗斋在文献整理工作方面卓有成效,同时也更受大家重视。
暗斋不是不研究,也不是不能研究,而是他不重视理论研究。考虑到日本当时的学术界实际情况,恐怕最缺的正是可靠的宋学经典文献,如果没有这样的文献做基础,所谓理论研究不可能产生,也最好不要产生,因为建立在不可靠文献基础上的研究,不如没有。因此,暗斋著述在整体上体现出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回归到可靠文献,然后才谈得上理论研究。在暗斋看来,文献与研究谁先谁后,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三) 整理方式:重结集审定,轻文献完备
暗斋的文献编纂类型多样,有类书,如《文会笔录》《周书抄略》,还有丛书,如 “抄略” 系列,包括《程书抄略》《朱书抄略》《张书抄略》。就某一个人的著述或某一类著述而言,他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文献,可见他非常重视对史料的结集审定。
文献完备,是文献整理的重要原则, “编纂古代文献的成果最基本的要求是:全备、真实和科学,这也是古文献编纂工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全备,是对文献编纂工作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要求”[10]。但暗斋对此是轻视的,比如在编纂周敦颐文献时,三部濂溪学文献均未收录与周敦颐相关的诗歌、题名、年谱、历代褒崇、春秋享祀等等。他的 “抄略” 系列丛书,也都是依据内容取材,每人史料均仅见一斑。即便是对最为崇拜的朱熹,暗斋编纂的文献也不是完备的,只是选取部分以推广之,这不利于完整的研究一个人、一个学派的思想。
(四) 编纂理念:重史料校勘,轻注释义理
暗斋的文献编纂理念既服务于整理出适合日本人阅读的文献,也服务于在日本传播中国真正的经典。尽可能避免不可靠文献,推广真正的经典文献,而这样的文献又没有或者不多,于是暗斋自己编纂提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暗斋重视史料的准确,轻视对文献内容的注解。
出于对文献可靠性的考量,暗斋非常重视文献版本,不止史料来源、文献版本要可靠,史料的校勘也要精审。他经常谈及某个文献时说 “皆非其旧” ,即表示他对此史料可靠性的怀疑。要确保文献的可靠,就必须重视考据,而在考据中又必然牵扯到辨伪,暗斋正是这样做的。
仅举一例。在整理完朱熹《山北纪行十二章章八句》后的小跋中,暗斋对其中的一首诗表示异议, “尝阅明人编周濂溪书,往往收此第五章于彼者,误也” 。暗斋说的这首诗是 “斯须暮云合,白日无余晖。金波从地涌,宝燄穿林飞。僧言自雄夸,俗骇无因依。安知本地灵,发见随天机” 。所说的 “明人编周濂溪书” ,据前述应指明代胥从化、谢贶编的《濂溪志》。查此志,它的确收有这首诗,题目作 “天池” 。再看宋刻十三卷本《元公周濂溪先生集》,却没有收录这首诗。此外,明代弘治间(1488-1505)周木刊《濂溪周元公全集》十三卷本、刊于明嘉靖15 年(1536)吕柟本《周子抄释》也均没有此诗。但刊于明嘉靖14 年(1535)的周伦编、黄敏才刻印的《濂溪集》六卷首录此诗,明万历21 年(1593)年的胥从化本是沿袭黄敏才本的。此后,多个濂溪学文献刊本均收录了此诗。再看《朱子全书》第20 册⑤,其中收录有朱子所写诗歌《游天池》,接着是《山北纪行十二章章八句》,其中第五首即这首诗。有学者认为此诗作者正是朱熹[11],笔者也持此见。从这件事来看,暗斋眼光独到,问学谨慎,重视考据与辨伪,不盲从文献。
暗斋为每一部编纂的文献都加上了日文训读,以帮助日本人阅读,这在训诂学上接近于音韵训诂。他对自己所编纂的文献虽进行了部分评点,但对于字词、内容的注释极少。从这里可知,暗斋在文献整理上重编纂、轻注释,在具体训诂方法上,重音韵训读、轻字词注释和义理疏解。
三、山崎暗斋文献学思想的学术价值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略窥暗斋治学路径之一:极其重视文献考据。仅就暗斋的文献工作来说,他好像仅是对文献资料进行了整合,缺乏对文献文字背后的深度剖析与升华,比较平面。因此,井上哲次郎认为,山崎暗斋奉朱子学为唯一真理,忠诚地崇信朱子学,把它视之为金科玉律,是 “盲信朱子言说的精神奴隶”[12]。也有学者批评暗斋的朱子学是 “教条主义”[13],暗斋的学说 “在儒学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创见的”[14]。这些观点的确反应了暗斋学问的一些缺点,但并不是全部事实,李甦平就看到了暗斋的学说对朱子学道哲学、人哲学、理哲学的强化[15]。文献作为思想的载体,绝不可缺却低调隐匿,暗斋的文献学著述尤其如此。结合日本当时的学术现状,其文献学思想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研究可靠文献,矫正学术风气
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前提是所使用的文献必须是 “可靠” 的文献。如果文献不可靠,那建立在这些文献基础上的研究的价值,必然是值得怀疑的。而偏偏就是在文献的可靠性方面,当时的日本学界出现了问题,即当时日本存在对汉籍进行随意歪解现象。日本学者中村元就严肃地指出了这一点: “日本人常常曲解汉文文献的原文,注意这一点使非常要紧的。在传播中国思想时,对原始资料的曲解是日本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日本人摄取了中国思想的许多最优秀的文化与智力方面的成果,但是似乎他们并不常常觉得必须严格遵从中国人的思维方法。” 歪解的原因之一是,日语的构造与汉语不同,对汉语著述缺乏准确的表述能力;另外, “翻译这些汉文著作的日本译者知道汉文没有严密的文法,就对汉文原文进行非常随便的解释,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把他们自己的思想加到里头去”[16]278。这样导致的结果 “显而易见的是,日本人很少正确地理解汉文原文”[16]279。学人看到的文献是已经被曲解过的版本,而非著述原文,在这样的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和理解,很可能会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中村元举例说: “因为汉文文献常常被人加以修改,所以通过这些文献传播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思想并非原封不动地被人接受,特别是佛教,传入日本人的生活中去以后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7]279他还简要地论证了 “林罗山完全不是按照朱子学的原来面貌来介绍朱子学的” ,并认为中江藤树(1608-1648)及其弟子熊泽蕃山(1619-1691)也是如此。林罗山、中江藤树和熊泽蕃山与山崎暗斋是同时代人。中村元的研究是否完全可信暂且不论,但他指出的日本学者在研习汉籍方面存在着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审暗斋这种对宋学史料原封不动的、教条地整理的做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被批评为 “教条主义” 的山崎暗斋,是一个成功的文献学家。正是由于暗斋的文献整理工作,让日本学人研究宋学有了可资依赖的基础,其意义与价值在于对当时社会上歪曲解释汉籍原典的做法作了恰当矫正。
(二) 编纂集中文献,提高文献使用效能
首先,暗斋将散落多处的史料集中一处,提高了文献的使用效能。当时日本的情况不仅是没有可靠的濂溪学文献,其他文献也是如此。这些史料也并非是看不到,而是不集中,散落在多种文献中。翻检暗斋著述,可知其文献阅读量非常惊人。对一个研究者来说,如果每研究一个问题,都要翻阅众多分散的文献,可以想知他研究的时间成本得有多高。既然学界缺乏这样的文献,而暗斋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他就得自己去编纂。他以一人之力,将数量巨大的、可靠的史料编辑整理成书,既避免了学者使用不可靠的文献,也避免了学者为获得可靠文献而浪费大量宝贵时间,客观上积极地推动了日本的学术发展。
其次,暗斋编纂整理的文献,开阔了学界视野。由前引暗斋的序中可知,当时在日本流传的濂溪学文献并不多。截止到清初,中国已编辑整理的濂溪学文献至少已有四十多种了,而暗斋只是看到过胥从化、徐必达两种,仅这还是 “非其旧” ,意思是它的内容被曲解了,或有版本的缺失。名震一时的大学者暗斋尚且如此,可知当时日本学界一般人所能看到的宋学文献就更少了。既然学界需要却又没有这样的文献,那么暗斋编纂整理出的文献,对开阔日本学界研究濂溪学、朱子学的视野,就显得非常有价值。
(三)依据主题确定体例,呼应、引导学术研究
就濂溪学文献来说,据笔者目前所见的从宋至今的60 多种中国所编的濂溪学文献刊本,未见有这样做的——依据主题确定体例。以周敦颐为例,他的思想当然可以分为若干个主题,但中国学者却没有这样做,原因可能是在中国搜集周敦颐的史料相对方便;从宋代就开始编纂的濂溪学文献,到明代就有四十多种了,无需编者分类,学者在研究时,自会根据需要划分。而传到日本去的濂溪学文献并不多,而且在江户时期学者们所能看到的仅有的文献也并不可靠,若是采取像中国濂溪学文献那样的编排,需要找寻的史料太多,来源、可靠性也都极难保证。那么,编纂濂溪学文献有效快捷的途径便是依据日本学术界的研究需要确定主题,然后紧紧围绕这些主题搜集有限的史料。对于日本学界来说,历代朝廷对周敦颐的册封、祭祀、后裔优恤、祠堂书院、文人歌咏等部分并不重要,周敦颐只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存在于日本儒学界,所以关于他的文献也要呼应学术界的这种现状,于是,中国濂溪学文献中的历代官方褒崇、春秋享祀、古代艺文、世系遗芳、序跋题记史料等,都被暗斋忽略不计了。这样以来,因为找寻的史料范围狭窄,且仅限于周敦颐哲学思想部分,那么史料来源一般可以确保,可靠性也大致能保证。于是,在当时的日本,依据主题编纂文献来呼应、引导学术研究,也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了。
注释:
①如其弟子林罗山在题《惺窝先生像》中引濂溪作比: “道学勃兴桑海东,高标清节啸松风。背山别业似濂水,庭草生生意思中。” 弟子松永尺五(1592-1657)在《尺五先生全集·惺窝先生三十三回忌日拈香并叙》中直言惺窝: “尊崇宋元性命之道学,遂脱却嵩山少林之禅机,接得濂溪伊洛之道脉,解法衣,着司马之深衣,抛贝叶,讲晦庵之集注,始点和训于六籍。” 林罗山在《惺窝先生行状》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昔仲尼没千有余年,周茂叔独接不传之统,道不在兹乎!若先生则是矣。”
②此本凡例后题署 “永明县知县胥从化编订,道州儒学署学正事举人谢贶编校,训导刘报国同校” ,也称为胥从化本。
③比如吴平、钱荣贵在《中国编辑思想史》(学习出版社2014 年版) 中探讨了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许慎《说文解字》、陈寿《三国志》、萧统《文选》等大量的历代经史子集书籍的编修、编辑思想。
④方孝孺(1357-1402),号逊志,著有诗文集《逊志斋集》。
⑤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490-491 页。此本采用的底本是《四部丛刊》中影印的明嘉靖11 年张大轮、胡岳所刊《晦庵先生朱文公集》。
——一种可能的阐发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