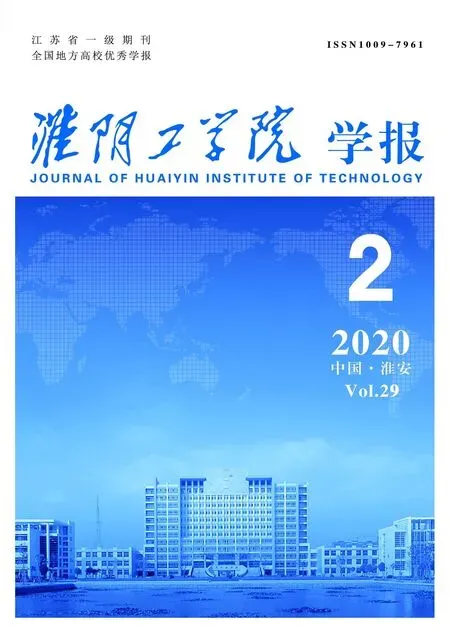明代大儒罗汝芳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耿加进
(淮阴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罗汝芳,号近溪,明代思想家,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近溪既传承了阳明心学重觉悟的为学进路,又发扬了泰州学派重践履的思想特色。其一生重讲学,以讲学为生命,在丰富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既富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教育思想。下面就近溪教育思想的核心要旨略陈己见。
1 “学只求仁”的教育宗旨
罗近溪在经历了一番人生磨难和求学体验后认识到,求仁是孔门教人的宗旨。他说:“孔门宗旨,只在求仁”[1]128。“孔门立教,只是求仁”[1]129。仁是什么?仁者人也。仁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在近溪看来,教育的本质无非就是教人做人。这也是儒家的一贯思想。但近溪重新从孔孟思想中拈出一个仁字,有其实践意义。自程朱以来,本极具亲和力的儒家思想被不断地观念化,学者沉溺于理与气、心与物的哲学思辨中,而对现实的人生却缺乏实在的关心。阳明曾提出自己的担心,担心学者陷于概念上的思辨而不着实际的践行,提出要破除“光景”。近溪对程朱的烦琐体系自是不满,对阳明的良知学也有担忧,在他看来,阳明过于强调良知而于具体工夫的下手处未免有所忽略,他认为,良知应该有个“实落”处,必须“实落”在爱亲敬长上,爱亲敬长才是致良知工夫的下手处。他说:“而此说良知,则即人之爱亲敬长处言之,其理便自实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与孔子‘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的宗旨,毫发不差,始是传心真脉也”[1]86。由此可见,近溪强调孔门求仁宗旨,也就是要把宋明儒者从玄远的哲学思辨中拉回到现实的教育实践中。
仁者人也,求仁也就是追求做人。近溪把“仁”比做“种子”,求仁也就是“培养种子,使其成熟耳”。他说:“今日为学第一要得种子。《礼》谓:‘人情者,圣王之田也。’必本仁以种子。孔门教人求仁,正谓此真种子也。然其正经注脚,则却曰‘仁者人也。’人即赤子,而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爱亲,故曰:‘亲亲为大。’至义、礼、智、信,总是培养种子,使其成熟耳。”[1]212”。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培养人心中本具之真种子,使之成熟。这个理论建立在孟子的性善论基础上。孟子认为,人先天地具有善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教育的意义即在于不断地扩充人之善端,使其成为德才兼备的全人。近溪更是用“圣人即是自己[2]248”“圣人即常人”这样的表述来强调,圣与凡并无本质差别,每个人都内在地具有成圣的可能性。他说:“圣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圣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圣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圣人矣;常人本是圣人,因其自昧,故本圣人而卒为常人矣[1]212。”
求仁宗旨落实到具体对象上,就是成为具有孝弟慈美德的君子、大人。所谓君子,才德之谓也。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君子。尽管近溪说,圣人即自己,但这是从建立个人信心上说的,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可能性,因为每个人都具有仁义之种子。尽管成圣是儒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但落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能真正成为圣人,他们理想中的目标还是君子。圣人是完人,高不可攀,活着的人中没有人被称为圣人,而君子较之圣人,则具体得多,现实得多。近溪理想中的君子,怀有赤子之心,以仁为己任,具有孝弟慈的美德。我们今天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本质而言,与儒家所谓的“君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儒家关于君子的培养,对现代教育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 “唤醒人心”的正面引导
《腾越州乡约训语》有一段话颇能反映近溪在教育方法上的特点:
坐中诸友咸曰:“往见各处举行乡约,多有立薄以书善恶,公论以示劝惩,其《约》反多不行,原是带着刑政的意思在。若昨日,公祖(按,指近溪)只是宣扬圣训,并唤醒人心,而老幼百千万众俱踊跃忻忻,向善而不容自己。真如草木花卉,一遇春风则万紫千红,满前尽是一片生机矣”[1]762-763。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近溪在教育方法上重视正面引导。这也是儒家一贯的教育思想。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63。靠行政命令、刑罚等手段,只能让老百姓害怕,不能使之向善,而通过道德、礼制等手段则可以引导其向善。孔子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161。这也是强调正面引导的重要作用。
孟子为这种正面引导提供了理论依据,即人皆有仁义礼智四端。在孟子看来,教育并不是把外在于人的东西强加于人,而是把人所“固有”的善性引发出来,因此,教育的作用在引导。孟子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3]278。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点滴可汇成汪洋,同样,人之善端也可通过“扩而充之”而充斥于天地之间,成浩然之气。
而到了宋明儒家,不再强调正面引导,而更多地是突出反面约束的作用。如程朱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他们认为,人心不古、天道不彰就缘于人欲横流,必得私欲净尽,方得天理流行。王阳明也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4]25。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具足,良知知善知恶,但良知并不能自然呈现,需要去除物欲。这就需要格物的工夫。其释“格物”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4]22。所谓“日减”“正其不正”,都是从消极方面对人加以约束。
近溪赞赏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但对其“致”字却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有问“如何见得是致的工夫”,近溪答曰:“致也者,直而养之,顺而推之,所谓致其爱而爱焉,而事亲极其孝;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长极其弟。则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1]86。所谓“直而养之,顺而推之”,就是主张从正面培育人之善性,也就是孟子的“扩而充之”。善的地盘做大了,不善的地盘就自然会缩小。与“扩而充之”相反的功夫是“寡欲”,即通过减少欲望来相对扩大善的地盘。近溪主张从正面进行引导。他说:“人能体仁,则欲自制”[2]249。近溪的这一教育思想与其良知观密切相关。近溪与王龙溪、王心斋一样,也主张良知现成具足,当下呈现,“捧茶童子却是道”就是表达这一思想的著名论题。近溪以童子捧茶与众人饮茶这一生活细节为例指出,一切皆是顺心而动的结果,无有造作,都是良知的当下呈现,平常心就是本心的当下呈露。王心斋也有“百姓日用即道”的类似表述,但心斋所表达的是,道不离百姓日用,而百姓日用要合乎道还需要先知先觉的启迪和引导。
良知当下呈现,“妙用圆通”,因此,应顺良知而行,“自信从”“自觉悟”,近溪指出:“但能一觉,则日用间可以转凡夫而为圣人,若不能一觉,则终此身弃圣体而甘为凡夫矣”[1]105。“觉”的关键在“信”,必须“一呼即应,一应即止”,“截钉截铁,更不容情”,不能“自生疑畏”[2]117。近溪认为,圣人与凡人在根本上并无区别,关键在于能否信得过良知:“原无高下,原无彼此;彼非有余,此非不足;人人同具,个个现成;亘古亘今,无剩无欠。以此自信其心,然后时时有善可迁;以此信人之心,然后时时可与人为善;以此信千百世人之心,然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1]426。既要相信自己,也要相信别人。相信自己,方能坚定地循良知的指引去做。相信别人,方能注重沟通,而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思考,近溪在开展乡约教育时,注重正面引导,进行正面宣传,以“唤醒人心”为目的。朱元璋的《圣谕六条》是近溪的重要教育内容,这除了政治上的需要之外,主要是因为在近溪看来,《圣谕六条》宣扬的正是儒家提倡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而这些伦理道德内在于人心,只要顺着人之心去引导,就能得到受教育者的认同。
现在教育重视知识传授,而忽视人心的涵养。知识教育如果不能与人心涵养结合起来,这些知识就只是外在于人的异质存在。知识教育自然重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需要知识革命和科技创新,但没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我们难以在知识上取得突破、在科技上有重大创新。人类先进的知识,无不是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获得的。近溪唤醒人心的思想理念,不仅让我们自信,也让我们信人。惟有高度的自信,才能不被旁门左道所迷惑,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惟有相信他人,与他人建立互信,才能共建人类的美好家园。
3 “乐在其中”的乐学思想
我们一般以为,圣贤之道必充满艰难与困苦,近溪认为,圣贤之道只是一条“寻常”之道,“乐在其中”,所谓乐,“只是个快活而已”。他说:
圣贤之道,原只是寻常,而学者讲求善当体会。所谓“乐”者,窃意只是个快活而已。岂快活之外,复有所谓乐哉?“活”之为言生也,“快”之为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圣贤之所谓乐[1]337。
在儒家,“乐”是从学习中得到的一种重要的生命体验。《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3]55。孔子告诉人们,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学习能够让人忘却生活的烦恼,颜回之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身居陋巷,生活极其艰苦,但颜回“不改其乐”,这种悟道之“乐”非一般人所能感受。颜回之“乐”被后世学者作为一种精神境界而加以认同,周濂溪常教其弟子“学颜子、仲尼乐处”,而阳明更是提出“乐是心之本体”的观点,肯定“洒落为吾心之体”,而王心斋则提出了“乐即学,学即乐”的乐学思想,其子王东厓承其父提出了“乐即道,道即乐”的命题。东厓认为,道或心就其本然状态而言,莫不具有“乐”的本质,故学者的目标就是学此“乐”。近溪是从“生”意释“乐”的,他说:“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则明白开示学者以心体之真,亦详细指引学者以入道之要”[1]337。仁是人心之真种子,种子具勃勃生机,故人之在世自然能感受到生意活泼之乐趣。
当然,这种快乐不是感官上的快乐,而是孟子所谓“理义之悦我心”的精神之乐。近溪说:“此乐有自本体而得,则生意忻忻,赤子爱悦亲长处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则天机感触,理义之悦我心是也”[1]112。此种快乐既可是心体的自然流露,如赤子之爱亲悦长;也可由“用功而得”,即从理义的学习领悟中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和愉悦,正如吴震教授所说:“‘心地快乐’从根本上说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忻喜’之情,而应当是人的理性的一种自然流露”[5]450。
泰州学派提倡乐学有其社会背景。底层老百姓生活艰苦,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对他们而言,读书学习是件十分辛苦艰难的事。要对这些人进行教化,就要简化教育内容,让老百姓愿意接受、易于接受。因此,心斋说:“天下之学,唯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6]5。近溪说:“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须轻省”[1]89。
关于乐学,儒家内部的认识并不一致。比如朱熹明确表示“曾点不可学”,在他看来,一味追求“曾点乐趣”而忽略理对人心的约束,有可能走向狂荡一路。黄宗羲对泰州学派倡导乐学思想的传统表示担忧:“心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处最难理会,稍差便入狂荡一路”[7]719。儒家所谓的学,主要是内向体验,即孟子所谓“反身而诚”,而这种体验又因语言的模糊性而难以清楚表达,因此,一些学者或不下功夫,或下错功夫,错把己见当真理,而行为放荡。近溪以孝弟慈为良知之实落处,正是担心学者把良知当作一光景而玩弄,误入歧途。孝弟慈即是致良知功夫的下手处,也是学者追求的至高目标。他说:“盖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义。殊不知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也”[1]135。
不管怎么说,乐学不仅有其思想史之意义,对当下的教育实践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第一,乐学是一种精神状态。乐学是一种对待学习的态度。每个人都有学习的需要,要善于引导受教育者正确地对待学习,快乐地接受教育。第二,乐学要善于发现和肯定。人的价值感和存在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确认。每个人都有得到别人肯定和承认的需求,并能够从这种肯定和承认中获得愉悦。因此,教育者要善于发现和肯定受教育者的优异表现,这样既可以强化其行为,也可以增加其自信。第三,乐学就是学乐。没有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乐是高层次的精神愉悦,不下得一番苦功夫不可得,没有这个体验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快乐的。
4 “觉悟为先”的学习思想
近溪本人是一个勤奋刻苦的人,在学习方法上也多有体悟和经验,而这些体悟和经验对于今天的学习者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4.1 立志为先
有问用功当从何处下手,近溪答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学,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后立与不惑,只是此志愈真切,而愈精愈纯焉耳。故志与学,原非两事,亦无间歇时也。今日之急务,未立志者,须先严辩;已立志者须更勇猛”[1]113。明确志向,学习才有方向和动力,才能精进不歇。近溪自述,初学道时“每清昼长夜,只挥泪自苦”,四十年来“夜分方合眼”,又不敢踏实睡去,鸡鸣又起,从没有安安稳稳地睡过一觉[1]297。他批评时下学者发愤只为功利,而讲学问、为圣贤却不思发愤。他说:“今中举之心, 人人发愤, 时时发愤, 至于讲学问、为圣贤, 其受用百倍中举者, 却又不思发愤, 是尚为能充其类也哉? 诸君又只知孔子发愤忘食, 亦未思下文说‘不知老之将至’,则是年弥高而愤弥甚也。孔子至老, 犹思发愤, 而少壮刚强反悠悠, 此又不能充类之甚者矣”[1]283。又说:“今欲学为圣人,而非特立坚志,亲就良朋,且却脱尘烦,专居静地,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其能有成者,盖百无一二人矣”[1]270。
4.2 为学次第
这个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有方向,再下功夫,还是在功夫中探寻方向。王门后学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歧的,王龙溪认为,良知现成,当下呈现,应该以良知为指引去下功夫,此即所谓本体功夫。而钱绪山、聂双江等认为,不下一番去除物欲的功夫,本体不显,因此,应该以功夫为先。我们前面说过,近溪是主张良知当下见在的,故其主张从良知本体上下功夫。他说:“以用功为先者,意念有个存主,言动有所执持,不惟己可自考,亦且众共见闻”[1]282。如果以用功为先,怎么用功必然要有一个做主者,这在逻辑上是很清楚的;而既然有一个做主者,可知本体当下见在,因此,近溪认为,良知本具,天命常在,有主导,自然知道下功夫。而盲目下功夫,“理无根据者,必事终废弛”。他以园丁举例,如果不懂得培育芝兰的道理,而盲目施以各种肥料,只会把芝兰弄死[1]282。有问:“近时用工,殊觉思虑起灭,不得安宁,谓之奈何?”近溪答曰:“天下事理,当先本根,本根既正,则末节无难矣。今度所论工夫,原非思虑之不宁,实由体之未透也”[1]269。近溪认为,悟透心体,才是根本,相对于根本,功夫只是末节。下面这段话更是清楚地表达了近溪对为学次第的基本观点:
“古人论学,的有次第,所以本末始终,知所先后,乃可近道。故修齐治平,必先正心诚意,正心诚意,必先格物致知。今不先求知得明白,乃即胡乱便下手处去做”[1]278。
4.3 一以贯之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3]190。表面上看,好像孔子否定“多学而识之”,实际上,孔子想强调的是,学问要能一以贯之,否则多则无益。近溪指出,孔子批评子贡,非否定其多学,而是“病其徒事多学,而不能一贯以多学”[1]60。近溪又说:“多学乃始能一,则孔子不应尽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学以学,而不知一贯以学也”[1]61。多学与一贯的关系就是博与约的关系,没有博学多识,一贯必然落空,而博学多识,不能化约升华、一以贯之,则不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想。多学与一贯的关系,也就是前文的为学次第问题,先有学问方向和宗旨,然后落实去做,则一切闻见皆能成为涵育思想的资源。
4.4 学必贵时
这是关于学习的时空条件的讨论。“当下”,在阳明学语境中,指良知现成,当下具足。当下既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概念,也是一个与空间相关的概念,即此时此地。良知当下具足,就应该从此时此地下手,实落去做。学习要有“当下”意识,时不我待,不重当下,终无可学之时。因此,近溪又特拈出一个“时”字,他说:“孔子一生,只受用一个‘时’字,故其立教始初,即要人时习。盖学必贵习,习必贵时”[1]130。朱熹释“时”为“时时”,强调时间的持续性,而近溪坚持释“时”为“因时”,突出的是时的“当下”意。他说:“时时习之,于工夫似觉紧切,而轻重疾徐,终不若因时之为恰好。盖因时,则是工夫合本体,而本体做工夫,当下即可言悦,更不必在俟习熟而后悦”[1]80。“时时”,模糊不确定,“因时”表达的是当下的确定性,动静语默皆因顺时宜,当学则学,当止则止,一切随顺心体,应物自然。
4.5 读书有法
关于如何读书,近溪的观点仍有价值。一是要寻作者本意。近溪说:“凡看经书,须先得圣贤口气”[1]96。意思是,读书在善于领会圣贤之意,不能拘泥于文词,也不能盲目信从注疏。语言是为了表达思想,而由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它只能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并不能完全地把思想表达出来,此即所谓的“言不尽意”,而这个“意”则需要读者来揭示。二是要联系上下文。近溪说:“读书须将一上下文气理会”[1]346。他以《中庸》“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载者培之,倾者覆之”为例,指出朱熹的注不合上下文意,并联系上下文释以己意。不管近溪之解是否合乎《中庸》之本意,读书要联系上下文这一思想还是能给我们启示的。三是要过信关。近溪:“学问要过信关,未过此关,大信则大进,小信则小进;既过此关,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1]200。近溪自述,他奉父师之命读经书,一字一句不轻放过,“遵奉久久,不觉于孔圣心源,稍有契悟”[1]108。根基未立,多信方有所获。及至根基既立,则能从疑问辨释中收获更多。
注释:
① 罗近溪先生明道录(卷四),京都:中文出版社刊和刻近世汉籍丛刊本.
② 近溪罗先生一贯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6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明长松馆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