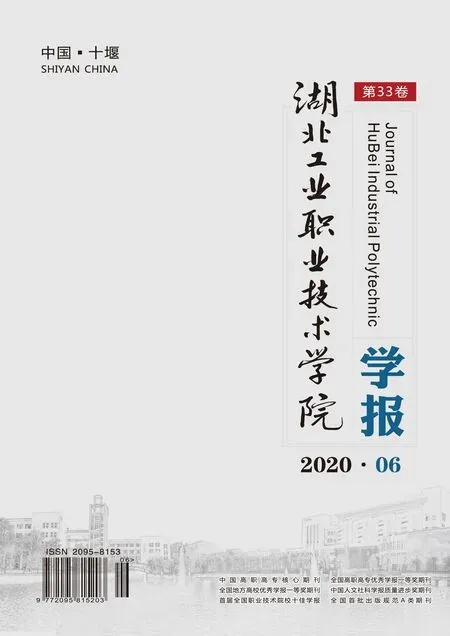异化与反抗
——残雪与李沧东的比较阅读
刘海燕
(重庆文理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中国作家残雪和韩国作家李沧东,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并逐步具有了世界性的知名度。女作家残雪的作品在海外有非常多的读者,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李沧东在以小说成名后,跨界成为导演和编剧,因其执着的艺术追求,其电影作品《绿洲》《密阳》《诗》《燃烧》等都在国家电影颁奖上获得佳绩。虽然两位作家可能并不相识,也并没有互相的影响,甚至两人的叙述风格也差异较大,但两人对人性异化及其反抗的关注却提供了比较的可能。
一、人性的异化:《山上的小屋》与《战利品》
《山上的小屋》是残雪的处女作,发表于1985年;《战利品》是李沧东的处女作,发表于1983年。虽然所属国家不一样,但共同的时代背景还是提供了较为相似的主题。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中国也在70年代末期真正开始了改革开放,走向了现代化。所谓工业化和现代化,其本质是试图将欧美发达国家的理念和技术本土化。那么,这些技术、理念背后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本国传统的模式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一种生活方式受到冲击的早期,较为常见的反应是对其冲击的负面现象的关注。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便是呈现社会变迁下的社会问题和人性异化。显然,《战利品》和《山上的小屋》都选择了这一倾向,并且都选择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
《战利品》中,叫做“具本守”的叙述者“我”,退伍之后重新上学并最后成为了一名教师,金长寿和吴美子是“我”的中学同学。叙述的开始,金长寿因为肝癌死去了,“我”却没有感到伤心和痛苦,而勃发出了对吴美子强烈的性欲。这促使着“我”给吴美子打电话,告诉她这一讯息,并约她出来面聊。然后,整个小说在叙述“我”对吴美子的强烈性欲的线索下,不时穿插中学时代以及退伍后三人之间的交往。意外的是,吴美子对“我”的意图心领神会,主动和“我”去了旅店,主动试图和“我”发生关系。然而,在激情之中“我”却突然故意拿出死者金长寿的骨头展示给吴美子,最后她带着恐惧和愤怒离去,“我”将骨头从窗口扔了出去。
小说的末尾说到:“商业街笼罩在黑暗里。我久久地俯视这死亡般的黑暗。如同有人正在某个地方死去,有东西散发着腐烂的味道,有只耗子偷偷地啃噬腐朽的家具一样,在灰烬中重生的火星将会逐渐变大,烧掉某些东西。”[1]这句充满暗示性的语言为揭示小说提供了指引。黑暗的商业街,岂不就是对工业化经济的暗示;而那个正在某个地方死去的人、腐烂的味道、腐朽的家具,岂不就是韩国的文化传统。当然,李沧东还是充满着期待,期待已经腐朽的文化传统能浴火重生,走向新的发展。从象征和隐喻的角度再回到故事中,那些看起来不合常规的人物行为并得到了解释。
“我”和“吴美子”其实都是在两个层面上具有象征性。其一,象征着一种异化之后的畸形心理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唯个人、唯欲望的生活方式。金长寿是“我”崇拜的人,是“吴美子”的初恋男友,然而“他”在病床上的挣扎以及最后的死亡,都没有引起“我”和“吴美子”的同情和痛苦。他死亡前,虽然“我”一直在陪伴,但这种陪伴却没有对病人的关怀。与其说是陪伴,不如说“我”在欣赏金长寿的死亡表演,也在等待着一个追求吴美子的契机。无疑,金长寿的死亡,是“我”接近吴美子的最后时机。因此,他刚死去,“我”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以至于“我”无法控制打电话时强烈的情绪反应。这种变态的欲望和畸形心理,其实质又是一种征服欲、权力欲。中学时期,金长寿是同学们的中心,大家围绕在他周围;工作后遇见吴美子,汽车这一狭小的空间成为了权力的隐喻,吴美子的美国丈夫是权力的中心,吴美子是其附属品,而“我”和吴美子的母亲则是边缘人物。在这两个时刻,吴美子都成为了中心人物的情人,仿佛是一种“战利品”。因此,作为边缘人物的“我”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权力的争夺自然而然指向了吴美子,仿佛征服了吴美子、获得了这个战利品,“我”就实现不一样的人生方式。因此,对吴美子的欲望,其实则是权力欲。在此层面的隐喻中,吴美子就象征着战利品。然而,她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但她对中学男友的死没有丝毫的伤心、与美国丈夫在一起也仅仅是因为金钱,甚至主动引诱“我”,她显然已经被异化,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其根源,恰恰是美国丈夫所隐喻的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生活方式,把经济、身份、欲望、权力等作为了社会的中心,人在这样的情境中慢慢失去了对自我和尊严的关注,沦为了欲望和权力的“战利品”。
其二,“我”和“吴美子”又象征着维护文化传统的一种努力。“我”的教师身份,使我对韩国文化传统的变化有了更多的敏感,“我”试图去寻找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以“吴美子”这一女性角色作为象征。因此,“我”对她强烈的性冲动其实是超越肉体的,是一种强烈的找回传统的信念。横亘在“我”(寻找)和吴美子(传统)之间的,是金长寿和美国丈夫。金长寿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反叛者,他虽然死去了,但却阴魂不散地一直在场,这便是裤兜里的骨头的隐喻;美国丈夫虽然叙述不多,但“我”对吴美子的欲望以及整个幽会过程,却时刻置于其是吴美子丈夫之一前提下,隐喻着传统文化依然被西化无法逆回了。因此,“我”对吴美子强烈的想象,最终发现吴美子已然不是想象中的吴美子,意味着传统依然变化了,这是事实,所以“我”和吴美子最后必然无法具有肉体的结合,“我”以一种戏谑的方式(用骨头吓唬吴美子)来进行着无能的反抗和最后的宣泄。
《山上的小屋》与《战利品》相似,都关注人性的异化,都以第一人称叙述,也都用人际关系作为隐喻。然而,不同的是,《战利品》以一种挽歌情感去叙述文化传统的变迁,而《山上的小屋》则以愤怒的语气叙述异化之后的生存困境。小说中,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充满了冷漠、对立,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清晰。夫妻之间,父亲的行为不被母亲认可,两人没有交流,父亲总在做梦和打鼾,让家里每个人都坐立不安;母亲不断地阻挠“我”、控制“我”,直勾勾地看着“我”,甚至恨不得拧断“我”的胳膊;妹妹在母亲的控制下,监视着“我”,不断与“我”作对;父亲到了夜里,变成一只狼,围着房子嚎叫。山上的小屋中,有个暴怒的人,日夜不停地砸着木板。显然,这个暴怒的人,就是“我”,在强烈的压抑和控制中,“我”产生了强烈的抗拒。然而,不论“我”怎么抗拒,“我”始终被束缚在小屋里,始终被监视着。原本充满温暖的家庭,在小说却变成了如此压抑和绝望的场所。权力和非理性是罪魁祸首。所有的行为都是母亲发号施令,她控制着父亲和妹妹,使之成为了自己的帮凶。“我”却有着自己的思想和判断,母亲便百般阻挠和控制。在异化的权力下,人失去了理性,非理性横行霸道,因此生存变成了一种痛苦。“我”开关抽屉,挖出围棋和扑克,实际上是寻找和保持理性的一种努力,但却总是徒劳,连想象中山上的那间小屋其实也并不存在。
总之,人性的异化是残雪《山上的小屋》和李沧东《战利品》的共同主题,并且两者也都将目光聚焦了权力,通过人际关系的异化去呈现在权力控制下扭曲的人性。不同的是,李沧东是以性欲来象征权力欲,而残雪则重在权力压抑下的生存图景。李沧东试图找出原因,以寻求解决的办法,因此他明确地将西方工业文化对韩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作为了根源,他意识到传统依然无法回归而未来又无法期待,所以他最后走向了戏谑和宣泄;残雪却不太关注原因,也不太愿意去寻求解决之道,她只是去呈现一种异化的状态,一种可怖的、痛苦的、扭曲的生存方式。片段化的场景、梦魇般的叙述成为残雪去表达这种非理性、非人性生存的主要方式;而李沧东,在寻找根源和解决办法的内在愿望下,以象征的人物和故事性的叙述呈现自己的思考。
二、无能的反抗:《苍老的浮云》与《一头有心事的骡子》
在李沧东小说集《烧纸》封底的介绍中提到:“这些作品都是以城市边缘人和小人物为关注点……他的小说不以大事件为线索,而往往围绕着生活的细节……他拙朴的笔触下隐藏的是这些细小的事件背后巨大的悲剧感。”[1]这部小说集的主要人物分别有:《为了大家的安全》的乡下老太婆;《火与灰》中亡子的父亲;《祭奠》中瘫痪的老人;《烧纸》等候丈夫的妻子;《脐带》中的职场新人金大植;《大雪纷飞的日子》中的新兵金永民;《舞》中贫穷的夫妻;《空房子》中工厂经理尚洙;《为了超级明星》中替儿子看狗的乡下父亲;《一头有心事的骡子》中的临时清洁工大杞;《战利品》中的教师本守。单纯看这些人物的身份,似乎确实较少有人物处在社会的上层,连相对较有身份的教师本守,也是一位入职不久、收入较低的普通职工,因此容易给读者一种“边缘人”或“小人物”的假象。这种习惯性的界定方式往往导致对作品的简单归类,而失去了对作品本应具有的更慎重更深沉的思考。
残雪的小说,不论是早期的《山上的小屋》,还是最新出版的《茶园》,很少出现通常所言的大人物,往往是住在地下室、破旧小区的形式古怪的各种普通角色。然而,不管是李沧东还是残雪,用“边缘人”和“小人物”来定位其作品似乎也显得仓促了一些。作为较为常见的表述文学作品人物的一种方式,“边缘人”和“小人物”往往是在相对于“精英人物”和“大人物”而言。当说到“边缘叙事”或“小人物叙事”的时候,是在强调其不同于“主流叙事”和“大人物叙事”的独特性。残雪和李沧东的小说,并不是在强调阶层身份,而是中在挖掘一种时代精神状况,或者一种现象背后深刻的人性发现。
残雪和李沧东的小说,都充满着一种无声的恐惧感。无声与恐惧,形成了一种张力。前者的《山上的小屋》中,压抑、痛苦和恐惧包围着小屋中暴怒的人,他却没有呐喊,没有嚎叫;《苍老的浮云》中,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害怕着,而他们又往往意识不到真正恐惧的是什么;《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里,阿梅因为莫名的恐惧无法安稳入睡,甚至需要用被子紧紧地蒙住头,还要用箱子压在被子上;《老蝉》中,居民们对老蝉的恐惧和愤怒;《茶园》中对死亡的恐惧。李沧东的小说亦如是,充满恐惧,却又压抑在沉默中:《火与灰》中儿子死亡之后,母亲在沉默中走向宗教,而父亲则孤独而迷茫地寻找儿子骨灰撒入的小河;《祭奠》中“我”“姐姐”和突然来访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之间的矛盾反衬了病床上瘫痪父亲的沉默;《烧纸》中妻子苦苦地寻找和守候丈夫,死死地隐藏着苦难的经历;《大雪纷飞的日子》中,女孩一个人默默地在大雪中等待着,幻想着;《空房子》中那个有声音却没有内容的电话;《为了超级明星》中无法言说的老人;《一头有心事的骡子》中无声却发情的骡子;《战利品》中一直在场的死人的骨头。
在这些作品中,无声有时是空间的表现形式,有时是恐惧的根源。《火与灰》《烧纸》《为了超级明星》倾向于前者;《空房子》《一头有心事的骡子》《战利品》则更倾向于后者。如果说有声音意味着至少有一条释放恐惧的途径,而无声则意味着长久的压抑,意味着这种恐惧只能被封闭在个体的精神空间。《火与灰》中,母亲的沉默和悲痛最终在宗教的庇护下释放,在日复一日的诵读和唱经中慢慢被隐藏;但父亲却陷入了更深刻的沉默,他在寻找儿子离开的那条河,其实是在寻找一条路来走出自己的悲痛和恐惧。他恐惧的,是生存的无意义。以前有儿子在,一家人和谐地过着普通的生活,他并没有去思考存在的价值。但是儿子死后,家庭情感的纽带依然破裂,夫妻之间也勉强按照刻板的程式一样的生活,没有更多的对话,没有更多生活选择,只是日复一日的追思和悲痛。妻子最后走进了宗教,而他觉得宗教依然苍白,甚至自欺欺人,提供不了生活的意义。《火与灰》,儿子火葬的骨灰,自焚大学生燃烧的火焰,这个父亲在思考、在寻找,最后他看到了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穿透了死亡,正在上升。”或许他看到了超越的途径,看到了希望。《空房子》中,住进豪宅的尚洙和妻子,因为莫名其妙的电话(最有喘息没有声音)而恐惧,寝食难安甚至神经衰弱,最后尚洙还被误当成盗贼被抓紧了派出所。实质上,他们恐惧的是生活的不稳定性。
如果能够去反抗现实,那或许有着某种希望;但如果恐惧本身就是无声无形的,那么反抗往往也就失去了靶心。也有可能,人在许多时候只能做出某种反抗的姿态,而实际上,这种反抗是无能的。无能,意味着本身缺乏力量,意味着即使具有一定的力量,却也显得可笑和渺小。
有学者认为,残雪的小说展现的便是“由反抗而产生的荒诞体验”[2]。此言不虚,残雪的小说是充满着反抗的,总是会有一个引路者带着某个人物踏上反抗之路。但这条路却并不清晰,所以让反抗往往沦为一种姿态,缺乏真正的力量。《山上的小屋》中,“我”的反抗是无声的,也是无力的,只能在夜里悄悄地挖出围棋,只能给抽屉抹上油以免被发现;《苍老的浮云》中,更善无和虚汝华成为了知音,志同道合,但这种反抗也封闭在狭小的房间里,最后两人都走向了死亡。在残雪后来的小说中,反抗被富于了积极的色彩。长篇小说《边疆》中的寻找,已开始被富于了较为确定的意义;新作《秘史》中,反抗的姿态被转换为对希望的追索,主要人物对“金孔雀”的寻找其实是超脱庸俗人生的一种隐喻。
在李沧东的小说,反抗有着明确的结局,那就是失败。《为了大家的安全》中逐渐有所反省的京哲,却无法对抗众人的平庸、冷漠和暴力;《火与灰》虽然在最后看到了一丝希望,不过这一丝希望更多指向的是对生存价值的一种醒悟,他或许意识到为了真理或者启蒙或者某种价值而全身心投入甚至流血牺牲也超越于庸俗而模式化的生活,但并不意味着找到了启蒙世人的途径,抗议的人仍然不断地死亡着;《祭奠》中,父亲与从未谋面的哥哥的离开,既可以说是对往事的一种和解,亦可以看成是对变异了的亲情的绝望,因此父亲的离开变成了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却只是一种逃避,不会对我和我姐的自私起到一点作用;《烧纸》中,坚强的妻子,无法反抗暴徒,无法反抗世俗;《大雪纷飞的日子》中,新兵的善良和反抗最后失去了生命,而女孩无奈地跟在了兵长后面,那条路大概是通往更加黑暗的夜;《为了超级明星》父亲伺候儿子,儿子伺候狗,最后父亲帮儿子伺候狗。无法忍受屈辱生活的他,对流浪儿的收留,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同情,又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抗,这种反抗的结局却是流浪儿对他的无情戏弄。
如果注意到残雪和李沧东笔下的身体,会发现更多的共性——都缺乏真正的生气,往往是一具空洞的肉体。此处的身体,笔者指的是一种源自生理的激情,一种本能的欲望,它是一种生命力,是一种活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具有一种解放的价值。然而,在残雪和李沧东的小说中,身体的存在是以一种“无性”的方式,没有真正的源自本能的冲动。
不妨略微比较一下《苍老的浮云》与李沧东的《一头有心事的骡子》。《苍老的浮云》中,对身体的描述是“木乃伊似的身体”“皮肤上绿的斑点”“光光的头皮”,这里没有任何的美感可言,展现出来的是丑陋。甚至连更善无和虚汝华这对相互影响的知音,两人的肉体结合被描述成为两个骨架的碰撞。有评论家认为,残雪小说中的病态、肮脏和幽暗,显示了作者对生命的怀疑、对本体荒谬的思考以及人类难以摆脱的忧患意识的再思考[3]。
《一头有心事的骡子》是李沧东小说中身体叙事较为突出的一篇。大杞是城市的临时清洁工,自从他来到城市开始工作之后,他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阳痿了。他每天牵着骡子去清扫城市的垃圾,慢慢感受到一种无法排解的绝大恐惧感和虚无感。他不知道这样的生活的意义所在,心灵得不到丝毫的温暖,生命没有丝毫的激情,连身体都无法燃起一点欲望。相反,骡子却永远充满着欲望,常常把自己的生殖器毫无顾忌地展示出来。骡子死于欲望,死于人们对其欲望的捉弄。骡子的存在,本身让大杞还有一种想象投射的自我安慰。骡子死后,他再无留在城市的念头,决定离开此地回到乡下。阴差阳错,被朋友带到了妓院,在妓女的挑逗下,居然恢复了欲望、恢复了能力,与妓女发生了关系。
那么,为什么大杞一直无能,最后和能妓女发生了关系?韩国评论家秦炯俊认为,大杞和妓女的拥抱“是站在同等立场上的拥抱,是真实具体的拥抱,而不是站在优越的立场上追求觉醒,也不是基于有意识的努力而做出的袒护行为。”[4]换句话说,因为大杞和妓女都是社会的底层,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有着真实而温暖的情感,这不是欲望,不是权力关系,只是生命的一种共鸣行为,由此试图说明,生活本身即是如此,无所谓好坏。当然,这是一种解读方式,不过,似乎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大杞在和妓女发生关系之前,问了一个问题:“你能生小孩吗?”为何单单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这个才是关键!阅读李沧东的小说,无法忽视的现象是,小说中既有复杂多样的隐喻和象征,也有一些隐藏着的关键语句,如《战利品》中结尾之处,如《一头骡子的心事》里的这句话。或许可以这样思考:性的行为在生物学意义上恰恰超越了个人的快感,它指向的是生殖,也就是种族的繁衍,这是性的真正本源,所以大杞的这个行为既不是阶层的认同,也不是某种报复的快感,而是在一种象征的层面上回到生存的原本上。在象征的意义上,他在那一刻实际上抛掉了束缚他的社会暴力,回到了自然的生存方式,因此走还是不走,就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社会对其已不再是约束。他发现了生存的自然状态,就像那头骡子一样,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下,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欲望,这是一种自然,也是一种姿态。在这一刻,大杞终于明白了离开城市只不过是一种无望的逃避,而恰恰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自然才是找回自我的唯一方式。
总之,残雪和李沧东的小说,都有着一种强烈的反抗,残雪从早期绝望而孤独的反抗,走向了一种更加积极的反抗姿态,这种积极姿态与要反抗的现实形成了对立,是对反抗对象的彻底拒绝;而李沧东的小说中,反抗具有强烈的悲剧性,虽然最后也充满着一点希望,但这种希望并不是改变了现实,而只是对现实的承认或者说和解,对现实的回避,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解脱之处。与残雪不同,李沧东的小说中,被压抑的无性身体,往往会转换成自然的身体。《一头骡子的心事》中,回到自然只是个体的一种心灵慰藉,不是一种超越。《火与灰》中僵化停顿的夫妻关系,生存的无意义,最后在少女的笑容中发现充满希望的未来;《舞》被穷困压抑的身体,最后在一无所有的清醒认可中,走向身体自然而激情的舞蹈;《战利品》强烈的渴望与身体无关,最后在丢弃身体之一部分的过程中找回了自我。
三、结语
比较,是为了发现。将残雪和李沧东置于同一视域中,发现人性的异化是两位作家的共同主题,李沧东是以性欲来象征权力欲,而残雪则重在权力压抑下的生存图景。由此,他们去思考生存的价值以及反抗的可能性。残雪笔下的反抗,具有一种解放的积极姿态,而李沧东的小说世界,却笼罩着一种强烈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