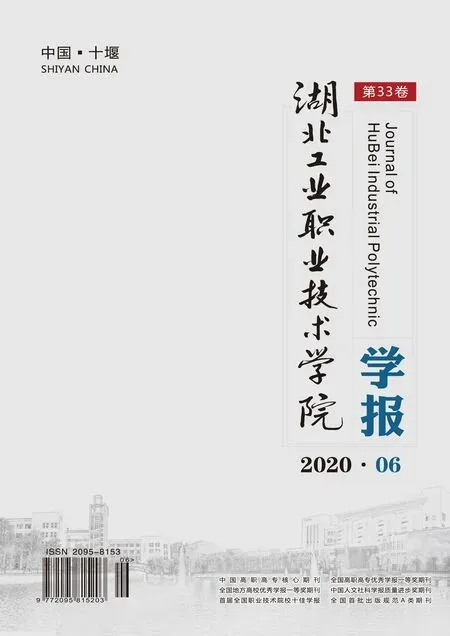《黑客帝国》的空间政治与身份建构
黄 夏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
上映二十余年,《黑客帝国》(The Matrix)系列电影早已在全球范围内收编了一批庞大的狂热粉丝,其所实现的商业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该系列电影还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在科幻电影领域,《黑客帝国》三部曲不仅成功形塑了母体空间和真实空间两大空间维度,还涉及了虚拟与现实、人类与机器等伦理命题的讨论,体现了沃伦斯基导演的空间意识与哲学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游走于两大空间的主人公尼欧,其伦理身份发生了多次变动:从程序员变成黑客,并最终成为人类社会的救世主。结合空间理论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来看,尼欧人物的成长轨迹实际揭示了空间政治与身份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阐释。
一、母体空间的规训系统
《黑客帝国》的英文片名为The Matrix,在拉丁文中“Matrix”最早意为“怀孕的动物”,后引申为“子宫或母体”。在英文语境中,“Matrix”一词还有铸模或模型、岩石或矿脉、数字矩阵等涵义,对比之下,该电影的中文译名稍显片面。实际上,除了字面的多重指向,“Matrix”在电影中的符号意蕴更为复杂。首先,“Matrix”是一种虚拟程序,即促使电脑运行的数字代码,其次,它是一套控制系统,为控制以尼欧为代表的人类而生成的虚拟世界;再次,它是一个种植基地,在那里人类被禁锢在盛满培养液的玻璃器皿里,身上插满了各种插头以接收系统发送的感官刺激信号。归根结底,用剧中人物墨菲斯(Morpheus)的话来说,母体空间就是控制,其存在意义在于首先为人类建构一个梦幻空间,以掩盖人类早已被改造为系统自身的动力能源的事实。聂珍钊指出:“人类不仅在创造科学,发展科学,也同样接受科学的影响及科学对自身的改造[1]252。由《黑客帝国》的动画版即故事前传可知,曾经在人类和机器战争之时,人类自以为可以借助黑雾覆盖地球以阻挡机器的动力来源——太阳光线,结果却反遭机器的再深度利用。因为机器发现人体所产生的生物电和体热,可以为其提供一种更为高效的发电环境。在这种背景之下,人类自身的繁衍彻底被母体空间管控,婴儿的出生再也无需母亲的十月怀胎,只需经由机器的生产培育。这也就解释为什么基努·里维斯所饰演的男主人公尼欧可以无父无母,不涉及任何血缘关系。
正如福柯所言,“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2]在《黑客帝国》中,身处母体空间的人类生活如同普特南设想的“钵中之脑”实验。人脑被截下放入培养液中,其神经末梢与一台超级计算机相连接,便可以使大脑的主人具有一切如常的幻觉。通过变换程序,计算机同样可以使其体验到任何情境,甚至可以消除脑手术的所有痕迹[3]。母体空间正是以神经交互系统无所不在的触角,掌控着人类的所有活动乃至感知层面:一方面,母体空间将人类禁锢在玻璃器皿里,提供培养液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另一方面,为了促使人类“忘却”自身处境,母体空间架构一个模仿人类生活的虚拟空间。在此语境中,母体空间掌握了绝对的控制权,人类则完全丧失了主体性,不仅身体被严重束缚,甚至意识亦无法实现自由,只能沉湎于母体空间为其编织的瑰丽泡沫之中。简言之,在母体空间中,人类的“囚徒”状态是因身体禁锢而起,最终延伸至思想层面的彻底不自由。在此,人类身体已经卷入权力规训的政治机制,“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4]
在母体空间中,生活在1999年的男主人公首先有一重光鲜亮丽的伦理身份:一名软件公司的普通程序员,名为托马斯·安德森(Thomas Anderson),有社区安全账号,定时缴纳个人所得税。“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有时甚至是强制性约束,即通过伦理禁忌体现的约束。”[1]264软件公司的运作模式参照母体空间的生存法则,每位员工是公司整体的一部分,必须服从整体的发展,否则便被清除。该公司老板所鼓吹的管理之道,恰恰对应着安德森与母体空间脆弱的关联。安德森之于母体空间,不过是虾米与大海,只要他愿意接受控制,母体空间随时可以为其锻造一份远大的前程。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关于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其中,空间表征为构想空间,代表的是社会统治阶级所构想的与生产关系相关联的空间构建原则[5]。为了确保人类安心地为机器运作提供动能,母体空间以二十世纪末的生活状态为模型,为人类仿造了一个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现代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切都是经由机器复制的数字代码,人类社会处于一个静止的平衡状态。历史上的人机大战被完全抹杀,未来也不会发生变化,既没有创新,也不会进步。“这不仅意味着我们没有栖身的过去,也无力创造自己的未来,一切都是已经被二进制形式存贮的‘程序’所决定的,人本身沦为一个计算过程中无关紧要的‘参数’”[6]98,由此断言,母体空间的运行法则即保障所有个体都服从其控制,不允许任何差错的发生。而以史密斯为代表的特工队伍便是母体空间的防卫系统,负责清除各种异端分子,保障母体空间的稳定运转。
在安分守己的表面生活之外,男主人公另有一重截然相反的伦理身份——网络世界的著名黑客尼欧(Neo),他终日坐在电脑前寻找黑客组织的首领墨菲斯。身处母体空间的男主人公,愈发感受到其中的不真实,但受限与自我的认知水平而无法窥探其本质。尽管此时的尼欧有违于母体空间,但因为身体并未获得解放,他仍处于母体空间的控制之下,犹如仰仗呼吸机存活的病人。尼欧以黑客身份进行的各种破坏行动,并不会对母体空间构成致命的威胁。安德森和尼欧的生存空间是迥异的,甚至是相对立的:一面是陷于控制的安逸,一面是寻求反抗的潜伏,分别指向人类对于母体空间的两种选择。安德森代表的安逸无疑是主流选择,甚至可以在母体空间中占有99%的比重。如墨菲斯断言,“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被解救,更有甚者,他们对此麻木不仁,死心塌地地依赖着这个系统,以至于为它而战。”如厌倦了为真实空间争斗的塞弗(Cypher),打算与史密斯合作重新回到母体空间的控制,享受快乐又虚幻的一生。随着伦理身份的切换,男主人公尼欧内心深处质疑现有生活的潜意识很快暴露人前。当墨菲斯抛出蓝色药丸和红色药丸的选择之时,尼欧毫不犹疑地吞下后者,即放弃高度文明的虚拟世界。由剧情发展可知,红色药丸实际是一套追踪程序,墨菲斯以此为线索,从种植基地中找到尼欧的身体。由此,尼欧获得了第一次重生。
二、真实空间的反抗运动
从空间形态来看,真实空间的时间大体接近2199年,比母体空间前进了两百年。不同于母体空间的舒适,真实空间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人类社会,生存条件十分低劣。正是在这黑暗贫瘠的文明荒漠,人类建立起与母体空间相对峙的反抗基地,影片中涉及了两处重要的地点:一为尼布甲尼撒舰(Nebuchadnezzar),二为锡安城(Zion)。尼布甲尼撒舰是墨菲斯的战舰,尼布甲尼撒为古巴比伦国王之名,这位国王战功显赫,自少年其便随父亲四处征战,曾将犹大王国的贵族和平民掳至巴比伦,最终致其灭国。在电影中,尼布甲尼撒舰是黑客运动的策源地,该舰作为入侵母体空间的媒介,对扩充人类的反抗同盟起到关键作用。舰长墨菲斯曾多次利用战舰,帮助沉睡之人觉醒,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困境,从而脱离母体空间获得人身解放,男主人尼欧正是其中一例。换个角度看,墨菲斯领导的反抗运动,实际是对母体空间的人力资源的有计划掠夺。
至于锡安城,位于地球深处,聚集了所有被解放的人类。相比之下,尼布甲尼撒舰只是总部派遣外出的一个行动单元,锡安城才是真实空间反抗运动的大本营。在宗教语境中,锡安为圣城耶路撒冷的小山,相传为耶和华的居住之所,也是大卫之王宫和所罗门之圣殿的修建地址。对于犹太人而言,锡安是上帝为其保留的圣地和家园,象征着上帝的荣耀和永恒的安宁。在电影中,锡安城作为人类尚存的最后一处庇护所,其角色定位与巴什拉在其《空间的诗学》提出的家宅概念相暗合,即“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融合中,联系的原则是梦想。过去、现在和未来给家宅不同的活力,这些活力常常相互干涉,有时相互对抗,有时相互刺激。”[7]相对于母体空间对人类的控制,锡安城是人类社会的最后家园,呈现出民主共和的空间表征,这实则是身处真实空间的人类对于政治传统的追念。“锡安的议会结构很像古罗马的元老院,由各个氏族的贵族代表为主要的成员,兼有立法权和管理权的国家机关,制定一切法律和制度,通过执政官执行。”[6]73对于真实空间的架构,人类重新着眼于古老的民主实践,将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糅为一体,为的便是实现未来空间能与母体空间相抗衡的期待。也就是说,以锡安城为代表的真实空间的存在意义即解放更多的人类,组建一支庞大的觉醒者队伍,反抗母体空间的控制。
在这个语境中,从母体空间觉醒的尼欧开始被奉为人类社会的救世主。救世主(the One)的字母组合来源于尼欧(Neo)一词的直接倒置,回到电影中,这更像导演安排的一场镜子游戏。在尼欧吞下红色药丸之后,眼前的镜子开始溶化与流动,他一伸手便可轻易穿透,似乎在暗示即将迎来一个镜子的虚幻空间。事实正好相反,尼欧需要面对的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在这空间置换的间隙,尼欧对于自我身份开始有了全新认知。与此同时,这场镜子游戏还延伸至战舰上的墨菲斯和崔妮娣。以拉康的镜子理论观之,“着迷于镜子,并被映于其中的统一的整体形象诱惑的幼儿的后面,一定存在着主体、镜像和第三人称的他者的目光。”[8]在电影中,墨菲斯和崔妮娣分别从先知那里知道自己与救世主的关联,他们两人的目光是尼欧之救世主身份成立的重要环节:前者以寻找救世主为使命,主动将反抗运动的领导权让渡于尼欧;而后者注定与救世主相恋,在电影中崔妮娣的关键一吻让尼欧获得了第二次重生,并且击败了特工史密斯,最终以此证明了救世主的强大。
然而,尼欧对于自我的“救世主”身份定位始终存有疑问。面对电子乌贼的大举入侵,洛克司令官提出空港外围防卫计划,要求动员全体公民,不论男女老幼。洛克司令官的救城计划直接挑战了墨菲斯信奉的救世主论,也对尼欧的“救世主”身份提出极大的质疑。为解决自我的身份困境,尼欧按照先知的指示,回到代码之源。正是在此,尼欧被母体空间的设计师告知另一个残酷的事实:锡安城的反抗只是编程系统的固有异常,属于母体空间的另一套控制系统,且救世主的职责亦非拯救人类,而是将一切归零,重新部署母体与锡安的对抗格局。之前通过救世主的选择,母体空间已完成了五次升级。由此可见,真实空间的人类所谓的觉醒只是一种“伪觉醒”,他们开展的反抗运动也只是母体空间运转机制的一部分,并未完全脱离其控制与规训系统。“在具体的选择中,由于选择的伦理性质不同,其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亦不同。”[1]267知道真相的尼欧,没有像前辈们一样义无反顾地成全谎言,他拒绝接受系统的安排,选择救下身陷重围的崔妮娣。这不只是为了两人的爱情,更是对于救世主既定宿命的反抗,寓示着尼欧的真正觉醒。
三、虚实两界的制衡关系
历经母体空间与真实空间的双重颠覆,尼欧的空间认知出现了结构性错位。离开代码之源后,尼欧的生命并无任何异常,但意识被困于一个由火车人控制的程序中,即母体空间与真实空间的中间地带,既被母体空间拒绝,亦无法返回真实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已被消解。刚好有一对父母和女儿,他们只是程序,却如同人类一样相信爱和宿命,甚至甘愿为爱牺牲自身。其中的父亲拉玛对尼欧说:“宿命和父爱一样,只是一个字眼,但也可以表达出‘我来到此处来的目的’。”在此,无父无母的尼欧通过一个程序接触到了人类家庭的伦理关系,即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仿真”。“仿真”是鲍德里亚提出的一个概念,认为“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种非真的状态,但这种非真的状态是一种‘模拟’之真,它虽然不是原始的朴素之真,但却是比那种原始之真还要更加‘逼真’。”[9]当真实的界限日益模糊,程序生产的虚拟世界无限接近现实世界之时,其中暴露的矛盾问题亦将趋向一致,甚至可以互相印证。为摆脱控制,尼欧从母体空间逃到真实空间,却发现真实空间同样深受控制。在真实空间中,不仅是设计师规划的“控制”,更重要的是,机器文明对人类生活悄然无息的渗透。尽管锡安城的人们拒绝母体空间的控制,甚至为此与机器抗争,而事实上,热能、水力等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所有资源皆来自机器的运转。由此可见,人类和机器早已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关联,这又何尝不是控制?母体空间与真实空间皆处于控制系统之下,人类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在控制之中寻求生存的自由。
在电影中,生存问题最终成为两大世界共同面临的考验,也为两者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可能。在真实空间中,电子乌贼向来是人类生活最大的困扰。按照母体空间的派遣,电子乌贼的攻势愈发凶猛,在锡安城外疯狂集结,人类危在旦夕。在母体空间中,史密斯的迅速扩张使得母体空间的系统濒临崩坏。史密斯在决斗意外得到尼欧身上的核心代码,不仅获得重生,还可以将母体空间的所有程序和人类复制成自己。事实证明,从杀毒程序变成特殊病毒的史密斯,已经具备毁灭母体空间的能力,只凭一己之力便可占领母体空间,耗尽其中所有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大世界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皆因机器文明的膨胀而起。“在新的社会时代,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伦理道德关系遭到破坏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1]185对于人类而言,电子乌贼代表的是高度发达的机器文明,对于母体而言,史密斯则来自机器文明的自身异化。而针对生存危机的解决,两大世界对救世主各有期待:对于真实空间而言,救世主可以终止战争,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安宁;对于母体空间而言,救世主则意味着世界重启,帮助控制系统实现升级。在母体空间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人类对于救世主的信仰不过是一种虚妄。随着形势的变化,救世主的身份问题将重新定义。据齐泽克所言,“黑客帝国系列影片的关键特色是逐步把史密斯提升为主要的负面英雄,提升为对世界的威胁,提升为对尼欧的某种否定。”[10]作为救世主的对立面,史密斯的异化使得母体空间陷入极度被动,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对尼欧而言是一个契机,为其提供了与机器大帝的谈判筹码。
尼欧救世主身份的最终定位来自两个世界的利益博弈。决战之前,尼欧与崔妮娣乘坐奈奥比的逻各斯战舰(Logos)到机器之城,以史密斯作为筹码与机器大帝谈判,试图换取人类的和平。这并不仅仅为保全锡安城,更重要的是,是为寻求两大世界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与此同时,尼欧决定返回母体空间,并非简单地服从救世主的既定宿命,而是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实现两大世界的制衡,他需要面对的是彻底异化的史密斯。史密斯的能量来源于尼欧,实际是尼欧的负极,即作为尼欧之恶而存在。表面上看,在这场以一对多的决斗中,尼欧的胜算几乎为零。正是因为看到史密斯的优势,尼欧允许自己被他同化,形成更为强大的能量场,引发母体空间的全面瓦解,并使之实现前所未有的改革。由此断言,史密斯与尼欧的决斗,既是尼欧的自我之争,是善之我与恶之我的对抗,也是人类的欲望之争,是伦理底线与欲望深渊的较量。尼欧以一人之死成全了两大世界的和平稳定,也因此成就了自我的救世主身份,体现了人类正义与理性的胜利。由于尼欧的牺牲,母体空间和真实空间最终形成了对立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为人类社会建构一种全新的空间格局。
《黑客帝国》结局的空间架构实际为现代社会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科技伦理命题。随着现代科技的深入发展,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日渐消弭,人类正在逐步进入数字技术建构的虚拟空间,并且极有可能在其中获得比现实空间更为优越的体验。相比于现实空间,虚拟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人类对于乌托邦寄予的期待。在此背景下,科技文明的过度发展,人类社会将该如何与之共存?是选择入梦,在虚拟空间满足自我?抑或是是选择觉醒,直面现实世界的残酷?对于这些问题,《黑客帝国》的回答是倾向现实的。正如齐泽克所言,“《黑客帝国》最终扭转了这种颠倒:将理想化和非理想化的境地结合起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即母体为我们创造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完美境地,处于一个适当的位置,因此,实际上我们被迫处于一种为母体提供能量的电池的被动状态。”[11]换言之,《黑客帝国》实则确认了现实空间的人类的生存处境。科技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的历史大势,而我们同样亦有无法推却的历史责任——对科技文明的膨胀保持警惕,谨防虚拟空间的“糖衣炮弹”,时刻坚守人类的伦理底线,最终实现利益共赢。
四、结语
统观《黑客帝国》三部曲,母体空间以神经交互系统的技术优势,控制着人类的所有行动乃至感知活动,是体现权力运作的虚拟空间;基于现实空间的满目疮痍,真实空间的人类建立起与母体空间相对峙的反抗基地。结尾之处,母体空间与真实空间从对抗走向统一,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利益共同体,而主人公尼欧的多重身份最终定位为救世主,完成了人类自身的身份建构与自我超越。通过两大空间的架构,该系列电影重新探讨了虚拟与现实、人类与机器等伦理命题,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现代社会的科技生态问题。科技发展之大势已不可逆转,在此伦理环境下,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日渐消弭,诸多固有的二元对立观念亦不断被打破,人类又该何以与科技共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