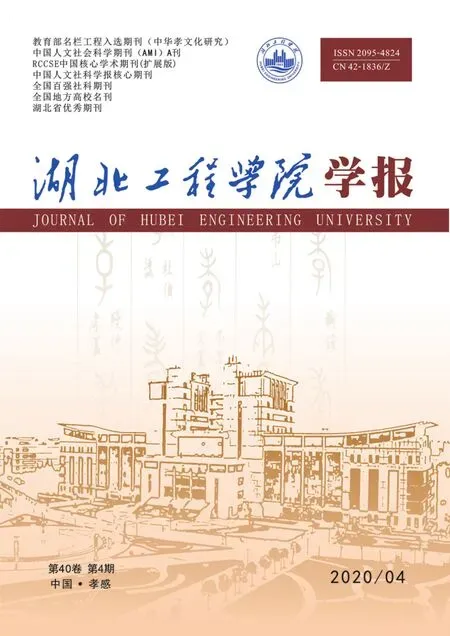事亲之“孝”与“至孝”:《庄子》中“孝”观念的两层意涵
张文虎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庄子》中的“孝”有两层意涵:其一,事亲之“孝”;其二,“至孝”。“至孝”是“孝”的最圆满表达,事亲之“孝”与“至孝”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性关系。本文将从事亲之“孝”入手,逐层分析事亲之“孝”的特点、内涵及“尽孝”的手段,然后探索“至孝”的构成以及“至孝”与事亲之“孝”的关系。庄子以“自然本性”(“命”)作为“孝”存在的合法性源头,因此事亲之“孝”带有非责任性的特点。子女对双亲“尽孝”,关键在于让双亲从内在精神方面感到“心安”。让双亲感到“心安”则需要“子”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忘身”;二是“行事之情”。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可以有效避免“伪孝”的产生,因此“真心”是“孝”的基本精神内核,而“亲”与“子”之间的“和睦”是“真心”得以显现的保障。庄子认为事亲之“孝”可能会伤害“亲”“子”双方的身心健康,于是提出“至孝”观念。庄子“至孝”的理想目标,是他所构建的“方外”之理想世界的内在要求,也是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之逻辑推进的必然结果。对存在于“事亲之孝”中的人伦关系的解构则是“至孝”得以形成的根基,而由“事亲之孝”到达“至孝”,则需要“忘”的修养工夫。
一、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
庄子把“孝”置于“自然本性”(“命”)的视角下阐释,即“自然本性”(“命”)是“孝”存在的合法性源头。(1)虽然《庄子》一书并非庄子独作,但在“孝”这个问题上,外杂篇的论述理路基本沿着内篇的论述理路所进行,因此,内篇与外杂篇的观点皆用庄子之名。
如《人间世》曰: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庄子·人间世》)
庄子借孔子之口表达论点,他认为子女对双亲之“孝”由“命”所决定,“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此句郭象《注》云:“自然结固,不可解也。”成玄英《疏》云:“此之性命,出自天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1]155郭象与成玄英皆把“命”理解为人的“自然本性(性命)”。“自然本性”(“命”)与生俱来,不事“人为”,因此子女对于双亲之“孝”亦自然固有,应自然奉行。“自然本性”(“命”)不包含“人为”之事,所以庄子不认为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行为是“孝”存在的依据。子女对双亲之“孝”,并不是由于“亲”与“子”之间的责任与义务,而是由于“本性(性命)”之“自然”,因此庄子所讲的“事亲之孝”带有非责任性的特点。
子女对双亲“尽孝”,关键在于让双亲感到“安适”,“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此种“安适”不讲求物质等客观层面的满足,最重要的是让双亲感到“心安”,曾子“尽孝”的例子便体现出这一点: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后仕,三千钟而不洎亲,吾心悲。”弟子问于仲尼曰:“若参者,可谓无所县(悬)其罪乎?曰:“既已县(悬)矣。夫无所县(悬)者,可以有哀乎?彼视三釜三千钟,如观鸟雀蚊虻相过乎前也。”(《庄子·寓言》)
金钱等外在之物只是“行孝”的手段,而外在事物没有一定准则,“外物不可必”(《庄子·外物》)。若依据“外在之物”去“行孝”,行孝者心中定有“哀乐”的变化,此种变化亦可导致双亲的心中产生“哀乐”的变化,从而让双亲“安适”的目标不能达成。所以庄子说:“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成玄英《疏》曰:“夫孝子养亲,务在顺适,登仕求祿,不择高卑,所遇而安,方名至孝。”[1]156“不择地而安之”就是无论自身处何种境遇(无论“位高”或“位卑”,无论“富”还是“贫”)都应让双亲感到“心安”。
那如何才能让双亲感到“心安”呢?庄子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成玄英《疏》曰:“夫臣子事于君父,必须致命尽情,有事即行,无容简择,忘身整务,固是其宜。苟不得止,应须任命也。”[1]157由此可知,此句不仅是处理“君臣”关系的方法,亦是处理“父子”(“亲”“子”)关系的法门。让双亲感到“心安”应把握两点:第一点,“行事之情”;第二点,“忘身”。“行事之情”就是安于自身之所遇,把握所遇之事的实情至理,任其发展。
那“忘身”该如何理解?庄子说:“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 他认为养亲(“尽孝”)需要做到“缘督以为经”,此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把“督”释为“中”,郭象《注》云:“顺中以为常也。”[1]117第二种解释把“督”释为“虚”,郭嵩焘曰:“督者,居静而不倚于左右,有脉之位而无形质。缘督者,以清澈纤妙之气,循虚而行,止于所不可行,而行自顺,以适得其中。”[1]117其实,这两种解释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可以相互贯通。对于第一种解释,庄子说:“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缘督(中)”即为“得其环中”,把握“环中”即把握“道枢”,“缘督以为经”即顺“道”以为常,把握常“道”(自然之道)。对于第二种解释,庄子曰:“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缘督(虚)”即为“顺道”,而达“道”则需要“心斋”的工夫。由此可知,这两种解释皆强调顺应自然之“道”在养生、养亲(“尽孝”)方面的重要作用。把握“道”则需要“心斋”的修养工夫,因此,养生、养亲(“尽孝”)主要指一种精神方面的修养。此修养达到一定境界,则“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庄子·逍遥游》),可以“保身”、“全生”、“尽年”。此种修养,要以人的内部精神世界为准则,不能过分关注身体及外在之物的变化。如庄子论“养生”时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由以上论述可知,“忘身”是忘却身体及外在之物的变化,把他们从“心”中祛除,而提升精神层面的修养。
子女对双亲“尽孝”,关键在于让双亲从内在精神方面感到“心安”。让双亲感到“心安”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忘身”,即忘却自身身体及外在之物的变化,把他们从“心”中去除,而进行精神层面的修养。另一方面,“行事之情”,即安于自身之所遇,把握所遇之事的实情至理,任其发展。事亲之“孝”由“自然本性”(“命”)所决定,且带有一种“非责任性”的特点。“事亲之孝”与“亲”“子”双方之间的伦理性、责任性的“亲情”(人为)无关。此种“非责任性”的“孝”可以有效地避免“伪孝”的产生。《庄子·外物》篇记载的一则故事,便是有效例证:
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
郭象《注》曰:“慕赏而孝,去真远矣,斯尚贤之过也。”成玄英《疏》云:“闻其因孝而贵,于是强哭诈毁,矫性伪情,因而死者,其数半矣。”[1]945以庄子之观点分析此事,“真”孝者不会在意“生死”,“生死”是人自然的变化,“生死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愚,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也不会关注自己身体及外在之物的变化(“善毁”),从而不会得名得利。党人亦过度关注自己身体及外在之物的变化,“强哭诈毁,矫性伪情”,把“孝”仅仅作为取得名利的工具。“演门孝者”这个群体,“去真远矣”。由此可知,“真”是“事亲之孝”的基本内涵。
二、“真心”为“事亲之孝”的内核
庄子认为“真心”是“孝”的基本精神内核,而“亲”与“子”之间的“和睦”是“真心”得以显现的保障。
《庄子·渔父》(2)王船山说:“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盖内篇皆解悟之余,畅发其博大轻微之致,而所从入者未之及。则学庄子之学者,必于杂篇取其精蕴,诚内篇之归趣也。”但对于《渔父》篇,他却说:“若《让王》以下四篇(即《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自苏子瞻以来,人辨其赝作。……《渔父》《盗跖》则妬妇骂市,瘈犬狂吠之恶声;列之篇中,如蜣蜋之与苏合,不辨而自明,故倶不释。”他之所以对《渔父》篇指责,一方面受苏轼以来的传统观念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他没有确考《渔父》整篇文章与内篇的联系。在“真”“孝”这一主题上,《渔父》篇确实能“ 发内篇未发之旨”[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1:196]。记载:
孔子悄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忠贞以功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真者,精诚之至也。”成玄英《注》曰:“夫真者不伪,精者不杂,诚者不矫也。”[1]1032“真”者“不伪”,“不伪”即不事人为,所以“强亲者虽笑不和”“真亲未笑而和”。“真”者,“受于天”“自然不可易”,不做作,所以“不矫”。“真者在内”,“在内”者不受“在外”者所扰,而“在外”者“不可必”(《庄子·外物》),所以“在内”者纯而“不杂”。“真”即纯一、不事人为、不做作。如上文所言,子女对双亲“尽孝”,关键在于让双亲从内在精神方面感到“心安”,“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亲以适为主”,而“真”是处理“事亲”(孝)之事的准则,“其(真)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由此可知,“真心”是“孝”的基本精神内核。
但如何才能保障“真心”的显现呢?这要从“亲”与“子”的两方面来考虑:一是“子”对“亲”应该“孝”,二是“亲”对“子”应该“慈爱”。
一方面,“子”对“亲”之“孝”应不“谀其亲”。“孝子不谀其亲”(《庄子·天地》),“谀”字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成玄英《注》曰:“谀,伪也。”[1]447孝子应对双亲怀有“真心”,保持尊敬,不应被世俗之见所干扰,成为流俗的“道谀之人”。如《庄子·天地》篇所言:
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孝子……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所谓然而然之,所谓善而善之,则不谓之道谀之人也。然则俗故严于亲而尊于君邪?谓己道人,则勃然作色,谓己谀人,则怫然作色。而终身道人也,终身谀人也,合譬饰辞聚众也,是终始本末不相罪坐。
第二种解释,陈鼓应把“孝子不谀其亲”译为“孝子不阿谀他的父母”[2]358。
其实,“伪”与“阿谀”这两种释法,都表达了“子”对“双亲”应怀有的“真心”。但陈先生的翻译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即“子”不应该“唯父母之命是从”,对于双亲错误的言论与行为应加以劝阻与制止,这也是对父母“真心”的体现。
另一方面,“亲”对“子”应该“慈爱”。“孝”存在于社会交互性关系中,“亲”“子”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子”对“双亲”之“孝”是“孝道”的主要内容,“亲”对“子”之“慈爱”则是“孝”得以显现的前提。
《庄子·外物》篇记载了几则关于“孝”的故事:
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
成玄英注曰:“孝己,殷高宗之子也。遭后母之难,忧苦而死。而曾参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邻乎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义重,而至忠至孝,尚有不爱不知,况乎世事万途,而可必固者!惟当忘怀物我,适可全身远害。”[1]921
孝己、曾参、比干(比干的事例既包含了“亲子关系”又包含了“君臣关系”)三人皆对双亲“尽孝”,但自身却遭受大难(“死”或“悲”)。导致此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双亲”违背了“自然本性”(“命”)的要求,忽略了“亲”“子”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事实。“亲”若“欲其子之孝”,则他们需要“爱”子,如此才能使“孝”自然显发,因此,“亲”与“子”之间的和谐是“孝”(“真心”)得以显现的保障。
“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以“真心”为内核,有效地避免了“伪(俗)孝”的产生,但仍处于社会伦理的架构之内(“子”对“亲”采取“尽孝”的形式)。从成《注》可知,“亲”“子”双方处于社会伦理关系的架构之内,“孝”的交互性特点要求“亲”“子”平等对待对方,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应“自然之性”的规定,这其中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庄子看出了把“孝”置于社会伦理架构之内的弊端——可能损害“亲”“子”双方的身心健康,于是庄子突破这种架构,构建出一种“方外之孝”——“至孝”。
三、“方外”之“至孝”
庄子“至孝”的理想目标,是他所构建的“方外”之理想世界的内在要求,也是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逻辑推进的必然结果。对存在于“事亲之孝”中的人伦关系的解构则是“至孝”得以形成的根基,而由“事亲之孝”到达“至孝”,则需要经过“忘”这一环节。
庄子在《庄子·天运》篇曰:
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 ?”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大宰曰:“荡闻之,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谓至仁不孝,可乎?”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矣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
此则对话由谈论“仁”始,但被商大宰引向“孝”,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亲”。庄子认为商大宰由“至仁无亲”推论出的观点并不成立,“至仁尚矣,孝固不足矣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 。成玄英《疏》曰:“商荡之问,近滞域中,庄生之答,远超方外。故知亲爱之旨,非过孝之谈,对执名教,不及孝之言也。”[1]499
庄子在这句话中,区分了“孝”的两层意涵。“孝固不足矣言之”之“孝”是指“事亲之孝”,因为“事亲之孝”还存在于社会人伦关系中,带有“亲”的因素,而“至仁无亲”,所以不能以“孝”(亲)言“仁”。商大宰以“亲”言“孝”,“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庄子认为商大宰以“亲”言“孝”的看法并没有“及孝”,由此可知,庄子所言“非过孝”“不及孝”之“孝”是一种“无亲”之“孝”。结合“至仁无亲”的说法,“无亲之孝”是一种“至孝”。
那庄子为什么提出“至孝”呢?“至孝”的内涵又是什么呢?成玄英《疏》中的两个词“域中”与“方外”为我们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思路。成玄英在此疏中用了“以庄解庄”(以内篇思想解释外篇思想)的诠释策略,“域中”与“方外”出自《庄子·大宗师》篇“临尸而歌”的故事,故事如下: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域中”与“方外”分别对应“方内”与“方外”。“方内”是指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世俗世界,“方外”是指庄子所建构的以“逍遥”“无为”为根基的理想世界。庄子之“方外”世界,要超越世俗之礼乐文化,“孝亲”是礼乐文化世界的重要观念,所以“方外”世界亦超越“孝亲”这一观念。因此,庄子的“至孝”理想目标,是他所构建的“方外”之理想世界的内在要求。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由“自然本性(性命)”决定,而“自然本性”在生活世界中的开展,便形成庄子所谓“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生活图景。“至孝”是这种生活图景的重要部分,因此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的逻辑推进,必然达至“无亲”之“至孝”的设定。
庄子提出了六种“孝”道,此六种“孝”道也是通向“至孝”的六个环节,分别为:敬孝,爱孝,忘亲,使亲忘我,兼忘天下,使天下兼忘我。此六种“孝”道存在两种“亲”的关系:其一,血缘之亲;其二,非血缘之亲。(3)非血缘之亲是指“亲”“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在社会伦理生活中还存在“亲”的关系。如《外物》篇所记载“孝己”的故事,孝己与其后母便是“非血缘之亲”。“敬孝,爱孝,忘亲,使亲忘我”这四种“孝”道对于“血缘之亲”与“非血缘之亲”皆适用。“血缘之亲”与“非血缘之亲”皆由“自然本性(性命)”所决定,但“非血缘之亲”的范围无限,天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非血缘之亲”的一部分,因此“兼忘天下,使天下兼忘我”是专门对“非血缘之亲”而言的(4)王夫之说:“与天下相忘者,不私其亲,其亲亦不私焉。”从王夫之所言可知,“忘天下,使天下忘我”应在“亲”的视域下理解[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4]。,并由“非血缘之亲”而扩展到整个“天下”。
“事亲之孝”由“自然本性”所决定,同时被决定的还有“亲”“子”这种社会人伦关系。在生活世界中,此种人伦关系成为“俗孝”“伪孝”产生的源发性因素,也是通向“至孝”而需要突破的关键性屏障,对存在于“事亲之孝”中的人伦关系的解构则是“至孝”得以形成的根基。“亲”“子”关系的客观化存在,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抹杀,如若强行隔断此种关系,亦不符合庄子的本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于是庄子采取一种主观抽离的方式解构“亲”这种人伦关系。这种主观抽离的方式便是“忘”(5)黄圣平说:“《庄子》论孝,重在忘亲。‘忘亲’之‘忘’意味着父母与子女间角色意识的消解,也意味着‘孝’‘慈’等名教观念的遗落与淡忘。”[黄圣平.《庄子》论“孝”探微[J].西南大学学报,2018(4):33]。“使亲忘我”与“使天下兼忘我”两个环节的完成便达到了解构“血缘之亲”与“非血缘之亲”的目标。此目标的完成,使“孝”从社会人伦关系中解脱,达到“至孝”的境界。
“亲”属于社会伦理范畴,含有一种交互性关系。对“亲”这种关系的解构必定要从父母与子女双方入手,所以庄子构建了“忘亲,使亲忘我,兼忘天下,使天下兼忘我”的图景。庄子所说的“忘”是指双方互相 “忘”,即《庄子·大宗师》篇所言的“相忘”,“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据陈霞研究,庄子“相忘”的内容可分为忘物、忘德、忘知、忘己四个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着逐次递进的关系。“忘物”就是忘掉“外物”及因“物”所产生的欲望。“忘德”就是忘掉道德,将人从各种社会关系和礼乐文明塑造的 “我”中解脱出来。其方法就是忘掉 “仁义”、“礼乐”、“天下”,让人与人之间互相遗忘。“忘知”就是从对知识的追求中超脱出来。“忘己”是忘掉自我,忘记身心,在 “忘己”之中将人生进一步提升,最终使人“同于大通”,回到与 “物”的原初和谐之中。[3]
那庄子忘“亲”之内容有什么呢?首先,“忘亲”即“忘敬孝”“忘爱孝”,“孝”属于“礼乐”文化的内容,因此“忘亲”即“忘德”。其次,“忘亲”包含“忘知”“忘己”两个方面。陆西星对“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疏解道:“爱孝易而忘亲难,忘亲则不识不知,不知帝力之何有。盖熙皥之民而混沌之德也,故以为难。忘亲易而使亲忘我难者,凡亲之不能忘我者,我以有心感之也,今也使亲忘我,则是我无心也,亲亦无心也,浑然化而入于无迹矣,故尤以为难。亲犹一家也,至于忘天下而使天下倶忘我焉,则忘之尽矣,非至人,其孰能之哉?”[4]“忘亲则不识不知”就是从对知识的追求中超脱出来,即“忘知”。“凡亲之不能忘我者,我以有心感之也,今也使亲忘我,则是我无心也,亲亦无心也。”“无心”就是忘记身心,即“忘己”。经过“忘德”“忘知”“忘己”三个阶段,便完成了对“血缘之亲”与“非血缘之亲”的解构。因为“在 ‘忘己’之中将人生进一步提升,最终使人“同于大通”,回到与 “物”的原初和谐之中” 。“同于大通”即庄子所言“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方外”理想世界,所以经过“忘德”“忘知”“忘己”三个阶段,便达到了“至孝”的理想目标。
四、结 语
《庄子》中的“孝”观念有两层含义:其一,事亲之“孝”;其二,至“孝”。事亲之“孝”带有非责任性的特点,因此子女对双亲“尽孝”的关键在于让双亲的内在精神方面感到“心安”。让双亲感到“心安”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忘身”,即忘却自身身体及外在之物的变化,把他们从“心”中去除,而进行精神层面的修养。二是“行事之情”,即安于自身之所遇,把握所遇之事的实情至理,任其发展。此种“非责任性”的“孝”可以有效地避免“伪孝”的产生,因此“真心”是“孝”的基本精神内核,而“亲”与“子”之间的“和睦”是“真心”得以显现的保障。事亲之“孝”处于社会伦理关系的架构之内,“孝”的交互性特点要求“亲”“子”平等对待对方,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应“自然之性”的规定,这其中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庄子看出了把“孝”置于社会伦理架构之内的弊端——可能损害“亲”“子”双方的身心健康,于是庄子突破这种架构,构建出一种“方外之孝”——“至孝”。庄子的“至孝”理想目标,是他所构建的“方外”理想世界的内在要求。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由“自然之本性”决定,而“自然本性”在生活世界中的开展,便形成庄子所谓“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生活图景。“至孝”是这种生活图景的重要部分,因此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的逻辑推进,必然达至“无亲”之“至孝”的设定。由事亲之“孝”到达“至孝”,则需要经过“忘德”“忘知”“忘己”的修养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