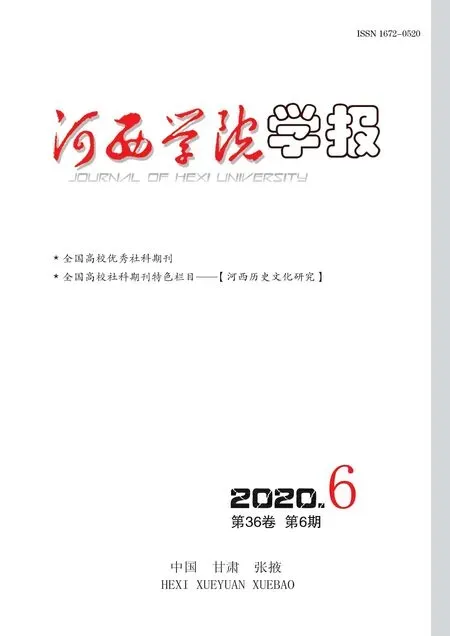古代河西走廊蚕神再考
高 彦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20 世纪30 年代以来,随着大批敦煌、吐鲁番、汉简文书以及大量考古研究成果的公布,学者们发现自两汉讫宋初,古代河西走廊的桑蚕业不仅有一定的规模生产,而且民间祭祀先蚕的活动也一直“沿而无衰”。陈炳应对河西桑蚕业作了较早考证,认为至迟从距今四千年左右,甘肃东部地区即已掌握了蚕桑丝织技术,已从事蚕桑丝织生产了。①李并成对甘肃西部河西走廊的桑蚕业做了细致的考察,得出河西从事养蚕织丝当始于西汉时期,发展于魏晋时期、鼎盛于唐代、衰落于宋初的结论。②闫廷亮对历代河西的桑蚕生产做了梳理,特别是对明清时期河西地方史志中记载的桑蚕信息做了概述,总结到古代河西地区是闻名遐迩的蚕桑生产区域,到近代,在桑蚕业衰败的背景下该地仍有养蚕织丝的零星分布。③赵玉平利用S.5639《蚕延愿文》,对文书中的十位蚕神逐一做了考察。④以上学者除用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对甘肃东、西部的蚕桑丝织业做了梳理外,还采用图像志的方法对敦煌地区的蚕礼进行了探究。受其启发,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敦煌文献拟对古代河西蚕神再做一探讨。
一、文献所见河西走廊桑蚕业
两汉时期,河西走廊的桑蚕业生产已有很大的发展,出土文献对此情况多有记载。《居延新简》741JF16:1-16保留了一份《永始三年(公元前14 年)诏书册》,其中一条“治民之道,宜务于本,广农桑”的律令极为紧急,诏书要求下辖县乡立马执行,于是张掖太守、守郡司马宗行长史事十月传达,十一月已至金关啬夫吏。此简出土于金塔县汉金关遗址,该地属河西走廊境内,从诏书内容所提及的地域推测,与张掖毗邻的酒泉郡、乃至敦煌郡都是实施“广农桑”措施的重点地区。此项措施自实施后,颇见成效,从百余年后河西走廊成为丝绸路上重要经济地区可见一斑。
魏晋以降,河西走廊的桑蚕业已达到规模化生产。《晋书》载:“会稽王道子尝问其西土所出”,天锡应声曰:‘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⑤面对王道子的诘难,前凉王张天锡用“桑葚”巧妙答复,不仅成功地处理了这场公关危机,还对河西第一特产做了宣传和推广。佐证河西桑蚕业发展势头好的资料还很多,甘肃魏晋壁画墓就是其中一例。嘉峪关壁画墓中有多幅描绘桑园、采桑、缫丝场景的画面。例如,新城6 号墓东壁的《采桑护桑图》,画中有一株亭亭如盖的桑树,树下右侧是一提桑笼胸前挂彩缨的妙龄少女,左侧则是一拉弓射箭的英俊少年。从简洁生动的画面看,这种诗情画意的采桑场景无疑体现的是远离战争,社会安定的河西生活。此外,嘉峪关1号墓后室南壁、3号墓中室东壁和后室北壁、7 号墓后室南壁、12 号墓后室后壁及13 号墓后室后壁的“绢帛图、“卑女采桑图”,及新城4 号西晋墓“驱鸟护桑图”、5 号墓前室北壁“采桑图”等,都是墓主日常生活及财富的真实写照。据李并成统计嘉峪关墓中专绘采桑、蚕茧、丝帛以及蚕丝工器具的画面有140 幅,占砖画总数660 幅的21.2%。除嘉峪关外,酒泉东晋十六国墓画砖中也发现了“采桑”、“护桑”图。如下河清1 号墓,丁家闸5 号墓后壁左侧和酒泉果园乡西沟村7 座魏晋墓均描绘几组束高髻,穿窄袖裥色裙挎篮采桑的妇女。如前所述,酒泉墓的“桑园图”、“护桑育蚕图”,均是河西走廊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如实反映。
入唐以后,河西桑麻种植的规模更大。大谷2836号文书《长安三年(703)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碟》记载:“其桑麻累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盛唐时,河西凭借着冠绝寰宇的综合实力一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其发达程度如《资治通鉴》描述,“自安定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闫相望,桑麻翳野”,是时中国强盛“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⑥“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占领了河西的广大地区,但在长达七十多年的吐蕃政权时期,当地政府对农桑业仍采取鼓励政策。譬如,S.3287背《吐蕃子年五月沙州左二将百姓汜履倩等户口状》等多件文书都记载了“丝绵部落”生产、生活的日常。部落是吐蕃的基层行政单位,丝绵部落实为编制养蚕户组成的部落。据敦煌文书记载,吐蕃时期沙州(敦煌)原有的州、县、乡、里都被撤销,代之而起的是吐蕃部落,部落长官通常由部落使、部落大使担任。另外,吐蕃对多植园囿、植树养蚕的河西望族也授予大使头衔。阴家为敦煌望族,在当地拥有大量的农田、牲畜等财富,阴嘉政也因此担任“部落大使”,“山庄四所,桑杏万株”(P.4638)描述阴家来说也算是名至实归。由此可见,吐蕃对河西实行部落建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拉拢河西豪族让其参与到政权的管理中,以此达到民族关系的缓和与政权的巩固。其次,从国策上看,“奖励耕织”一直是吐蕃惯有的经济手段。P.2162《吐番寅年沙州左三将纳突历》中,有关敦煌百姓的纳突地点就多次提到蚕坊、百尺、百尺下村落等。从带有浓厚吐蕃色彩的纳突地点,我们获悉此阶段的桑蚕生产已到规模化经营的程度。再者,从长期的经济效益看,该经营方式对整个河西走廊丝织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活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归义军时期(848~1036年),河西农桑又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P.5007《敦煌》所吟:“仕女尚□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的景象,正是张氏归义军统治河西时期。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军镇,为何在经济上取得富足一方的政绩?究其原因,我们以为与归义军节度使统领百姓积极发展农业有关。如张议潮、张淮深叔侄统治时期,节度使妇人多次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地带领妇女养蚕缫丝。P.3720《张淮深造窟功德碑》曰:“夫人,颖川陈氏,柔容美德,淑行兼仁。闺门处治理之心,抚下施贞明之爱。居尊不弃于蚕桑。”S.5630《张淮深造窟记》又曰:“屈尊不弃于蚕桑”。归义军统治的中后期,敦煌蚕丝业更是一幅“蚕田善熟”、“蚕赋马鸣”的情景。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云:“畎平河之溉济,蚕赋马鸣”。Ch.00207《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记》又云:“次愿城隍晏谧,兵甲休行,无闻刁斗之声,永罢鼓鼙之响。春蚕善熟、夏麦丰登,东皋广积于千箱,甫亩倍收于万斛。”P.2085《燃灯文》载:“国泰人安,田蚕善熟;令公延寿、宝祚长兴。”安西榆林第20 窟宋雍熙五年(988)的发愿文亦有“蚕田善熟”的祈愿词。从上述材料可知,归义军时期尽管中原板荡、河西政权更替频繁,但瓜(敦煌)、沙(安西)二州桑蚕生产仍在当地政府的重视下有序发展。
二、文献所见河西之蚕神
敦煌文献S.5639 现存36 篇佛教斋文,《蚕延愿文》是其中一篇以“蚕农称意”为祈愿目的的斋文,黄征、吴伟二位学者最早对这篇斋文做了校勘整理,推测此卷写于公元935~974年间。
从《蚕延愿文》获知:河西民间祭拜的蚕神,不是官方所推崇的先蚕螺祖,而是民间供奉的本土神祗。《蚕延愿文》中列举了河西民众对牛王沙门、马鸣菩萨、王母、麻姑、蛟人、务女、后土夫人、九天玄女、龙王、电母十位神祇的供奉,其中牛王沙门、马鸣菩萨是印度佛教中的天神和高僧,其它八位均为中国的本土神祇。这种多神祇崇拜的现象在我国民间较为普遍,如雷闻在《书评:(唐宋民间信仰)》中所说:“在祭祀对象选定原则、祭祀目的和仪式的严格程度上,‘国家’与‘民间’一向存在着显著的区别”。⑦鉴于《蚕延愿文》中诸神祇所司职务的功利性和象征性,笔者拟对愿文中的女性神祇逐一考证,尤其是对河西民众影响较大两位神人——西王母和麻姑,做一重点论述,以期揭示河西蚕神信仰的风貌及其信仰体系的构建过程。
(一)西王母
西王母是中国上古神话中地位最显赫的女神,人们亲切称她为“始祖母”⑧“丰产女神”⑨“女阴之尊”“掌不死之药的女神”。文献中有“王母”“西母”“金母”“神母”之说,但在民间,老百姓习惯称之为“西王母”。西王母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的渔猎时代,《太平广记》引《风俗通》曰:“舜之时,西母来献白玉琯。”⑩从现有文字资料看,最早记载西王母的《山海经》,有五则材料描写其为氏族领袖。她的外貌,该书称:“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11]。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即西王母是帝王之女、人间君主,这种传说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记载。如《竹书纪年》载:“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12]又《穆天子传》卷三,西王母对天子答曰:“嘉命不迁,我惟帝女。”[13]
西王母成为中原一带供奉的吉神,与周天子西征、西汉帝王供奉有关。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王开始西征,穆王十二年,犬戎没有及时进贡,周穆王以此为由,亲自领兵对犬戎征伐,这是周天子第一次西征。从战果看:穆王伐犬戎,仅仅以俘获五个君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乃至“荒服不至”而告终。穆王十七年,周王第二次西征,这次穆王到犬戎地区受到了当地部落首领的热情接待。《穆天子传》曰:“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14],以至“乐而忘归也”。从这两则史料得知,西周时期是西王母由“人巫合一”的半人半兽形象演变为“王巫合一”人物形象的重要阶段。神职上,她由掌“司天之厉及五残”的氏族领袖转变为“操不死之药”的君主。此时的王母,实则完成了两次形象的转变。西汉时,皇帝信奉“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新儒家思想,加之统治者迷信方术,西王母又被尊为统御三界十方的群仙领袖,于是她的第三个形象——“道仙”又被成功塑造。《汉武帝内传》云:“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褡襡,文彩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玄璚凤文之舄。”至此,经过三次身份华丽转变的西王母,最终成为中原一带官方和民间共同尊奉的吉神。
河西与西王母建立联系的文献《山海经》卷二〈西山经〉载:“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郭璞云:‘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者,别自栖息于此山也。’[15]三危山在鸣沙山对面,在佛教未传时,该地“原是道教信仰的天下”[16]。敦煌壁画中有多幅西王母与东王公的长卷式故事画,如第249 窟、第285 窟、第294 窟、第296窟、第305 窟、第401 窟均是描绘二神外出巡天游览的场景,画中西王母高髻束冠、着大袖长袍、拱手而坐、表情肃然,俨然一副王者形象。敦煌文献亦有西王母为道仙的内容。如P.2004《老子化胡经玄歌》是一件讲述老子西出函谷关到西域对胡人实行教化的文书。其中第六首讲老子在周代西入流沙以前与尹喜会面的事情,其曰:“欲得求长生,读之易精神,将喜入西域,迁喜为真人。”《尹喜哀歌》中第四首,歌颂尹喜化胡后进谒西王母时的一段因缘,喜吟唱:“道见西王母,问我子何归?耻身不学道,意欲觅仙师。”从整首玄歌来看,河西地区早已把西王母纳入到本地神话信仰的体系当中,且在百姓心中她的排位要高于老子和尹喜。
对河西民众而言,他们为了满足自身一己的利益,往往给神祗赋予新的职能。如《蚕延愿文》所讲,王母为先蚕,肩负着赐蚕之职。那么,西王母为何在唐五代又被河西地区奉为蚕神呢?究其原因,笔者分析如下:
1.与遵循织丝为业的女德有关
在卷帙浩博的文献中,西王母与妇女“休其蚕织”的内容比比可见。如六朝小说《汉武别国洞门记》云:西王母曾率领众仙“采桑于白海之滨”。魏晋时期是道教迅速发展的时期,王母被纳入道教神仙体系成为掌管女仙名籍的先蚕,一方面与“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的妇功有关。另一方面与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的政治形势有关。唐五代,王母被河西百姓奉为蚕神,还有佑庇一方平安的“使命”。P.3645《东方朔偷桃》载,王母指东方朔曰:“此小儿三度到我树下偷桃,我捉得,系著织机脚下。放之而去之,今已长成。”
汉代画像砖中,有一类西王母手持“工”字形器物的图像,据刘海宇考证,此类器物的名称应为文献中所见的“纴器”,这种器具不仅用来整理葛麻类纱线,也用来络蚕丝,是古代常见的绕线用具。[17]笔者查阅十六国时期魏晋壁画墓的相关资料,惊喜地发现河西地区有两处西王母画像与前类画像砖十分相似。一幅是酒泉丁家闸5 号墓的壁画,画中西王母是高髻饰冠、凭几正襟危坐、拱手于袖中的形象。另一幅藏于高台县骆驼城砖墓中,画中西王母束高髻,着大袖袍,凭几拱手而坐,手中不再持“工”字形纴器,而是用“工”字华胜装饰头发。
华胜又名花胜,今指妇女发簪两端的装饰。华胜原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发饰。刘熙《释名·释首饰》曰:“华,象草木华也。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则胜也,蔽发前为饰也。”[18]颜师古《汉书·司马相如》中注:“胜,妇人首饰也,汉代谓之华胜。”[19]《后汉书》解释为:“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20]高春明说“胜”的原始雏形为“中部为一圆体,圆体的上下两段附有对向的梯形饰牌,使之系缚在簪钗之首,横插在两髻。”[21]另一说是织机上的构件。在郭宝钧[22]、日本小南一郎[23]研究的成果上,沈从文对“胜”做出了总结性回答。先生认为胜即榺,原指织机部件中的经轴,后来人们将其刻画在纺织轮上,成为纺织的象征,并可能从此前后演化成妇女的首饰,寓意男耕女织的分工。[24]近年来,一些年轻学者对“华胜”一物重新做了考证。如李松以汉画砖上西王母手中所持对置双三角形器物为研究对象,指出此物是“卷绕丝或线的器具,即绕线架或绕线板”与纺织有关。刘海宇认为“戴胜”与发饰(头戴玉质华胜)无关,西王母“戴胜”应读为“持纴”,“戴胜杖”即持纴杖。笔者通过对中原汉画砖和河西魏晋壁画中西王母形象的反复比较研究,赞同学者们的主流观点,认为《山海经》所述西王母“戴胜”应与发饰有关。从图像看,汉画像砖及魏晋壁画墓中西王母戴的“工”字形或“对置双三角形”玉胜,笔者认为是缩小版的“纴器”,与模仿纺织工具的部件有关。而她手中所持或面前所搁置的“工”字形器具(或称“持纴”或“持胜”),为纺织工具的部件。从《山海经》中西王母“戴胜”到魏晋壁画墓中“持纴”形象的转变,实则与王母被奉为蚕神,倡导妇女养蚕缫丝的妇功有关。
2.与佛教传入有关
河西地区是佛教传入中原的首站,从石窟塑像及壁画中的各色人物形象看,都有异质文化的渗入。例如,从西王母的神仙造型看,既有本土特色,又有中、西亚等地的文化风格,同时她还是一个兼备释道精神的神仙领袖。正如詹姆斯所言“佛教传入中国后,紧接着汉代于公元220年衰落,她离开了她昆仑的家,昆仑的仙境归于佛和他的极乐世界。”[25]莫高窟壁画中,西王母和东王公形象及所绘位置往往和帝释梵天很接近,这说明西王母的地位次于佛、弟子。唐五代时,西王母被河西民众奉为蚕神,与“佛教在中土逐渐普及之后,西王母神话的影响最终削弱了”[26]有关,也与河西多神祗信仰有关。
(二)麻姑
考稽典籍,有关麻姑的神话源出于《神仙传》卷三《王远传》:讲述了麻姑执米成珠、三见沧海变桑田的故事。“(王远)因遣人召麻姑相问,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麻姑自说:‘接待以来,己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为陵乎?’”[27]道教神仙谱系中,麻姑的地位仅次于西王母,而麻姑和王母搭上关系的文献《神仙传》却迟至东晋。该书中的“麻姑献寿”,记载了建昌人麻姑修道于牟州东南余姑山的故事。相传,三月三日是西王母的寿辰。蟠桃会上,麻姑献给西王母的寿酒是她在绛珠河畔用灵芝酿造的,因酒浓香四溢,各路神仙都夸王母有口福,娘娘也因此封麻姑为“女寿仙”。其后的史料也偶见“麻姑献酒”,但其内容不再与西王母延寿相干。如《太平广记》卷289 记载,李相泌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28]
麻姑一向被塑造成消灾避祸、保境安民、庇护百姓、永葆长寿的神仙。其形象正如《敦煌愿文集》中五则麻姑延龄的史料所言:S.1441《二月八日文等范本》:“伏持胜善,次用庄严我河西节度使尚书贵位;伏愿五岳比寿,以(舆)日月而齐名;禄极(仓)沧瀛,延麻姑之万岁。”此愿文是二月八日纪念释迦牟尼诞辰而举行的隆重法会上宣读的,歌颂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功德文。[29]S.4536《愿文》:“司空鸿寿,同五岳而治河煌,内外宗亲,比麻姑而受荫。”P.2726《比丘法坚发愿文》:“伏愿麻仙比寿,王母齐坚;万善来集,千殃弥远。”P.3093《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若说天男天女,寿量大难算数,全胜往日麻仙,也越当时彭祖。”P.2058《发愿文》:“国王保受(寿),以(舆)欢祝(彭祖)而周(同)年,举郡黎明,比麻姑而延荫”。S.5757《结坛发愿文》“伏愿南山等寿,同王母之延龄;位极五候,比麻姑之万岁[30]。”以上材料中的神祇除麻姑外、还提及西王母及彭祖,在敦煌愿文中他们都以寿星著称[31]。麻姑本是我国民间普遍供奉的神抵,但在河西民众看来,无疑是本土方仙信仰的性质。余欣将“某一神祗的职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逐渐分化和转移。这种神祗职能的扩散性转换”称之为“神祗的碎化”。[32]对河西民众而言,为了满足自身一己的利益,往往给神祗赋予新的职能,如《蚕延愿文》中王母被奉为先蚕的形象一样,麻姑也肩负着赐蚕、补茧之职。由此足见民间对神祗的崇信,实质是植根于神明满足实际需求的灵验性来决定的。
(三)其他女性蚕神
《蚕延愿文》的女性形象还有本土化的其他五位女性神祗。
务女,即女宿。亦作婺女、须女,与织女同义,为二十八星宿之一。《史记·天官书》:婺女,“其北织女”[33]厉玄《寄婺州温郎中》诗唱吟:“婺女家空在,星郎手未携。”
蛟人,亦写鲛人、泉先、泉客,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鱼尾人身的生物。《山海经》就有人鱼图像和文献记载。张华《博物志》受到《山海经》影响,创造了一个鲛人擅织的新视角,卷二载:“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34]。鲛人以织绩、泣珠、报恩形象跃然纸上是在晋唐之间。宋代之后,鲛人又以东方美人鱼的姿态走向世俗生活,如《洽闻记》《徂异记》《类》所载妇人鱼、妇鱼、海人鱼等。
后土就是皇地祇(大地女神),又称地母元君、尊称后土娘娘。“后土”之称始于春秋,汉代被列入皇朝祀典,并为历代沿用。隋以前,“王朝祀后土,多以皇后配祀;隋以后,国家祭祀后土,则以皇帝配祀”[35]。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年间三次到汾阴后土祠扩建祠庙,至此,后土崇拜达到鼎盛。宋徽宗封后土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被道教列为“四御”尊神之一。自元以降,随着道教走向民间,皇帝再无亲祀后土之举,明代以后纯为民祭,至清代则为乡社所祭,后土娘娘成为社日善男善女求子祈福的神仙。
生殖女神玄女,自“仙化”成为战神(黄帝之师),曾在阪泉之战中奉王母之命协助黄帝大败蚩尤,后被提升为尊贵的九天玄女。汉晋时期上升为身兼数职的女神——房中术神、战神、丹药神、术数神。隋唐已降,玄女依旧是传授兵法、通晓军事的女战神。明清之际,玄女已演化成贴近民众的送子娘娘。
电母是司掌闪电的神祗,又称“金光圣母”或“朱佩娘”。雷电崇拜,始于上古。电母女性形象明确记载于正史的时间较晚,《元史·舆服志》载,电母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为女人形,纁衣,朱裳,白袴,两手运光。”[36]
以上通过对《蚕延愿文》中蚕神的考述,我们得知西王母、麻姑、蛟人、务女、后土夫人、九天玄女、电母不仅是河西神话体系中的重要人物,还是宗教系统中掌教化、掌生育的神祇。首先,上述七位神祗是一个掌握专业技术的宗教团队。如在蚕事活动中,后土夫人、九天玄女和电母对食饲、修供、点烛等养蚕环节做工作,最后的缫丝织布由技艺精湛的鲛人和务女协助完成,西王母则在整个活动中发挥着总体布局和统筹协调的作用。另外,从蚕神团队精细化分工和科学操作所透漏信息的看,唐五代的河西蚕农已掌握了较高水准的育蚕、纺织技术,桑蚕缫丝业也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次与生育有关。五代之际河西政权更替频繁,战乱多,人口损失严重。河西百姓将七位蚕神设定成女性,并为掌生育的玄女等先蚕设坛祭祀,不仅表达来年风调雨顺、桑壮蚕肥的美好希冀,更与他们对女性生殖力渴望,人口繁衍的夙愿有关。
综上所述,古代河西走廊是我国著名的农业区域,当权者明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之道,由此确立“农桑并举,耕织并重”的国策,继而鼓励百姓“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以达“事务有序,惠被诸产”的统治目的。女子养蚕缫丝,不光关乎着一家一户的基本生活,还在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西王母和诸神祗被奉为先蚕,与统治者“王政之本在乎农桑”的政策不谋而合,故在古代河西走廊一直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极力推崇。再者,蚕神崇拜是一直是我国神话和宗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信仰的推助下,河西官员和民众重视农桑生产,以致在少数民族和汉族政权的交替统治下,始终没有放弃以农为本的生产传统,这也为河西走廊丝路文化的源远流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注释:
①陈炳应:《甘肃、新疆的蚕桑丝织探源》,《陇右文博》,1996年第l期。
②李并成:《古代河西走廊桑蚕丝织业考》,《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③闫廷亮:《古代河西桑蚕丝织业述略》,《古今农业》,2011年第4期。
④赵玉平:《唐五代敦煌蚕神考——以敦煌文献S.5639《蚕延愿文》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3期。
⑤[唐]房玄龄:《晋书》卷86《张天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52页。
⑥[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唐纪”玄宗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19页。
⑦雷闻:《书评:(唐宋民间信仰)》,《唐研究》第9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⑧持此观点的学者刘宗迪、赵宗福二人,论证了西王母神话源于中国本土,是由始祖母信仰转化而来。赵宗福:《西王母的始祖母神格考论》,《青海社会科学》,2012 年第6 期。刘宗迪:《西王母神话的本土渊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⑨杨文文:《西王母神话与上古丰收庆典》,《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
⑩《太平广记》卷203《风俗通》,第5 册“舜白玉琯”,北京:中华书局,第1530页。
[11] 袁珂:《山海经校注》卷2“山经柬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0页。
[12] 李民等:《古本竹书纪年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13] 王贻樑、陈建敏校释:《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1页。
[14]《穆天子传汇校集释》,第161页。
[15]《山海经校注》卷2,第54页。
[16] 高国藩:《敦煌本西王母神话及其旅游价值》,《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7] 刘海宇:《汉代画像砖中的西王母持纴器图考》,《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18][汉]刘熙撰:《释名》卷4,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9页。
[19]《汉书》卷57《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98页。
[20]《后汉书》卷30《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3676页。
[21] 高春明:《中国服饰名物考》,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
[22] 郭宝钧:《古玉新诠》,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9年。
[23][日]小南一郎著、孙昌武译:《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24]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25][美]简·詹姆斯、贺西林译、张敢校:《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下)》,《美术研究》,1997年第3期。
[26] 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
[27][宋]张君房著:《云笈七签》第四部,卷109《神仙传》蔡经条,中国古典精华文库,第1466页。
[28]《太平广记》卷289,“妖妄”李泌条,第2297页。
[29] 目前发现曹议金出任节使的发愿文有三篇,经马德研究,认为该文书是曹议金完成98窟顶壁画绘制后的一次庆祝法会上功德祈愿文残文。该功德文在《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8册第38页有图版,定名为“河西节度使尚书曹议金修大窟功德记”(P.3781)。
[30]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337页、第586页。
[31] 彭祖与麻姑同寿,P.3457《司空建大窟功德赞文》:“次为司空已寿,以彭祖而齐年”。见马德:《曹氏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一文。Φ323V、Φ326V《河西节度使大王曹议金造大寺功德记》:“次伏惟我大王已躬延寿,以彭祖而齐年。”见《俄藏敦煌文献》第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3页。
[32] 余欣:《神祗的“碎化”:唐宋敦煌社祭变迁研究》,《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33]《史记》卷27《天宫书》,第1311页。
[34][晋]张华撰,范宁校著:《博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页。
[35] 尹虎彬:《浅谈后土与后土崇拜传统》,《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36]《元史》卷79《舆服志》,第19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