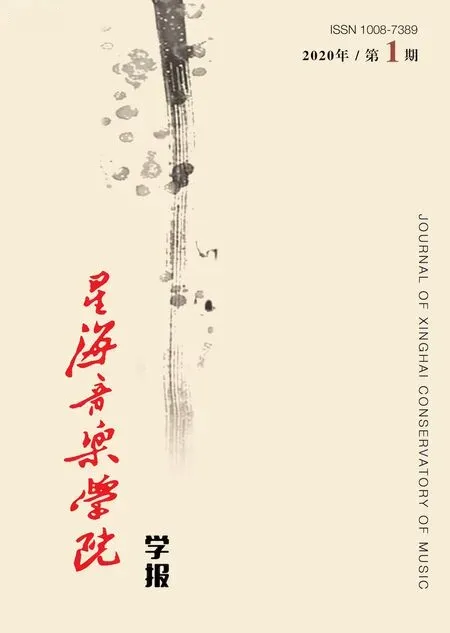少年冼星海的音乐之路
——冼星海马来亚生活初探
魏 艳,常 钰
长期以来,冼星海在马来亚(1)马来亚,全称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是指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86年租借槟榔屿经营,1819年取得新加坡管辖权,1824年取得马六甲管辖权,1826年英国将三地并称“海峡殖民地”。它与英国后来取得管辖权的“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合称为“英属马来亚”。的生活经历,以及回国时间等,已有的文献和记录均较模糊,甚至不乏纰缪,连冼星海本人的自述(2)“传记”泛指冼星海撰写的《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1939)和《我的履历(简单历史)》(时间不详)。对此也含混不清,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几为空白。在对冼星海音乐经历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早在1992年,台湾音乐学者颜廷阶编撰的《中国现代音乐家传略》(3)颜廷阶:《中国现代音乐家传略》,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92年。中概要记录了冼星海在马来亚的求学经历与回国成因,但这份资料似乎并没有引起大陆学者重视。2007年,新加坡养正学校校友团访问广东番禺冼星海纪念馆,发现该馆缺少冼星海在新加坡及养正学校的学习生活展件,在深感遗憾的同时,决心要把冼星海在马来亚经历挖掘出来。经过多方努力,2015年,养正学校校友何乃强(4)何乃强(1937- ),笔名幼吾,1937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顺德。曾就读于养正学校、中正中学和圣·安德烈学校,1966年毕业于新加坡大学医学院。1971年获医学硕士,1975赴澳洲深造学习,同年获新加坡医学院院士,1978年获澳洲大洋洲皇家内科学院院士。1985—1987年任新加坡小儿科学会会长,1998—2001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副院长,2003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圣约翰爵士勋章,著有《儿科病房》(1987)、《父亲平藩的一生》(2004年获新加坡文学奖)、《医生读史笔记》等。先生所著《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5)何乃强:《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新加坡:玲子传媒,2015年。(下称“何著”)在新加坡出版,冼星海在马来亚鲜为人知的经历终于浮出水面。在此基础上,笔者得以梳理冼星海在马来亚这段经历,并尝试探讨这段生活对他此后音乐道路的影响。
一、南下马来亚—新加坡
1928年开始,西方列强大肆介入东南亚各国,掠夺橡胶、矿产等资源,“白人既惮气氛之炎蒸,复惧投资之亏损”(6)刘继宣、束世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30页。,西方殖民者遂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南下的华人开发殖民地。英国统治在马来亚各地的开发政策宽松,华人因此纷至沓来。新加坡是英殖民者在马来半岛较早统治的一块殖民地,以此为“大本营”逐渐扩展到马来亚其他地区。南下华人大多选择到新加坡投资经商、采矿筑建。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需要不断补充工人和劳动力,也由此推动了国人南下马来亚的务工潮。
幼年冼星海和母亲黄苏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入下南洋的大潮。
家庭生活的变故是黄氏和冼星海南下马来亚的主要原因。带上年幼的儿子南下闯荡,黄宗英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冼星海是遗腹子,父亲冼喜泰是位海员,在父亲去世后,母亲便带出生不久的冼星海投奔了外祖父。冼星海七岁时,外祖父离世,没有了经济支柱,冼星海母子变得无依无靠,如何谋生成为她们生活下去的重要考量。
严峻的社会生活环境是冼星海母亲选择南下的客观原因。20世纪初,在西方列强不断的侵略下,清政府将巨额债务压力转嫁老百姓,苛捐杂税与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使得百姓苦不堪言,谋生就业的机会日趋稀少。可想而知冼星海母子的艰难生活。与此同时,马来亚被英国殖民者圈定为殖民地后,当地的矿产资源、自然资源亟待开发,但是,当地原住民劳动力有限,这就给南下的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特别是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居民,他们离马来亚比较近,环境、气候等因素也适宜。外加此前已有大量华人定居于此,所以马来亚的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也相对容易接受和适应。对无依无靠的星海母子来说,下南洋大概也算当时最好的选择。
这时期有一些名为“水客”的操船者,长期航船往返于珠三角与马来亚—新加坡之间。除送货外,他们还可以托带款项,买卖商品,为人介绍工作等。冼星海母子大概也是通过这些水客的介绍,搭乘他们的货船,南下马来亚谋生。打工者在船上没有自己的固定铺位,他们是在地上铺上一张席子,临时屈身于船舱底层,甚至还需要在船上工作以换取伙食补给。新加坡记者王振春曾描述,冼星海母子在船上为了生计干一些零活儿(洗甲板、打扫卫生等)(7)何乃强:《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新加坡:玲子传媒,2015年,第35—36页。。
在登陆新加坡本岛之前,大多数南下的华人都要在一个离岛进行疾病的隔离检疫,冼星海母子也不例外。这些华人被安置隔离的离岛“棋樟山”,即今天的圣约翰岛,距离本岛约6.5公里,这里建有一座传染病隔离站,即便是没有疾病也被要求在此隔离,少则一个星期,多则半个多月。20世纪初,各国医疗水平十分有限,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在热带地区时有“爆发”。南下马来亚—新加坡的国人多是国内生活底层的“难民”,他们的卫生健康着实不好。因此,殖民政府要求他们在登陆本岛前,必须在棋樟山接受隔离观察。期间,这些打工者被强行要求用一种乳白色、气味刺鼻的消毒水洗澡,用以杀菌。一日三餐由自己来做,官方提供米、糖、牛奶、鱼罐头等食材。隔离者直到被确认为“安全”后,才可登岛。
这段经历常被我国闽南人称为“禁龟屿”,也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南下马来亚—新加坡华人的悲凉记忆,而冼星海在他自传中没有提及南下这一经历。
二、中学—西学辗转求学
冼星海母子抵达马来亚—新加坡本岛之初的具体生活状况尚无从考证。参考同时代旅居新加坡的广东籍华人生活境况,大概能勾勒出冼星海母子初到马来的生活。
南下到马来亚—新加坡的华人有群居的生活习惯。来自不同省、地区的人们常常聚居在不同区域、街道内。如福建人常聚居在新加坡的厦门街、北京街、中国街;而广东番禺、南海、顺德等地区的人们则常聚居在牛车水区。(8)何乃强:《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新加坡:玲子传媒,2015年,第41页。(9)19世纪的新加坡没有通自来水时,这里的居民常赶着牛车到别处取水用来生活,“牛车水”地区因而得名。随着广东华人不断南下,这里渐渐成了来自番禺、顺德等粤籍华人的聚集区,并较多岭南建筑、广式美食,讲广府方言。冼星海虽出生在澳门,但祖籍是广东番禺人,母子俩讲的是广府话,故此生活在环境相对熟悉的牛车水区有很大可能。
华人们在牛车水的街道旁开设店铺,经营买卖。但环境不佳,道路两旁凌乱。冼星海母子大概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为他人做帮佣谋求生活。细节无从查询,至于影片《少年冼星海》所呈现冼星海母亲在“牛车水小学”校董曾先生家做帮佣,寄居在曾家,并非真实可信。因“牛车水小学”是子虚乌有的虚构(10)何乃强:《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新加坡:玲子传媒,2015年,第121—122页。。现在的“牛车水”已是新加坡重点打造的旅游区,被称作新加坡的“Chinatown”(唐人街),很得大陆游客青睐。一百多年前,这里同样凝结着华人族群的“气息”,冼星海正是从这里初涉乐坛。
生活稳定后,定居马来亚的华侨们开始考虑子女教育问题。最初是请一些内地的读书人到家里教课,而后,渐有类似私塾的教馆出现,华工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里学习。六岁的冼星海来到马来亚—新加坡,正值适龄入学年纪。牛车水区当时有许多私塾,遍布各个街道。根据冼星海自传可知,“最初是读旧式的学校,读了不少四书五经”(11)冼星海:《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载冼星海全集编委会:《冼星海全集(第1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80页。,“旧式的学校”很有可能就是这种“私塾”。
20世纪初,许多读书人选择南下谋生。这些“吃墨水”的旧学者可谓“生不逢时”,本想靠着读书科举来谋个一官半职。无奈清政府垮台,新学兴起。许多留日学者回国教书,带来新学,也有坚守传统的学者,他们到华人聚集的南洋谋生,坚持私塾“旧学”。这些私塾的环境很差,有的竟设立在商铺楼上。一张大长桌,许多适龄男孩子还留着清朝的旧辫子围坐在一起,跟着先生读些旧式的启蒙教材。同时练习描红,写毛笔字。因为大多数私塾只有一间简陋的屋子,不能提供学生活动的操场、音乐教室。教书先生们大多也是采用旧式私塾教育,坐姿不端、背书不畅就用戒尺敲打学生手板或其他体罚。冼星海初到马来亚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接受旧式教育并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这从他后来喜爱书法及诗词可见一斑。
英殖民者控制着马来亚各区的政治、经济,1862年,英国国教圣公会创办了圣·安德烈学校,招收华裔、马来裔、印度裔等各族儿童,施行全英文授课的宗教教育(讲读圣经等内容)。冼星海在自传中所述“十一岁时入英国办的英文学校”(12)冼星海:《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载冼星海全集编委会:《冼星海全集(第1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80页。即圣·安德烈学校。冼星海入学时间大概是1915年或1916年,因还不能确定他所说为实抑或虚岁。
尚不确定冼星海母亲是如何得知圣·安德烈学校并让冼星海去接受西学教育,但可以想见,她对儿子有较高期许,让冼星海在更好的环境读书求学,将来能够有资历求职。当时新加坡的殖民者承认英国教育,冼星海若能从圣·安德烈学校毕业,就能拿到由英国剑桥颁发的中学教育文凭,便可以在新加坡政府谋得一个文员、书记员的职位。冼星海曾使用过Sinn Sing Hol这一英文名字,来源于其中文名字的粤语发音,也有接受英文教育的影响。
可惜冼星海只读了一年便退学了,具体原因现已无从知晓。冼星海在圣·安德烈学校的校友吴汉辉曾在文章中这样写到:
他那日字型的面孔,黝黑而添层茶色,更显出营养不良的征示,何况惯听到他曾晕倒街上,益使我们替他担心。(13)广州市番禺区广播电视台:《星洲苦旅——冼星海在新加坡的艰难岁月(纪录片)》,2016年。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冼星海当时窘迫的生活状况,可能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可以想见,冼星海母亲做帮佣所得可能也仅够糊口,无力支付“英校”的学费与伙食费。这也许是冼星海只读了一年便匆忙退学的原因之一。此外,“英校”的全英文教育对于冼星海能否适应也是一大问题,他在“英校”与其他族裔的同学如何交流,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让少年冼星海难以适应而退学。
冼星海大约是在1917年离开圣·安德烈学校,此后两年,母子俩的去向暂无确切记录。何乃强推测,这两年他们大概是去了马来亚的其他地区。基于养正学校校友郭鸿锦的文章中“冼氏即随其母由马来亚内地来校申请入学”(14)何乃强:《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新加坡:玲子传媒,2015年,第48页。判断(文中的“校”即指“养正学校”),冼星海是在1919年就读养正学校的。故此,从离开“英校”到1919年入养正学校,两年时间里冼星海母子大概是在郭文中提及的“马来亚内地”生活。另外,何著中也曾提到,当时新加坡的经济情况不好,冼星海母亲有可能在新加坡找不到太理想的工作,而马来亚内地的橡胶业、矿产业发达,就业机会要比新加坡多,冼星海母亲或许选择前往马来亚内地谋生。
从地理和政治上分析,也存在着这种“出走”的可能,新加坡与马来亚内地仅隔一道柔佛海峡,出行相对容易。另外,当时的马来亚与新加坡均属英国殖民管辖,所谓“新马一家”,即英国称之为“海峡殖民地”,两地流动大概也不需要什么繁杂的手续,至于冼星海在自传中并未提及马来亚,只是说“南洋”“新加坡”等,过于简略,造成冼星海母子这两年的经历“空白”,大概去向只是推测,具体还有待更为确凿的史料考证。
三、养正学校初涉乐坛
20世纪初,受戊戌变法影响,旅居南洋的侨胞渐渐开始倡导新式学堂教育。同时,南洋一些地区,如爪哇岛等荷兰殖民属地,统治者惯用“愚民”统治手段,不允许华人子弟入官方创办的教育机构,是促使华人自主办校的主要因素。即使是殖民者允许华人子弟就读官办学校,如圣·安德烈学校,这些华人子弟在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接受纯粹的西方教育也会有许多不适应,这也算是华人办校的另一个动因。简而言之,南洋华人希望下一代既能够融入充满西方文化“色彩”的新环境,又不失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本性”。因此,他们创立了兼顾中西的新式华文学校,既有中华传统的华文课程,又有西方现代学科概念的学习内容。
新加坡养正学校就是华人在这种新教育理念中酝酿而出的,其中一个较为朴实的初级目标,即不使南来的移民子弟“目不识丁”。1905年,由27位在新加坡颇有威望的华侨共同出资,创立了“广肇小学”(15)取“广肇”一名因为这些华侨祖籍源于广州、肇庆,故此得名。。数月之后,惠州籍华侨也加入办学之中,取名“广肇惠养正学堂”。“养正”二字取《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一句,意指蒙童时期就要施以纯正无邪的品质教育,这是造就圣人的成功之路。
养正学校建校之初,设在柏律路,首任校长陆敦揆。在第二任校长宋木林的带领下,除常规的全日制教学外,增设了“半日制”(华人子弟可以上午在“英校”学英文,下午到养正学校学中文。同时也可上、下午学习内容颠倒)、“夜校”、“女生部”等班级。这里以中文授课为主,同时也有英文、德育等课。1917年,广东岭南大学的钟荣光南下新加坡筹集资金,新加坡华侨们请他为养正学校推荐一位校长,于是,林耀翔(16)林耀翔,1888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番禺,信仰基督教。幼年在番禺读私塾,14岁入香港皇仁书院学习,1905年入广东岭南学堂就读。1910—1913年任岭南学堂附属小学校长。191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18年出任新加坡养正学校校长,1921回国任岭南大学附属华侨中学校长,岭南大学附中副校长等职。1930—1933年主管新加坡岭南分校。1933—1935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1937—1959年,再度出任新加坡养正学校校长。1983年辞世。这位曾担任岭南大学(17)岭南大学,前身为1888年美国长老会哈巴·安德牧师在广州沙基创立的格致书院,英文名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基督教学院)。1900年迁至澳门,中文更名为岭南学堂。1903年英文更名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广州基督教学院),中文名沿用岭南学堂,1904年迁回广州。1906年开始招收大学层次的学生。中华民国成立后应政府要求更名为岭南学校。1917年第一批大学生(共三名)毕业,同年大学部独立,定名为岭南大学,设有文理科。1927年岭南大学正式由国人接管,钟荣光担任校长,更名为私立岭南大学,增设农、商、医学等科系(学院)。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原岭南大学被拆分或于其他学校合并成中山大学、中山医院院、华南理工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附小校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学士,被推举执掌养正学校(1918)。
根据养正学校校长林耀翔回忆,“余初度南来掌养正之翌年,冼君得友人介绍来校作工读生”(18)何乃强:《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新加坡:玲子传媒,2015年,第66页。。林耀翔来到“养正”的第二年,冼星海随母亲来校报名申请入学。林校长“缘家境困难,慈母受用别埠乏人照料,故准其(冼星海)在校食宿,课余使助区先生(区健夫)整理乐器,遂随班习铜乐……”(19)何乃强:《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新加坡:玲子传媒,2015年,第66页。冼星海入养正学校学习时,学校已经从柏律路搬迁至乞纳街的翠兰岗。
林校长使生活窘迫的冼星海得以继续读书,为了减轻冼星海母亲在外帮佣的操劳,还准许冼星海住校,并让他在课余时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即整理学校军乐队的乐器,冼星海此前几乎没有这样接触这些西式乐器,他很快对此产生了兴趣。整理乐器不仅解决了冼星海在校的日常费用问题,重要的是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
冼星海在音乐上的才华很快就被一位“伯乐”——养正学校的音乐老师区健夫慧眼所识。
区健夫,广东顺德人,曾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有良好的英文基础。后来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学习。20世纪初,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多所“陆军小学堂”,广东省的“陆军小学堂”建立在黄埔平岗乡,故这所学校又有“老黄埔”之称。这里培养出了李济深、邓演达、叶挺等革命将领,还培养了诗人、音乐家、德语翻译廖尚果(青主)。区健夫是“老黄埔”的哪一期学员不确定,大致可以推定他在这里曾学习过音乐。廖乃雄在《忆青主——诗人作曲家的一生》中提及,青主在读“老黄埔”时就摆弄过乐器,这里还有一些供学生演唱的简谱歌本。
区健夫从“老黄埔”毕业后曾在广东参加过李福林的部队,1917年南下新加坡,到养正学校任教,教授体操和唱歌。到任不久后便组织了“养正学校军乐队”,1919年冼星海来校工读,课余时间就是帮助他整理乐器。
区健夫“性好音乐,嗜之如命”(林耀翔语),走路常是口哼小曲,手提钥匙摇打节拍。特别迷恋粤剧,自己编写剧本,改良粤剧。冼星海帮助军乐队整理乐器,区老师很快就发现他是一位颇具音乐天资的少年。他教授冼星海如何吹奏乐器,根据冼星海的嘴型、气息流量特点,先是让他吹奏短笛,后来又改教他吹奏单簧管。
区老师平时喜欢单独上课,而冼星海又是工读生,课余时间要到区老师那里帮他整理乐器,因此师生二人接触的时间要比其他人更多。区老师的军人气质在教学中表露无疑,十分严厉。学生吹奏的节奏稍有偏差,他就会大声呵斥“唔嘚!唔嘚!”(普通话:不对!不对!),一边呵斥一边在学生的大腿上打拍子,要么就用钥匙敲击桌子,久而久之桌子都被他敲出了一个坑。天资加勤奋,冼星海在区老师的严厉教导下进步很快,他被“任命”为配带金线三粒星肩章的养正学校军乐队队长,当区老师外出或忙于其他工作时,冼星海甚至可以代他行使老师的“职权”。冼星海的音乐才华让林校长感到惊奇,他感慨“(冼星海)以性近音乐勤敏过人,天才渐露,随学未几进步神速,造诣超侪辈……”(20)何乃强:《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新加坡:玲子传媒,2015年,第90页。。
冼星海与军乐队的同伴们在养正学校的八角亭内学习和排练。“八角亭”是养正学校的最高建筑,有五六十平方米大,是区老师的办公室兼住处,同时也是军乐队的排练场。这里存放着贵重的乐器,平时大门紧闭,学生不得入内。只有冼星海例外,因为整理乐器,可以随意出入,也有了很多机会跟随区老师学习音乐。
区老师喜欢带领军乐队排练一些激昂的进行曲,《双鹰旗下进行曲》《华盛顿邮报进行曲》是他们的常备曲目。区老师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痛恨军阀的胡作非为。当听说广西军阀莫荣新、陆荣庭等人帅军强占广东时,区老师愤慨的利用粤曲小调创编了一首《打黄衣大汉歌》,教养正学校学生们演唱,情绪激昂。这些催人奋进的进行曲和激昂的旋律,无疑会在少年冼星海的心里埋下进行曲音乐的“种子”,它们与冼星海后来创作的大量救亡歌曲有着相似的进行曲音乐风格。
冼星海母子在新加坡无亲无故,母亲为了生活到“外埠”打工,而冼星海则寄宿在养正学校,更多的时间“蜗居”在八角亭内“摆弄”乐器,除了学习、参加军乐队排练,没有太多课余活动。有时会在星期日休息时,和同学参加“美以美青年进德会”的活动,阅读圣经、唱诗、祈祷、布道等,这可能就是孤单的冼星海为数不多的业余生活吧。
1921年1月,军乐队成员在养正学校第二操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成为养正学校校友们的永久记忆。五个月后,林校长被广州岭南大学任命为“岭南大学附属华侨中学”校长,在动身回国之际,林耀翔决定带回一批约20人左右的优秀华侨学子回国在该校学习,冼星海很自然地作为这些优秀学生中的一员回到祖国大陆。
到岭南大学附中之后,由于家庭贫困,冼星海一直也是半工半读,他指挥学校军乐队,在社会活动中表演单簧管独奏,一直延续着自己的音乐爱好并逐步将其设定为人生理想。

图1 “养正军乐队”合影,前排左四为冼星海,后排着西装者为区健夫。(21)图片源于《养正学生月刊》的发行人兼财政梁迅民先生的收藏。
四、马来亚之旅对冼星海音乐生活的影响
马来亚—新加坡及养正学校的音乐生活经历,既培养了冼星海的音乐学习基础,也历练了他的品格。冼星海青少年的学习历程,几乎都靠“半工半读”维持,困苦的生活和窘迫的环境,锻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毅力,这种坚韧的品质一直是他此后战胜各种困难的力量。南洋经历对冼星海来说是宝贵而独特的,它们磨砺了冼星海的性格、意志,也成为他日后选择职业音乐家的重要“起点”。
在养正学校军乐队的音乐经历,开启了冼星海的音乐生涯,也影响了他后来的音乐学习之路。回到“岭大”附中后,冼星海参加过附小童子军联谊会,当他在台上吹奏单簧时,台下的师生们深感“惊艳”。冼星海由此获得了“南国箫手”(22)广东当地人常把单簧管(clarinet)称为“洋箫”。的美名。冼星海对单簧管这件乐器最为熟悉,甚至情有独钟,后来他在巴黎的成名作,室内乐三重奏《风》就是为女高音、单簧管和钢琴而作。冼星海能在他最初的音乐创作中,选择包含单簧管在内的小型器乐重奏形式,与他在新加坡时期的乐器演奏学习和实践密不可分。
养正学校军乐队不仅锻炼了冼星海的器乐演奏技能,同时也培养了冼星海的指挥领导才能。身为军乐队队长的冼星海,在组织和排练乐队方面积淀了经验。冼星海的音乐指挥才能在此后一直发挥着作用。
1921年冼星海离开新加坡养正学校,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附属华侨中学及岭南大学附中继续半工半读或兼职挣取生活费和学费。指挥才能成为他工作的主项,除了指挥本校的管乐队,冼星海兼任岭大附设华侨学校音乐助教员、青年会全会事业部音乐主任、青年会ANY弦乐队主任等。在广州培正中学担任音乐教师时,冼星海受聘指挥“培正银乐队”。这个乐队是美国人组建和资助的,为当时比较难得的一支乐器配置健全、有较高演奏水准的军乐队,冼星海的军乐指挥水平,在当时的岭南地区也是首屈一指的。
也许就是从指挥养正学校军乐队到岭南大学军乐队等不断实践,冼星海也特别钟爱指挥艺术。当他去巴黎留学后,在极为艰苦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下,还能在主修作曲同时,选修音乐指挥,这与其青少年时期的音乐实践有一定关联。
1935年,冼星海从巴黎回到上海,一度的心愿是想指挥素有“远东第一乐队”之称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交响乐团。冼星海曾约请上海的中国演奏家筹组临时管弦乐队,亲自指挥这个乐队举办了多次交响乐音乐会。抗战时代,冼星海将“音乐家”和指挥交响乐队的理想转化为救亡歌咏运动实践,通过指挥教唱救亡歌曲,以及培养歌咏指挥音乐人才,冼星海的指挥才能得到了更普遍和有效的发挥。
1939年到延安“鲁艺”之后,冼星海得到了深入开展专业指挥教学机会。通过指挥大型合唱作品,他将自己的指挥才能较为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培养和影响了一批学生。冼星海能够充分调动乐队和合唱队员的情绪,也特别善于处理庞大的合唱作品,黄准等音乐家曾撰文追忆冼星海的指挥教学。1939年5月11日,冼星海在“鲁艺”音乐系的周年纪念音乐会上,亲自指挥演出《黄河大合唱》,成功的演出奠定了其“人民音乐家”的重要地位。
冼星海的音乐生涯从少年远赴南洋新加坡参加养正学校军乐队开始,经历了岭南大学的历练与成长,他对音乐指挥有着特殊的偏爱,也从中逐渐奠定了成为音乐家的理想。他在国内辗转北京、上海等地求学,继而克服重重困难到巴黎接受专业作曲和指挥学习,回国后尝试组织和指挥中国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在风起云涌的抗战时代大潮推动下,他选择冷却自己想要成为“大音乐家”的梦想,将歌曲创作与音乐指挥的热情投入到群众歌咏活动。经历了上海和武汉时期从事救亡歌咏活动和音乐创作的初步积累,当冼星海来到延安“鲁艺”,厚积薄发,他的音乐创作与指挥才能终于得到较为充分的施展。可以说,冼星海青少年时期在马来亚—新加坡的音乐生活和经历,对他回国后音乐人生的选择及其此后的音乐道路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结 语
七岁时我便漂泊到南洋,最初是读旧式学校……十一岁时入英国办的英文学校,后又进入中国的高等小学。(23)冼星海:《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载冼星海全集编委会:《冼星海全集》(第1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80页。
我曾入过英文学校一年,高等小学两年。(24)冼星海:《我的履历(简单历史)》,冼星海全集编委会:《冼星海全集》(第1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85页。
这是冼星海对自己少年时南下马来亚—新加坡经历的自述,但对圣·安德烈学校、养正学校、林耀翔校长、区健夫老师等均未提起。为什么冼星海对自己的教育启蒙和音乐生涯初始概括得如此简略?他把这些疑问留给了后人。
冼星海有两份自述,均为1939年在延安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附件。撰写自传时,他对自己少年马来亚—新加坡的经历写得亦十分简略,毕竟当时年少,这段经历也没有太多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略写”也无可非议。然而,冼星海也未在其他文论中公开阐述过相关内容,笔者推测,冼星海或许是不愿意坦露与宗教相关的生活经历,担心由此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质疑。冼星海就读的圣·安德烈学校,属于英国国教圣公会创办,本就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养正学校的林耀翔校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冼星海在养正学校期间,也曾和同学们参加过“美以美青年进德会”组织的宗教活动。对于这段经历,冼星海用“英国人办的英文学校”“中国人办的高小”之类的语句一代而过,极可能是想淡化宗教对自己的侵染。
在《悼亡师保罗·杜卡斯》一文中,冼星海对巴黎音乐院杜卡老师的深情溢于言表。对丹第、奥别多菲尔等老师的回忆,也表明他心怀感恩。然而对有着知遇之恩的校长林耀翔、音乐老师区健夫及养正学校和圣·安德烈学校,至今未见冼星海写过的相关文字!冼星海或许因为某种苦衷而“隐去”了马来亚—新加坡的部分生活经历,亦或无法“追忆”年少生活的诸多细节。林耀翔校长和校友们却对他印象深刻,当然,这与冼星海后来成为一代巨匠而使人对他赞誉时可能会略为夸大不无关联,但冼星海的音乐成就却当之无愧。
冼君冼星海幼年时在本校为苦学生,既无惊人之外表,亦无特殊之天资。然自入校后,见其年虽幼小,惟其刻苦耐劳之精神,奋斗向学之毅力,实有过人之处。且不以贫苦而自卑,大有舜人也我亦人也之气概,此则非一般儿童所能及,无怪其终能以刻苦奋斗而成为当代音乐之青年成功人物,得万人景仰也!(25)何乃强:《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新加坡:玲子传媒,2015年,第81—82页。
这是71岁的养正学校老校长林耀翔对英年早逝的学生冼星海的追忆。
马来亚—新加坡时期是冼星海苦难人生的起点,也是他音乐人生的重要开端。冼星海在这里历练了品格和意志,积淀了音乐学习基础,初步确立了音乐家之努力方向和目标。历史可以被一时“忽略”,但不会被忘记。探究少年冼星海的生活和音乐经历,对于推动冼星海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而冼星海留下的疑问也将推动冼星海研究在未来变得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