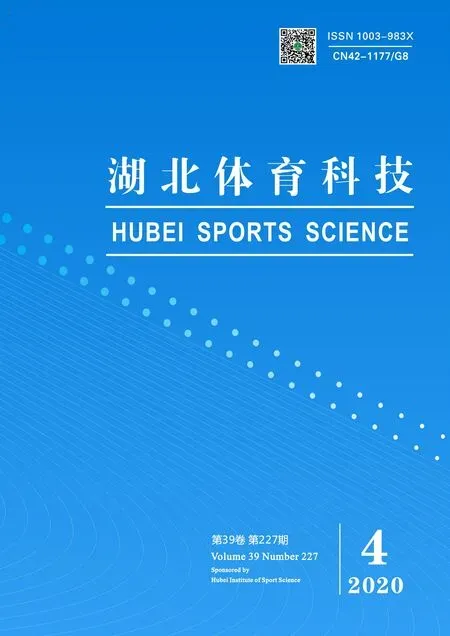中医常见外治法在急性运动损伤中的治疗优势
余 辉
(湖北省体育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湖北 武汉 430000)
中医药在急性损伤中的治疗原则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中[1],在后世不断发展中形成针灸、推拿、手法复位等急诊操作和理论。这些操作和理论逐渐完善,形成具有中医基础理论指导的中医急诊体系[2]。在众多医家典籍中,急诊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东晋时期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大量的急救医疗方案。《黄帝内经》在疾病描述和治疗上,以“卒、暴”等强调急诊的重要性。后世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医急诊在维护健康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运动观念的日益兴起,运动成为大众强生健体的重要方式。同时体育竞技也成为一种主流文化[3],被大众接受和支持。在挑战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时,损伤常常伴随着竞技运动员,因此如何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的治疗急性运动损伤成为运动医学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运动医学与常规的急诊有所不同,在很多情况下,保障急诊的同时,还需要维护和满足运动员继续竞技等特殊要求。
运动损伤(Sports Injuries)是指在运动中导致机体生理结构破坏或紊乱的机体损伤[4]。急性则是发生迅速,多发生在运动场上的运动损伤。运动损伤属于中医中的伤科学范畴,其治疗涉及中医多种治疗手段。伤科出自《周礼·天官》,“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即诊疗跌打损伤的专科。伤科萌芽于商周时期,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明清。在古代伤科多以兵家常用,为后世留下众多医术典籍[5]。例如汉代的《折伤薄》、唐代的《理伤续断方》、明朝《正体类要》、清代《伤科补要》等。运动损伤依据症状大多可以归纳为伤科疾患,故沿袭伤科典籍对运动损伤诊疗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医药治疗急性运动损伤上,在运动医学与中医学结合中逐步发展成熟,形成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多养护等全方位的运动急救体系[6]。其中针灸、按摩、拔罐、手法复位、中药熏蒸、中药制剂等在急性运动损伤中运用越来越多。针灸的镇痛、疏通经络等疗效在运动竞技中不仅仅治疗运动员的伤情,在竞技中也可为运动员提供继续比赛的可能,是针灸的重要优势。推拿是缓解痉挛、肌紧张、韧带拉伤等急性运动损伤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运用手法辅助治疗。拔罐是消肿止痛、舒筋活络的重要治疗方式,是大量运动或维持运动的的治疗方式。手法复对于轻度骨折,关节脱位、骨折、软组织损伤等损伤可立即恢复其功能,在急性骨、关节损伤中具有重要作用。中药熏蒸是利用中药药性局部作用起到治疗作用的方式,有利于迅速缓解损伤造成的伤害。中药制剂是当前临床运用较为广泛的中医药治疗运动损伤,膏剂、喷雾等在临床中运用广泛。除此之外,针刀、牵引等手段也是急性运动损伤的重要治疗方式。本文总结急性运动损伤中医常见外治法治疗及优势,为临床提供治疗提供指导。
1 针灸在急性运动损伤中的治疗优势
针灸是中医药中外治法中最为庞大的一部分,它以操作简便、刺法灵活等优点备受大众喜爱。在《黄帝内经》针灸占据九卷,有68篇之多[7],理论十分丰富,为后世伤科独立体系奠定基础。例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中“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跗上动脉;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见血已,左刺右,右刺左。”记载了坠落后内、外伤的治疗。在后期的典籍中,伤科从条文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疾病独立的体系。例如在《难经·第十四难》中言,“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萎不能起于床。”阐述了损伤脉络诊断。唐吴兢《贞观政要·征伐》:“道宗在阵损足,帝亲为针灸。”阐述足损伤后针灸治疗。《诸病源候论》中言,“从高顿仆,内有血,腹胀满。其脉牢强者生,小弱者死。得笞掠,内有结血。脉实大者生,虚小者死。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针药结合。针灸治疗在伤科涵盖于各种损伤之中,与中医药其他治疗方法共同构成伤科治疗体系。如《正骨心法要旨》言,“身有所伤血出多,四肢不收曰体惰,急于肪下关元穴,艾柱灸之病即瘥”。其后又言,“若脉浮微而潘,当知亡血过多,依经于三结交关元穴灸之,或饮大补气血之剂而调之,则病已矣”。清俞正燮《癸巳类稿·持素毕》:“宗气营卫,有生之常,针灸之外,汤药至齐。“
《医学源流论》中言:“外治之法,最重外治”,因此针灸在外伤中的治疗十分广泛,涉及多种适应症。同时针灸具有“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调和阴阳、扶正祛邪”等功效[8],在伤运动损伤中具有重要优势。运动损伤多见于生理结构破坏或紊乱,导致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则痛,引起淤血疼痛等症。气壅、血凝则气血失衡,阴阳失调,出现阳胜阴虚的大热之象。日久则会出现阴虚或阴阳离绝的症候。因此针灸的功效和伤科的治疗是一致的,运用针灸及时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缓解疼痛,消除肿胀,减轻局部症状;通过针法,调理气滞血瘀,调和阴阳,达到阴平阳秘的在状态。同时通过针灸,提高机体免疫能力,依靠自生修复功能,修复损伤,减轻内服药物对机体的毒副伤害。在现代研究中,发现针灸在镇静、镇痛、调节机能等方面可迅速起效,在临床中具有重要的优势[9-11]。这些优势在疗效在运动竞技中损伤同时,还可以为竞技中运动员提供继续比赛的可能。加上适应症广泛、简单易行、副作用少等优点,针灸在急性运动损伤中具有十分广泛的运用,并逐渐发展为运动医学重要的外治方法。
2 推拿在急性运动损伤中的治疗优势
推拿按摩是中医外治法中常见的一种,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其发展成熟时间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黄帝岐伯按摩经》专著,隋唐时期为十三科之一理论成熟,明清时期继续发展理论更加丰富,治疗更加多元化。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在自然生活中,时常有劳作或猛兽攻击形成的外伤,外伤疼痛,人们用手去抚摸、按揉,收到治疗效果。这是推拿按摩形成的实践,通过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发展形成推拿按摩体系[12]。早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有俞跗使用推拿治疗疾病的记载。“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药,酒而以桥引、案杌、毒熨等法”。《礼记·内则第十二》记载,“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在医家宗书《黄帝内经》中,对推拿按摩进行了阐述,总结了推拿部分适应症。例如《黄帝内经·素问篇》有“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的论述。推拿本身是针对损伤、疲劳等症状逐渐演变发展而来。因此推拿在伤科的运用是从萌芽时就固有的,春秋战国时期医家经典就有大量记载。如《周礼疏案》中有:“扁鹊过虢境,见虢太子尸厥,就使其弟子子明炊汤,子仪脉神,子游按摩。”记载了推拿按摩治疗因脑震荡、中毒等引起的尸厥。隋唐时期推拿按摩成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例如《诸病源候论》中有,“夫腕伤重者,为断皮肉、骨髓,伤筋脉,皆是卒然致损,故血气隔绝,不能周荣,所以须善系缚,按摩导引,令其血气复。”阐述了按摩在伤科中的运用。明清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丰富,推拿也出现了流派[13],形成了依据适应症为基础的特色治疗,对伤科治疗的适应症选择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推拿具有“疏通经络,行气活血,理筋散结,正骨复位”等伤科作用[14],在急性或慢性运动损伤中具有重要优势。其主要针对软组织、肌肉损伤,关节脱位,肌肉劳损等适应症。当生理结构发生改变,经脉壅塞不通,气滞血瘀,不通则痛,故疏通经络,行气活血。在此基础上,推拿更强调按照生理结构,合经络穴位、时令,运用外力[15],辅助生理结构恢复。推拿是缓解痉挛、肌紧张、韧带拉伤、关节复位等急性运动损伤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以穴位、生理结构为基,结合手法作用,可迅速或长期服务运动损伤。推拿历史悠久,因自身优点,深受人民喜爱,它不仅是中医外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急性运动损伤中运用也十分广泛。
3 拔罐在急性运动损伤中的治疗优势
拔罐治疗疾病记载最早见于汉代《五十二病方》用于外科拔脓,经过后世发展拔罐技术在众多疾病中都有运用[16]。但值得注意的是,拔罐法一直处于治疗技术,未被中医纳入独立的医疗体系中。在明清以前,拔罐运用十分局限,多为治疗痈疽时排脓。例如《肘后备急方》中“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明清丰富了用于常见疾病,主要以通经活络、活血行气、止痛消肿、散寒、除湿、散结拔毒、退热等作用运用于各种病证[17-18]。例如《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拔罐可治风寒头痛及眩晕、风痹、腹痛等症”。伤科的运用在明清以前也多属于后期排脓,在明清后逐渐发展到软组织损伤、扭伤、痉挛等适应症。
拔罐治疗针对淤血、肿胀、痉挛等运动损伤,在镇痛、消除病因中具有重要作用[19-20]。在各大体育赛事中,均可见到拔罐应对急性运动损伤的急诊。在现代研究指出,拔罐通过负压,促使红细胞破裂出现溶血,产生组胺,随着血液循环系统促进器官的生理功能[21-22]。在损伤治疗中,拔罐可以加快肌肉排泄,对急性损伤的应急治疗十分有利。中医认为损伤常会引起血瘀血肿,引起局部经脉壅塞,导致气血淤积不散。拔罐可以开腠理,引邪外出,邪气外出则气血通畅,伤情好转。总之,拔罐治疗在运动损伤中有现代科学的重要依据,也是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总结,在运动损伤中的治疗十分重要。
4 手法复位在急性运动损伤中的治疗优势
手法复位又称为中医正骨,是元十三科之一[23]。《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诀》认为“今之正骨科,即古跌打损伤之证也”。手法复位其主要治疗骨折、关节脱位和软组织损伤等适应症,是中医骨伤学中的重要理论。正骨早在原始社会就有甲骨文等相关记载,经过解剖学发展,逐渐形成为骨伤科和伤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周礼·天官》“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中的金疡、折疡就有骨及骨关节损伤相关的适应症治疗。《黄帝内经》提出“肝主筋,肾主骨”将五脏与五行紧密联系,形成中医的五行体系[24],是手法复位的理论形成时期。后世依据《黄帝内经》发展出治疗基本原则,例如《太平圣惠方》以此认为骨伤治疗要以“补筋骨,益精髓,通血脉”的治疗原则为基础。隋唐时期标志着手法复位的成熟,例如《备急千金要方》记载“一人以手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矣。推当疾出指,恐误啮伤人指也。”是最早的下颌复位手法。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是骨伤科第一本专著,记载了大量的手法复位治疗方案,例如“凡手骨出者,看如何出,若骨出向左,则向右边拔出;骨向右出,则向左拔出”的手法拔伸治疗关节脱位。明清时期在中医理论的极大发展中,手法复位也走向更为繁多,适应症更为广泛的发展。例如《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手法总论》中“盖正骨者,须心明手巧,既知其病情,復善用夫手法,然后治自多效。”发展了手法复位在诊断中的作用。
手法复位经过几千年的长期发展,经历了从单一的临床经验记载,到有方法有目的的治疗[25]。这个过程中也体现出了中医手法复位在依据生理结构,借用手法辅助恢复骨骼完整、关节通利中的重要作用。手法复位常常利用小的辅助工具或者徒手对患者治疗,尽量早期,尽量减少在此损伤的原则下治疗,是其重要的优势。手法复位一直是中医骨伤科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特色治疗方法,被大众广泛认可。在运动医学中,中医手法复位在适应症多、治疗创伤小、恢复快等方面的优势上,备受运动员喜爱和认可。
5 中药熏洗和中药制剂在急性运动损伤中的治疗优势
中药是中医治疗中最为重要的体系,早在远古时期,就有用草本治疗疾病的记载。在医家源头《黄帝内经》中就有十三方[26],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被誉为中医四大经典,记载了大量中药药效及疾病治疗。后世在中医基础理论和哲学指导下,不断深化中药治疗效果,通过配伍、炮制等方法增加其药性。在伤科中的除了内服外敷的中药或方剂外,在增强要先上选择不同剂型从而增强药效也是其重要的方式,例如在伤科选择膏剂、酒汀、散剂、丸剂等[27]。 《伤科补要》中“重者,筋断血飞,掺如圣金刀散,用止血絮扎住,血止后,若肿溃,去其前药,再涂玉红膏,外盖陀僧膏,止痛生肌。”阐述不同方剂的不同剂型对伤科的完整治疗记载。本身利用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消肿散结等治疗方剂,为减轻毒副作用和局部靶向治疗,选择外用中药熏洗[28],有效的对局部伤情治疗。同时运用不同剂型的特点,针对局部伤情进行局部治疗是中药制剂的重要优势。
在《黄帝内经》中对伤科的治疗认为应当先服用中药,在进行其他治疗,如《素问·缪刺论》中“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的论述。正如《理淪骄文》记载,“外治之理及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说明中药外治和内治其机理原则都应相同,外用毒副作用更小更安全,所以部分中药在大剂量时外用更为恰当,所异才有内外治的区别。在外治剂型上的改变,更多时为了更好更快的作用于伤处,例如熏洗法上,在《仙授理伤续断方》中“治男子妇人骨断,用此煎水洗后整骨了却用乌龙角贴。”已有明确记载。制剂上《仙授理伤续断方》也记载了“大承气、小承气、四物汤;黄药末、白药末;乌丸子、红丸子、麻丸子;桃红散、紫金散、七宝散;”等[29-31]。总之,中药外治运动损伤同内治法理相同,治疗原则相似,不同的是外治法为增加药效,固定患处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进,使药物更快、更强的治疗伤情。中药外治适合于所有损伤,适应症广泛,治疗形式丰富,在运动损伤中治疗优势突触。
6 总结
在长期的中医药实践中,中医药对急性损伤有一系列的系统治疗方案。随着运动医学的发展,中医药逐渐从伤科学发展到运动医学中。在运动医学的特殊要求下,中医药以丰富的治疗形式,良好的治疗效果被运动医学吸纳,为运动损伤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 多适应症药物准入评估方法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