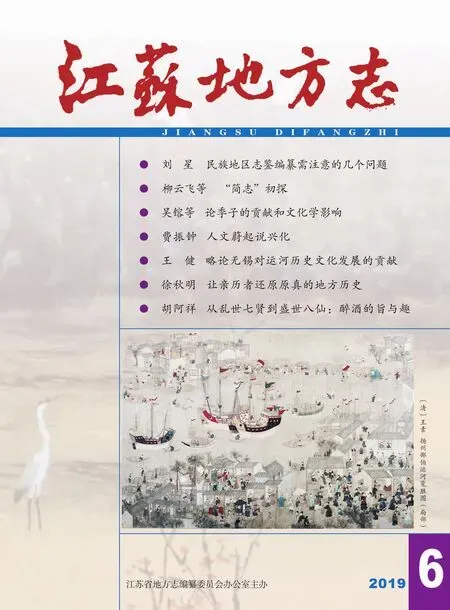从乱世七贤到盛世八仙:醉酒的旨与趣
◎胡阿祥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也是一部酒的发展史、酒的文化史。在中华传统文化观念中,酒可养老,如《诗经·豳风》:“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酒可治病,如《汉书·食货志》:“酒,百药之长”;酒可壮胆,如俗语“酒壮怂人胆” “酒壮英雄胆”;酒以成礼,如《世说新语·言语》:“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酒以成欢,如白居易《琵琶行》:“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酒以解忧,如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相对言之,文人名士与酒更有缘分,酒也因此从日常生活的饮品升华为精神文化的象征。从竹林七贤开始,酒与名士结下了难解之缘。兰亭修禊,酒成为文人雅聚的典型符号。在陶渊明的生活与诗文中,酒几乎是永恒的母题,杜甫《饮中八仙歌》可谓文人名士、官员平民的醉酒群像图……现代古井贡酒拥有国家级非遗九酝酒法、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魏井”与“宋井”,融会了老庄道家智慧、曹操献酒传说、华佗济世情怀、聂广荣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传承创新的瓶型(以厚重黑色为主色调,瓶头像顶戴,瓶标似补子)与酒具(“步步高升”酒杯,酒令扑克),值得彰显的价值观(“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于是,古井贡酒虽然是物是体是器,古井文化则是魂是美是道。
那么,如何理解是物是体是器的中国酒、是魂是美是道的中国酒文化呢?不妨以笔者相对熟悉的中国中古时代为例,略举四例,以见一斑。
一
先说竹林七贤,以见乱世的醉酒之旨。
竹林七贤,即以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位为代表的一派名士。当曹魏正始、嘉平之间,他们经常相聚于竹林之下,相聚后的主要事情就是清谈喝酒,除了嵇康以外的六位也都非常能喝。其实能喝酒、酒量大,与是不是名士没有必然关系,那么竹林名士是如何喝酒的呢?
以刘伶为例,《世说新语》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反击讥笑他的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屋室是我的裤子,你们诸位干嘛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呀?《世说新语》又记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这是说,夫人劝他戒酒,刘伶要夫人准备酒肉,他要敬祝鬼神,发誓戒酒,刘伶发的誓言却是“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就又喝酒吃肉,酩酊大醉。再如阮籍,《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戎)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这叫我行我素,风流而不下流;至于阮籍的侄子阮咸,他与酒友们以大瓮盛酒,围坐畅饮,有时酒香引来群猪争饮,阮咸也不在乎。诸如此类的喝酒,才当得上名士吧。
问题在于,竹林名士为何如此喝酒乃至醉酒?竹林名士的肆意畅饮,看似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其实他们喝的大多是闷酒、苦酒、含泪带血的酒。当其时也,司马师、司马昭阴谋篡窃之势已成,并且残酷地剪除异己,于是竹林名士借酒浇愁、借酒远祸、借酒装糊涂,毕竟喝酒有助于进入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酒后说错话、做错事可以有回旋的余地,久醉不醒也是逃避政治斗争、远离人事纠纷的有效手段。比如阮籍曾经沉醉60 天不醒,借以拒绝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的求婚;刘伶常常乘着鹿车,边走边喝,并对拿着铁锹的随从说:“若是我喝死了,你就掘地埋我。”这样的喝酒,是不是一种巨大的、深刻的乃至绝望的悲哀?这就是乱世的醉酒之旨吧。而在竹林七贤之后,酒与名士结下了难解难分之缘,如东晋名士王恭的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也就是说,名士的外在表现是,无所事事,酣畅饮酒,又“吾将上下而求索”地清谈着人生的困惑、生死与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妙追求,比如治世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就是如此。
二
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故事,发生在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上巳节。在这个全民娱乐的盛大节日,时任会稽内史即相当于现在绍兴市市长的王羲之,邀请了来自诸多世家大族的好友与自家的子侄,共赴“会稽山阴之兰亭”,举行曲水流觞、行酒赋诗的雅聚。名士们列坐在蜿蜒的溪水两旁,然后由小书童在上游将盛满米酒的耳杯放入溪流中,随水缓缓自流,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就取饮并即兴做诗,如果做不出诗,就得另外罚酒。结果26 人成诗41 首,包括四言诗14 首、五言诗27首,而包括王羲之七子王献之在内的另外15 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我曾一时兴起,想算算三斗酒是多少,结果吓了一跳。当时一斗等于2000 毫升,三斗就是6000 毫升,等于现在的12 斤。当时当然没有蒸馏酒,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即指出:“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之,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接滴露。”而考虑到酒醪中的酒精浓度达到20%以后,酵母菌就不再发酵,因此元朝以前中国酿造酒的酒精含量一般不会超过18%。但即便是酒精度十几度的低度米酒,即便名士们大多既好酒、也能喝,这样的罚酒,还是不仅考验着胃容量,而且考验着肝功能,多数人还是会被罚得大醉的。由此看来,王羲之主持的这场东晋版“中国诗酒大会”,比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难度更大,因为参加这样的大会,不仅要求文思敏捷、出口成诗,而且还要有酒量、有酒胆打底子。
当然,除了罚酒的趣事以外,这场“东晋诗酒大会”还留下颇为丰厚的文化遗产。比如在诗歌方面,这场大会集中创作的诗歌数量,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而且显出中国山水诗的端倪;在书法方面,当时诗酒大会结束后,众人意犹未尽,提议把这些诗汇编成集,并公推东道主王羲之作篇序言,王羲之一番客气之后,乃于酒酣耳热之际,即席挥毫,心手两畅,物我两忘,写出了后来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在文章方面,一气呵成的《兰亭集序》,不仅书法堪称“神品”,文章也是千古名作。王羲之在文章中,既描述了上巳节习俗,赞美了自然环境,也抒发了文人情怀,肯定了生命价值,其中“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将喝酒、作文、雅聚、抒情融为一体。
其实,早在西晋元康六年(296),朝廷大官石崇就在首都洛阳他的别墅金谷园里,主持过一场连续几天的诗酒大会,而且流觞、赋诗、罚酒以及主持人石崇写成《金谷诗序》等等,与50 多年后王羲之的兰亭聚是一样一样的,换言之,从形式到内容,可以说王羲之都是学石崇的。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因为石崇其人的品行太过不堪,比如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积财如山、穷奢极欲、荒淫无耻,导致当时声名显赫的金谷宴、优美铿锵的《金谷诗序》,后来几乎完全被兰亭聚、《兰亭集序》盖过,时至今日,大概除了专业人士外,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金谷宴与《金谷诗序》了。这样的历史事实与文化现象,说明富贵豪奢、寻欢作乐、醉生梦死之徒,毕竟如同一闪而过的浮云,容易消逝,而胸怀旷逸、灵秀自然、风流雅致的名士,则如风如雨,风靡后世,雨润后世,使人长久地向往、追忆乃至模仿。比如自此直到近现代,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批文人、书家相聚兰亭,举办雅集活动,并辐射到全国许多地方,甚至传播到日、韩等国。由此,弥漫着酒香酒趣的兰亭雅集,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意象、一道优雅景观。
三
从东晋治世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开始,酒成为文人雅聚的典型符号。而到了衰世的晋末宋初,陶渊明的诗文既散发着浓烈的酒气,酒又可谓陶渊明诗文乃至生活之凸显的乃至永恒的母题。
陶渊明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中,形容自己“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衔觞赋诗,以乐其志。”
陶渊明的《饮酒》20 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仕途的黑暗险恶,或表现退出官场后的怡然陶醉,或发泄艰难困顿中的牢骚不平。最著名的第五首这样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体现了他追求恬淡生活、大道自然的生活境界。
陶渊明酷爱喝酒,而且几乎每饮必醉。有酒的时候,他与客人一起畅饮,如果他先喝醉了,就跟客人说:“我喝醉了,想去睡觉啦,你可以回去了。”有一次,有位郡将拜访陶渊明,正赶上他酿的酒熟了,他就取下郡将头上的葛巾滤酒,滤完之后,又把葛巾还给郡将戴上。
这样的陶渊明,及至后世,遂被称为六朝名士最后一抹灿烂的晚霞,被看作中国隐士的典范。其实,陶渊明并无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功,他留给后世的遗产,是在衰世中坚守着高尚的节操与独立的人格,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依草附木、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陶渊明的清结合陶渊明的酒,酿成了流芳千古的一壶清酒,这壶清酒,可谓陶渊明生活与诗文、精神与品格的鲜明写照。
四
陶渊明去世后300 多年,把陶渊明视为一生知己的唐朝大诗人杜甫,写出了闻名遐迩的《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不妨稍微解释一下杜甫白描的“饮中八仙”之行为举止:贺知章醉后骑马,摇来晃去像在乘船,不料老眼昏花,跌到井底,竟然还在里面安睡,汝阳王李琎酒过三斗,才去觐见天子,路上偶遇装载酒曲的车马,酒香使他垂涎直流,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水味如酒的酒泉,左相李适之为了过足酒瘾,常常不惜日费万钱,牛饮起来,好像巨鲸吸纳百川之水,他宣称举杯痛饮,乃是为了逃避政事,只求让贤,潇洒美少年崔宗之举杯豪饮时,以白眼仰望青天,醉后的摇曳之姿,有如玉树临风。我们知道,竹林七贤的阮籍能作青白眼,他以青眼视友人,以白眼看俗人。崔宗之竟以白眼视天,这比阮籍更为狂傲;苏晋吃斋念佛,却仍好饮,处在斋与醉的矛盾中,结果往往是“酒”压倒了“佛”,把佛门戒律忘得干干净净,李白饮酒一斗,立可赋诗百篇,他常常醉眠长安市上酒家,哪怕天子召唤,也因酒醉而不肯上船,并且自称是“酒中之仙”,草圣张旭三杯下肚,就在王公贵戚面前倨傲不恭地脱帽露顶,而他奋笔疾书,笔走龙蛇,字迹就如云烟一般舒卷潇洒,一介布衣焦遂,饮酒五斗方见微醺,此时的他高谈阔论,雄辩机锋,总是语惊四座。
杜甫的这首《饮中八仙歌》,写于大唐盛世的巅峰时代天宝年间,明人王嗣奭《杜臆》评道:“描写八公,各极生平醉趣,而都带仙气。”那么何谓“醉趣”与“仙气”呢?关键在于醉趣中是否带有仙气,所谓“仙气”,大概就是借着酒力之兴奋与麻醉之力量而触发灵感,然后无所阻碍地发挥其天性与天才,这是平素并不容易看到的奇迹,所以称之为“饮中八仙”。这“八仙”都是当时欲有所为却被迫无所为、不得已沉湎于醉乡者,他们都是愤世疾俗、恃才傲物、豪放旷达、似醉实醒的“酒徒”。如果只是烂醉如泥,形如死猪,或借酒骂座,或呕吐狼藉,那就属于酒后丑态了,既谈不上“醉趣”,也谈不上“仙气”。
品味了乱世一群名士即竹林七贤喝的苦酒,治世一场聚会即兰亭流觞流的雅酒,衰世一位隐士即陶渊明酿的清酒,盛世一类酒客即“饮中八仙”饮的仙酒。虽然魏晋隋唐时代,烈性白酒尚未出现,然而所谓历史,不外乎就是乱世、衰世与治世、盛世,而联系着这样的历史情境与世道变迁,酒的文化内涵,酒的苦涩甘甜,是含泪带血的酒,还是解脱适意的酒,也是因时随世而变。我所感悟的酒的形而下与酒的形而上,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酒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日常,也是我们精神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