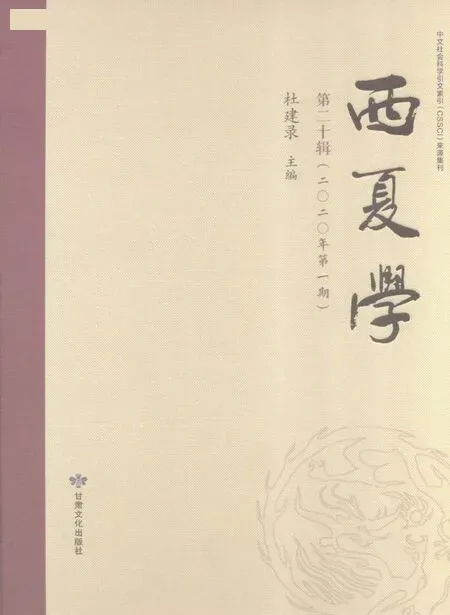汉字音在日译汉音与党项语中变读形式的比较研究
孙伯君 孟令兮
日语和西夏语尽管相隔万里,语言也不属于同一个语系,但两种语言有相近的音节结构,即它们的辅音韵尾均不够丰富,没有像中古汉语一样的-p、-t、-k和-ŋ等辅音韵尾。
我们知道,日语原有两套古老的汉字音,日译吴音和日译汉音(kan-on),中村久四郎《唐音考》认为日译吴音是东晋和宋齐时期(4—5世纪)的汉语,而日译汉音则是隋唐时期(6—10世纪)的汉语①中村久四郎:《唐音考》,《史学杂志》XXVIII,1917年,第1142页。。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日译汉音反映的是唐代中期的汉语语音,是8、9世纪,日本从中国长安一带学来的当时被认为“标准”的字音系统②平山久雄:《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在日本汉字音中的反映及其演变》,《中文学术前沿》第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3页。。
西夏(1038—1227年)是党项人于1038年建立的王朝,都城是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其主体民族汉语称之为“党项”,蒙古语称之为“唐兀”,藏语称之为“弥药”。党项人和现在四川省境内的“木雅人”有某种渊源,都是古代羌人的支系。他们所操母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一般认为党项语(西夏语)属于羌语支,与木雅语比较接近③孙宏开:《羌语支属问题初探》,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9—224页。。西夏遗存的记录汉字音的文献,主要是黑水城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记音材料、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梵汉对音,以及藏文佛经残片中的汉字记音等,反映了12世纪流行于河西一带的西北方音。
可以说,日译汉音和西夏文献中的汉字音是时代相继的中古西北方音语料。不过,由于受本族语音节系统的影响,唐、宋时期汉字音借用到这两种语言中时,往往会发生音素的替代、增音、减音等变读,与汉族人所说的汉语不甚一致。
高田时雄曾基于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各种民族文字文献所记载的汉字音的不同,指出唐代的西北方音中存在着各种“变体”①高田时雄(Takata Tokio)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mong Ancient North-Western Dialects in Chinese,载波波娃(Irina Popova)、刘屹主编:《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的研究视角与问题》,圣彼得堡,2012年,第249—250 页。。所谓“变体”,当指中古西北方音存在很多由于母语与汉语的音位格局差异,是所读汉字音有变读成分的“番式”汉语。毫无疑问,日译汉音也应属于唐代西北方音的“变体”。
马伯乐、高本汉和中、日学者均曾利用日译汉音研究唐代的西北方音,高本汉曾提醒人们注意这类材料的变读:“第一类材料自然在将来可以得出很有趣的结果。不过我们对于这一类材料要当心一点。因为各民族要迁就自己语言的读音习惯,对于外来的借字都有曲改读音的倾向,甚至改得认都认不出来了,所以有时简直连相近的音值都不一定找得到了。”②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7页。所谓“第一类材料”即指外国语言里翻译中国字的对音与中国语言里翻译外国字的对音。
一、入声字在两种语言中的变读
(一)入声字在日译汉音中的变读
中古汉语的入声韵是以塞音-p、-t、-k收尾的闭音节或促声韵,敦煌藏汉对音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汉语入声字-k、-t、-p韵尾分别用藏文-g、-d(-r)、-b注音,如“纳”’dab,“甲”kab,“法”p’ab,“答”tab;“达”dar,萨sar,“灭”’ byar;漠’bag,“伯”peg,“睦”’bug,“目”’bug③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2—86页。,尽管-t被-r所替代,但毫无疑问唐五代西北方音还保留全部入声韵尾,而因为藏文的g、d、b不能用作后加字的,所以当时汉语入声韵尾仍然是-k、-t、-p。
综合来看,中古时期的入声字在日译汉音中的变读有两种情况:一是在-p、-t、-k之后增加i、u等元音;二是-p、-t、-k脱落。桥本进吉先生曾这样总结入声字在日语中的变化,并称这种变读为“国语化”:“入声音[-p][-t][-k]在古代国语里并不存在,由母音直接向[-p][-t][-k]这样的闭锁音过渡,这与国语音节的一般构造也是大相径庭的。这样的发音对于日本人来说无疑是困难的。因此,为使之国语化,则在其最后的子音后,加上[i][u]等母音,将[-p]发成「フ」,将[-t]发成「チ」或「ツ」,将[-k]发成「キ」或「ク」,把它们当成另一个音节,或者干脆把后面的子音省略掉,使之变成以母音结尾的音节。”①桥本进吉(Hashimoto Shinkichi):《国语音韵 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57年,第254—255页。
平山久雄先生也曾说过:“日本人曾在-p、-t、-k后面添上一个元音*u或*i来模拟汉语入声字的韵尾。这是由于古代日语没有以辅音收尾的音节的缘故。”②平山久雄:《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在日本汉字音中的反映及其演变》,《中文学术前沿》第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3页。
下面表1里是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p、-t、-k在日语汉音中的变读规律③本文所用中古音和日译汉音的例子摘自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中国音韵学研究》第四卷“方音字汇”,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47—731页。。
上述日译汉音大部分是高本汉从《汉和大辞林》与《汉和大字典》中摘录的。有些是理论上的读音,不过存世日本古代文献可以佐证这些字音,如长承本《蒙求》(注音承袭10世纪的某种文献)被认为是汉音的典型代表,沼本克明曾对其注音按汉语的声、韵、调加以整理,以下的例子与字典中的读音基本相合:“合”kapu、“急”kipu、“猎”repu;“密”bitu、“窟”kutu、“葛”katu;“木”boku、“药”yaku、“直”tyoku;“剧”keki、“石”seki、“壁”peki④沼本克明:《吴音、汉音分韵表》,筑岛裕(编):《日本汉字音史论辑》,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第121—243页。。
可以看出,中古汉语的大部分入声字在日译汉音中的变读形式是于-p、-t、-k韵尾后添加元音*u或*i,由一个闭音节变读为两个开音节。此外,据考证,日本7—8世纪的文献中有一些利用汉字的音读来书写日语地名、人名的例子中,还有在-p、-t、-k韵尾后面加a、e、ö的情况,如:东京有“葛饰区”,“葛饰”*katsushika;福冈市有“博多区”,“博多”*hakata;“博士”*hakase(也作hakushi);“伊达”*idate、“乙训”*otökuni。无论如何,汉语中古时期的入声字在日译汉音中的变读大部分都是增音的形式。
(二)入声字在西夏语中的变读
西夏的资料显示12世纪河西方音入声韵尾全部失落了。龚煌城通过考察《番汉合时掌中珠》标音汉字已经得出当时丢掉所有的入声韵尾的结论①龚煌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567页。。
孙伯君则根据西夏新译佛经,归纳其中的梵汉对音规律,进一步证明了当时的入声韵塞音韵尾已经失落,如②孙伯君:《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西夏资料所反映的汉语塞音韵尾全部失落的情形,是一种基于党项语音节中没有塞音韵尾的“番式”变读。与日译汉音增音的变读形式不同,西夏人口语中的中古汉语入声字是一种减音的形式。
二、鼻音-m、-n、-ŋ韵尾在两种语言中的变读
(一)鼻音-n、-ŋ在日译汉音中的变读
中古汉语有-m、-n、-ŋ三个鼻音韵尾。汉字进入日本之前,日本固有的和语中没有拨音ん(ン)。桥本进吉先生认为拨音ん(ン)产生于平安朝后期③桥本进吉(Hashimoto Shinkichi):《国语音韵 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57年,第173页。,是受汉语的影响而产生的。最初,汉语鼻音韵尾-m、-n,日本采用增音的变读形式,分别读作mu、mi,na、ni,如“心”读作*simi;“三”读作*samu;“信”读作sina。随着汉字的继续传入和影响,又逐渐把-m、-n读作-n,产生了拨音ん(ン)①刘富华:《从鼻音n、ng与拨音ん的关系看汉语对日语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第30—37页。。汉语鼻音韵尾-m、-n在日译汉音中均标注为拨音ん(ン),如表2。尽管标作拨音ん(ン),但马伯乐(Henri Maspéro)认为:“8世纪的-n就像日语里所有别的辅音一样,需要和元音一起念出来。……‘浑’字从11世纪起也被转写成ku-ni,显得是打算直接转写当时的汉语读音。”②马伯乐(Henri Maspéro )著,聂鸿音译:《唐代长安方言考》,中华书局,2005年,第12页。
日译汉音把汉语鼻音韵尾-ŋ变读作元音-i、-u,如表3。

表3
(二)鼻音-n、-ŋ在西夏语中的变读
西夏语中有一部分鼻音-n能读出来,应该是长期与汉语接触而产生的。大部分失落,相应的音节读作阴声韵,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丙”“并”“边”“变”,为同一个西夏字注音;“爹”“丁”“顶”“鼎”“典”为同一个西夏字注音③龚煌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541—543页。。
后鼻音韵尾-ŋ在党项语中变读作-u、-i,《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大量宕摄、梗摄、曾摄、通摄字失落鼻音韵尾-ŋ,分别与果摄、蟹摄合流,读作-u(o)和-i。如:宕摄的“黄”“刚”“姜”与果摄的“哥”“果”“个”为同一个西夏字标音;梗摄的“庚”“更”“耕”“粳”与蟹摄的“皆”“芥”“界”为同一个西夏字标音①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5—246页。。
梵汉对音中,大量宕摄字与梵文o/u对音,如“光”对ko,“口浪”对rō,“商”对śo/śu,“当”对tu等;梗摄字与梵文元音i/e对音,如“丁”对te,“矴”对te/ti,“口命”对bhe/bhi,“铭”对me,“宁”对de/dhe/dhi,“形”对he,“永”对ve等等②孙伯君:《西夏译经的梵汉对音与汉语西北方音》,《语言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19页。。
上述情况说明党项人的口语中,汉语的宕摄(*-aŋ)变读作果摄(*-o、*-u),梗摄(*əŋ、*-iŋ)变读作蟹摄(*-ai、*-ei)。
中古后鼻音韵尾-ŋ在日译汉音与党项语中的变读,与这两种语言没有后鼻音韵尾有关。
三、中古汉语声母在两种语言中的变读
(一)精组字在日译汉音中的变读
日语中齿头音和正齿音只有s-声母,而没有*ts-、*tsh-和ʨ-、ʨh-,因此,日译汉音中把齿头音和正齿音均变读作s-,如表4。

表4
这种变读与阿尔泰语系的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对汉语的变读类似。《女真译语》为精母汉字标音常用心母字,如“总兵”在《女真译语·人物门》对音为“素温必因”,“总”变读作“素温”;汉语精母字“子”(瓦子)、从母字“皂”的声母,“都司”的“司”,用同一个女真字标音③金启孮:《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66页。。
蒙古语中齿头音也只有擦音s-,汉语ts-、tsh-、s-均读作s-,如元代《张应瑞先茔碑》《竹温台神道碑》《忻都神道碑》:“藏”sink,“匠”sank,“紫”“资”“集”si,“赠”sink,“左”soo,“总”sonk;“参”sam,“钱”san,“齐”si,“秦”sin,“青、清”sink,“全”soin④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3—746页。。
(二)汉语非(f-)声母字在党项语中的变读
党项语用喉音合口字xu-或xiw-(龚煌城拟音)替代f-,如西夏文《类林》卷三“范式”对译作①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页。,西夏文《德行集》第6叶“太傅”对译作,“大夫”之“夫”对译作“xu1”②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日译汉音往往把非声母字读作喉音合口字,如表5。

表 5
四、结语
日语和西夏语尽管不属于一个语系,但同属辅音韵尾不够丰富的语言,音节结构相近。在标注唐、宋时期汉字音时,尽管音素的替代、增音、减音等变读有增有减,或同或异,但总的趋势是一样的,如:中古时期的入声字在日译汉音中有两种变读形式,一是增音,二是脱落,而党项语只有脱落的形式;中古时期汉语鼻音韵尾-ŋ,日译汉音和党项语的变读形式一样,均读作元音-i、-u。上述辅音后边增加一个元音和减掉音节末辅音等变读,都是与本民族语的音节结构特点发生的趋同变化。考察和比较汉字音在日译汉音与党项语中的变读形式,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如下的事实:不同系属的语言在与其他语言接触的时候,如果它们的音节结构相近,也会发生共同的变读,而这些属于共时变读的形式与历时演化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