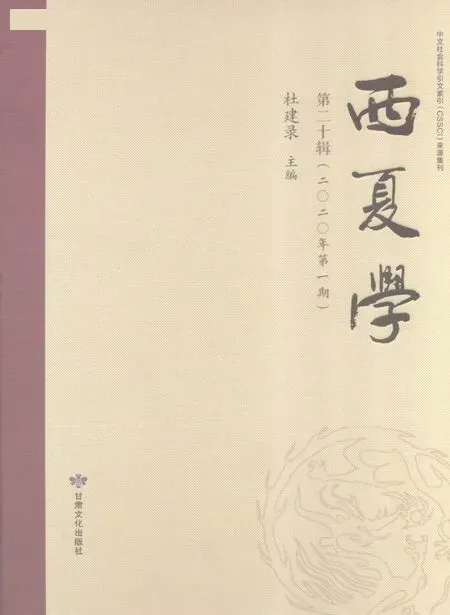菏泽博物馆藏两方元代西夏遗民墓碑史料价值初探
刘志月
察罕族出西夏皇族乌密氏(乌密为嵬明音转),其父在西夏时期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他在幼年时被成吉思汗收为养子,称作“五儿”,并赐蒙古姓氏。在前四汗时期,察罕参与了蒙古平定金朝、西域、西夏的战役,并立下赫赫战功。第六次蒙夏战争时,他制止了蒙古军在甘州和中兴府的屠城①[明]宋濂:《元史》卷一二〇《察罕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2956页。。察罕的战功和仕履赢得了前四汗的信任,为该家族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塔出为察罕之孙,在参与平定南宋的战役中立下了战功。他至元元年入侍世祖,历任山东统军使,佥淮西等处行枢密院事,淮西行省参知政事,江西都元帅,江西行中书省右丞等职。必宰牙为塔出次子,察罕曾孙,史籍可见他在元代中后期曾任征东行中书省左丞②塔出与必宰牙事迹均见[明]宋濂:《元史》卷一三五《塔出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2—3275页。。
学界有关察罕家族的研究,业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现有研究成果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三点。第一,察罕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③汤开建:《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载《党项西夏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84页。整理了察罕家族人物的姓名字号,族称、居地、世次,职官、爵位、谥号,主要事迹。《略论元代的察罕及其家族》④孟楠:《略论元代的察罕及其家族》,《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45—51页。和《唐兀人察罕家族研究》①陆宁:《唐兀人察罕家族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103—111页。梳理了察罕家族成员的仕履。第二,察罕家族成员的婚姻情况。《元代西夏遗民婚姻研究》②孟楠:《元代西夏遗民婚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11—17页。虽然没有考证出塔出妻子明理氏的族属,但将必宰牙之妻伯也伦考证为泰安郡武穆王李鲁欢之女(蒙古人)。《元代〈故漕运同知粘合公妻逸的氏墓志铭〉考释》③翟丽萍:《元代〈故漕运同知粘合公妻逸的氏墓志铭〉考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29—33页。考出察罕玄孙女瑞童嫁于女真人粘合世臣,世臣之曾祖粘合重山在金朝末年作为质子随侍成吉思汗。《元代西夏女性遗民人物史料整理与研究》④张琰玲:《元代西夏女性遗民人物史料整理与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10期,第94—98页。一文中列举了元代西夏女性遗民人物表⑤严格来说,该表其实收录了嫁入西夏遗民家族的其他女性人物,这些女性人物既有蒙古人,也有色目人、汉人,用“西夏遗民女性人物”概称之颇为不妥,理应称为“元代西夏遗民女性及女眷人物表”。,该表整理了察罕家族女眷明理氏和伯牙伦二人的封赠与事迹。第三,察罕及其家族的汉化及其成因⑥马云:《浅谈西夏后裔高智耀和察罕家族的汉化及原因》,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以上研究所依据的史料无出《元史》《至正集》《道园类稿》等传世文献,而出土文献史料在察罕家族史的研究中无疑是一大缺失。所幸的是,出土于菏泽市赵王河郭庄段的两方碑石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这两方碑石其一为《中书省右丞塔出夫妇墓碑》。墓碑立石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十四日,石灰岩质。碑身高148厘米,宽79厘米,厚26厘米。圆首。碑首左上角残缺,又有长方形底座,长97厘米,宽33.5厘米,厚24厘米。此碑2008年征集入藏菏泽市博物馆⑦孙明:《菏泽市古石刻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94—195页。。现陈列于博物馆南墙侧的碑廊中,为自东向西数第4方。笔者于2017年8月对碑刻进行了现场调查,按照片将墓碑文录于下:
1. 男中奉大夫工部尚书必宰牙
2. 节妇刘氏明理太夫人
3. 中书省右丞塔出相公之墓
4. 大德十一年丁未六月十四日立石
其二为《中书右丞必宰牙夫妇墓碑》,墓碑立石于元统三年(1335年)四月。石灰岩质。碑身高147厘米,宽74.5厘米,厚25厘米。圆首。碑阳额横向阴刻楷书“大元”二字。此碑2008年征集入藏菏泽市博物馆⑧孙明:《菏泽市古石刻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99页。。现陈列于博物馆南墙侧的碑廊中,为自东向西数第7方。现按调查所获得的照片将墓碑文录于下:
1. 男祥童舍人
2. 孝妻完者夫人建立碑石
3.大 忽都罕夫人
4. 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必宰牙相公之墓
5.元 伯也伦夫人
6. 男武略将军嵩州达鲁花赤寿童
7. 元统三年四月吉日
这两方元代西夏遗民墓碑,事涉察罕之孙塔出和察罕曾孙必宰牙,为察罕家族的研究补充了新的史料。以下试对其史料价值略做初步介绍。
一、揭示了元代西夏皇族的又一去向
西夏皇族后裔的最终归宿曾在21世纪初引起过一场学术争鸣①1994年,李范文发表《西夏皇裔调查纪实》,公布了李培业先生是西夏皇族后裔的消息。1995年,李培业撰写《西夏皇族后裔考》,对质疑其为西夏皇族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对此,史金波等人撰写《西夏皇族后裔考论》一文,考证了西夏皇裔的迁入地,认为李氏族谱的可靠性令人怀疑,攀附的可能性更大。2002年,李春光在新安县发现《明忠义官李公墓志铭》,并于2003年编撰《西夏皇裔在新安》一书,搜集和整理了与李恒家族相关的史料。对此,史金波认为这一墓志铭为研究西夏皇族后裔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由于世系缺载,还需进一步考证。。就研究现状来看,能以一手史料确证元代以后有西夏皇族迁入的地区,无非大都路、龙兴路、淄川县、新安县以及平江路等少数几个地区②平江路为邬密公夫人迁入地。大都路、龙兴路、淄川县为李世安家族的迁入地。新安县为李恒家族的迁入地。。除“寓第在吴门天宫里”③[元]陈基著,丘居里、李黎点校:《陈基集·夷白斋稿》卷二八《听雪斋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的某位邬密公(即“嵬名公”)以外,迁入其余四地的西夏皇族,都是李惟忠(在蒙夏战争期间被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大王所收养)一脉的后人。而《元史》中其他的西夏皇族后裔,诸如察罕、李桢、卜颜帖木儿等,他们最终何去何从,在传世史籍中的记载并不确凿。菏泽市博物馆藏墓碑的碑主塔出与必宰牙,分别为察罕之孙与曾孙④由于明朝官修《元史·察罕传》中,未尝叙及布兀剌、塔出与察罕的亲缘关系,且将察罕与塔出置于两传,分别列于卷一二〇与卷一三五。使得后世史家最初并不知晓塔出与察罕的关系,如清代乾嘉学派文人汪祖辉谓塔出为“布兀剌子也,案失书氏族”,钱大昕在编纂《元史氏族表》亦未将塔出和布兀剌列入察罕家族表之下。直至民国初年,屠寄与柯劭忞方才依据许有壬《故粘合公妻逸的氏墓志铭》中“高祖察罕,太师、河南武宣王,开国有功。父必宰牙,辽阳行省右丞”等记载推测出布兀剌为察罕次子,塔出为察罕之孙。,属“西夏之贵臣,唐兀之令族,乌密其氏也”⑤[元]虞集著:《虞集全集》(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98页。,有助于揭示元代西夏皇族后裔的又一去向。
墓碑之出土地在今赵王河郭庄段,即今菏泽市牡丹区东郊,元代属济宁路曹州所辖。由此地先后出土塔出、必宰牙父子二人的墓志来看,元代的曹州已然成了察罕家族的祖茔,而不仅仅是权厝之所。即便塔出常年“行省于江西”且“以疾卒于京师”⑥[明]宋濂:《元史》卷一三五《塔出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5页。,也仍需将灵柩运回曹州安葬立碑。而就其他元代西夏遗民来看,往往也会将祖茔置于家族的定居地,如居住迁居于濮阳县柳屯镇杨什八郎村的唐兀杨氏家族,即在村外的金堤河边营建祖茔,至今尚存。因此,曹州作为察罕家族在元代的定居地,应无疑义。
那么,察罕家族又是如何与曹州结缘的呢?在西夏灭国以后,察罕继续追随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南征金朝,“从略河南”①[明]宋濂:《元史》卷一二〇《察罕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2956页。;在蒙宋战争爆发后,又与诸王口温不花合力攻克光州、天长县、滁州、寿州、泗州等地。定宗贵由即位后,察罕依旧以淮泗地带作为防区,领命“拓江淮地”,立下赫赫战功。元宪宗蒙哥在位时,察罕以军功受赐“汴梁、归德、河南、怀、孟、曹、濮、太原三千余户为食邑,及诸处草地,合一万四千五百余顷,户二万余”②[明]宋濂:《元史》卷一二〇《察罕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2956—2957页。。也就是说,曹州最初是以食邑的形式被分封给察罕家族的。然而,元代功臣勋贵对于汉地五户丝食邑仅有获取经济收益的权利,而并无常驻或镇戍之实。至少在察罕和其子木花里、布兀剌两代,该家族尚未定居于曹州。
察罕之孙塔出,早年侍奉元世祖,因“占对多称旨”而深受皇帝宠爱。至元四年,元世祖令“给以察罕食邑之半,又还其所俘逋户三十”③[明]宋濂:《元史》卷一三五《塔出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3页。,曹州可能再次以食邑的形式被分封给察罕后人。同年,宋将刘整降元,向元世祖献策南征,元朝对南宋的战争再度爆发。塔出于此间任山东统军使与淮西行枢密院佥事,继承父志,在淮泗地带与宋军作战,并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升任淮西行省参知政事,“帅师攻安丰、庐、寿等州,俘生口万余来献”。因军功,塔出被元世祖赐予“葡萄酒二壶,仍以曹州官园为第宅,给城南闲田为牧地”④[明]宋濂:《元史》卷一三五《塔出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3页。。就地缘而言,曹州为元朝中书省辖地最南端沿线,是宋元战争淮泗战场的后方;元廷将曹州官园赐予塔出作为宅邸,应该是为了便于他在前线指挥战事。
也就是说,这一支西夏皇族后裔正式定居于曹州,应始于1274年。曹州为上州,在元初隶东平路总管府。至元二年严实遭到忽必烈罢黜以后,忽必烈采取了对投下封地的行政建制进行调整的举措来整顿和改革投下制。严实辖下的东平路被分为济宁、东昌、东平三路和曹州、高唐、冠州等直隶都省。东平路是投下户较多的地区,《元史》有载:“皇子阔端、驸马赤苦、公主阿剌海、公主果真、国王查剌温、茶合带、锻真、蒙古寒札、按赤那颜、坼那颜、火斜、术思,并于东平府户内拨赐有差。”⑤[明]宋濂:《元史》卷二《太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35页。这与东平路一分为十的状况相符。
上述史料中提到的火斜、术思,即《元史》中提到的太宗丙申年“分拨曹州一万户”⑥[明]宋濂:《元史》卷九五《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2432页。的和〔斜〕温两投下。据《曹州禹城县隶侧近州郡事状》可知,曹州所辖的禹城县为和斜、拜答汉的封地,食邑户约四千余户①[元]王恽著,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八五《曹州禹城县隶侧近州郡事状》,中华书局,2013年,第3499页。。塔出的身份与火斜、术思类似,“止系千户功臣之家,不同诸王、公主、驸马等族人”,塔出因在淮泗前线参与元朝平定南宋的战役,立有军功,所以曹州被赏赐给他作为封地。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平路获得封地的还有与黄金家族世代通婚的弘吉剌氏。上文中的按赤那颜即位弘吉剌部的按陈。《元史·察罕传》记载成吉思汗将弘吉剌氏的宫女赐予察罕②[明]宋濂:《元史》卷一二〇《察罕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2955页。,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将察罕纳入亲族之中。此后,察罕家族的部分家族成员也可能存在与弘吉剌家族继续通婚的现象。
自1274年曹州成为塔出的封地,直到1335年所立的必宰牙的墓碑,可证明该家族在元代至少定居曹州达六十年以上。
二、阐明了察罕家族的婚姻关系
《中书省右丞塔出夫妇墓碑》是塔出与妻子的合葬墓碑。塔出之妻,明初官修正史《元史》相关记载仅寥寥数字,谓塔出“妻明理氏,以贞节称,旌其门闾”③[明]宋濂:《元史》卷一三五《塔出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5页。;又柯劭忞《新元史》将“明理氏”改为“默哷氏”④柯劭忞:《新元史》卷一二六《塔出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84页。。柯书所录,或受清人改译元代人名的影响。“明理”(Mingli)是一个典型的蒙古语音汉译名,元人以此为名者,按《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统计有11人之多⑤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7年,第2473—2474页。,其中不乏元宪宗皇后明理忽都鲁(Mingli Qutulug)、元文宗时中书省平章明理董阿(Mingli Tungga)、翰林学士丞旨明理帖木儿(Mingli Temur)等蒙古贵族。因是,现当代学者多将塔出妻“明理氏”视作少数民族,甚至将塔出与明理夫人的婚姻视作唐兀人与蒙古人通婚的例证,谓“明理氏极有可能也是蒙古人……察罕一支男系都娶蒙古人上层为妻”⑥陆宁:《唐兀人察罕家族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105页。。然而,这种说法只是望文生义,并不正确。根据墓碑文,“明理”只是塔出夫人的名讳而非姓氏,她本来的汉姓刘氏,被《元史》的编纂者有意或无意的漏掉了。从“刘氏明理”的姓名来看,这位女性更有可能是一名西夏人或广义上的汉人(包括汉、契丹、女真等民族)。塔出与刘明理的婚姻,也更应视作元代西夏遗民族内婚姻或与汉人通婚的案例。
又据《元史》本传,塔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行省江西,寻以疾卒于京师”⑦[明]宋濂:《元史》卷一三五《塔出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5页。,即塔出去世约在1280年;而此合葬墓碑立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年代距塔出去世已有27年之久。碑文称刘明理为“节妇”,应是赞美她在27年间并未改嫁,为夫守节之事。与《元史》载明理“以贞节称,旌其门闾”亦能够互相应证。
关于必宰牙的婚姻,《元史》称其“妻伯牙伦,泰安郡武穆王孛鲁欢之女,亦守义有贤行①[明]宋濂:《元史》卷一三五《塔出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5页。”,与今泰安市岱庙藏《大元太师泰安武穆王神道之碑铭》载孛鲁欢第五女“适山东宣慰使必宰牙”相吻合。二者均未言及《中书右丞必宰牙夫妇墓碑》上位于必宰牙名讳右侧的“忽都罕夫人”。从墓碑刻文的位置来看,忽都罕夫人与伯也伦夫人的地位应该是平起平坐的,二人间并无正侧之分,可惜的是由于史籍无载,我们无法考察忽都罕夫人的生平。或许是因忽都罕夫人早卒,必宰牙方才娶伯也伦续弦。
此外,该墓碑还说明必宰牙之子寿童娶“完者”(亦蒙古人名)夫人为妻,联系必宰牙之女瑞童嫁与女真人粘合氏家族②[元]许有壬著,傅瑛,雷近芳校点:《许有壬集》卷五八《逸的氏墓志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43—644页。以及塔出娶汉姓女子刘氏来看,察罕后裔通婚对象的族属存在多元化特征,该家族在选择通婚对象时似乎更重视门第的高低。
在定居中原时期,察罕家族势必与当地其他民族产生深刻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产生汉化倾向,这一点在察罕家族的通婚对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塔出的妻子明理氏“以贞节称,旌其门闾”,必宰牙的妻子泰安郡武穆王孛鲁欢之女伯牙伦“亦守义有贤行”③[明]宋濂:《元史》卷一三五《塔出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5页。。必宰牙之女瑞童嫁与女真人粘合世臣,到瑞童和粘合世臣这一代时,察罕家族与粘合家族已联姻三代。粘合世臣死后,瑞童守节自誓。为了旌表她的贞节,朝廷初封瑞童为恭人,再封威宁郡君。她一方面“励节治家,坐亦有常处,田园经葺有加焉”,勤俭持家,经营自家的千亩田园。另一方面,她悉心教子,对禄童严格要求,她叮嘱禄童“先烈烜赫,继承不坠,责其在汝矣”,果然禄童不负所望。瑞童死后,禄童恰在京师,回来奔丧。禄童托其友陆恺所述其母的行实,请许有壬撰写墓志铭。许有壬认为自唐宋以来,“世变无常,风移俗易”,提倡贞节的遗风已经殄灭不存。而瑞童夫人的善行,可称之为女德的典范,瑞童也因为一人之品行,为乡人所称道④[元]许有壬著,傅瑛,雷近芳校点:《许有壬集》卷五八《逸的氏墓志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43—644页。。
三、补充了察罕家族成员的仕履和封赠
菏泽博物馆藏的两方西夏遗民墓碑中,一共保留了四条仕履信息,分别是必宰牙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任工部尚书,寿童于元统三年(1335年)任嵩州达鲁花赤,以及塔出墓碑中的“中书省右丞”和必宰牙墓碑中的“中书右丞”官衔。在这四条仕履信息中,前两则无疑是必宰牙和寿童确实曾出仕过的官职,可补正史之阙。而“中书省右丞”或“中书右丞”却存在疑点,似乎不是二人生前就任过的实职。
就塔出而言,他短暂的戎马生涯,几乎全在江淮地区与江西行省两地对南宋作战。除踏上仕途之前在大都侍奉忽必烈,以及去世前不久短暂入觐以外,塔出似乎并未长久留驻大都,乃至任职于中书省。再者,《元史》对其最高官职的记载也只是在至元十四年(1277)江西行省成立后,以“资政大夫、中书左丞、行中书省事”①[明]宋濂:《元史》卷一三五《塔出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4页。(即江西行省左丞)。又李治安先生论及“因蒙古俗尚右,故右丞位左丞之上”②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上),中华书局,2011年,第29页。,可知左、右丞间虽品级相同,却仍有职权高下之分,墓碑之书写不应僭越。又如必宰牙,《元史》载其“仕至征东行中书省左丞”;其女瑞童之墓志则云“父必宰牙,辽阳行省右丞”,该墓志成文于至正四年(1344年),而必宰牙至迟已于元统三年(1335年)逝世,故而志文所书“辽阳行省右丞”,应是必宰牙生前最高官职。如若“中书右丞”是必宰牙生前的实职,为何《元史》与《瑞童墓志》均不载?
笔者认为,两方墓碑上“中书省右丞”和“中书右丞”前,应省略了“追赠”二字,之前学界所知元朝对察罕家族的封赠,仅有察罕本人“赠推忠开济翊运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河南王,谥武宣”以及察罕长子木花里“赠推诚宣力功臣、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武毅”两例③[明]宋濂:《元史》卷一二〇《察罕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2957页。。塔出与必宰牙的墓碑,虽然只记载了赠官,而未记载元廷追赠予他们的功臣号、王号和谥号,但也是证明察罕家族在元代深受蒙古族统治者宠幸,享有较高政治地位的注脚。
1227年,西夏末帝李投降蒙古,旋即被杀,这标志着与宋、辽、金鼎足而立的西夏王朝结束了近190年的统治,屈服于蒙古大军的铁蹄之下,而后西夏皇族在浩瀚的史籍中湮没无闻。菏泽出土的两方元代西夏遗民墓碑将曹州确定为西夏皇族后裔在元朝的迁入地。察罕家族传至必宰牙时虽历经四代,但该家族凭借在察罕一代就已建立起的政治资本和之后该家族成员为平定南宋以及战后的治理过程中立下的功绩在元朝的地位依然显赫。与此同时,察罕家族通过与弘吉剌氏、忙兀氏孛鲁欢、粘合氏等家族联姻的策略,不断扩大政治影响,从而保证了家道不辍,瓜瓞绵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