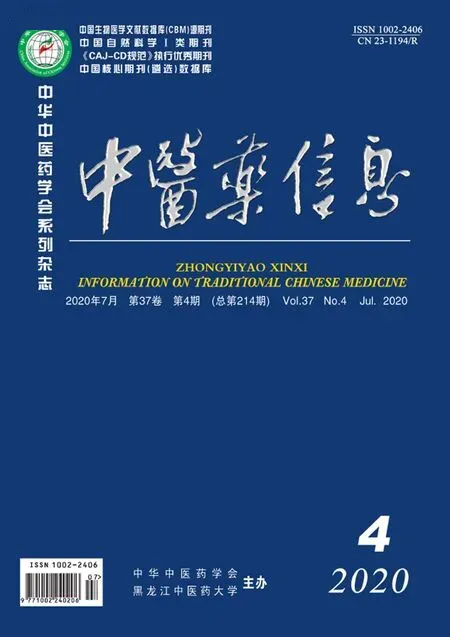潘洋教授从标本论治溃疡性结肠炎临证经验
吴屹波,潘洋,陈铭佳,邵淑慧,巩淑萍
(1.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6,2.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溃疡性结肠炎系一种原因不明的结肠黏膜和黏膜下层连续性炎症,常累及直肠[1],在国外,其最高患病率分别为欧洲505/10万,加拿大248/10万和美国214/10万,且发病率和患病率存在地区差异,城市地区高于农村[2]。在我国,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3]。目前研究认为,其发病多与遗传因素、免疫异常、炎症介质生成增多、神经精神因素、变态反应、感染及肠道菌群失调与发病关系密切,病情反复缠绵,有恶变趋向。治疗主要以抗感染、免疫抑制剂及调节剂、激素类药物为主,尚无理想的药物与治疗方法。
潘洋教授,黑龙江省名中医,二级教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带头人,全国六批师承指导教师,从医30余载,强调“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标本同治”,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笔者有幸随潘洋教授临诊,受益良多,将经验总结如下。
1 审证求因分标本
中医学中并无溃疡性结肠炎之名,依据其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里急后重等临床表现,可归属于“痢疾”“久痢”和“肠澼”等范畴[4]。该病最早记载于《黄帝内经》,《素问·太阴阳明论篇》曰“饮食不节,起居不时,则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 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曰:“太阳司天之政,四之气,风湿之争,民病注下赤白。” 在《金匮要略》中更将其病机责之为“以有热故也”。潘洋教授指出此病以泄利无度,便下脓血为主要症状,但病机虚实夹杂,临证之时当审明病机,分清标本,勿犯虚虚实实之戒。
1.1 标实
1.1.1 大肠湿热利不止
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虽有四时六气之不同,但湿热蕴结大肠仍为本病的癥结所在。其成因或由外感湿热、疫毒之邪,伤及胃肠,运化失司,湿热郁蒸,相互搏结,阻滞气血运行,蕴热成毒,热迫肉腐,化为脓血,发为痢疾,故《沈氏尊生书》有云:“大抵痢之病根,皆由湿蒸热壅,以致气血凝滞,渐至肠胃之病”;或由饮食所伤,过食肥甘酒炙,进食不洁之物,致湿热内结,血液瘀滞,化为脓血,则成湿热之痢。朱丹溪论述为:“赤痢乃自小肠来,白痢乃自大肠来,皆湿热为本……”,“皆由肠胃日受饮食之积余不尽行,留滞于内,湿蒸热瘀,郁结日深,伏而不作,时逢炎暑……又调摄失宜,夏感酷热之毒,至秋阳气始收,火气下降,蒸发蓄积,而滞下之证作矣。”
1.1.2 血络受损疡难平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其功以通为用,以降为顺。湿热之邪阻截于肠道,大肠传化失司,必然影响及大肠血脉的流通,继而造成大肠局部的气血瘀滞,日久郁而化热,或与湿热相搏,使湿热等邪气留滞固着难去,反复发作;病邪与瘀血相搏结,致血络破损益甚,形成内疡,瘀血不去,新血不生,肌肉不长,疮疡不敛,局部组织病理损害进一步加重。在肠镜下可见病变区域黏膜有充血、出血点、糜烂、溃疡等;粪便检验可见到红细胞等。
1.2 本虚
1.2.1 脾肾亏虚证迁延
潘教授认为该病的发生是在脾肾虚弱的基础上,感受外邪、饮食不慎或忧思恼怒引起大肠传导失常,气机不畅,损伤肠膜脉络而发病。正气亏虚是该病发生的前提,久病及肾,脾肾亏虚日益严重,病情反复发作,所以在本病的后期多见正虚之象。李中梓的《医宗必读·痢疾》中提及“愚按痢之为证,多本脾肾,然而尤有至要者,则在脾肾两脏。……是知在脾者病浅,在肾者病深,肾为胃关,开窍于二阴,未有久痢而肾不损者,故治痢而不知补肾,非其治也。”《景岳全书》亦有:“凡里急后重者,病在广肠最下之处,而其病本则不在广肠而在脾肾”的论述,“脾肾虚弱之辈,但犯生冷极易作痢”,“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
1.2.2 阴阳并损邪难除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血阴阳共同构成人体的正气,气之与血、阳之与阴互根互用,相互转化,维持着人体机能的平衡。该病病程日久,下利无度,或治疗失当,徒耗正气,致使气虚统摄无权,血逸脉外,进而血虚无力载气,气随血脱,长此以往,气损及阳,血损及阴,阴阳并损,精气内夺,积损成劳,正气无力御邪,邪气胶着,如油入面,则更加难以驱除。
2 论治权衡别虚实
潘教授认为在认识本病病机特点之上,进行辨证论治,湿者利之,热者清之,湿热蕴结是溃疡性结肠炎的癥结所在,故清热利湿为本病的主要治疗法则,且湿属有形之邪,其性黏滞,与热邪胶结,灼伤血络而致出血,每致瘀血,而疮疡不愈,针对病机又当凉血、活血、止血生肌以愈内疡,同时针对正气之亏虚,权衡虚实之轻重加减治疗,更为贴切。
2.1 清热利湿
针对大肠湿热,潘教授常选用白头翁、青黛、黄连、黄柏、马齿苋、败酱草等药物加减治疗,白头翁功能清热解毒、凉血止痢,且苦能燥湿,本品苦寒降泄,专归大肠经,善除大肠热毒蕴结而凉血止痢,《药性论》记载其有“止腹痛及赤毒痢”之功,为治热毒血痢里急后重之良药,经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其具有抗氧化、抗炎、提高免疫力的作用[5];青黛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之功,《本草逢原》谓其“泻肝胆,散郁火,治温毒发斑及产后热痢下重”,《本草求真》中云:“青黛,大泻肝经实火及散肝经火郁”,清热之效甚捷;黄连、黄柏、马齿苋、败酱草均以清热利湿见长。
临证之时,潘教授时常告诫同为大肠湿热,亦有湿热并重、湿重热轻、湿轻热重之别,结合患者四诊,尤以舌脉为重,判断湿热之进退,以指导组方用药;选用药物时,一方面通过调整药味组成,一方面调整药物用量,使所拟方药切中病机,方能增强疗效。
2.2 扶正固本
对于脾肾亏虚的病机,选取党参、黄芪、白扁豆、补骨脂、肉豆蔻、砂仁等药物。党参味甘,性平,具有补中益气、止渴、健脾益肺、养血生津之功,现代研究表明含有糖类、三萜类、甾体类、生物碱类、木脂素类及黄酮类等多种化合物,具有健脾作用,可以治疗脾胃虚弱等症,这可能和党参具有调节胃收缩、保护胃肠道黏膜及抗溃疡等药理作用有关[6];黄芪具有益正气、壮脾胃、排脓止痛等的功效。现代研究证实黄芪的免疫调节作用主要依赖于黄芪多糖及黄酮类化学成分,而黄芪多糖可多途径刺激免疫系统,并促进干细胞活化,促进机体免疫细胞尽快分化,并可起到心肌、肝、肺、肾、脑等的保护作用[7]。对于正虚严重患者出现“五更泻”或者泻下无度,日行大便10余次者,酌情选取四神丸、参苓白术散、桃花汤等方剂加减治疗。
2.3 久病入络
潘教授认为溃疡性结肠炎虽然表现出便下鲜血的症状,其发生因素有湿热之邪迫血外溢之病机,但亦有久病入络之瘀血阻滞,血不能正常循行于脉络之机,故遣方用药不可过于胶结湿热,一味清热利湿,而忽略活血化瘀。现代研究证实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内镜下可见肠道黏膜血管的纹理模糊、紊乱或消失,严重时出现黏膜的出血和溃疡形成[8],故于临床治疗时酌加三七,地榆、槐花、香附、丹参、桃仁、鸡血藤等止血、化瘀、通络等药物。
2.4 止利勿过
对于溃疡性结肠炎反复发作且腹泻次数较多患者,潘教授常选取诃子、赤石脂、五倍子等收涩的药物,但同时指出“止利勿过”,其含义有二方面:一方面为止利勿早,避免一见泄泻即予涩肠止泻之剂;另一方面为止利勿过度。潘教授认为本病有别于病机单纯的泄泻,虽然病机以脾肾亏虚为主,但大肠湿热伴随其中,湿热之邪易阻滞气机,若止泻过早或者止泻过度,都会导致实邪留滞,闭门留寇,临床根据实邪之进退,加入木香,青皮,枳实等消导之品,取“通因通用”之意。
3 典型病例
患某,男,56岁,哈尔滨市,2018年2月1日初诊。主诉脓血便反复发作三年余,加重1周。三年前因进食辛辣食物并劳累后出现腹痛、腹泻伴有鲜血等症状,自服黄连素等止泻药病情缓解,其后症状反复出现,再服前药无效,检查肠镜示:溃疡性结肠炎,曾应用柳氮磺胺吡啶等药物,症状时常反复,1周前出现诸症加重。现症见泻下赤白,夹有黏液,日5~7次,乏力,口干苦,舌质红,苔黄腻,脉数略细。经四诊合参,中医诊断:泄泻(肠道湿热,血热妄行)。治法:清热利湿、凉血止利。组方:白头翁 20 g,秦皮 15 g,黄连 15 g,黄柏20 g,白芍 20 g,生甘草 15 g,生地榆 20 g,槐花 20 g,仙鹤草 20 g,木香 10 g,生薏苡仁20 g,三七 5 g,太子参 10 g,炒白术 20 g。上方7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温服。
二诊,服药后,大便中脓血减轻,时有黏液,每日3~5次,口苦减轻,乏力改善,舌质红,苔略黄腻,脉数略滑。上方中减白头翁、黄柏为15 g,加入鸡内金30 g,神曲15 g。15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温服。
三诊,服药后,大便脓血偶作,无黏液,日1~3次,不成形,无乏力,纳食较前增加,时有晨起口苦,舌质转淡,苔略黄,脉数。上方中加入茯苓10 g,白扁豆 15 g。15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温服。
四诊,大便无脓血及黏液,大便每日1~2次,成形,纳可,精神佳,小便时黄。继服上方加入佩兰10 g。30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温服,以巩固疗效。
按语:本例患者发病之初由于劳累伤气,加之进食不适,致湿热之邪内陷大肠,兼有治疗失宜,而病作。经长期治疗,未能去除湿热之邪,病情由急转缓,湿热之邪盘踞难以速去,并见热迫血络之征,血去阴伤,脉数中略细,故参标本之主证,拟清热利湿,凉血止利之法,白头翁汤清热利湿止利,芍药甘草汤缓急止痛,地榆、槐花、仙鹤草凉血止血,三七、木香行气血之滞以止血,生薏苡仁、炒白术利湿,增强止利之功,太子参兼顾阴虚。二诊随湿热略轻,而积滞增,略减轻清热利湿之力,加入鸡内金、枳实以消导祛邪。三诊之后邪热渐攘,脾湿渐增,配伍茯苓、白扁豆、佩兰以健脾利湿。依法调整,随证治之,切中病机,可期佳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