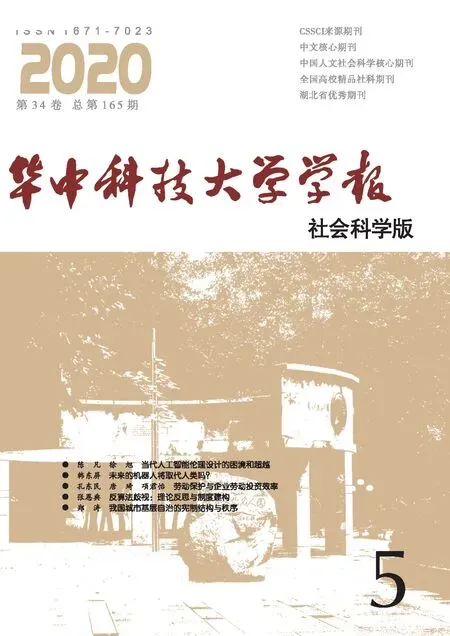“公众”的界定、识别和选择
——以美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经验与问题为镜鉴
□张晏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9月1日起施行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简称《暂行条例》)细化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决策机制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对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五大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进一步予以规定。其中,公众参与位列五大法定程序之首,体现了民主决策原则,是程序正当性和行政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在各类行政决策中,由于科学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环境决策常常需要决策于未知之中,且因涉及价值判断,必须通过公众参与来增强其决策的正当性。《暂行条例》第3条将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纳入决策的事项范围,具体到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程序中,公众参与更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即所谓“环评如果没有咨询和参与就不能称之为环评”[1]。可以说,目前环评中的公众参与代表了我国公众参与的最高水平[2]。然而,从我国环评公众参与的实践来看,由于“谁来参与”“何时参与”“如何参与”“参与的效力”“信息公开”以及“法律责任和救济”等方面的规则尚存不足,一些公众参与沦为形式化的事前参与或非制度化的事后参与,从而催生了大量群体性事件②2012年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该项目通过发放千余份调查问卷的方式征求过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公众的意见,进行了环评报告公告,通过了原环境保护部的审批,形式上满足了所有程序性要求,但事后仍然引起民意的极大反弹。参见左林,李微敖.什邡失措:政企忽视民意引公众焦虑致企业损失[EB/OL].(2012-07-16)[2020-06-10].https://business.sohu.com/20120716/n348284788.shtml.。
其中,“谁来参与”是公众参与程序设计中首先应当界定的问题。这一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复杂,对此《暂行条例》并未予以界定。现行环评立法对公众“有关”和“可能受影响”的抽象描述也难以为公众的认定提供明确依据,决策者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完全可以不着痕迹地刻意选择符合自己利益或政策目标的公众来操纵公众参与的结果,环评机构和建设单位甚至在“公众”上弄虚作假,从而轻易地通过后续层层的形式检验①例如,2017年金麒麟旗下全资子公司济南金麒麟刹车系统有限公司新增“高性能刹车盘涂装项目”环评报告书中,参与调查的公众中有数十名是公司内部员工,且不在调查范围内小区居住。参见李超.金麒麟子公司环评涉嫌造假公众调查员工参与[EB/OL].(2017-03-16)[2020-06-10].http://www.sohu.com/a/129056570_433524.。针对这一现象,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针对建设项目环评以公众提交意见表的方式替代易被操纵的问卷调查,将公众参与的主动权交给公众,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认定“公众”的难题。由于对公众范围增加了“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界定标准②《办法》第5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鼓励建设单位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法定公众的范围狭窄,严重限制了公众参与功能的发挥。同时,关于公众代表选择规则的规定过于原则和单薄③对于如何选择公众代表,《办法》仅在第15条第二款中规定:“建设单位应当综合考虑地域、职业、受教育水平、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程度等因素,从报名的公众中选择参加会议或者列席会议的公众代表,并在会议召开的5个工作日前通知拟邀请的相关专家,并书面通知被选定的代表。”,仍然给刻意选择和肆意造假留下了巨大空间。此外,法院仅对公众参与进行形式审查,在公众的认定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④例如,在2015年伍权、陈权、黄用诉湛江市环境保护局一案中,原告诉称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没有依法调查附近村庄、村民,没有征求村民的意见。报告所述调查了17个单位、250人是虚假的。法院对此并未进行实质审查,认为湛江市环境保护局在湛江市环境保护公众网对受理信息进行了公告,公开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简本,公告期限为10个工作日,公告期间被告没有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参见(2015)湛开法行初字第31号行政判决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符合其他所有程序要求,公众参与机制也只具有形式意义,无法真正发挥其效用。
众所周知,环评制度起源于美国,在联邦机构环境决策中增加公众参与的要求始于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简称NEPA)。该法不仅创设了环评制度,而且在环评程序中嵌入了公众参与的概念[3]。在后续实施中,“公众”的界定得以不断明确,并逐步建立识别特定公众和选择公众代表的一系列规则。本文的核心目的正是通过考察美国环评公众参与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总结和分析美国在“公众”认定上的经验得失,旨在为我国相关规则的完善提供有益的思路,从而有助于我国公众参与实效的提升和行政决策合法性的达成。
二、公众的概念与制度逻辑
(一)公众的概念共识:“感兴趣的人”和“受影响的人”
虽然“公众”在环评著述中反复出现,“公众”(public)、“公民”(citizen)、“利害关系人”(interested party)、“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等用语常交替使用,但很少有学者专门给出其定义。在试图回答“谁应当参与”这一问题时,在美国,广泛的共识认为“公众”是对某一决策感兴趣(interested in)或者受到该决策影响(affected)的任何人[3]。对公众的这一界定至少可以追溯至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4]118。杜威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公众及其问题》中使用了对决策感兴趣和被影响的人来界定“公众”[5]。与之相应,美国的环评立法虽未明确界定“公众”,但在表述时特指对决策“感兴趣和受影响的人”。
根据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简称CEQ)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实施条例》(Regula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Procedural Provisions of NEPA,以下简称CEQ条例)⑤NEPA设立了环境质量委员会以实现该法的功能。CEQ为联邦机构执行NEPA的程序规定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实施条例》。,环评中的公众参与分布于《环境评估》(Environmental Assessment,简称EA)的准备⑥40 C.F.R.§1501.4(b).、《查无显著影响报告》(Finding of No Significant Impact,简称FONSI)的公布和评议⑦40 C.F.R.§1501.4(e).、《环境影响报告》(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简称EIS)的范围界定⑧40 C.F.R.§1501.7(a)(1).、EIS草案提交公众评议⑨40 C.F.R.§1503.1(a).,以及最终EIS对公众评议的响应⑩40 C.F.R.§1503.4.等多个阶段。
其中,CEQ要求各机构在环评的早期对备选方案进行“范围界定”(scoping),以确定公众希望在评价中看到哪些问题,并明确提出邀请受影响的联邦、州和地方机构、任何受影响的印第安部落、行动的拥护者以及其他感兴趣的人(包括基于环境理由可能与行动不一致的人)参与⑪40 C.F.R.§1501.7(a)(1).。CEQ还要求各机构在编制EIS草案和编制最终EIS之前应当征求可能感兴趣或受影响的个人或组织的意见⑫40 C.F.R.§1503.1(a)(4).,以及提供与NE-PA有关的听证会、公共会议和环境文件的公告,以便通知可能感兴趣或受影响的人和机构①40 C.F.R.§1506.6(b).。
之所以要求邀请或通知感兴趣或受影响的群体,是因为公众有时并不知道他们感兴趣或可能受到决策的影响。但是,即使公众收到邀请或通知,也可能没有参与程序所必需的手段、能力或者信任水平[6]88。因此,CEQ条例特别规定联邦机构应当最大限度地鼓励和促进公众参与影响人类环境质量的决定②40 C.F.R.§1500.2(d).。为实现这一要求,各机构除了有义务通知外,还有义务为公众参与提供便利,必要时提供资金。例如,美国环境保护署(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被授予拨款来提供资金赠予非营利组织以支持和鼓励其参与③42 U.S.C.§4368.。显然,邀请、通知、鼓励和促进公众参与环评的一系列规定隐含着参与公众“越多越好”的价值取向。
(二)公众的制度逻辑:信息规制
实际上,参与公众“越多越好”的理念背后是由环评本身的制度逻辑和公众参与程序的目的与功能决定的。NEPA诞生于相信官僚综合理性的时代[7]。环境决策应当建立在充足信息的基础上,要求各机构在提出一项计划时慎重考量此计划实施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其他替代方案,相信一个机构在拥有了充足信息的条件下会作出正确的决策[8]。同时,由于多元的公众代表了不同的事实、知识、利益和价值,这为实现充分的信息获取和交流提供了基础。公众可能拥有决策所需的更完整的信息并能得到精确权衡,经过公众参与和协商作出的决策可以被期待为更具理性、更有效率[9],同时也能避免事后的无序参与和争议。促进知情的决策和促进知情的公众参与是NEPA的两大目标④40 C.F.R.§ 1500.1(b),(c).,这两大目标构成了环评公众参与程序的设计初衷。
因此,“公众”的概念在美国的环评中是被有意地宽泛使用,在“谁应当参与”这一问题上,立法以“感兴趣和受影响的人”来宽泛界定“公众”,并要求联邦机构邀请、通知、鼓励和促进各方参与和协作,目的其实是试图通过信息规制(informational regulation)⑤关于信息规制的概括、形式、示例等,参见Cass R Sunstein.Informational Regulation and Informational Standing:Akins and Beyond[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99(147):613-675.而不是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或者市场手段来提升环境决策的理性和正当性。这种以吸纳各方参与环评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在美国更加开放和怀疑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规制机构拥有有限的公众信任,显然错在参与范围太广而不是太窄要更为明智[6]87。正是基于这些考虑,鼓励最大限度的参与成为环评公众参与的应有之义。
三、公众的异质与类型
宽泛界定之下的公众并非同质(homogenous)的实体[3]。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对公众的描述充分体现出这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该委员会认为公众一般指的是既扮演公民角色又作为“感兴趣和受影响的人”的正式代表——可能获益或受损,或者选择知情和参与环境决策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可能包括特定的种族、儿童、受影响的社区、职业类别或其他类别的个人、群体或组织,也包括在传统的政策论坛中没有得到充分代表的弱势群体;既包括公司、非营利咨询或者游说组织、协会,也包括公共官员、机构、作为个人或者代表组织的科学家[4]15。公众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处的不同地位,存在的不同形式,以及具有的不同知识和观点,也体现在他们所代表的不同利益和关注的不同损害,不仅是死亡率和发病率,也包括身体、社会、经济、生态和道德等各方面的影响[6]80。基于公众的异质性,上述委员会将公众区分为利益相关者、直接受影响的公众、留心公众和一般公众四个类型[4]15。
(一)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是指被影响或者将要被影响、或者对于决策结果有着浓厚兴趣的组织化的群体。在美国,常将“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画上等号。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包括对决策感兴趣和受影响的任何人[10]7。但是,组织化的利益团体⑥利益组织化,是指在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一些分散的利益主体基于其利益的基本一致性而进行联合,并以一定的组织结构约束这种联合的状态。参见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221.和非组织化的个人显然在参与机会、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参与效果等方面均具有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有学者将狭义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为在决策进程中有组织的利益团体或其代表,而与公民个人区分开来[11]。经过组织化的方式对个体利益诉求进行内部的过滤和协调,可以使得利益表达更加集中、有力,因此也更有可能对决策产生影响[12]。
组织化群体的突出代表是环保组织,这是美国环评公众参与当中最重要的公众类型,特别是当环境决策涉及事项的规模较大时,常有赖于环保组织的参与。例如,对于具有全国性关注或影响的活动,CEQ条例要求机构应当在联邦公报上公布并且邮寄给合理预期为感兴趣的全国性的组织,制定规则的机构可以向要求定期提供该公告的全国性组织邮寄公告,并且保存此类组织的名单①40 C.F.R.§1506.6(b).。
(二)直接受影响的公众
通常来说,只关注狭义的利益相关者就足够了,但是对于一些议题,审议需要更广泛深入,美国的实践表明不应忽视那些在决策问题上享有利益却没有正式组织起来的市民,否则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13]49。直接受影响的公众是指将会体验到决策结果带来的正面或者负面效果的个人和非组织化的群体,这类公众更符合通常理解中“公众”字面上的含义。从工具意义上说,使用参与程序将利益相关者和其他类型的公众包含进去,可以确保程序不会被没有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组织化的利益所俘获[4]15。
但问题是,环境要素的特性不同,环境问题的影响范围迥异。例如,有毒物质污染距离场所较远的公众可能就不受影响,而对于空气污染,由于空气的流通,确定受影响的公众相当困难[14]。由于环境问题边界不明,环境决策事实上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发生在特定地点的环境问题可能具有超出地方的深远影响[3]。因此,CEQ条例中的国家/地方二分法被打破,是否受到影响、受到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的判断绝非易事,如何确定谁是“直接受影响的公众”必须结合决策的特定情境予以具体判断。
(三)留心公众
留心公众是指可能对议题发表评论而影响公众意见的媒体、文化精英和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在信息化时代,留心公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无处不在,同时对其他公众的影响力无可避免。公众常基于来自媒体或者专家的二手信息形成对有关风险的技术和活动的态度和立场,并且有时会被机构或者其他公众利用以扩大其影响力。因此,即使是留心公众间接参与也往往具有实质性影响。在某些场合,留心公众的直接参与是必需的,甚至是主要的。例如,当风险的特征呈复杂性②有些风险结构简单,损害的可能性很好理解,风险(以及减少风险的措施)并无争议,这些被称为线性风险(linear risks)。所有其他类型的风险都是复杂性(complex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组合。复杂性风险是指原因和结果间的关系受到很多干预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指的是因果关系链条的判断不足以确信,而模糊性则产生于个体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对于与风险相关的事件的输入和结果出现争议时。关于风险的特征,参见Ortwin Renn.Stakeholder and Public Involvement in Risk Governa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 2015, 6(1):8-20.时,争议往往与关于复杂的剂量-反应(dose-effect)关系或减少脆弱性措施有效性的重大科学分歧有关。此时,参与主体应当包括来自不同科学阵营的专家,将新知识或额外的知识引入协商,需要经由专家小组、专家听证等达成专家共识[15]。但是,留心公众基于自身的发现、认知和社会信念有时会相当偏颇,决策者应当充分重视留心公众在信息公开、风险识别和风险沟通中的巨大作用[16]。美国的实践表明,同行评审有助于增加客观性和减少偏见。
(四)一般公众
除了上述三类主体,在美国的实践中还特别强调一般公众的地位和作用。一般公众是指没有受到议题直接影响但可能对此发表公众意见的所有个体,一般很少被纳入参与过程。但是美国环境保护署科学咨询委员会(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Science Advisory Board)认为当根据现有的科学证据最终只能作出价值判断时,要想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应当让所有相关方的代表包括一般公众共同公开地澄清存在共识和分歧的领域、理解和应用相关科学,并就如何最好地处理环境问题达成一致[10]6,尤其当风险的特征呈模糊性时,不再只是涉及有关风险的争议,还包括对未来的看法、基本价值观和信念之间的差异,以及对人类控制自身技术命运能力的信心程度。因此决策应当面向公众公开,要求最为广泛的参与,也应包含一般公众代表[15]。
需要指出的是,环境问题往往源于公地(commons-based),涉及大量不同的利益,个人可能甚至都没有认识到其利益受到了威胁[14]。同时,一般公众虽然可能不会受到环境决策的直接影响,但作为公民必将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注意力的发展而成为对决策感兴趣的人[10]7。因此,一般公众、利益相关者以及直接受影响的公众的区分是模糊的。也正是基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美国环评公众参与的设计对“公众”的认定更多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当然,对于公众类型进行划分是有意义的,决策者能够根据特定决策所涉事项规模、环境要素特性、环境风险特征等因素对不同类型的公众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
四、公众的代表性与选择策略
即使在具体决策中侧重某些特定类型的公众,决策者仍需面对数量庞大的潜在参与者。关于NEPA有效性的研究表明,机构在具体确定谁是公众这一问题上并不成功[17]。如何在具体决策中将抽象的“公众”予以具体化,如何保证参与公众的代表性是决策者面临的巨大难题。
(一)选择公众代表的必要性——包容性原则的不足和不能
CEQ条例并未针对合适的参与人数或者何谓“最大限度”的参与作出限制[18]。基于环评的制度逻辑和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一般认为当公众参与包含感兴趣的和受影响的所有人时会更加成功。这种包容性(inclusiveness)被认为是环评公众参与程序应当贯彻的原则之一[4]3。但事实上包含太多的主体可能会产生负面的结果。
一方面,就成本和时间而言,如果决策者努力容纳尽可能多的意见,就可能产生最低公分母(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的解决办法,使得公众参与程序繁琐且效率低下[14]。这与异质性和相互依存度(interdependence)有关。异质性很高、相互依存度很低表明组织规模会阻碍合意的形成,此时参与者数目多,沟通效率越低,交易成本也就越高。对NEPA的批评之一就是该法通过延缓决策来阻碍联邦机构的决策,这会给行政机构履行法定职责的能力带来负面影响[7]。另一方面,公众的异质性使得“公共”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有学者认为甚至不存在公共利益。公众中的不同成员具有不同利益,导致对参与具有不同的期望。被允许参与的个人和组织越多,就越难以满足他们不同的期望。反过来,被辜负的期望将导致挫败感,最终削弱公众参与环评的意愿[3],反而会有损决策的质量。
除了考虑决策质量和效率的要求外,实际的参与过程也对选择公众代表提出了需求。实践中,决策者在满足立法所规定的最低公众参与要求基础上还会进一步加强与公众的互动,除了对所有公众开放的通知和咨询外,还会以审议式民意调查(deliberative polling)、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s)、联合事实调查(joint fact-finding)等方式与公众代表进行更密切的合作甚至达成协议[19]。另外,即便拥有足够的人力财力考虑和回应所有公众的意见,有时也可能根本无法实现包容性原则的要求。并非所有公众都能够或者想要参与,因为可能没有时间、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20]32。有时会存在直接参与不能的情形,例如儿童、残疾人士等弱势群体,还可能包括未来世代,非人类种群和生态系统。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利益代表间接参与可能是唯一的选择[6]88-89。
可见,虽然美国相关立法和理论都以包容性原则为主导,但是实践中选择公众代表成为一种必然,而如何识别公众并且对其代表进行选择仍缺乏明确和系统的规则。
(二)特定公众的识别方法——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
在美国的实践中,决策者可以综合运用由其引导的自上而下法和来源于公众的自下而上法来识别特定的公众[13]48。在邀请和通知关键公众时可以运用自上而下的技术方法,通过考虑下列问题识别特定的感兴趣和受影响方:谁拥有有益的信息和专长?谁之前曾经参与过类似的情境?谁之前曾经想要参加类似决策?谁可能受到影响?谁可能受到影响但却不知道自己会受到影响?如果不被包含在内谁将合理地被激怒[6]88?美国EPA发布的《公众参与指南》提供了更为详尽的问题清单①美国EPA发布的问题清单,参见EPA.Public Participation Guide[EB/OL].(2018-02-22)[2020-07-07].https://www.epa.gov/international-cooperation/public-participation-guide-process-planning#step2.来帮助识别特定的利益。该清单包括谁将受决策直接影响?是否有部分社区会因为该项目而承受不成比例的负担?谁将受决策间接影响?谁想参与?关于该议题,谁已经参加或者联系过决策者?如果对决策没有输入(input),谁将感到失望?谁能够影响决策?谁能够主张具有受到决策影响的法律上的资格(法律权利)?……近二十个问题,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后,将会形成一个全面的公众名单。随着更多公众被决策者识别,更多公众对决策变得感兴趣,该问题清单也将随之不断增加。
除了自上而下法,还可以适用来源于公众的自下而上的进路,即由公众识别自己,决策者通过吸引公众的持续参与来动态地进行公众的界定和辨别[13]51。这一方法体现在CEQ条例对于公众听证会、公共会议和公共通知的规定中。从理论上说任何想参与的公众都可以参与,可以有效弥补自上而下法不可能预先识别出所有相关群体的局限。为了帮助关心联邦决策环境影响的公民和组织有效参与根据NEPA进行的环境审查,CEQ发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公民指南:让你的声音被听见》①具体内容,参见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A Citizen’s Guide to the NEPA:Having Your Voice Heard[EB/OL].(2011-07-28)[2019-08-13].https://www.energy.gov/sites/prod/files/nepapub/nepa_documents/RedDont/G-CEQ-CitizensGuide.pdf.,对环评程序进行了详细介绍,特别介绍了公众参与的时机和方式,包括如何主动参与和进行评议,以及在机构没有给予公众充足参与机会时应当采取的措施,包括及时提出意见,主动和决策者联系,寻求相关机构的援助,以及寻求行政和司法救济等,这为公众的主动参与提供了指导。
但问题在于决策者对于公众的识别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立法的要求,这实际上具有广泛的裁量空间。对机构根据NEPA作出的决策,司法审查限于该机构是否按照严格解读NEPA的程序要求并对拟议行动进行了“严格检视”(hard look)②Bering Strait Citizens for Responsible Res.Dev.v.U.S.Army Corps of Eng’rs, 524 F.3d 938, 947(9th Cir.2008).,即使“严格检视”规则要求法院对机构行为作出“全面、彻底、深入的审查”,确保该机构“严格检视”与其最后决策有关的资料,但是法院毕竟不得对机构决策的实质性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或“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插嘴”③Citizens to Preserve Overton Park, Inc.v.Volpe, 401 U.S.402, 416(1971).。例如,在Ark Initiative v.Tildwell一案中,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就原告是否属于“感兴趣的人”,机构是否应当亲自邀请原告参加行政程序进行了审查。法院认为“在所引用的条文当中,没有任何规定要求机构在有关NEPA的规则制定程序中个别地通知任何和每一个潜在的‘感兴趣的人’”。法院通过审查行政记录认可相关机构在促进公众参与时所付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并断言“很难看出任何对规则制定感兴趣的个人或组织会错过参与的机会”④64 F.Supp.3d 81(D.D.C.2014).。这种审查密度使得机构以卷帙浩繁的行政记录作为规避良方,既很难对其予以实质限制,也使得效率更为低下。
(三)公众代表的选择策略——自我选择、选择代表和抽样技术
在识别特定公众的基础上有时需要进一步选择公众代表。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提出选择公众代表时需要考虑四个关键要素:参与是充分广泛的;选择过程是公平的;代表人能够被其所代表的感兴趣和受影响的人接受;参与者带来的知识、经验、观点为审议所需要[6]89。这些要素看起来是明确的,但是如何满足却相当困难。选择公众代表通常的策略包括自我选择、选择代表和抽样技术[21]352,但这三种策略均存在一定局限。
其中,自我选择对应着识别公众的自下而上法,是美国听证和通知评议规则制定中的标准程序。这种方法看起来为公众提供了广泛且公平的参与机会,但实际上却可能存在某些局限。首先,自我选择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参与者自身的反应和能力,因此有利于组织化的利益和那些拥有足够资源来搜集通知、动员组织成员、提交评议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的人[6]90,可能会不适当地低估甚至忽视重要但没有能力的参与者,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被影响的潜在参与者。其次,该方法预设所有关注自身利益的人都会参与,主动权掌握在公众手中,这可能导致参与者人数太少,无法完成必要的任务,或者人数太多,无法很好地进行互动的现象[20]34。
第二个策略是选择代表。公众参与的代表性越强,参与的有效性就越大[22],但问题是谁来决定以及如何决定谁能代表公众。当公众参与过程被用作决策工具时,必须确保所有相关的利益以充分和平衡的方式得到代表[10]13。这正是选择代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至少有四种类型的代表:选举代表(正式政治代表);任命律师或其他专家(归属代表);根据他们与所有或部分相关方的共同特征选择参与者(描述性代表);根据其特定观点选择参与者(实质性代表)。前两种代表形式在政治制度中是传统的类型,对于公众参与机制而言,后两者往往是合适的,但很难说哪种更好[20]33。公众在时间、资源、受教育程度、表达愿望和看法的能力上大相径庭,这使得描述性代表很难保证代表具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能力。实质性代表则可能仍然会导致非组织化或者沉默的公众包括未来世代无人代表,而是偏向于占支配地位的参与者,例如专家、官员、利益集团,这也导致代表的不是更广范围的公众而是有一些极端的观点[23]。
第三个策略是利用样本技术,这也是选择描述性代表的常用方法。理想状态下,随机抽样能够确保受影响人群的所有价值和偏好能够平等地进入程序[21]353。但是随机抽样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在小型群体中随机抽取可能很难公平地反映出利益范围,样本规模必须足够大;二是随机抽样假定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发言权,但有时需要考虑特殊的群体,例如儿童;三是随机抽取的个体可能因兴趣、参与时间、理解议题的能力等不同,导致有些群体比其他群体可能得到更好地代表[6]90。此外,由于影响未必平均分布,在随机抽样中没有被选择但却受到直接影响的人可能会感觉被剥夺了保护自身利益的基本民主权利,结果可能会寻求其他方式发声。而随机抽样出的代表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责任感,态度是否会在参与中发生改变都会影响参与的效果[21]354。
如何选择适用这三种策略,与决策的质量和正当性的考虑有关。关注正当性的学者倾向于建议通过公开邀请或者通过代表,使已经组织化或者如果反对决策将组织化的相关方参与。关注决策质量的学者则认为应当让所有重要观点和知识来源都得到代表[4]119。同时,由于这三种策略各有其弊端,在美国的实践中,会针对特定决策权衡各策略的优点和局限综合加以运用。例如,运用自我选择策略后通过内部协商缩小规模,同时选出确保各方利益平衡的代表,或者增加随机选出的一般公众参与访谈或调查以扩大视野。实践中还有在程序的不同阶段由不同类型公众经不同选择策略参与决策的做法[6]91。结合具体决策和议题的特点灵活综合多种策略并细化程序设计,可以更好地满足公众代表性的要求。
五、我国相关规则的完善路径
与美国将公众参与作为环评制度的核心不同,我国的环评主要由行政机关主导,公众参与不足且效力有限。与之相应,我国相关立法在公众的界定和识别上花费的笔墨并不多,尚未真正建立起认定“公众”的具体规则。当然,中美法制体系和环评程序设计迥异,美国的相关规则也存在一定争议,但如果基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环境决策的复杂性、环评的制度逻辑以及公众参与的目的功能来看待“谁应当参与”的问题,美国的经验对于提升环境决策质量和保障公众权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应当看到美国实践中出现的效率低下等问题并以此为戒,从而为我国相关规则的完善提供镜鉴。
(一)为获取充分的信息有意放宽对“公众”的界定
美国“感兴趣”和“受影响”这一宽泛界定公众的模式是由环评的制度逻辑和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决定的,相较之下,我国的公众范围显得过于狭窄。2002年《环境影响评价法》、2009年《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和1998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以“有关”公众的措辞模糊化处理①其中,2002年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经过2016年和2018年两次修订,1998年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于2017年修订,但有关公众的条文均未修改。。2006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第15条突出了“受影响”的判断标准,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56条采用了“可能受影响”的表述。在此基础上,新实施的《办法》延续了“有关”和“可能受影响”的用语,同时第5条增加了“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限定,结合相关技术标准②2016年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中规定:“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是指建设项目整体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范围,具体根据环境要素和专题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未明确具体评价范围的,根据建设项目可能影响范围确定。”2018年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规定:“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根据建设项目排放污染物的最远影响距离D10%来确定。”,将“评价范围”等同于“影响范围”,仍未实质性突破以往“可能受到直接影响”和“存在利害关系”的标准。近年来我国环评领域的频繁改革,旨在简化审批、提高效率、解决环评中的“慢、难、繁”问题[24]。在这种思路之下为避免增加决策成本和负担,我国环评中的“公众”仅限于“可能受到直接影响”的公众,而不包括“可能受到间接影响”和“感兴趣”的个人或群体,导致更容易基于片面的信息出现遗漏和失误,尤其是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代表环境公益的社会组织被排除在法定范围之外,这不符合公众参与的普遍实践。
实际上,“感兴趣”和“受影响”这种界定方法并非美国所独有,1998年《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即《奥胡斯公约》同样使用了这一模式[25],我国也认可这一共识①2011年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众参与》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在5.3公众的范围中指出:“按照目前国际推行的环评公众参与最佳实践模式,如国际影响评价协会的《公众参与国际最佳实践原则》、国际金融公司的《公众参与及信息披露良好实践手册》等,公众参与的范围应覆盖所有受建设项目影响和对其感兴趣的群体,统称为利益相关方。”。对此,立法应当予以确认,放宽对“公众”的界定,更好地通过各方信息的输入和交流促进形成更为明智的决策,这也是在放松事前管制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必然要求。
(二)为多元主体提供参与和影响决策的机会
美国环评中的公众参与旨在为代表所有相关方的主体提供参与和影响决策的机会,为更好地解决具有争议的环境风险问题提供可能。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但我国对于公众的界定基本对应“直接受影响的公众”,难以与强势的企业和可能被俘获的政府经由平等对话以捍卫其合法权益。同时,由于立法没有明确环保组织在公众参与中的地位,环保组织在实践中尚未真正进入制度化参与程序当中,往往只能以宣传、倡导和推动舆论关注等为主要参与手段[26]。此外,专家的主体地位也不明确。我国目前相关立法有时将“专家”和“单位”“公众”相并列,似乎将专家排除在公众范围之外,有时又将“专家”列为公众,并将咨询专家意见和专家论证会作为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而专家基于个人专业兴趣的主动参与目前尚缺乏法律依据。至于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一般公众”更是没有参与的空间。这样一来,无法确保与决策有关的重要知识和存在冲突的价值都能进入环评进程,这不仅影响决策质量,也容易引发事后的无序参与,反而导致效率更低。
因此,在宽泛界定公众范围的前提下,应当明确各类主体特别是环保组织作为组织化利益团体的突出作用。同时,为促进科学分析和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除了明确专家的法律地位外,还应尽可能给予包括一般公众在内的所有相关方的代表都能得到充分参与的机会,并对事实和价值予以关注。
(三)以提升环境决策的质量为目标兼顾效率
美国对于“公众”过于宽泛的界定虽然有助于环境决策质量目标的实现,却大大提高了决策成本,并为后续公众的识别以及公众代表的选择带来了一定困难,加剧了决策的迟延。对美国联邦机构完成EIS所需时间的统计显示,从发布意向书到发布作出决策的记录平均需要4年零6个月②数据来源,参见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Counci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Timelines(2010-2017)[EB/OL].(2018-12-04)[2020-07-09].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1/CEQ-EIS-Timelines-Report.pdf.对此,特朗普政府试图设置2年期限以加速环评进程,这可能会限制公众评议且不利于少数族裔,参见Rachel Frazin.Trump to move forward with rollback of bedrock environmental law[EB/OL].(2020-07-14)[2020-07-25].https://thehill.com/policy/energy-environment/507315-trump-to-move-forward-with-rollback-of-bedrock-environmental-law.。与之相反,我国对于效率的追求却处于另一个极端。例如,《办法》对“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外公众的区分就已经凸显出效率的考虑。虽然在建设项目环评中不再倚重频繁造假的调查问卷,但公众提交意见这种形式在缺乏鼓励和引导的情况下,本来公众的范围就很狭窄,再加上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期间过短③《办法》第10条中仅规定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很可能出现参与不足甚至不能的情况,也就很难出现公众对环境影响方面质疑性意见较多的情形,无法满足开展深度公众参与的前提,这样一来会导致程序简化,最终参与公众的数量过少,虽有助于审批提速,但却难以保证决策质量。
如果在环境争议中包含所有公众将浪费时间和金钱,但是如果参与程序不符合一般公众或者组织化群体的期望也同样会浪费大量的金融、组织和制度资源[4]15-16。在“公众”的认定上应当以提升环境决策的质量为核心目标同时兼顾效率,过于追求效率则可能本末倒置、得不偿失。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办法》第14条规定了公众提交意见后的深度公众参与,根据公众质疑性意见的不同,分别召开公众座谈会、听证会或者专家论证会,这种区分不同阶段、适用不同参与形式、聚焦不同公众的做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环境决策的质量和效率要求。如果能够在公众意见调查阶段吸收美国更为开放式的界定模式,同时借鉴美国针对决策的特定议题和背景,例如决策所涉事项的规模、环境要素的特性、环境风险的特征等因素对不同类型的公众给予不同关注的做法,将更有助于环境决策质量和效率的统一。
(四)限制决策者自由裁量权以保障公众权益
虽然美国环评立法和相关研究都以包容性为原则,但实际上不可能包含任何人,这给决策者的自由裁量留下了空间。对此,立法对机构应当邀请或通知哪些公众、征求哪些公众的意见以及如何通知特定公众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除了针对关键公众的识别和通知外,还要求机构通过当地报纸广告、媒体发布等方式,或者在联邦层面上在联邦公报上予以公共通知,并为公众参与留出了较为适当的时间①40 C.F.R.§1506.10(b).,客观上能够起到限制裁量空间的作用。实践中,相关机构为自上而下法提供具体指引,进一步压缩裁量空间,为自下而上法提供便利以鼓励参与,法院则严格检视行政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众的程序性权利。
相较而言,我国立法和实践对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具体的限制和相应指南。例如,在规划环评中,现行立法主要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将可以采用的参与形式列明,由组织者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给予组织者较大的选择权[27]。这意味着采取调查公众意见、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和听证会中任何一种参与方式都可通过程序检验,使得公众的范围难以预期,甚至可以轻易排除普通公众的参与。在司法环节,法院一方面对利害关系人认定的范围过于狭窄,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实质性审查,一旦满足形式要件就认为公众参与程序合法[28]。
对此,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经验,通过精细化的立法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南明确公众识别的基本原则和规则,特别是明确应当考虑的因素、建立识别公众的问题清单并制定开放性的长期有效的特定公众名单。为避免美国在司法审查中遭遇的困境,应当在“严格检视”规则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审查密度,更深入地挖掘行政记录,集中于决策者是否符合立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程序规则的判断,实行“更为严格的检视”[29]。
(五)细化公众代表的选择策略并加以综合运用
对于如何选择公众代表,虽然随机抽样、自我选择和选择代表的策略在我国目前的立法当中均有一定体现,但现行立法点到为止,实践中也未发展出具体的方法和限制。对于自我选择策略,《办法》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规定由于除了信息公开外没有配套的鼓励措施,因此不能保证公众的主动参与,也因受制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限定而无法体现公众的广泛性,同时环保组织也缺乏参与空间。在选择代表策略上,仅有《办法》第15条针对召开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的情形规定“应当综合考虑地域、职业、受教育水平、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程度等因素”,如何“综合考虑”显然见仁见智,并不能实现对裁量空间的实质限制。至于抽样技术,主要体现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18条对审查小组的专家从专家库内随机抽取的规定上,但是专家库和专家名单如何确立,随机抽取时如何保证与研究方向相匹配且满足利益代表性要求均缺乏具体的规定,后续也缺乏同行评审等保障专家中立性的程序设置。此外,公众代表的数量还需满足占总人数一定百分比的要求②例如,《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与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评函〔2012〕138号)要求对于评价范围内可能受到影响的公众,按不少于当地常住人口10%比例进行调查。,但表面上符合人数的要求并不足以代表公众的利益,即不能保证所有的价值和偏好都能得到反映。
为确保参与公众的代表性,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在明确选择原则和关键要素的基础上,针对各策略的局限细化公众代表的选择策略。例如,针对自我选择策略,应当在设定合理参与时限的基础上加强对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通知和引导;针对选择代表策略,应当将描述性代表和实质性代表相结合,选出那些有时间、知识或专长,能有效地参与和投入,并且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所在组织观点的人[30];针对抽样技术,则应当考虑样本库的规模和样本库本身的合理性和利益代表性。此外,还需要对各选择策略综合加以运用以平衡各策略的优缺点。当然,美国对于选择策略的运用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如何更好地选择公众代表仍有待实践进一步的探索和创新。
结 语
公众参与程序是确保重大行政决策“不可任性”的重要手段,“公众”的界定、识别和选择是该程序设计中最为初始和基础的一环。环境影响的范围界限不明使得是否“受影响”难以判断,环境问题的科学技术背景给外行公众的参与带来了障碍,环境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现有科学证据不足而转向价值判断,环境决策始终面临着科学和政策难以分离、事实与价值相互纠结的困境,这是难以确定“公众”的根本原因。面对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所引发的环境决策困境,美国环评公众参与立法立基于环评的制度逻辑和公众参与的目的功能,有意宽泛界定公众的范围,并在具体决策中努力与特定议题相契合,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公众识别和选择的方法和策略,公众参与程序设计始终围绕环境决策的质量、效率、正当性等目标展开,试图在制约决策者权力的同时保障公众权益,却也因为繁琐和拖沓的决策进程而饱受诟病。与之相反,我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观念和对于公众范围“宜窄不宜宽”的惯性思维造就了我国环评公众参与中公众范围狭窄、公众参与或流于形式或被操纵,甚至弄虚作假的现实。这背后既反映出决策者对公众参与的消极和回避态度,也反映出对效率的极致追求。
基于美国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我国相关规则的完善应当回归环评的制度本源,以提升环境决策的质量为首要目标,在放宽对“公众”的界定、确保多元主体特别是组织化的利益团体得到充分参与的同时,通过结合决策具体情境,侧重特定类型公众,针对不同参与阶段和不同参与形式吸纳不同公众等方式兼顾效率。为限制决策者或组织者在选择公众上的自由、保障公众权益,应当经由立法的精密设计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南明确公众识别的基本原则和规则,法院也应当发挥其积极作用以确保程序规则得到严格遵守。在选择公众代表时,为满足公众代表性的要求,应当在明确选择原则和关键要素的基础上,针对随机抽样、自我选择和选择代表策略各自的局限细化各项策略并加以综合运用,使各方的信息和价值得以在有限的参与程序中影响决策,从而更好地实现公众参与的目的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