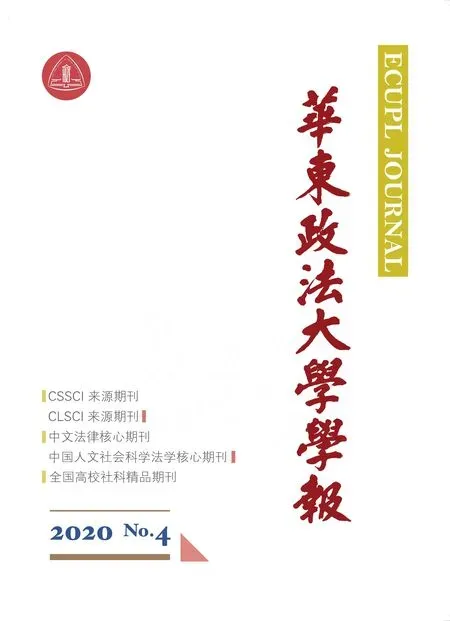“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重构
王 浩
一、绪论
从《合同法》第49 条到《民法典》第172 条,我国的民事立法对于表见代理的成立要件始终聚焦在“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但这显然太过笼统,与其说是要件,倒更像早期文献对表见代理所下的定义,“在无权代理的场合,倘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的效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这里所说的无权代理,包括无代理权、超越代理权限及代理权消灭之后的代理三种情形。”〔1〕章戈:《表见代理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1987 年第6 期。究竟何为 “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从近期文献来看,有说是指客观上存在代理权表象,〔2〕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822 页。有说是指相对人主观上善意无过失。〔3〕参见汪渊智:《代理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84 页。但从“桐城路分理处诉东方房地产公司借款、抵押担保合同纠纷案”的判决(以下称“(2000)经终字第220 号”)和近年来的司法解释〔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 条。看,“有理由”的判断总要结合代理权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这两个方面。这或许是受到早期文献的影响,如曾有学者指出:“表见代理的成立还须具备以下特别要件:第一,客观上须有使相对人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的情形,这是成立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第二,相对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这是成立表见代理的主观要件。如果相对人出于恶意,即明知他人为无权代理,仍与其实施民事行为,或者相对人应当知道他人为无权代理却因过失而不知,与其实施民事行为的,已失去受到法律保护的必要,故不能成立表见代理。”〔5〕章戈:《表见代理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1987 年第6 期。于是,问题最终落到了究竟何谓“客观代理权表象”和“善意无过失”以及两者又是何种关系。
这些本是相对人保护标准问题上绕不开的课题,也是早期文献重点关注却未能澄清的疑点。但近年来学界的关注重心似已不在此,而更多转向了“本人的归责性”。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中已包括了本人的因素。〔6〕参见尹田:《我国新合同法中的表见代理制度评析》,载《现代法学》2000 年第5 期;冉克平:《表见代理本人归责性要件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律科学》2016 年第1 期;杨芳:《〈合同法〉第49 条(表见代理规则)评注》,载《法学家》2017 年第6 期。只是因为表述过于笼统,以致人们只能从中见到相对人之所以值得保护的一面,这才有了后来在本人可归责性问题上眼花缭乱的争论。不过,“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中究竟可发现何种本人的因素,似仍有探讨之余地,这就涉及“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实质到底为何的问题。
总之,无论是判断相对人是否值得保护,还是认定本人应否承担表见代理责任,有关“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解读都至为关键。此处亟须对历来的学说和审判实践做一清算,以明确“客观表象”的具体所指、“应当知道”的认定标准、客观表象与过失认定间的关系等,再以之为基础进一步探明“有理由”的实质,明确相对人可保护性与本人可归责性之间的联系。于此意义上,本文的任务已不限于对“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阐明,而是重构。
二、解析“代理权表象”
(一)客观上存在代理权通知
早有文献指出,单凭行为人自称有代理权,难以构成代理权表象;能够构成代理权表象的,通常是这些情形:本人向相对人直接或间接表示过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行为人持有代理权证明文件、本人知道行为人实施无权代理而不否认等。〔7〕参见章戈:《表见代理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1987 年第6 期。从审判实践看,这些情形的确多能成立表见代理。比如,在一起行为人未经授权签订补充协议的事例中,法院就因本人在签订原协议时以盖章确认的方式间接表示了行为人有全权代表签约的权限,最终肯定了表见代理。〔8〕参见(2005)民一终字第94 号民事判决书。(2000)经终字第220 号判决虽最终以相对人有过错为由否定了表见代理,但直言:行为人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所出示的本人的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客观上形成了代理权表象。明知无权代理而“放任”,则被法院视作了主张表见代理成立的一方应予证明的事实。〔9〕参见(2016)民终字第110 号民事判决书。除此之外,行为人被本人置于某种通常伴有代理权的职衔地位等,也是实践中常提及的一种“代理权表象”。比如,一起“董事长”私刻公章以公司名义订立担保合同的事例中,法院认为:“董事长虽不一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其相较于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显然享有更大的权力,故其对外实施的行为更能引起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10〕(2016)民申733 号民事裁定书。
笔者认为,上述情形区别于仅行为人自称有代理权的主要之处,在于一般情况下相对人均会认为已无必要向本人核实确认代理权限。比如既然本人已表示过行为人有代理权,交易发生时相对人自然无须再向本人核实。行为人持有代理权凭证的场合亦是如此。代理权凭证最典型者就是授权委托书。现行法虽将之定义为代理权授予的书面形式,但对外而言,授权委托书从来就是一种凭证,起到证明代理资格的作用。〔11〕参见章戈:《表见代理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1987 年第6 期。至于本人明知无权代理而容忍的场合,以及本人将行为人置于某种通常伴有代理权的职衔地位的场合,由于相对人一般情况下皆可从中推断出行为人已被授权,故无必要再向本人核实。
进而言之,上述各情形中,相对人一般情况下之所以无须再向本人核实有无授权,皆因本人一方的举止态度一般情况下已构成了旨在表明行为人有代理权的 “代理权通知”。所谓客观上存在代理权表象,即指本人一方的举止态度一般情况下存在“代理权通知”的表示价值。需注意,学者们总是刻意区分代理权通知与出具代理权凭证、明知无权代理而不加阻止等其他情形,似乎这些情形非属代理权通知。〔12〕早期的文献,如章戈:《表见代理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1987 年第6 期;近来的文献,如叶金强:《表见代理中信赖合理性的判断模式》,载《比较法研究》2014 年第1 期。但既然本人有选择表示手段的自由,这些不过就是代理权通知的不同形态。具体而言,本人让行为人持有代理权凭证的场合,行为人往往充当了本人的使者,转达自己已被授权之旨意,故构成通过使者作出的代理权通知。本人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却不加阻止的场合,实质就是一种推断的代理权通知。本人将行为人置于某种通常伴有代理权的职衔地位的场合,无论本人自身是否知晓此举的意义,客观上也均构成推断的代理权通知。另外,有学者认为印章之占有是一种独特的代理权表象,〔13〕参见叶金强:《表见代理中信赖合理性的判断模式》,载《比较法研究》2014 年第1 期。但由于印章本身即可表明印章所有者愿为意思内容承担责任,〔14〕参见陈甦:《公章抗辩的类型与处理》,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3 期。故印章向来被视作代理权凭证的范畴,与之类似的还有空白的授权委托书、介绍信、盖章或签字的空白合同书等。〔15〕参见章戈:《表见代理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1987 年第6 期。换言之,包括印章在内的这些特殊代理权凭证的出具,其实仍属于通过使者作出的代理权通知,只不过凭证本身所传达的信息尚不完整,故属于待补充的代理权通知。
(二)“代理权通知”以外的因素?
所谓代理权表象,除“客观上存在代理权通知”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所指?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只有“客观上存在代理权通知”,相对人一般情况下才会认为已无必要再向本人核实。
譬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商事合同案件适用表见代理要件指引(试行)》(以下称“指引”)中提出,“行为人原有代理权已被终止但被代理人未对外告知”,是代理权表象的考量因素。的确,在肯定合理信赖的实际判决中,提及这类“不作为”者并不少见。〔16〕如(2000)经终字第220 号民事判决书 、(2013)民申字第2207 号民事裁定书。但是,若之前本人未亲自或通过出具代理权凭证等方式对外告知行为人已被授权,则就无所谓之后的“不作为”。也即代理权表象仍要归因于客观上本人之前作出了代理权通知(之后客观上又未撤回该通知)。《指引》还提出,“合同关系的建立方式是否与双方以往的交易方式相符”,也是代理权表象的考量因素。的确,在肯定合理信赖的判决中,诸如“签订过与本案性质相类似的合同”“连续多次的行为”等常有所见。〔17〕如(2001)民二终字第175 号民事判决书、(2013)民申字第2207 号民事裁定书。难怪有学者认为,当事人之间首次交易采用的表征不足以构成权利表象,“必须是其于数次交易中采用的表征方可构成外观”。〔18〕崔建远:《论外观主义的运用边界》,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5 期。但实际上,过往有无交易、交易方式是否相同等并非关键。关键是,通过过往多次同类交易,本人的举止态度业已表明行为人有长期持续从事此类交易的权限,且此种代理权通知未有撤回,所以相对人深以为在本次交易之际无须再向本人核实。《指引》又提出,诸如“行为人签约前曾陪同合同相对人参观考察被代理人的施工现场”“签约地在被代理人营业地或办公场所”等也是代理权表象的考量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往往只有在与行为人的职衔地位相结合时才能引发信赖。
有个别判决在认定代理权表象时还特意提及案外第三人的言行:“……加之○县公安局相关人员亦确认其在建工程系X(本人——笔者注)承建、A(行为人——笔者注)系该工程的负责人,Y(相对人——笔者注)有理由相信A 的行为代表X。”〔19〕(2013)民申字第743 号民事裁定书。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实际上此处重要的并非公安局相关人员的确认行为,而是所确认的事实,即本人将行为人置于“负责人”之地位,也即这里让相对人打消向本人核实之念头,实质仍是一种推断的代理权通知。
此外,《指引》提出,诸如“合同是否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被代理人实际支付过合同价款;被代理人与合同相对人就履约问题进行过交涉”等也是代理权表象的考量因素。但是,如果行为人未以本人的名义订立合同,则原本就不构成“代理”。〔20〕《民法典》第925 条(《合同法》第402 条)中所谓“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实际从意思表示解释的角度而言仍是指“以本人的名义”。参见朱虎:《代理公开的例外类型和效果》,载《法学研究》2019 年第4 期。至于其他因素,均与代理权表象无关,因为这些因素都存在于行为人缔结法律行为之后。众所周知,判断相对人是否有合理信赖,取决于“法律行为缔结时”的情况。〔21〕如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2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683 页;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载《法学》2013 年第2 期;杨芳:《〈合同法〉第49 条(表见代理规则)评注》,载《法学家》2017 年第6 期。实际上《指引》中也有相关表述,即“相对人主张自己善意且无过失,应证明自己知悉权利外观事实的时间早于实施交易行为,实施交易行为后或风险产生后才了解的相关事实则一般不能支持对相对人善意的判断。”另外,《指引》认为“标的物的用途、交付方式与交付地点等是否与被代理人有关”,“被代理人是否取得履行合同的利益”也是代理权表象的考量因素。但如后所述,诸如交易方式、性质有无异常等与其说是代理权表象的考量因素,毋宁说是判断相对人有无过失的因素。〔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4 条也是将这类因素视作善意无过失的判断因素。
有学者认为,代理人与本人之间存在父母子女、夫妻等关系的,也可引发代理权表象。〔23〕如史浩明:《论表见代理》,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1 页。《指引》也提到,与本人之间的身份联系越密切,就越容易成立代理权表象。但除家事代理等少数情形外,为何身为本人的至亲,就一定可以让理性相对人打消向本人进一步确认核实的念头?实际上,在一起儿子以父亲的名义代父亲收款的事例中,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称“最高院”)也没有认定代理权表象的存在。〔24〕参见(2014)民申字第 657 号民事裁定书。
三、解析“相对人善意无过失”
(一)主客观两方面的关系
在“有理由”的判断构造中,作为客观方面的代理权表象与作为主观方面的善意无过失是何关系?所谓“有过失”,即指相对人有核实代理权存否之义务而未尽到。〔25〕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2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686 页;汪渊智:《代理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86 页。如上所说,“代理权表象”是指本人一方的举止态度在一般情况下构成“代理权通知”,以致相对人在一般情况下无须再向本人核实有无代理权。反之,若不存在代理权表象,则一般情况下相对人自应核实后再行交易。所以一般而言,正如《指引》所说,“权利外观因素越充分,越能够说明合同相对人主观上善意无过失”。不过,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毕竟不能等同。前者的着眼点是“一般情况”或“一般相对人”,而后者强调的是“具体相对人”的主观样态。正因此,尽管存在代理权表象,但相对人仍可能因“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而不得主张表见代理。〔26〕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2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683 页。(2000)经终字第220 号民事判决书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二)有过失之认定
也就是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虽然存在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代理权表象,但个案中的相对人仍须核实确认代理权之有无。
比如,相对人身份特殊。(2000)经终字第220 号判决中,虽然缔约时行为人持有各种证明材料,但法院仍认为相对人作为金融机构未全面核实行为人有无贷款资格、存在过失。在“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08)民二终字第124 号]中,最高院认为,相对人作为金融机构却未对私刻的公章、伪造的证明文件等进行核实和鉴别,存在过失。而从最高院的若干其他判决看,一般情况下,相对人并不负有核实凭证真伪的义务。〔27〕如(2013)民申字第2207 号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620 号民事裁定书。
又如交易方式特殊。一起行为人以单位名义订立建设工程合同并收取款项的事例中,虽然相对人举证证明行为人缔约时持有合同书、公章在内的多种证明材料,但法院仍以行为人个人而非单位财务部门收取合同款、违背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常识为由,认定相对人存在过失。〔28〕参见(2016)民申3688 号民事裁定书。
再如交易性质特殊。一起行为人就本人所建商品房与相对人订立预售合同,以清偿行为人的公司所欠相对人债务的事例中,虽然行为人缔约时持有授权委托书等材料,但法院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明显是为了清偿自己公司的债务而损害本人的权益,相对人缔约时未尽审查义务、存在过失。〔29〕参见(2002)民一终字第7 号民事判决书。
要言之,相对人并非任何时候都有高度的确认核实义务;除非因身份、交易方式、性质等具有特殊性,相对人才负有高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
(三)强化相对人的注意义务?
但是,近来审判实践中有种须注意的苗头,即为保护看似无责的本人而进一步强化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比如,在一起银行职员冒充行长持假印章假存单骗取存款的事例中,尽管相对人只是普通储户,但法院仍特别强调,相对人对行长身份疏于审查、存在过失。〔30〕参见(2013)民提字第95 号民事判决书。有学者认为,在一些案件中,法院就是以“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为名隐晦地考虑了本人的可归责性。〔31〕参见杨芳:《〈合同法〉第49 条(表见代理规则)评注》,载《法学家》2017 年第6 期。
在解释论上多要求表见代理之成立须本人有可归责性,而现行法只规定“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状况下,上述思路看似化解了立法论与解释论之间的矛盾,实际却未必妥当。基于此类思路,诸如行为人盗用授权委托书、印章之类的场合,即便不提及本人有无可归责性,也可以相对人未向本人确认核实为由,径直否定表见代理。然而,诸如盗用之类的情事极具隐蔽性,甚至本人自身都未必知晓,又岂能要求相对人尽一般注意后可以知晓?尽管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中包括了本人的因素,但这不等于本人一方的所有内部情事都会反映至外部可视的层面。〔32〕有学者认为这正是正面承认可归责要件的理由之一。参见叶金强:《表见代理中信赖合理性的判断模式》,载《比较法研究》2014 年第1 期。所以此类思路的实质,无非是为保护本人而通过拟制相对人的过失以否定“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进一步而言,要求相对人交易时尽可能确认核实,是否与代理制度之本旨相符,也不无疑问。不难想象,一旦普遍科以确认核实义务,相对人为求将来免于被认定“有过失”,必会在所有场合皆尽可能对代理权有无进行调查核实,以致交易成本大幅增加。如此,人们是否还愿意选择代理来交易就有了疑问,而表见代理制度或许就成了代理制度的“掘墓人”。要知道,早年拉邦德(Laband)之所以提出代理权无因性,目的就是要将代理权打造成一种“形式化”的交易资格,以取代权限有无的实质性调查。〔33〕Vgl. Laband, ZHR10, 240f.此外,强化注意义务还可能让相对人得不到任何保护。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171 条第3 款所谓的“善意”是指“善意无过失”。〔34〕参见纪海龙:《〈合同法〉第48 条(无权代理规则)评注》,载《法学家》2017 年第4 期;夏昊晗:《无权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载《法学》2018 年第6 期;张家勇:《论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的双层构造》,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3 期。于是,一旦相对人在表见代理成否的争议中被拟制为“有过失”,那么相对人不仅无法向本人主张表见代理责任,甚至无法追究无权代理人的责任。
四、“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实质
(一)相对人视角下的“代理权通知”
如上所见,“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判断构造简言之,即从客观表象入手、以主观认知为准。此种判断构造并不陌生,意思表示的解释中也有所见。关于意思表示的解释,《民法典》区分了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对于前者应从相对人的认识出发予以解释,以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35〕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440 页。也就是说,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表意人的举止态度构成某种意思表示的,那么表意人的举止态度就应被解释作这种意思表示。相对人的认识是否合理,往往可以根据表示的客观含义、也即一般情况下的含义予以判断;但若相对人明知或应知表意人对表示所赋予的特殊含义,则自应按此含义解释意思表示,此时相对人并无需保护的合理信赖。〔36〕参见朱晓喆:《意思表示的解释标准——〈民法总则〉第142 条评释》,载《法治研究》2017 年第3 期;纪海龙:《真意保留与意思表示解释规则——论真意保留不具有独立的制度价值》,载《法律科学》2018 年第3 期。要言之,关于意思表示的解释,一方面需探寻表示在一般情况下的含义,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对个案中的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的认定。
既然“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判断构造对应这种解释规则,那么所谓“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实际是指经解释“本人作出了代理权通知”。如上所言,“代理权表象”即本人的举止态度在一般情况下具有“代理权通知”的表示价值。又如上所言,即便存在代理权表象,但若个案中的相对人实际明知或应知行为人无代理权,则仍不能谓“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也即此时本人的举止态度已不具有“代理权通知”的表示价值。
需注意,“本人对外作出代理权通知”只是从相对人的角度所作之解释,也即对某一举止态度的“规范解释”。至于本人实际是否“有意”作出某种内容的代理权通知,或者是否意识到其行为已构成通知,则是另一回事。众所周知,表意人是否有相应的效果意思,并非意思表示的成立要件。另按流行的观点,即便没有表示意识,也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成立。〔37〕如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98 页;纪海龙:《走下神坛的“意思”:论意思表示与风险归责》,载《中外法学》2016 年第3 期;杨代雄:《意思表示中的意思与意义:重新认识意思表示概念》,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1 期。当然,正如此类意思表示可否撤销一样,与本人内心意思不符的代理权通知,或者无通知意识的通知是否可以被撤销,却又另当别论。
(二)确保“代理权通知”的准确性
表见代理立法与代理权通知有关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代理交易离不开代理权通知。在实际的代理交易中,相对人之所以与自称代理人的行为人开展交易,是因为有“材料”证明行为人有代理权。这个“材料”可由相对人自己去收集,但必然导致——与本人直接交易相比——更大的交易成本。有鉴于此,本人如欲利用代理开展交易,必然会在代理交易之前或同时,以某种形式对外证明行为人有代理权,从而让相对人的处境并不会因非直接交易而更不利,“代理权通知”应运而生。法律相应要做的,就是为代理权通知的证明力背书:只要相对人受领了代理权通知,也即本人的举止态度表明行为人已被授权,那么无论实际有无授权、嗣后代理权是否消灭,相对人都可向本人主张代理行为的效力。这便是表见代理制度,一种旨在确保代理权通知准确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出现,使代理权的授予很大程度上为外部通知所取代,“通知”也因此成为本人与相对人的法律关系形成之实质基础。
当然,“代理权通知”在教义学上无法归为“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因为“代理权通知”是告知代理相对人“本人‘已授予了’某人代理权”,也即告知一个业已发生的法律关系,属观念通知,非创设权利。这与德国民法典上的所谓“代理权外部授予行为”(《德国民法典》第167 条、第170 条〔38〕《德国民法典》第167 条:“意定代理权的授予,以向……代理应对之发生的相对人的表示为之。”同法第170 条:“意定代理权以向相对人做出的意思表示授予的,意定代理权对该相对人保持有效,直至授权人将意定代理权的消灭通知相对人。”本文中德国民法典的条文译文均参考自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有些不同。此种行为虽也以代理之相对人为对象,但其表示价值是“本人‘授予’某人代理权”,故不是告知业已发生之事实,而更像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也即“意思表示”“法律行为”。〔39〕Vgl. 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 1971, S.32.
最近,有学者主张,我国的表见代理立法实质上就是有关代理权外部授予行为的规定,故而表见代理仍属“有权代理”的范畴。〔40〕参见迟颖:《〈民法总则〉表见代理的类型化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8 年第2 期;娄爱华:《私刻公章与被代理人责任》,载《法学家》2020 年第3 期。另外,徐涤宇主张“表见代理之法律效果的发生,也以代理权之授予为根本”,参见徐涤宇:《代理制度如何贯彻私法自治:〈民法总则〉代理制度评述》,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3 期。此种观点大有可疑。首先,承认代理权可通过向代理交易之相对人作出意思表示的方式发生,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即代理权只是一种“资格认证(Legitimation)”而非一种主观地位,〔41〕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935 页。故代理权的发生也可不以代理人的受领或承诺为要件。而在我国,虽然表面上受域外学说的影响存在各种有关代理权性质的学说,但实际上对代理人而言,代理权依然只是一种根据其意志发生变动的主观地位。正因此,《民法典》第173 条第2 项才规定代理人可以通过“辞去委托”单方面消灭代理权。同时人们更倾向于认为代理权的授予应得到代理人的同意,代理人也应对代理权的取得支付某种对价。〔42〕参见江帆:《代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年版,第71、72 页。事实上,我国民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将代理权授予看作一种类似于委托合同的关系。比如,基于本人授权产生的代理权被称为“委托代理”、委托代理被表述为“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有关复代理的规定完全是合同编中有关转委托规定(《民法典》第923条)的翻版等,皆为明证。〔43〕有学者甚至根据《民法典》第163 条等认为我国民法上的代理权授予行为仍属于委托合同的范畴。参见刘骏:《再论意定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载《交大法学》2020 年第2 期。即便将代理权授予行为抽象于委托合同,理论上也仍可将前者视作一种类似于委托合同的无名合同。也即本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两个合同关系,一个是委托、雇佣等基础合同关系;另一个是旨在发生代理权的无名合同。〔44〕我国代理法受日本民法的影响较大。日本民法上,代理权授予行为就常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于内部基础合同关系但类似于委托的无名合同,而代理权也常被视作一种主观地位。参见新版注釈民法(4)(有斐閣,2015 年)27 頁、29 頁〔佐久間毅〕。总之,在我国的代理法语境下,代理权的发生似仍应以代理人的受领乃至承诺为要件,所谓的“代理权外部授予行为”并无立足之地。其次,无论从《民法典》第172 条的文义,还是立法前后的学理观点来看,我国的表见代理制度明确以“无权代理”为前提。罔顾这一事实,硬将《民法典》第172 条解读为以代理权外部授予为基础的“有权代理”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既然明确了“有理想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是指本人作出代理权通知,那么将表见代理强行解释为代理权外部授予其实已无必要。的确,代理权外部授予之承认有助于保护代理相对人。即只要本人对外表示本人授予行为人以代理权,那么无论本人与行为人的内部关系实际如何,行为人的代理行为就作为“有权代理”对本人始终有效,直至本人向相对人通知代理权消灭为止。但如上所述,此种保护目的同样存在于以代理权通知为基础的表见代理立法中。作为表见代理之基础的代理权通知实际上已取代了代理权授予,成为法律关系变动的实质基础。简言之,代理权通知与代理权外部授予行为一样,也可使代理交易的相对人仅凭本人一方的表示就径直与代理人开展交易,而不用顾忌实际的内部关系。虽然以精确著称的德国民法典基于行为所具有的不同表示价值分别规定了代理权外部授予和以代理权通知为基础的表见代理(《德国民法典》第171 条、第172 条〔45〕《德国民法典》第171 条:“(1)某人以对相对人的特别通知或以公告发出授予了他人以代理权的通知的,该他人因该通知而在前一情形对特定相对人,在后一种情形对任何相对人,有代理的权能。(2)代理权存续到该通知被以发出通知的同样的方式撤回之时。”同法第172 条:“(1)授权人将授权书交付给代理人,且代理人向相对人出示该授权书的,视同授权人发出的授予代理权的特别通知。(2)代理权存续到授权书被返还给授权人或宣告为无效时为止。”),〔46〕参见王浩:《表见代理中的本人可归责性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3 期。但正如金德尔(Kindl)所说,当存在代理权通知的时候,相对人就没有动机要求本人再向自己实施一个代理权外部授予;本人通知了代理权已被授予之后,也无理由再去做出一个相同内容的代理权外部授予的表示。〔47〕Vgl. Kindl, Rechtsscheintatbeständ und ihre rückwirkende Beseitigung, 1999, S. 13.
(三)只涉及某一类型的表见代理?
尽管表见代理制度与代理权通知之间有莫大关联,但从《合同法》到如今的《民法典》,我国的表见代理立法始终未见“代理权通知”之类的表述。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理论界抱有这样的观念,即表见代理未必都与代理权通知,也即本人的表示行为有关。比如,近来有学者将表见代理刻意区分为“客观型”和“主观型”,依据是前者的基础仅是行为人的行为,如行为人持有授权委托书,后者的基础涉及本人的行为,如本人明知无权代理而容忍。〔48〕参见周清林:《合理类型化下的无权型表见代理确定》,载《政法论坛》2018 年第1 期。
之所以产生上述观念,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国学者对代理权通知的形态缺乏正确的认识。如前所述,我国学者在谈及代理权表象时很少意识到,代理权凭证、明知无权代理而不加阻止等不过是代理权通知的不同形态。如果代理相对人的眼中仅有行为人自己的表示行为,而没有本人的表示行为,又怎会不向本人核实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受到比较法的影响,或说是对比较法缺乏正确的理解。比如,日本民法典分别于第109 条、第110 条、第112 条规定了三种表见代理。其中,第109 条所规定的“授权表示型表见代理”,正相当于《德国民法典》第171 条以下的表见代理,其核心要件即“代理权授予表示”,也即“代理权通知”。第110 条规定的是“越权型表见代理”,核心要件是“第三人有正当理由相信代理人有权限”。第112 条规定的是“代理权消灭后的表见代理”,即“代理权的消灭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第三人因过失而不知道该事实的除外”。如此一来,似乎代理权通知只涉及某一类型的表见代理。在我国《合同法》制定以前,我国理论界就存在这样的认识:德国民法典虽率先创设了表见代理制度,但《日本民法典》第109、110、112 条却是“最完整”的表见代理立法。〔49〕参见史浩明:《论表见代理》,载《法律科学》1995 年第1 期。“最完整”的表见代理制度似乎告诉我国的立法者,表见代理可适用于一切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场合,代理权通知只是其中一种场合。于是无论《合同法》第49 条还是后来的《民法典》第172 条,均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设定为表见代理的唯一要件。同时这些规定的文义暗含了三种类型的表见代理,即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代理权消灭后的表见代理,其中没有代理权的表见代理又常被学者理解作“授权表示型表见代理”。〔50〕参见汪渊智:《代理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90 页;叶金强:《表见代理构成中的本人归责性要件》,载《法律科学》2010 年第5 期;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载《法学研究》2017 年第2 期;徐涤宇:《代理制度如何贯彻私法自治:〈民法总则〉代理制度评述》,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3 期;解亘:《论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的规范形态》,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17年第12 期。但事实上,日本民法是否意在规定一套“最完整”的表见代理制度,大有疑问。日本民法典第109 条参考自德国民法典草案,而第110 条沿用了日本旧民法典上的规定,该旧民法典则由法国人博阿索那德(Boissonade)所起草。对这些来源不同、表述不同的规定背后是否潜藏某种共同的原理或要件,日本民法典的起草者自身也未必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对两个规定的适用对象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区别,也不无疑问。而近来日本理论界的一个动向,即认为无论第109 条还是第110 条、第112 条,皆与本人的代理权通知有关,而表见代理责任实质就是一种“表示责任”。〔51〕参见王浩:《表见代理中的本人可归责性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3 期。
总之,在代理权通知与表见代理的关系上,或许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误会。因这一误会,在《合同法》制定后的几十年间,“代理权通知”一直没能成为我们适用和研究表见代理制度的坐标轴。
五、回归法律行为论
(一)警惕向一般原理的逃避
明确了“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是指“本人作出代理权通知”后,自然就发现了本人承担表见代理责任的依据。然而,传统上人们却更愿意从笼统的权利外观思想或一般归责原理的层面来把握本人的可归责性。近年来,有的学者就以善意取得和表见代理同属“权利外观责任”为前提,论证了本人可归责之必要,并强调应以风险归责思想指导可否归责的判断。〔52〕参见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载《法学研究》2017 年第2 期。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只是见到了表见代理与善意取得之间存在“一般原理”上的共性,但却未能发现表见代理自身的特殊性。
的确,善意取得论与表见代理论都受信赖保护原理的支配,在归责原理上也有共同之处。早期权利外观理论的代表人物威尔斯帕西亚(Wellspacher)正是通过对表见代理、动产善意取得在内的众多规定进行归纳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定式:“当某人因相信外部事实而缔结法律行为,且该外部事实在法律或交易观念上构成权利、权利关系或其他重要法律要素的表现形式时,若该外部事实确由因信赖保护而承受不利益之人所造成,则该信赖应得到保护。”〔53〕Vgl. Wellspacher, Das Vertrauen auf äußere Tatbestände im bürgerlichen Recht, 1906, S.115.对于此种求诸权利外观之惹起的归责思想,无论是将风险理论应用于信赖保护领域的先行者米勒-厄兹巴赫(Müller-Erzbach),〔54〕Vgl. Müller-Erzbach, AcP 109, 130.还是信赖责任之集大成者卡纳里斯(Canaris),〔55〕Vgl. Canaris, a.a.O., S. 480.都认为本质上就是“风险承担”或“风险分配”的思想。但须注意,今日德国学界在讨论表见代理的归责问题时,目光并未停留在抽象的归责原理上。“二战”后,弗卢梅开创性地提出,《德国民法典》第171 条、第172 条、容忍代理权等是“代理权外部授予”的具体形态,表见代理实际属于有权代理、法律行为论的范畴。在这一观点刺激下,将表见代理置于权利外观责任的传统阵营开始对本人的可归责性进行反思。卡纳里斯的观点就是典型。他一边坚持以代理权通知仅是宣告而非设权表示为由,将表见代理归于权利外观责任的范畴,一边强调权利外观责任也应类推适用意思表示的规则,并认为过往主张权利外观责任不能参照这些规则的观念是概念法学之误。〔56〕Vgl. Canaris, a.a.O., S. 35f.与此同时,弗卢梅开创的“表见代理=代理权外部授予说”,经帕夫洛夫斯基(Pawlowski)、〔57〕Vgl. Pawlowski, JZ 1996, 127f.希尔肯(Schilken)、〔58〕Vgl. Schilken, in: Staudingers, BGB, 2014, §167 Rn. 29a.梅尔克特(Merkt)、〔59〕Vgl. Merkt, AcP 204, 653f.维尔巴(Werba)〔60〕Vgl. Werba, Die Willenserklärung ohne Willen, 2005, S. 150ff.等一众学者的努力,也大有复兴之势。难怪有学者特意告诫裁判者:在表见代理的归责问题上,必须尊重错误表示可撤销等现行法上的规定,切不能借助诚信原则之类的原理来兜售自己的“衡平情感”。〔61〕Vgl. Wieling, JA 1991, 228.
可见,将表见代理的归责问题还原为一般原理问题,实在有些简单化了。必须认识到,即便表见代理属于权利外观责任的范畴,仍与法律行为论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如前所述,作为表见代理之基础的代理权通知事实上成为本人与相对人间的权利义务变动之基础,发挥着类似于法律行为一样的作用。故而,对于代理权通知及表见代理,可以也应当类推适用错误意思表示可撤销等规定。如果真有所谓的代理权外部授予行为这种法律行为,那么这一道理更是不容辩驳。因为无论如何,代理权通知的相对人所能获得之保护,绝不应在有同样功能的代理权外部授予行为的相对人之上。至于善意取得,只是为保护登记簿或占有的公信力所特设的所有权取得规定,真正权利人失去所有权也不过是善意受让人取得所有权的反射效果,与法律行为论并无直接关系。此间差别,并非是将表见代理责任与善意取得统冠以“权利外观责任”之名就可以抹去的。〔62〕值得注意的是,卡纳里斯就认为“责任”应区别于“权利的丧失”,所以他的信赖责任论虽然包括了表见代理,但恰恰排除了善意取得。Vgl. Canaris, a.a.O., S.3.
比如,擅自使用本人交付保管的代理权凭证的场合,若简单类比善意取得或套用风险理论,则或可成立表见代理。〔63〕参见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载《法学研究》2017 年第2 期。但从法律行为论来看,因此种场合本人欠缺表示意识(通知意识),故可否成立表见代理,不无疑问。即便表示意识非意思表示成立所必要,也应认为:通知意识欠缺虽不妨碍代理权通知和表见代理的成立,但仍须类推适用重大误解法律行为可撤销的规定(《民法典》第147 条),允许本人通过撤销代理权通知来否定表见代理责任;有过失时,承担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当然,由于重大误解法律行为的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是九十日(《民法典》第152 条第1 款第1 项),故本人知道或应知道无权代理后九十日内保持沉默的,仍要承担表见代理责任。又比如纯粹通过伪造盗用代理权凭证营造代理权表象的场合,也无须比较占有脱离物可否善意取得的问题,因为法律行为论早已给出答案。此类场合下,本人对代理权通知的发生全然不知,也未实施过任何行为。这颇像“行为意思”欠缺之事例。而按通说,欠缺“行为意思”的“行为”无法成立意思表示。〔64〕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98 页;纪海龙:《走下神坛的“意思”:论意思表示与风险归责》,载《中外法学》2016 年第3 期;杨代雄:《意思表示中的意思与意义:重新认识意思表示概念》,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1 期(不过纪海龙、杨代雄自身似认为行为意思不应是意思表示的成立要件)。所以,纯粹通过伪造盗用代理权凭证营造代理权表象的场合,自始不成立代理权通知,也不发生表见代理责任。〔65〕此处仅指代理权外观全赖于凭证盗用伪造而发生的情形。如果除伪造盗用的凭证外尚有其他足以构成代理权通知的因素(例如,本人明知行为人盗用、伪造凭证实施无权代理而不加阻止,或本人已将行为人置于某种通常伴有代理权的地位等),则仍可能成立表见代理。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当年《民法总则》并未如其草案一样,将伪造等情形一概排除在表见代理的适用范围外。参见杨代雄:《结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存在的几个问题〉》,载《东方法学》2016 年第5 期;谢鸿飞:《代理部分立法的基本理念和重要制度》,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5 期;陈甦:《公章抗辩的类型与处理》,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3 期。有学者似乎认为,如果本人应当知道伪造、盗用凭证,或对于伪造、盗用凭证存在过失的,亦有成立表见代理之余地。〔66〕参见冉克平:《论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实施法律行为的私法效果》,载《清华法学》2018 年第6 期;周清林:《伪造印章下的表见代理构造》,载《法商研究》2020 年第2 期;娄爱华:《私刻公章与被代理人责任》,载《法学家》2020 年第3 期。但是,正如欠缺行为意思的场合不可能因表意人存在过失而致意思表示成立,本人有无过失本身尚不足以影响代理权通知及表见代理的成立。
用风险归责思想为本人担责寻求依据固然并无不当。一旦法律放弃过失归责,风险归责恐怕就成为最具“理论逻辑一惯性和解释力”的归责原则。〔67〕参见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载《法学研究》2017 年第2 期。尤其如果认为“单一化而可能绝对化的思考方式”就应当为“多元化和动态的综合权衡”所取代,〔68〕参见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载《法学研究》2017 年第2 期。那么以全因素之权衡比较为基础的风险归责思想确有其优势,同时借助类型化的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风险归责原理变得更为具体从而具有可适用性。
但仍须指出两点。第一,有关意思表示成立、效力的判断规则本来就是对表示风险进行分配的规则,〔69〕参见纪海龙:《走下神坛的“意思”:论意思表示与风险归责》,载《中外法学》2016 年第3 期。并且相对明确客观。借助这些规则,本可为表见代理的归责问题形成相对明确客观的判断框架,弃之不顾是否妥当?毕竟风险思想有着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尚不足以完成构建要件的重任。〔70〕参见张驰:《表见代理体系构造探究》,载《政治与法律》2018 年第12 期。此外,如果对于表见代理的归责问题依据抽象的归责原理给出的论断,恰与意思表示成立、效力的规则不相一致,则又如何是好?比如,有学者一方面主张行为意思是意思表示成立的必备要素;〔71〕参见冉克平:《意思表示瑕疵:学说与规范》,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44 页。另一方面认为,伪造盗用代理权凭证等虽原则上不成立表见代理,但本人对于盗用等确有过失的,亦可例外成立表见代理。〔72〕参见冉克平:《论伪造、盗窃代理权凭证实施法律行为的私法效果》,载《清华法学》2018 年第6 期。第二,现行法原则上是一个相对固定不动的体系,〔73〕Vgl. 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 1983, S.78.有关意思表示成立、效力的规则即如是。无视这些规则而改采动态评价,到底是有助实现个案公平,还是可能沦为个人价值判断之间的角力,不无疑问。〔74〕参见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载《法学研究》2017 年第2 期。比如,对于盗用代理权凭证是否成立表见代理,在持风险归责思想的学者之中,有的认为应成立表见代理;〔75〕参见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载《法学》2013 年第2 期。有的却认为一般情形下不能成立表见代理。〔76〕参见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载《法学研究》2017 年第2 期。
(二)不保证代理权通知的“意思真实性”
有学者近来提出,即便可以类推意思表示效力的规则,撤销存在瑕疵的代理权通知,也不影响表见代理的成立。其理由大致为:代理权通知被撤销后,代理权表象作为一种事实依然存在,而表见代理恰恰是基于此种事实引发的,与代理权通知的效力无关。〔77〕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制度中的积极信赖保护:兼谈我国民法典总则制定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外法学》2015 年第5 期。但笔者认为,所谓撤销通知后代理权表象作为事实依然存在,无非是指本人不能以代理权通知非出于真意来对抗代理相对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表见代理制度实质上是在保证代理权通知的“意思真实性”。但这恐怕已超出了表见代理制度的本旨。必须指出,表见代理制度仅仅意味着:当外部的代理权通知与内部关系不一致时,本人不能以内部关系对抗相对人。要言之,表见代理制度旨在保证代理权通知的“准确性”。至于代理权通知是否与本人的真意一致,表见代理制度则无法保证。毕竟现行民法已经明确:存在意思瑕疵的表意人可以不受表示的拘束,即使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该表示完全出于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当然,以上论断仅就民法上的表见代理制度而言,至于商事领域的表见代理制度是否还可保证代理权通知与本人意思的一致,完全可以,也应当另做讨论(详见本节之(四))。
(三)关于交付空白授权委托书
有疑问者,是此种情形:本人为缔结交易交付已盖章或签名的空白授权委托书、空白合同书或者干脆交付一枚公章,而后被交付者违背本人的指示滥用这些材料,声称其有某种代理权。对此,我国的司法实践早已肯认本人应承担合同责任。〔7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 条第1 项。但域外学者似有不同看法,即由于空白文书被他人不当补充,导致本人客观所作之通知或表示与其主观真意不一致,构成表示错误,所以本人不应承担履行责任。〔79〕最近的文献如:「白紙委任状と表見代理」植木哲編『髙森八四郎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 法律行為論の諸相と展開』(法律文化社,2013 年)149 頁。更有观点认为,虽然本人有意交付了有滥用可能的空白书证,但毕竟无法说本人积极认识到这些书证会被滥用,反而本人正由于相信行为人会遵照自己的指示才交付了空白书证。也即本人并非有意制造了与其意思不一致的表示,只是某种“有意识之过失”。此种主观状态与其说类似故意作出虚假表示的真意保留,不如说更接近于“非真意表示”。〔80〕Vgl. Müller, AcP 181, 534.《德国民法典》第118 条规定:“非出于真意,而在真意的欠缺不致被人误解的期待中做出的意思表示,无效。”
笔者认为,滥用空白书证可否成立表见代理,着眼点在于“填充权限”。通过空白书证实施代理交易的场合下,代理人必须完成两个行为:一是通过填充空白书证替本人完成代理权通知;二是以代理人身份缔结法律行为。问题就在于,代理人违反本人的指示填充书证所形成的“代理权通知”是否还可归属本人?既然本人交付内容不完整的书证,就往往会赋予被交付者一定的“填充权限”。本人通常会就如何填充作出指示,但仍留给被交付者得视情况而定的“自由意思”空间。故被交付者行使填充权限,完成最终归属于本人的表示,与“代理”颇为相似,而不当填充空白书证的行为本身也类似于越权代理。所以,正如越权代理也可能因构成表见代理而对本人有效,不能仅因填充悖于本人的指示,就当然认为填充所形成之表示无法归属本人。实际上,从交付空白书证这一举动,相对人往往可以推断出本人授权被交付者得在一定范围内填充这些空白书证。加之本人对此完全知晓,故而即便被交付者逾越实际的填充权限,本人也不得以该实际的权限对抗相对人,而表见代理成立的基础正在于此。另外,即便空白书证的被交付者私下补充完书证后再提交相对人,本人也依然受约束。尽管此处似不涉及对填充权限的信赖,但由于本人同样交付了空白书证或公章、行为人同样滥用了这些材料,没有理由因这些材料是公开滥用还是隐蔽滥用而区别对待。
此处唯需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本人交付空白书证或公章后,被交付者又擅自将这些材料交予他人,该他人冒称代理人并滥用这些材料的,本人不应承担表见代理责任。笔者认为,多数时候本人意图的只是空白材料的“直接被交付者”代为填充,所以当“其他人”手持空白证书营造出其有填充权限的表象时,虽相对人可以认为本人作出了有关填充权限的通知,但此通知与本人的意图不一致,构成通知错误。此时应对填充权限之通知类推适用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定。结果填充所形成之代理权通知无法归属于本人,表见代理之成立也就无任何可能。日本最高裁判所有云:“除了以任何人都可使用之意思而交付的场合另当别论外……不能因为委托书上的受托人的名字为空白,就当然认为,于该人将委托书又交付给第三人,第三人滥用该委托书的场合下,本人也要承受滥用者所缔结之契约的效果”。〔81〕最判昭和39 年5 月23 日民集18 巻4 号621 頁。
第二,“空白”并不意味着被交付者的填充权限无边无际。相反,多数时候相对人应当清楚持有者的权限必然在一个范围内。正所谓,持空白合同可以去收购通常数量的谷物,但不可能出让企业;〔82〕Vgl. Canaris, a.a.O., S.59.持空白合同可以求购现代油画,但不可能是毕加索的真迹。〔83〕Vgl. Müller, AcP 181, 527.而且,空白书证上记载的内容越少,“权利外观性”可能越小。在委托书、合同书除签名盖章余皆空白,或行为人只持公章一枚的场合,理性的相对人只会相信行为人仅被授权从事经济价值极一般的交易。否则,可能因“未核实确认”而无法主张表见代理。〔84〕以公章为例,虽然公章常被视作授权表征,但在传统认识中,相对人仅凭公章这一单独因素建构信任的,仍难逃“过于轻信”之指责。参见陈甦:《公章抗辩的类型与处理》,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3 期。
(四)适用于商事交易的特则
就商事交易中的表见代理而言,民法中意思表示成立、效力规则的适用应有所谦抑。例如,企业内负责管理代理权凭证的职员擅自使用这些凭证实施交易的,不应允许企业方以不知该职员擅自行动为由进行抗辩。又如,企业方将行为人置于通常伴有代理权的职衔地位的,通常就不应允许企业方主张自己不知此举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商事领域的表见代理不仅保证代理权通知与内部关系的一致性,还一定程度上保证代理权通知与本人意思的一致性。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本人须为所谓的“组织风险”买单,〔85〕参见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载《法学研究》2017 年第2 期。更因为商事交易对交易保护有更迫切的需求。此外,代理相对人为经营者的,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86〕参见王建文、李磊:《表见代理判断标准重构:民商区分模式及其制度构造》,载《法学评论》2011 年第 5 期。如是,则于商事代理交易的领域缓和本人可归责性之要求,亦属均衡。
需注意,由本人买单的“组织风险”不应被随意扩大,民法中意思表示成立、效力规则对于商事表见代理也非全部失灵。例如,“代理权通知”纯粹出自伪造、盗用代理权凭证的场合,即使关涉商事交易,也不能成立表见代理。〔87〕商法学者也持相似观点,如石一峰:《商事表见代表责任的类型与适用》,载《法律科学》2017 年第6 期。伪造、盗用者与本人内部有无职务关系,也在所不问。又如,企业方因受胁迫而作出代理权通知的,民法有关受胁迫法律行为可撤销之规定仍有类推适用的余地,企业方可以撤销推断的代理权通知,以阻却表见代理责任。
六、举证责任
关于“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 条规定,相对人“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但理论界对此不乏批评之声。〔88〕比如,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载《法学》2013 年第2 期。《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一书也提出:诸如行为人持有公章、介绍信,或者行为人确曾担当过本人的代理人等事实由相对人承担证明责任,而本人则须对相对人主观上是否为恶意或在缔约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失等进行举证。〔89〕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年版,第102、103 页。
司法解释将代理权表象与善意无过失的举证责任全分配给代理相对人,此种立场确有疑问。实际上,“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身并非待举证证明的“事实”,而是“评价”。即便将“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重构为“本人作出代理权通知”,亦是如此。因为如前所述,某种内容的代理权通知是否存在,属于规范解释,也即评价的问题。评价是否成立,取决于是否存在支持该评价的事实,即评价根据事实,以及是否存在妨碍该评价的事实,即评价妨碍事实或评价障碍事实。〔90〕参见司法研修所『民事訴訟における要件事実』第一巻(法曹会,1985 年)34 頁。从举证公平、标准明确等角度而言,评价妨碍事实之主张属于抗辩的范畴,应由主张评价不成立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91〕参见司法研修所『民事訴訟における要件事実』第一巻(法曹会,1985 年)34 頁以下;另见伊藤滋夫=難波孝一(編)『民事要件事実講座』(青林書院,2008 年)218 頁以下(難波孝一)。就“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或“本人作出代理权通知”而言,代理权凭证之出具等事实属评价根据事实,故应由主张该评价成立的一方,即相对人,承担证明责任。而“相对人恶意”属评价障碍事实,故应由否定“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一方,即本人,承担证明责任。至于“相对人过失”,因也属评价,故本人与相对人应分别就过失的评价根据事实与评价障碍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诸如相对人身份特殊、交易过程或性质特殊等(故而相对人应负更高的注意义务),均作为过失的评价根据事实,可由本人承担证明责任。
此外,诸如代理权凭证的伪造、盗用、被保管者擅自使用等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前所述,虽然规范解释上“本人作出了代理权通知”,但本人实际无行为意识或通知意识的,仍会阻却代理权通知之成立及效力,进而阻却表见代理责任的发生。以上无论哪种事实,均应由主张代理权通知不成立、无效及表见代理责任不发生的本人承担证明责任。〔92〕有观点认为,本人将案涉公章与备案公章加以鉴定比对已证明两者不一致的,本人就公章为假的举证责任即告完成;相对人在此情况下仍主张非备案公章为真,自应负举证责任。参见陈甦:《公章抗辩的类型与处理》,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3 期。然而,仅仅与备案公章不一致是否就能证明公章为假,进而本人是否完成了公章为假的举证责任,不无疑问。如果相对人不仅要证明“本人作出代理权通知”的根据事实,还需证明本人存在行为意思和表示意识,那么显然过于严苛。毕竟就常态而言,表示行为客观存在的场合,表意人内心一般都具有作出这一表示的意识和意思。
七、结语
“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这样的表述使表见代理制度的适用更具弹性的同时,也使该制度的适用容易游离于制度初衷。所谓“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是指本人对外作出了旨在证明代理权存在的通知,故相对人无须再向本人确认核实行为人是否有代理权。当然,本人是否作出代理权通知,如同意思表示的解释,取决于相对人的视角。同时,对于代理权通知的成立和效力,还可类推适用有关意思表示成立、效力的判断规则。比如,本人欠缺行为意思、通知意识,或代理权通知不成立,或本人可撤销代理权通知,结果均不发生表见代理责任。在此意义上,表见代理制度的初衷旨在保证外部的代理权通知与实际内部关系的一致,杜绝本人作出通知后又以内部关系对抗相对人。至于代理权通知与本人的真实意思是否一致,至少民法上的表见代理制度无法保证。即便相对人以为代理权通知是出于本人之真意进而相信代理权存在,本人仍得以意思瑕疵对抗相对人。这或许让人感觉相对人的信赖未得充分保护,但不过是表示责任问题上业已形成之评价标准的一体适用而已。〔93〕当然,理论界向来不缺乏对意思瑕疵相关规定的反思,比如,梅伟:《民法中意思表示错误的构造》,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 年第3 期;杨代雄:《法律行为制度中的积极信赖保护:兼谈我国民法典总则制定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外法学》2015 年第5 期;韩世远:《重大误解解释论纲》,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3 期;解亘:《意思表示真实的神话可以休矣》,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 年第2 期;冉克平:《意思表示瑕疵:学说与规范》,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214-2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