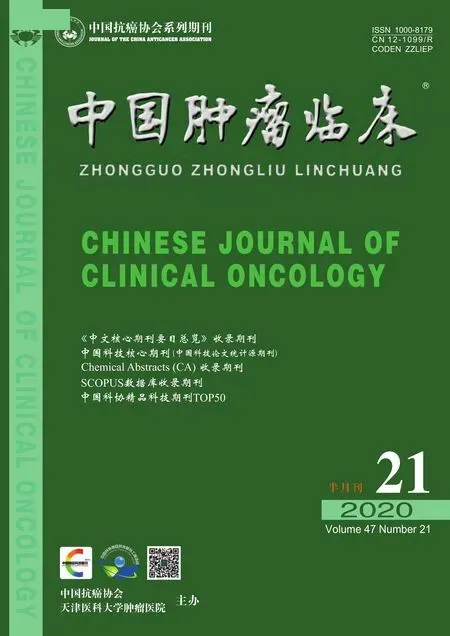胆囊癌系统性治疗研究进展*
刘凌玥 白雪莉 梁廷波
胆囊癌(gallbladder cancer,GBC)是胆道系统常见恶性肿瘤,发病率居消化道肿瘤第6位,中国年新发病例约5.3万,年死亡病例约4.1万[1-2]。手术治疗是唯一可能的GBC根治性治疗手段,但因GBC起病隐匿,恶性程度高,病程进展迅速,患者就诊时往往已处于晚期,丧失了手术治疗的机会,总体预后极差[3]。故而系统性治疗在GBC治疗中尤显重要。本文即主要针对局部晚期GBC、转移性GBC,围绕化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三类系统性治疗手段进行阐述。
1 化疗
对于晚期GBC,吉西他滨+顺铂(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的GC方案是一线化疗的标准方案。2010年报道的Ⅲ期ABC-02研究显示,晚期胆道癌(biliary tract cancer,BTC)患者采用GC方案化疗可取得比单用吉西他滨化疗更长的中位总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mOS;11.7个月vs.8.1个月,P<0.001)和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mPFS;8.0 个月vs.5.0个月,P<0.001)[4]。该研究GBC亚组中GC方案较吉西他滨单用有更高的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37.7%vs.21.4%),GC方案/吉西他滨单药治疗GBC患者的死亡风险比为0.61[4]。该方案在BT22研究中也显示了相似的疗效[5],由此GBC化疗步入以GC方案为基础的两药联合阶段。常用铂类化疗药物还有奥沙利铂,有研究将GC方案与吉西他滨+奥沙利铂(gemcitabine and oxaliplatin)的GEMOX方案进行对比,发现应用GC方案的晚期GBC患者有更长的中位无事件生存期(4.67个月vs.3.88个月,P<0.05)、更少的肝损伤和外周神经病变,而GEMOX方案血液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更适于心肾功能不全者,两者的缓解率、OS无显著差异[6]。有研究发现在经过3或4个周期的GC或GEMOX方案化疗后,侵及肝、结肠、淋巴结等的局部晚期GBC有46%可进行R0手术切除,术后患者的mOS显著提高(中位数未及vs.9.5个月,P<0.000 1)[7]。吉西他滨+替吉奥(gemcitabine and S-1)的GS方案在Ⅲ期研究中显示出不逊于GC方案的疗效(mOS:GC 13.4个月vs.GS 15.1个月),且用药过程中不需水化,与GC方案分别适用于有不同禁忌证的群体[8]。
除了吉西他滨+铂类两药联合方案,基于吉西他滨+铂类的三药联合化疗方案也在临床中应用。有Ⅱ期单臂研究显示,对BTC患者,吉西他滨+顺铂+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联合化疗可实现高于GC 方案所报道的mPFS(11.8个月)、mOS(19.2个月),其GBC亚组的mPFS、mOS 分别为4.1 个月、15.7 个月[9]。也有Ⅲ期研究发现,吉西他滨+顺铂+替吉奥的GCS 方案对BTC 患者较GC 方案有更长的mOS(13.5 个月vs.12.6 个月,P<0.05)和mPFS(7.4 个月vs. 5.5 个月,P<0.01)[10],尚未报道GBC亚组数据。此外,为克服耐药而设计的吉西他滨衍生物acelarin联合顺铂也显示出较好的治疗前景[11],正在进行Ⅲ期临床研究。
在经过一线化疗仍有疾病进展的患者中,仅少数可进行二线系统性治疗,原因包括肿瘤进展导致并发症、全身状况恶化等[12]。Ⅲ期ABC-06 研究显示,对BTC患者(GBC占21%),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奥沙利铂的mFOLFOX 方案结合积极症状控制可取得比仅用积极症状控制更高的生存率(6个月25.9%vs.11.4%,12个月50.6%vs.35.5%),肯定了以5-FU 为基础的二线化疗的意义[13]。但该研究并未设计5-FU 单药治疗组,有研究认为以5-FU为基础的双药化疗的mOS、mPFS 并不优于5-FU 单药[14]。此外,5-FU+伊立替康+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奥沙利铂等方案已由Ⅱ期研究证实了安全性与有效性[15-16],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大规模随机研究。
当前晚期GBC的化疗疗效并不理想,对于晚期BTC患者的研究中,GBC亚组的数据提示其与肝内、外胆管细胞癌对于同一组药物的化疗敏感性不同,仍需进行仅针对GBC患者的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以明确各化疗方案的意义。此外,基于分子检测的精准化疗及化疗与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联合或有前景。
2 免疫治疗
GBC 免疫治疗包括肿瘤疫苗、过继免疫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等。WT1 和MUC1 是疫苗研究中的常用靶标,有研究认为疫苗联合化疗可提高包含GBC在内的BTC患者的疗效[17-18],但仍缺乏大规模研究的验证。将疫苗靶点扩展到多个、研制“个性化”疫苗或有前景[12]。嵌合抗原受体T 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modified T-cell,CART)治疗也显示出成效,两项分别靶向EGFR 和HER2 的I 期CART 治疗研究显示了其安全性和治疗前景[19-20]。当前研究进展最迅速的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其作用基于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细胞毒性T 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 antigen 4,CTLA-4)等与其配体相互作用所介导的免疫抑制、肿瘤免疫逃逸[21-22]。有研究发现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升高、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 deficiency,dMMR)、高微卫星不稳定(high-level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H)可预测免疫治疗的有效性,且与不良预后相关[12,22]。阻断PD-1 或其配体PD-L1、PD-L2是近年的研究热点,一项收集了66份GBC 标本的研究显示肿瘤组织中PD-L1 阳性率达54%,阳性结果可能是GBC预后的预测因子[23]。
围绕PD-1 单抗派姆单抗的两项研究,KEYNOTE-028 中24 例应用派姆单抗的PD-L1 阳性晚期BTC(含GBC)患者中,有17%达到PR、17%达到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24]。KEYNOTE-158 纳入了104例PD-L1阴性或阳性的晚期BTC患者,应用派姆单抗后有5.8%达到PR(其中1 例患者PD-L1 阴性)、16%达到SD。两项研究的12 个月生存率分别为28%、33%,治疗效果未显示出与PD-L1 表达的关联性[24-25]。在包含45 例晚期BTC(含26%GBC)患者的Ⅱ期研究中,另一种PD-1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实现了22%的PR 和38%的SD,12 个月生存率达到52%[26]。也有研究显示在接受纳武单抗治疗的患者中,PD-L1阳性者的mOS、mPFS较PD-L1阴性者更长(mOS 11.6个月vs.5.2 个月,mPFS 2.8 个月vs.1.4 个月)[27]。有报道介绍国内1例PD-L1表达强阳性(≥50%)的复发转移GBC 患者,在接受纳武利尤单抗治疗联合放疗后,多发转移灶消失或明显缩小,获得超过6 个月的PFS[28]。此外,基于抗PD-1、抗PD-L1响应不佳的肿瘤中有增强的TGF-β 信号的实验结果,同时拮抗PD-L1和TGF-β的M7824在BTC患者中也显示出一定疗效,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达23%[29-30]。
一项Ⅰ期研究比较了PD-L1单抗度伐单抗单用或与CTLA-4 单抗tremelimumab 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单药、双药组分别有5%、11%BTC 患者达到PR,mOS分别为8.1个月、10.1个月,预示了联合免疫治疗的前景[31]。纳武单利尤抗联合CTLA-4 单抗伊匹木单抗等方案也正在研究中。此外,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方面,一项研究显示纳武利尤单抗+GC方案在BTC(含33%GBC)患者中实现了37%的PR,高于纳武利尤单抗单用,也高于ABC-02 研究所报道的GC 单用[27]。另有研究发现抗PD-1 治疗联合化疗疗效优于单纯抗PD-1 治疗、单纯化疗,在BTC 患者中三种方式的mOS 分别为14.9、4.1、6.0 个月[32]。纳武利尤单抗+伊立替康+5-FU、派姆单抗+卡培他滨+奥沙利铂、度伐单抗+tremelimumab+GC 等联合方案正在研究中,除疗效值得期待外,也需严密关注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当前对于GBC 免疫治疗的研究主要是Ⅰ期、Ⅱ期研究,尚待Ⅲ期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验证其临床治疗潜能。且现缺乏具备良好灵敏性、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预测特定患者的免疫治疗获益,PDL1等现有预测因子的检验方法尚待统一,新的标志物也有待开发。
3 靶向治疗
GBC 的靶向治疗基于对肿瘤发生发展过程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肿瘤基因异质性决定了靶向治疗的多样性。
HER2 基因扩增见于10%~19%的GBC,与细胞表面HER2的过表达相关,是肿瘤发生的关键驱动力且提示不良预后[33-34]。研究发现,在9例应用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或拉帕替尼治疗的GBC 患者(8 例有HER2 基因扩增或过表达)中,1 例达到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4 例PR、3 例SD[35]。有报道介绍1例国内的GBC复发转移患者,接受曲妥珠单抗和拉帕替尼联合治疗后多发转移灶部分缓解[36]。也有文献报道1 例HER2 基因扩增的复发转移GBC 患者接受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治疗后,实现了超过1年的持续缓解[37]。有研究显示在19 例有HER2 突变的晚期BTC(含42%GBC)患者中,来那替尼治疗实现了2 例PR、4 例SD,其中1 例获得PR 的GBC 患者在后继活检中显示HER2 突变丢失[38],预示靶向HER2 基因突变治疗的潜能。对于靶向EGFR 的单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一项联合帕尼单抗、吉西他滨、伊立替康的Ⅱ期研究显示,28例晚期BTC(含17%GBC)患者的mPFS、mOS 分别为9.7、12.9 个月,GBC 和胆管癌亚组间结果无差异[39]。有两项研究分别在GEMOX 化疗上联用厄罗替尼或西妥昔单抗,纳入研究的GBC患者较少,且均未显示出相较于单独化疗组更多的治疗获益[40-41]。有研究认为KRAS突变型患者应用EGFR靶向药物效果更佳,之前研究报告的疗效不理想或因未筛选KRAS 突变型患者[42]。此外一项汇总分析显示,同时靶向HER2 和EGFR 的varlitinib 联合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药物在BTC(含19%GBC)患者中实现了27%的PR 和42%的SD,显示出良好前景[43]。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与肿瘤生长、侵袭、转移密切相关。靶向VEGFR 的贝伐珠单抗与靶向EGFR 的TKI 厄洛替尼联用,在晚期BTC(含19%GBC)患者中显示12%PR、51%SD,mOS达9.9个月[44]。在BTC(含20%GBC)患者中,贝伐珠单抗联合GEMOX 化疗相较于单用GEMOX 化疗显示了更长的mPFS(6.48 个月vs. 3.72个月,P<0.05),但mOS 未显示提高[45]。仑伐替尼可抑制VEGFR、FGFR、PDGFRA 等,单药治疗在面向晚期BTC(含39%GBC)患者的单臂研究中显示了12%的ORR、85%的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mOS达7.4个月[46]。
PIK3CA 突变见于6%~12.5%的GBC[33],其导致的PI3K/AKT/mTOR 通路活化可促进GBC 的发生发展。一项研究将mTOR 抑制剂伊维莫司作为晚期GBC 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在12 周时显示25%的DCR,mPFS和mOS分别为2.1和5.6个月[47]。PI3K抑制剂copanlisib 联合吉西他滨或GC 化疗在Ⅰ期研究中证明了安全性,疗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48]。
关于RAS/RAF/MEK/ERK 通路,一项单臂研究将MEK抑制剂曲美替尼用于8例晚期GBC患者,有5例SD、3 例疾病进展[49]。另一项Ⅱ期研究显示,化疗后进展的BTC(含32%GBC)患者单用曲美替尼疗效不优于单药化疗[50]。一项研究联合应用了RAS/RAF/MEK/ERK通路中BRAF的抑制剂达拉非尼和MEK的抑制剂曲美替尼,在32 例晚期BTC 患者中实现了41%的ORR,mPFS 7.2 个月,mOS 11.3 个月[51]。MEK抑制剂司美替尼也在单用或联合GC 化疗中显示出治疗前景[52-53]。
NTRK 基因融合及下游MAPK 通路激活相关药物恩曲替尼、拉罗替尼等在实体瘤研究中显示出疗效[33],在BTC 中的应用尚在研究中。有研究显示BRCA1/2 突变胆管癌患者使用PARP 抑制剂治疗结局优于铂类化疗[54],但并未纳入GBC。仅1例病例报告显示BRCA1 突变的GBC 患者获益于奥拉帕尼[55]。对于有RNF43突变患者的Wnt抑制剂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当前研究已经显示,对未经生物学标志筛选的GBC 患者给予靶向治疗效果有限,靶向药物的精准治疗还需基于获取肿瘤组织及进行分子分析,这对血液中循环肿瘤DNA、细针活检标本的检测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患者治疗过程中靶点的突变也对靶向治疗提出了新的挑战[56]。
4 结语
GBC 的化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在过去十年中迅速发展,新药的开发与临床试验的开展为许多晚期患者带来希望,但当前GBC进展快、预后差的形势并未被改变,针对GBC 系统性治疗的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亟待开展。基于分子检测手段的丰富、具有精确作用位点的药物的推广,个体化、精准化治疗是GBC系统性治疗的未来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