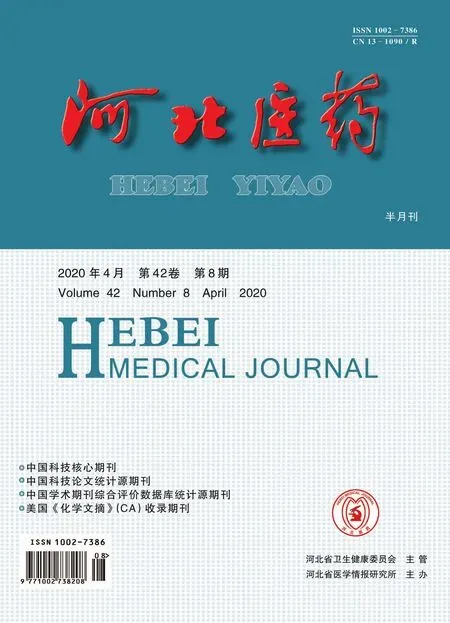分子靶向药物在肝细胞癌临床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聂佳欢 侯世科 程明
肝癌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四大常见原因,5年生存率为18%,其中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占原发性肝癌的90%,慢性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酒精中毒引起的肝硬化是HCC的主要危险因素,其次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1]。HCC的生物学行为较为恶性,但由于肝脏的代偿能力较强,在HCC早期并没有较为明显的症状,大多数在临床发现时已经处于进展期,且常合并严重的并发症,而根治性手术治疗,如肝脏移植、肿瘤切除及射频消融等只适合部分早期患者(大约30%),2/3的患者确诊时已无法进行手术切除,因此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十分重要[2]。对于晚期HCC患者,常规的全身化疗并不能改善患者的生存益处,临床三期试验研究显示:单用多柔比星、PIAF方案(顺铂、IFN-α、多柔比星和氟尿嘧啶)和FOLFOX4方案(氟尿嘧啶、甲酰四氢叶酸、奥沙利铂)对HCC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均显示为阴性,甚至可能增加部分患者的毒性[3]。近年来,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成为肿瘤治疗的研究热点,该类药物与传统化疗药物相比,具有靶向性、高特异性、不易耐药、疗效显著且副作用小等优点,而目前用于HCC治疗的分子靶向药物主要分为一线药物(如索拉非尼、仑伐替尼)与二线药物(如瑞格非尼、卡博替尼、雷莫芦单抗及免疫检查点靶向药物等)[4]。
1 肝细胞癌的一线分子靶向治疗药物
1.1 索拉非尼 索拉非尼(Sorafenib)是一种口服的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Ⅲ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索拉非尼可将晚期HCC患者的总体生存中位数从7.9个月提高到10.7个月,但索拉非尼组患者的腹泻、体重减轻、掌跖红肿综合征和低磷血症等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高[5]。有荟萃分析显示,索拉非尼对所有HCC亚组患者均有益处,其中对于肿瘤局限于肝脏(无肝外转移)、丙型肝炎病毒阳性、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较低的HCC患者,索拉非尼的治疗益处更大[6]。
目前,索拉非尼主要适用于肝功能保存良好(Child-Pugh A级)和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stage, BCLC)C期或B期在局部治疗后有所进展的晚期HCC患者,在评估索拉非尼临床安全性和耐受性的研究中显示,使用索拉非尼治疗的BCLC B期HCC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5~20个月[7],Child-Pugh A级患者的总生存期中值为13.6个月[8]。索拉非尼已被广泛用于治疗不可切除的肝癌(HCC),大多数研究也是在肝功能完好的Child-Pugh A级患者中进行的,Leal等[9]比较了Child-Pugh B HCC患者与Child-Pugh A HCC患者使用索拉非尼治疗的总体生存期及其耐受性,结果显示,Child-Pugh A患者的中位生存期(12个月)明显长于Child-Pugh B患者(6个月)(P=0.046),而该研究中所有患者的总体生存期为10个月,其中Child-Pugh B患者总体生存期为6.5个月,表明Child-Pugh B患者可以耐受治疗,并也可能受益于索拉非尼。
索拉非尼对晚期HCC患者的有效性,促进了索拉非尼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或作为辅助治疗的研究。在中期HCC患者试验中,索拉非尼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对比安慰剂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结果显示2组的总体反应率与疾病控制率分别为55.9%、41.3%与89.2%、76.1%,而2组的肿瘤进展时间(分别为169 d、166 d;HR=0.797,P=0.072)与总体生存期(HR=0.898,P=0.295)均无明显差异,表明索拉非尼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是安全的,但并不能显著改善患者预后[10]。另一项研究同样显示,通过纳入399名Child-Pugh A级的HCC患者,索拉非尼联合TACE组的无进展生存期(238.0 d)与安慰剂组(235.0 d)相比无明显差异(HR=0.99,P=0.94),表明索拉非尼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并不能改善无进展生存期[11]。 Bruix等[12]评估了手术切除(900例)或局部消融(214例)治疗后的HCC患者辅助治疗索拉非尼或安慰剂的疗效与安全性,结果显示索拉非尼组的无复发生存时间为33.3个月,而对照组为33.7个月(HR=0.940,P=0.26),表明索拉非尼在HCC手术切除或消融治疗后的辅助治疗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措施。
在不良反应中,掌跖红肿综合征是索拉非尼常见的不良反应,且有时可导致索拉非尼治疗的终止。为了允许索拉非尼继续使用,Naganuma等[13]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研究,评估了口服营养补充剂(包含β-羟基-β-甲基丁酸,L-精氨酸和L-谷氨酰胺)对索拉非尼导致掌跖红肿综合征的预防作用,结果显示预防组掌跖红肿综合征发生率(32%)显著低于对照组(60%)(P=0.047),表明预防性补充β-羟基-β-甲基丁酸,L-精氨酸和L-谷氨酰胺可有效预防晚期HCC患者索拉非尼治疗导致的掌跖红肿综合征。
1.2 仑伐替尼 仑伐替尼(Lenvatinib)属于多靶点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及其受体VEGFR1(FLT1)、VEGFR2(KDR)和VEGFR3(FLT4)的激酶活性,还可抑制其他促血管生成和肿瘤发生通路相关的RTK,包括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及其受体FGFR1、2、3和4,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PDGF)受体PDGFRα、KIT和RET,其中对FGFR4的抑制被认为是其抗肿瘤作用的关键因素[14]。
Ⅱ期临床研究显示,仑伐替尼治疗晚期HCC患者后,肿瘤进展时间为7.4个月,客观反应率为37%,疾病控制率为78%,总体生存期为18.7个月,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高血压(76%)、掌跖红肿综合征(65%)、食欲下降(61%)和蛋白尿(61%),表明仑伐替尼治疗晚期HCC患者具有临床疗效,且不良反应可接受[15]。而Ⅲ期临床试验通过纳入1 492名患者,对比了晚期HCC患者分别使用仑伐替尼或索拉非尼的疗效,结果显示,仑伐替尼组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3.6个月,并不低于索拉非尼组(12.3个月),同时仑伐替尼组在无进展生存期(7.4个月)、进展时间(8.9个月)和客观反应率(24.1%)方面均显著高于索拉非尼组(分别为3.7个月、3.7个月、9.2%)(P<0.05),表明仑伐替尼是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一种潜在的新治疗方案[16]。而亚组分析中国人群显示,仑伐替尼和索拉非尼组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15.0和10.2个月(HR=0.73,P=0.02620),与索拉非尼组相比,仑伐替尼治疗还显著延长了疾病进展时间(中位数分别为9.2、3.6个月,HR=0.45,P<0.00001)以及客观反应率明显高于索拉非尼组(43.8%比13.2%,P<0.00001)[16]。因此仑伐替尼被视为索拉非尼的替代一线治疗选择,随后,2018年8月16日FDA批准仑伐替尼可作为一线治疗用于不可切除HCC患者。
但是目前仑伐替尼的临床使用经验仍不足,有研究报道对于机械心脏瓣膜患者同时患有不可切除的HCC,该患者在经过介入放射治疗后,联合使用仑伐替尼与华法林,但经过4 d联合治疗后,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上升到4.13,但肝功能并没有影响,从而不得不停止治疗[17]。因此由于仑伐替尼和华法林联合治疗可导致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升高,对不能切除的HCC患者进行伦伐替尼和华法林钾联合治疗应慎重,并应密切监测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
2 肝细胞癌的二线分子靶向治疗药物
2.1 瑞格菲尼 瑞格非尼(Regorafenib)与索拉非尼的化学结构具有相似之处,但对VEGFR激酶具有更强的抑制,并且具有更广泛的活性,可阻断或抑制血管生成、肿瘤发生、转移和肿瘤免疫的蛋白激酶的活性,最早用于治疗难治性转移性结直肠癌和胃肠道间质瘤。2017年,Bruix等[18]首先通过评估瑞格非尼对索拉非尼治疗期间进展的HC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瑞格非尼可改善索拉非尼治疗期间进展的HCC患者的总生存期,其中位生存期为10.6个月,而安慰剂组为7.8个月(6.3~8.8)(Hr=0.63,P<0.0001),无进展生存期也显著优于安慰剂组(3.1月比1.5个月,Hr=0.46,P<0.0001),所有瑞格非尼组的所有患者(共374例,100%)、安慰剂组患者中179例患者(共193例,93%)出现了不同程度不良反应,其中瑞格非尼组中分别出现了高血压(15%)、掌跖红肿综合征(13%)、疲劳(9%)、腹泻(3%),表明证明瑞格非尼对接受索拉非尼治疗期间的HCC患者具有生存益处,而不良反应可接受。随后在2017年,瑞格非尼获得批准用于治疗索拉非尼失败后的晚期HCC。
Finn等[19]研究了使用索拉非尼后,再服用瑞格非尼治疗HCC的疗效,结果显示瑞格非尼组(索拉非尼治疗后再服用瑞格非尼)从索拉非尼治疗开始到死亡的中位时间事26.0个月,而安慰剂组(索拉非尼治疗后再服用安慰剂)治疗后的中位时间为19.2个月,而自索拉非尼开始治疗36个月后,瑞格非尼组的存活率为31%,安慰剂的存活率为20%,表明索拉非尼治疗后使用瑞格非尼治疗HCC可以延长生存期,且与索拉非尼治疗前疾病的进展速度及索拉非尼剂量无关。
有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瑞格非尼治疗HCC患者的血浆和肿瘤样本,以研究与瑞格非尼反应相关的遗传、microRNA (miRNA)和蛋白生物标志物,通过评估266种蛋白,其中有5种蛋白(血管生成素1、胱抑素B、转化生长因子β-1、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受体1、C-C趋化因子配体3)的降低与瑞格非尼治疗后总生存时间的延长显著相关(P<0.05),而血浆中的甲胎蛋白和c-MET水平与瑞格非尼治疗无关,评估的9种血浆miRNA(MIR30A,MIR122,MIR125B,MIR200A,MIR374B,MIR15B,MIR107,MIR320和MIR645)水平与瑞格非尼的总生存时间显著相关,肿瘤组织的测序分析显示27种致癌基因或肿瘤抑制基因中有49种突变,在10例HCC进展患者中发现3例存在CTNNB1突变,在7例治疗有反应的患者中发现1例VEGFA扩增,表明上述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和肿瘤的遗传特征可用于鉴定最可能对瑞格非尼治疗有效的HCC患者[20]。
2.2 卡博替尼 卡博替尼(Cabozantinib)可抑制多种酪氨酸激酶,包括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MET、VEGFR-1、-2和-3、AXL、FLT-3、KIT、MER、RET、ROS1、Tie-2、TrkB和Tyro3。在临床前研究中,卡波赞替尼显示了抗血管生成的作用,在体外还能抑制内皮细胞的形成、HCC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并抑制HCC细胞向小鼠肺和肝的转移[21], 最早作为进展性转移性髓样甲状腺癌和晚期肾细胞癌的二线治疗[22]。
Ⅱ期临床试验显示,Abou-Alfa等[23]通过纳入707名先前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的晚期HCC患者(且至少接受一次全身治疗后病情仍发生进展),结果显示卡博替尼组的总体生存期显著高于安慰剂组,卡博替尼的中位生存期为10.2个月,安慰剂组为8.0个月(Hr=0.76,P=0.005),卡博替尼组的中位无进展期为5.2个月,安慰剂组为1.9个月(Hr=0.44,P<0.001),卡博替尼组的客观反应率为4%,而安慰剂组的客观反应率低于1%(P=0.009),在不良反应方面,卡博替尼组的发生率为68%(掌跖红肿综合征17%、高血压16%、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升高12%、疲劳10%、腹泻10%),安慰剂组为36%(掌跖红肿综合征0%、高血压2%、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升高7%、疲劳4%、腹泻2%),表明卡波赞替尼可显著提高晚期HCC患者的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但不良反应发生率是安慰剂组的2倍。与其他Ⅱ期临床试验相比,本次试验纳入标准的主要区别在于纳入了接受过2次以上系统性治疗的患者,因此无法与瑞格非尼或雷莫芦单抗进行直接比较。
虽卡博替尼的临床疗效得到肯定,但其成本效益分析显示,卡博替尼的治疗成本较高,至少为每片50美元才能具有成本效益,因此卡博替尼并不是HCC二线治疗中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法[24]。另外,与卡博替尼相关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可能需要对使用这种药物治疗的晚期HCC患者进行更频繁的监测。
2.3 雷莫芦单抗 雷莫芦单抗(Ramucirumab)是一种重组IgG1单克隆抗体和VEGFR-2拮抗剂,也是惟一已进入HCC临床试验晚期的抗血管生成单克隆抗体。目前,雷莫芦单抗已被批准作为晚期胃或胃食管交界区腺癌(单一用药或与紫杉醇联合)、转移性结直肠癌中(联合FOLFIRI方案)、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联合多西紫杉醇治疗)的二线治疗。
Ⅰ期研究确定雷莫芦单抗最大耐受剂量(MTD)是从2 mg/kg/周到20 mg/kg/3周不等,随后Ⅱ期试验中,在42例晚期HCC患者中测试了雷莫芦单抗作为一线单药治疗,显示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4.0个月,客观反应率为9.5%,中位总生存期为12.0个月。雷莫芦单抗治疗HCC的第一阶段Ⅲ期试验称为REACH试验,试验中雷莫芦单抗作为二线治疗进行了试验,纳入565例Child-Pugh A级HCC和BCLC-B期或C期的晚期HCC患者,并且对一线索拉非尼不耐受或治疗失败,结果显示雷莫芦单抗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2.8个月)、肿瘤进展的中位时间(3.5个月)、客观反应率(7%)、疾病控制率(56%)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2.1个月、肿瘤进展的中位时间为2.6个月、客观反应率为<1%、疾病控制率为46%)(P<0.05)。然而在主要终点方面,雷莫芦单抗组中位总生存期(9.2个月)与安慰剂组(7.6个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87,P=0.14),即REACH试验是一项阴性试验,但亚组分析中,对于基线甲胎蛋白浓度≥400 ng/ml的患者有统计学上显著的生存益处(中位总生存期7.8个月比4.2个月;HR=0.674,P=0.006),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但基线甲胎蛋白<400 ng/ml的患者未观察到生存益处[25]。在总体人群中,甲胎蛋白血浓度升高被认为是预后不良的标志,因此上述研究表明在血清甲胎蛋白值高的患者亚群中,他们可能受益于雷莫芦单抗。
为了进一步证实甲胎蛋白≥400 ng/ml的晚期HCC患者使用雷莫芦单抗的益处,又进行了REACH-2试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安慰剂组,雷莫芦单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8.5个月比7.3个月,HR=0.710,P=0.0199)、无进展生存期(2.8个月比 1.6个月,HR=0.452,P<0.0001)均显著改善,而2组的客观反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比1%,P=0.1677),另外雷莫芦单抗组中有3名患者的死亡与研究治疗有关(1名患有急性肾损伤、1名患有肝肾综合征、1名患有肾功能衰竭),但仍然使甲胎蛋白≥400 ng/ml患者的总体死亡风险降低了29%。结果表明REACH-2是一次阳性试验,即雷莫芦单抗可提高先前进行了索拉非尼治疗且甲胎蛋白≥400 ng/ml的晚期HCC患者的总体生存期[26]。进一步的亚组分析显示对于男性、65岁以下的患者、白人和亚洲患者、非乙肝或丙型肝炎患者以及肝外转移的患者,雷莫芦单抗的疗效明显更好,此外,无微血管侵犯的患者、BCLC评分为B或C的患者、先前接受局部治疗的患者以及因疾病进展而停止使用索拉非尼的患者也证明了雷莫芦单抗的益处[26]。有研究进一步将REACH试验与REACH-2试验中甲胎蛋白高的患者数据进行合并处理分析,共542名患者(REACH试验中250名患者、REACH-2中292名患者)中,316名患者使用雷莫芦单抗治疗, 226使用安慰剂,结果与REACH-2试验中的结果类似,雷莫芦单抗可显著改善甲胎蛋白高的HCC患者的总体生存期(8.1个月比5个月,HR=0.694,P=0.0002)[27]。
2.4 免疫检查点靶向药物 HCC是一种典型的炎性相关癌症,HCC在肿瘤微环境中可诱发相关免疫应答和多种免疫因子,从而导致HCC的免疫逃避。而近年来,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已在包括HCC在内的多种肿瘤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免疫检查点是在多种免疫细胞中表达的表面蛋白,主要提供免疫抑制信号。而人体内的免疫检查点主要包括: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CTLA-4)、B/T淋巴细胞衰减因子(B and T lymphocyte attenuator,BTLA)、T细胞免疫球蛋白结构域和黏蛋白结构域3 (T cell immunoglobulin domain and mucin domain-3,TIM-3)等,因此阻断上述分子的单克隆抗体对多种人类癌症表现出抗肿瘤活性[28,29]。临床研究显示PD-1/PD-L1抑制剂、CTLA-4抑制剂可显著抑制多种肿瘤,并延长患者的生成时间,目前美国FDA已批准用于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结直肠癌、霍基金淋巴瘤、肾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而免疫检查点靶向药物在HCC中的临床研究中也同样显示一定的治疗疗效。
2.4.1 替西木单抗:替西木单抗(Tremelimumab)是一种完全人类IgG2单克隆抗体(mAb),可与CTLA-4结合,并抑制CTLA-4介导的T细胞激活下调。一项纳入20名晚期HCC的二期临床研究,每90天给予15 mg/kg的替西木单抗,直到肿瘤进展或严重毒性,结果显示部分缓解率为17.6%,疾病控制率为76.4%。进展时间为6.48个月(95% CI=3.95~9.14),且患者体内的乙肝病毒载量也显著降低,表明单一药物替西木单抗对HCC的治疗安全、有效[30]。因此,Duffy等[31]进一步研究了替西木单抗联合射频消融或化学消融对HCC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部分缓解率为26.3%(95% CI=9.1%~51.2%),85.7%的HCC患者中的乙肝病毒显著减少,而CD8+T细胞数量明显增多,且6个月和12个月无肿瘤进展生存率分别为57.1%和33.1%,肿瘤进展的中位时间为7.4个月(95%CI=4.7~19.4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12.3个月(95%CI:9.3~15.4个月),表明替西木单抗联合肿瘤消融治疗HCC是一种潜在新的有效治疗方法。该研究还显示,14例丙型肝炎患者中有12例的血清丙肝病毒载量下降了200倍以上,表明CTLA-4阻断剂还可以控制HCC丙肝患者的病毒载量。
2.4.2 纳武单抗:纳武单抗(Nivolumab)也是一种完全人类IgG4单克隆抗体,是一种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恢复被抑制的效应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在一项国际性、多中心、开放标签的临床Ⅰ/Ⅱ期研究中,EI-Khoueiry等[32]通过纳入262名HCC患者接受纳武单抗治疗,结果显示客观缓解率为20%(95%CI=15%~26%),其中3名患者为完全缓解、39名患者为部分缓解,其缓解持续时间为9.9个月,中位疾病进展时间为4.1个月,总生存期为15.6个月。不良反应方面,25%发生3/4级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6%患者发生与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类天疱疮、肾上腺机能不全、肝脏疾病)。结果表明,纳武单抗具有治疗HCC的潜在疗效,其安全性可控。基于上述研究,纳武单抗于2017年9月成为是第一个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作为二线药物治疗HCC的免疫检查点靶向抑制剂,但尚未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批准。而进一步研究显示,纳武单抗在亚洲人群中的客观缓解率为15%,其中乙型肝炎病毒阳性、丙型肝炎病毒阳性及未感染肝炎病毒患者的客观缓解率分别为13%、14%和21%,中位反应持续时间为9.7个月,中位总体生存期为14.9个月,表明亚洲患者的治疗反应、安全性与总体治疗人群相似[33]。Finkelmeier等[34]纳入了34例晚期HCC患者,其中19名患者为Child-Pugh A期(55.9%)、14名患者Child-Pugh B期(41.2%)、1名患者为Child-Pugh C期(2.9%),通过建立单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Child-Pugh分期(HR =7.742,95%CI=2.619~22.783,P<0.001)和ECOG评分(Hr=3.441,95%CI =1.049~11.268,P=0.041)是显著影响Nivolumab治疗晚期HCC患者生存危险因素,而纳武单抗治疗前进行索拉非尼治疗可降低HCC患者的生存风险((HR =0.387,95%CI=0.152~0.988,P=0.047)),但在多变量模型中只有Child-Pugh分期仍是HCC患者存活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结果表明Child-Pugh 分期与HCC的预后显著相关。
2.4.3 派姆单抗: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也是一种人源性PD-1单克隆抗体,一项2期临床试验通过纳入169名HCC患者,每3周静脉注射200 mg的派姆单抗,持续2年,或直到疾病进展、患者退出治疗,结果显示客观反应率为17%,1%的患者是完全缓解、16%的患者是部分缓解,总生存期为12.9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49个月,同时33%的患者病情进展、44%的患者病情稳定,其中73%的患者出现了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天冬氨酸转氨酶浓度升高(7%)、丙氨酸转氨酶浓度升高(4%)、疲劳(4%),表明派姆单抗对先前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的晚期HCC患者有效且可耐受[35]。另外,派姆单抗对于索拉非尼治疗失败的转移性HCC患者同样有效,可显著减小肿瘤的体积、降低甲胎蛋白水平[36]。基于上述研究,2018年11月,派姆单抗也被批准作为HCC的二线药物治疗。 而进一步的不良反应相关因素研究显示,治疗前血浆中高水平TGF-β(≥200 pg/ml)与派姆单抗治疗后不良的治疗效果显着相关,表明TGF-β可能是派姆单抗治疗HCC疗效反应的预测性生物标记物[37]。
2.4.4 度伐单抗:度伐单抗(Durvalumab)属于高亲和力的人源性IgG1单克隆抗体,可阻断PD-1、PD-L1和CD80结合。有研究通过进行腹腔注射Durvalumab(10 mg/kg每2周1次,持续12个月),评估了度伐单抗对HCC治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结果显示客观缓解率为10.3%,疾病控制率为33.3%,中位总生存期为13.2个月,其中80%的患者出现相关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疲劳(27.5%)、瘙痒(25.0%)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22.5%),未出现因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而死亡[38]。
在临床前研究中,抗PD-L1和抗CTLA -4抗体联合使用较单药治疗增强了抗HCC肿瘤的活性,说明这两条治疗途径可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Kelley等[39]进行了1/2期的临床联合治疗研究,通过纳入40例HCC不可切除的患者,联合使用度伐单抗与Tremelimumab进行治疗,结果显示客观反应率为20%,24名(60%)患者出现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最常见的(≥15%)与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疲劳(20%)、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18%)、瘙痒(18%)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15%)。另有24例患者中止了治疗,其中3例是由于与治疗有关的不良反应有关(肺炎、结肠炎/腹泻),16例是由于HCC发生进展,4例发生与治疗无关的死亡(心脏骤停、静脉曲张出血、HCC破裂),另有1例进入临终关怀护理,表明抗PD-L1和抗CTLA -4抗体联合治疗对临床患者有效。而关于度伐单抗对HCC治疗的3期临床试验仍正在进行中[40,41],目前还没有相关数据,因此其应用价值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HCC是最常见的肝癌,目前已是癌症相关病死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常发生于有基础肝病的患者,如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肝等。HCC的全球疾病负担正在增加,一级和二级预防措施以及更好地监测方案对减少与该病有关的发病率和病死率至关重要,然而仍很少有HCC患者(<10%)可治愈[42]。根治性肝癌治疗仅在早期阶段可用,包括局部消融手术、手术切除或肝移植,对于不适合局部治疗的患者以及转移性HCC患者,系统治疗是首选治疗。而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是HCC新的治疗方法,多年来索拉非尼一直是晚期HCC全身治疗的标准治疗方法,但目前不再是HCC的惟一可用于系统治疗的药物,一线(仑伐替尼)与二线(瑞格非尼、卡博替尼、雷莫芦单抗) 靶向药物也逐渐被不同国家批准用于HCC治疗,而一些其他新的药物也显示对HCC的治疗前景[43]。而二线药物中的免疫检查点靶向抑制剂目前也成为研究热点, CTLA-4和PD-1/PD-L1抑制剂均可为部分HCC患者提供有效的疾病控制,但PD-1/PD-L1抑制剂的耐受性更高,肝毒性更低,而PD-1/PD-L1和CTLA-4的HCC的联合治疗疗效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可能有助于减轻单一药物治疗诱发的相关不良反应。
总之,上述临床试验结果证实了分子靶向药物治疗在临床HCC患者中有效性与安全性,然而部分不良反应在这些治疗中也很常见,因此积极预防治疗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对于改善患者的耐受性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 河北医药的其它文章
- 膝骨关节炎患者自我管理措施及干预模式研究进展